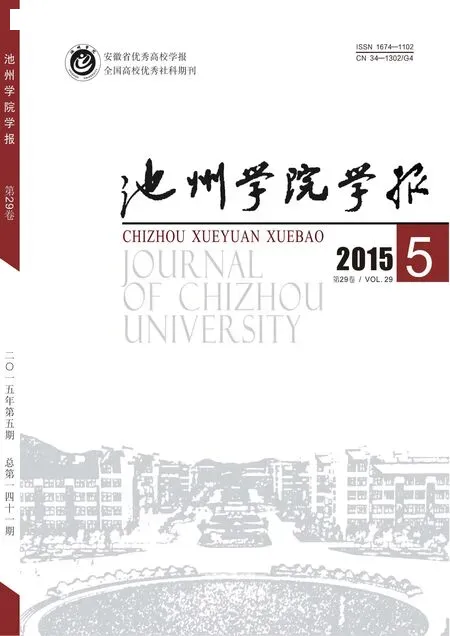情感教育:京派文学功利思想之辨
钱果长
(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池州247000)
情感教育:京派文学功利思想之辨
钱果长
(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池州247000)
[摘要]京派在长期的历史评价中都没有摆脱被视为“艺术派”的尴尬处境。其实,京派对文学与人生和文学与政治一直进行着双向度的思考,一方面因强调两者的联系,在一定层面上表现出对文学功利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因主张文学对人生和政治的超越使其文学功利意识呈现复杂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这种复杂性特点,反而遮蔽了对京派文学功利思想本真的认识。京派缘于文学的本质意义是情感表现,提出了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并以“美”和“爱”的理论在文学活动中加以实施,进行社会启蒙和人性救治,达到实现对人的重造和民族品德重造的宏愿。
[关键词]京派;文学功利思想;情感教育;“美”和“爱”
沈从文在上世纪30、40年代检视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时提醒人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民国十五年后,新文学运动同上海商业结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二是民国十八年后,新文学运动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1]。如此一来,新文学运动表面上虽然热闹,实际上却显示出堕落倾向,由此主张“重造文运”,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观——摆脱新文学的商业作用和政治效果,追求纯正的文学。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这种疏离政治和商业的文学态度和创作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已构成京派的“精神标记”,成为人们辨识他们及其文学的符码。人们对京派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京派荣枯兴衰的“历史命运”均与这一“精神标记”有所关联。30、40年代左翼文学家对京派的批评,特别是1948年由邵荃麟执笔的同人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对京派的判定,视京派是“反动的文艺思想”,其中就有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为艺术而艺术论”[2],直接导致了京派在此后30余年的销声匿迹。而80年代在反“左”的思想大潮中,京派又被人们视作“纯文学的典范”而重享尊荣。京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这种命运“反差”背后,实际上牵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京派文学功利的理解和认识。左翼斥京派“为艺术而艺术”,批判的正是京派文学的无政治功利性;而京派被抬到“纯文学的典范”的高度,虽是推崇京派,但选取的价值标准与左翼对京派的批判如出一辙,因为纯文学的概念只在反对文学过分功利化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效,其本身的立场和标准并不可靠。所以在不同历史时期,京派在人们视野中的?
非与是,最终都没有摆脱被人们视为“为艺术”派的窘境。
京派被视作现代审美主义的代表,他们追求艺术审美、坚守文学独立,在文学的社会意识与艺术意识之间,有着一定的偏于艺术一途的倾向。比如他们认为在文学创作上,当社会的良心与艺术的良心出现矛盾时,前者应顺从于后者[3]。但显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凭此判定京派是“艺术派”,只是躲在艺术的“象牙之塔”中专注于自我表现的一群“隐士”,在根本上又是不符合京派实际的。周作人早在1920年代就对“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两面开弓,其中认为“艺术派”视“个人为艺术的工匠”[4],重技工轻情思,对其将艺术与人生相隔离进行了批评。在30年代,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发刊词中表明“十九世纪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5]。而萧乾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也公开声明标榜不起“为人生而艺术”,但“也不想去为‘艺术至上’呐喊”[6]。批评家刘西渭对有人将自己归入“艺术派”则予以否认,对于一般人的嘲笑谩骂,他一笑置之。因为在他看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流弊是幻术,戏法,那不是艺术”[7]。京派文学家的上述言论表明他们从来就不是主张“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者。在追求艺术审美的征途中,京派文学家没有忘记时代对文学的影响。朱光潜曾经断言“各时代的文艺成就的大小”,“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的多寡深浅为准”[5]。所谓从文化思想背景吸收养料,就是使文学植根于时代与人生的沃土中。在此基础上,朱光潜形成了关于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8]的看法。作为对京派作家具有巨大凝合力的杨振声,直言不讳文学改造国民精神的担当责任与意识。面对1930年代的中国现状——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经济破产、民族堕落、内乱无办法、外患不抵抗,造成这样的局面,呼唤文学应自觉地“负一份责任”[9]。这样看来,在如何处理文学的社会意识与艺术意识的问题上,京派显然不是走向极端,他们稳健、理性,在坚持文学独立原则的基础上,求取两者的契合和联姻。就京派作家的创作来说,他们确实为读者构筑了“世外桃源”般的文学世界,但就在这样了世界里却往往内含着“国民性改造”和“民族品德重造”等之类的大题目。京派不是“艺术派”,不是形式主义者,归根结底也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境遇戚戚相关。现代中国的战火频仍、内忧外患,使置身于时代大潮中的京派作家不具备走向艺术“象牙之塔”的客观物质环境。所以在现代中国,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实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写作,而京派作品大部分都有着某种“温和的社会性”[10]。
首先,京派非常注重文学与人生的联系。朱光潜曾以“花与土壤”的关系作喻,“人生好比土壤,文艺是这上面开的花”[11],从而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世相的返照,“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12]沈从文则认为“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13]。李健吾认为“一出好戏是和人生打成一片的”[14],进而直接地宣布在人生与艺术之间,“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15]。因为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京派文学积极地介入社会人生,描摹人生世相,表现出一定的功用意识。就在左翼作家批评京派文学是“沙龙”里绅士淑女的玩意儿,把京派作家的生活想象成“大概是很‘雅’的”[16]同时,京派文学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不声不响地驳斥了对方,他们既写乡村社会又写都市人生,既写高门巨族又趋向“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17]的生活,其文学触角的伸展是十分广阔的。京派作家涉猎广阔的人生,很合乎他们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中“道”的理解。他们认为这里“道”不是“道德教训”,而是“人生世相的道理”,而世上没有其它东西能比文艺更能给人深广的人生观照和了解,由此主张与其说是“文以载道”,不如说是“因文证道”[18]。也许正是秉持着这种“道”的理解,当人生的文学在1920年代末趋向没落,特别是流入趣味主义的泥淖时,一向对文学的功利主义有所不屑的沈从文却倡导起了文学的功利性。他说文学的功利主义虽然已成为“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但是较之于那些在朦胡里唱着“迷人的情歌”的文学,“功利也仍然有些功利的好处”[19]。
其次,京派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般来讲,京派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是担忧文学在与政治的结合中,会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点缀,沦为政治的工具,文学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二是担忧政治对文学的压抑——经过作家主体的中介,对作家的写作方式造成压迫。京派作家遵循的是从“思”字出发的用笔方式,而政治压抑下的文学写作“却必需用‘信’字起步”[20],从而导致创作主体自由性的丧失。这两种“担忧”使京派对政治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不无厌恶之感。但京派作家又普遍意识到,在当时一个“出乎文学,入乎政治,出乎政治,入乎文学”的时代,文学不可能不在宽泛意义上与政治发生关系。李健吾就曾说过:“文学不是绝缘体,一切人类的现象都是它的对象。在这些现象之中,政治是一块吸力最大的磁石”[21]。因为强调文学与人生的联系,而政治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领域,由此对于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京派也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在京派作家中,沈从文是对文学政治化反对最多也最为有力的作家,但他也曾明确表明“个人对于诗与政治结合”“表示同意”[22]。作为理论家的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以两章的篇幅探讨“文艺与道德”的问题,而其中的“道德”实际上指涉的就是“政治”①。可以说,京派以较大的热情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一方面出于对文学本体性的珍视始终对政治作为外力侵入文学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当政治成为作家的信仰,凝定为作家的生命体验时,他们对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持的则是肯定和赞赏的态度。沈从文在《记胡也频》、《记丁玲》中就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探求,他曾反问“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而他给出的回答则是“文学原许可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它“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23]。这其间,我们发现京派再次对文学功利性的认可,甚至被他们一度强烈非议过的文学工具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同样是沈从文,在抗战相持时期预言中国抗战必胜“乐观是有理由的”,其原因就是那些所谓的日本“支那通”把近代中国在文学革命后,“将文学当作工具,从各方面运用,给国民的教育,保有多少潜力这一件事根本疏忽了”[24]。
以上所述,京派在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中,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对文学功利性的认同。但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京派注重文学与人生的联系,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关注,分别与“人生派”文学所主张的文学为人生、左翼文学所强调的文学为革命、为阶级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文学与人生之间,京派一方面注重文学与人生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反对文学为人生。在新文学发生后不久,面对文坛上“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的分野,周作人就曾指出“人生派”文学容易讲到功利里去,他们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从而变成坛上的说教,由此提倡“人生的艺术派”[25],既不必使文学隔离人生,也不必使文学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4]。朱光潜则认为“使文艺植根于人生沃土上”和“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是两码事,其中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5]。他援引布洛的“距离说”,将“距离”作为人生与文学间的中介。在他看来,传统的文以载道说、文学工具论以及极端的写实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些丧失了文学与人生之间的距离,基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人生的艺术化”[12]的主张。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还是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都体现出京派对“为人生”的文学所具有的功利性的警惕和反对,在他们主张的背后,实质上潜伏的正是京派在文学上的一种“不为”的精神和态度。而对于文学与政治,京派虽然不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但他们更多强调的是文学对政治的重塑。沈从文在《怀塔塔木林》《试谈艺术与文化》中都曾表露过“艺术重造政治”的理想,就在他赞成诗与政治结合的《谈现代诗》一文中更是明确地表示诗与政治的结合应该再进一步,诗人应该“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需是‘重造政治’而写诗”。此文写于1947年,因此在30、40年代,沈从文是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所宣称的“好的文学作品照例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26]的信仰。对于左翼作家所高唱入云的文学担负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使命,京派作家在根本上是否定的。朱光潜在抗战时期谈及30年代因“静穆说”与鲁迅发生的分歧时就说过文学并不具有这种伟大的功能,认为我们中国人从传统上总是过于夸大文学的力量,而统治者也因此总是习惯于干预和摧残文学,结果是两两相害,“既于政治改革无效,也妨碍了文学自身的发展”[27]。由此,我们发现京派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总是在进行着双向度的思考,一方面强调他们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主张文学对人生和政治的超越性。
正是基于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双向思考,京派的文学功利观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应该说众多的研究者已充分注意到了这点,比如所谓的“介入意识”和“超越意识”说[28],“由狭隘功用观转向广义功用观”、“由入世功用观转向出世功用观”、“由外在功用之证明转向内在功用之倡导”的“三种转移”说[29],如此等等,但问题在于他们大都把这些复杂性特点直接等同于京派的文学功利观本身,反而遮蔽了京派文学功利观的本原。那么,京派到底对文学持着怎样的功用意识呢?
在京派作家看来,文学的本质意义从其起源上讲就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现。周作人在1924年后文学观发生转向,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其要义即是文学是以自己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为艺术的。坚定地认为文学只有情感、没有目的。朱光潜认为“文艺是情感的自由发展的区域”[30]。杨振声的看法是“支配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最有力的是情感”,“而读品中刺激情感最有力的是文学”[9]。沈从文则认为自己作品最好的读者除了刘西渭外,“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先生”,因为他们从中得到或知道了一份“‘情感发炎’的过程记录”[31]。京派作家共同服膺于“情感表现说”的文学理论,缘于这种认识,他们对文学功用的看法就不可能像人生派文学或左翼文学所表现的那样急功近利,他们总是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和态度去看待文学活动,从而在文学功用观上表现出相同的趋向,这种趋向即是:文学所能发挥的只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教育”的作用。对此,京派各家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其中以周作人、朱光潜和沈从文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
最早作出这种认识的是周作人,他把这一作用说成是“无形的功利”。周作人在提出“自己的园地”文学观后,他说这种文学观本意上不是“为福利他人”,但因为使他人引起共鸣,他人能够得到“精神生活的充实而丰富”,由此具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4]。个中原因在于这种文学表现了著者“对于人生的情思”,可以“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25]。与周作人的“无形的功利”说相比,朱光潜的说法则更趋明朗。在《文艺心理学》中探讨文艺与道德时,他首先认为情感的势力比理智要强大,所以文艺对人的影响要更加深广。对于文艺的这种影响作用,他赞同托尔斯泰的说法,“在传染情感,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30]。并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文艺可以“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30]三个方面。而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中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拿文艺做宣传或谄媚的工具,认为“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并将这种功用视为文艺的“自家园地”[11]。对于文学的功用明确使用“情感教育”这一说法的是沈从文。在《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中他通过检视新文学运动史,发现自梁启超的文体革命到抗战时期的文学,新文学与政治联系紧密,成绩终究不好,但文学与政治相比,特别在青年人中,在情感上所发生的影响,进而在行为上有所表现实是较深,由此让人明白语体文中的文学作品对当时或明日的“国家发展”和“青年问题”如何不可分或可能起些什么作用[32]。毋庸置疑,沈从文在此流露出的正是他对文学功用的一般看法。
京派作家既然确立了文学只具有情感教育作用的文学功用意识,那么文学究竟该以怎样的情感去对读者施以教育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对此,他们一方面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五四”时期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其文学理想中共同竖起“美”与“爱”的大旗——相信美即是善,而爱则“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33]。面对现代中国的种种忧患图景,京派作家更为忧心的是识美知爱的人太少。“‘美’字笔画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人人认识,可是真懂得他意义的人却很少”[34]。许多人总是被政治、金钱和宗教所拘囿,他们所需的只是“生活”,对于“生命”则无什么特殊理解。对于现代中国社会闹得如此糟糕的局面,他们则认为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大半由于人心太坏”,因此要“洗涮人心”。而“洗涮人心”就得从“怡情养性”做起,因为要求“人心净化”,必先要求“人生美化”[35]。正是基于这样的隐忧,京派作家以超出习惯的“心”与“眼”,在文学功用意识上超越了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诉求,希望以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力量实现社会的启蒙和人性的救治。
关于“美”与“爱”的理论,沈从文对之阐述得尤为充分。首先是“美”与“爱”的产生。他说,宇宙同人心,复杂难辨,但目的显明,都是求生命永生。而永生的意义,要么表现为精子游离而成子嗣的生命延续,要么表现为凭借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这些看似相异,但实质相同,都是源于“爱”的结果。而“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36]。对于“美”的存在,他认为“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进而由此得出生命的最高意义,即是这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36]。但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只知道在“实在”上(指金钱、宗教和政治等)讨生活,从不追问生命该如何使用才觉更有意义,因此“在一切政治、哲学、美术的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维护”,从而导致了“神的解体”[36]。最后他指出倡导“美”与“爱”的目的所在。因为在“神之解体”的时代,“世上多斗方名士,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阉宦情绪,多无根传说”[36]。因此以倡导美与爱的新宗教来实现人的重造和国家民族品德的重造。除沈从文外,朱光潜、萧乾等人对美与爱都有所阐发,他们一致将艺术的美与善并举,认为美的欣赏本身就是一种潜意识的教育,从而越出形式主义的藩篱,最终形成具有京派特色的文学理想。
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家们面对思想闸门开启时出现的种种社会人生的问题,就曾在他们的创作中对此开出了“美”和“爱”的“药方”,企望用“美”和“爱”来弥补社会人生的缺陷,净化人生,已经体现出较为朴素的理性主义色彩。但与问题小说作家相比,京派作家对“美”和“爱”的艺术表达更具理论上的自觉。首先在文学创作上,他们自觉地以此作为他们的创作动机和目的,从沈从文到新时期复出的汪曾祺,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都一以贯之。沈从文在讲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曾经这样说道:“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直言其写作就是为了颂扬一切与自己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37]。正是抱着这样创作动机,所以他写《边城》,主要表现的只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主意只是借边地小城的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所牵连,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来“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8]。汪曾祺在新时期复出后所写的《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其创作目的也非常明确,即“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因为他相信美和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39]。除创作外,京派作家甚至将“美”与“爱”的倡导也贯穿在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等活动中。朱光潜在30、40年代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都是学术著作,但其中都贯穿了一个“很单纯的目的”,即研究如何教人“免俗”,如何用“人生艺术化”的美学力量,达到“洗涮人心之坏”的效果[35]。而在文学批评中,京派批评家李长之对美学或美育也是十分热切,他认为美学上的原理既关乎“整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又关乎“各个国民的起居饮食”[40]。由此在文学批评中颇为自觉地践行以审美教育来实现对国民和文化的重新铸造。
注释:
①朱光潜在1981年读《文艺心理学》的校样时写到:“讨论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七、八两章,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制时代写的,其中的‘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政治’。”参见“作者补注”,《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M]//沈从文全集:第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6.
[2]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M]//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香港:香港生活书店,1948:1-19.
[3]萧乾.创作四试·战斗篇·前言[M]//鲍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338.
[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张明高,范桥.周作人散文:第2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28.
[5]朱光潜.理想的文艺刊物[M]//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432;431-432;432.
[6]萧乾.美与善[M]//萧乾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49.
[7]李健吾.使命·跋[M]//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57-158.
[8]朱光潜.《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M]//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242.
[9]杨振声.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M]//杨振声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0]吴福辉.“平津文坛”漫议[J].现代中文学刊,2012(1):4-9.
[11]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M]//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482.
[12]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M]//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91.
[13]沈从文.论穆时英[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33.
[14]李健吾.文明戏[M]//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52.
[15]李健吾.使命·跋[M]//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58.
[16]胡风.蜈蚣船[M]//胡风评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39.
[17]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M]//陈学勇.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143.
[18]朱光潜.文学与人生[M]//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62.
[19]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0.
[20]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M]//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19.
[21]李健吾.关于鲁迅[M]//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32.
[22]沈从文.谈现代诗[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78.
[23]沈从文.记丁玲[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17-118.
[24]沈从文.给一个广东朋友[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14.
[25]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M]//张明高,范桥.周作人散文:第2 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36;136.
[26]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给一个军人[M]//沈从文全集:第17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8.
[27]金绍先.“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忆朱光潜与鲁迅的一次分歧[M]//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81.
[28]张大伟.“超越意识”与“介入意识”——“京派”的文学作用论[J].甘肃社会科学,2001(1):71-73.
[29]刘峰杰.论京派批评观[J].文学评论,1994(4):5-15.
[30]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312;324;325.
[31]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44.
[32]沈从文.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77-178.
[33]沈从文.从现实学习[M]//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5.
[34]沈从文.昆明冬景[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70.
[35]朱光潜.开场话·谈美[M]//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6;6.
[36]沈从文.美与爱[M]//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59;360;361;361.
[37]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25.
[3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
[39]汪曾祺.关于受戒[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228.
[40]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316.
[责任编辑:余义兵]
作者简介:钱果长(1978-),男,安徽青阳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14D103);池州学院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2013RWZ005)。
收稿日期:2015-07-15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28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