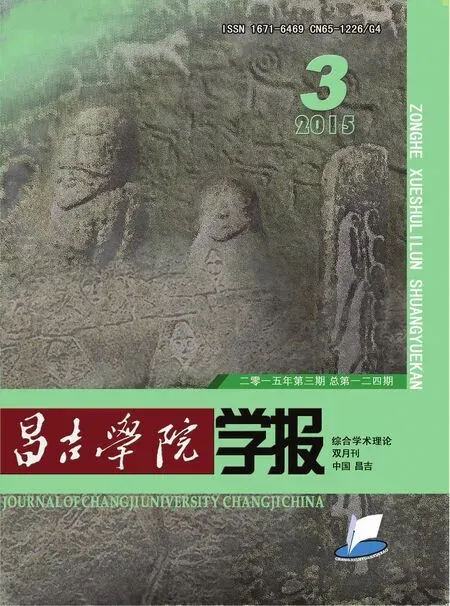《古炉》:鲜活形象画面下的“文革”剖析
摘要:小说《古炉》对1965年冬天至1967年春天那个历史时期古炉村触目惊心的贫困的展示引人思考:当年中国应当进行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是搞一场狠抓阶级斗争的“革命”还是搞一场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古炉村里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引人思考: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小说中的善人和狗尿苔这两个人物的意义是与“文革”的仇与斗的思想潮流相对立,是对“文革”的否定。《古炉》可以说是政治小说,但它不同于中国以前的革命政治小说的写法,它是把那一段政治历史当作乡村社会生活来写的,流水般的鲜活精到的乡村生活细节和民俗风情构成的生活画卷,使小说魅力无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5)03-0043-07
收稿日期:2015-05-03
作者简介:刘求长(1942-),湖南省新化县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文革”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新时期文学开始期的重要文学现象是“伤痕文学”,这其中就有一部分小说是以“文革”为题材,展现“文革”的惨烈悲剧的,如郑义的短篇小说《枫》等等。但近40年中出现的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其数量总体上却是不多的,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更是凤毛麟角。作家贾平凹曾经是那场“文革”的经历者(虽然因为当年年少他实际上只是一个旁观者),出于作家的良心,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创作了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古炉》,展示那场“革命”的无谓的悲剧性,让“文革”结束近40年后的读者、评论家与作家一起在观看了古炉村演出的那场“文革”悲剧之后,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文革”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进行一番理性剖析。
古炉村触目惊心的贫困引人思考:当年中国理应进行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读者跟随作家经历了从1965年的冬天到1967年的春天古炉村的一段社会生活。古炉村虽然具有“山也青水也秀”的自然环境,在外人看来很是“特色”,但一进入古炉村人们的日常生活,读者看到的却是农民(当时叫“人民公社社员”)极度的贫困。民以食为天,可是这里的老百姓却正是缺吃的。读者看到,这里家家户户日常的饭食就是包谷糁糊汤加酸菜。且看小说中的十二岁孩子狗尿苔家的晚饭:“吃晚饭时狗尿苔端了碗在院子里吃,碗里就有了星星,他是朝着星星喝一口,星星还在,再喝一口。婆说:猪呀,响声恁大?狗尿苔说:饭稀得只能吸着喝能不出声?婆说:夹些酸菜搅一搅饭就稠了。” [1]即使他过生日,他奶奶(人们称她“婆”或“蚕婆”)也只有能力为他做一顿稠稀饭吃。有一天婆做了一碗米儿面,狗尿苔“狼吞虎咽吃起来,他觉得那一碗饭是那样香,一口饭还没咽下喉另一口就吃进去,喉咙里像是伸着一只手,要把饭和碗都要拉进去。” [2]一次邻居家稀罕地吃一次蒸米饭,邻居家主人吃得好香,而在一旁看着的狗尿苔则馋得受不了,当一只苍蝇叼了一粒米饭粒飞来,叫他和另一个小孩牛铃拍下来,狗尿苔就拾起这粒米饭想吃了它。 [3]这个十二岁的男孩个子老不长,晚上睡觉老尿坑,家里吃食太差了!另一个身体不好更不长个的小孩瞎女端了个裂了缝的木碗在院子里吃红薯面糊糊,当有人问他吃什么时,“没想孩子说:不要吃我饭,不要吃我饭!” [4]孩子竟然怕旁人抢吃了他的饭食!这情景读者看了岂能不心酸心痛!“人都说1965年是阴历蛇年,龙蛇当值风调雨顺,虽然麦秋两季收成还好,但人人还是得吃稻皮子炒面才能勉强着吃饭不断顿。稻皮子炒面是冬天里拿软柿子拌搅了炒熟的稻皮子和谷糠,晒干磨出的面。炒面吃着还甜甜的能下肚,却常常是下了肚就拉不出屎”。 [5]多么艰难的日子!社员开石死了,村里人感叹:“唉,可怜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就死了。” [6]与物质贫穷并存的是文化贫穷。村里除了水皮、守灯、霸槽等少数人上过学,人们普遍地没有文化。狗尿苔十二岁了还没上学。男人女人大多言语粗野,脏话随口而出,尤其是一些妇女,骂起街来连篇的脏话恶语,粗野不堪。与贫困相连的便是病,“古炉村里许多人都得着怪病。” [7]有年轻人头发全秃了的,有心口疼的,有哮喘的,有腰痛得直不起来的,有夹不住尿了的,有害鼓症的,有半身不遂的,“过不了两三个月,村里就要病或死一个人。” [8]
到1965年,新中国成立已经16年了。我们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岂能容忍如此贫困!邓小平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9]如何改变贫穷?遵循当年中国通行的思维惯性,只能是用“革命”的方式。那么该进行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21世纪今天的中国的绝大多数读者肯定会做出明确回答:要进行一场能够解放生产力,能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大力发展经济的“革命”,也就是“文革”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样的“革命”。可是在当年的古炉村,和全中国各地一样,搞的却是狠抓阶级斗争的“革命”,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坚决维护平均主义大锅饭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容许有任何一点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狠抓阶级斗争就需要树立敌人,古炉村本来是没有阶级敌人(即“四类分子”)的。社教时公社张书记来检查工作,说:古炉村这么多人,怎么能没有阶级敌人呢?于是,守灯家就成了漏划地主,守灯他爹一气得鼓症死了,地主成分的帽子便留给了儿子守灯。狗尿苔的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抓丁,1949年去了台湾,他奶奶(婆)就成了伪军属。守灯和婆便被树立为村里阶级斗争的对象。 [10]后来派出所王所长来古炉村侦破投毒致死人命的案子,说:“四类分子定得太少了,就是定得太少才出了这案子!”于是又定了第三个阶级斗争的对象,即那个原本为出家人后来被政府命令还俗的善人。 [11]十二岁的狗尿苔则因为出身不好成了一个“准”阶级斗争的对象,作为贫下中农的霸槽可以把他骂作“你个国民党军官的残渣余孽”,水皮可以骂他为“小四类分子”。显摆自己有文化的水皮让狗尿苔用“爱戴”一词造句,狗尿苔造句说“我也爱戴毛主席!”水皮说:“你是啥出身,你没资格爱戴毛主席,重造!” [12]小说的描写告诉今天的读者,当年为了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为了要进行阶级斗争,本来没有斗争对象也硬要树立斗争对象。读者所看到的古炉村里的几个阶级敌人是这样一些人:守灯,他家本来不够地主成分。“文革”中造反派的马部长曾轻蔑地说古炉村穷,说守灯家这个地主“在别的地方屁也不是!” [13]土改时本来守灯家也没有划为地主,是在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后于社教运动中被补划为地主的。守灯本人是个年轻人,本人从来没有剥削过谁压迫过谁。社员立柱对守灯说:“总是说阶级敌人搞破坏哩,我没见过你有什么破坏么。” [14]守灯有文化,“文革”开始后“扫四旧”时从他家里搬出来好多书烧了。他有家传的手艺,他一心想钻研烧瓷的技术,只是人们不允许他搞。民兵连长天布说守灯:“他成分是高,你没看见古炉村还有比他手巧的?” [15]婆,她只是一个普通农妇,她丈夫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抓走的,只是后来去了台湾。婆心地善良,经验丰富,心灵手巧。她能用纸或树叶剪出活灵活现的动物与植物形象,织布染布做衣裳,为新生儿接生,为死者穿戴入殓,为人治疗小伤小病等等她都内行,村里人都总是找她帮忙。为了保护自己和捡来的孙子狗尿苔,她谨小慎微地规规矩矩地活着。善人(本名郭伯轩)幼时家贫失学,以放牛佣工维持生计,三十二岁入庙拜师,社教中被强迫还俗入住古炉村当社员。他除了参加劳动就是为生病的人说病,教人以善行替自己治病。这样的三个正正当当地活着的人居然被树为阶级敌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至于十二岁的孩子狗尿苔(大名叫“平安”),与去了台湾的爷爷和作为“四类分子”的奶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当年是很讲血统的),他是婆拾来的一个孩子,他居然也与阶级斗争的对象沾上了边。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对象的作法是很荒谬的。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16]他又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17]小说的描写告诉我们,新中国建国与土地改革之前,无论是守灯、婆还是善人,都不处在“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地位,不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经过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中国已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已经是“消灭阶级”的国家。因此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8]用主观构想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观念代替客观现实存在的矛盾并大力实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革命,古炉村及全中国的贫穷状况岂能改变?
恩格斯说过:“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 [19]。显然,“唯有借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唯有进行一场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革命,才能改变古炉村及全中国的贫穷状况,而人为地、不断地狠抓阶级斗争,只能使古炉村和全中国越斗越贫穷。
发生在古炉村的“文化大革命”引人思考: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
小说的描写告诉读者,古炉村穷困不堪,人们当然也怀有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的愿望,但古炉村的老百姓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起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古炉村人人靠为集体干活挣工分,村里根本不存在一个占有土地的剥削阶级和另一个没有土地的被剥削阶级,也并没有什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古炉村的“当权派”就是党的支部书记朱大柜,他虽然有点自私,但一直是跟上级领导保持步调一致,在村里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古炉村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从外面、从上面传来的,“革命”的发展进程也是与县里、镇里乃至与省里和北京城里是大致一致的。造反的学生来串连,来煽风点火,来组织造反队伍,村里不安分想干大事的青年农民夜霸槽出来充造反头头。他们干的第一桩“革命”大事也是“破四旧”:砸碎村头石狮子的嘴,砸了山门上的雕刻,把窑神庙墙上的“妖魔鬼怪”图画全铲了,砸了窑神庙屋脊上的龙头凤尾,然后是砸社员家屋脊上的砖雕,收缴并销毁家家户户收藏的“四旧”物品,如守灯家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一千零一夜》等书籍,《古炉村形胜图》画作以及三个青花瓷瓶;如六升家的雕花相框,狗尿苔家的捶布石等。下一步是正式成立造反组织“古炉村联指”,成立“榔头队”,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书朱大柜,押解公社书记张德章到古炉村游斗。再往后是村里又成立了一支与“联指”榔头队相对立的“联总”红大刀队。加入榔头队的都是夜姓的人,加入红大刀队的都是朱姓的人。虽然两派都称造反派,但观点不同,对对方不服气,都要争夺村里的主导权。再下来便是两派之间惨烈的武斗,武斗的结果是死伤五十余人,损坏房屋、家具、麦草、树木无数,死伤牛、猪、狗、鸡、猫等无数。最后是在1967年的春天,霸槽、天布等六名村内及镇上来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分子被枪毙。
观看完古炉村这场“文化大革命”戏剧演出的读者都会产生两点观感:一是荒诞感,二是悲哀感。荒诞感的产生是因为:原本诚心诚意紧跟中央和上级领导狠抓阶级斗争的当地领导人,“文革”中却成了被斗争的人,被批,被斗,被关押,被游乡示众,身心都饱受折磨。那些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人物,固然在那场“革命”进程中威武神气了一番,其中的榔头队一派在物质上也抢了占了享受了,但结局却再惨不过了。“文化大革命”原本是有辉煌的目标的,但结局却如此黯然失色。悲哀感的产生,是因为原本贫困的古炉村,“文革”前人们毕竟还享有贫穷中的那种相对平静,可是这场“革命”带给他们的却是除了贫困,再加上心惊胆颤的动乱和人身财产的重大伤亡与损失。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革命的根本目的与根本意义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类社会为什么发生革命?马克思在他的被理论界称之为“唯物史观的总结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得十分清楚:“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20]因为旧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就是为了打碎这个桎梏,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以顺利发展。可以说,衡量一场“革命”是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归根到底就是看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1]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理论上也不敢回避这一点。《决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22]但读者在观看了古炉村的“文革”戏剧演出之后却不能不想:这场“文革”是为了打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吗?这场“文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吗?读者看到的却只是与此正相反的东西。古炉村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以及原有的一套生产经营方式与分配方式当然都没有任何改变。“文革”所要强化与固化的正是这些致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东西。为大集体干活的农民出工不出力。“男人们都磨洋工的”,说“肚子饿得人能干动?”妇女们则找时间干私活,“从怀里拿出鞋底来纳”。 [23]社员给队里交自家的尿水前,使劲往尿窖里掺水,公开说是“都哄生产队哩” [24]。打麦场上麦子打下来了,人们便变着法子偷拿麦子。 [25]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出工干活,却要求照样记工分,于是不闹革命的人不愿意了,也不想出工干活了。支书被揪斗了,生产队长也不想干了,没人组织生产了。村里两派对立,夜姓人家和朱姓人家本来是亲戚关系,现在闹得水火不容。强势的一派占了村里的公共财产,停止了村里唯一的一项来钱的非农业经营活动烧制瓷器。“革命”激发出了人们人性深处的全部劣根性: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享受着抢来的物资,残忍地对待敌手,以破坏为痛快。武斗一爆发,搅扰得全村鸡犬不宁,损失惨重。无辜的人们愤怒地骂:“古炉村成啥了么,监狱么!” [26]“完了,完了,古炉村啥都没有了!” [27]武斗受害人骂:“文化大革命我日你妈,你这样害扰人?!” [28]读者不能不发出叹息:原本就是贫困不堪的古炉村,来上这样一场“革命”,更是雪上加霜了。长不高的狗尿苔只能喝更稀的糊糊,更加长不高了。那个身体不健壮又老怕人抢吃他破碗里的红薯糊糊的小孩瞎女,身体只怕会更糟了。
马克思曾经说:“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 [29]可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却硬是按照命令制造出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观点来看,它根本不能算是一场革命。古炉村的老百姓彻底否定了它。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样彻底否定了它:“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30]
善人和狗尿苔:《古炉》中两个有特别意义的人物
小说《古炉》中有两个人物是有特别意义的,他们是善人和狗尿苔。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中,这两个人物的意义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与为人处世的方式及人生境遇正好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斗争哲学的对立面,正是对“文革”的否定。
善人是从寺庙里还俗出来的。在古炉村的成年人中,他的思想与行为是最为脱离社会现实的。他的意识始终沉浸在与眼下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他所理解和掌握的那一套中国传统文化里,他几乎是只要一张口,就是与人说善恶论因果。他的主要活动除了参加劳动就是被人请去说病。他的说病方式、方法就是从善恶心理和行为上给人找病因,并教人以善心善行去医治自己的病。他在说病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宣扬他信奉的那一套行善去恶的人生哲学。比如他劝导人说:“你要练习看见人先笑后说话,找人的好处,心里才能痛快,病才能好。”“怨人是苦海,越怨心里越难过,以致不是生病就是招祸”。 [31]“社会就凭一个孝道作基本哩,不孝父母敬神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32]“贤人争‘不是’,愚人才争理呀!” [33]“今后你们谁能矮到底,谁能成道,学道就是学低,才能成己成人。” [34]善人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与人无争。旁人说他:“你真个好人,啥事都往好处想。” [35]他为人说病,为人接骨,武斗中勇敢地用法子隔开武斗双方,尽力保护被打的人。他相信恶有恶报。对那个在古炉村第一个掀起造反浪潮的人物黄生生,善人就预言他会不得好死的。果然那人被对立派的人砸死时身首异处,鸟把他的头啄得稀巴烂。善人说:“他若能活着,还算有天理么?” [36]占据窑神庙的造反派要炸倒山上的百年白皮古松当柴烧,善人与他们抗争无果,悲愤中一病不起,最后在夜里燃烧自己的住所山神庙自焚。善人自焚时,在自己家里睡觉的狗尿苔听到了唱戏的乐声,婆说“那就是天乐吧。”“善人要走了,天上给他响乐哩。” [37]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中的善有善报。
小说对善人这个人物的塑造会让读者想到小说《白鹿原》中的圣人朱先生。朱先生终生宣讲和履行仁义,博得各方敬仰。善人虽然没有朱先生那么高的地位和声望,更没有朱先生那样高的学问,但他始终言行一致地扬善行善,与当年社会鼓吹的以仇恨和恶斗为根本思想的潮流形成对比。作者在文字的表面上并没有把这个人物与小说剖析“文革”的主题联系起来,但在意义的深处二者是相互联结的。
《古炉》没有把哪一个人物当主要人物来写。狗尿苔当然也不是主要人物,但他却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视点,或说是古炉村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眼见者。笔者以为,这个小小人物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对“文革”斗争哲学的批判。一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如果是生活在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哪怕是生活在一个只是基本消灭了贫穷的初级阶段的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应该是不会那么用心去操心吃喝穿住那些事的,更不会去想“我出身不好,而且一辈子都会出身不好” [38]那样沉重的政治问题的。可是读者面前的狗尿苔,却是一个一年到头半饥半饱,已经开始了认真为吃饭问题操心的人物。“狗尿苔心里想,米汤糊糊还不是一顿饭?能省一点,家里的存粮就多一点,如果一天能吃一顿饭而肚子不饥,那就好了”。 [39]比饥饿更加沉重的则是他切切实实感受到的政治歧视和事事处处的不平等。村里开大会,别人都是找地方坐着,他的奶奶(婆)和守灯是“四类分子”,却得在会场前头老老实实地站着。青黄不接时上面拨来救济粮,他家是“四类分子”,没有得救济粮的资格。队里死了一头牛,分牛肉时从贫下中农分起,“四类分子”排最后,狗尿苔眼巴巴看着别人分到了肉走了,轮到他却没肉了,只给了他一点牛百叶,守灯则什么都没分上。队里打麦扬场没有风,要行一个乞风仪式,按例要找一个三代单传的孩子当“圣童”,人们想来想去只有狗尿苔合适,但马上有人反对:“他当不了圣童么,出身不好能当圣童?” [40]村里死了人安葬后要吃一顿饭,安排入席也讲阶级成分:“是贫下中农的先入席啊!” [41]只有一件事是婆想到而狗尿苔现在还未想到的,便是家里成分不好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姑娘嫁不出去,婆“心里不舒坦,虽然狗尿苔现在还小,将来却必须要面临婚姻的事” [42]。在狗尿苔心里,觉得出身贫下中农就是福。婆把家里的一头小猪给了人,小猪跟狗尿苔很亲,被送了人它不愿意。狗尿苔安慰小猪说:“人家是贫农,光景也好,知道吗,长在他们家有福!” [43]小说一再说到狗尿苔不长个,不长个固然因为吃不饱,但狗尿苔自己道出了此中更重要的原因:“他总是兴冲冲地做着什么事,冷不丁就有人说他的出身,这就像一棵庄稼苗苗正伸胳膊伸腿地往上长哩,突然落下个冰雹就砸趴了。他想,被冰雹砸过的庄稼发瓷不长,他的个头也是被人打击着没长高的。” [44]连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都居然承受着如此沉重的现实政治压力与心理压力,这岂不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主张南辕北辙?“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 [45]《共产党宣言》确定的奋斗目标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6]
狗尿苔从现实社会中很难得到多少幸福,好在他拥有一种“特异功能”,即他能听懂一切动植物的语言,能与世上一切动植物交谈并快乐相处。这种特殊的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又与现实社会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对照。
鲜活的生活画卷
从以上的评说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古炉》是一部政治题材的小说。不错,我们至少可以说,《古炉》的基本主题是政治的,即它是展示“文革”的一个历史片断并在读者的不知不觉中引导他们对“文革”进行剖析的。但读者翻开小说读下去,又没有太多的读政治小说的那种感觉。这可能是因为小说所写的“文革”不是北京城里或省城里发生的“文革”,其中的人物并没有专事政治而又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是普通农村里的普通农民。而笔者则认为,这是因为《古炉》的写法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乃至新时期之初文学中的政治小说不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革命政治小说大致是把写小说当作政治任务来对待的,即写小说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写小说也就往往成了写政治。即以陕西著名老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为例,尽管这部小说立足于陕西农村生活,读这部小说也可以从中读到20世纪50年代初陕西农村的许多生活情景,但读者读《创业史》首先就感觉到是在读政治,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尤其是作家的每一句抒情式的议论,都是承担着表现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样的政治主题的。而小说《古炉》则与那一类革命政治小说不同。《古炉》就是在写生活,就是在实实在在地再现当年当地的农村社会生活的鲜活情景。作者是在写从1965年冬天至1967年春天那种“火药味”十足的生活,但《古炉》中的那一段生活,仍然是十足的乡土味道的,仍然是保留着许许多多中国农村传统风习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作家贾平凹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熟悉到“彻底”的那种程度和将那种生活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那种高超的语言艺术技能。可以说作家熟透了他所要描写的那些农村人物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的心理意识,他们的外在形态,他们的全部语言习惯,作家再以他十分擅长的、精到的细节描写笔法将这一切鲜话地展现于文字。贾平凹笔下的细节描写真是炉火纯青了。为了节省篇幅,笔者不拟在此举例。读《古炉》,你会感到是长流不断的生活细节从眼前流过,一种我们既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生活扑面而来,令人有一种强烈的因观赏人生图画和领略乡土风情而产生的惬意感。
深深植根于民族生活与地域生活土壤中的民俗风情,即使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里,也不能从农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铲除。村里死了人,大家自动来帮着料理后事。蚕婆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人给死者入殓,该给死者穿上几层几套衣服都有讲究。男人们去拱墓,墓坑选在哪里,要论一论风水。村里人都拿上一刀纸钱来烧给死者。丧事办完后,请大家吃一顿饭。这办丧事的过程中显现出乡里乡亲的人情味。开石得了“稀屎痨”,就请婆去给他招魂。婆拉长声音呼唤:回来哟!回来哟!开石就应声道:回来了!回来了!村里人染家织布为了避免染坏,婆教她们先要敬梅葛二仙。小男孩瞎女体质弱,他妈听从建议要给瞎女“撞干大”,结果“撞”上的这个“干大”竟然是十二岁的孩子狗尿苔,婆就让狗尿苔认了这个“干大”。这实在饶有趣味。
《古炉》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表白:“小说有小说的基本写作规律。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 [47]在笔者看来,作者的这个创作意图是在作品中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有“水中着盐”的道理。 [48]小说《古炉》展现的乡土生活图画便是“水”,对“文革”性质的解剖便是水中的“盐”,这“盐”其味虽浓其形却隐匿。而这正是《古炉》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