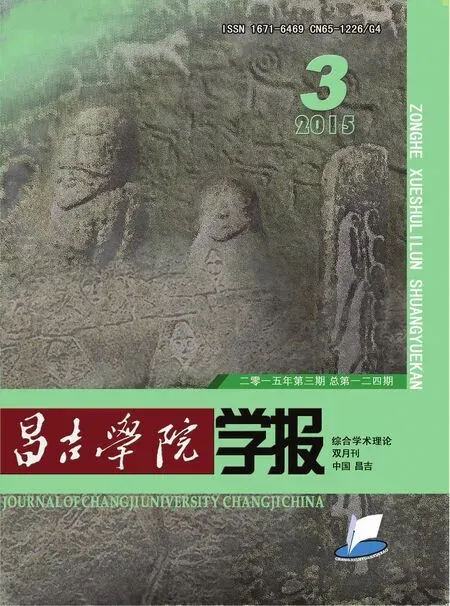高原女神的节制歌吟:神佛文化影响下的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书写
摘要:藏传佛教文化与原始苯教文化对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创作影响深远。本文首先对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书写进行概述,然后重点分析宗教文化与女作家创作的关系。一是在神佛文化的影响下,新时期藏族女作家书写雪域高原时呈现出神幻色彩;二是在宗教“禁欲”理念主导下,女作家节制的叙事风格。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5)03-0007-07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倪金艳(1989—),女,河北省沧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多民族文学。
翻阅《藏族文学简史》、《藏族文学史略》等相关的书籍,会不由地发现自公元18世纪出现作家文学的长篇小说以来,男性作家统治着藏族文坛,女性作家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藏族女性作家才以高原女神的姿态走进读者的世界。从文学格局而言,相对于以汉族为主的文学现状,藏族文学处于边缘地位;而相对于男性为中心的创作事实,藏族女性作家处于“边缘的边缘”。新时期藏族女作家顶住双重边缘的压力,以清新、节制、典雅、含蓄、恬美的书写风格为藏族文学留下靓丽的一笔。雪域高原的女作家们深受藏传佛教与原始苯教的神佛文化影响,从书写理念到内容再到叙事风格,呈现与汉族女性作家不同的文学气质,进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史。
一、概述: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书写
“新时期”一词,最早见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文件,而“新时期”以小说的形式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是以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为肇始,至今这一文学阶段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此处的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书写是指1977年至今,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五大藏区的女性作家(以青藏高原女作家为主),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文学现象。
1981年益西卓玛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长篇小说《清晨》,开了藏族女性文学书写的先河,改变了女作家文学创作失语的状态。自此,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构成了文坛的又一道风景线。90年代至新世纪,藏族女性作家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作品数量、质量均有质的提升。从创作队伍看:有央珍、白玛娜珍、梅卓、完玛央金、唯色、格央、永吉卓玛、尼玛潘多、白玛曲珍等;从创作题材看:有诗歌、散文、小说;从文本内容看:包括书写雪域高原的自然景观、风土民情,抒发对高原的热爱之情,像完玛央金的《完玛央金诗选》、白玛曲珍的《彩色高原》;追溯、反思民族历史如梅卓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记录社会变化如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格央的《雪域的女儿》;关注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状况,像梅卓的《麝香之爱》、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女作家的笔触及到自然、社会、民族、部落、物质、精神、现实、神话等各个方面,她们蕴满了对高原故土的热爱,在新时期书写新的文学篇章,构筑起瑰丽多姿的藏族女性文学世界。
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无论题材有何不同,无论切入角度和写作技巧如何千差万别,但藏传佛教与原始苯教文化基因融于文本之中(由于苯教以万物有灵的神灵观为认知方式,因而佛教与苯教文化统称为神佛文化)。神佛文化影响女作家作品创作,在内容上表现为对宗教民俗景观的书写,呈现出神幻的色彩;叙事风格上因受佛教文化节制欲望教义的影响,文本偏向节制内敛含蓄。
在藏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佛教文化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至于“藏族文化的形成,以藏传佛教诸派的形成为标志” [1]。但“自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原与印度两路传入藏区,传入后的佛教与藏区土著苯教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由此成为藏族人民的精神依归。” [2]可以说佛教吸收了苯教文化后,藏域宗教世界具有神佛的双性特征。宗教文化是藏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与藏民族水乳交融,它指引并约束着藏民的日常生活,塑造着民族气质与心理特征。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宗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是社会群体的心理共鸣,也是人对周围世界的一种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藏族女性把宗教信仰看得至高无上,充满了对信仰的敬畏和崇拜,她们清楚地认识到,除了父母的呵护外,佛的加持是幸福的根源。所以当女作家成为书写主体时,宗教文化是不可逾越的写作内容。
二、神幻:藏地民俗景观的展示
用马丽华的话来说,这是一片“弥漫神佛文化色彩的高原土地”。佛教在吸收原始宗教苯教万物有灵论、灵魂不灭论的观点后,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即便是山神、湖神、灶神、帐篷神等神灵也均打上了神佛宗教文化的色彩,因而用自己认知的方式,书写神佛文化景观是女性作家创作的题中之义。笔者主要从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诗意的生命观和独特的神佛意象书写三个方面论述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的神佛色彩。
首先:书写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的观念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人们无法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形成既热爱又恐惧的复杂心理,继而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观念。藏人臆想并架构了一个庞大繁复的神灵系统,“他们需要它的存在并相信了它的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就生活在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
在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创作中,万物有灵的观念隐含在文本内部。女作家中梅卓用唯美又略带哀伤的语调书写藏地的神秘,在《羊年的水命:转湖·洪水》“藏历铁羊年的春天是从转湖开始的。青海湖是安多藏区的第一大神湖,在高原,每一座神山和每一座圣湖都是有生肖的。青海湖在十二生肖中属羊,因此每过十二年,在圣湖的本命年里,人们都会来到湖边,沿顺时针方向转一圈或数圈,许愿、还愿,奉献上敬意,或者誓言。” [3]青海湖作为藏地圣湖拥有无限魔力,俗世中的人可以通过向圣湖祈福来增加福运;并且藏人相信借助圣湖的力量,心诚便可以得神湖保佑实现夙愿。仅看众人的行为,便能感知对神湖的笃信:“等到羊年的羊月,羊月的羊日,这个特别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一大早起来,沐浴焚香,让周身散发着柏枝和藏香的芬芳,胸中揣着虔诚的希望,大声祈祷,幸福的泪水盈满眼睛……” [4],“人们携带家口拥向湖边,手上缠着108颗念珠,嘴里颂着六字真言,燃起柏香,奉上美酒,把深藏着喇嘛的祝福‘德’抛进湖水,然后就全身俯地,朝着湖水叩拜,把心中的愿望默默地讲给湖神,愿湖神做主,为我们带来幸福的明天。” [5]除了圣湖崇拜外,对神山的崇敬也是同样的虔诚,长篇小说《月亮营地》中在万物有灵的神灵观念支配下,对达日神山的叙说弥漫着神幻的浪漫色彩。“达日神山的山神是一位身披银铠银甲、手指银剑银旗的战神,也是青藏高原著名的十二护法神之一。达日山神前矗立着信徒们奉献的经幡旗帜和石刻经文。每当轮回到十二生肖的马年,远远近近的牧人就会骑上马儿带着家人纷纷赶来,参加十二年才有的祭山盛会。因为这一年是达日神山的本命生辰年” [6],而且坚持“愿望总能实现,只要有了这一年的衷心祈福和祭祀。”神山神湖由于人的朝拜祭祀而增加了神性光彩。在雪域高原神山圣湖祭祀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倘若缺乏这样的神灵系统,藏人或许会感到不自由,内心也难以宁静。
其次:表现诗意的生命观。藏传佛教文化中轮回转世的生命观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皆为不同,轮回是对生命的理解,也是佛教文化关注的根本问题。佛教义理深植藏区每一个人的心中,因而笃信业报轮回,相信前世今生来世。在藏族人心中,人有生死并讲究因果报应,此生作恶,来世必定会在“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中轮回,承受无边苦海;而此生行善,来世才能轮回于“三善趣”(天、阿修罗、人)。转世能否幸福,依仗今生的所作所为,因此修行变得至关重要;也恰恰因为轮回转世的信念,相信苦难终将过去,成就了藏族人乐观阔达的性格特征;同时,生命世世代代不停息,物质终为过眼云烟,此生无需贪恋,所以藏人倾其所有捐赠寺院,换取来世幸福。
转世、因果报应的生命观念,避免了物质至上主义,也因来世的存在,心有畏惧与笃定。面对艰辛的现世,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为今生的痛苦寻找到精神依托,用一句话总括藏族人的生命观:来世的而非现世的,乐观的而非忧患的。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宗教窃取了人的自然的一切内涵,转赋予一个彼岸的神的幻影。” [7]藏族人在知天命乐观外向的表情下,隐忍着来自佛教的空、虚、无,来自生命本源外发出的无奈,前定的认命。
轮回转世的生命观渗透在藏族女作家生命肌理中,成为集体无意识的组成部分,以命定的认知观念呈现在文本中。新时期女作家汉语创作均对生命表达了自己的认知,我们仅以梅卓《麝香之爱》为例进行解析。《出家人》中曲桑和洛洛的爱情故事浸润了藏传佛教生死轮回的宿命感,一世无缘的情人寄希望于来世相逢“再见,洛洛,我们来世再相见吧”,谆谆嘱咐“别忘了我,你别忘了我……”不仅是今生的不相忘更多的是轮回转世中莫要相忘,再续情缘。而宿命几近残忍的对待前世中青梅竹马的年轻人,今生偶遇的曲桑和洛洛(此时姓名互换,男性曲桑变为女性洛洛,女性洛洛转世为男性曲桑),宿命的牵引使二者相爱,而分离后相约的信函佛珠却再次遗失在茫茫红尘,永无相聚的可能。曲桑与洛洛每次相遇,都无法脱离命中的注定无缘,无论几世轮回,也无论以何种身份相遇,都逃脱不掉宿命的安排。但年轻人相信轮回寄希望于下几世,此世无果,至少还有来世的可能,只要“别忘了我”!另一个中篇小说《麝香》同样以轮回作为叙事背景,除了吉美与甘多的爱情,还穿插叙述了夏玛与灵人的故事,夏玛未能与相爱之人结合,被迫成了尼姑,将自己关闭在禅房中八年,八年中灵人一直陪伴,灵人因爱而不能后自尽,是夏玛的化身。我们都知道佛教禁止杀戮尤其是自残,灵人在第一次自尽后,要承受七次同样的自尽才可以和凡人一样转生为人。这种爱的决绝让人震撼。
今生的爱没有善果,寄希望于转世,来世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尚是未知,但怀有对未来的希冀总是幸福的,藏人便在对来世的期盼中,默默地忍受了今生的苦闷无奈,这诗性的生命观值得品咂。
最后:展示藏地独特的神佛意象。
雪域大地,神佛笼罩着一切。置身高原腹地,眼前浮现出一顶顶帐篷、大量的乘马、成群的牛羊、身着藏服的藏族牧民、穿着袈裟的喇嘛、五颜六色的经幡、不停摇转的转经筒、逐渐增高的玛尼堆……耳边萦绕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哞”的响声、呼呼的转经声、咩咩的羊群叫声、牦牛的哞哞声、打酥油的嗒嗒声……这是高原所独有的意象。此处,我们只简单阐述玛尼石、经幡、朝圣三种高原意象。
玛尼石、玛尼堆、玛尼墙、刻玛尼石是草原上一道风景。刻有六字真言、慧眼、神像造像、各种吉祥图案的玛尼石,它们是藏族民间艺术家的杰作。玛尼石的作用一是祈福和禳解,二是供人们转经礼拜,随时匡正自己的思想行为。在远离城镇和寺院的乡野村寨,玛尼堆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所在,于是在地广人稀的牧区,无处不在的玛尼堆担负起了经堂和道场的部分功能。梅卓的《走马安多·嘉那玛尼石经城》是一篇论述玛尼石的游记文章。“结古镇东约5公里处的新寨村,有一座巨大的玛尼石城,相传结古寺第一世嘉那活佛晚年定居于该地的东南山坡,并开始兴建玛尼堆,人称‘嘉那玛尼’……目前,玛尼石经城东西长283米,南北宽74米,高2.5米,有20多亿块玛尼石……” [8]并于1986年被列为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信徒们以玛尼石堆当作转经对象环绕着,为自己、家人和他人祈福消灾。
经幡又称风马旗、祈愿幡、祭马,将经咒图像木版印于布、麻纱、丝绸和土纸上,形成一条条、一片片、一串串的各色风幡,这些方形、角形、条形的小旗被有秩序地固定在门首、绳索、族幢、树枝上,在大地与苍穹之间飘荡摇曳,构成了一种连地接天的境界。在灵气聚集之处如神山圣湖,挂置印有敬畏神灵和祈求护佑等愿望的经幡,经风吹送有利于愿望向上苍神灵传达和实现。女作家文本中关于经幡的描述更是频繁,“山上的经幡在风中呼呼作响,向山神献上我们的敬意,风中的经幡代表我们的心声,报答千万年来保佑我们的福地” [9]“楼顶四角均有高出一二尺的小塔,插有各色的经幡”,“彩色的经幡迎风飞扬”,“天下的经幡是母亲的祝福”……经幡是僧俗信众精神世界与神灵交通的一种媒介物,岁岁年年、日日夜夜在风中飘扬,犹如无数僧众日以继夜地诵颂着真经,蔚为壮观。
叩着等身长头的虔诚朝拜者是藏地又一景观。拉萨圣城是距离佛祖最近的地方,其它地区的藏族人将抵达圣城视为无尚福泽,尤其是以叩等身长头的方式到达拉萨。叩等身长头的每一动作都是有其含意的。双手合十,象征领受了佛的旨意和教诲;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和移至面前、胸前,表示心、口、意与佛和合为一。叩拜时,心发所愿,口诉祈求,这样才能实现心愿。藏族人的朝圣某种程度上与穆斯林朝圣意义相仿,只为心中坚定的信仰,千里迢迢奔赴圣城,完成精神之旅。它不同于基督教信众在教堂忏悔,忏悔是为了赎罪,而藏族人的朝圣则是为自己更多的是他人祈请福泽。作家们为虔诚的朝圣者震撼着感动着书写着,在《朝圣者之旅》中“我们又与朝圣者相遇。三位男子,正一步一叩首,用身体丈量着到圣城拉萨的道路” [10],“下山时,遇到两位朝圣的女子,20多岁的样子,她们叩着头,从江达来,已走了1个月零4天 [11],“刚到林芝县,又遇到一家朝佛的,爸爸妈妈带着5个小孩子,走了两年,遇到神山圣迹就转一圈,不知何时才能到达拉萨呢?” [12]虔诚的朝圣者是藏区的人文景观,他们叩着等身长头,不畏沿途的艰辛与漫长,甚至认为死在朝圣的路上是最大的幸福,虔诚之心撼动俗世中的你我。
充满神佛色彩的雪域大地,无处不在的神灵,保佑着有情众生。源于苯教信仰的神灵观念为藏地高原增加了神秘色彩;深入肌体的藏传佛教文化,轮回转世的生命观为艰涩人生增添了希冀与诗意;在神佛文化熏染下,藏地的人文景观玛尼石、经幡、朝佛的人群与神山圣湖共同构筑起了雪域高原的迷幻之象。
三、叙事:节制的欲望书写
虽然受现代文明侵染较少,藏族人原始思维色彩保留较为完整,诗性的想象随处可见,这与草原人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息息相关。无处不在的神灵保护着雪域众生,同时也束缚了人们的思维。较之于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更为深广久远。佛教中“节制欲念”的教义指导着信众不要执迷物质享受,修来世幸福才是根本。此外,佛教中因明学注重培养人的思辨能力,利于增强逻辑思维。在佛教文化规约下,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叙事中含蓄节制的特点明显。
与汉族女性作家尤其是90年代红极一时的陈然、林白、海男等以自己的性体验作为叙事对象,赤裸裸表露欲望的写作方式不同,梅卓、格央、央珍等藏族女性作家,即便是感情充沛也会尽量避免直白浅露的宣泄。总体上看,90年代的汉族女作家写作时注重物质化、私人化、人物形象审丑化;而藏族女作家则有意识的节制欲望的泛滥,呈现非个人化的特点,人物形象多为中性。同时,藏族女性作家的写作特点也不同于藏族男性作家如龙人青、扎西达娃等无所顾忌的风格。
欲望由情欲和物欲两方面组成,节制的欲望书写既包括自觉规避情欲的泛滥,也包括对物欲的贪婪。总体而言新时期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创造以克制的态度处理情欲与物欲。
一方面,自觉规避情欲的泛滥。
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情欲自然而然也常见于文学作品中,有些甚至以夸张地、现场直播的笔法,写出纵欲的全过程;而女作家则有意识地回避,仅是点到为止。像《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和《太阳部落》中,均有肉体欢愉的场景,但作家们对此种情节的处理偏向保守、含蓄、温和。
《太阳石》中写到千户夫人耶喜与管家完德扎西缠绵时“他不能,但是他体内的男性欲望已经毫无余地地苏醒了,他抱住眼前的绝色妇人,把热唇紧紧地贴在她渴望的唇上……” [13]写到此处视角随之转变“雕花木床从下面把他们托举起来,仿佛一株升向天空的高高的树梢,两只哑然许久的小鸟,正在上面迎着火焰的热情,鸣唱出动情的歌谣。” [14]书写欲望时,以它物代之,类似于汉族古典诗词中的比兴手法,以鸟儿成双成对的高歌来比兴耶喜夫人与完德扎西的鱼水之欢。处理洛桑达吉与桑丹卓玛第一次爱恋时,写到“这对互相等待已久的有情人,终于紧紧地拥抱了。洞外,是缠绵的雨,是雨的眷眷私语,是抒情歌曲最后那悠悠的音……” [15]洞外缠绵的雨水亦是对洞内的影射,洞内的洛桑达吉与桑丹卓玛也如呢喃的雨滴,柔情似“雨”拥抱、亲吻、互相拥有……
汉族女性作家对于情爱肉欲叙述的露骨程度,大家均已熟悉,此处不再举例。藏族男性作家在处理爱欲时,较之女性多了一份随心所欲,顾忌明显较少。擅长写“草原童话”的龙仁青在《人贩子》中处理欲望时写道“尼玛看着老婆的屁股,脖子上的喉结不由得滚动了几下。他喝了一大口清茶,吃了一大嘴馍馍,心里有种热乎乎的感觉” [16],接着“那种热乎乎的感觉慢慢变得有些灼烫起来”,最后情欲达到顶端“眼里的目光就像是灼烫的火苗”;《雪青色的羊卓花》“那一天,洋卓头上的雪青色头巾像是一团灼人的火焰,烧坏了吉明的眼睛,吉明至今仍能感觉到眼睛被火烧伤后的那种不舒服” [17]欲望如火焰灼烧着充满欲望的人;对于女人的性欲需求,图多则直言“那当然,娶她来,就是让她干家务伺候老子睡觉的,要不娶她干嘛?”女性本身成为了男人的欲望,女性作家在表述欲望时比男作家隐晦含蓄。
另一方面,有意节制物欲的放纵。
财富的占有是每个人的正常需求,俗世生活中,财富的积聚意味着温饱自足,虽财富并不能换来一切,而身无分文注定寸步难行,因此拥有物质财富及享受美好生活,是人奋斗的动力。文学中塑造了多位“守财奴”和纵欲者形象,像葛朗台、泼留希金、夏洛克、达尔丢夫等,他们将追求财富当成了毕生的目的,聚财的方法也是残忍与卑鄙。与之相比,在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对物质生活的贪婪享受较为逊色,守财奴与贪婪无厌者形象基本没有。即便梅卓《太阳石》中养尊处优、身上配满饰物、把金银珠宝看得很重的尕金,也并不贪心于物质享受,且没有像曹七巧般时刻提防他人窃取自己的财富。当懦弱的丈夫遇到危机时,尕金毫不吝啬地打开百宝箱为丈夫解围。相信“有钱的人就是自由,来去可以无限制……但没钱的人就等于没有一切,没有一切就等于没有尊严” [18]的尕金,不但不令人厌恶,反而多了几分可爱和真实。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生活在拉萨八角街的姬姆措与嫂子玉拉精心打理着绸缎店,生活无忧吃饱穿暖并能佩戴漂亮的首饰。而在一天二人不约而同的出走,舍弃现有富足物质生活,笃定的奔向未知的一切。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中的一直苦苦追寻的雅玛,其丈夫泽旦爱着自己,可以给自己与孩子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但却是唯利是图、吃喝嫖赌之人,雅玛毅然决然地与之解除婚姻。雅玛背着沉重的镣铐,追寻理想的爱情,追求自我身份的确立。
新时期藏族女性作家汉语书写时自觉规避情欲物欲泛滥的写作方式,与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及整个高地文学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较少有关。
第一,藏传佛教节欲观念的影响。藏传佛教文化认为无明烦恼是业之因,其中贪、嗔、痴三毒便是业因。烦恼皆由心生,心有贪欲难免沉沦于物质享受,而贪欲自然包括对情的贪婪和对物的占有享用。佛教教义主张“五戒十善”,“五戒指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十善的内容包括身三、口四、意三,即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即不贪、不嗔、不痴。” [19]五戒十善是佛教伦理道德的基础,要求人们必须做到起码的伦理准则。在佛教信仰中,下一世要得人身或者往生天上,就必须恪守五戒十善。戒律中不淫邪、不饮酒、不贪、不痴则是对欲望的节制。今生不贪,来世才能幸福。其次,藏传佛教认为,情欲是生死之根,无边的苦都因爱欲所生,只有断除淫欲,清净梵行,才能了脱生死,求得解脱。“清心寡欲”的观念定格于人们的观念中,女作家会受其影响,因而创作时自觉地规避欲望泛滥乃情理之中。此外,佛教“重精神轻物质”的修行观念,倡导众生轻视物质的享受,因而有情众生对物质的需求停留在基本满足的阶段,没有对“剩余欲望”的额外追求。勤劳节俭的藏族人,将财富捐赠寺院,兴佛法、保来世,免遭轮回之苦。所以《佛子》中,生活清苦极至的阿依琼琼为了向寺院捐赠,将作为生活物质来源的羊卖掉,如数上交;并在转经之前,将“用五百元供一只大转经筒”,三百元献给寺院,并坚信寺院收到布施,将会超度苦难的逝者。
第二,受女性身份的束缚。藏族女性观念受到印度文化中关于女性观的影响,印度“男净女秽”的偏见随着佛教文化传入而传入藏区。与男子相比,“女人”本身就是一种多染、多欲、懦弱、善妒、烦恼的存在,女人因人格缺陷导致精神不净,终造成“五碍”(即不能以女身作转轮圣王、帝释、梵王、魔王、佛)。印度女性观加上“罗刹女”的传说,使人相信“女性对于男性来讲是不够洁净的”,“女人会让护身符失去功效”。进而产生一系列行为约束如“女孩子不能坐在男孩子的衣服上的,不能把脚跨过男孩子的头,不能把自己的脏衣服扔在男孩子的身上,洗衣服的时候要先给男孩子洗……” [20]女性在“不洁”观念的束缚下,思想也被绑缚,在创作中自然不自然的受到制约。女子成为不洁、贪欲的代名词,更需克制自身行为方能改变这一凡俗印象。此外,作为女儿、妻子、母亲,作家们要考虑到作品问世后家人阅读的情况,为避免尴尬也会自发节制的叙事。
第三,偏居高地的藏族女性作家,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影响较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但主要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影响深远。内地“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女作家们,情感上更容易接受女性主义理论,书写时更放纵,形成了现当代文学中“下半身写作”的潮流。而藏地的女作家们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远远少于藏族古典传统。无可否认,新时期的藏族女作家几乎都是汉语写作,藏族传统文学的学习与掌握水平有待商榷,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生活藏域女性作家的熏陶,化为集体无意识深藏在思维中。且藏族古典传统文学多是僧侣文学、经院文学,这势必表现出理性节制凝练的特征,显示在女作家的创作中,便成为节制化书写风格。
此外,藏族女作家的创作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以客观写实的姿态,言说着藏族人的生活方式,遵循传统文学的理念,中规中矩的书写着这片熟知的大地。或许藏族女性作家也意识到了,藏地也进行着现代化,现代文明冲击着传统的文化理念,但这些终不足以让其直接宣泄物欲、肉欲、情欲,于是坚持以反思的态度客观冷静的创作着。
藏族女性作家书写欲望时的节制克制,在欲望泛滥的时代,颇具古典的审美范式,令人耳目一新。但并非所有女作家皆为如此,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与《复活的度母》,大胆而热烈地表达性的需求,对肉欲情欲的处理较为“前沿”。这两部小说主人公放纵情欲,像雅玛不停的更换情人,甚至因为与仅有一面之缘的青年欢爱,造成病人意外死亡的医疗事故。从表面看白玛娜珍的这两部长篇充满了欲望的写作,但从更深层次上看,是处于文明交织的冲突中,女性意识觉醒后,追求自我主体性存在的一种体现。而“涉世”未深的女主人公们,面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诱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能在滚滚的红尘中不停地寻找、尝试、再寻找……有些比较庆幸,寻找到了精神寄存处——将宗教作为最终归属,平息骚动不安的心灵;而有的却只能在交织的文明中,与初心渐行渐远,沦落为迷途的羔羊。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曾在《火的独自及片段》中豪迈的表示:“在中国我可以预言,最杰出的诗人将产生在更接近自然和具有独特文化的领域上……” [21],相对于中原腹地,生活在藏地高原上的女作家们身处与众不同的文化圈内,独特的自然与社会文化为她们的写作增添了成功的砝码。统观新时期藏族女作家的汉语书写,宗教文化一直隐性或显性的存在于女作家的写作中;而神佛文化作为价值理念则一直深埋于每一位作家意识深层。回归于女作家汉语创作层面看,一方面她们从宗教中取材,像《复活的度母》、《佛子》、《出家人》,增加了文本的迷幻色彩;而另一方面受如轮回转世观念的指引,编织着爱恨情仇;同时佛教的教义也规范约束女作家的写作手笔,使文本呈现出理性节制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神佛文化内化为新时期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的隐性线索,为我们深度解读文本提供了观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