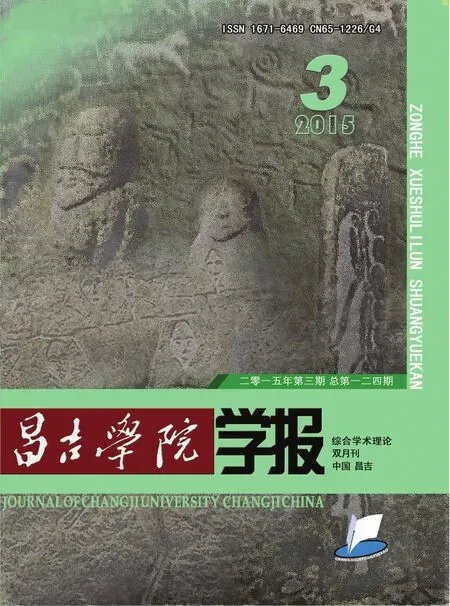维吾尔族女性走向何方:当代维吾尔文情爱小说中女性形象探析
摘要:维吾尔当代女性文学中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情爱小说占有很大比重,女作家们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被维吾尔传统婚姻观和道德伦理观裹挟,在爱情、婚姻、家庭中陷入悲惨境遇的各种女性形象,体现出维吾尔族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民族发展的忧患意识。同时提出在全球科技高速发展、现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维吾尔族女性走向何方的质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5)03-0001-06
收稿日期:2015-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女性作家与作品研究”(12XZW 039),新疆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课题“新疆维吾尔文学作品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14036)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晁正蓉(1974—),女,陕西临潼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维吾尔语言文学、维吾尔文化。
爱情一直都是文学世界永恒的主题,追求美好的爱情,能与自己相爱的人白头偕老是许多人理想的生活目标,维吾尔当代文学作品中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可将其归入情爱小说。情爱小说即爱情小说(Ro⁃mance novels),是小说的一种类型,泛指以爱情故事为主体的小说。爱情本身容易牵动人的情绪,小说又常以人物的冲突情节来反映人物性格,爱情往往存有冲突性,便成为小说作家常用的题材。维吾尔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创作了不少情爱小说。细读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女作家们通过塑造一个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当代维吾尔女性真实地生存状态,同时也对维吾尔族传统道德、婚姻、家庭观念提出了质疑。
一、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贤妻良母”形象
母亲不仅承担缔造孩子生命的责任,还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维吾尔情爱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专门将母亲形象提出来进行描述,但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已刻画出了众多善良无私,为家庭贡献一切的贤妻良母形象,这些母亲熏陶和影响着一代代维吾尔女性。
大部分维吾尔文情爱小说中的母亲,都是传统的,集慈爱、温柔、善良等于一身的女性形象。在这些文本中,母亲形象成为传统文化性别特点的符号化象征。作家大多会把母亲放置在一个苦难的环境中,通过母亲与苦难的对抗,反映她们的坚忍与牺牲, [1]76这些母亲形象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大都没什么文化,也没有工作,她们生活的全部就是下地干活、洗衣做饭、相夫教子、侍奉尊长。就算受过一定教育,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女性,也仍然承担着全部繁重的家务劳动,无论自己受多少委屈她们都坚强地承受。但是她们却都没有得到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和尊重,而像是家里免费的奴婢。她们从未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甚至还被丈夫随意打骂。
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轨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最能体现身为维吾尔女性,身为一个母亲悲惨的境遇。“母亲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生下我时,当听说是女孩后,背过脸哭了。可怜的母亲,可能是因为生男孩的希望破灭而哭泣,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同自己一样不幸的人而哭泣,或者是二者兼有……” [2]248在维吾尔族传统观念里,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女性生活在狭窄的圈子里,小时候服从父兄,结婚后服从丈夫,世代处于卑下的地位。当生下女孩的“我”,母亲流泪了。她的眼泪预示着我未来的命运。母亲在有生之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当“我”考上大学,能够自立,满怀希望能对母亲敬敬孝心时,她却因操劳过度,抛下所有的苦难撒手而去。而“我”一直以为通过努力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时,处境却同母亲如此相似。这样的母亲形象,也同样出现在其他情爱小说中。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天边的微笑》中,海里倩姆的母亲省吃俭用、忠诚、辛劳地照料了丈夫一生,却没有得到丈夫一丝眷恋和柔情。《小路》、《天使》中女主人公的母亲也是为了维持家庭,默默地承受一切,最后过早地离开人世。
在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中,女人不需要接受太多的科学文化教育,目前这种观念在新疆很多地区,尤其是南疆地区依然大量存在。人们不把女性看作是可以自立的个体,她们的任务是呆在家里,生儿育女,照料家务,而男人的任务才是养家糊口。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幸福的生活,“但是维吾尔教育观念并没有使大多数女孩子在婚后摆脱传统的任人摆布的家庭地位。” [3]171-172即便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女性,婚后也无法避免陷入家庭的藩篱。近年对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女性的调查显示:78.4%的家务劳动都由妻子完成。剩余的由妻子和保姆完成。 [4]23-25
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那眼睛》中,通过一个男人对自己已逝妻子生前的回忆,更能深刻体会出一个勤劳、善良、逆来顺受的维吾尔族母亲形象。“他欺骗了她一辈子,就连对别的女人付出的爱的十分之一也没有给过她,只是把他当作孩子的母亲、家庭的支柱和一个忠于自己的佣人而已。她原先也上过学、有文化、可以是有所作为的女人,然而,却把自己的一生、前途和健康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丈夫、家庭和孩子们,他想不起来她什么时候舒舒服服地躺下休息过一次,或安安心心地吃过一次热饭热菜。不论什么时候她总是那么忙碌。……那些没完没了的劳作和家里的琐事吞噬了她。”就是这样的妻子,他也没有好好对待过“他从来没有好言好语地向妻子问寒问暖,一生中从来没有给她送过什么礼物,若在单位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也总是拿身材消瘦、大眼睛、胆小怕事的妻子出气。孩子们呢?怎么也都不能体谅母亲的难处呢?他们莫非是受了他对妻子态度的影响不成?……她遭受了如同地狱般的煎熬,孩子们却没有为她做任何事。”“是啊,他是有愧于妻子的。可是,在世界上如此生活的难道就只有他一个人吗?他的父辈是如此生活的,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女人是家庭的主妇,家务事主妇不干还由谁来干?” [5]279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会反省的。作为一个男人当他反省自己和妻子共处的日日夜夜时,发现自己有愧于那么无私、善良、勤劳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当他拷问自己的灵魂时,心灵深处产生了一丝忏悔和惭愧,可是转瞬间,这些悔恨便在这男权社会传统观念的保护下荡然无存,他为自己找到了托词和借口,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变得理所应当,同时良心也得到了解脱。通过男性的口吻和立场,批判男权社会的世俗观念,以及男性自私、无耻的一面。这样的传统观念与现代先进文化显得那样格格不入,而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仍然大量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真是值得人们深思。
二、沉默寡言,缺乏与子女沟通的母亲形象
有修养的母亲会铸造孩子的品质,有深度的母亲会影响孩子深刻思考。维吾尔族家庭的教育主要是对子女进行思想品德、伦理道德、生活常识、劳动技能和宗教文化教育,不少身为人母的维吾尔族妇女本身文化知识水平低,在教育孩子方面没有科学的指导。她们每天将家人的吃穿住行照顾好就已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因此,跟孩子心灵的沟通少之又少。对孩子进行科学文化的熏陶就无从谈起。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很多缺乏与子女沟通的母亲形象,正是作家对现存妇女地位低下的忧虑和抗争。
著名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露珠》中吐尔逊尼牙孜汗在上小学时每天都和母亲一起在棉花地里除草,但是当她小学毕业后,母亲突然不让她出门拔草了,但母亲没有告诉她真实原因。《沙枣花》中处于青春期的赛丽曼对沙枣林充满幻想,当母亲看到她从沙枣林中走出来时,便勃然大怒,“她好像要找出什么人似的窥视了一遍四周,然后拽着女儿的手向家里走去。”她没有告诉孩子为什么禁止她进入沙枣林。因此,当女孩看到沙枣林里漫步的一对对情侣,更是将那里看做神秘的地方而充满好奇。正是因为母亲不了解青春期的女孩应如何沟通交流,而总是采用回避的方式,于是造成女孩遇到了感情方面的困惑,不敢跟父母交流,最后以悲剧收场的结局。
热孜万古丽·玉素甫在她创作的情爱小说中塑造了大量这样的女性。如《离别之旅》中的玛依努尔,《飞蓬之梦》、《红遍乡村》和《小路》中的女主角。而女性意识强烈的女作家哈丽黛·伊斯拉依尔在作品《彩色旋风》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小说中的父亲不苟言笑,脾气暴躁,而善良、慈爱的母亲没能给孩子一个坚强的臂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遇事往往因为害羞对母亲也难以齿口。
维吾尔族长期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是男女青年不能公开交往,特别是女性家教管理更严格,不允许参加任何社交活动或与男青年往来。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极高。青春期的少女,对男女之恋充满神秘感和好奇心,但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小说中的女性又缺乏和母亲的交流沟通,更缺少对性知识的了解,因此上演了一幕幕悲剧。《飞蓬之梦》中的女主角,《神秘的苹果》中未婚先孕的少女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
三、在婚姻的枷锁中挣扎的女性
社会的变迁促进了维吾尔族女性婚姻家庭生活观念的变迁,提高婚姻质量,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平等、和睦、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成为广大维吾尔族女性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因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维吾尔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并不美满。小说中主要体现为两种婚姻形式:一种是包办婚姻,另一种是自主婚姻。但是这两种婚姻的结局竟然都如此相似,女性最终仍与她们的母辈一样,成为家庭和生活的依附者,处于男子的附庸地位。而各种无形的社会规范又都要求她们的言行举止与传统社会规范一致,她们无法勇敢地冲破这婚姻的枷锁。
1.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加汗巴格》中,女主人公莱丽是一位像生活在童话世界般天真、可爱的女孩,在她还未成年时,就被害怕孤独的爷爷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一个大她很多的男人亚森。莱丽婚后像霜打的花儿一样蔫了,以往银铃般的笑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次,在赛马会上,她遇到了自己心动的男孩吉利力,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直到爷爷去世,丈夫突然消失多年后,她仍然没能和她相爱的人在一起,一个人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直到静静地老死在核桃树下。作品《沙枣花》中的赛丽曼刚满16岁就被父母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彪悍男人,新婚之夜,当她沉浸在美好的幻觉中时,却被不知道要对她做什么的赤身裸体的丈夫吓成了神经病。
在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这样的悲剧,原因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偏远地区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文化教育事业还很落后,还没能彻底改变包办婚姻的局面。文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婚姻意识。新疆广大维吾尔农村深受传统婚姻观念、陈规陋习的影响,这些都极大限制和妨碍了维吾尔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剥夺了许多女孩受教育的权利。而女性教育水平的低下又导致社会生活对女性进一步的排斥,使许多女性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恶性循环中。女性的愚昧、无知迫使她们处于任人摆布的状态。多年来虽然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但是维吾尔族广大农村地区仍固守传统观念不改变,没有将宗教观念与现代先进文化相适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包办婚姻和早婚的现象至今仍存在。这类女性形象在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情爱小说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其他作家也不同程度在小说中塑造了包办婚姻造成多家不幸福,造成多个心灵受伤的女人形象。《轨道》中的玛依努尔与阿不力克木真心相爱,但是却被迫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没能跟自己初恋情人阿不力克木结婚的玛依努尔,在阿不力克木与阿斯亚结婚的当天自杀了。玛依努尔的死,给阿斯亚的家庭生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最终也导致阿斯亚婚姻的不幸。阿尔孜古丽·比拉尔的《阿尔曼的心愿》中,小主人公阿尔曼的父母以前都有自己钟情的恋人,是包办婚姻让他们生活在一起,于是在无爱的婚姻生活中的阿尔曼的父母总是处在无休止的争吵中,阿尔曼对家唯一的记忆就是父母争吵不休。包办婚姻不仅造成了两个家庭的不幸,更是伤及到更多的人。类似的描述在《灵魂的征途》中也有反映。主人公“我”回忆小时候,“不知为什么父母经常当我的面没完没了地吵闹,他们不顾我的不安和恐惧。争吵到最后总是在妈妈的哭泣、爸爸的叹惜和我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的呜咽声中结束。” [6]135《薄荷》中的再那甫,《死亡》中的迪里拜尔,《晚秋霜冻》中的拜合提努尔,《痛苦》中的比力克孜等等都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早在“五四“时期,我国妇女就力争打破封建枷锁,并为之做出巨大的努力,转眼,时光已飞逝将近一个世纪,直到现在我国维吾尔族农村妇女的生存境遇仍没多大改观。这是历史的悲剧。作者塑造众多女性形象,正是要提醒人们:人类在长期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式构成的人类的行为文化模式虽然很难被打破,受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影响的维吾尔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提高,打破束缚女性枷锁的道路虽然也很艰巨,我们女性自己应该为维护女性权利,保护女性发挥自己的作用。
2.走进婚姻的坟墓
随着国家教育法和婚姻法的普及,自主选择对象越来越普遍,在城市,自由恋爱已成为维吾尔族青年女性首选的择偶方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向自主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自由恋爱的双方婚后的生活也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在伊斯兰教传统观念以及维吾尔传统道德观的束缚下,女人仍处于弱势地位,无论婚后生活多么不幸,妻子也无权提出离婚,只能由男方单方面提出。《轨道》中阿斯亚的丈夫因婚后仍然思恋自己的初恋情人,经常辱骂毒打妻子阿斯亚,甚至在外面与其他女人鬼混,而阿斯亚为了孩子和维持家庭,一直保持沉默,最后致使精神失常。传统观念就像一条铺设好的“轨道”,要求妇女严格按照它的轨迹运行,否则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主人公阿斯亚,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曾经为自己母亲的不幸悲哀过,曾痛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压制妇女的家庭,把母亲也拯救出来。但阿斯亚最终不但没能解救自己的母亲,自己反而也在既定的轨道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离别之旅》中玛依努尔经历几次感情失败后与自己相爱的塞达尔结了婚,但是婚后不久,塞达尔就移情别恋,为了家人,为了孩子,玛依努尔一直硬撑着。这些固守破碎的婚姻,为了让父母放心的观念都深受维吾尔“孝敬父母”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与伊斯兰教教规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按伊斯兰教来看,不孝敬父母者两世(今世和来世)都得不到幸福。特别是来世进不了天堂。这种观念根植于人心,形成维吾尔族特定的社会道德观念。 [7]也形成他们心中“好女人”的样板。阿斯亚、玛依努尔等女性形象都触动了维吾尔妇女不幸的根源,她们让我们看到,传统观念下“好女人”的文化面具是怎样扼杀女性的天性和鲜活的情感,遮盖她们的真实存在的。她们像一颗颗沿固定轨道运行的行星,运转的中心始终是男权社会。在这种环境中,作为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地带的女人,能做的只能是忍耐。这正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西蒙·波娃所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论点。
四、无知、清纯的少女形象
维吾尔作家在情爱小说中也塑造了不少美丽、善良、情窦初开,追求美好爱情的少女形象。这些涉世之初的女孩大胆追求真爱,但都以悲剧告终。小说中的少女形象,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从事农耕还是读书,从外貌描述来看几乎都符合维吾尔族传统对女性审美的要求。她们长发飘飘、含蓄羞涩、美丽端庄,就算身体有某些小缺陷,总体也给人楚楚动人的感觉。而小说中的少女也常常以男性乐于接受的形象为标准来调整和改造自己。维吾尔族传统婚恋观念往往将女性的外貌看作第一位。中篇小说《飞蓬之梦》中被称为“黄毛丫头”的阿依姆古丽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美丽的青春少女,她每天割飞蓬的时候,都遥望着地平线,想象着地平线另一边人们的生活;为了获得真爱,为了能到地平线那头去看看,她夜夜在飞蓬地等待那位答应娶他并带她去乌鲁木齐的穆罕默德,但最终是在等待中逝去了青春年华。《神秘的苹果》中的女孩轻易便将自己献给一见钟情的男孩,并怀孕,但男孩在一夜情后就像突然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她也只好听从家人的安排嫁给了大自己很多的男人。《幸福》中的女大学生因在大学恋爱、怀孕最后被迫退学,而当时对她信誓旦旦的男友早就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作者在情爱小说中塑造了大量这类清纯、痴情的少女形象,她们对爱情充满美好、单纯的幻想,自主意识薄弱,接受新观念能力差,分辨能力不强,性知识缺乏,轻易将自己委身于某个钟情的男人,但终究落下被抛弃的结局。实际上,他们的爱情早已化为泡影。但是她们却仍在痴痴地等待。作家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揭示了当下维吾尔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被随意蹂躏、抛弃的现实。同时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并不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在现代社会维吾尔族女性仍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束缚,难逃厄运。她们在宗教教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双重压力下,不能呼吸。小说在对维吾尔女性愚昧、落后、无知、痴情的生存境遇如实展示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民族发展的忧患意识。
五、坚强、勇敢、自立、自强、自信的女性形象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维吾尔族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她们开始觉醒,更多的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并且开始大胆地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作家在情爱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这样的女性,她们反叛和否定束缚女性发展和自由的陈旧观念,在她们看来,爱情是美好的,但并不是女性的全部,她们决不为爱情丧失自我,也不为爱情牺牲独立。她们大胆地追求真爱,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存,开始独立自主地确立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她们不再只是生育的奴隶,她们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尊严。她们也不再满足于男性中心文化的禁锢,不能忍受男性身影对于世界的遮蔽,往往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
《绿色的希望》中因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大胆与丈夫离婚去寻找真爱的“我”,因有孩子的拖累没能再婚,但是并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小说肯定了女性处理家庭变故的能力,赞扬了现代女性在破裂婚姻下的坚强。从家庭的枷锁中解放开来,从丈夫背叛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与外界接轨,显示出破裂下的坚强。
《啊,生活》中喀什的年轻少妇古丽琪克热和丈夫离婚后,在疗养院遇到了自己所钟爱的医生卡斯木,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和医生卡斯木一起踏上了爱情之路。古丽尼莎·加玛勒在《好梦成真》中成功塑造了一位独立不羁,秀外慧中,自立、自主、自强、自信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维吾尔现代女性形象——海维拉。在单位,她是一位主治医师,有着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家中,她是一位好母亲;当丈夫背叛之情败露以后,她气愤但保持了一位知识女性在此种境遇中难能可贵的理智和尊严;她不屈于女性在无爱的婚姻家庭中屈辱地位,于是,当久已心仪的梦中情人真切地出现在她眼前时,她一反《轨道》中阿斯娅的优柔寡断,勇敢地去追求人性的自由,好梦成真。这些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标志着新的婚恋观已经形成。尤其是2011年莎吉旦·苏来曼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也有爱的权利》引起很大的反响。作品以现代理性眼光审视民族传统文化,以男性独白的口吻客观、公允地道出:“人们的传统观念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并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我有寻找真爱的权利,这种纯粹的爱与金钱、年龄、地位、是否离异没有关系。作品女性现代意识强烈。
是的,女性只有把自己从女性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实现自我价值。只有束缚女性的枷锁真正被打破,女性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虽然女性在社会文化,道德标准下始终没有摆脱男权的制约,但作品触及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女性的自主意识。虽然还不是很深入,但也可以说明作家们已开始思考这些实质性问题。
作家们以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维吾尔族女性生命意义的描述,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展示发人深思。随着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维吾尔族女性社会地位地不断提高,作家们一定能塑造出现代色彩和民族个性完美结合的维吾尔女性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兼备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于一身,在祖国各条战线上辛勤耕耘,获得幸福生活的维吾尔族女性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