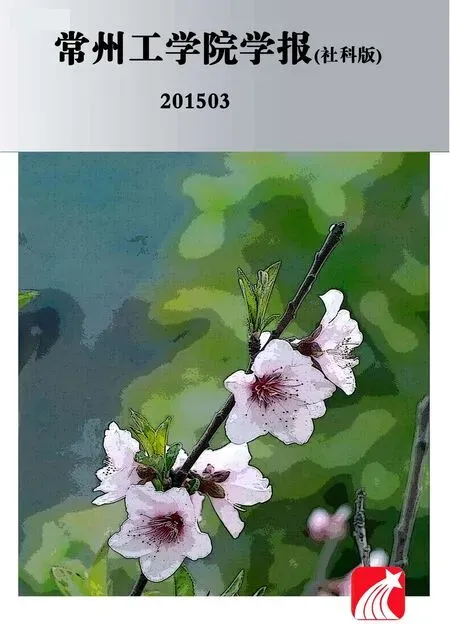异域环境下对中国传说的新书写——以严歌苓《白蛇》为例
异域环境下对中国传说的新书写——以严歌苓《白蛇》为例
符燕鸿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中西方文化从未停止过碰撞,而海外华文作家往往处于碰撞的风口浪尖。中国文化是他们舍弃不去的精神烙印,西方文化又时时渗透在他们的生活里。身处文化夹缝,流传千年的中国传说在他们的改写下绽放了炫目的光彩。以严歌苓为例,她的《白蛇》以古老的“白蛇传说”为意象,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发生于“文革”时期的女同性恋故事。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针锋相对多年的中西方文化开始交融。故事的借用意象与发生背景都为我们熟知,其人物情节与书写方式却给我们带来惊喜。作者对这个传说全新书写既体现了作者在创作探索上取得的成就,又为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一阵来自域外的清风。
关键词:严歌苓;白蛇传说;异域;中西方文化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5.03.004 10.3969/j.issn.1673-0887.2015.03.012 10.3969/j.issn.1673-0887.2015.03.005
收稿日期:2015-04-28
作者简介:符燕鸿(1992—),女,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5)03-0017-05
引言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继续发展。作家离开故土远渡重洋,切身感受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经历的记录,更是文化碰撞的产物。在众多海外华文作家中,严歌苓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歌苓发表了大量长短篇小说,曾获得两岸三地多项文学大奖。陈思和认为:“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1]在严歌苓充满人性观照的作品中,有一些是描写同性恋的,这些小说干净而美丽,《白蛇》是其中颇为成功的一篇。
作者以“白蛇传说”为线索,通过多个版本交插叙述,将一个发生于“文革”时期的同性相恋故事逐步揭示于我们眼前。目前对该小说的研究多着重于小说“文革”背景、独特的叙述方式或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某方面对比,缺乏系统分析作者对“白蛇传说”意象的借用与创新。因此,本文将以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为依据,探讨中国的古老神话“白蛇传说”在异域发生变化的具体内容、主要原因及积极意义。
一、传统在异域的变化
如其他民间传说一样,“白蛇传说”在流传中经过不同地区、文人、说唱艺人的改写而出现了如今版本众多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根据几个颇有代表性的版本,经过十年的反复删改,完成了现代戏曲《白蛇传》。田本“白蛇传说”中,白素贞与许仙两情相悦,得成眷属。法海却以降妖为名多次作梗,后在婴儿弥月之期,不顾许仙苦苦哀求将白素贞摄入金钵,压在雷锋塔下。最后,白素贞之子许仕林祭塔时雷峰塔轰然倒塌(1953年改为小青击败塔神救出白素贞)。田汉版“白蛇传说”是最为现代人熟知且接受的版本,白娘子善良忠贞、小青刚烈忠心与许仙懦弱痴情的形象都深入现代人心中。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为人们所熟知的民间传说却在严歌苓笔下面目大改,作者以“白蛇传说”为意象,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白蛇故事。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到叙述方式与传统书写全然不同。在这样的改写中,“白蛇传说”完成了它在异域的流变。
(一)双蛇形象凡人化,许仙形象缺位
在人物设定方面,《白蛇》迥异于以往版本。人们一般认为白蛇形象经历了“妖怪—义妖—神仙”的演变。田汉笔下的白素贞是一个神化的完美女性,她聪慧清醒,法力高强而又善良贤淑,更敢于为了自己的幸福与恶势力抗争。而在严歌苓的《白蛇》中,“白蛇”形象的投射——舞蹈家孙丽坤却始终是个平凡的女子,并非传说中的十恶不赦或完美无瑕。舞蹈给她带来过荣誉,她却对此懵懵懂懂。鲜花、掌声、英俊的男子,她都曾经拥有,但是又如此模糊,令她记忆深刻的只有舞蹈。当政治的风暴来到,这个无辜的女子也无法幸免。她被赶下舞台关进仓库,自尊与骄傲在一次次对自己私生活进行细致自白中变得慷慨无畏。在这样的绝境里,徐群山(珊)唤起了她内心的情爱,她像一条度过寒冬的蛇重回人间,但是徐的女性身份又将她推入了另一个无底深渊。当她从疯癫中苏醒,真正爱上眼前的珊珊时,时代的癫狂业已结束。在一个安稳而平凡的年代,她选择了屈服,打算将这段被视为畸形的爱恋深藏心底。而她在公共汽车上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呼唤着“徐群山”,却表明这段感情无法轻易从她心里抹去。
过去的故事中,青蛇只以附属的身份出现,恰如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串联情节的丫鬟仆役角色。田汉版的《白蛇传》中,小青宛若白蛇的影子。她伴白蛇游湖、为白蛇说媒、陪白蛇盗仙草、同白蛇一起大战法海……而严歌苓笔下的“青蛇”形象——徐群珊(山)却是整部书的绝对主角。她“轻蔑女孩子的肤浅鄙夷男孩子的粗俗”[2]25,她追问“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恋之上的生命”[2]25?男子的特质与女子的特质在她身上交融,在一个混乱的年代,她有了不必恪守社会既定性别的机会。她自由游走于代表男性的“山”与代表女性的“珊”之间。当她是徐群山时,清朗的眼睛、举止中偶尔流露出的羸弱与柔情令孙丽坤痴迷不已;当她还原为徐群珊时,一头短发、傻小子般驼着背与男子般的爽朗再次虏获了孙丽坤的心。她原是孙丽坤的舞迷,从小就爱上了扮演白蛇的孙丽坤。再一次见面时,她却已反客为主,成为孙丽坤心里的王,一声令下足以颠覆“白蛇”的世界。最后,徐群珊也逃不过“笨手笨脚地学做一个女人”[2]43的命运,但她脸上永远挂着的淡淡厌恶似乎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反抗。而她的一头短发,先被视为不伦不类,后被视为当时最流行的“张瑜头”。这似乎隐喻着“雌雄同体”的徐群珊们和她们的“畸形爱恋”也许会有一天为社会所接受。
许仙是传统“白蛇传说”中的重要角色。在田汉的剧本里,他眉目俊朗,对爱忠贞,在断桥上曾对白素贞真诚地表白“你纵是异类,我也心不变”[3]。但在《白蛇》里并没有传统意义的男主角,更难以确定哪个是许仙形象的投射。令孙丽坤遭受批判的捷克舞蹈家,“文革”后与孙丽坤订婚的体育老师,乃至与徐群珊结婚的助教,都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仅有个不甚明晰的轮廓,离我们心中的许仙形象相去甚远。而青蛇形象的投射——“雌雄同体”的徐群珊甚至让我们觉得许仙已经没有了存在于文本中的必要。许仙形象的缺位使得《白蛇》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完美无缺的爱情传说模式。
(二)神话传说意象化,与现实故事交融
对人物形象进行颠覆的同时,《白蛇》的故事情节也相应发生了变动。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白素贞与许仙情深义重,白素贞愿为许仙“盗草”且上山“索夫”,许仙得知白素贞为蛇后仍选择“逃山”,而小青敬爱白素贞,为维系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敢与法海“水斗”……这些熟悉的情节到了严歌苓笔下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片段。当这些传说片段与孙丽坤、徐群珊的生活交织时,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阐述的局面。原本旨意明确的情节,其意蕴悄然发生改变。
首先,透过幼年徐群珊的眼睛,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青蛇忠诚勇敢。从男儿身变为女儿身,青蛇毫无怨言,始终全心全意追随白蛇,而所谓的男主角许仙带给白蛇的只是磨难。一部以许仙与白蛇为主角的舞蹈,徐群珊怜惜的却是青蛇。作者正是通过徐群珊向我们控诉了传说中的不公平:本应与白蛇相依为伴的青蛇,在人们加入一个无所作为的许仙之后,几乎成了故事里的局外人。当这样的不公平被揭示后,我们的目光终于落到被忽视了几千年的青蛇身上。此后,徐群珊的形象逐步与青蛇的形象重合,她开始了不断的质疑与抗争,并一跃成为了书中的主角。
其次,当孙丽坤在布景仓库与徐群山目光相对的时候,她宛若看到了白蛇在断桥上与许仙相遇,目光流转从此一见倾心。随着两人见面次数的慢慢增多,她又感到徐群山是来搭救她的,如同青蛇去搭救盗仙草的白蛇。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青蛇形象与许仙形象发生交融。若许仙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的是青蛇;若白蛇落难时,拯救她的还是青蛇。那许仙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此时,青蛇形象延续了之前青蛇始终守护白蛇的描述,而又有了取代许仙地位的可能。在一个既有秩序被破坏的年代,所有事物都不自觉地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这样的偏离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令一个国家蒙受苦难,又蕴含着一线生机,使得本不被认可的事物有了存在的可能。孙丽坤与徐群珊就在如此混乱的生活境况中完成了白蛇与青蛇的爱情书写。
再次,孙丽坤被徐群珊带到招待所后,徐开始播放白蛇哭许仙的独舞音乐。彼时“许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吓死之后,白蛇盘绕在他的尸体上,想以自己的体温将他暖回来”[2]33。作者由此隐喻:神话中的白蛇虽为异类却有着人类最本真的感情。她对许仙的爱坚贞不渝,为挽回许仙的信任不惜饮下雄黄酒,为挽救许仙的性命不惜盗取仙草。反观现实,当徐的女性身份现形后,孙丽坤无法从两性情爱的陈腐理解中找到出路。她“在那张性别似是而非的年轻的脸上啐了一口”[2]38后便陷入了哭笑失禁的真空中。当她从真空中清醒,才发现自己是如此想念徐群珊。可见,若白蛇被现实秩序所驯化,面对异于常规的爱人,她的下意识反应是抗拒与逃避。当她逃入没有任何规则的真空后,才能重新确认自己天性中对爱的最原始追求。
最后,徐群珊与一个本分的男子结婚时,孙丽坤送上了一座昂贵的玉雕。在新房里,两人同时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戏文中,断桥怒斥许仙之后便是白蛇与许仙和好如初。青蛇最初对白蛇有着男子对女子的爱慕,在白蛇蒙难时又以姐妹之名为白蛇奋不顾身,到了最后还是只能退到一旁。传统中认为最完满的结局是白蛇当配许仙,青蛇追随白蛇。当时代恢复平静时,平静表象下的异动都将被强大的秩序所遏制。白蛇与青蛇间终究隔了个许仙,无论孙丽坤与徐群珊如何努力,她们的恋情都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当她们走上社会认可的、所谓正常的生活道路时,这种生活对她们本身而言又正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传统与现实的悖论似乎无可调和,就在这样的矛盾中这部现代“白蛇传说”落下了帷幕。
(三)叙述方式多样化,以私密话语为主
传统神话传说倾向于由一个统筹全局的叙述者将故事娓娓道来,虽有奇幻的情节,但人物与叙述口吻却是严肃可信的,仿佛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田汉的剧本亦是如此,情节虽有奇幻之处,但详尽的地点、人物无不强调了故事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作者作为唯一的叙述者,将事件的前因后果毫无遗漏地传达给读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作者更重视的是自己的价值观是否为读者所接受。可见,“白蛇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已从偏重故事情节到偏重思想内涵。相较之前,其故事情节或许变得更加丰富,但丰富的情节亦只为烘托出作者笔下唯一的宏大主题。
严歌苓的《白蛇》抛弃了单一叙述方式,以四个“官方版本”、三个“民间版本”和七个“不为人知的版本”交叉叙述。作者不再刻意追求某个深刻的主题,她讲述了一个真诚的故事,并将它放置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横向扩展了小说的包容性。在一片嘈杂声中,“不为人知的版本”——两个女人的内心独白逐渐变得清晰。当读者从中把握了事情的始末后,再回过头来看“官方版本”与“民间版本”,即能发现它们是如此失真与可笑。
“官方版本”由三封信(S省革委会宣传部致周恩来总理;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致省文教宣传部;北京市公安局致S省革委会保卫部)与一篇《成都晚报》特稿组成。孙丽坤精神失常之后,政治指示层层下达,追问事件的真相,最终却不了了之。在庄重严谨的官方语调下,我们看到个人历史在官方的剪贴拼凑下变得无足轻重。“民间版本”的叙述者包括建筑工人、歌舞剧院的工作人员和精神病院的病人护士。他们是事件的目击者,比官方更贴近事实却依然徘徊在真相之外。当孙丽坤被定性为“反革命”,她的种种经历早已变成了民间谈资。而民众不在乎事件的真相,总是随意歪曲揣度他们看到的一切。当孙丽坤沦为一个过气的舞蹈家,更没人真正在乎她经历过什么。众说纷纭的民间,似乎并不存在所谓事实。
唯一揭示真相的只有“不为人知的版本”。作者通过引用徐群珊幼年时的日记、孙丽坤的心里独白等以私密叙述方式真实再现了个体的状况。对比前两个版本,两个女性的自白显得如此坦率。徐群珊幼年时对孙丽坤的迷恋与克制,孙丽坤对徐群山的爱慕对珊珊的怜惜,时代对个人命运的随意拿捏……所有的一切缠绕成一团,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自行梳理。当官方权威话语与民间猎奇话语在个人心灵秘史下被解构之后,白蛇与青蛇从尘埃满布的历史中走了出来。她们不再是硬梆梆的泥塑,任由创作者与看客摆布,她们成了顾盼生姿的鲜活女子,开始上演一场原始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现代“白蛇传说”。
二、个体体验的书写
“神话故事往往是一种人性原型,因此长达数千年之间,依据原型,可以不断在特殊时空及社会背景下演绎出不同的版本。”[4]“白蛇传说”作为一种原型,千百年来都不断地被改写。在改写过程中,其异类基调越来越淡薄,到了严歌苓笔下,它直接变成了凡人的演义,带着传奇的影子。相较于传奇性,显然作者更乐于探索其人性原型在非常态环境下的丰富内涵。而严歌苓先经历“文革”后移居海外的人生体验更使得《白蛇》迥异于传统书写。
(一)身份认同的思考
“文革”时,随着父亲萧马被打成“反动文人”,作为反革命后代的严歌苓“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当时的主流文化之外。“文革”结束后,经过一阵短暂而平静的日子,严歌苓选择在而立之年远赴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写作硕士学位。初到美国,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的确让她灵感迸发,书写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与此同时,移民者的寂寞孤单又始终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5]从“文革”到移民,身份得不到认同的感觉在严歌苓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当如此深刻的记忆投射到写作中,她毅然选择了一种边缘性写作姿态。她喜欢站在故事背后,通过书写边缘人物的经历揭示世界不公与人生荒谬。因而,当她开始审视“白蛇传说”这样完满的神话故事时,她的目光自然不会停留在许仙与白蛇的爱情上。在严歌苓看来,白蛇与青蛇因其异类身份不见容于法海才是挖掘故事的突破口。结合自身经验,作者在《白蛇》中提出:在一个拷问人性的时代,人中“异类”的身份是否会得到认同,这是一个严峻的人生命题。
传说中,白蛇持家有道并为许仙诞下孩子,这些情节使得白蛇的异类形象减弱,令读者心理上更偏向于认可其人妻身份。而许仙的人类身份更为世人接受他与白蛇的爱情埋下伏笔。若故事的主角换为白蛇与青蛇,她们妄图在人间享受一场欢愉,那世人会认可她们的感情吗?剥去她们的蛇妖身份,在一个人人扮演法海角色,以为自己维护着公平秩序,实质上迫害他人的时代,两个被普通人视为异类的女子,她们将何去何从?文本中,最后孙丽坤(白蛇)与徐群珊(青蛇)各自有了自己的异性伴侣,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当是作者的无奈之笔。或许,严歌苓也未能为身份得不到社会认同的个体想到一个较好的归宿。而文本最后社会对徐群珊短发看法的转变,隐约表明了作者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渴望一个更包容的社会出现。
严歌苓在不露声色之中完成了对“白蛇传说”的叩问和改写。除去许仙与蛇妖的幌子,两个异于世俗的女子因坚守天性而被误读,最终她们放弃了抗争却同时被社会给予了看似适当的身份而接纳。传统“白蛇传说”对个体命运与时代际遇错综关系的掩饰,在《白蛇》中被揭下了面纱,使得我们能够倾听身份得不到认同的个体在宏大历史下的微弱呼声。
(二)异域与本土碰撞
每个寓居他乡的海外作家都曾经历过一次思想上的“大洗脑”,亦像是“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6]。中国文化是他们身上无法舍去的精神烙印,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开始渗透于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间,作家将自身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使两种文化实现碰撞与交流。中国文化自成一体与中国古老的说书传统曾使我国叙事文学长期处于叙事封闭化单一化局面。而中国人“尚圆”的传统观念更促使许多神话故事最后都以“大团圆结局”满足国人的审美需求。田汉的改写也跳不出这个基本框架,若除去白蛇的蛇妖身份,她和许仙宛如任何一本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再看严歌苓,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后,神话重现的时代——“文革”,在她笔下可谓众声喧嚣。
当神话的极度完满与现实的极度残酷在文本中相互映照时,神话被现实所解构,现实亦因神话的介入得到反思。若作者止步于此,在神话语境与现实语境的交锋下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也已完成,但长期浸染于国外语境使得严歌苓的写作变得更加深入。她不满足于国内对“文革”的书写仍停留在记录时代伤痕与反思时代阶段,她将写作重心从历史大背景转入个人内心,官方与集体的声音成为陪衬,个人的呼声低沉却清晰。西方一直重视个人价值,其文学作品在刻画私人心理活动与歌咏苦难中的爱情等方面往往令人难忘。《白蛇》对幼年徐群珊的日记及她与孙丽坤隐忍爱情的出色书写显然得益于西方文化。而丑陋时代中同性恋歌有了歌唱的可能,和平时代里它却只能戛然而止。这样的情节显然已经不是“文革”主题所能涵盖的。作者通过层层语境铺垫,引导读者进入自己苦心搭建的文学世界,当故事戛然而止时,由文本引发的思考仍在继续。
徐群珊与孙丽坤的形象颠覆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对西方女权主义做了个遥远的呼应。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将“雌雄同体”观引入文学批评中,在她看来,“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7]。这样的描述与徐群珊的形象相吻合,她鄙夷绝对的女性或男性。当她以徐群山的身份出现,是女性化的男性;当她以珊珊的身份出现,是男性化的女性。而孙丽坤在爱上徐群珊之前曾有过不同的男人,离开徐群珊后有了自己的异性伴侣;她爱男子形象的徐群山,亦爱女子形象的珊珊。从这个形象身上,我们能看到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影子。酷儿理论认为人类性倾向在许多时候都是模糊不清的,许多人都体验过异性恋与同性恋两种感觉。从文本看来,孙丽坤的性取向的确难以判定。从徐群珊到孙丽坤,她们的出现将神话传说拉下神坛却未树立新的价值标准。严歌苓也公开承认自己“是非模糊”[8],面对异域与本土两种迥异文化,她的确难以做出评判。作者只能通过模糊书写使两种文化在文本中交融,从而令读者能在阅读中对两种文化进行反思。
三、结语
神话传说贯穿于人类漫长的历史,当历史向前流动时,更富于时代感的新内容时时准备着替换过时的旧内容。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国作家对传说进行新书写时往往是打着传说的幌子演绎人性。“白蛇传说”到了当代再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李碧华的《青蛇》记录了一场现代欲望纠葛,严歌苓的《白蛇》写了复杂人性在时代下的躁动。其中,严歌苓在创作中以个人体验作为出发点,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历史、中国传说熔铸于一体。这样的书写方式既能使中国读者在阅读古老传说中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又为《白蛇》翻译为英文并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埋下伏笔。严歌苓一直是一名富有进取精神的作家,她曾经宣称要“玩遍所有的叙事花招”[9]。作者在《白蛇》里玩的“叙事花招”显然是成功的,评论家与普通读者都意识到《白蛇》的价值不可低估。
无人知道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完成。时至今日,中国作家的探索仍在继续,或将如李杭育先生所预言的“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10]。中西方文化终会有一天完成交融。在这个发生交融的过程中,严歌苓作为一名自觉的推动者实在功不可没。
她的移民身份方便她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中西方两种文化,进而寻找两种文化间的契合点。她对“白蛇传说”的创造性改编足以体现她在寻找契合点上的成功。严歌苓以她的创作试验推动中国文学发展、促进中西方文化融合,对中国当代文坛发展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52.
[2]严歌苓.白蛇[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田汉.田汉戏曲选:下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56.
[4]朱崇科.戏弄:模式与指向:论李碧华“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J].当代,2002(7):130.
[5]严歌苓.错位归属[M]//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94-195.
[6]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45.
[7]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91.
[8]张琼.此身·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J].华文文学,2004(6):66-68.
[9]沿华.严歌苓 在写作中保持高贵[N].中国文化报,2003-07-17(01).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81.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