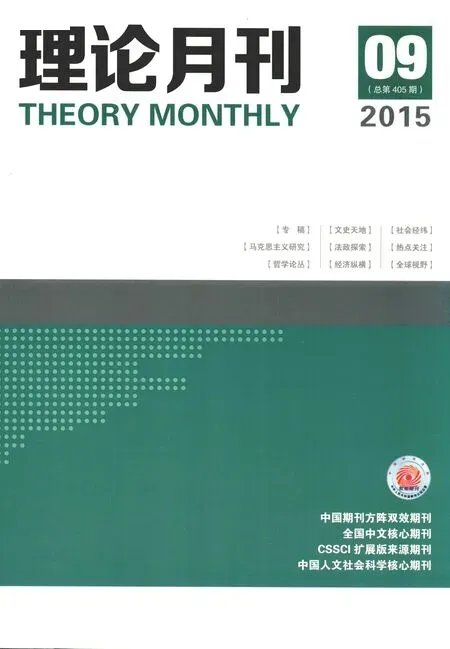集体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及其规制路径分析
□赵宸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集体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及其规制路径分析
□赵宸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近年来集体腐败成为我国一种高发的腐败形态。集体腐败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合作的行为模式,它的形成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不可分离。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传递信息形成的行为约束,其形成与社会中的文化、传统不可分离。非正式规则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实践效果。信任和服从是集体腐败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故对集体腐败的治理也应在制度设计时将对信任、服从等非正式规则的回应制度化、法制化。
集体腐败;非正式规则;信任;服从
1 引言
集体腐败又称窝案,指多名官员结成同盟,共同开展腐败行为,并将腐败收益归自己所有。近年来,集体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一种主要的腐败形态。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韩杼滨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窝案”、“串案”增多已成为我国腐败活动的新特点。[1]十八大后,我国针对腐败的查处进一步体现出腐败行为集体化的趋势。2013年一年,除中石油、铁道部两个大型集体腐败案件外,仅媒体就爆出了10多起集体腐败案件,涉案人数达数百人,个案的最高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元。[2]在这些案件中,行贿者、受贿者及其他参与人员的行为相互依赖,人际关系与权力地位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纵横交错跨行业、跨地区的腐败网络。[3]集体中的成员为规避风险,最大化自身利益相互绑定,订立攻守同盟,形成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共同利害关系。[4](P9)
集体腐败的危害不仅在于其零和博弈的特点无益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在于这种腐败行为导致内部监督统统失灵,使得权力这只老虎肆意妄为。集体腐败中,许多核心成员既是掌权者,又是监督者,如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5]为寻找保护伞,小团体往往主动渗透司法、纪检等专门监督机关,将监督人员拉入腐败网络。这种“执法者犯法,反腐者变腐”的局面很容易使民众将针对具体事件的不满转化为普遍性的信任危机,伤害政府的公信力。故而如何规制集体腐败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集体腐败的成因,目前学界多将之归结为法律的缺失,主张通过立法限制权力,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近年也有学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对集体腐败现象进行了分析,主张通过网络监督和加重刑事处罚对之进行规制。[6]本文认为,在我国有关法律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集体腐败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现有的社会条件中必然存在孕育集体腐败的制度基础。个体做出某种行为并非由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更多的是由于他处在怎样的环境。同理,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约束框架下有意识地选择了 “合作”腐败既不能简单的归于法律的缺失,也不能仅仅归责于中国看重“人情”。当前司法实践中,对集体腐败的查处方式已体现出对非法律层面的关注,但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本文希望利用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规则的研究框架对集体腐败的形成机制予以分析,对集体腐败的规制从理论层面进行探索,促进集体腐败治理的法治化。
2 集体腐败中的非正式规则
2.1制度与非正式规则
根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7](P3)个体层面上,这些约束减少了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使个体可以通过分析有关约束条件,在政治、经济或社会领域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国家层面上,这些约束会形成一个约束矩阵,决定社会中不同组织的行为方式,形成特定的社会治理结构等。[7](P7)诺斯的定义直白地将制度的对象全部涵盖了进去。具体而言,他将这些约束分为了三类: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正式规则是由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制定的,包括了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7](P65)非正式规则指人们在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无意识形成的约束,包括习惯、行为准则、思想意识等。[7](P50-51)它们多源于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传递的信息而非国家的强制规定,是制度的内在体现。[8](P47)实施机制通过影响契约执行的成本影响权利保障方面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对应的经济绩效。[8](P81-83)这三种约束共同作用,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制度,并决定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模式。
在这三种约束中,非正式规则是在人类长期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信念。它根植于群体的文化之中,赋予个体对社会行动与结果间联系的意识倾向性。[9](P34-35)非正式规则在长期作用中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由群体内部制裁约束(socially sanctioned norms)的行为准则,当人们形成遵从惯例的习惯时,这些惯例便会凝聚道德力量,形成信念。由于人们依据信念行事的成本较低,因此,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便容易产生依赖性。[7](P56)即使正式规则发生变化,相应的非正式规则也很难立即连动,从而导致改变后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间的紧张。[10](P351-352)也因此,若想将一项新的正式规则植入社会,相应的非正式规则必须改变。
2.2集体腐败与非正式规则
近年来,学界在分析集体腐败及其成因时,普遍认为现有法律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主张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加强惩治力度来抑制集体腐败的发生,这是一种对“正式规则”的理解。事实上,当正式规则的运行不尽如人意时,我们更加应当考虑法律法规的失灵是否与社会中长期形成的非正式规则有关。集体腐败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然而,人毕竟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行为模式的选择离不开社会环境因素。因此,从“非正式规则”角度分析人为什么会“合作”更为合适。
毋庸置疑,“信任”和“服从”是形成合作不可缺少的因素,也在集体腐败的形成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1信任。“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基于对对方行为意图的积极期望而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风险。”[11](P7)信任包括依赖与风险两个要素,前者指一方允许其行为选择被另一方的行动所决定;后者指如果另一方不合作会使信任者损失某些利益。[11](P6)在任何一个群体里,信任的建立都是合作的基础,而如何建立信任及建立信任的难易程度会受到非正式规则的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尚处于“自然秩序”(natural state)向“开放社会”(open access)过渡的阶段,政治关系具有不稳定性。[9](P27-31)在此情形下,人们往往习惯于通过熟人关系对政治关系进行巩固,规避风险。而“家”作为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几千年来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便是其体现。[12]在“差序格局”中,人们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他人与自己的熟悉程度对圈子进行划分,以血缘、地缘、业缘作为重要的连接方式。对“自己人”表现出极强的信任,对非自己人则表现出较强的不信任。[13](P69)
基于“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人们往往对自己的亲人最为信任。当亲人遇到困难时,个体多不问具体原因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亲人解决问题。这解释了集体腐败出现“家族化”趋势的原因,当亲人,特别是子女需要时,父母往往想尽一切办法给予帮助,其中当然也包括利用自己的权力提供方便。而公职人员如果主动滥用权力换取收益时,也往往相信自家人不会出卖他,而将自己的血亲、姻亲等一步步编织进腐败网络。近期被查处的大量集体腐败案件多体现了这种特点,如中石油窝案中的周家,茂名官场窝案中的原市委书记罗家。[14]这些家族腐败案往往一人当官全家受益,一旦案发也是一损俱损,全家落马。
在亲人圈以外是熟人圈,熟人圈多以老乡、同学这些有共同生活经历的人为主。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天然的亲近感,并在长期互动中不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好感,如通过拜访、问候,馈赠礼物等方式增进感情。在此基础上,双方采用人情法则相处,即当对方遇到难题时,给予对方帮助赠予人情。[6](P187)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这种“报答”的意识促使人情收受方建立了在人情的施予方以后有需要时给予相等或更多帮助的观念。这种社会性的观念也使得不按照人情法则行事的人遭到其他人的谴责和孤立,而通过人情法则考察的双方关系则会更近一步,从工具性的交换关系逐渐上升为情感性的交换关系。[4](P10)当双方关系变为情感性时,双方的关注点也会从“利害”上升为“责任”,将信任和合作作为一种义务,双方的交换关系也得以稳定。[4](P10)
在集体腐败网络中,围绕着公职人员及其亲属这个最内层核心的多是老乡、同学等熟人好友。他们首先通过地缘、业缘等与公职人员建立联系。然后通过长期相处,与公职人员通过人情法则进行利益交换。通过一次次符合人情法则的相处,他们与公职人员关系愈发紧密,最终实现拟亲化,与官员“称兄道弟”,发展出人际信任关系。在2007年著名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中,郑的一名福建老乡也是广州某药企老总,在经济上给与郑极大的资助,让在北京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的郑筱萸放心地花钱活动官职。而当上国家药监局长后,郑筱萸投桃报李,在企业的新药批文、注册审批等方面给予了相应的回报。[15]
在熟人圈之外还有一层陌生人圈,在中国社会,人们对陌生人往往表现出极强的不信任。[16](P143)与陌生人的交往多是即时的公平交换,一分钱换一分货,不可延期支付。从陌生人变成熟人第一步便是需要一个熟悉的中间人,通过这个中间人的斡旋,两个陌生人方能建立最基础的弱关系。然后的相处,便与熟人圈的相处模式相同了。只是这种相处需要经过更长时间、更多次互动才能完成拟亲化的过程。在集体腐败案件中,大部分的官商勾结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先通过别人的介绍,公职人员与商人相识。然后,权力掌握者利用自己对信息的占有优势,充当中间人,牵线搭桥以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通过一次次的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形成稳定的联盟。以铁道部窝案中商人丁书苗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关系为例,丁书苗1997年通过时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局长罗金宝介绍认识了刘志军,与刘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在之后的相处中,二人建立了良好的交换关系。刘试图将丁的企业作为自己的仕途基础,为自己提供资金支持,而丁为刘花钱也十分大方。最终,刘利用职权干预了多个项目的招标,帮助丁获得总额1700多亿元的项目,自己也从中收取了巨额好处。[17]
在上述三个圈子中,熟人和陌生人实现拟亲化被纳入自己人圈子的时间成本高,风险也较高,但是集体腐败中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关键元素。因此,集体腐败圈子的最终确立通常是个缓慢的过程,但其一旦形成,便具有了与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相仿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处于网络中的个人利用权力创设寻租机会,利用网络中自己人易于协调与沟通的特点不断汲取利益,并在小圈子内分享,使网络中的自己人得到情感和利益上的满足,激励各主体进行下一轮寻租行为。[6](P187)通过不断的互动,严密的腐败关系网络建立,圈子内的人互相认同与接纳,圈子外的人则受到排挤、冷落与提防。
2.2.2服从。集体腐败中,并非所有人自始就积极主动地参与腐败行为,很多人是被动涉入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从事腐败行为,未准确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当腐败行为扩散至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处腐败之中时,他们尽管不赞成腐败行为,但已很难退出,被迫继续卷入其中。[18](P97)这一现象表明,自身的价值观不是社会生活中决定人们行为的唯一要素,存在着其他多种力量冲击着人的价值观,导致人们做着自己并不赞同的行为。[19](P7-8)其中,“服从”这一非正式规则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使得父权的权威思想根深蒂固,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演化为对权威的服从。[20](P174)人们每到一个场合都会通过打听他人的信息,对地位进行排序,进而确定是否存在权威。一旦确认,人们便会在行为上对权威产生依赖,进入一种“代理状态”,当权威发出指令时,人们认为自己对他负有义务,是执行其意愿的代理,同时由于自己处于代理状态,对自己行为的内容便不用承担具体的责任。[19](P148-150)
群体效应也促进了“服从”的产生。中国人在行为上对他人的意见、看法、标准等十分敏感。人们日常习惯打听别人的观点,特别是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据此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不标新立异。总体而言,人们更倾向于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致,社会顺从度很高。[20](P175)
集体腐败案件中,权力碎片化导致的时间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得很多公职人员出现理性的无知,盲目的服从上级的命令。由于收集与工作有关的完整信息成本过高,公职人员并无动力也无能力获取组织运作所需的全部信息。收到上级指令时,个人往往觉得自己只需听话,其他都不用过问。[21](P71-72)加上行政机关的运作存在结构距离,即由于组织中各层级与职能分割明确,组织中各成员只需负责总任务中的一小角。[18](P99)各成员对这一小角的工作与最终后果间的距离被拉大,使他们难以对组织目标进行切实思考。成员们习惯于以机械化的方式完成工作,这种对规则的强调,却使得规则变成了目标本身,导致了目标的替换,间接的培育了腐败的温床。[21](P72)
在这样的情形下,当腐败行为累积到个体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后果时,由于个体已在腐败行为中投入了时间、努力等成本,当事人更加容易被腐败束缚,从不自觉的涉入腐败转变为主动腐败。[22](P126)即使个体希望退出腐败集体,在“服从”思维的作用下,有效的退出也非易事。①当然,个体的这种选择并非中国独有,外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在我国,由于人们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在行为上更倾向于选择服从而非退出。有关内容可参见Miceli.M.Near JP.What makes whistle blowers effective?--Three field studies.Human Relations,vol.55 2002。(首先,同事、上级往往会给个体施加巨大的压力,告诫个体小集体所形成的规则便是正当制度。如果个体的反抗表现的较明显,团体也会对该个体实施排挤或者打击报复。在此情况下,个体忌惮于自己的前途可能受到不利影响而不得不继续服从于集体的行动。其次,由于个体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法接受“大家都说我错了、不好”的情形,当自己所想与集体产生对立时,个体往往对自己产生不信任,倾向于服从集体。再次,当个体继续从事腐败行为时,他们会认为因为自己不得不听命行事而不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一切有领导担当。)当然,在此过程中,个体会由于行为本身的不道德性而产生紧张感,他们常会通过躲避来屏蔽自己行为的感知后果,弱化心中的负罪感,如:少收他人一些财物、帮别人办事时更加用心等等,他们也会通过自我欺骗来减轻心中的不安,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很多腐败分子都曾经高举“反腐”大旗,一边强调廉洁、法治的重要性,一边进行腐败行为。[19](P178-179)
总之,在集体腐败中,由于理性无知的作用,个体最初对于上级的指令总是习惯性的遵守。即使个体感觉到体系的目的可能具有违法性或破坏性,令个体对权威或上级的指令有所怀疑,个体也多是在内心进行痛苦的自我怀疑,极少会做出破除体系的行为。习惯性的服从令团体运行的某些规则上升为集体内部的一项制度,使个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腐败行为嵌入到集体行为规则中,使之成为组织内部的惯例。[21](P69)当个体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时,其已被集体腐败束缚无法退出,只能越陷越深。
3 集体腐败的解决方式——从非正式规则入手
当我们面对腐败问题时,常常想着从正式规则出发,以笼统的立法解决问题。在这个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法律当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法律并非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如果法律忽略了非正式规则及其成因,那么极有可能创造一个“法律很多但秩序很少的世界”。[10](P354)对于集体腐败亦是如此,既然“信任”与“服从”对个体选择“合作”腐败有着深刻的影响,对集体腐败的治理也不妨从这两个角度着手,选择针对这些非正式规则的方式入手。
第一,破坏连接点,解决内部监督失效的问题。如前文所述,腐败网络很多由地缘、血缘或业缘等关系相连接。针对这种连接形式,期待所有公职人员有意识地忽略这种关系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破坏其结点却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采用公职人员轮岗、一把手空降、异地任职等措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地缘、业缘的连接,防止腐败网络的形成。同时,当内部监督可能因腐败网络的形成而失灵时,可以引入外部力量突破这一网络,借助自媒体平台引入民众监督便是可行的方法。自媒体平台是一种近距离且互动性较强的介质,它可以显著降低民众参与监督的成本,使这种免费外部监督的广泛性和动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民众对权力的运行进行评议,对权力腐败进行批评、抗议和控诉,这种信息的零距离传播和公开的互动性使官方无法不理会民众公开的信息,从而既可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也可震慑潜在的腐败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集体腐败内部监督失灵的困境。[23](P237)
第二,梳理权力流程,使公职人员对自己的职责有整体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公职人员最初无意识的涉足于腐败很多是与权力碎片化有关的理性的无知而产生的。尽管分权有利于权力的制衡,但随着专业化加深,分权可能导致权力的碎片化。公职人员可能无法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或是行为的后果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期限方能显现。对于此类人群,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陷入腐败之后,短期的退出成本往往高于继续腐败的成本,使得他们多拒绝主动退出。因此,避免此类人群深陷集体腐败深渊的有效措施是避免其第一步无意识的介入。针对这种情况,制定完整清楚的权力流程图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权力流程图以图形的方式将权力的运行程序、行使依据、承办岗位、职责要求等内容表现出来,这种简单明确的图示可以使公职人员了解完整的权力运行模式,定位自己所处的环节,了解自己的行为后果,从而避免“无知”的涉入腐败。
第三,修改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款虽然在文字上赋予了公务员抗命权,但在实践中却极有可能加剧下级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首先,法律没有规定当公务员认为上级决定错误时向哪一级的上级提出意见。从法条语义推断,这里的上级很可能是下命令的直接上级。此种情形下,由于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和晋升很大程度上与直接上级对他的主观评价密不可分,而提出异议却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出于自己日后晋升的考虑,下级公务员并无提出不同意见的动力。其次,法律没有规定公务员提出异议的方式,导致实践中下级公务员就算提出异议,也极易被上级否认,导致上级向下级推卸责任。[24](P31)再者,条文中提到“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关于“明显违法”该如何界定?如果是上级命令与法律规定明显冲突的情况较容易处理,公务员可以意识到“明显违法”。[25](P53)但如果命令针对的事项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性或只是庞大计划中的一小个环节,下级无法准确的判断上级的决定是否“明显违法”,也就只能依命令行事。而当违法结果产生时,上级可能以此违法后果威胁下级,使得下级不得不继续听命于上级。可见,尽管法律赋予公务员抗命权,但实践中因为规定不明确,抗命权未必能起到有效作用。针对这一点,可以通过细化公务员法第54条的规定,明确抵抗权的行使方式,如参照德国规定,公务员对上级指令有异议时,可向更高一级上级而非直接上级反映。[26](P54)同时,本条亦可增加公职人员如果事后知晓上级决定违法后的退出和减轻责任机制,使得非自愿涉入腐败的公职人员知情后可以退出甚至举报,从而有效的瓦解集体腐败。
4 结语
诚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权力与利益间形成粘连,提供了腐败滋生的土壤。而在中国社会信任与服从的非正式规则的影响下,集体腐败更是成为了近年来的严重问题,阻碍了我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依法治国,规制集体腐败势在必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为腐败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指明了方向。对集体腐败的规制也应建立在法治和制度的框架之下。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我们应当注意人们行为模式的选择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信任和服从这两种非正式规则在集体腐败行为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信任的作用使集体腐败的圈子呈现出以亲人圈为核心,熟人圈、陌生人圈环绕于周围的混合网络结构。服从的作用使许多个体从无意识的涉入腐败转化为被动嵌入腐败网络甚至主动参与腐败,从而巩固集体腐败的网络。因此,在对集体腐败的治理中针对这两项非正式规则对症下药,能够破坏集体腐败生长的土壤,强化反腐败法律治理的效果。
本文所提出的集体腐败非正式规则层面的分析既非认为非正式规则是导致集体腐败的唯一因素,也非主张只有通过改变非正式规则方能对集体腐败进行治理。本文只希望为集体腐败的规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成因,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之进行规制。可喜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注意到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在对集体腐败的查处中,实践中多从公职人员亲朋好友及工作中的上下级入手调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能进一步将对信任和服从这两项非正式规则的回应系统化、制度化,不仅有助于对集体腐败的惩处,更能有效的防止集体腐败。
[1]韩杼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EB/OL].(2006-02-22).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06-02-22/ 00018-292.html,2014-12-21.
[2]王选辉.357官员卷入贪腐“窝案”[EB/OL].(2013-09-16).http://www.fawan.com.cn/html/2013-09/16/ content_455058.html,2014-12-21.
[3]唐利如.腐败网络:特征、类型与机理——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腐败及其治理[J].兰州大学学报,2011,(1).
[4]陈国权,毛益民.腐败裂变式扩散:一种社会交换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2013,(2).
[5]王妹.24省份书记兼人大主任[EB/OL].(2013-02-07).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2/07/ content_409760.htm?div=-1,2014-12-21.
[6]汪明亮.人际关系视角中的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分析[J].现代法学,2011,(2)
[7]〔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8]〔美〕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M].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美〕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10]〔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1]Rousseau,D.M.,Burt,R.S.,Sitkin,S.B.,&Camerer,C.(1998).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 view of trus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3,393-404.转自:姚琦,马华维.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当代信任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
[14]新华社.亲人协作便于互相渔利——透视家族腐败案件频发的根源[EB/OL].(2014-06-28)[2014-12-23].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6/28/ c_1111363965.htm.
[15]赵何娟.郑筱萸腐败路线图:负“人情债”起家“结团”寻租[EB/OL].(2007-04-10)[2014-12-23].http: //www.china.com.cn/news/txt/2007-04/10/content_80 93660.htm.
[16]邹宇春,敖丹,李建栋.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2,(5).
[17]何春梅.丁书苗被公诉 涉嫌非法经营和行贿[EB/ OL].(2013-9-7).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3-09-07/100579358.html,2014-12-23.
[18]薛刚.“涉入”与“知情”:集体腐败道路上分离的两点[J].政治学研究,2010,(1).
[19]〔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M].赵萍萍,王利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20]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1]张鹏.我国公务员集体腐败问题研究——基于过程模型的视角[J].政治学研究,2011,(5).
[22]Donald Palmer,Extending the process model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42,2008.
[23]吕世伦.社会、国家与法的当代中国语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4]贺日开.公务员法中的制度创新与疏漏——兼与何颖教授商榷[J].中国行政管理,2006,(12).
[25]刘金荣.公务员不服从的行为研究[J].理论研究,2006,(2).
[26]〔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M].朱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王友海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30
D630.8
A
1004-0544(2015)09-0163-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FX005);江苏省博士计划项目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赵宸(1986-),女,江苏南京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