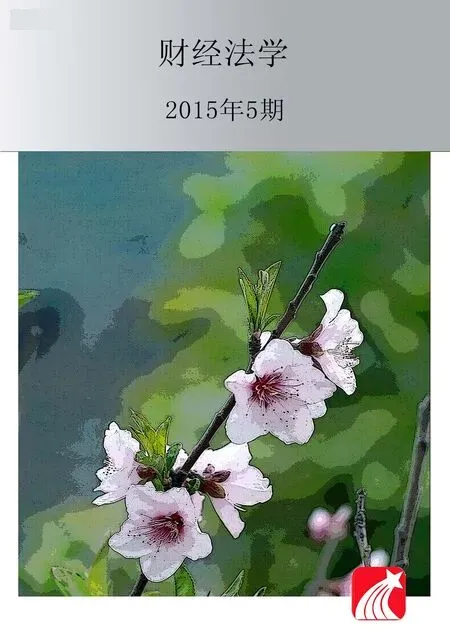《合同法》第122条的理解和适用
夏昊晗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官方的权威解释和学者的主流意见均一致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解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问题的请求权竞合原则。[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在解释第122条时明确以“请求权竞合”作为标题。但是,该条究竟是采纳请求权自由竞合说还是请求权相互影响说,则不无疑问。韩世远教授认为该条采纳的是请求权由竞合说,而并非请求权相互影响说。[1]自文义考虑,这种观点可资赞同。值得注意的是,赞同请求权竞合的学者几乎都主张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进行一定限制。[2][3][4]然而,学者只是笼统表明了限制的必要性,而对于应该如何合理限制竞合,则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失之简略。写作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探讨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合理限制责任竞合之下受害人的自由选择权。然限制自由选择权的前提是允许请求权竞合,因此,作为先决问题,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侵权责任扩张背景下应否继续坚持请求权竞合原则。
一、侵权责任扩张与请求权竞合原则之坚持
当代法律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传统上由合同法调整的生活领域日益被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在侵权法的不断侵蚀下,合同法所独占的领地正不断萎缩。在此背景之下,有论者发出了“契约已经死亡”的惊世之语。[5]这种说法虽然有过于夸张之嫌,但是却生动地表明了侵权责任扩张之发展态势。具体到我国,诚如王利明教授所言,尽管《侵权责任法》第2条试图将是否保护债权作为区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的界限,但由于采取了开放式保护民事权益的立法技术,导致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处于一种不断扩张的态势。[注]关于侵权责任法扩张的具体表现,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以侵权责任法的扩张为视野》,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107~109页。
众所周知,各国立法是否采取请求权竞合原则与其侵权法保护范围之宽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法国奉行禁止竞合原则,即合同关系的存在往往排除侵权责任,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民法典》采用的是比较宽泛的一般侵权责任条款,责任范围比较笼统和概括,如果允许竞合,则合同法将被侵权法完全侵蚀。[6]而德国则奉行允许竞合原则,采取请求权竞合说,即基于合同的请求权和基于侵权的请求权各自独立,互不影响,受害人(债权人)得择一行使,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德国民法典》没有采取如同《法国民法典》那样大的一般条款,而是使用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致使侵权法保护的法益范围十分有限。在此情形下,如果禁止竞合,将导致合同关系的存在不是增强而是弱化了一般法律保护义务,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7]
在我国侵权责任大为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即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合同法》第122条确立的请求权竞合原则。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合同法》制订当时我国侵权法制的状况。当时尚没有专门的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之规定首先体现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该条对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范围做了抽象概括式规定,与法国的一般条款模式极其类似,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因为《民法通则》的宽泛规定而仿效法国法禁止竞合。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比,现行《侵权责任法》可以说在保护范围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超越,只是将部分保护范围予以较为明确的揭示或作为特殊侵权行为予以特殊规定。因此,我们今天似乎也没有理由改弦易辙。更为重要的是,责任竞合是客观存在的生活现象,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在成立要件、举证责任、赔偿范围、诉讼时效等方面亦存在重大差异,与禁止竞合说和请求权规范竞合说相比,请求权竞合说允许责任竞合,赋予受害人自由选择权,这显然有利于更为周全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也更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正是因为如此,《合同法》通过后,虽然第122条备受指摘[8][9],但是主流观点依然认为应该予以坚持。[注]关于采取请求权竞合说的合理性的详细论证,参见参考文献[1][2][4]。
二、请求权竞合原则的缺陷分析
如上所述,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请求权竞合原则,但是也应该正视请求权竞合原则的内在缺陷。请求权竞合原则的内在缺陷大抵主要体现为如下两方面:一方面,请求权竞合原则虽然允许受害人自由选择以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主张权利,但是受害人一旦选定,则只能以一种责任为请求权基础,或者为违约责任,或者为侵权责任,不能同时主张,这就是我国《合同法》明确的“择一请求”原则。“择一请求”的限定在一些情况下将导致受害人的利益不能获致全面的保护。比如,某甲购买一台电视机,其后因电视机爆炸,某甲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花费医疗费若干。按照《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某甲要么根据买卖合同要求卖方赔偿电视机的损失,要么根据侵权责任法要求卖方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无论选择以何种方式主张权利,某甲都不能够完全挽回自己的损失,因为合同法保护的是均衡性利益(quivalenzinteresse),根据合同法无法要求赔偿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注]需要注意的是,崔建远教授认为合同责任亦可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参见崔建远:《精神损害赔偿绝非侵权法所独有》,载《法学杂志》 2012年第8期。但主流观点则持反对意见,于此,可以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以侵权责任法的扩张为视野》,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114-115页。,而侵权法保护的是完整性利益(Integritätsinteresse),根据侵权法无法要求赔偿电视机本身的损失。这个例子表明,本来意在周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请求权竞合原则在特定情形下有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根据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基于违约和侵权的两个请求权独立并存,在成立要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方面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但是,如果严格遵循,在特定情形下有可能偏离特定的立法目的或违背私法自治的精神。前者体现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有可能导致合同法规定的特殊责任限制或诉讼时效的规定形同虚设,使得法律之特殊目的因当事人的选择而落空,违背了立法者的原意。[10]后者则表现为,请求权的竞合有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双方通过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丧失意义。[11]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不做深入讨论[注]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涉及的是产品自损的赔偿问题,与请求权竞合的限制牵涉不是很大。按照传统见解,侵权损害赔偿不包括产品自损在内。至于这种见解合理与否,此处存疑,暂且不表。,下面将着力讨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三、请求权竞合原则缺陷之克服
请求权竞合原则的缺陷已如上所述。问题是,该如何克服乃至消除这种缺陷呢?下面首先分别介绍德国法中的处理方式以及我国学者和司法判决的处理意见,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具体的类型化分析。
(一)德国以“请求权相互影响说”作为修正手段
在德国法中,由Dietz教授提出的“请求权自由竞合说”[12]在处理责任竞合问题上居于原则性的主导地位。[注]韩世远教授认为德国法采取的是“请求权相互影响说”(参见参考文献[1])似有不妥。德国学说和司法虽然一致赞同依法律规范之意旨进行冲突利益的价值衡量,在特定情形下将合同法中的特殊规定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由此观察,德国法似乎采取的是“请求权相互影响说”。但是,必须注意到,“请求权相互影响说”于此只是起到了部分修正“请求权自由竞合说”的缺陷的作用,并没有撼动“请求权自由竞合说”的原则地位。可以说,“请求权自由竞合说”是原则,而“请求权相互影响说”是例外。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例外对原则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请求权自由竞合说”的理论基础,因为既然承认两个请求权的互相影响,则等于变相否认了两个请求权的独立性,而这正好是“请求权自由竞合说”的核心所在。但是这种对逻辑上的一以贯之的破坏依然不影响德国学术和司法对这种原则加例外方式的认同,因为这种方式更为灵活地解决了责任竞合带来的难题。Vgl.Katzenmeier, Christian, Vertragliche und deliktische Haftung in ihrem Zusammenspiel, Berlin 1994, S. 157.但是面对完全自由的责任竞合所导致的问题,德国学说和司法界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放弃了对于严格的逻辑一贯的遵循,在承认“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原则地位的前提下,吸收“请求权相互影响说”的合理成分,对请求权的自由竞合做了一些例外处理。具体方法则是,根据法律之规范意旨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价值衡量,在必要的时候将合同法中的有关特殊规定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这种例外主要表现为将合同法中的责任限制条款和短期诉讼时效以及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适用于侵权责任。[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责任竞合的场合,德国法没有出现将侵权责任的规定适用于与之竞合的合同责任的做法,这可能是因为侵权法规定的是一般保护义务,而合同是特殊保护义务。此外,德国法也在极其个别的情况下明文禁止竞合。以下申述之。
立法明确限制竞合的情形比较罕见。《德国商法典》第434条第1款和第436条第1句将托运人和收货人针对承运人的基于货物丢失或毁损以及迟延交货而产生的侵权请求权置于第426条规定的和合同约定的责任限制之下。[注]《德国商法典》第434条第1款规定:“对于托运人或收货人因货物丢失或毁损或因超过交货期限而对承运人享有的合同外的请求权,亦适用在本节中和在货运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和责任限制”。第436条第1句规定:“因货物的丢失或毁损或因超过交货期限而对承运人的人员中的一人提出基于合同外的责任的请求权的,该人也可以援用在本节中和在货运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及限制。”《德国航空运输法》第48条第1款亦有类似规定。[注]《德国航空运输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航空旅客)针对航空运输承运人基于其他请求权基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在本节规定的条件和限制的前提下方得行使之。”在涉及运输合同的情况下,立法明确限制竞合的合理性在于:德国的运输法遵循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比较严格的责任之下,德国法只要求承运人对具有典型性的运输合同风险承担责任。如果托运人和收货人在此之外可以根据遵循过错责任原则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要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则将使立法对于承运人的责任限制成为具文。[13]
当合同法将债务人的责任限定于故意、重大过大、违背在处理自己的事务中通常所应有的注意义务的场合,即合同法降低债务人的注意程度的时候,德国法主张,与合同责任竞合的侵权责任也应该相应地受此限制,其理由主要在于,如果侵权责任无需受此限制,则合同法规定的责任限制在实际上将只有极小的作用。[14]这种责任限制主要见于《德国民法典》规定的赠与人责任(§521)[注]《德国民法典》第521条规定:“唯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可以归责于赠与人。”,出借人责任(§599)[注]《德国民法典》第599条规定:“唯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可以归责于出借人。”,受寄人责任(§690)[注]《德国民法典》第690条规定:“寄托被无偿地承担的,受寄人只须就其在自己的事务中通常所尽的注意承担责任。”。此时将合同法规定的责任限制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的合理性在于:这些合同是无偿合同,合同法为鼓励这种无偿行为,为赠与人、出借人和受寄人设置了较一般情况下低的注意义务,如果不将这种限制适用于与合同责任竞合的侵权责任,则立法者通过这种规定意欲实现的法政策考量将无法实现。但是,德国学术界对于这种责任限制在侵权责任中的适用前提尚存有不同认识。以《德国民法典》第521条规定的赠与人责任为例,主流意见认为,第521条规定的责任限制不仅针对赠与义务的不履行,而且也适用于与赠与有关之保护义务的违反,只是在违反保护义务的场合,保护义务的违反必须与赠与之标的存有内在的关联,否则第521条规定的责任限制不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15]比如,如果受赠人在去赠与人家中取赠与物的时候因赠与人的楼梯瑕疵不幸滑倒而受伤,那么对于受赠人所受之身体伤害,第521条规定的责任限制不适用于侵权责任请求权。[16]而少数派意见则认为,第521条规定的责任限制仅仅针对赠与义务的不履行,不适用于与之相关的保护义务的违反。[17]
在诉讼时效方面,德国法区分不同情形,将合同法中规定的特殊时效规定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德国民法典》第195条和第199条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请求权的发生和债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但自请求权发生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0年,在人身伤害的场合,最长不超过30年。在此之外,《德国民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比较短的特殊时效,主要涉及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租赁合同、使用借贷合同。如《德国民法典》第438条规定:在瑕疵履行的场合,买受人行使其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自买卖物交付时起开始计算,第634a条为承揽合同关系进行了同样规定。第548条规定:在使用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因租赁物变更或毁损而享有的赔偿请求权,经过六个月而完成消灭时效,自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时开始计算,承租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在租赁关系终止后,经过六个月而完成消灭时效,第591b和第606条分别为用益租赁合同和使用借贷合同做了同样规定。在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中规定短期时效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快速地了解合同关系,使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尽快确定;而在租赁关系和使用借贷关系中规定短期时效的目的在于保护承租人和借用人,其合理性则在于,在租赁物或借用物发生变更或毁损时,出租人和出借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般能够发现,而且,在经过很长时间后,租赁物在交接时的实际状态已经很难确定。[18]德国司法实践将《德国民法典》第548条、第591b条、第606条规定的短期时效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与此同时,认为第438条和第634a条规定的短期时效不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19]这种区别处理虽然偶尔也受到批评,但得到了学术界主流意见的支持。这种区分处理的合理性在于:在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中,因为瑕疵履行导致的对受害人其他权益的损害有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生,如果统一适用短期时效,则买受人的利益无论根据合同法还是侵权法都将得不到足够的保护。[20]而在租赁合同和使用借贷关系中,由于租赁物的改变或毁损通常都构成所有权之侵害,如果不适用短期时效,那么合同法规定的短期时效将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作用。这样处理,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租赁物和出借物变更或毁损的情况下,债权人通常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现。[21]有些学者提出将第438条规定的短期时效也适用于侵权责任,不过限制于财产损害,如果涉及人身损害,则不扩张适用。[22]但是这种区分没有更强的说服力,因此遭致主流意见的坚决反对。[23]
在合同约定责任限制(免除责任或限制责任条款)的情况下,德国主流观点认为这种责任限制并不一定必然适用于侵权责任。[24]只有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责任限制包括侵权责任在内的这种意图足够清楚和明确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此认为。[25]因此,合同双方合意约定之责任限制是否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实质上是个合同解释的问题。
(二)我国学者意见和司法实践
在坚持“请求权竞合说”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的主流意见在处理责任竞合问题时的态度与德国法的处理意见非常接近。[注]之所以如此,笔者愚见,王泽鉴先生对于德国法的介绍在此起到很重要的桥梁作用。王泽鉴先生认为:“依请求权竞合理论,债权人原则上固得自由选择侵权行为或契约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唯为顾及法律对契约责任所设的特别规定,其侵权责任的成立应受限制。”参见参考文献[10],第83页。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为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应允许债权人就请求权的行使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特别约定时,应依特别规定或特别约定。这样,既不与立法目的相违,又尊重了当事人双方的意愿。”[26]对于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王利明教授以无偿保管人的责任为例加以说明。[4]崔建远教授亦持有类似主张,他认为,“如果法律直接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只能产生一种责任,排除责任竞合的发生,那么就应该遵守法律的这种规定”。并进一步指出,“即便法律没有明文,就其立法目的应予限制责任竞合的,亦应限制,”并以无偿赠与人之责任限制为例展开说明,认为在无偿赠与的场合允许竞合,则《合同法》第191条规定的责任限制就形同虚设了,“为了贯彻法律宽恕无偿奉献者的精神,应该优先适用合同法,限制竞合”[2]。 在目前所见的学者当中,傅鼎生教授对于请求权竞合限制的论述最为全面,他将请求权竞合限制分为背离立法目的和违背私法自治两种情形,前者包括合同法规定的特殊责任限制和短期时效的适用,后者则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27]这已经是与德国法完全相同的处理方式了。
值得注意的是,韩世远教授认为我国《合同法》采取“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并认为“请求权相互影响说”既然承认两个请求权的相互作用,则事实上已放弃两个请求权独立并存的概念。[1]由此观之,则不难推断出,韩世远教授是反对将合同法中的特殊规定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的,也正是如此,对于《合同法》第374条规定的关于无偿保管人的责任限制是否适用于侵权行为的问题,韩世远教授认为“殊值怀疑”[1]。当然,韩世远教授也提出,“当法律明确排除责任竞合时,则从法律”[1]。固守“请求权自由竞合说”,拒绝对之进行适当修正,显然无法有效地解决请求权完全自由竞合所带来的难题。
此外,以张新宝、刘士国、汪世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主张在医疗责任、产品责任、交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等特殊侵权行为领域排除合同责任的适用,即在此情况下完全排除责任竞合。[28][29][30]这种主张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法院在审判该类案件时倾向于按照侵权责任来处理问题。这种主张的实质其实已经是放弃请求权竞合原则,改采偏向于侵权责任的“法条竞合说”。因“法条竞合说”具有显而易见的弊端,这种主张和司法实践遭致王利明、崔建远和韩世远等教授的明确批评。[2]
(三)具体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德国法的处理办法和我国主要学者的意见,下面结合我国立法的规定,按法律明确限制竞合的场合、有悖立法者价值预判的场合、有违私法自治理念的场合进行具体的类型化分析。
1.法律明确限制竞合的场合
就笔者所见,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限制责任竞合的明文规定。在未来的立法中,是否有必要针对一些特殊类型的合同限制责任竞合,此处不做讨论。
2.有悖立法者价值预判的场合
在责任限制方面,如同德国法一样,我国《合同法》也明确将一些无偿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的注意义务予以降低,将债务人之责任限定在故意、重大过失的场合,如第189条规定的无偿赠与人责任、第374条规定的无偿保管人责任、第406条规定的无偿受托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限制是否应该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下面以无偿赠与人责任为例展开说明。我国有学者主张将这种责任限制适用于侵权责任,理由与德国并无二致,盖因赠与系无偿的,立法为鼓励此行为,为赠与人设定了较低之注意义务,如果允许竞合,则立法者的目的将落空。[2]在论及无偿赠与人责任之限制适用于侵权责任时,崔建远教授没有区分不同情形,似乎认为无偿赠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对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从《合同法》第189条的文义来看,立法者规定的这种责任限制应该只适用于赠与财产毁损、灭失的场合,也就是说立法者是将这种限制限定在损害均衡性利益的场合,而不包括损害完整性利益的场合。举例说明,某甲赠送其友人一辆轮胎存有安全瑕疵的汽车,虽然某甲并不知道轮胎存有安全隐患,但是如果某甲善尽了通常的注意义务本可以发现,则在发生车祸致使其友人人身伤害并导致汽车完全损毁的情况下,某甲固然无须赔偿汽车本身的损害,但是却需要赔偿其友人所遭受的人身损害。这种思考同样适用于无偿保管、无偿委托等无偿合同关系。
在诉讼时效方面,由于只有在侵权责任之诉讼时效较违约责任之诉讼时效长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去讨论违约责任的短期诉讼时效是否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所以首先要梳理一下我国立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看是否存在这种情况。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两年。与此同时,《民法通则》第136条为四种情形规定了一年的短期时效[注]涉及四种情形:(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问题在于,这一年的短期时效是否仅仅适用于合同责任,还是同时适用于侵权责任?傅鼎生教授似倾向于将《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的一年短期时效限制在违约责任的场合,尽管没有进行任何论证。[27]于此,便出现了违约责任适用一年短期时效和侵权责任适用两年普通时效的差异,在出现责任竞合时,当然便有必要将一年的短期时效适用于侵权责任。但是立法并没有明确将这一年的短期时效限定为仅适用于合同责任,无论根据文义解释还是根据第136条在《民法通则》中所处的位置,应该认为这一年的短期时效既适用于合同责任也适用于侵权责任。[注]笔者的这种意见也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的一封复函中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诉讼时效期间问题的复函》(1991年11月19日 [1991]法经字第160号)指出,因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引起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诉讼适用《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的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准此以解,则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诉讼时效适用上的困难。需要注意的是,鉴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处理的时间周期往往较长,《合同法》第129条将这种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规定为四年。这点与德国法有所不同,德国法为特定合同一般规定较短的诉讼时效。笔者认为,在发生责任竞合的场合,根据立法目的,应该将此四年时效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总的来说,由于我国立法没有像《德国民法典》一样对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租赁合同等规定较普通时效较短的诉讼时效,在责任竞合的场合,一般不存在诉讼时效适用上的困难问题。[注]至于是否有必要区分规定不同的诉讼时效,则为另一个问题,此处不做讨论。
此外,我国《合同法》第157条和第158条规定了买受人的检验义务和通知义务,这是《德国民法典》所没有规定的。[注]因为实行民商分立,德国于其《商法典》第377条规定了买受人的检验义务和通知义务。在买受人怠于检验或通知的场合下,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购买的标的物将被视为符合约定。一旦标的物有瑕疵并导致损害,买受人将丧失根据合同主张权利的机会。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买受人是否可以根据侵权责任主张权利呢?笔者认为,《合同法》规定买受人承担检验义务和通知义务只是针对购买的标的物本身的数量和质量状况,也即仅仅涉及买卖合同的履行义务,因此,即使买受人未及时进行检验和通知,如果嗣后因为标的物的瑕疵导致买受人其他财产和人身损失,则买受人也有权利根据侵权责任要求出卖人赔偿损失。
3.有违私法自治理念的场合
我国有学者主张,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合意约定的免责条款有效的情况下,从尊重私法自治的立场出发,应该禁止侵权责任的竞合。[31]这种观点可资赞同。但是,这种主张也可能面临两个问题:首先,侵权责任是否可以预先排除?其次,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是否包括侵权责任在内?
关于第一个问题:与合同法是任意法不同,传统上认为侵权法乃强行法。[32]这是否意味着受害人无权自由处分自己的赔偿权利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基于侵权行为而获取的赔偿权利在本质上依然是民事权利的一种,只要不违背法律和善良风俗,受害人作为权利所有人,自得自由处分。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上所述,德国法要求当事人双方的约定排除责任条款必须明确排除侵权责任方可将免责条款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但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排除侵权责任毕竟是不多见的现象,那么在没有明确约定排除侵权责任的情况下,该如何认定呢?这取决于对合同进行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一些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通常会发生竞合的合同关系中,比如,在保管合同、医疗合同、运输合同中,如果合同双方约定了免责条款,那么该免责条款应该适用于侵权责任,否则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将完全失去意义。而在那些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发生竞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场合,原则上应该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免责约定不包含侵权责任在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推断出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免责条款时将侵权责任考虑进去了。尚需注意的是,对于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应该根据《合同法》第53条和第40条的规定认定其有效性。[注]《合同法》第53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第40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如果免责条款是通过格式合同规定的,则对其应该严格解释。
四、与相关问题的区分
在探讨如何合理限制责任竞合的问题时,需要将其与下述三个问题区分开来,不宜混为一谈:一是,一些学者和法官将实质上根本不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作为责任竞合问题来处理。比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当事人之间事先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虽然不法行为人未给受害人造成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也只能按侵权责任处理。”[4]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自然无从谈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的是侵权法和合同法的界分问题。二是,在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选择以某种请求权为基础对其较为有利,而选择另外一种请求权则对其较为不利。此时,有学者和法官主张应该禁止竞合,只允许受害人根据对其最为有利的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比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因不法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的,当事人之间虽然存在合同关系,也应按侵权责任处理,因为合同责任并不能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人身伤亡、精神损害提供补救,只有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才能对受害人提供补救。”[33]这种观点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角度出发的思考,出发点是对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涉及的并非是否允许竞合的问题。从私法自治的角度观察,任何人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这种存在实质竞合且不存在合理限制理由的情况下,应该赋予受害人自由选择权。当然,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受害人因精神状态等原因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法官按照对其最为有利的请求权基础做出判决,或者在受害人是公法机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应该由法官限制受害人选择对其较为不利的请求权。三是,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出现不适当限制受害人请求权的情况,比如在医疗事故、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等领域,由于这些领域基本都被纳入特殊侵权行为的范畴,司法实践倾向于否定受害人的自由选择权、一律按照侵权案件处理。[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吴庆宝先生认为,特殊侵权行为不能发生责任之竞合,详阅吴庆宝:《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限制》,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第35页。在《合同法》出台之前,张新宝教授曾主张将医疗事故责任定位为侵权责任,在合同法没有专门规定医疗合同之前,不得采取责任竞合观点。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崔建远教授和王利明教授对此持批评态度,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5版,第313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扩张为视野》,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108页。在法律没有另行特别规定,且这种限制并无足够理由支持的情况下,突破法律的明文规定对责任竞合进行限制显然有违法治精神,殊非允当。[注]关于产品责任案件应该允许竞合的论证,参见张民、崔建远:《责任竞合的“收”与“放”——我国〈合同法〉第122 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关于医疗责任案件应该允许竞合的论证,参见艾尔肯:《论医疗损害赔偿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这三个问题涉及的其实都是现行法的正确运用问题,而本文所说的竞合问题,是指在存在实质竞合的场合如何合理限制受害人的自由选择权。
五、结语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采取“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产生竞合的情况下赋予受害人自由选择权,对于受害人利益之保护实属必要,应予坚持。唯“请求权自由竞合说”亦存固有之缺陷,我们理当吸收“请求权相互影响说”的合理成分,在个案中对相互冲突之利益进行价值权衡,在必要时,根据法律规范之意旨和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欲实现之意图,将合同法中的特殊规定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合同约定适用于与之竞合的侵权责任。如此,方可实现立法者之价值预判,并与私法自治之理念相契合。需要注意的是,责任竞合问题之处理并非单纯的法律逻辑之演绎,而是蕴藏着周全保护法益之法理。因此,在立法未明确禁止竞合的场合,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唯有在有足够理由支持的情况下,方可对受害人的自由选择权予以限制,这既是法治精神之要求,也为周全保护法益之所需。
此外,在解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问题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合理界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保护法益之区别,前者在于保护均衡性利益,而后者则在于保护完整性利益。唯有在合理界分的基础上,我们方能对责任竞合问题做出符合法理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