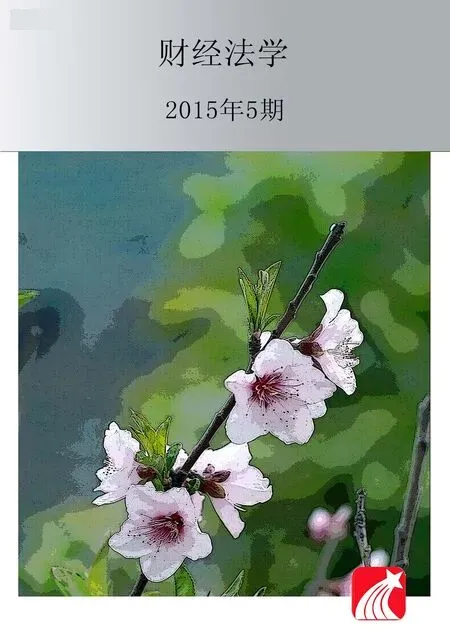中国民法总则起草(制定)座谈会综述
田 木
2015年6月27日下午,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中国民法总则起草(制定)座谈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法学》杂志社及台北大学的专家学者和部分来自实务界的特邀嘉宾等近30人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主要就“ 中国民法总则起草(制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民法总则制定中对商法的考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民法总则的起草——传承与超越
中国政法大学王卫国教授回顾了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谈到民法典的编纂是我国几代法律人民法精神的传承。自欧洲最新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制定后,欧洲大国都已有了自己的民法典。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制定民法典,这符合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中,民法典正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复兴的标志。他指出民法典一定是传承的产物,如历史上最有名的《拿破仑民法典》就是传承于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我们首先要有顶层设计,应站在民法通则的起点上走向民法总则,再走向民法典。如《民法通则》中的“联营”体现了当时起草者努力适应经济改革、与时俱进的精神,我们要传承这种态度与精神。我国历史上的立法精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及司法实践都要吸收到民法典中。另外,王卫国教授还认为,制定民法典不能只对现有法律做减法,否则会造成债法总论缺失,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制度缺失,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碎片化,商法定位模糊等问题。民法总则的制定要做加法,如进一步完善财产权,把无形财产纳入财产权范畴,将债法总论和人格权的基本内容引入民法总则,整合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为民事责任等。
中央财经大学陈华彬教授强调中国制定民法总则要把握新的社会容貌与新的时代特色。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编纂民法典都有其政治目的,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为了巩固大革命成果,实现拿破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1896年《德国民法典》是要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法律、一个民族的理想。亚洲的日本颁布《日本民法典》与中国清末编纂民法典,都是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挽救民族危机。今天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只有制定了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科学的民法典,才可以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攀登上了法律文明的最高峰,才可以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梦。另外,陈华彬教授还强调,民法典的制定应充分整合立法资源、整合学界共识,整合学界通说,积极吸纳制定《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大民事法律的经验。此外,民法总则反映的是人类在民事生活领域共通的规则,因此不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欧洲各国、日本及台湾的立法经验我们都应借鉴。立法技术上应采取潘得克吞模式,即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制定民法典。在民法典的体例安排中,应将人格权法列入民法总则,因为人格权法内容较少,单独成编或与其他编难以协调,且人格权法为人法,放在总则中可突出民法为人法的本质特征。从取得时效制度的本质与域外立法经验看,取得实效制度不应规定于民法总则中,应规定于民法典物权编中。
台北大学终身荣誉特聘教授陈榮傳针对中国法学会版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中的具体条文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提出民法总则与民法典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平等自治的理想,认为有价证券是依据法律行为产生的权利架构,所以不应将其归为民法总则中的“物”。“代理”不应单独成章,而应为“法律行为”章中的一节。此外,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不同于西方,如祭祀等问题虽然不能严格界定为某种法律关系,但未来民法总则或民法典都应予以考虑,民法典在传统法制、未来民法发展与整个法治架构之间应起到桥梁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杜颖教授就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是否编入民法典的问题做了探讨。她梳理了域外四种主要知识产权立法模式,即分离式(脱典式)、整体植入式、在民法典里只规范民法与知识产权连接点的连接式、仅将知识产权总则编入民法典的双重立法模式。她主张采取消极的连接方式,即在民法典中规定“有关知识产权,适用知识产权单行法的规定,无知识产权单行法规定的,适用民法典规定”。这种连接方式争议最小、最便捷,同时又兼顾了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殊性和前瞻性。
在特殊民事权益个体的保护上,中央财经大学朱晓峰博士将目光投向了胎儿利益保护。他对比分析了现有的民法典建议稿后,提出了分层设计、区别自然人与胎儿的权益保护安排。
二、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不足与完善
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建远教授指出目前民法通则对于意思表示的要素并未做出明确的阐释,民法总则应当明确意思表示的构成,这对于个案的处理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现行《民法通则》、《合同法》无法解决虚伪表示、隐藏行为等问题,民法总则对这些问题须积极关注。
崔建远教授指出,实务中对赌协议等相关设计是以一个或者几个相关联的法律文件统合一系列法律关系。按照单一法律关系的认识,如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虚伪表示、隐藏行为等都无法合理解决这种多重法律关系问题。希望我国民法典能超越德国民法的思考路径,给予这些商事法律关系特别关注、整体思考。在法律行为的解释规则乃至裁判规则的设计上都应有所创新。此外,对于需要经过行政主管机关批准而生效的合同,如果合同一方采取拖延等策略使行政主管机关无法审批,造成合同成立而不生效。他主张此种情况应适用《合同法》第45条,即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并希望民法典中对此予以明文规定。
《中国法学》杂志社编审朱广新研究员认为现行《合同法》存在一定的不完备之处。如《合同法》第50条关于越权制度的规定,本质上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解决的是法人越权行为效力是否归属法人的问题,因此该条应规定于民法总则的法人制度中,而不应规定于合同效力之中。现行法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不够完备,一些重要的意思表示类型,如真意保留、第三人欺诈、第三人胁迫等,虽然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一些判例,但现行法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他还强调,法律行为是践行意思自治的基本工具。从逻辑上讲,应该先考虑行为构成再考虑行为效果。而我国法律行为制度采取的是“重效果、轻行为”立法模式,即我国是以效力类型为纽带,对行为做出了分类规定。其弊端在于现行法框架中无法对意思表示的特殊性做出明确规定,无法顾及特殊法律行为的特殊法律效果。
中央财经大学武腾博士认为,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计中,应当从《合同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的棘手问题出发,结合比较法经验进行法律条文的精细化设计。
三、民法总则制定中对商法的考虑——分立或合一
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对比了域外民商事立法模式及我国民商事立法继受情况,指出我国现行法除《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主要民事法律外,还有《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信托法》、《海商法》等单行商事法律,我国现行民商法立法模式既非单一的民商分立模式,也非纯粹意义上的民商合一模式。
刘凯湘教授认为彻底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制度并不妥当,其会影响民法自身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法律适用也不便捷不实用。比如在民法典的法人制度中,法人设立如果包含所有民商事主体的设立,如股份公司、商事合伙的设立等,民法典条文就会太冗杂,损害民法典的协调。再如,一些商事原则如营业自由、盈利性原则等如果写入民法典也不妥当。另外,他还强调,民法与商法都是私法,具有大量相通之处,但商法相比于民法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因此“形分实合”是民法典应当采取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在民法典中加入一条“商事行为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无规定的适用本法”。此种立法规定在民商合一的基础之上,尊重商法的特殊地位,法律适用也会更加有效便捷。
中国人民大学朱岩教授认为,民法典是市民社会基本法律规则,侧重于所有权、合同等核心价值与基础法律制度的规定。商法是市场经济中商人间的法律,其最大特点是盈利性。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扩张,导致民法(尤其是财产法)商法化。近现代民法中关于弱者保护的功能逐步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商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肢解传统民法的作用。他尤其指出,商事单行法虽然概念、体系、思维源于民法,但与民法实质分立,其封闭式逻辑自洽缺乏与基本民事制度的沟通,如公司法与民法通则中的法人制度并没有直接承接关系,证券法中商事侵权与侵权法中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没有直接联系。此外,信赖保护原则在商法中地位更高,构成了对传统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的限制,因此民法总则中应当赋予商事活动当事人自主约定诉讼时效和惩罚性赔偿的权利,给予商事格式条款更为宽松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