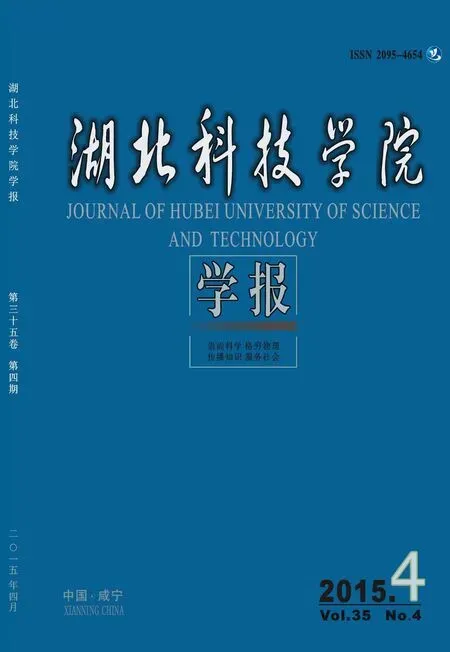证券投资基金模式下所得税扣缴制度探析
李 亚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1)
证券投资基金模式下所得税扣缴制度探析
李 亚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1)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后,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投资相关所得税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而这一模式的确立,使得长期以来证券投资基金所得税扣缴制度中被投资企业的扣缴股息、红利、利息所得的做法不仅不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而且更是与扣缴义务成立的基础及扣缴制度设定的合理性依据相冲突。而由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替代被投资企业履行相应扣缴义务,则可以解决原有扣缴制度中的不合法及不合理的问题。
证券投资基金;扣缴义务;所得税
一、被投资企业扣缴义务人地位之合法性审查
考察被投资企业扣缴义务设立背景,该制度制定之时,基金在税法上是具有纳税主体资格的。虽然1998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颁布的文件中,“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利息时,不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未明确有关被投资企业是为个人还是基金代扣代缴的所得税。但是,后续2002年所颁布的《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2012年颁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两份规范性文件,均明确表明被投资企业所代扣代缴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基金而非基金份额持有人。此外,在1998年的文件中,对基金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表述,也体现了基金在当时的纳税主体地位。在这种前提下,被投资企业在向基金分配时,对基金产生的所得代扣代缴所得税则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做法,在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条颁布后继续运行,则问题重重。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在个人所得税中,应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具体到利息、股息、红利的所得问题上,依照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其扣缴义务人应是直接向纳税义务人支付利息、股息、红利的单位”。因此,所得的支付则成为我们认定所得税扣缴义务人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的关键。而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支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1997年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税》规定,“扣缴义务人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配到个人名下时”,才认定为“所得的支付”。具体到证券投资基金的分配机制,被投资企业向基金分配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时,该笔所得是分配在基金名义之下的,只能认定为是向基金支付,而不是向投资者的支付。而基金背后投资者的所得的支付,应当是在基金将所得分配到投资者名义下,即基金向投资者分配收益时才发生。既然基金份额持有人为纳税义务人,而被投资企业又不是向其直接支付所得的单位,此时若由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基金份额持有人所得税,则明显有违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被投资企业扣缴义务人地位的合理性审查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纳税义务的前提下,被投资企业在向基金分配股息、红利、利息等所得时,能否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还应考察由被投资企业向基金支付的所得是否归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确定该笔所得归谁所有,我们需要明确基金的法律地位以及基金与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的关系。目前,由于国内信托制度的不完善,有关基金法律地位、法律性质仍未有明确规定,这也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收制度的混乱的原因之一。从组织形态来看,基金分为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两种,前者依据公司法设立,其法律主体资格自不待言。后者的法律主体地位,一直以来,则倍受争议。而目前,我国法律认可的也仅为“契约型基金”。因此,后者的法律地位的认定,成为影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收制度的关键。
那么,“契约型基金”到底是作为一种法律客体还是一种法律主体而存在的呢?如果将基金视为一种法律客体,将这一法律客体且归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这样一来,被投资企业向基金分配的所得即实质上归属于投资者所有。被投资企业分配该笔所得时,扣缴投资者取得该部分所得的所得税也符合税法规定。然而,若将基金视为法律主体,拥有独立的基金财产,产生独立的所得,那么由被投资企业在向基金分配所得时,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代扣代缴所得税的做法则显得极为不合理。考察整个《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定,及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法律主体的特性显然已难以忽视。
首先,从基金财产的独立性来看,无论是基金管理人还是基金托管人均不得将其财产纳入其固有财产,且二者在破产、依法被撤销、依法被解散时亦不得将基金财产纳入其清算财产。同样,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向基金投入财产后,也丧失了对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其只能依据基金合同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规定行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并不享有基金财产行使占有、使用、处分等所有权权能,且其收益权也只是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依据而享有,并非以对基金财产的所有权为依据而享有。同时,在基金债权债务方面,基金财产债权不得与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固有财产的债务相抵销;基金产生的债务,基金份额持有人仅以其出资份额承担有限责任。根据以上的种种特点,可见,基金资产是受基金目的拘束,并为基金目的而独立存在的,具有与各基金当事人相互独立的地位,并非任何基金当事人的财产,而是“具有潜在主体性的财产的集合”。
其次,从基金的组织性来看。整个证券投资基金即是由投资者提供资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提供专业化管理服务而形成,构成了“财产和人(自然人)的有机集合体”,具有组织体特征。突出表现为,基金意思的形成并非由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受基金合同、金融市场状况、投资人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独立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任意一方。
最后,从基金运行法律效果归属看,基金运行中所产生的费用、债务、税收都以基金财产独立承担,基金财产投资产生的收益也归入基金财产,管理人和托管人只能依据有关协议提取报酬,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只能以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分配条件来实际取得收益。
且在证券市场中,证券投资基金一旦成立,即成为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不仅参与股票、债券的买卖,甚至通过入主上市公司,直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和内部治理,充当上市公司的积极股东。这些都表明,证券投资基金本身即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法律主体的特质。若在税收制度中将基金视为法律客体,不仅不符合我国基金法律规定和整个基金运行的现状,也不符合整个商事信托发展的需要。新修改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虽将基金排除于基金财产投资产生税收的纳税义务人范围之外,但并不意味着也否定了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
基金的独立主体地位,即意味着基金能产生其独立的所得。实际上,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实践操作中,分配到基金的所得是归入基金自身财产中的,根据基金运行的需要用于再投资、基金运行费用支出、基金运行产生亏损的弥补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则为基金扣除基金运行过程中各种费用支出、弥补亏损之后,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分配的那一部分。因此,继续由被投资企业其向基金分配相应所得时即代扣代缴所得税,则不可避免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该所得税的纳税客体是基金所得而非投资者所得,显然与“基金财产投资相应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的规定相违背。二是,由于被投资企业向基金分配所得时间优先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取得所得的时间,被投资企业的代扣代缴行为发生于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成立之前,属于对纳税义务人财产权利的侵害。
三、被投资企业履行扣缴义务所导致的税收中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冲突
我国基金所得税税收制度采取基金在向投资者分配所得时,保留基金取得该笔所得时的性质和投资者层面单层征税的做法。该制度立足于“税收中性”原则要求,即不论纳税人是直接从事某些资产的投资(比如购买政府债券或者上市公司股票),还是间接地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比如投资基金)投资,所受到的待遇都应该是相同的。由于我国税法对个人和企业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有着不同的税收规定。根据“税收中性”原则,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所得税,应当按基金份额持有人享受的不同的税收待遇,分别扣缴其所得税。然而,现实中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所得税时,就分配给基金所得统一扣缴20%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投资者因此而不合理地承担了20%的个人所得税,高于其直接投资的税收负担,有违“税收中性原则”。
坚持税收中性原则,被投资企业根据投资者身份的不同分别扣缴税款,必须全面掌握基金背后投资者的信息。而我们知道,作为证券投资基金,尤其是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其背后有着大量投资者,且这些投资者长期处于变化之中。被投资要及时有效获取该部分信息,并进行管理实属困难。比较扣缴直接投资者的所得税,被投资企业扣缴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所得税的复杂性和成本会大大增加,有违扣缴制度所应遵循的比例原则。
因为扣缴制度,是国家出于税收债权保障、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以及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目的,通过立法的形式扩充纳税人税收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由第三人即扣缴义务人为税收债务实现提供担保的结果。对扣缴义务人而言,扣缴义务是一种负担,是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即税收利益的考虑,对其自由、财产等相关权利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基于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综合考量,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避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严重失衡。
比例原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适当性原则,即行为应符合目的的实现;二是必要性原则,有多种手段有助于目的实现时,应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手段;三是比例原则,即所实现的公共利益与损害的私人利益不能形成明显的失衡。具体到证券投资基金的扣缴制度:其一,从适当性原则来看,被投资企业扣缴的所得税对应的纳税客体为基金所得,而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得,显然不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纳税义务人的规定,不利于基金税收制度的目的的实现。其二,从必要原则来看,在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模式中,被投资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并非唯一的选择,正如《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条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亦为法律所认可的扣缴义务人。且相比被投资企业,管理人在了解基金背后投资者信息更加方便,有利于实现基金税收制度中“所得性质上传”的要求,避免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投资者就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额外承受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因此,被投资企业承担扣缴义务并非是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手段。其三,从比例原则来看,如之前所讨论的,由被投资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不仅不利于实现征管效率及降低征收成本,反而让被投资企业承受了过度的负担,容易造成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失衡。因此,由被投资企业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显然与设立扣缴义务时所应遵循的比例原则相违。
四、现行制度下所得税扣缴义务主体的调整
既然我们讨论了投资者通过基金分配所获得的属于上市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利息等所得不能采取被投资企业扣缴的方式进行。那么,这部分纳税义务由谁来承担更为合适?
修改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而根据国家有关税收征收规定来看,目前规定“其他扣缴义务人”也只有“被投资企业”。而被投资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又存在诸多弊端,那么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这部分扣缴义务交由管理人承担将如何呢。一方面,从基金运行模式看,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的管理与执行机构,其为基金分配方案的法定执行机构。即,基金管理人为形式上向份额持有人支付收益的主体,且份额持有人的所得亦产生于基金管理人实际分配收益之时。故由其担任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既符合现行法有关扣缴义务人为实际支付所得单位的规定,也满足扣缴义务履行的前提,即纳税义务人产生所得的要求。其次,从扣缴制度设定原则来看,管理人作为基金管理与执行机构,其在掌握投资者信息方面,有着其他主体所不具有的优势。其作为扣缴义务人,既能保证其有效管理纳税人信息,根据纳税人享受税收待遇不同履行扣缴义务,维护“税收中性”;又能保证稽征效率,和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因此,综合而言,由基金管理人承担这部分所得的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更恰当。
最后,就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于我国并未形成统一、规范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因此,对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既方便个人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税收收入。而对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投资者而言,一方面,由于已有较完善的企业纳税申报制度已经较为完善,税务机关对企业信息掌握也比较全面,由企业自行缴纳也能较好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在计算纳税所得额时,需要进行费用摊销、成本核算等,所得在期间中无法计算,所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定纳税义务于纳税年度届满之日发生。而由基金管理人在向企业分配所得时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缴义务履行先于企业纳税义务成立,属于对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害。因此,证券投资基金的扣缴制度应当仅针对个人投资者,企业投资者完全可以在获得基金所分配所得之后自行缴纳相应所得税。
[1]汤洁茵.证券投资基金纳税主体资格的法律确证[J].税务与经济,2008,(6).
[2]杨小强.税收筹划:以中国内地与港澳税法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95-4654(2015)04-0012-03
2015-02-01
F830.9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