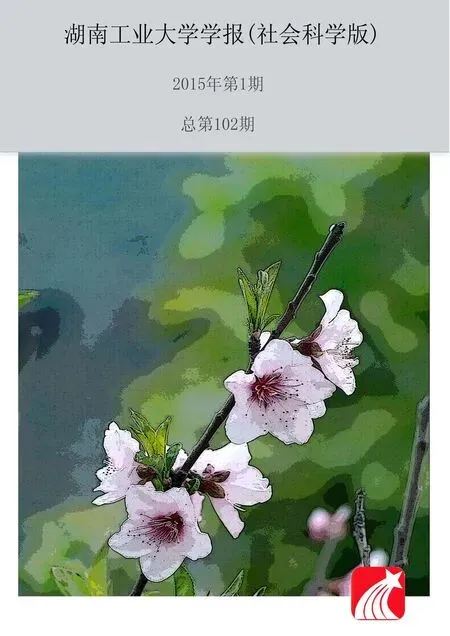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逻辑起点
易棉阳,贺 丽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株洲412008)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逻辑起点
易棉阳,贺 丽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株洲412008)
中国农村信用社普遍建立于建国初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其理论起点既不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也不完全是马恩列的合作理论,主要是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理论起点决定了它是一种既背离了国际合作原则又不完全遵循马恩列合作理论的特殊制度安排这是导致日后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集体化;集体金融组织
一 研究背景
建国初年的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普遍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供销合作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慢慢淡出,信用合作社中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也大都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唯独农村信用合作社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迄今仍是中国农村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之”字道路:即建国初年政府按自己的合作理念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1958-1978年的体制变革中政府彻底破坏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1979-2002年政府按国际公认的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试图把它建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但无论是1980年代“恢复三性”的改革,还是1990年代“重新规范”的改革,都没有能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建成符合国际合作原则的信用合作社。对于此种结局,政府颇为无奈,在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政府取消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传统称法,而直接表述为“农村信用社”,这不是无意中的简称,而是合作理想落空后的无奈选择。
“农村信用合作社”去掉“合作”两字,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不需要合作金融组织,事实上,在商业银行撤离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发展急需合作金融组织提供融资。发轫于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信用合作社,100多年来在西方得到了健康而快速的发展,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迄今已经建立起了完整而有序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体系。既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而且也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但为何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却不能走上真正的合作道路呢?或者说,改革以来30多年的以恢复“合作”为目的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最终以放弃“合作”而结局呢?这个耐人寻味的结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文献从制度异化的视角来给出解释:中国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政府的介入使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重点转向政府,逐渐背离了为社员服务的合作制原则,从而出现偏离合作制的异化现象。这种解释实际上蕴含了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演变逻辑:最初按合作制原则建立,然后破坏合作制,最后又按合作制原则来规范建立,三个阶段的合作制是同一种合作制。但在深入研究19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运动史后,发现,建国初年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并非按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组建,也就是,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其起点之时就偏离了合作制,就不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这个逻辑起点决定中国农村信用社在日后的演化过程中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这就是说,要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做合意的解释,必须要回到中国农村信用社的逻辑起点上去。
二 理论起点: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
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产业工人成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为免受高利贷和工商业资本家的剥削,英国工人率先组织起合作社,在英国的示范推动下,合作社逐步传及欧美国家,由欧美再传及世界。从19世纪开始,西方就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合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合作理论流派,主要有:以欧文和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合作理论、以英国金威廉和法国毕薛为代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合作理论、以法国布朗和德国拉萨尔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合作理论、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合作理论、以德国雷发巽和舒尔茨为代表的合作企业学派,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理论。这些理论都闪烁着时代的光辉,但对后世的合作社实践产生了直接而重大影响的是合作企业学派和马恩合作理论,前者于20世纪中叶成为西方的主流学派并指导着20世纪西方合作运动;后者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运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世界第一家信用合作组织由合作企业学派代表人物德雷发巽于1847年创办,在德国信用合作的示范推动下,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信用合作运动,信用合作取得了与生产合作、消费合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世界信用合作遵循主要由合作企业学派所构建的、由国际合作社联盟于1934年所规定的国际合作七原则:(1)门户开放,即入社自由,任何人只要愿意承担社员责任,都可以入社,不受人为限制以及任何社会、政治或宗教的歧视; (2)民主管理,合作社由社员所同意的方式选举或指定人员管理,对社员负责,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时享有一人一票的权力;(3)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确定;(4)股本利息受严格限制;(5)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6)社员与合作社之间采取现金交易;(7)促进社员教育,合作社应对社员进行合作社经济和技术知识的教育,以使社员深入了解合作社的本质与好处。[1]为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合作事业的发展,1966年和1995年国际合作联盟对合作原则进行了两次修订,增删一些原则,如删掉了政治中立原则,增加了关心社区、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等原则,但入社自由、民主管理、为社员服务等原则始终得以严格遵循。当前国际上有一种共识:按照国际合作联盟所公布的合作原则组建和管理合作社,或者说严格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的合作社,便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所遵循的合作原则就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符合国际合作原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研究合作问题,马恩的合作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首先是关于合作社的性质与功能。(1)合作社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中间商人对农民剥削的手段,同时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中间环节,这一点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得非常明白“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2](2)合作社是改造分散的传统小生产、建立社会化农业大生产的过渡环节。受机器大生产的冲击,传统小生产“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3]小生产者必然成为社会的弱势者,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通过建立合作社把传统小生产改造成社会化大生产。其次是关于合作社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对于小生产者而言,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就决定,这个阶段的合作社必须要允许而且要保护小生产者的私有产权。当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化水平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应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取代,实现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最初阶段,要坚持以自愿原则绝对不能对农民进行暴力剥夺,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4]在向合作社过渡过程中,倘若农民“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5]
马恩的合作理论最早在苏俄得以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在俄国推行共耕制。列宁去世以后,为满足苏联大规模工业化对资金、粮食的需要,斯大林从1928年起在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斯大林在继承马恩列合作思想的同时也曲解了马恩列合作思想:(1)把合作化等同于集体化。列宁曾提出共耕社、集体农庄、农业公社是合作社应经历三种历史形态的理论,斯大林却认为共耕社和农业公社都不适合于苏联,只有“集体农庄运动是唯一正确的形式”,认为“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6](2)违反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剥夺办法推行集体化。1928年起,斯大林采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以强大的压力强迫农民整村、整乡甚至整地区加入集体农庄,对于不配合的农民,则采取杀、关、流放的极端手段予以惩罚。斯大林所推行的集体化运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所建立的合作社既不同于列宁时代按马克思主义合作制建立的合作社,更不同于按国际公认合作原则建立起来的合作社。
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必然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指导,但“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曾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广泛流传,由于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更多的吸收了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斯大林的合作思想成了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能不体现出较多的苏联模式的印痕”。[7]1943年11月毛泽东所发表的《组织起来》一文成为中国合作运动的指导性理论文献,文章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合作社的未来就是“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8]毛泽东在1955年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9]从建国前后十几年毛泽东的报告中看到,毛泽东始终把苏联的集体化视为中国合作化的楷模,1950年代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化运动,这就决定,在合作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合作社,在理论起点上既不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也不完全是马恩列的合作理论,主要是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
三 制度起点:既背离国际公认合作原则又不完全遵循马恩列合作理论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理论起点决定了它是一种既背离了国际合作原则又不完全遵循马恩列合作理论的特殊制度安排。
(一)背离自愿入社原则
国际公认合作原则把入社自由列为国际合作七原则之首,马恩列合作理论反复提醒不要以暴力剥夺方式强迫农民入社,把自愿入社视为合作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此,中国共产党曾有清楚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1933年苏维埃政府规定要“使各人自愿入社,不得用强迫命令方法”。[10]解放战争时期,合作运动在解放区蓬勃开展,中央反复强调“根据过去经验:第一,必须是自愿结合的,必须严禁强迫加入;第二,必须是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10]建国以后到1953年信用合作高潮来临之前,自愿原则仍然得到较好的坚持,1951年颁行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就开宗明义地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宗旨是“劳动人民根据自愿两利原则,大家凑集股金,吸收存款,互通有无,以解决社员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11]1953年农业合作运动全面展开以后,自愿原则就遭到了破坏,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提出“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怎样才能在较短时期内达到这个目的呢?毛泽东提出“要有数字控制,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12]通过数字摊派来建合作社实际上是鼓励地方以强制命令开展合作运动,这是对自愿的背离。1953年起,各地纷纷采取强制命令迫使农民入社,有的基层干部威胁农民“不入社就是走蒋介石道路”,有的召开全区富农批斗大会,县委宣传部长在大会上威胁“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有的采取“熬夜”和“车轮战”办法强迫农民入社,所谓“熬夜”就是召集农民全家老少开会,不同意入社就不散会,所谓“车轮战”就是今天甲去、明天乙去、后天丙去,轮流进农户家动员,直到“同意入社”为止;有的威胁农民“不入社不给贷款,不卖给化肥”;还有的甚至对不入社的农民进行粗暴的打骂与捆绑。[13]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以后,在强制农民入社的同时,对农民的最初入社股金进行了剥夺,私人股金变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集体资产,社员称这种情况叫做“归大堆”。
(二)背离民主管理原则
国际公认合作原则为确保社员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特意设计了一人一票的制度安排。马恩没有专门研究合作社的民主管理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讲到合作社是一种企业,意识到要用现代管理制度管理合作社,但没有具体设计某种制度安排来保证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斯大林通过暴力剥夺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不可能实现民主管理。在合作运动高潮中普遍设立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农民自愿组合而成而是政府强制捏合的结果,在这种信用社里,实际控制者是要么是政府基层官员,要么是受政府支配的内部人,广大社员对信用合作社事务既不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也不具有决策权。1958年以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迭次变更,使社员完全失去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权力,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为基层政府一个部门;1962-1968年,农村信用社又先后归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管理;1969-1976年,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接管农村信用社;1977-1996年再度先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1958-1996年差不多四十年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权力完全脱离了社员。1996年行社脱钩前后,政府按国际公认合作原则来来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试图通过成立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来保证社员的管理权力,但因时代久远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已经模糊难辨,加之随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日益富裕,对几十年前所入的微薄股金及其收益已无多大兴趣,因而对社员大会也无多大兴趣。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最高权力机关的社员大会形同虚设,立基于此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更不可能反映社员的集体意志,信用社重新陷入被内部人控制的困境之中。
(三)背离互利互助原则
无论是国际公认合作原则还是马恩列合作理论,都认为合作社要实现社员的互利互助。但互利以自愿为基础,因为信用合作社本身就是农民凑集股金互相调剂资金余缺的互助组织,如果是自愿入社,社员之间可以议定入社股金数额及股份收益,但如果是强制入社,入社股金数额和股份收益不再由社员议定而归信用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者决定,控制者就有可能利用权力损害社员利益,互利原则就遭到破坏。1953年之前,互利原则得到了较好的坚持,但合作化高潮来临之后,互利原则被破坏,主要表现在信用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者平调中农资金填补贫农入社股金缺口,损害了中农利益,中农把此种现象称之为“揩油”。对于“揩油”现象,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予以坚决制止,毛泽东一方面说“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即贫农——引者注)不要‘揩油’”,另一方面又说“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全大局,……小小的入社时不公道,也就算了”。[14]信用合作社社员之间的互助又是建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如果农民是被迫与自己不愿意合作的人合作,心中本就不满,何来互助?如果在强制结社过程中,一部分社员损害了另一部分社员的利益,利益受损者心中积满怨气,又怎会与损害其利益者互助?在1953年之前,信用合作社基本上按自愿原则成立,社员之间在信用社内实现了资金上的互利互助。如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分得土地的农民缺乏生产资金,信用合作社的信用贷款解决农民生产上的燃眉之急,遏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剥削,入社农民高兴地把信用合作社成为自己的“小银行”。在合作化高潮中,因自愿和互利原则被破坏,社员之间互利也遭到破坏,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信用合作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成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信用社由群众自己的金融互助组织变成为基层政府机关的账房,充当了社队平调、挪用社员资金的工具,有的公社和生产大队随意挪用信用合作社资金作为财政性开支,有的公社领导干部甚至贪污、挥霍信用社资金,如1959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的16亿元贷款中就有8亿元被干部挪用和挥霍。[15]信用合作社蜕变为基层政府机关之后,不可能再发挥社员之间互助合作功能。
(四)成为实现政府政治与经济意图的工具
国际合作原则明确规定合作社“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马恩列的合作理论赋予了合作社三大使命:改造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的生产关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些使命要么是政治使命要么是带有政治意图的经济使命,要实现这些使命,合作社不可能保持政治中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坚持了马恩列的合作观,所以,合作社的身上肩负着改造传统小生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三大使命,建国前后党中央所发布的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讲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合作社的使命。建国前夕,中央关于合作社经济的作用作了如下规定:“如果没有广大的合作社作为桥梁和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行有力的领导”,要使小生产者按照无产阶级的计划进行生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16]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权”。[17]刘少奇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就不能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18]由于斯大林把合作社的建立与“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同起来,这就使得斯大林时期的合作社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受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信用合作运动过程中,为了达到对农村旧势力专政的目的,利用信用合作社对富农地主进行斗争,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文件和领导人关于合作社的讲话中,处处充斥着“斗争”的字眼。如早在1932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信用合作社,为便利工农群众经济周转和借贷,以抵制私人的高利剥削”,它“由工农群众集资组织,富农、资本家及剥削者均无权组织和加入”。同年中央苏区财政部编印的《合作社工作纲要》中再次强调信用合作社的“社员一定要是非剥削的阶级成份,如工人、中农、贫农、雇农、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等,对于剥削阶级如商人、富农、厂主、工头等绝对不准他加入”。[19]建国后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20]通过斗争创立的合作社,本身就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定性为“劳动人民群众的资金互助组织”的农村信用社,非“劳动人民”不能入社,非“劳动人民”系指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农业合作化实现之后,对入社限制有所放松,1957年修改后的农村信用社章程规定“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可以入社,但“在入社后的一定时期内,没有被选举权,不得担任社的干部”,或做“候补社员”,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农村信用社开展贷款业务也要划清政策界限,社员享有贷款优先权,在资金可能的范围内,对非社员可以发放贷款,但不放款给地主、富农和商人。
四 结论与探讨
1.1949-1952年,土地改革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点,为帮助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资金的困难,党在农村中领导农民开展信用合作,但这个时期信用合作处在试点状态,还不构成一场全国性的信用合作运动。试点时期的信用合作采取的是“典型试办、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办法,不仅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可以自由入社也可以自由退社,而且充分尊重各地条件的差异,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试办不同形式的信用合作组织。信用合作搞不搞,主要取决于农民的意愿,政府起着引导而不主导、规范而不强迫的作用。试点时期的信用合作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
2.1953-1956年,中国进入三大改造时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实现,这个时期的农村信用合作成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环节。以什么方式推进,以什么速度推进,都不再取决于农民而是政府,政府的作用由引导变主导,规范中含有强迫。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信用合作属于典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点是可以快速、有效地实施制度变迁。1954年2月全国第一次信用合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快马加鞭,火烧屁股”的发展口号,要求信用合作社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行一步,一个月以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特别提出信用合作要“积极而又迅速地加以发展。”会后,全国农村信用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4年底,全国共设立12.6万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覆盖全国70% 左右的乡镇,其中有9万多个信用社是秋后三个月建立的。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确定1956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的方针是“积极发展信用社,建立新社,巩固扩大老社,争取应入社的人大部分或全部加入信用社”,1955-1956年,农村信用合作进入高潮时期,至1956年,全国97.5% 的乡建立了信用合作社,数量达16万个,入社农户达1亿户。[21]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信用合作化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点是民众意志绝对服从政府意志,甚至违背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全国普遍设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仅背离了自愿结社原则、违背了互利互助原则、抛弃了民主管理原则。
在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中,初始制度安排一旦选定,政府会不断地颁布法律法令等正式规则来强化初始制度安排,这实际上是政府不断地向社会发出并强化一个初始制度安排具有合法性的信号,“合法的东西应该合理”是人们的习惯思维,于是,人们就会认可初始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制度变迁就会沿着某一条路径不断地强化初始制度安排,这就是诺思所指出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设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既不是符合国际合作原则的合作金融组织,也不是按马恩列合作理论组建的合作金融机构,而是一种苏联式的集体金融组织,这便是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初始制度选择。1957年农业合作化实现之后的20多年里(文革时期除外),政府所颁布的所有法令和所主导管理体制变更,都是在探索如何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办成集体金融组织。195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家银行基层营业所合并组成信用部,取消农村信用社原有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下属机构,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人民公社一部分的信用部也自然而然演变成集体金融组织。1962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银行工作“六条”》公布实施《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大跃进时期下放的管理权收归国家银行,重新明确信用社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此次调整改变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随意挪用信用部资金的混乱状况,但信用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性质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因中央银行的接管而更加官办化。文革时期,信用社下放给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管理,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信用社干部把业务管理制度斥为“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拒不执行,出现信贷“撒把”,存贷款不记账的混乱状况。这个时期,信用社成为贫下中农管委会的账房,任意挪用资金,不再是一个正常的金融组织。文革结束后金融行业拨乱反正,国务院于1977年颁布《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明确定性“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把信用社依然定性为集体金融组织,1980年中央财经小组在研究农村信用社工作时指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对,搞成‘官办’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金融组织。[22]这段话蕴含了三层意思:其一,在政府决策层的眼中,信用社本应该是集体金融组织;其二,下放给人民公社和收归国家银行的两种做法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集体金融组织的有效方式;其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目标是办成真正的集体金融组织。
在1980年代初迅速完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中维系了20多年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生产大会、生产队,因土地分配到户而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层重新考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要求:“信用社要进行改革,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23]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首次以正式文件宣布信用社的改革方向是合作金融组织,接下来的问题是,依据何种合作理论来规范发展信用社?对外开放使人们(包括金融学者、金融业从业者和政府官员)的眼光纷纷投向国外,发现按国际合作原则建立起来的信用社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于是,国际合作原则成为1984年以后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标。理论界和业界一直有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在1957年以前是具有合作性的,只是在1958年以后遭到了破坏,1984年之后的改革就是恢复信用社的合作性,所以,在官方的文件中,长期是使用“恢复”两字。本文的讨论已经清楚地揭示,不是恢复而是以另一种合作原则来重塑信用社。
然而,初始制度安排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决定“重塑”将面临双重阻力。这些阻力包括:
1.1985年开始的城市化改革面临资金困难,需要集中农村资金予以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抽水机”功能(即把农村资金集中起来转贷给农业银行,再由农业银行带回城市)正好符合城市改革的需要,政府没有很大动力把掌控于自己手中的信用社发还给民间;
2.在社会主义国家,私营经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四种不同经济成分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经济,合作经济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面前低人一等,但比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则高过一头,于是,合作向集体过渡,集体又向全民靠拢,便成为一种必然现象和规律。作为集体金融组织的信用社,其职工享受与银行员工相同的待遇,其负责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作为合作金融组织的信用社,其职工不再享受银行员工待遇,其负责人同样也不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信用社,内部人并不希望甚至抵制把信用社办成符合国际合作原则的信用合作社。这双重阻力再加上农民对信用社改革的冷漠,使得1984年以后的历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都是无功而返,到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最终放弃了“合作”两字,这应该是直面现实的明智选择。
[1]尹树生.合作经济概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3: 10-2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417.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1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1.
[6]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78.
[7]冯开文.论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变迁的格局与方向[J].中国农村观察,1999(3):76-82.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3.
[10]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北京:三联书店,1957:133,731.
[11]易棉阳.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路径与制度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J].2011(2):100-107.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16.
[13]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322.
[14]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29.
[15]池茂传主编.合作银行经营指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1.
[16]张闻天.张闻天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36-37.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370.
[18]刘少奇.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79.
[19]许 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长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5.
[20]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97.
[21]卢汉川.当代中国的信用合作: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92-96.
[22]汪澄清.金融创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24.
[23]尚 明.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59.
责任编辑:徐 蓓
The Logical Starting of China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YIMianyang,HE Li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China's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generally establish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of China.Its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is not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inciple and also not entirely by Marxism cooperation theory,butmainly from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theory of Stalin.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Chines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reform can't achieve its desired goal is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a's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theory is not only deviat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t also does not follow the special system arrangement of Marxism cooperation theory.
China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collect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
F832.35
A
1674-117X(2015)01-0025-07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1.006
2014-06-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农贷助推农村水利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湖南案例”(11YJC790246);中国博士后基金“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的农民合作与农业发展绩效”(2012M521520)
易棉阳(1977-),男,湖南涟源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史;贺 丽(1979-),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
——浅评《入社礼的仪式与象征:关于生与再生的秘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