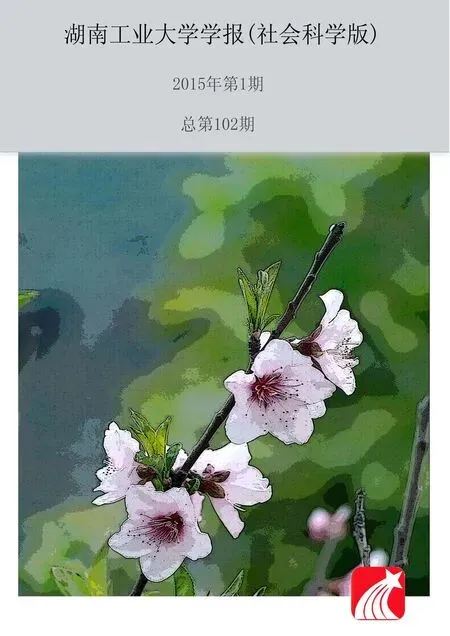魔幻现实、当代体验与时代图景*
——论吴刘维近年小说创作
郑润良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魔幻现实、当代体验与时代图景*
——论吴刘维近年小说创作
郑润良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吴刘维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绝望游戏》以及中篇小说《天堂无窑》《我岳父就这样老了》《送雪回家》《有人落水》等作品,充分反映了作家对文本形式的用心,以及他传达当代体验、铺陈时代图景的创作野心。
吴刘维;魔幻现实主义;底层文学
一
湖南作家吴刘维的创作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小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萌芽》《湖南文学》《长白山》《希望》等文学杂志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湖南日报》《青年报》等报纸发表了多篇散文,短篇小说《你不要烦我》获第一届湖南文学新秀选拔赛三等奖,短篇小说《小城有家羊肉铺》获第二届湖南文学新秀选拔赛二等奖,散文《长命乐》获湘赣两省征文赛一等奖。但之后他歇笔近20年,直到近年才重新回归文学。他的悄然退场少有人知,重新登场却颇为强势。2010年,他的长篇小说《绝望游戏》[1]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获得专家的好评,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进入2011年上半年京东商城书店财经小说排行榜和长沙地区畅销书排行榜,并在《长沙晚报》连载;中篇小说《天堂无窑》《我岳父就这样老了》《送雪回家》[2-4],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不管他当初为何退隐,他的重新出场,都表明他对这个世界的强烈的发言欲望,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交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么,多年之后,他携长篇小说《绝望游戏》等作品重返文坛,究竟要将什么样的体验传递给读者呢?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小说创作出现了审视当代现实的热潮,长篇小说领域以一大批曾经引领80年代文学新潮的老作家关注当下现实的新作最为引人注目,格非的《春尽江南》、莫言的《蛙》、贾平凹的《带灯》直面当下现实;韩少功的《日夜书》、马原的《牛鬼蛇神》也将其擅长的知青叙事延伸到后知青叙事,表述曾经的知青们的当下生活状态;还有余华的《兄弟》《第七天》,虽然评论褒贬不一,但这两部作品都将视角转向当下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自2004年起也出现了“底层文学”的热潮。与90年代兴起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关注小市民的日常尴尬与自我满足不同,“底层文学”将视线投向阶层固化现实下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呼吁对底层困境以及阶层固化现实的关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家们面对现实发言的欲望空前高涨,都力图为急剧变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五四以来“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脉流的凸显,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作家们也面临着新的课题,正如有论者所言,“即吊诡的是我们看似对离我们更切近的‘现实’要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化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要求的设置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5]
《绝望游戏》《天堂无窑》等作品同样是以人事纠葛、底层困境等当代现实问题为聚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重返文坛的吴刘维为何一下子就能进入读者视线的中心。那么,吴刘维发现了何种“现实”,他又借助何种文学形式超拔于现实呢?
《绝望游戏》糅合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无雪城《经济前沿》杂志主编吴谷生一年当中所经受的种种坎坷遭遇。吴谷生年轻有为,杂志在他手上影响日增,但他也面临种种困境。在单位里,杂志原副主编牛小琴联合旧员工与他对抗,牛小琴的丈夫夏天也在会上公然叫嚣辱骂他;在家里,他与妻子王回香的婚姻已走到尽头,两人分居已久,但妻子的坚持使这场离婚战变成持久战。更麻烦的是,三年前他好心帮助一个业余作者蓝萍萍出书,反而背上了一桩官司。蓝萍萍因为自己的书没有独立书号不能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把责任推到吴谷生身上,并希望借助媒体力量炒作自己,弄得不明真相的媒体,轮番对吴谷生展开轰炸,搞得吴谷生声名狼藉,蓝萍萍还直接到公安局告发吴谷生。而吴谷生所信赖的宾律师采取的战术,事实上使他一步步陷入了困局。这一年,应该是吴谷生有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年。用吴谷生好友马军的话就是,“通俗一点讲,这一年,应该叫做‘买单年’。今年这一年,是你吴谷生的‘买单年’。你为离婚所承受的失望和无奈,是为你十六年的婚姻买单;你为蓝萍萍出书事件所承受的折磨和摧残,是为你所在公司的过失、为北京那家出版社的推卸责任、为蓝萍萍的失败人生、为宾律师‘拖’的战术买单;你为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焦虑,是为省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前沿》杂志社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买单;你被媒体的炮轰所承受的痛斥和唾弃,是为无雪城媒体的急功近利买单;你为亲友的过世所承受的打击和痛苦,是为你生命中失去的那份亲情和友情买单;你对原莹的情感左右为难的尴尬状态,是为你总是怕身陷其中、总是要逃离的奇怪性格买单!”作者通过主人公吴谷生一年的悲剧性遭遇,传达了被都市欲望游戏吞噬的现代人的绝望体验,吴谷生“无辜”而不幸地成为都市欲望游戏的牺牲品。
相对于乡村的简单与淳朴,都市是繁华而芜杂的,是各种欲望游戏的渊薮。盛行其间的首先是官场欲望游戏。在权力欲望的支配下,职务不再是一个人发挥能力与担当的标志,而首先是个人威望与利益的保障品。因此有了暗箱操作,有了拉帮结派,有了勾心斗角。吴谷生到任以前,杂志社的工作一直由副总编牛小琴主持。主持了近三年工作的牛小琴,一门心思把“副”字摘掉,偏偏杂志社的主管部门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征途不但没帮她摘掉“副”字,反而新招来一个总编压在她头上。一气之下,她暗中联合杂志社原有员工,集体对抗外来的和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反吴行动。由于爱人牛小琴没被重用,夏天盯上了新上任的宋征途,他联合经济研究中心少数在宋征途改革举措中受损的中层干部和研究骨干,分头在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游说,开展比牛小琴反吴行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倒宋运动。出身乡村、心性淳朴的吴谷生因此备受此种官场欲望游戏的煎熬。在我看来,这也是他最终虽然有惊无险免受官司折磨却还是选择逃离无雪城的真正原因,因为留在无雪城,他还得继续承受这种官场欲望游戏的煎熬。
同时,在欲望游戏原则的支配下,媒体不再以追求真实为标准,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和利益,而是以吸引眼球从而赢得更多的受众关注为目标,一味营造一夜成名的神话,一味炒作各种爆炸性新闻,这也是蓝萍萍走上不屈不挠告发吴谷生之路的真实原因。蓝萍萍自身并无过硬的文学功底,却在无雪城的媒介文化中滋养了一夜成名的幻想,“一个山村女子,单枪匹马地闯进无雪城,眼里看的,耳里听的,尽是名呀利呀,加上无雪城电视台没完没了的选秀大赛、造星运动,让人误以为一夜之间便可以成名得利。”她的真正目的不是告倒吴谷生,而是借此机会名扬四海。令她没想到的是,虽然她成名的愿望达到了,但并没有因此达到改善个人生活的目的,仍旧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事业,没有婚姻,仍旧一无所有。可以说,她和吴谷生都是欲望游戏原则支配下的媒体文化的牺牲品。
在此情境中,原本庄严的法律也成了一场欲望游戏。小说中的宾律师在处理吴谷生的官司时一直采取“拖”的战术,尽量不与蓝萍萍正面交锋,结果使得官司越拖越大。正如小说中人物所分析的,宾律师“想凭借自己的智慧,跟公检法之间玩一场法律游戏。这其实是一出老鼠躲猫的游戏。猫最终会把老鼠吃掉。因为公安局掌握着侦查权,检察院掌握着审查权,法院掌握着判决权。宾律师选择这样一种不明智的办案方式,最终把当事人逼到了非常尴尬和被动的处境。老鼠也许能侥幸躲过猫的捕杀,但更多时候反倒激怒猫,使得猫的捕杀行为变得更猛烈。三年下来,我们不幸成为了宾律师游戏中的牺牲品。”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战术,究其原因,还是利益因素,“律师其实好比军火商。军火商总希望战火不断。战期越长,战争越激烈,军火商获利的机会越多,获利的空间越大。原本一桩小官司,宾律师一拖便是三年。把时间拖得越久,把官司拖得越大,宾律师收你的钱越多。”这种欲望原则支配下的法律游戏,对于当事人而言,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和打击,它使吴谷生一步步陷入困境,心力交瘁。吴谷生的好友周未兵,则死于老同学石默编织的商业游戏。
因此,无论是官场游戏、法律游戏,还是媒体游戏、商业游戏,其实质都是欲望游戏。吴谷生不幸地被置于游戏的中心,惨遭蹂躏。显然,吴谷生的遭遇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他所遭遇的各种欲望游戏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伤害,对于游戏中的主动者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损害。比如,牛小琴和夏天,原本可以拥有平静、优裕的生活,却因为欲望蓬勃,心理失衡,不见得比吴谷生好受。蓝萍萍从这场官司以及媒体游戏中,也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好处。在欲望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胜者。无雪城欲望游戏的盛行,无疑与无雪城总体的文化氛围直接关联。吴谷生非常精准地将无雪城文化总结为“享乐文化”,换言之就是欲望规则支配的文化。传说中的无雪王死于暴饮暴食的享乐。他的子孙们不仅纵情享乐,而且还玩出大气象,“无论吃饭喝茶,无论听歌喝酒,无论洗头洗脚,一概大场面。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吃饭;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喝茶;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听歌;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喝酒;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洗头;上千人在一个大厅里洗脚。场馆的外面,一律摆放着上百辆小车。”这也是吴谷生的学生李明朝之所以能发迹的真正原因。从能够让人们梦想成真的“明朝梦片”,到让人出一身冷汗的“幽灵城”,李明朝开发的项目撩拨着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当无雪城人所有的花样都玩尽,所有的花样都玩得令人生厌,李明朝开始为无雪城人设计模拟监狱“失乐园”,重新刺激无雪城人的感官和神经。因此当吴谷生被关在看守所时,他突然想到看守所外面也是一座监狱——“享乐之狱”。以满足个人欲望为最高目标的无雪城人,最终都成了欲望的囚徒与奴隶,并且为了一己私利互相折磨,展示如萨特《地狱》中所言“他人就是地狱”的鲜活图景。
写作的目的,说简单点,就是让读者看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与温暖。残酷往往与悲剧相关,其缘由有人性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直面残酷,可以使我们少一点幻想,多一点清醒。亲近温暖,则让我们找到生存的方向与坚持的理由。把残酷和温暖都写透写足,写得踏实,写得一点不含糊、不造作,这样的小说应该就是好小说了。同样,《绝望游戏》中不仅有绝望、残酷,也有希望、爱与温暖。正如小说中吴谷生自创的信息中所言,“感情如同三种花。爱情是烟花,美丽我们的生命;友情是雪花,纯净我们的生命;亲情是棉花,温暖我们的生命。”与原莹之间的爱情,与卜心吟、马军、周未兵之间的友情,还有与父母、女儿之间的亲情,是支撑吴谷生走过这一年的坚实动力,也为作品的总体基调增添了暖色。
三
正如前文所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曾经的先锋作家加入了对当下现实的审视与书写。莫言、格非等人新世纪以来书写当代现实的长篇大作的成就,表明他们在文本形式、现实思考方面都有丰厚积淀之后,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吴刘维歇笔近20年后携新作重返文坛,从《绝望游戏》的文本形式及其所传达的社会思考来看,近20年的潜隐,他绝非真正与文学隔离,而是在暗中发力,以达到厚积薄发的效果。
吴刘维笔下的崇尚享乐文化、欲望游戏且功利主义盛行的无雪城,无疑是对当下中国都市现实的隐射。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进程骤然加快,在带来社会物质的全面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的失范及趋利主义的盛行。这种普遍的功利心态,迄今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绝望游戏》明显借鉴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处处充满魔幻色彩,正如有论者所概括的,“小说中,无雪城不是一座不下雪的城市,而是雪飞扬在空中却不落地的城市。除了雪花飘飞却从不落地外,无雪城还有着一些离奇的事件,无从解释:去考察无雪城的东郊农场风水的十位风水先生,在发现东郊农场的秘密之后,全部在无雪河中遇难,无一生还;无雪河上每建成一座新桥,当时在任的市长必暴死,无论想尽办法也不能避免市长的死亡。生活在这样一座神奇的城市中的吴谷生,能在梦中感受到祖母亡灵的嘱托,能为外婆、岳母的亡灵所庇佑,能预感到身边的人的死亡,能见到已经离开人世的人。”[6]任何一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助于深化文本的表现主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这篇小说亦幻亦真,充满寓言色彩。雪可以象征纯洁,这座欲望蓬勃的都市因此与雪花无缘。千人同乐的场景也充满魔幻与讽刺色彩。吴谷生能够预感身边的人的死亡,比如好友周未兵的死亡,事实上增强了人物命运的宿命色彩。周未兵屡屡受骗,最后又被老同学蒙骗,一无所有,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他的死亡及吴谷生的预感,都强化了小说所表达的欲望游戏对人的吞噬这一主题。
从《绝望游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吴刘维对于文本形式的用心,以及他传达当代体验、铺陈时代图景的创作野心。通过《绝望游戏》,吴刘维事实上已经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对时代图景进行了全盘扫描,但作品最着力描述的还是以吴谷生为代表的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状况。
对于作家而言,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是写作的捷径。《绝望游戏》选择以杂志主编吴谷生为叙述中心,肯定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小说主人公吴谷生与作者姓名相近,并且都是杂志主编,很容易让人将二者产生联想。通过吴谷生这一人物形象,作者充分调动自身经验,为我们细腻描述都市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各种人事纠葛与内心纠结。
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利益分配的差异,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如何深入描述不同阶层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严肃课题。对此,吴刘维有信心,也有了相应的积累。写完中产阶层,吴刘维将笔锋一转,转向底层,创作了中篇小说《天堂无窑》《我岳父就这样老了》等作品。
四
2004年以来,批评界关于“底层文学”的呼声与讨论日趋热烈。底层概念在文学场域中的重新浮现自然有它的必然性。“近20年社会阶层的分化正在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现代生活的临近并不能真正遏制这种分化。”[7]底层困境以及阶层固化、阶层隔膜等问题已引起众多作家的关注。吴刘维歇笔多年,但甫一出山即能顺应文坛新潮,表明了他对时代核心精神命题的持续关注与深度思考。
《天堂无窑》描述一出“三叔”导演的通过所谓“矿难”骗取赔偿和保险金的戏剧。奇怪的是,我们对“叔叔”的行骗得逞都会心生快意。当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出现明显偏颇,弱势者即便有图利的诡诈行为也能获得人们的同情,何况“三叔”为的是子女的教育费和抚养费。本性良善的三叔被迫走这一步棋,我们因此要质问的不是三叔的良心,而是这个社会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作者把三叔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导演的这出戏剧编排得天衣无缝,处处彰显三叔的精明,包括用他人尸体冒充自己,使小说蒙上喜剧意味。
和《绝望游戏》一样,《天堂无窑》同样调用了作者熟悉的生活资源。作者坦陈,“三叔”这个人物形象有他二叔的影子,“写《天堂无窑》这篇小说,源于二叔几年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二叔深为两个孩子念大学的高额费用困扰,说:‘我恨不得被砸死在窑里,拿赔偿金来供细孩念书。’这句话像是一声惊雷,一直在我心里轰隆作响。我老家在山沟,要缓解生存压力,要给孩子一个出路,二叔们别无他法,只有拼尽身家性命。”[8]底层矿工为了下一代的未来,竟然宁愿以性命相博,令人唏嘘!吴刘维用喜剧形式包装这一悲剧性故事,使这个故事的悲剧内涵与喜剧因素互生张力,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效果。但在我看来,假如没有用他人尸体冒充这个情节,三叔为子女从容赴死,则悲剧性与喜剧性反差更大,审美效果更佳。
《天堂无窑》之后,是描述城市底层平民生活的《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与《天堂无窑》中的“三叔”相似,这篇作品所呈现的城市底层平民“我岳父”的生活应该说是悲哀的,尤其是他的骤然变老。“我岳父”原本外表英俊,50多岁的人却一点都不显老。因为亲戚帮他办了一张老年证,为了让这张老年证发挥作用,使他省掉每天上下班的公交费,他刻意扮老,结果丢了工作,连“爱情”也丢了。我岳父原本是个爱干净、爱体面的人,但就为了一天省区区几块钱,他将自己的体面与干净置之不顾。这其中掩藏的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一个人为了区区几块钱放弃自己的体面与尊严,这正反映了他生活的窘迫与无奈,如小说中所言,“老百姓过日子,不算计不行,算计得好,勉强能将日子打发掉,不算计或者算计不好,恐怕只能度日如年,没法将日子捱到岸的。”与过日子相比,体面和尊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我岳父”在扮老中逐渐习惯了老态,逐渐变老了,原本英俊的外表也逐渐变形了。我岳父对自己的“变老”倒也心安理得,毕竟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用刻意扮演就能自由使用老年证了。直到一直与他心有灵犀的姨妹在重逢后见到他的老态大惊失色而后仓皇离去,才让他真正感受到自己的“老”带给他的巨大损失。小说让我们看到底层平民在物质窘迫中逐渐丧失了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外表和内心隐秘的快乐。与《天堂无窑》相似,作者用喜剧形式包裹这一故事的悲剧性内核,我岳父扮老、智斗公交司机的故事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感觉酸楚。
《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之后,作者通过《送雪回家》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式”白领的生活。小说主人公陈子鱼是某旅游网站的旅游体验师,工资不低,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四处旅游,享受艳遇。表面上,陈子鱼的生活是令人艳羡的。其实不然。陈子鱼有一个相伴多年的深爱的女友,大学毕业后两人都有了不错的工作,而后租房同居,并筹划攒钱买房结婚生子等美妙图景。可是他们攒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房价的节节攀升,使得陈子鱼逐渐对这种疲于奔命且遥遥无期的生活,产生彻底的厌倦感和挫败感。他的一个和他一样出身底层工人家庭的同事因病自杀,促使他决定放弃已有的人生规划,放纵自己。在“帮帮帮”QQ群里,他领受了一个任务,将北方的雪送到千里之外的三亚一个临终老人的手里,让毕生未见过雪的老人没有遗憾地离开人世。等他终于送达之后,他才明白,老人让他送雪最主要还是为了让自己身患残疾的妻子见到雪。老人与他妻子之间的感情让他骤然醒悟,决定和女友重修旧好。由于高房价等现实原因,来自底层家庭的“中国式”白领在城市中的生活,绝非流行小说或电视剧描绘得那么美好,“天天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而往往是望房兴叹,在“蚁族”与“屌丝”之间徘徊。小说对“中国式”白领的生活困境与心理异常作了深刻揭示,小说的温馨结尾更多地表达了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美好祝愿。
在新作《有人落水》中,作者以一个亡灵为叙述视角,讲述他的底层生活与曾经的官场人生。以亡灵为视角,在中外小说中并不鲜见,国外著名的例子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国内最近的例子则是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当然,一种艺术手段的运用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功。《佩德罗·巴拉莫》被誉为世界文学经典,余华的《第七天》由于主人公形象不鲜明,被许多论者讥为“新闻集锦”。相对来说,《有人落水》中的人物形象要厚实丰满得多。亡灵的视角使作者能够自由地在现实与记忆里穿梭,并营造出类似《绝望游戏》的亦幻亦真的魔幻效果。小说主人公大学毕业后跻身官场,由于精于经营,步步高升,官至城管局副局长。为了与同僚竞争局长位置,他决定依靠情人晓倩施展“美人计”扳倒对手,却不知晓倩是对手所设棋子,他因而锒铛入狱。他出狱后回到自己成长的“望月湖”,终日与小偷、按摩女等底层人群为伍,却也在他们身上感受到深厚的情谊,直到有一天因为救一名落水的三陪女意外身亡。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阶层的生活差异与道德差异。跻身官场的“我”曾经尔虞我诈、步步为营,妻子和情人都成了自己进步的棋子,最终反遭了别人算计。而小偷瘦脖子、三陪女沈殿来等人物,这些向来被人们歧视和鄙弃的边缘人群,却让“我”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光辉。在吴刘维的作品中,总是绝望与希望并存,残酷与温暖同在,这是作家有意追求的一种平衡与救赎,虽然绝望与残酷往往描述得格外真切,希望与温暖则多少有些虚妄。
五
一个作家如果只会调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资源进行写作,那么他总有江郎才尽的一日,优秀的作家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包容万象的野心。从《绝望游戏》中,我们已经感受到吴刘维这方面的深厚素养,《有人落水》等篇章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种能力。事实上,这也是吴刘维的自觉追求,“把每个小说做得都不太一样,让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性,是我写小说的一个追求。我力求做一个非典(非典型性)作家,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地域、人物乃至结构、语言,将每个小说打造成一处崭新的风景。除了电子时代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所不知的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每次写作因此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新奇的冒险和智慧的挑战,既充满着刺激与神奇,也充满着前途未卜的忐忑,过程也许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乐。”[9]对于吴刘维而言,这种痛苦与快乐,无疑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吴刘维.绝望游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
[2]吴刘维.天堂无窑[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 (10):86-100.
[3]吴刘维.我岳父就这样老了[J].文学界·湖南文学,2013(2):4-24.
[4]吴刘维.送雪回家[J].创作与评论,2013(8):47-63.
[5]霍俊明.余华“现实叙事”的可能或不可能[J].小说评论,2013(5):90-94.
[6]晏杰雄,周刍.在混沌中走向宁静和清明——评吴刘维长篇小说《绝望游戏》[J].当代文坛,2013(1):142-144.
[7]南 帆.曲折的突围[J].文学评论,2006(4):50-60.
[8]吴刘维.虚构的力量[J].中篇小说选刊,2011(s3):41.
[9]吴刘维.创作谈:小说理应比生活更精彩[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3):85.
责任编辑:黄声波
M agical Reality,Contem porary Experience and Tim e Picture——On W u Liuwei’s Novel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ZHENG Run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China)
The long novelDesperateGame and novelettesNo Cellar in the Heaven,My Father-in-law isGetting Old Like That,Sending Snow Home,andSomeone Falls into theWaterwritten byWu Liuwei in recent years fully reflected his great attention on the text form of novels aswell as his creation ambition of conveying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and elaborating the time picture.
Wu Liuwei;magical realism;bottom literature
I207.42
A
1674-117X(2015)01-0010-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1.003
2014-05-28
郑润良(1976-),男,福建福安人,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