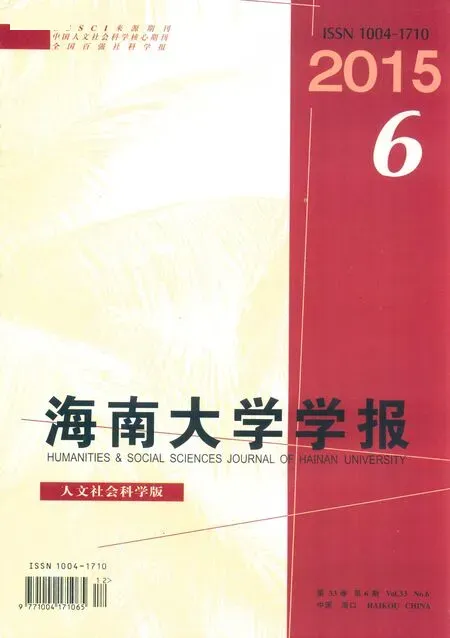杜甫《戏为六绝句》与曹丕《典论·论文》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杜甫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戏为六绝句》中,郭绍虞先生云:“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之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也。”[1]3笔者认为,《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1]3,并非“无所依傍”,正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所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2]同样,《戏为六绝句》在理论体系之建构和文学观点之阐发上,亦自有其“来处”,那就是全面继承了《典论·论文》的文学思想,这应当不是偶然和巧合。《典论·论文》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批评论、作家论、文体论、文气论和价值论五个方面,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诗学思想可以说与之环环相扣,极为契合。全面比较研究这两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文,这对杜诗学研究的深入拓展当不无裨益。
一、“文人相轻”与“轻薄为文哂未休”
曹丕的“文人相轻”观点与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轻薄为文哂未休”之论很相近。从曹丕的“轻”到杜甫的“轻薄”有一个发展过程,而曹植、刘勰、钟嵘的相关言论则是连接起二者的重要链条。以此为依据,对“轻薄为文”这一充满歧义并为历来学者聚讼纷纭的命题进行详尽而全面的辨析。
首先,《论文》开门见山指出了文学批评界的不良风气,即“文人相轻”,“轻”为轻薄、轻鄙、讥嘲之意,就如“而固小之”之“小之”。《戏为六绝句》也在第一、二首指出了这种“文人相轻”的陋习,所谓“今人嗤点流传赋”、“轻薄为文哂未休”云云,以嗤点、哂笑、轻薄等词对应“相轻”和“小之”。杜甫这种观点和语词上的对应继承是有其依据和渊源的。如曹植《与杨德祖书》针对孔璋不自见之患,“前有书嘲之”,又称“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3]166,“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3]166。曹植《与杨德祖书》与曹丕《与吴质书》和《典论·论文》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这里曹植以嘲、嗤、讥弹、诋诃、掎摭等语词来指责文学批评的弊端,正可为中介,让人们清晰看出杜甫嗤点、哂笑、轻薄与曹丕“相轻”的承传关系。
其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对《论文》借鉴引用最多,不但直接引魏文帝“文人相轻”之言,而且在具体引班固、傅毅的例子时,称“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以及“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云云[4]714,径以嗤、嗤笑来代替和表述。此外,如称“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4]714很明显,这里,“博徒”与“轻言”互文见义,即轻薄之徒的轻薄之言。
同样,钟嵘在《诗品序》中也对当时批评界的弊端有所指责,且直接用“轻薄”之词,如云:“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5]对此,可以说,杜甫“轻薄为文哂未休”之“轻薄”当是继承了曹丕、曹植、刘勰、钟嵘等大批评家之意,这应该是不错的。
其次,以此为根据,来辨析历来学者赋予“轻薄为文哂未休”的诸多歧义,并给出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综合郭绍虞先生《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来看,历来对其解释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
其一,称尔曹、今人哂笑四杰“为文轻薄”或文体轻薄。如郭绍虞云:“轻薄为文,是说当时人讥笑其文体轻薄。”[6]61这种观点自宋代以来差无异议,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引赵次公云:“四子之文,大率浮丽,太公以之为轻薄为文,而哂之未休也。”[1]17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杜子美笑王杨卢骆文体轻薄。”[1]17汪师韩《诗学纂闻》:“‘轻薄为文’四字,乃后生哂四家之语,非指后生辈为轻薄人也。”[1]21史炳《杜诗琐证》云:“轻薄为文,乃讥哂四子之言。以后生自为轻薄之文而反哂前辈,亦与上句不贯。”[1]21
其二,指后生、尔曹、今人“轻薄为文”、“为文轻薄”或文体轻薄。如卢元昌《杜诗阐》云:“‘轻薄为文’,谓今人文体轻薄,非谓轻薄四杰。”[1]20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轻薄为文,即今人也。”[1]21
其三,“轻薄为文”是分指的,“轻薄”指后生、尔曹、今人为轻薄之人及轻薄之口,这里的“轻薄”是与“文人相轻”的“轻”同义,也就是嗤点、哂笑之义,“为文”指四杰所作之文,合起来就是(尔曹、后生、今人)“轻薄”四杰为文而哂笑之。关于这一点,施鸿保《读杜诗说》所言最详:“四公之语言,当时杰出,今乃轻薄其为文而哂笑之……今按‘轻薄’字,始见《西京杂记》,‘茂陵轻薄者化之’,言人之轻薄也。绝句漫兴云:‘轻薄桃花逐水流’,《赠王侍御契》云:‘洗眼看轻薄’,《贫交行》云:‘纷纷轻薄何须数’,皆是此意。此诗谓后生轻薄之人,讥笑前辈为文也。前二说皆非。”[1]22之前亦有诸家持此观点,如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轻薄,即指后生辈。”[1]18黄生《杜工部诗说》:“‘当时体’三字,出后生轻薄之口,非定论也。”[1]20洪迈《容斋四笔》:“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1]20周甸《杜释会通》:“当今轻薄子每以前贤为可笑。”[1]20卢世漼《读杜私言》:“若王杨卢骆为轻薄所哂,几无完肤,而子美直骂轻薄身名俱灭,仍以‘万古江河’还诸四杰。”[1]20吴见思《杜诗论文》:“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当时文体杰出,今日轻薄之流,为文何似,而哂之哉!”[1]21张爕承《杜诗百篇》:“‘轻薄’、‘尔曹’,皆指后生。”[1]21仇兆鳌《杜诗详注》:“四公之文,当时杰出,今乃轻薄其为文而哂笑之。”[1]21
对于以上历代注杜学者的三种解释,郭绍虞先生总结道:“然谓杜推尊四子,而以轻薄为文指后生嗤点之辈,则亦未当。……故‘轻薄为文’当为讥哂四子之语。”[1]44由于郭绍虞先生之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影响,并专力集解《戏为六绝句》,再加上《中国历代文论选》在高校中普遍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之教材,故而他所支持的第一种解释基本成了学界的不易之论。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相近,只不过是主体的改换。
笔者认为,第三种解释当更为符合杜甫之原意,尤其是仇兆鳌和施鸿保以杜诗“其他论诗之句互为印证”,显得更为合理,而这正运用了郭绍虞先生的阐释方法,即“至于加以抉择,斟酌去取,则又一以杜甫论诗主旨为衡。本其集中其他论诗之句,触类旁通,互为印证,则群辐共毂,一贯非难,而诸家曲说,昭昭然白黑分矣。”[1]3惜其在本句中对此方法则未如施鸿保般加以运用。
我们说第三种解释更为符合杜甫原意,即“轻薄之人,轻薄之口,轻薄之意”,总起来说有三个理由:一是同意施鸿保“本其集中其他论诗之句,触类旁通,互为印证”的阐释学方法和依据。二是内证凿凿,即本组绝句中“不薄今人爱古人”之“薄”,亦仅为“轻薄”之意,而非轻薄之文或文体轻薄。三是旁证,即上文所论述的杜甫继承了曹丕、曹植、刘勰、钟嵘以来的相轻、轻薄、轻鄙、轻贱、嗤笑、讥哂等语词涵义和理论内蕴,而上述这一切文献论证都是为了说明杜甫对曹丕理论的接受和继承及两文之间的关系。
二、“贵远贱近”与“不薄今人爱古人”
与上文曹、杜所认识到的“文人相轻”及“轻薄为文”这一批评界弊端相关,在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上,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主张则完全继承了曹丕“贵远贱近”等论断。在如何实践这一正确的批评原则上,刘勰指出批评家的基本素养就是博观、博练、博见,而曹丕所谓“勤学、重寸阴、著书不朽、少壮当努力”以及“备历五经四部”等博学苦读的见解与杜甫“读书破万卷”这句经典亦不谋而合。此外,关于“文人相轻”这一命题中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主体以及涉及到的各自两组文人群体等,《绝句》和《论文》都有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贵远贱近”与“不薄今人爱古人”。针对“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曹丕提出“审己度人”的观点,同时指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崇己抑人(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的三种错误批评方法。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受其影响,在引用曹丕“文人相轻”之论后,提出了“贱同而思古”这一总的说法,同时提出与曹丕相近的三种观点,即贵古贱今者、崇己抑人者和信伪迷真者。对此,正如彭玉平所云:“最为典型的相轻形态——贵古贱今。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同时代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耳熟能详的‘贵古贱今’、‘贱同思古’、‘厚古薄今’都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7]
《戏为六绝句》中,杜甫也在论述文人相轻即嗤点、哂、轻薄之后,提出了他的学习和批评标准,即“不薄今人爱古人”,在如何对待古今遗产的态度上,给出了一个正面的说法,可以说是对曹丕“贵远贱近”,刘勰“贱同思古”和“贵古贱今”之反面说法的一个总结。另外,“不薄今人爱古人”也正同于刘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薄、爱”与“憎爱”同义,在句中是互文见义的。这与之前葛洪《抱朴子·广譬》所云“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情也;信耳而遗目者,古今之所患也”,之后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云“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所言相同,诸如此类颇多,兹不赘举。而元稹所谓“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之论显然是对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以及曹丕、刘勰理论的深入总结,其《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6]66
其次,“备历五经四部”与“读书破万卷”。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认为,要想做到文学批评上的公允,即“不偏于憎爱,无私于轻重”,那么,“务先博观”,即博览群书,勤学苦读,要重视学问积累,也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4]714,这显然继承了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谓“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嫒;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云云[3]166。《典论·论文》虽未有直接谈博览读书,但从其著书立言说及《与吴质书》和《典论·自叙》相对照则可以推而及之。
《论文》最后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继承了儒家立言不朽的传统,并在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穷达著书”说,即“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3]159并称徐干“著论,成一家言。”这种立言不朽、发愤著书而成一家之言的志向,显然是以“重寸阴”“惧乎时之过也”的珍惜时间的读书博观为基础的。在《与吴质书》中也用与此相似的说法,如称“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以及徐干“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3]165再如《与王朗书》:“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8]16而《典论·自叙》则明确提到“勤学”“备历五经四部”“靡不毕览”云云。如云:“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客,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8]12
同样,杜甫之“不薄今人爱古人”、“别裁伪体亲风雅”及“转益多师是汝师”等都是说要广泛学习古今作家作品,唯有“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也就是说,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公允批评标准,是与“转益多师是汝师”及“读书破万卷”分不开的,这显然继承了曹丕、曹植、刘勰以来的相关观点。
第三,“文人相轻”这一文学批评现象中,文人中的“轻者”和“被轻者”都是批评家主体,即是互相的。而作为《论文》和《戏为六绝句》之作者的批评家曹丕和杜甫,则是第三者,是旁观者,他们独立于“文人相轻”这一批评现象之外,所谓“旁观者清”,故而二者的批评标准都是客观公允的,这也是二文和二人的相似之处。当代学者诸如来新夏、彭玉平等的相关“文人相轻”论文中,也已同时提到杜甫和曹丕,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前后承传关系。
关于曹丕,来新夏在《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一文中称:“鲁迅对曹丕‘文人相轻’的口号有重大的突破,在《五论》一文中,认为‘相轻’之说只是站在旁边看文人轻来轻去的第三者,而真正卷入窝里斗的只有‘被轻’和‘轻人’两种。”[9]关于杜甫,彭玉平在《论“文人相轻”》一文中也引用鲁迅《五论文人相轻》云:“文人之间轻来轻去,难免有人看不过眼,起来棒喝一声‘文人相轻’,遂在相轻的文人之外多了一位第三者,虽也是文人,却不在相轻的文人之列。‘相轻’的文人与说‘文人相轻’的文人始终是生存在两个圈子中的。”接下来称“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于批评初唐四杰‘轻薄为文’、‘劣于汉魏近风骚’的‘尔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就属于相轻的圈外人,也就是第三者。”又称:“杜甫从诗歌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六朝、初唐文学的价值,从第三者的角度对‘尔曹’因为无知而相轻的现象做了严肃批评。”[7]
最后,《论文》和《绝句》中的“文人相轻”各有两组文人,其行文顺序及所论作家群体都有可比较之处,亦能看出二者之间的承传关系。《论文》开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接下来古以傅毅、班固为例,“今之文人”则以“建安七子”为例,一为个体,一为群体。进而提出他“审己以度人”的正确批评标准。《绝句》开篇两首论文人之嗤点哂笑,第一首以古代南朝庾信为例,第二首以今朝“唐初四杰”为例,也是一个体,一群体,然后提出他“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公允批评标准。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论文》中“文人相轻”的现象,古代是古代文人间即傅毅和班固之间,今之文人是七子之间的“良难以相服”。而《绝句》中,“轻者”皆为同一批人即今人、后生、尔曹,而被轻者分为古人庾信和今人四杰。二是,《论文》中不管古今文人,他们之间相轻的原因都是因为“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而《绝句》中的“今人、后生、尔曹”之轻薄之徒的轻薄之处就在于,他们既“贱古”(庾信)又“薄今”(四杰),眼中只有自己,真是“可笑不自量”(韩愈《荐士》语)。也因此,《论文》最后便以描述事实的反面批评标准“贵远贱近”和“向声背实”来作结,而杜甫则以与实际批评情况相反的正面批评标准“不薄今人爱古人”作结。
二者还有两点相似之处:一是,《绝句》中第一首和最后一首的前贤、后生之说,即前贤畏后生,(后生)未见前贤云云,《论文》中虽未有相关言论,但曹丕《与吴质书》中则提到:“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3]165两文是互补而且必须对照解读的,所谓“诸子但为未及古人”正与《绝句》“未及前贤”同,而“后生可畏”则是“前贤畏后生”的翻版了。另一个是,《论文》中称扬七子“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而《戏为六绝句》中赞赏“四杰”亦以“龙文虎脊”和“历块过都”为喻,同时在杜甫另一篇重要的论诗诗《偶题》中亦有“騄骥皆良马,麒麟带好儿”之句[6]64,俱以俊马为喻。
三、“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与“能诗不能文”“尽得古今之体势”
文体论是《典论·论文》理论体系中的重点之一,《绝句》中相关的文体观点与之有一定的相合之处,虽不是很鲜明,但若与后世学者对杜甫诗文文体创作的评论总结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杜甫的“能诗不能文”和“尽得古今之体势”与曹丕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及其“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极为契合。
首先,曹丕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与杜甫的“能诗不能文”。《论文》在第一段认为“文人相轻”的表现是“以己所长,相轻所短”,而所长所短都指文体而言。他反对这种文坛不良风气,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此外,因为四科八体不同,包括体裁体制之“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体”以及文体风格之“雅、理、实、丽”“四科”之不同,故而“能之者偏也”。也就是说作者个性禀赋不同,才能有限,故而大多只能偏长一体。他在具体以文体和文气(才性)评论七子的时候,七子都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鲜能备善。如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的辞赋虽“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对于其它文体,二者则都不擅长,即“然于他文,未能称是。”[3]158陈琳和阮瑀长于章表书记一类文体,为“今之隽也”,言外之意其它文体为其所短。这是从文体体裁的角度来说明他的“能之者偏也”的文体观。同时他还从文气清浊也就是文体风格的角度来说明他的作家“偏长一体”也即擅长某种风格的文体论,如称“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也就是说在“和与壮”及“壮与密”这两组因文气清浊不同而形成的对立文体风格中,二者都是偏长某一风格而不能兼备之。
《绝句》中,杜甫看到了庾信由南入北之前后期文体风格的转变和不同,前期之“徐庾体”是“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后期则“文章老更成”,形成了“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壮阔豪逸风格,而“今人嗤点”的则是他的“流传赋”也即前期宫体诗风,不免有偏,失之公允。此外,王杨卢骆的“当时体”,则指四杰擅长四六骈文文体体裁,即宋长白《柳亭诗话》所云“初唐四杰草创初开,未脱陈、隋风调”[1]19,黄生《杜工部诗说》所谓“四子未泯齐梁余习”[1]20,故而“轻薄”者“哂”之“未休”。这正如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所云:“‘当时体’三字。文章各代别有体裁,不得执一以论。”[1]21
在《绝句》偏长某体的文体理论之外,自宋代以来历代学者争议老杜创作上“能诗不能文”的文体论则一直绵延不绝,可以说是对曹丕《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体论的某种回应,对照起来颇有意味。大多学者认为“少陵拙于为文”,“无韵者殆不可读”。如陈师道云:“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诗样吟,退之不合以诗句似做文样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然开天以前文体,大略皆如此。”刘克庄云:“余观杜集无韵者,唯夔州府诗题数行颇艰涩,容有误字脱简。”仇兆鳌曰:“杜诗皆熔经铸史,而散文时有艰涩。”[10]鲁迅也称:“杜甫的诗好,文章也就不行。”[11]其原因,如熊礼汇所云:“前人分析杜文成就不高的原因,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即杜甫平生专注于诗的创作,仅以作文为余事,而作文又是以诗为文。”[10]
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意见者,通过反驳杜甫“能诗不能文”的文体观,进而肯定杜文的成就和地位,如刘开扬《杜文管窥》云:“世人每读杜诗而厌读杜文,以为非其所长,于我何益,盖未深思耳。杜文与太白、独孤及诸人之文亦四杰之后、韩柳之前文章发展之里碑也……欲知文章发展之历程者,不可不读杜文也。”[12]唐代司空图认为子美之文与其歌诗一样优秀,如《题柳柳州集后》云:“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思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13]所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云云,以杜甫为例,正可与曹丕“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之论相参看。
其次,曹丕“唯通才能备其体”与杜甫“兼备众体”和“集文体之大成”。《论文》中在肯定“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以及大多作者偏长一体的同时,与之相对立的,则提出“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论断,涉及到偏才与兼能的关系。这一点体现在《绝句》中,因为杜甫具有“别裁伪体”的辨体眼光和“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故而能够取得集文体之大成的巨大成就。关于杜诗的“集大成”特征和原因,自唐代元稹提出以来,历代学者多有论述,虽然所言各有千秋,但无疑“集文体之大成”应是杜诗“集大成”最核心的内容,其中包括集“文体风格”和集“文体体裁”之大成两个方面。他的这种“兼备众体”的“集文体之大成”说是对曹丕文体学思想的全面体现,并影响了宋以来相关文体理论的热议和争鸣。
具体来说,最早当属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6]66其后宋人继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严羽等大家都有精到论述。如欧阳修等《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14]秦观《韩愈论》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15]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16]严羽《沧浪诗话》云:“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其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17]明清以来所论亦不乏人,如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执此以论,杜真可谓集诗家之大成者矣”[1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李杜诗话》云:“微之、少游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释普闻《诗论》云:“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19]。
曹丕认为“唯通才能备其体”,也就是一个作家能够兼备众体与其才能有关,必须是“通才”方可。而杜甫之所以“诸体兼善”,这与他的“通才”是分不开的。如元傅若金云:“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植纲常、系风化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其集大成也”;清翁方纲《石州诗话》也认为杜甫之集众家文体之长,“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19];王运熙等在论杜甫时则将兼备众体和偏长一体结合起来:“杜甫历来被认为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指出,唐代许多诗人在创作上往往偏长一体,而杜甫则‘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20]。显而易见,上述历代批评家对杜诗兼备众体、备于众体、诸体兼善、尽得古今之体势、尽有古今文章之体的集文体之大成的高度评价和激赏,可以说就是曹丕“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体观的绝妙注脚,尤能说明杜甫对曹丕文体论的理论继承并通过创作实践体现出来。
第三,从文体风格论的角度来看,曹丕认为,不同才能、个性、禀赋的人,其诗文便显示出不同的风格来,也就是“文如其人”这一传统命题。《论文》中文气论的核心是“气之清浊有体”,也即清气、浊气和清体、浊体。这既是一种才性论也是一种文体风格伦。从才性论的角度看,曹丕指出作家的才能禀赋和气质个性是先天的,不可力强而致,提出了作家的才能、才气、通才之论。《戏为六绝句》中,杜甫则提出作家的“才力”,即“才力应难跨数公”。很明显,才力与才性相配。
所谓清气和浊气,清气指清健、阳刚之文体风格,也叫逸气,属壮美,也就是刘勰以来所说的“建安风骨”。浊气则指舒缓、阴柔之文体风格,也叫齐气,属优美,也就是齐梁绮靡之文风。曹丕显然欣赏的是前者。他在批评徐干“时有齐气”时,也肯定了刘桢有“逸气”。在《绝句》中,杜甫称许庾信文章的“老成”和“凌云健笔”及“纵横之意(气)”,便属于清刚之气,这正是曹丕所具有和肯定的“建安风骨”,相对应的则是老杜所代表的“盛唐气象”。杜甫欣赏“清”气在他文也处处可见,如所谓“清诗句句尽堪传”、“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等。尽管他极力赞赏清刚之气,但由于“转益多师”的态度,使他对不同的风格也能兼容并包,如《绝句》中的“翡翠兰苕”属优美阴柔之风格,而“鲸鱼碧海”则属壮美刚健之风格。
除此之外,关于文学的价值论方面,二者亦不乏相似观点。《论文》中,曹丕极大地肯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荣乐等都“未若文章之无穷”,“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便“声名自传于后”,提倡“发愤著书”、“穷达著书”而“成一家之言”,这完全继承了儒家立言不朽的文学价值观。《绝句》中,这种立言不朽和扬名于后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中,可以说就是对曹丕理论的浓缩和概括。而杜甫另一篇重要且能代表他诗学观的论诗诗《偶题》,开篇四句则又是对这一观点的重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其间关系,读者当自得之。
[1]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郑永晓,辑校.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733.
[3]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钟嵘.钟嵘《诗品》校释[M].吕德申,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55.
[6]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彭玉平.论“文人相轻”[J].中山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34-41.
[8]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来新夏.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N].光明日报,2003-08-13.
[10]熊礼汇.杜甫散文创作倾向论——兼论杜甫以诗为文说[J].杜甫研究学刊,2002(2):13-25.
[11]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N].文艺报,1956:19.
[12]张忠纲,赵睿才.20 世纪杜甫研究述评[J].文史哲,2001(2):13 -21.
[13]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50.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38.
[15]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M].虞行,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03.
[1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4.
[17]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71.
[1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98.
[19]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J].文学评论,1986(6):99 -106.
[20]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