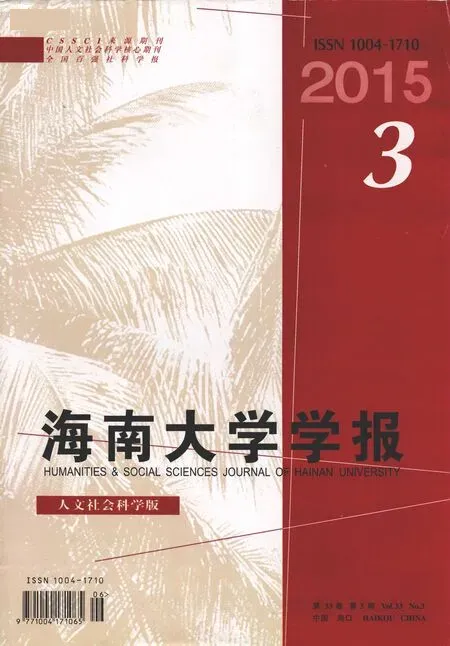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贾冬阳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570228)
“哲学”(φιλοσοφíα)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爱智慧”。那些亲自观察“自然”并将观察经验上升为抽象理论之人也因此被称为“爱智之人”(φιλóσοφοι)。但众所周知,“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如何理解此间差异?
最初,“爱智之人”被称为“论述自然的人”,以区别于“论述神的人”。因此,哲学最早的主题是“自然”,而非“习俗”[1]2。但据说,苏格拉底扭转了“哲学的朝向”,他将哲学从“天上”降至“大地”,并置于被生死善恶围困的人世,哲学自此事关诸如城邦与政制、操持与礼法、灵魂与正义……①在施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开创了对自然事物的新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诸如正义的自然或理式,或者说自然的正义,以及人或人的灵魂的自然,是比诸如太阳的自然更为重要的。”参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5 页。另参见林国华,《哲学朝“圣”的未完戏剧——〈巴门尼德篇〉剧情初步分析》,载《柏拉图的哲学戏剧》,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4 页。,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苏格拉底是在监狱中把哲学看成践行生死之举,还是在阿伽通家里把哲学等同于“爱欲”并进而思考“整全”,都是这一“转向”的结果——从“自然”转向“人世”。在这个意义上,探问“哲学是什么”,就与如何理解苏格拉底密不可分。
但,苏格拉底是谁?或者说,苏格拉底具有怎样的哲人面相?
据说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主要的资料来源有4 种,其中占时间之先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记述最丰的则是柏拉图的35 篇对话录。但奇诡的是,二者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却迥然相异。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具有“双重面目”或者说是“两种爱智者”的合体:既是生活在云端、具有探索天上地下奥秘之卓越“智能”(intellect)并因此超离城邦政治生活的“自然学家”,又是混迹市井,凭靠“智术”(sophistry)移风易俗贩卖意见败坏青年的“智术之师”。似乎是专门针对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则让人看到完全不同的哲人面相:自己的老师既非“爱智能”的自然学家,亦非“爱智术”的新派智识人,而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居间者”[2]22——这个“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对自然哲学一无所知,当然更是智术师的死敌[4]163-164。但令人惊讶的是,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笔下面相如此迥异的苏格拉底,却有着相同的命运——都被城邦判处了“死刑”。只不过,一个被烧死在舞台上,一个饮鸩狱中。何以如此?问题依然是:苏格拉底是谁?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的记述哪个更真实?抑或各有显隐?哲人面相隐没在重重迷雾之中……
一、“光与死”:阿里斯托芬喜剧《云》的谋篇
斯瑞西阿德斯的“痛苦尖叫”拉开了《云》的序幕,开场时正值茫茫黑夜。备受债务煎熬的斯瑞西阿德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盼着“天亮”②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布鲁姆说:“启蒙就是给过去黑暗的地方带去光明,就是用有关自然的科学知识取代原有的想法,即迷信”。见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占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11 页。对观埃斯库洛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452-3 行。。债是儿子欠下的,但他却毫不挂心,裹着羊皮大氅酣睡不已。奴仆也不服管束,鸡早就叫了,还赖在床上打呼噜。斯瑞西阿德斯感叹,战争搅乱了一切。这是开幕第一个场景[5]1-15。再看结尾,《云》以什么落下帷幕?同样是“痛苦尖叫”,不过这次叫喊的不是斯瑞西阿德斯,而是惊惶失措的苏格拉底和他的门徒。阿里斯托芬以一头一尾两次“痛苦尖叫”,把整部喜剧框在了中间。换言之,诗人用“痛苦”框住了“笑”。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如此谋篇有何意图?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斯瑞西阿德斯为何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切都源于自己“不恰当的婚姻”[5]38-55。
斯瑞西阿德斯本该是个过着快乐乡间生活的农夫,自从莫名其妙娶了一个娇奢懒惰毫无节制的贵族女子之后——“门不当户不对”——一切都变了,不仅二人各自原有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还生养出一个热衷赛马放纵无度的败家子——斐狄庇得斯(Φειδιππ δηζ)。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是“节俭”和“马”两重意思的组合。斯瑞西阿德斯本想依照父亲的名字叫儿子“节俭美德”,老婆则希望儿子更有贵族范儿,于是起名叫“骏马”、“福马”之类。争吵了很久,最后折中叫“俭德马”[5]57-65。如同这个含混名字的由来一样,父母二人按照各自的心性和生活方式塑造斐狄庇得斯。结果,母亲教导的“欲望”战胜了父亲希冀的“节制”,在斐狄庇得斯的灵魂中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底色。果不其然,热衷赛马的斐狄庇得斯不仅败光乃父家财,还欠下一屁股债。在希腊文中,“债务”(χρεζ)这个词与“必然”(χρεν)有共同的词根,意味着“对一个人的约束”——欠债还钱像“必然性”一样不可避免——它使人的自由受限[6]。反过来,“赖账”或者说“欠债不还”,就意味着追求“不义的自由”。
如果不是为了“赖账”,斯瑞西阿德斯不会想到苏格拉底和他的“思想所”。在他看来,只要给钱,这个人和这个地方,就能让儿子斐狄庇得斯学到赖账的技艺。这一细节暗示:哲学与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与“不义的自由”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无独有偶,在《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第一章,色诺芬也讲了一个苏格拉底与年轻人谈论自由的故事,但立义、取向与阿里斯托芬完全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渴望自由”的阿里斯提普斯说,控制自己身体欲望的能力即自制力,乃人之为人的标志之一。正因为人有自制力,才不会像鹌鹑、鹧鸪之类的鸟儿或其他动物那样因贪欲引来杀身之祸。言下之意,没有控制自身欲望的能力而热切地追求所谓的“自由”,与鹌鹑、鹧鸪之类的鸟儿或其他动物无异,不过是追求贪欲满足之徒甚或欲望的奴仆。借此反观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角色与情节,人们不禁要问,斯瑞西阿德斯之所“求”与思想所之所“教”,究竟有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传授两类“知识”或“技艺”:一是追求纯粹理则的“自然学”(诸如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生物学、音律学等),一是强词夺理变幻莫测的“诡辩术”。虽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但二者——要么超越政治,要么败坏政治——都以“自由”的名义将人带离属人的“居中之域”。《云》中的一切恶果,都根源于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人在传授斯瑞西阿德斯所求的诡辩赖账之“技艺”?阿里斯托芬让雅典观众以及后世的读者看到的是从“吊篮”下降到“地面”的苏格拉底!不过,下到地面后,其言传身教已非蔑视常人的自然学家的做派,而更像另一种人——“智术师”。
公元前5 世纪下半叶,一场对整个西方影响至深的“启蒙运动”席卷了希腊各个城邦、尤其是民主的雅典③参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雅典的智术师启蒙运动与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本质上一以贯之。。在这场运动中,最积极的鼓噪者就是周游列邦兜售各种新奇知识的“智术师”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智术师的经典定义即:“智术师实际上不就是贩卖滋养灵魂的东西的大贩和小贩吗?据我看,智术师就是这样子的人。”(《普罗塔戈拉》,313c)。他们为启蒙运动打上了这样的标记:摆脱传统宗法观念的束缚,通过技术理性解决所有现实政治、经济乃至伦理问题。换言之,缺乏慎微美德的新派智术师,把只适合极少数人在“思想所”中搞的形而上学普及化或通俗化,公开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言下之意,人人都应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敢于以普遍怀疑的精神质疑习传宗法与政制秩序⑤启蒙大师康德曾借用贺拉斯的诗句为“启蒙”打出这样的口号:“Sapere ande(敢于明智)”!与普罗塔戈拉之见简直如出一辙。在《答何谓启蒙》中,康德认为,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乃是一种“不成熟”,启蒙就是“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反驳康德,与康德同时代的著名哲人门德尔松,大文豪维兰德分别通过翻译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两个苏格拉底的优秀学生的著作,来清除启蒙哲学的“流毒”。参见刘小枫编修《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47页。。面对雅典民主文化中的教育乱象,苏格拉底告诫雅典盲目而热切的向学青年,智术师们贩卖的东西对人的灵魂是否真的有益,他们自己并不清楚,除非买主碰巧是个“灵魂的医生”。否则,一旦付了学费、经过学习,智术师的教导就“进到灵魂本身中去了,离开时,灵魂肯定已经不是受到损害就是获得了裨益”[7]314b。这无异于说,作为启蒙者的智术师自身就需被启蒙——启“启蒙”之“蒙”。
害怕被训练成一个女里女气的白面书生,斐狄庇得斯死活不肯去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否则还怎么见自己的骑士朋友[5]119?无奈之下,老迈不堪且记性很差的斯瑞西阿德斯只好硬着头皮亲自前往。
仅凭“我是来求学的”,斯瑞西阿德斯就被苏格拉底的门徒当成了自己人,轻易便混进了思想所低矮的门墙。当他突然看见坐在半空吊篮中“凝视太阳”的人时,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要找的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对斯瑞西阿德斯说的第一句话则是,“朝生暮死的人啊,你叫我做什么?”[5]225虽然苏格拉底瞧不起朝生暮死的常人,但在斯瑞西阿德斯的“央求”与“诱惑”下,还是从“空中”下降到“地面”,同意教他“高深的学问”[5]235。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学得了高深的“自然学”或“形而上学”,亦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追求“云一般的自由”[5]314-334。虽几经启发、引导、调教,既蠢又笨的斯瑞西阿德斯还是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观察世间万物,苏格拉底失望之极,一怒之下将其赶出了思想所[5]783-794。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对苏格拉底和他的思想所来说反倒是好事,思想所仍将像往常一样平静的研究天上和地下的事物[8]27。可是别忘了,斯瑞西阿德斯有个天性不良但却聪明伶俐的儿子。在“云神”的鼓动下,斯瑞西阿德斯逼迫斐狄庇得斯进学“思想所”。进学之前,斐狄庇得斯严厉地警告父亲,“总有一天你要后悔的!”可以说,接下来的剧情朝着斐狄庇得斯的这一警告性“预言”或“诅咒”发展[5]864。
但意味深长的是,阿里斯托芬设计了一个奇特的情节——在云神的主持下,最终败坏并“磨亮”斐狄庇得斯舌头的,不是苏格拉底,而是在与“正理/正义言辞”对驳中胜出的“歪理/不义言辞”[5]889-1114。换言之,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传授“歪理”,但最终服膺“正理”还是“歪理”,完全是斐狄庇得斯自己的选择[8]29。可是,“歪理”毕竟来自“思想所”,因此,苏格拉底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正理/正义言辞”和“歪理/不义言辞”之间的交锋,俨然古今“教育法权之争”。“正理”秉持古老的道德与教育观,“那时代我成功地传授正直的德行,人人都遵守贞洁、谨慎、廉耻和节制”[5]960-999,叱责“歪理”诉诸“自然的必然性”的新式道德与教育观无耻、下流,通过鼓荡“不义的自由”、撩拨无节制的欲望而败坏青年,告诉他们一切只要快乐就好……结果使他们心胸狭隘、长舌如妇,还“把坏事看成好事,把好事看成坏事”[5]1008-1023。面对“正理”的叱责,“歪理”断言,根本就没有正义这种东西[5]901。“正理”反驳说,正义在诸神那里!“歪理”质问“正理”,如果正义在神那里,那么宗法诗人笔下描述的那些“神的不义”又该如何解释呢[9]185?“正理”无言以对,只能以谩骂回击。施特劳斯深刻地发现,无论“正理”还是“歪理”,双方的前提都是:“宙斯存在,人们必须按照宙斯的意志生活”。区别则在于,“‘正理’暗示,人们应该照宙斯的话去做,‘歪理’则坚持认为,人们应当或可以模仿神,做宙斯所做的”。由于没能辩赢正义与神同在,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正理”绝口不提宙斯或诸神支持正义,直接导致了“正理”的失败[8]29-30、33-34。
学徒期满,斐狄庇德斯被塑造成了一个“新青年”。凭靠所学,他不仅羞辱了债主并赖掉全部债务,甚至连父亲和诸神也不放在眼里。他兑现了先前的“诅咒”,借“启蒙歪理”的不义言辞,不仅证明儿子打老子天经地义,还通过援引欧里庇得斯关于兄妹乱伦的诗句来证明母子乱伦也是正当的……[5]1418。
“打父亲”和“乱伦”都意味着:“家庭”被摧毁了,“父子关系”也随之分崩离析。而这一切,正是斯瑞西阿德斯无比珍视的生活基础。“家庭”及其“伦常秩序”的破坏,无异于毁掉了他赖以生存的根基。对神的畏惧是禁止乱伦的唯一保障。但启蒙智术师的教诲却恰恰摧毁了这一保障,最终导致斯瑞西阿德斯失去了他的家庭[8]41-49。“受苦”让他重新学会敬畏神明。斯瑞西阿德斯一边后悔不迭,一边怒不可遏纵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苏格拉底终因“渎神”和“败坏青年”二罪而遭致灭顶之灾。
作为保守派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表面上轻松、谐趣甚至粗俗,但关切的主题却非常严肃,他始终关注城邦政治生活与家庭以及私人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云》剧的谋篇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云》以斯瑞西阿德斯对“天光”(理性之光)的吁求开篇,以启蒙思想所在“火光”(习俗之光)中的灰飞烟灭收尾,一头一尾两种“光”刚好把整部喜剧框在了中间,也把“死”框在了中间——要么“家庭”与“城邦”死,要么“哲人”死。换言之,在现实欲望中凭靠“信仰”与“权威”生活的城邦民众,不管信仰多么坚定,权威多么神圣,都经不起启蒙精神的“蛊惑”与“解构”——“旧的生活摧毁了,新的生活又在无限遥远的灰色云雾中——他们不找苏格拉底清账找谁?”[10]
如此令人震惊!在关涉苏格拉底的历史资料中,占时间之先的竟然是一部“喜剧”,而且还是一部夸张的把苏格拉底描述得既邪恶又愚蠢、荒唐可笑的喜剧!虽然施特劳斯精妙的分析让人看到阿里斯托芬“友好示警”的可能性,但事实上,作为“原初的控告者”,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中”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毕竟与雅典民主法庭在“现实中”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一道,把苏格拉底送上了饮鸩之路[2]52。
二、柏拉图纠弹阿里斯托芬:《申辩》之为关津
不算“书简集”,在柏拉图传世的35 部对话中,明确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有27 篇,其中有25 篇直接以某个人物命名。除了神话人物“米诺斯”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据此可以确定,在“戏剧笔法”之外,柏拉图写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史家笔法”。二者混合交织在一起,既描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又显示了哲学与政治、知识与意见、哲人与民众、启示与理性的悖论式紧张及其各自的限度。问题依然是,作为柏拉图作品中唯一的或者说真正的主角、或隐或显贯穿其全部作品的苏格拉底,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柏拉图为什么要记述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政治时期的“哲学生活”与“政治遭际”?较之苏格拉底在喜剧中的形象,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如此高贵、睿智、中和,何以与阿里斯托芬笔下那个可笑的角色有着相同的命运?柏拉图的“史家笔法”显示着什么,他的“戏剧笔法”又隐藏了什么?困难重重。难怪伯纳德特意味深长的说,“‘哲学是什么’似乎与如何阅读柏拉图这一问题密不可分”[11]。
在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中,题目中唯一出现“苏格拉底”名字的是《苏格拉底的申辩》。这是《申辩》独一无二之处,它的独特性还在于描绘了苏格拉底的一生,描绘了他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与城邦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12]54。这种“紧张”迫使苏格拉底在整个城邦面前为自己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辩护,以应对“喜剧”和“现实”的“双重指控”。对苏格拉底而言,“原初的控告”比“当下的指控”更可怕,因为陪审团中很多人从孩童时代就被他们说服了,换言之,苏格拉底不信神的传言在雅典人的头脑中由来已久[2]52。无论如何,苏格拉底之死,深刻影响了柏拉图一生的思考与写作。施特劳斯看到,柏拉图的35 部对话,正是35 部哲学的辩护书。因此,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法庭以“渎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判处死刑这件思想/政治事件,是阅读柏拉图的“首要前提”,用施特劳斯的话说,是进入柏拉图思想世界的大门[12]54。那么,柏拉图笔下的哲人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
柏拉图并未申诉城邦的判罚本身有问题,而是力图表明,雅典民众搞错了人。这无异于说,无论是谁,只要“不信城邦的神”且“败坏青年”,都该被判刑。因此,苏格拉底的自辩,也就集中在自己如何对待“神”与“青年”上。虽然在整个“申辩”中,苏格拉底主要对付的是关于他败坏青年的指控,但城邦对苏格拉底的主要控告则是不敬神[12]68。因此,搞清楚苏格拉底与“神”的关系,就有可能理解苏格拉底式的爱智活动何以非但没有败坏青年,反而为了雅典青年灵魂之美善以及城邦的“好生活”而殚精竭虑。
根据最早的记载,苏格拉底从对神圣或自然事物的研究转向全力探索“人类事物”,即正义的事物、高尚的事物以及对人之为人而言是善的事物,似乎恰恰是出于他的“虔敬”[1]4。
事情起于凯瑞丰(注意他在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形象)去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求谶,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2]54-55?女祭司皮提亚的回答是否定的。来自德尔斐的神谕让苏格拉底大为惊讶:按其本性,“神绝不会说谎”,但他“自知无知”,自知即便有知也不过是“属人之智”(human wisdom)而非“超人的智慧”(wisdom greater than human)[2]54。神谕究竟何所云?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苏格拉底开始“到处巡游”,省察自己、检审他人——只要是“自以为”或“众人以为”有智慧者,他都盘查到底,像一只牛虻粘在马身上,“明知会结怨,满腔苦恼、恐惧”,但“必须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2]56,“不做任何背义慢神之事”[2]68,“不计性命安危,宁死勿辱”[2]65。
什么样的“检审”或“探问”会危及性命?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写作都告诉世人,苏格拉底关心这样的人世问题:“节制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虔敬是什么?”、“德性是什么?”、“知识是什么?”,诸如此类⑥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甫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他(苏格拉底)时常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问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虔敬的,什么事是不虔敬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I.1.16。另参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51 页。。“X 是什么?”,这是典型的古希腊哲学的探问方式,它探究事物的“本质”或者说“自然”。但这种“知- 无知”的哲学探问,却让苏格拉底经历了从“质疑神谕”到“宁死事神”的转变[2]65-66,70-71。由此可以说,苏格拉底一生的爱智活动都与“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苏格拉底那里有“哲学”,那么,他的“哲学”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绝非冲突性的。换言之,苏格拉底的哲学与超验的神域之间保持着一种内在相关。这种“相关性”,更因“神”的显/隐而扑朔迷离:引发、指令苏格拉底终身从事爱智活动的,是“显白的城邦神”阿波罗;而使苏格拉底得以被引发并领悟哲学之居间品性的,则是自幼年即降临其心的“隐微的命相神灵”⑦在古希腊语中,“δαι?μων”有“精灵”的意思,又有个人生活方式的意思。“δαι?μων”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介乎于神、人之间并“沟通神人”。关于苏格拉底的Δαι?μων,可参阅《申辩》31d,《会饮》202e 以下,亦见《申辩》40a-c,《游叙弗伦》3b,《王制》496c,《泰阿泰德》151a,《斐德若》242b-c,《忒阿格斯》128d 以下。另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第65-66页。。可见,苏格拉底听命于“两个神”:
一个是与生俱来的神秘神,它指示苏格拉底说“不”──即“无知”;另一个是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指示苏格拉底说“是”──即判断一切聪明人“是”不聪明的;两者合起来,得人的基本命题:“知无知”。详细地说,人可以“知向”最高智慧,但不可以“知得”最高智慧,所以,人归根结底是无知,即必须对神的智慧保持敬畏。[13]
“有形的”城邦神与“无形的”命相神灵,彼此既有截然相异的功能性区分,亦有合辙接榫的相契之处[12]64,73,二者一显一隐,在苏格拉底的生命中交织,共同塑造了其哲学品质与一生行止。然而,正因与神的这种内在相关性,或者说正是为了“事神”,苏格拉底才运用“反讽”与“助产”,亟亟于灵魂之美与城邦之善,“不计性命安危”,终致包括阿里斯托芬以及工匠、政客在内的雅典民众难识哲人面相,前后相继,共同将苏格拉底送上“审判”之路——正是在此众目睽睽时,苏格拉底点了阿里斯托芬之名并复述了包括他在内的“原初控告”:苏格拉底“行事不义,是个研究天上地下的事儿而瞎忙的人,还强词夺理,并将这些玩意儿传给他人”[2]52-53。在阿里斯托芬看来,苏格拉底无非“两种爱智者”的合体,而在《申辩》乃至其全部对话录中,柏拉图则让人看到,他的老师既非“智能昭昭”探究天地的自然学家,亦非“智术煌煌”强词夺理的智术之师,更未将这一切传授给雅典青年(苏格拉底否认他有过任何学生),而是关心雅典青年的灵魂,敦劝他们“修身进德”,而非在财富、名声和荣誉方面终身营营。概言之,苏格拉底的爱智活动主要体现在规劝人们把德性作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灵魂之美”与“城邦之善”乃苏格拉底的爱智生活终身关切之所在。
基于此“关津”,就有可能踏上理解哲人面相的另类道路,这条路执两端而扣中庸。
似乎专门为了纠弹喜剧诗人对此“双重面目”的指控,柏拉图在《泰阿泰德》⑧本文所引柏拉图《泰阿泰德》主要依据Joe Sachs(Plato’s Theaetetus,St. John’s College,Annapolis,2004)英译本,参考严群先生中译本(《泰阿泰德 智术之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插入了一段“题外话”:柏拉图戏剧般地重构了各执一端的这两类爱智者,并借“助产士”之喻,使苏格拉底与其保持了微妙的区分。柏拉图的笔法似乎在暗示,只有搞清楚了“自然学家”与“智术师”是谁,才有可能真正认清“哲人”的本来面目。
三、《泰阿泰德》中的“题外话”:在“智能”与“智术”之间
在历史考证派语文学家看来,与柏拉图的其他作品相比,《泰阿泰德》的写作年代与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都能精确确定[14]454;[15]915。之所以容易确定,基于两个情节要点。在对话结尾,与泰阿泰德谈完后,苏格拉底随即前往王者门廊应对梅雷图斯的控告[16]13,这得以确认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对话发生在公元前399年,即苏格拉底死前不久。那时泰阿泰德还是一个少年,或者说是一个尚未成年的毛头小子[16]14-15,虽尚未达至其天赋的顶点,但却天性敦敏、品行卓越。而在《泰阿泰德》的“序幕”中,泰阿泰德则已成为城邦栋梁,因在战斗中英勇负伤而被人从科林斯的营地抬回雅典。正是因为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欧几里得和忒赫珀希翁一致认为,泰阿泰德是个“真正的君子”,“既高贵又善良”[16]13。
历史上,有关科林斯的战役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94年,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69年。欧几里得称,与苏格拉底交谈时,泰阿泰德尚未成年[16]13。古典语文学家们根据这一情节,推测柏拉图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69年以后不久,是为了纪念泰阿泰德之死[14]454-455;[15]915-916。令人惊讶的是,得以确定“对话时间”和“写作时间”的这两个情节要点,一个在“结尾”,一个在“开篇”;一个暗示了苏格拉底之死,一个描绘了泰阿泰德阵亡前奄奄一息时的情状,也就是说,柏拉图用泰阿泰德和苏格拉底的一前一后两种政治性“死亡”框住了整部对话。柏拉图无异于在提示他的读者,要想恰切理解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对“知识本性”的理论探究,必须将其与对话的“政治处境”结合起来。若不顾微妙的戏剧性情节而单抽取所谓的“知识论”,很可能意味着一启步就踏上了歧路,丢失的将远远多于所获。
在《泰阿泰德》中,柏拉图讲述了在哲人苏格拉底、数学家忒奥多洛斯和智术师普罗塔戈拉之间展开的一场竞赛——谁才真正是雅典青年才俊泰阿泰德的“灵魂托管人”?换言之,谁才能给泰阿泰德以最好的德性教育?虽然此时普罗塔戈拉已经死去多年,但苏格拉底却通过“模仿”普罗塔戈拉的逻辑与言辞,使他参与了这场“教育法权之争”。但模仿智术师,难免使苏格拉底看上去就像个“智术师”——雅典人,包括阿里斯托芬在内,有能力辨别苏格拉底反讽般的“模仿术”与智术师的“修辞术”之间的区分吗?或者说,诗人有能力看清哲人的面相吗?起码数学家忒奥多洛斯就看走了眼,他把苏格拉底和普罗塔戈拉看成了一类人,即沉湎于玄谈(bare speeches)之人,他声称自己很早就放弃这种玄谈而转向了几何学[16]52。同样,在与苏格拉底交锋时,“无法感觉的数字与无处不保持同一的图形”即纯粹数理学问似乎也不在智术大师普罗塔戈拉的视野中[16]53-57。但是,当苏格拉底称普罗塔戈拉是忒奥多洛斯的“同道”和“老师”时,忒奥多洛斯却并未拒绝,于是,苏格拉底便巧妙地把数学家与智术师连接在了一起[16]51。柏拉图微妙的笔法让人看到,表面上数学家与智术师之间互不搭界、相距遥远,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抽象的理论生活的典范,一个是显赫的政治生活的高手——分居两个极端。但恰恰在“智能”与“智术”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隐秘关联。正是这两个极端,为测度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所隐喻着的“居中之路”或“临界之思”提供了参照系[17]54。这一“两极测度”在“题外话”中达至顶点。
苏格拉底在“题外话”中重构了两类爱智者——拥有“闲暇”的自由人与为法庭“滴漏”所限的演说家。为了获得对“存在”的认识,前者不计时间、自由地谈论,“只要他们能够切中要点发现真理”[16]64;后者则不然,处处为时间所限,且仰法官和雇主鼻息而行止。在郝岚看来,这段“题外话”绝非无关紧要的插语,实乃苏格拉底“针对这两类人在生活与灵魂上的差异的精心之作。”[17]57,297这令人想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
上升与下降是同一条路,“云上”的苏格拉底与“地上”的苏格拉底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前者穷究天上和地下的奥秘,后者则授人修辞术,二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同一性”,即苏格拉底必然依据自然学传授修辞学[8]20。这与《泰阿泰德》题外话中的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题外话”中重构这两种人,意欲何为?
沉湎于抽象理论的自由人在哲学上消磨了大量时间,他们自幼不知法庭、议会或其他公共场所之所在,轻视权力、财富、荣誉以及肉体的欢娱,“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遍究一切物性、而求其真其全,从不肯屈尊俯就近旁琐事”,甚至连邻居是人与否都不分晓[16]65。这类人在谈论哲学、几何学、天象学时游刃有余,一旦进入公共生活谈论俗世俗务则捉襟见肘,荒唐可笑,难免成为婢女的笑料和喜剧诗人的天然主题[8]4。忒奥多洛斯承认苏格拉底所言不虚,全是事实[16]67-68。反之,混迹市井、逗留于法庭之上的演说家则巧舌如簧强词夺理,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弱的变成强的,而一旦把问题提升至诸如正义与不正义的本质、幸福与苦难、以及一般而言“人是什么,其本性何以在行动上与其他物性相区别”等问题时[16]67-68,情况便倏然翻转,头昏脑胀、口舌拙笨、言语呐呐[16]68。“题外话”中这两种人所具有的生活方式和灵魂特征,与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原初指控几乎别无二致。虽然,《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更纯粹的自然学家,而“题外话”中的“哲人”则更关心伦理问题,但二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这一区分不至于被过分夸大,因为他们都是用抽象的“同一性原则”来审度人世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灵魂上的“差异性”[8]50。智术师似乎知晓这种“差异性”,但却因标榜“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丧失了一切尺度,坠于人世无法承受的虚无。
至此,通过柏拉图的笔法可以看到,无论是《申辩》中自我辩护的苏格拉底,还是《泰阿泰德》“题外话”中两面作战的苏格拉底,都不属于天上地下这两类爱智者中的任何一类。他们无论哪一类,都遗忘了“居中的人世”。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两类爱智者所开启的两端,才反衬出哲人的“临界身姿”。
四、结语、微妙之“二”
与独断形上本体的“自然学家”和鼓吹相对主义的“新派智术师”不同,柏拉图让人看到了一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恪守中道的“临界哲人”的爱智身姿。这令人回想《会饮》中“第俄提玛的教诲”,正是这位“异乡女先知”,引导苏格拉底看清了自己的哲人“命相”。
第俄提玛从“爱若斯是谁”讲起。她让苏格拉底认识到,作为“城邦神”波若斯(丰盈)和“城邦人”珀尼阿(贫乏)之子的“爱若斯”既不美也不好[3]72-73。他是一种“居间”的东西,即在“丰盈”与“贫乏”、“智慧”与“不明事理”、有死的人和不死的神之间。正因为“居间”,爱若斯才能把人们的祈求和献祭传译和转达给诸神,把诸神的旨令和对献祭的酬报传译和转达给人们,他使“神- 人”作为整体“连成一气了”[3]75-76。
作为城邦神与城邦人的子嗣,爱若斯虽然相貌丑陋且总与贫乏为伴,但却天性爱美。而“智慧”就是最美的东西之一,因此爱若斯必定“爱智慧”。那么,什么人总在图谋美的和好的东西并终生热爱智慧?第俄提玛告诉苏格拉底,“没有哪个神爱智慧,也没有欲望要成为有智慧的,因为,神已经是有智慧的了”[3]77,只有哲人才意识到自己的“欠缺”,才追求智慧,这种追求的最高状态就是“哲学”⑨关于“哲学”,对观《会饮》204b;《苏格拉底的申辩》20b-23b;《王制》472e-480a。。因此,爱智慧的人就处于“有智慧的和不明事理的之间”,他拥有的至多是“正确的意见”[3]73。拥有“正确的意见”意味着,哲人要对高和低、美和丑都有所认识,才有可能沟通高低、贯通美丑。单单追求高的东西,或沉溺于低的事物,都丧失了“整全”的视野。通过第俄提玛之口,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传递了一个重大教诲——作为对智慧的爱,苏格拉底式的哲学虽然总在追求美的和高贵的东西,但却必须从认识低的和丑的事物开始,并将其作为通往美和高贵的必由之路⑩对观《帕摩尼德》130c-e;《会饮》201e-202a,203c-204b。。
第俄提玛引导苏格拉底,或者说苏格拉底引导具有爱智热情的年轻人,为了“美本身”,爱智的有情人必须从那些具体的感官现象出发,沿着“爱欲的阶梯”,从一个身体、两个身体到所有美的身体,进而发现“灵魂之美”。苏格拉底举了两种灵魂之美,一种是美好的生活,一种是美好的法律。苏格拉底说,要是遇到一个人有美的灵魂,即便他的身体丑陋不堪(比如泰阿泰德),有情人也会爱恋他、呵护他,通过美好的言辞,使他变得更美、更高贵,于是需走向“操持”与“礼法之美”[3]89-90。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让人看到一个奇异的变换——为了教导情伴,有情人自己必须首先去关注和操持礼法之美。在此,教育与受教育交织在一起。经过这些操持,有情人才被领至各种知识面前,得以领略美的沧海,直至最终瞥见“美本身”[3]90-91。
在文本中,柏拉图以极其隐微的笔法暗示,一旦跨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谈论绝对抽象之美,“静观”就取代了“爱欲”,换句话说,静观吹熄了爱欲之火⑪1。吹熄了爱欲之火的“纯粹静观”,还是“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爱智慧”吗?爱若斯之为爱若斯,能最终挣脱、抛弃大地上的“母亲”而飞越至“父亲”的居所——神的领地?柏拉图的笔法让人看到,第俄提玛话锋一转,把对“美本身”的追求转换为对一种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追求“美本身”,归根结底为了“生育、抚养真实的美德”[3]93。换言之,大地上这热爱美与善的“生活方式之美”,才是属人的爱欲真正能够追求的。正如柏拉图在《斐多》中记述的,苏格拉底临刑前对一群热爱哲学的青年强调,人世间的或者说大地上的美才真正色彩缤纷、美不胜收……
第俄提玛最终让青年苏格拉底意识到,作为“居间的哲学”,既不能无度上升、僭越至美本身的明朗光照中,因为那是神的领地[3]77-78;亦不可两极震荡而翻转、沉潜于非存在的幽暗之所,因为那是人世无法承受的虚无之境。它只能临界探问于洞悉与昏昧、至善与虚无、光明与黑暗之间的隐微之地[18]159-160。正是在此“绝对”与“虚无”之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结果的“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16]51。真正执两端而扣中庸、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1]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M].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4]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五讲·第一讲[M]∥林晖,译.潘戈.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阿里斯托芬.云[M]∥罗念生.罗念生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尼柯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M].王双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
[7]C.C.W.TYLOR. The Protagoras of Plato[M].New York:Oxford Uni.Press:1976.
[8]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M].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9]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五讲·第二讲[M]∥洪涛,译. 潘戈.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0]张志扬.后叙西方哲学史的十种视角[M]∥萌萌.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35.
[11]伯纳德特.施特劳斯论柏拉图[M].∥郑兴凤,译.程志敏.宫墙之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77.
[12]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M]∥应星,译. 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13]张志扬.一段并不遥远的美学个案[J].文艺研究,2003(1):44-52.
[14]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谢随知,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454.
[15]汪子嵩.希腊哲学史: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15.
[16]JOE SACHS. Plato’s Theaetetus[M].Annapokis:St. John’s College,Annapolis:2004.
[17]JACOB HOWLAND.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Philosophy[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8.
[18]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M].New York:Basic Books,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