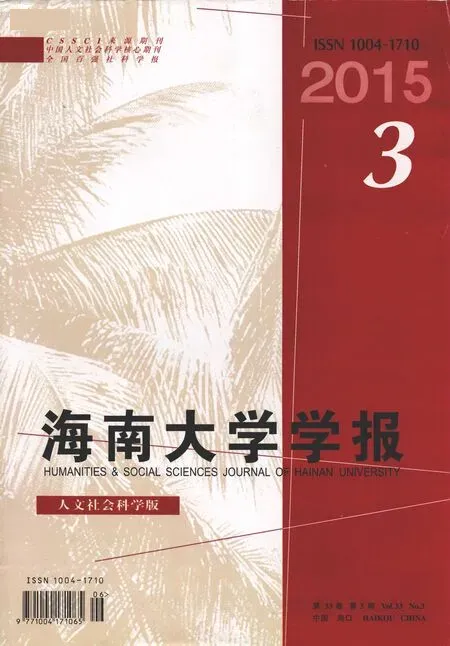科技创新对抗经济下行周期中财政政策的角色定位
刘安长
(1.湖南女子学院 经济管理系,湖南 长沙410004;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一、我国经济周期性下行的趋势判断及影响
2014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69 04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9 812 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123 871 亿元,增长7.4%;第三产业增加值125 361亿元,增长8.0%。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
从第二季度的数据来看,略好于一季度,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客观审视现阶段所处的经济状态,必须把其放入整个经济周期中来研究:自上一轮4 万亿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消褪后,从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自2009年以来首次“破八”(7.6%),并且一直持续到2014年第二季度(见图1),周期之长比较罕见。而专家预测下行压力依然很大。

图1 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我国GDP 增速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促进了全球经济在2010—2011年出现小幅反弹,但之后又跌落至3%左右,特别是美国2014年一季度还出现了负增长(-1%)。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增速也明显放缓,其中巴西降幅达到70%,俄罗斯和印度也下滑近50%。这表明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相同的经济下行周期。
因此,无论从以上历史数据来看,还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情况来判断,我国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1]。造成此轮经济下滑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同时杂糅了诸如初次分配结构扭曲、各种“红利”正在消褪以及劳动生产率降速等各种因素。经济下滑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货紧缩,纵观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但凡出现增速降到8%以下就意味着通货紧缩的风险将出现,历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此轮经济下滑,在CPI 上就有所体现:2014年4月,CPI 同比上涨1.8%,这是自2012年以来重回“1 时代”,如果未来物价持续走低,则通缩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而通缩一旦发生则会带来外需不振、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增大等负面效应,形成恶性循环。我国政府正在努力采取宏观政策“微调”、财政“微刺激”、科技创新等手段来对抗经济下行周期。
二、科技创新与经济周期关系的文献梳理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正在加大科研投入,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以期把自身从危机的阴霾中拉出来,重振经济。各国之所以均重视以科技创新对抗经济周期性下行,是因为自19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经历了若干次经济波动,均在低谷时期伴随着新的企业家群体、企业群体乃至新型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带动整个经济增长步入下一个繁荣周期,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科技创新的这种逆周期性作用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
早在1911年J·A·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对创新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用之解释了经济发展及波动的全过程。他开创性地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创新能为企业家带来超额利润,受利益的驱使,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于是增加了社会投资,信贷扩张,国民收入增加,从而使经济走向繁荣。当创新结束后,经济就会衰退。但由于创新活动是不连续的,下一轮创新引起的繁荣不能抵消掉上一轮创新结束带来的衰退,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就在繁荣与衰退中交替运行,呈现出周期性[2]。在1939年,他又在《商业周期》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创新与经济周期的思想,并把周期分为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三种;20 世纪70年代,Clark,Freeman,Mensch运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对Schumpeter 的观点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Romer,Lucas 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科技创新有利于摆脱危机,可以通过人为因素,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使经济避免周期性振荡,保持平稳增长[3-4];Van Dujin 提出“技术周期论”,这是研究科技创新引起经济波动内在机理最著名的理论,并把科技创新分为四种形态,由此推出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5];20 世纪80年代,Kydland&Prescott 共同创立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该理论认为经济之所以波动,不是Keynes 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根源于技术的冲击。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工资率和利率发生改变,市场理性主体会对此调整劳动需求,从而引起产量和就业变动,而一个部门的技术波动又会引起其他关联部门随之变动,由此带来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当然,国内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济下行趋势下,利用科技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产生逆周期性作用,如张耀辉等[6]。
科技创新对抗经济下行的理论与实证,学者们已经做过较多的研究,虽然有观点上的碰撞,但基本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科技创新有利于摆脱经济下行的困扰,熨平经济波动的幅度,拉动经济增长,与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能取得相似的效果,而且更加长久和稳固。对于科技创新如何对抗经济下行这样比较成熟的理论,无需再做探讨,但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创新行为应该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自发,政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府应该制定哪些财政政策有助于科技创新,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三、政府财政政策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科技创新有利于对抗经济下行已毋庸置疑,但创新行为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尤其是财政方面,如政府决定把钱投给谁?投多少?怎么投?)还是尊重市场选择,由企业来决定?学术界有颇多争议。政府主导派的代表性观点有,Basu&Weil 基于技术进步非中性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政治因素来控制发达国家对本国的技术侵略[7];Acemoglu 等指出发展中国家根据已有的禀赋情况,选择引进技术还是创新技术,以获得“适宜技术”,在此情况下,政府在技术创新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8];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的代表Freeman 和Nelson 分别以日本和美国为例,认为国家作为创新系统制定者对创新资源进行配置,能推动技术创新、推广和应用,为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起到更加高效的作用。国内学者更多是从科技创新的风险角度进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三:科技创新存在外溢性、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创新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而这些是通过市场机制无法克服的,所以需要政府主导科技创新。市场主导派的观点更多是从管理学的角度阐释的,Webster 认为市场主导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提升组织绩效,并且作用非常明显[9];Han 等也认为创新是市场主导之所以能持续创造顾客价值并实现良好绩效的根本原因[10]。国内也有相关文献做过探讨,郑文山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市场主导对技术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从技术创新意识、创新速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探讨了市场主导的技术创新实现机制[11];姚洋认为在经济发展早期可以由政府去培育产业,但到了中期阶段,由于创新是小概率事件以及政府主导创新会不计成本,所以由其主导创新必然会导致失败[12]。
关于科技创新到底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好的阐释,会议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而之前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角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来扮演的,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手段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方面,即由政府决定哪些是战略新兴产业,由政府决定对哪些创新行为给予财税政策支持,由政府确定投入多少资金进行创新研发等,而我国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政府对消费者创新需求信息的获得并不敏感,它只能由市场间接获取信息,因此政府在创新领域的投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及对创新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偏差性。政府认为创新就是要放弃传统产业,去发展一些新的行业,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倡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由政府确定七大领域,并在财税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然而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并没有摸清楚市场的需求与饱和度,其财税支持政策误导了许多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不管条件是否允许,都纷纷涌向这些新兴产业,结果导致产能过剩,使得一些产业黯然谢幕,其中光伏产业就是代表。据有关调查团队对“十二五”执行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十二五”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战略新兴产业的过剩,这也是政府财政政策的失误。当然,政府的财政政策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并非无需任何作为,因为正如政府主导派所言,科技创新的巨大投入、外溢性及不确定性是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因此,对市场与政府财政政策的角色分工上,笔者认为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引导企业专注于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商业模式创新,而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要更加注重基础前沿研究、科技创新环境营造和弥补市场失灵等。简单而言,就是市场唱主角,政府财政政策扮演服务的角色,为市场选择创新项目做好有力支撑。
四、科技创新中财政政策角色作用的发挥
面对金融危机来袭,各国的“救市”政策均带有凯恩斯主义的痕迹,即综合使用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工具。我国在当时也推出了4 万亿的救市计划,如今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等后果饱受诟病。正如Van Dujin 所言[5],Keynes 的逆周期政策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当市场出现饱和甚至过剩时,这种政策短期内会造成对大的周期波动的忽略,长期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来对抗经济下行。如前所述,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高强度、大范围的“强刺激”政策已被证明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而政府现阶段的“微刺激”政策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最终的效果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而对于科技创新的逆周期作用,这不仅是被学者们实证检验过的,同时也被国际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因此,在科技创新对抗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国家财政政策要充分做好各项服务,为科技创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是科技创新之源,基础研究中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产生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人类历史上三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强烈地依赖于基础研究的突破:第一次技术革命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这与近代力学、热力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电力的应用,这是电磁理论突破引发的成果。第三次技术革命是原子能技术、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这是在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只有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扎实功底和重大建树,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所提升,在全球经济分工中才能拥有主动地位和话语权。但基础研究前期投入成本高,周期长,这对以逐利为主要目标的企业而言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从事的,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将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性支持相结合,即在加强竞争性项目经费投入的同时,也加大对开展基础研究的基地和科研人才的稳定资助,加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以及科学研究中心等基地的建设费、运行补贴以及设备更新费用的投入,使得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能够排除后顾之忧,自行开展研究周期长、探索性强的科研工作,促进拥有自创性的科技成果产生。
(二)利用财政投入政策降低科技创新外溢性带来的负面效应
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性质,其所具有的外溢性会使得非创新者不用支付任何成本而搭乘“顺风车”——竞相模仿,从而瓜分创新者的市场份额,造成创新者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当这种外溢性过强而超出企业的阻止能力时,所有的企业都会终止创新,从而导致市场诱导创新行为失去作用。外溢性是市场机制无法自行解决的,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介入到科技创新的外溢过程中,增加科技创新主体的收益,这将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激励作用,也是推动持续创新的必要条件。其作用机理可见图2:

图2 科技创新的外溢性效应
如图2 所示,企业要想保持利润最大化必须使得边际收益(MRE)等于边际成本(MCE),此时的投入为I1,收益为R1,然而科技创新的外部性使得社会边际收益为MRS,大于MRE,因此要求企业的研发投入由I1增加到I2,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此时,采取财政补贴的形式把收益返还给创新者,使得边际社会收益“内部化”,降低外溢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能激发科技创新主体不断产生创新活动,增加创新产出。
(三)设立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解除企业风险障碍
科技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创新的投入与所带来的收益并非必然成正比,可能存在不需要太多投入就能获得巨大收益,也可能投入很多而并不成功;第二是科技创新的失败是缺乏继续投入的勇气和足够的财力支持,如果两者均具备,那总会在若干次失败后获取成功,但这若干次也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阻碍了许多企业进行创新投入。此时,可以财政资金为杠杆建立政府风险投资引导资金,通过其投入科技创新项目的示范性而引导风险投资的投向,并撬动社会各类资金参与风险投资,以增加风险投资机构的实力,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而可靠的资金支持。同时,因为科技创新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特点,有可能导致技术垄断或重复开发等风险,这时国家财政政策必须有所作为,对于重大且公共性较强的科研创新项目,可以通过统一安排财政资金吸引社会各大科研群体(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进行联合开发,这样不仅能充分发挥各大科研主体的优势,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化,从而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四)适当提高政府采购的招标价格以打破企业创新惰性
我国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把政府采购纳入了创新政策之中。由于受外溢性的影响,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存在动力不足和惰性,但如果提高政府采购招标价格,就可以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其作用机理是:假设创新投入成本为C,企业预期“内化”外溢性收益为R。当有两个及以上企业参与竞标,则每个企业的净收益为R1-C1、R2-C2。假设政府的招标价格为P,则企业的总收益为R+P,当R+P >C(或P>C-R)时,企业就会参与竞标。因此决定企业是否参与竞标有两个条件:第一,C 的大小。当企业研发能力越强,项目投入就越小,企业参与竞标的动力越足;第二,R 的大小。企业预期外溢收益R 越高,企业越有动力参加竞标。如果政府采取招标价格从高到低并以次低价格成交,则选中的企业一定是C-R 最大的。如果第二家企业退出,那招标价格不足以抵偿收益后的研发成本,即P <C2-R2,胜出企业的收益为R1-C1+P=(R1-C1)+(C2-R2)=(R1-R2)-(C1-C2)。如果没有企业参与竞标,则P(边界为P>C-R)足够高,就可以吸引足够多的企业参与竞标,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当竞选企业一旦增加,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竞价节约财政资金。此外,对企业已经研发出的高新产品和技术采取首购和优先购买政策也是值得重点考虑的方向,这不仅是对企业的一种直接支持,也是对企业创新行为的肯定。
[1]刘安长. 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宏观调控的尺度及政策选择[J]. 宁夏社会科学,2014(4):48-59.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6.
[3]Romer Paul M. Increase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86,94:1002-1037.
[4]Lucas R.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24.
[5]Van Dujin J.J.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J]. De Economist,1977,125(4):544-576.
[6]张耀辉,丁重. 政府主导外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J]. 产经评论,2011(3):25-35.
[7]Basu Susanto,David N.Weil.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Gro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1025-1054.
[8]Acenoglu D,Aghion P,Zilibotti F. Distance to Frontier,Selection,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6,4:37-74.
[9]Webster F. The Red is Covery of the Marketing Concept[J]. Business Horizaons,1998,31:29-39.
[10]Han J,Kin N,Srivastava R. Market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s Innovation a Missing Link?[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8,62:30-45.
[11]郑文山. 中小民营企业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理与策略[J]. 统计与决策,2010(15):187-188.
[12]姚洋. 政府主导创新不靠谱[N]. 中国经营报,2014-06-23(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