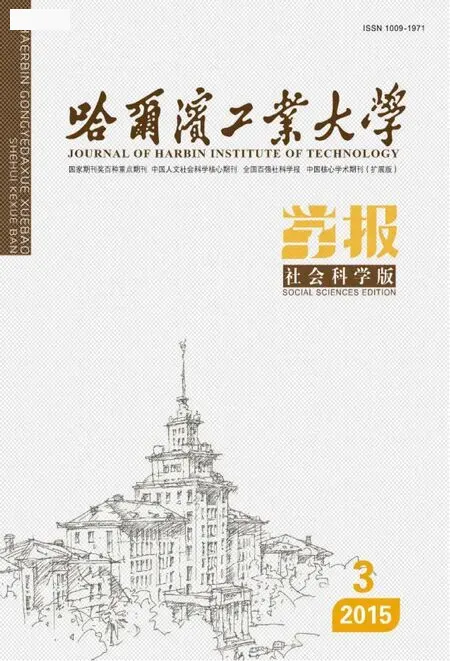韩驹的佛禅思想与诗学实践
方新蓉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637009)
有宋一代,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韩驹交游的士大夫,如蔡兴宗、徐俯、苏景谟、苏辙、王黼、李彭、汪藻、吕本中、钱伯言、曾几、江少明、赵鼎等,都与佛教关系密切,而他自己不仅游过、住过多家寺庙,还与众多的高僧大德来往频繁,如清凉惠洪、大慧宗杲、东林士珪、草堂善清、灵源惟清、山堂道震、万庵道颜、云居真牧、华藏密印安民、龟山平老、道潜、深老、秀老等。韩驹深为禅师们深厚的禅学功底、处世方式所折服。然而“宋代士大夫绝大多数在公事之余才参禅,功名利禄与禅学修养并进,忠孝仁义与般若性空不悖。……始终未能真正抛却世间”[1],韩驹亦如此,跳不出尘世之外,但他善于借鉴禅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来审视自身及整个世界,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思想上的解脱。
一、韩驹的佛禅思想
(一)意在无弦:率真自然、随物任化
黄庭坚认为“意象超妙,纯出自然而不事雕琢”[2]的陶渊明诗是在其“意在无弦”的思想下形成的,即《赠高子勉》其四所云“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这一点颇契合了参禅学佛的士大夫对佛道的领悟:率真自然、随物任化。韩驹《题采菊图》云:
往在京口,为曾公卷题采菊图:“九日东篱采落英,白衣遥见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风流可得成。”蔡天启屡哦此诗,以为善。然余尝谓:古人寄怀于物而无所好,然后为达。况渊明之真,其于黄花直寓意耳。至言饮酒适意,亦非渊明极致。向使无酒,但悠然见南山,其乐多矣。遇酒辄醉,醉醒之后,岂知有江州太守哉!当以此论渊明。复作二首:
黄菊有何好,且寄平生怀。遇酒兴不浅,无酒意亦佳。
……
悠然数酌尽,会心岂在多。醒来不复记,散发东山阿。[3]16596-16597
由上面的序和诗可以看出韩驹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京口时,他认为只要有酒,就可以适意,就可以达到陶渊明的境界。然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他推翻了有酒才能风流的观点,面对友人蔡天启屡次吟哦《采菊图》说这诗如何如何好的时候,辩驳道:寄怀于外物而不执着,才是旷达,才是率真,就像“黄花直寓意耳”。饮酒适意不是陶渊明最高超之处,如果没有酒,同样也可以悠然见南山,同样快乐多多,因此不要执着于饮酒适意,同样,也不要执着于黄菊。
也正因为不执着,所以他酷爱“高雅闲淡”[4]无思无营的韦应物的作品。韩驹《题韦苏州诗》云:“少时不知有韦苏州,晚读其诗……恨见之晚。”[5]21《诗人玉屑》卷五“陵阳诲人学韦诗”条也云:“余晚年酷爱此诗。”[6]115
(二)养性存心不问人:佛法在于自悟
禅宗讲即心即佛,慧能曰:“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7]351又曰:“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7]352佛法不应向外觅求,而是要对自心佛性进行体验与发现。《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曰:
侍郎韩子苍问道于草堂清禅师,致书云:“近阅《传灯》,言通意料,颇合于心。但世缘万绪,情习千端,未易消释,须有切要明心处,毋悋指教。”清答云:“欲究此事,善恶二途皆勿萌于心,能障人智眼文字亦不必多看,塞自悟之门。”子苍得此向导,述意云:“钟鼎山林无二致,闲中意趣静中身。都将闻见归虚照,养性存心不问人。”师得之大喜。[8]
韩驹看《传灯录》,认为书上所说与心中所想相合,好像领悟了佛道。但是一遇到世俗中千头万绪的人与事,心就不淡定了,起了千丝万缕的情绪,怎么也静不下来,希望清禅师指点如何才能明心、定心。清禅师教导他不要萌发善恶等分别分,外在的文字也不要多看,因为它只会障人眼目、心目,堵塞自悟之门。排除对外界的干扰和依靠,本着自心去悟。韩驹听到后,有所领悟:做官享受世俗与隐居山林没有差别,修养心性,心静下来了,一切皆空。既然是向内识取本心,那么把时间花在外在的坐禅上就是不对的了。其《送权师谒蒋山华藏二长老》云:“衹园寺里长连榻,衲被蒙头坐五年。……不知何事苦参禅”[3]16619,即反映了他的这种观点。
被韩驹视为作诗法则的金昌绪《春怨》中蕴含着佛性自具的意义。“师曰:‘东山老翁满口赞叹,则故是点检将来,未免有乡情在。云岩又且不然,打杀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9]云岩天游禅师认为法演吟咏日面佛月面佛艳诗有乡情在,没有认识到佛性自具,于是引《春怨》诗表示自己彻底抛却乡情这个外在追求,实现对自性的开悟。
对自性的开悟,就要时常反思自己,韩驹曰:“佛法本无多,未悟常自责。”[10]781就要寻觅自我解脱。韩驹《夜泊宁陵》曰:“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3]16615-16616在萧瑟的秋声秋色中,前尘往事一起涌上心头,茫然不知道身在何处。然而诗人最终没有陷入伤悲里,面对眼前一片蔚蓝、一片澄澈的江水和月光,忽然心胸澄净,脱离了人生的一切烦恼、是是非非,达到了物我两忘、自我解脱的禅境。
(三)文字性空:游戏三昧
文字性空,有文字与无文字无二,因此立文字就是不立文字。立下的文字可以发明佛旨,人们得以悟入,这也是一件大功德。韩驹《慈受深和尚语录序》曰:“若文字性空,说本无说,则虽数千万言,犹为不立也。慈受老人……平生说法具足矣。有能听之,如树林水鸟,则人得以悟入,其功不细。”[5]20以翰墨作佛事是一种游戏三昧。《大智度论》卷七云:“菩萨心生诸三昧,欣乐出入自在,名之为戏。”[11]“游戏三昧”是指达到超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脱境界。人生解脱的“游戏三昧”,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以文字为戏”。韩驹不少诗题目中就有“戏”“嘲”字眼,如知分宁期所作的《分宁大竹取为酒樽短颈宽大腹可容二升而漆其外戏为短歌》:
此君少日青而癯,迩来黑肥如瓠壶。缩肩短帽压两耳,无乃戏学驺侏儒。
人言腹大中何有,不独容君更容酒。未须常要托后车,滑稽且作先生友。
少陵匏樽安在哉,次山石臼空飞埃。茅檐对客夜惊笑,曲生叩门何自来。
老向人间不称意,但觉渊明酒多味。乞取田家老瓦盆,伴我年年竹根醉。[3]16592
韩驹把竹筒做成的酒樽当作人来写,以前是清瘦,现在是黑肥的大肚子侏儒,缩着肩膀,戴着小帽压着耳朵,坐在车后边。它陪伴过的杜甫、元结早就不在了,想起自己不得意的生活,干脆学陶渊明,一醉方休。韩驹在没有“戏”“嘲”字眼的诗中,也表现出文字为戏的特点,如《题大姑山》利用谐音,将山拟人化,称小孤山为“小姑”,澎浪矶为“彭郎”,“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长随女儿住”[3]16599。
(四)浮云过眼亦飞烟:人生如梦
佛教讲“诸法性空”,“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揵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12]。经过人生苦难的韩驹多次在诗中表现出了人生虚幻不实、人生如梦之感,如“中岁厌凡子,结交惟道人。况此丧乱中,益信空门真”[3]16599、“短 世 惊 人 如 掣 电,浮 云 过 眼 亦 飞烟”[3]16609、“复作千山去,真成一段空”[3]16629、“人生一梦炊黄粱,诸法本闲人自忙”[3]16603。
(五)崇尚隐逸:山林之好
葛兆光先生说:“我心是佛——我心清净——依心行动——适意自然,这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顺序十分自然的发展过程。”[13]韩驹因与僧人交往,对其淡泊名利、退隐山林、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无比向往,如他羡慕俞清老“日吃脱粟饭,时乘下泽车”,“人生但如此,其实足自娱”[3]16584。韩驹被贬到江西分宁,虽有悲伤,但想到自己可以在分宁寺庙饱参禅法,工作之余可以体会禅法,与僧人为友,喝茶论禅,心中又有了安慰,“王程傥余暇,兹焉著幽禅。自撷双井茶,与僧酌云泉”[3]16590。又如《去冬除守历阳未招还西掖今夏自应天尹移知齐安道由历阳珪老相访奉谏一首》云:“浮生浪扰扰,万法本自闲。为吏何足道论,逝将老榛菅。买田未及议,我实贫非悭。奉乞一庵地,往来泉石间。”[3]16597万法本闲,唯人自闹,世间万物本没有高下没有差别,有差别的只是人的内心,经历了仕途沉浮,诗人这才认识到自己在自寻烦恼,世间各种纷扰都是一场空,希望能归隐山林。
二、韩驹的诗学实践
宋代,禅宗成为士大夫们精神隐居的最好归宿,他们自觉而公开地把禅宗精神运用到诗学创作之中,甚至个别人形成了一套诗学观。韩驹即是其中一例。
(一)正心
宋代,宋儒们在讲究悟心的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大力提倡修心。《伊洛渊源录》载:“公(吕希哲)日夕劝导人主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心正意诚,天下自化,不假他术。”[14]韩驹把对儒学的继承与禅学的着力研习结合起来,提出“思无邪”即是“心正”,“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6]269。心正,写出的诗才具有高雅淳厚之内涵,才会同时看到美与丑陋,否则写出的诗就是邪诗。心正即意正,意正则思正,“作诗必先命意,意正则思生”[15]。韩驹对陶渊明的接受就是以其忠义和孝友为基础的[16]。心正,就要养、修。韩驹认为吴则礼平时素养淳厚导致其作品平淡,“著述觅句,淡然如一,此又见其所养者厚”[5]19。他反对不用心的作品:
觉范从高安来,馆之云岩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纸求传于觉范,觉范斯须立就,余见之不怿,曰:“诗当少加思,岂若是也容乎?容易乎?”觉范笑曰:“取快吾意而已。”……余欲删去冗长,定取精深数十百首……僧中初无具诗眼者,已刻版于书肆,每以为恨。[17]384-385
韩驹认为惠洪的作品有时意不正、思不正,所以其作品良莠不齐,但有僧人已经将它们全部刊刻,贻害后人,所以韩驹深以为憾。
(二)以禅学建立诗学
1.诗道如佛法
韩驹以禅喻诗,佛法有正邪,则诗道也有正邪,“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6]122。
2.诗用禅语、禅典
韩驹有不少的诗涉禅语。如《再用前韵简圆通止老妙慧光老一首》中“世界梦幻尔,岂特为微尘。更营露电躯,庇此泡影身”[3]16599全用《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语。又如《次韵吉父食筍乳长句》“我方厌苦饥虚病,公已深知识界空”[3]16634,其中“识界空”是作者有意用禅语,因为诗下诗人自注“识界空”曰:“《楞严经》云,舌识界三处都无。”再如《送东林珪老游闽》“诗如雪窦加奇峭,禅似云居更妙明”[3]16629中用名僧雪窦重显和云居智的禅典比喻圭老诗风奇峭和禅学妙明。
韩驹与禅师宗杲使用了相同的术语。韩驹和人诗云:“穷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鲶鱼上竹竿。”[18]这二个比喻在宗杲语录中也用,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一《示鄂守熊祠部(叔雅)》曰:“推穷来推穷去,到无可推穷处,如老鼠入牛角,蓦地偷心绝。”[19]898中 卷四《住径山能仁禅院》云:“鲶鱼上竹竿,一日一千里。”[19]826上 韩驹言:“作诗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语生,往往不佳。”[6]135其中的生熟论,宗杲也用它教诲士大夫参禅。卷二十六《答赵待制(道夫)》云:“生处放教熟,熟处放教生。……省无限力,亦得无限力。”[19]923上
3.诗用禅理、禅趣
韩驹有些诗虽未用禅语却富有禅意。《示龟山平老》其二“水横绝浦曾争渡,浪打船头又少留。安得一舟淮上钓,水生水落任沉浮”[3]16621,表现了诗人随缘自适、不与世俗相争的人生态度。韩驹曾长时间住宿寺庙,其寺庙生活也充满了禅意。《夏夜广寿寺偶书》(其二)“城郭初鸣定夜钟,苾刍过尽法堂空。移床独向西南角,卧看琅珰动晚风”[3]16631,写出了诗人参禅后静卧清闲自得。
韩驹通过对清幽静谧的自然景色的观照显露出一种自然适意的禅意、禅趣。如《黄龙山中》云:
未雨万木翳,既雨群山开。山神若眷予,一扫风中埃。摩云夹路松,禅伯手自栽。我来植拄杖,听度松风哀。幽赏未云足,暮色苍然来。何当白玉轮,碾上西南垓。[3]16591
山中天气多变,雨前黄龙山群山万壑一片昏暗,雨后阴霾尽皆扫除,经过风雨荡涤后的黄龙山一片清新、通透。一路走来,两旁是一行行禅师们种的高耸入云的松树,耳边是一阵阵掠过树梢的松涛声,美好惬意。暮色悄然而至,于是幻想什么时候那轮皎月会碾过山巅。
4.遍参与妙悟
“遍参”诗学理论的提出与宗杲关系密切。政和八年(1118),韩驹与没有开悟执着于文字知解的宗杲交游了二年(政和八年至宣和二年春),他们“日以吟咏为乐,所赋诗篇尤多”[20],“裁书访彭泽,倚杖话荆州”[10]801。建炎二年(1128)十月,宗杲与韩驹在金陵相聚五日。这次,让韩驹刮目相看,《佛祖历代通载》载韩驹“顷见妙喜,辩惠出流辈,又能道诸公之事业,衮衮不倦,实僧中杞梓也”[21]。韩驹亲身感受到了宗杲从不开悟到开悟的遍参经历,让他有了“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12]770的看法。韩驹认为作诗就要像禅僧们参禅遍参诸家一样,大量阅读、揣摩古人诗作,广泛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推敲锻炼,细细体味,日积月累,才能形成自己的佳作。
韩驹自己的人生历程也是遍参典籍,“忆吾童稚时,书亦甚所爱。传抄春复秋,讽诵昼连晦。饮食忘辛鹹,污垢失盥頮”[3]16602。诗论家的注释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遍参:
韩子苍《蕃马图》“回鞭慎勿向南驰”,“向南驰”三字出《李广传》[22]301。
韩子苍《赠童子举人》“十八重来诣太常”尽用《西汉儒林传序》[22]300。
韩子苍“楼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用唐人孙叔向《温泉》诗。“虽然水是无情物,流到宫前咽不流”,其诗见顾陶《唐诗类选》。[24]316
韩子苍《太一真人歌》“脱巾露顶风飕飕”,“脱巾露顶”四字出自李白诗“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22]316。
遍参古人,才知道古人诗意及其用典,如韩驹说:“陈述古《题述酒诗后》云:‘意不可解,恐其读异书所为也。’余反覆之,见‘山阳旧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17]19遍参古人,才可以将之作为文人交往的谈资,“念昔相见无他娱,诵诗征事相夸捷”。遍参古人,才知道古人的错误及其不足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曰:“渊明《田园》六首,末篇乃序行役,与前五首不类。今俗本乃取江淹“种苗在东皋”为末篇,东坡亦因其误和之。”[17]25-26韩驹为当时的青年晚辈不肯在读书上花功夫却妄想超越古人而叹惋不已,“近年人家子弟,往往恃其小有才,更不肯读书。大可悯叹耳!”[6]118读书不能停止,应贯穿人生始终。只有这样,作诗才有源源不断的素材与灵感,诗艺才可以循序渐进,《诗人玉屑》卷五“陵阳谓诗本于学”条云:“范季随尝请益曰:今人有少时文名大著,久而不振者,其咎安在?公曰:无他,止学耳。”[6]118
(三)不立文字不离文字
韩驹曾向苏辙学诗,苏辙将储光羲比之,“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23]938为什么呢?苏辙云:“见其行针布线似之。”[8]321行针布线字面意义为运针布置,安排丝线,就诗而言指在诗法上有脉理。苏辙《诗病五事》云:
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23]1228
在苏辙眼里,脉理是指内在的意或气象要贯穿一体,表面上的事件、文字可以相接相属,也可以不相接不相属。为文为诗的最高境界都是表面的不相连属,似断非断,是连非连,如果相连属了,一目了然,“寸步不遗”,那就是拙于纪事。由此可见苏辙的“行针布线”很有文字禅的意味:不立文字不离文字。这一点,韩驹很好地将之继承了下来,如“凡作诗须命终篇之意,切勿以先得一句一联,因而成章,如此则意不多属”[6]127,“凡作诗,使人读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读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终篇,方为至妙。”[6]121意脉连属就需要先命终篇之意,然后整体构思,思生,然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强调语序、次第即首尾有序、层次分明。
我们发现蕴含佛性自悟意的作品多为行针布线的典型。如前面已经分析有佛意的《春怨》,韩驹认为诗意连属,“大概作诗,要从首至尾,语脉联属,如有理词状。古诗云:‘唤婢打鸦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梦妾,不得到辽西。’可为标准”[6]121。的确,这首诗有着极为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打树上的黄莺儿是因为不想听它鸣叫。不想听它鸣叫是因为鸣叫会惊醒她已经到辽西与爱人一起的美梦。全诗一环扣一环,一气流转。又如作于海陵的《十绝为亚卿作》。道潜《读子苍诗卷》云:“大册雄文未许窥,百篇先读海陵诗。”[24]这说明道潜认为在香草美人之下有着禅意。我们以其五为例“君住江滨起画楼,妾居海角送潮头。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3]16607分析韩驹“行针布线”的特色。一、二两句叙事,呈现出两幅孤立的画面。第三句字面上以顶针手法将二三句用“潮”相连,并且引出新的意象“相思泪”,扣合传统“以水喻情”。第四句在内容上顺接“相思泪”流到第一句“画楼”,诗歌回环,但又用“不流”陡起波澜,使得妓之深情跃然纸上,叙事也摇曳生姿。这首诗有很强的模仿《春怨》的痕迹。它们都是叙事抒情诗,主旨都是女子相思,结构上除了前头(《春怨》是动作开头,有因果关系;《十绝为亚卿作》是位置图画开头,有并列关系)外,都是第二三句用顶针字相连,第三句与第四句都是顺流而下。
(四)句中有眼
“句中有眼”在诗学上“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以辨句法为主要内容的语言句子结构分析的文学批评模式”[25],在禅学上则启发了宗杲看话禅话头的提出。宗杲与韩驹关系密切,这种因缘使得韩驹多用看话禅的眼光看待诗学。
宗杲看话禅对话头的关注与韩驹对诗中字词的关注很相似。宗杲对话头的选择下了一番功夫。同样,韩驹也很关注每个字词,陆游曰:“予闻先生诗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远或千里,复追取更定,无毫发恨乃止。”[26]2235韩驹认为“赋诗十首,不若改诗一首。……虽少陵之才,亦须改定”[6]175。诗歌艺术没有穷尽,只有汲汲追求,才能臻于高妙的境界,“诗道无有穷尽。如少陵出峡、子瞻过海后,诗愈工。若使二公出峡过海后未死……又不止于是也”[27]277。杜甫、苏轼即使成就非凡,但仍可精益求精。
宗杲看话禅所参的话头是“眼”,同样,韩驹炼字不是为炼字而炼字,而是有“句中有眼”之意,《苕溪渔隐丛话》记载:“曾吉甫以诗迓之(汪藻)云‘白玉堂中曾草诏,水精宫里近题诗’。先以示子苍,子苍为改两字,……迥然与前不侔,盖句中有眼也。”[17]264-265魏庆之更是将之记入《诗人玉屑》卷八“句中有眼”,并说:“古人炼字,只于眼上炼,盖五字诗以第三字为眼,七字诗以第五字为眼也。”[6]173
宗杲看话禅的话头不是凭空生成,背后都有一个公案。韩驹讲字字有来历。陆游曰:“(韩子苍)历疏语所从来,其严如此。”[26]2235《诗人玉屑》卷六“陵阳论下字”条载:“仆曰:‘船拥清溪’‘拥’字有所自不?……公曰:李白《送陶将军》诗:‘将军出使拥楼船’。”[6]140韩驹对典故的解释证明了他学识广博,遍参诸家。使用典故不要刻意,该用则用,“事可使即使,不须强使”[6]157,“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为事使”[6]156,信手拈来,浑然不觉。
正因为韩驹如此炼字,所以他的诗“淡泊而有思致,奇丽而不雕刻”[28],如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他的同派仿佛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的叠成一堵墙,他不但叠得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29]。
(五)翻旧出新:独成一家
韩驹能独成一家,在于其思想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突出本心的地位,否定外在权威,“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11]1044,“熟路上不著活汉”[11]242,反对在参禅的过程中走前人的熟路,提倡创新精神。而翻旧案,把“死蛇弄活”成为禅门表现个性的特有方式。《碧岩录序》云:“自《四十二章经》入中国,始知有佛……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30]韩驹是“最能继承黄庭坚创新自立精神的两位诗人”[31]之一,他有不少翻案诗。如《代妓送葛亚卿》“刘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暂红。弱质未应贪结子,细思须恨五更风”[3]16637反用唐代王建《宫词》诗“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王诗认为桃花满地是自己想尽快结子导致,却叫人恨夜里五更寒风,是对五更风不公,而韩诗却为桃花辩护,认为桃花暂红是因为对刘郎的深情,吹落桃花遍地是无情的五更风,就应恨五更风,并以此来表葛亚卿的冷酷无情。
综上所述,韩驹深受佛教影响,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禅学,而且将之融入诗学,在诗学实践中印证着禅学思想。
[1]潘桂林.中国居士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07.
[2]顾易生.宋金元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5.
[3]傅璇琮.全宋诗:第25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965.
[5]曾枣庄.全宋文:第162册[M].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宋]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元]宗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M].大正藏,第48册.
[8][元]熙仲集.历朝释氏资鉴[M]//卍新纂续藏经,第76册:246上.
[9][宋]普济.五灯会元[M].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392.
[10][宋]韩驹.陵阳集[M]//四库全书:第113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11][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M].大正藏,第25册:110.
[12][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M].大正藏,第8册:217.
[13]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6.
[14][宋]朱熹.伊洛渊源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66.
[15][明]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3.
[16]程宏亮.韩驹诗文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49-50.
[17][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8]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434.
[19][宋]蕴闻.大慧普觉禅师语录[M].大正藏,第47册.
[20]嘉靖宁州府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599.
[21][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M].大正藏:第49册:690上.
[22][宋]曾季狸.艇斋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宋]苏辙.栾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4]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592.
[25]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161.
[26][宋]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7]程毅中.宋人诗话外编[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28][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M]//四库全书,第1141册:481.
[29]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15.
[30][宋]克勤评唱.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M].大正藏,第48册:139.
[31]张鸣选注.宋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