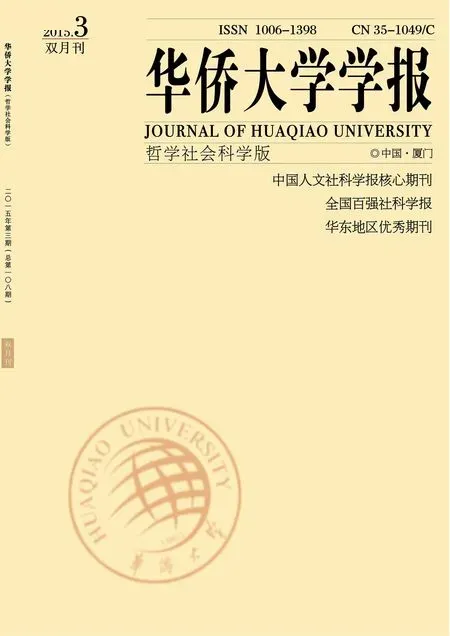论泰州学派对儒家经典诠释平民化的建构
○康 宇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晚明时期,盛极一时的“阳明学”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对经典进行过度的“六经注我”式诠释,已然颠倒了经典文本与解释活动的主客关系,从而让读者忽视甚至遗忘经典。于是,一场强调回归儒学原典、“返本开新”,拓展儒家经典诠释学发展新空间的运动兴起了。就整体而言,儒家们开辟出两种发展理路:一是有别王学空疏回归南宋朱子学格物解经;二是不背叛阳明学立场而修正王学之弊,让经典诠释与“百姓日用”相联,建构平民化诠释学。
作为“王门后学”之一的泰州学派,是后一条理路的开启者。他们在思想的运作方式上,将民间作为其组织学术的舞台,使大量社会下层人士介入到儒学经典诠释的思考过程中来;在理论上构建中让视角下移,将“百姓日用之道”置于儒家典籍内涵理解的核心之处,从而倡导了一种平民主义价值。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宪成)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1] 120可见,正是泰州学派对儒家经典诠释平民化建构的努力,使得明代儒学得以进一步发展。
一 以“身本论”替代“心本论”,重建儒家经典诠释形上学
在泰州学派兴起的年代,阳明心学的“心”仍是儒学经典诠释中最重要的解释本体。然而,社会实存的改变却预示着此种情况将会发生微妙变化: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滋生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众多平民为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组成了形式多样的会社、商团等,让组织替代家族成为国家基础具备了可能;社会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张扬。显然,这与之前统治者需要不断平定叛乱和镇压农民起义,重建社会秩序,以“破心中贼”为社会思想宣传核心内容的情境已大不相同。弘扬个体价值,让学术研究贴近平常百姓生活,让世人知晓人何以为人,社会等级伦常存在基础,成为时代赋予儒学研究新的课题。
应该说,“阳明学”确立的“心本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个人性。王阳明从“心外无理”、“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创立“良知”说,认为“心”是个体之心,是个体的主宰且造就了个体的精神,并与个体同存共亡,而“良知”即是“心”,也是人性普遍固有、不假外求的“本体”。所以在其经典诠释体系学说中,“致良知”是理解经典的最终目标,所谓经典为良知服务,解经就是为了“致良知”,“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2] 216经典是吾心的记载,它记录的是内心的事物,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即从属于良知。王阳明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六经注我”的热情解读经典,让个体的良知成为解经的主导,所谓“万物之理皆备我心”。
然而,这种对于“心本论”价值高扬并未体现出对个体“身体”的尊重。王阳明曾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2] 127即“心”是深达灵魂精神的形而上层面的范畴,“身”只是承载灵魂精神或屈从天理天命的、处于附属地位的容器,与“心”相比,“身体”的重要性要大大折扣。这样的观点明显将“身心”两分,让附着在“心”上的良知或曰伦理纲常的价值远高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权利。泰州学派显然看到了以“心本论”解读经典的弊端,他们把“身”与“道”看成同一个东西,强调自我之“身”是一个身心统一的整体存在,既包括良知之心体,也包括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而“良知”的根本作用就在于保重这个自我。学派代表人物王艮指出,“身”与“道”是同位的范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知安身不知行道,知行道不知安身,俱失一偏。”[3] 471在他看来,身体不仅是生理性、社会性、文化性的存在,更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身”可以合而为一,“尊身”即是“尊道”,“安身”即是“良知至善”,“保身”即是“良知良能”。另一学者王栋更直言:“万物皆备于我,旧谓万物之理皆备我心,则孟子当时何不说万理皆备于心。孟子语意犹云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总只是万物一体之意,即所谓仁备于我者,备于我身之谓也。故下文即说反身而诚,其云强恕而行,正是反身之学。由强而至于诚,都是真知万物皆备我身,而以一身体万物也。”[3] 465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万物皆备我身”,“身”是沟通至高法则与具体事物的桥梁,也是组织联系起天地间表面上各自为政的万事万物的内在核心。
沿着“身本论”的思路,泰州学派重建了儒家经典诠释形上学。其思想主旨是,对经典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万理皆备于心”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落到实处,将对圣人圣言天地万物的体认归结到“身”这一生命存在中。因为要“尊身”,尊重主体的精神自由,“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3] 471,所以个人解经释典时可以有独立思考,不受前人或权威者的束缚,不受固有诠释模式的拘束。由于“以一身体万物”,所以经典诠释也就是探索“身”,并在天地间寻觅自己恰当位置以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最终归宿的过程。
以“身本论”解释经典,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其一,它让儒家经典诠释走向世俗化成为可能。如果说“理本论”“心本论”建构了一个由“天理”主宰的“形而上”神圣的世界,人们只能被迫尊从的话,那么“身本论”则让人们摆脱了所谓“主宰“的限制,获得对感性欲望、肉体生命和自我性的肯定。“身”的挺立,意味着“私”的肯认,包含着对人的生理生命、感性生命的尊重,进而意味着对人欲的尊重。[4] 75随着“天理”神圣性的取消,“人欲”价值性的弘扬,人们开始相信经典所载“圣道”中既有道德精神的内涵,又有个体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约定,经典与世俗生活间达成了内在联系。其二,它让儒家经典诠释走向民间化。既然经典中所说的、所记载的都是与平民百姓生活相关的内容,那么就应让经典中的思想通过平民教育传播开来,不论老幼贵贱贤愚,凡有志愿学者,皆可教之传之。由于“身体”的被“发现”,儒学修养观中的简易追求得以实现,人们可以通过“体知”即“以身体之”之意,感悟经典、传播经典,所谓“以经论悟,以悟释经”。
值得一提的是,泰州学派毕竟是“王门后学”,其理论发展终究不愿违背阳明学根本立场,这决定了他们在理论创造上决非试图改变阳明“致良知”的立场与致思路向,而只是试图将“致良知”具体化为普通民众的实践。因而,“身本论”并非是对“心本论”的彻底颠覆。
二 以“淮南格物”替代“穷理”“正心”,发明“百姓日用之道”
“格物”是《大学》中的重要范畴,原指个体修身过程的一个初始阶段。进入宋明之后,儒家经典诠释者借“格物”范畴,发明出以朱子借形式化加以拓展的知识论解经和以王阳明借践行性予以证成的实践论解经,两种方法范式。前者主张“穷理”为解经主旨,要求明确主客、心物、心理二分,坚守“格物致知”的知识论立场,讲究向外以求;后者主张经典诠释目的在于“致良知”,解经思路是通过探索外心求理,以“格物”正心中之念。不过从本质上讲,“穷理”“正心”两种思路与普通百姓的具体生活还相距较远。面对这一情况,泰州对之进行了改良。
王艮围绕《大学》“三纲领”“格物致知”等条目及“修身为本”等文句的诠释,对“格物”提出了新的见解。[5] 106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絮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絮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日‘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絮矩是格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见絮矩‘格’字之义。”[3] 512显然,此时的“格物”已与“穷理”“正心”大相异趣;“格物”不再是一种单向求取的功夫(或求知,或去欲),而是一种“度于本末之间”,即在两个以上对象(物)之间的“比则推度”,以便确立其主次的关系。[]王艮进一步说:“格,絮度也。絮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3] 471即“格”为使矩归正、使吾身归正,“格物”是要明白个人是“本”,要以“自我”之“身”是否“安”作为度量标准。“格物”用于经典诠释,就是要从经典文体的分析中找到如何以“安身”为基,走向“良知致”之路。具体而言,即是明确个人与社会组织正确的互动关系,以及保障社会民众的人权与尊严的道理。由于王艮所在的泰州地处淮南,因此他发明的格物方法又称“淮南格物”。
王艮之后的泰州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淮南格物”。罗汝芳将“格物”规定为是以个体为本,践履“孝弟慈”规则。他说:“尝苦格物之论不一,错综者久之,一日而释然,谓《大学》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则尽《大学》一书,无非是此物事尽《大学》一书物事,无非是此本末终始尽《大学》一书之本末终始,无非是古圣《六经》之嘉言善行格之为义,是即所谓法程,而吾侪学为大人之妙术。”[7] 45所谓“嘉言善行”,即是“孝弟慈”,“从《大学》至善,推演到孝弟慈,为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未及家国天下。”[1] 299李贽则将“格物”界定为“明明德于天下”,“说到“格物”来,正是说‘明明德于天下’也。不‘明明德于天下’,亦说不得‘格物知至’。此《大学》之真血脉也,读者味之。”[8] 325“明明德于天下”的要求是“大畏民志”“使之无讼”,它涵盖一切顺民之事、安民之道。李贽的“格物”实际上把“格物”与“致知”等同。站在阳明学“良知”说的角度上观之,这里的“良知”所具有的本体性质已被等同于工夫,也就是说,此时“致知”之“知”和“良知”之“知”的关系被彻底地切断了。
应该说,“淮南格物”方法的出现是儒家经典诠释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创举。它高扬倡导个人主体价值的“安身立本”说理论大旗,升华了下层民众思想意识,尤为可贵的是,它推导出“百姓日用之道”,让经典成为满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百姓日用之道”,又作“百姓日用之学”“百姓日用即道”,是王艮率先提出的概念范畴。通过“淮南格物”,王艮总结出“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间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他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3] 472经典中所载的“圣人之道”是人的生存根据、价值之源,具有人的生存本体论地位。因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所以百姓日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也可从经典中找寻出来。王艮又言, “百姓日用”即是“中”,“‘中’也者,‘性’也,‘良知’也。”[3] 472“百姓日用”同样等同于“良知”,即发明“百姓日用之道”就是“致良知”。所谓良知是现成的,对良知的感悟需要对“百姓日用之道”的获取,当下即悟,返身可得,简易可行,“此学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万物霸柄。不知此,纵说得真,却不过一节之善。”[3] 654
与之相似,罗汝芳将“捧茶童子”与“道”相联系,从另一角度阐发“百姓日用之道”的道理。当有学者怀疑童子也能“戒慎恐惧”这一深奥的理学功夫时,罗汝芳说:“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汝辈只晓得说知,而不晓得知有两样。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天也。觉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个知,此则以虑而知,而其知属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顺而出之,所谓顺则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谓逆则成圣成神也。”[1] 317虽然茶房到厅有许多门限阶级,但是童子捧茶而来,却不曾打破一个茶瓯,因而“捧茶童子却是道”。在罗汝芳看来,“百姓日用”是“道”,是因为“道”源于“百姓日用”,并且“道本是个中庸,中庸解作平常。”[9] 12随后李贽将“百姓日用之道”进一步简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8] 29,让经典中的“道”更加生活化、世俗化,使得经典与普通人生活的紧密程度达到极至。
洋桔梗喜温暖,生长适温为15~28 ℃,当温度为18~25 ℃时洋桔梗生长最适宜[2]。其幼苗生长最好在20~23 ℃的日温、15~20 ℃的夜温。如果夜温超过25 ℃时会出现莲座(即簇生现象,表现为叶片为椭圆形,节间变短,生长缓慢)[5]。夜温20~23 ℃、日温28~30 ℃是莲座发生的临界温度。一般情况,夏天高温季节在温室内种植,通过启动水帘风机等设施,白天可控制在28 ℃以内,夜间控制在18 ℃左右,基本适合洋桔梗生长;如在连拱大棚内种植,白天通过卷起边膜、遮荫等措施温度虽可降至35 ℃左右,但对植株生长有一定影响,部分发生莲座现象。
实际上,王阳明也曾提到“百姓日用”,“在会稽。集同门讲于书院,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其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3] 656不过,王阳明讲“百姓日用”,是为启发人们的“良知”,以便破除“心中贼”,其相关论述实为对形而上“天理”的论证,以维护儒家伦理纲常。泰州学派所言“百姓日用”表达的是形而下的“人欲”,其维护的是平民百姓利益。所以“道”在这里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其虽载于经典圣言中,但却有现实、可靠的生活基础,正是它的存在让百姓生活作为一种本体存在具有现实合理性与不可剥夺性。如此,“道”不再具神秘性,有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内容,而圣凡之间也就是平等的,没有本质的差别了。[10] 34
既然儒家经典中所载的内容实为“百姓日用之道”,那么就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道”传播、教育给百姓,其形式自然不可繁琐,语言阐释亦不可深奥。于是,泰州学派将经典诠释不断平民化,思想表达日益口语化。典型的例子,王艮曾在《次先师》中用浅显的语言解释了高深的“良知”,他说:“知得良知却是谁?良知原有不须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之外知。”[1] 119就这样,泰州学派讲经宣理,不泥传注,而多发明自得,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及平民化的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将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的主张,传播开来,深入人心。
三 以“践行”替代“践形”,主张经典平民化解释之实用性
在儒家经典诠释学中,“践行”与“践形”一对彼此意义不同的概念范畴。前者以见之于客观的“行”为最高指向,并且也主要是作为主体之“言”与“知”的兑现和落实提出的;后者则以“善性”“慎独”为依据,以“诚意”为动力,要求将内在之“善”与“德”全面地彰显于主体的视听言动和貌相形色之间;前者之“知”“言”与“行”是一种主客观的关系,后者虽然也包含一定的主客观关系,但却主要不是一种主客观关系,而是一种在体与用、本体与现象双向统一基础上纵向立体的内外关系。[11] 36先秦孟子特别重视“践形”,他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12]尽心上这意味着任何人的身体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圣人才能使身体变得完整,“践形”具有浓厚的形上意蕴。到了宋代,随着朱熹对儒家经典诠释学知识论方向的定位,以“格物穷理”为核心的“外求”式解经方法日益盛行,与道德修养相关的“践行”逐渐成为理解经典的目的。至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虽称解经要践行事物,但终归强调的是从“心”上做工夫。从严格意义上讲,“践形”并没有被“践行”完全取代。
泰州学派倡导“身体论”,以仁教化天下,目的是疏理社会秩序,让“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社会得以实现。因此,他们的经典诠释充满了“实用性”色彩,让圣言、圣道践行于世,让“尊身”“安身”“保身”成为人们的共识。王艮指出,行道与安身是相统一的,体现了孔子“仁且智”的生命智慧,“仁者安处于仁而不为物所动;智者顺乎仁而不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随约乐而善道矣。”[3] 473经典思想践行于世,流行于百姓日用生活,可以让每个人都追求“内圣外王”,体现了“仁”,而人们在具体境遇中通过经典学习知晓如何既能安身又能将“万物一体”之仁道原则加以落实体现的则是“智”。同时,还要通过“践行”验证、把握经典“圣言”的真谛,“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有功夫做。”[3] 212研读经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瑞气腾腾宝祖山,如求珍宝必登山”[3] 214要获得“珍宝”式的知识,必须亲身实践。这些言论即是泰州学派“践行”总的原则。
为了让经典的思想更好地“践行”,泰州学派设计出一系列“实用性”命题与范畴。第一,“同心说”。所谓“同心说”是指,人心皆同,良知共有;天下同德,万物一体。王艮在释《中庸》时,认为每个人都是能知能行的;罗汝芳释“中和”时提出,“中”为天下同心之起始,“和”为天下一体之归属,两者在完整的价值体系中不可分离。[]正是经典存在,使得人人皆有的潜在“同心”达至完成的“同心”成为可能。第二,“下”范畴。“下”最根本的原始意义是空间上位于低下的、时间上处于后继的存在,后又演化出卑贱、愚昧、次等、末流等品格与资质上的贬义意蕴。泰州学派却一反传统之说,赋予了“下”极高的意义,让无足轻重日常琐事,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作为形下之器的四肢五体与高高在“上”的“圣道”“圣言”间达成联系,“世人不肯居斯下,谁知下里乾坤大。万派俱从海下来,天大还包在地下。”[3] 512肯定了下也就肯定了“百姓日用”的实用价值,承认了普通民众的地位作用,更强调了经典价值的彰显与具体的民间具体实践行动密不可分。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宪问“下学上达”不仅可以培育个体的道德人格,使其真正感悟人生,而且也是其掌握世间真理的必由之路。泰州学派认为,“下”是“学”的主脑,“下”规定了“学”的性质和方式,对经典的理解必须深入到“百姓日用”的点点滴滴中去,用具体行动直接体会和领悟,[15] 46“须从大处悟入,却细细从日用琐屑,一一不放过。三千三百,皆体仁也,圣人所以下学而上达。”[1] 299第三,“学乐”思想。泰州学派主张,学习经典要发挥人心之本体的自然之乐,“悦是人心之本体”“乐是心之本体也”“本体未尝不乐”。[1] 304人对儒家经典学术思想的理解领悟及对圣人君子典范的模仿效法须以“学乐”为基础, “学者不见真乐,则安能超脱而闻圣人之道?”[3] 472为了使民众在经典学习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做到不“累”而学,必须对经典诠释加以改造,并使之简易化,成为一种适应平民需要的简易儒学或平民儒学。要努力让民众做到“学不离乐”,通过学习经典教会人们懂得以超越性的视角去看待早已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感受、体验和认知良知天性的生发流行,籍此来体会心之本体的无事无愁、悦乐不愠的自由之“乐”境界,“故时时学习,则时时复其本体,而亦时时喜悦,一时不习,则一时不悦,一时不悦,则便是一时不习,可见圣门学习,只是此悦而已。”[3] 461
不仅如此,泰州学派还将“践行”经典真正落实于社会行动。以王艮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积极地在各地创办书院、举行讲会,展开各种讲学活动。王艮直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要将儒家经典思想推向平民,以道化俗。他的讲学主要面向社会大众,据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统计,其学五传而有弟子487人,除少数为官者,绝大多数为平民百姓。[16] 421王艮之后,泰州学派不管是官僚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热衷于教民化俗的平民教育实践,如韩贞自称“生成难并衣冠客,相泮渔樵乐圣贤”,多到乡间讲学,善于用浅显易记的韵文解读儒家经典;颜钧一生讲学于民间,其学“纯任自然”,取《大学》《中庸》而“心造”出易知易行的“大中学”,传授对象不分贵贱贤愚;罗汝芳甚至将儒家经典的“践行”思想应用于对囚犯的教育中,试图通过讲学唤醒犯罪者的“赤子良心”,其用意是以教育感化代替严刑峻法。
此外,泰州学派还创造出许多迎合百姓之心理与习惯的经典传播方式,目的是以百姓乐以接受的方式打动百姓的信仰心理。如颜钧运用“诗歌”“口诀”等手段,将儒家的忠孝仁义之说,以《劝忠歌》《劝孝歌》《快活歌》等方式传播,将《大学》《中庸》等经典思想,以“大中学庸,庸中学大”(就《大学》体会《中庸》思想,从《中庸》体会《大学》思想)等形式传授。又如何心隐创办了“萃和堂”,通过和聚宗族的实践,以倡导儒家经典中蕴含的伦理道德,使宗族弟子去私知爱,尊长先劳,相亲礼让等。
综上可知,泰州学派的“践行”已经大大超越了单纯的经典诠释,不仅突出了形而上“践形”的局限,而且与朱子学、阳明学中的外求修身、内求至良知式的“践行”内涵迥异,多出了更多切实、实用的实践应用色彩。这种思想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儒家经典诠释学说文化与学术的下移,另一方面也让儒学教育与学术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 泰州学派儒家经典诠释平民化的学术特质
在泰州学派的努力下,儒家经典诠释实现了平民化转向,这在儒家经学史的演进过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放大了个体在儒学体系中的作用意义:以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为标志,以个体行动者的存在为基础,以个体的共同兴趣为组织动力,充分反映出16世纪中国社会已初步呈现出的个体化社会特征,彰显了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特点。儒家经典诠释学说因此也扩大了自己的诠释空间,容入了更多可供诠释的对象。在这一轮“返本开新”后,儒家解释学乃至整个儒学系统获得了崭新的发展动力。
总结泰州学派对儒家经典诠释平民化建构的特质要素,可以看到:第一,充满了近代文化转型的启蒙因子。它让经典诠释与“百姓日用”相联,使得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一步步转化为近代平民意识。随着圣人、圣道、圣言上环绕的光环消退,“满街都是圣人”思想深入人心,市井平民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彰显。它又促成了一场心学革命,心性平等主义等命题的意义不断突出,这些明显偏向于从下层社会角度所作的论证让心学完成了一次由“正统”走向“异端”的思想突破。从此之后,政治平等、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成为后来心学者争相谈论的主题,一种内含特定色彩的人道主义与民主精神,由此生成。第二,佛学元素在经典平民化诠释的生成中不断闪现。泰州学派在对儒家经典诠释平民化的建构中借鉴了许多佛禅思想。如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之道”,认为本体的心性(道)不离人们日常生活与禅宗的“作用见性”——行走奔执等日常行为都是佛性显现,都是真如本体的自然流露,均是理体的妙用,即有许多相近之处;颜钧讲经发明的“七日闭关法”,指导学生如何通过七天时间的静坐默思以完成“一日克复,天下归仁”觉悟过程,所谓七天期满,必能“适达《四书》、《六经》如视掌”[17]。其中的“闭关”,本身即佛教的修炼方法。佛禅思想在泰州学派学说中的融入,一方面与王艮等人自身与“阳明学”关系密切,理解文本讲究“参悟”,间接受禅宗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传统儒学缺乏仪式学说难以满足个体听、想、思、悟等具体行为要求规范相关。泰州学派显然需要从业已形成系统方法的佛禅学说中汲取营养。第三,颇具美学意义的“狂”是其独具的学派个性特征。前文提到,黄宗羲称泰州学派为“赤手搏龙蛇”,其弟子行为狂放不羁,“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确,自王艮始泰州学派便以“狂”闻名于世。之所以“狂”,是因为他们认为“狂”是主体意识对外界的能动作用,也是实践行动的力量。王艮以“百姓日用”之说,赋予了“狂”以行动的动力源泉和行为指向,拓宽了经典诠释践履的对象范围,将普通百姓生活纳入到审美的视野中;罗汝芳提出“赤子之心”命题,并将之归结为“狂”的审美本体,他的“狂”开启了自我心、性、情、欲自由的大门,使得生命因此而敞开、觉醒和呈现等。
在“阳明学”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时代,泰州学派的出现为已渐为模式化、刻板化、空疏化的儒家解经学增加了几抹亮色。这是儒家经典诠释学说一次重要的学术转向,是儒学走向近代化的一次尝试与努力。不过也要看到,泰州学派以平民化方式诠释经典在明代社会中毕竟形单影只,难以形成凝聚力量;其由解读经典而形成的平民学说、教民学说,表述内容还仅限于儒学孝弟慈等具有道德整合性的传统概念。由于思想上的激进性,统治者对其亦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这也是该学派最终受政治、军事领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阻滞再也没有前进一步的直接原因。明万历年间,随着颜钧、何心隐、李贽、王襞、王栋等泰州学派重要学者的相继过世,以及东林书院兴起并成为吸引明代儒生新的中心,泰州学派逐步衰亡并最终谢幕了。然而,它的学术贡献后人不应忘记——正是在它的作用下,中国传统平民主义文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1]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王 艮.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 沈 玲.颜钧“孔仁颜乐”的审美境界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5] 姚文勇.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6] 黄卓越.王艮“淮南格物”论概念系统的再疏释——并论其对《大学》文本的解读[J].中国哲学史,2004(2).
[7] 方祖猷.罗汝芳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8] 李 贽.李贽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9] 罗汝芳.一贯编·四书总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0] 蔡桂如.泰州学派王艮民本思想述论[J].湖北社会科学,2009(12).
[11] 丁为祥.践形与践行——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的工夫系统[J].中国哲学史,2009(1).
[12] 杨柏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黄卓越.泰州学派平民主义思想之演进[J].中国文化研究,2002(2).
[14] 杨柏峻.孔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 邵晓舟.论泰州学派美学中的“下”范畴[J].中国文化研究,2008(3).
[16]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7] 颜 钧.颜钧集[M].黄宣民,点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