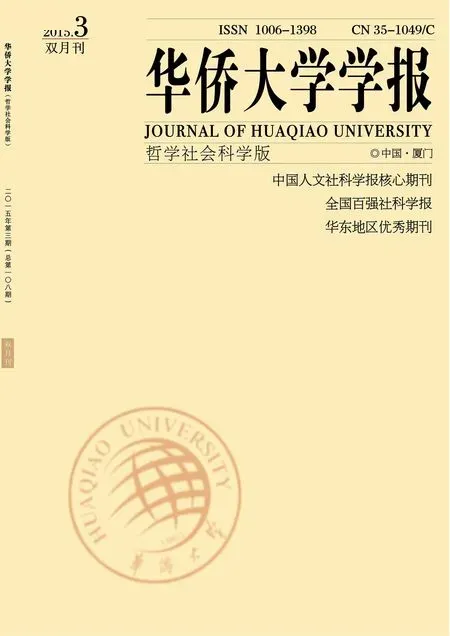胡适白话诗鼓吹的是与非
○毛 翰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胡适白话诗鼓吹的是与非
○毛 翰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胡适的白话诗理论鼓吹,主要见于《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及《尝试集》的三篇自序。《文学改良刍议》所论“须言之有物”等八事全部与诗有关。《谈新诗》的论点有四:诗体必须大解放,诗的进化即诗体解放,新诗语言须有“音节”,新诗语言须“具体”。《尝试集》自序的主要论点是:作诗如作文,文学革命毋庸置疑,打破一切枷锁镣铐,新诗的音节须顺应诗意,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这些理论鼓吹,在当时无不切中时弊,待时过境迁,则无一不可质疑。
胡适;白话诗;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尝试集
胡适关于白话诗的理论鼓吹,主要见于几个文本:《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以及《〈尝试集〉自序》,包括初版自序、再版自序和四版自序。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白话诗仍未走出被质疑的困境,虽不曾“一失足成千古恨”,却已是“再回头已百年身”了。回顾当初首倡者的激情鼓吹,以近百年来探索前行的经验教训,检视其理论的是非得失,应该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
一 《文学改良刍议》之刍议
1916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10月1日,陈独秀复函:“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①胡适与陈独秀这两封信,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胡适于是撰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
由百余字的要领,到六千多字的文章,八事的顺序倒过来,首先强调“须言之有物”,然后依次是“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想来是主次分明的需要,但其中属于形式的“须讲求文法”与属于内容的“不作无病之呻吟”顺序颠倒,则应是疏忽所致。
此八事全部与诗有关,亦不妨作为《诗歌改良刍议》。下面,笔者试依其内容与形式的顺序,就其所论的得与失,逐项作一浅析。
1.关于“须言之有物”
胡适写道:“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
对于“须言之有物”这一项,陈独秀原本是有疑问的:“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①见陈独秀给胡适的信,《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为此,胡适行文做了解释,说他所谓“言之有物”,与载道无关,而是指作品有情感有思想。而陈独秀的另一疑问:“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也如此。”②同上。胡适则未加理会。而这正是胡适此论的一处破绽。
诗言之物,惟“情与思二者而已”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包括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二者在内的诗,它们所要表现的,不仅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还有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一方,诗的内容是情感 (胡适认为包括美感。其实,“情”“思”“美”三项不妨并列)和思想(胡适认为思想即见地、识力、理想),在客观世界一方,诗的内容则应该是自然的景与物和社会的事与史。景、物、事、史在诗中出现,如果是作为意象 (景、物是自然意象,事、史是社会意象),作为表现手法,写景、咏物、叙事、咏史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主观的情与思。但有的时候,景、物、事、史入诗,它们自己即是诗所要表达的内容,即是目的,即是诗人所要表现的那个客观世界,诗人并不想借景抒怀,托物言志,叙事、咏史也并不另寓情思,不想自堕情障,自堕理障。此时,诗的内容不是“情与思二者而已”,而是写景、咏物、叙事、咏史而已。此时,景、物、事、史即使还算是意象,也已经是 (或近乎是)无意之象了。试读上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除了再现生活,还表达了多少“真挚之情感”和“高远之思想”吗?李白《望庐山瀑布》那“日照香炉生紫烟”的景物摹写中所透露的情与思,怕也是难以寻绎吧?白居易否定“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式的写景状物之作,说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③[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可是,景物诗为什么一定要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呢?唯美之作不可以聊备一格吗?诗应该有情感有思想,诗有时也不妨“得象忘意”“玩物丧志”。当“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④[清]叶燮《原诗·内篇 (下)》。,读者又何必冥思苦想,索求寄托?当诗无达诂时,诗其实也无须达诂。甚至连那“知人论世”的功夫也不妨省去,颂其诗,歌其词,沉醉其意象之美,不知其人,不解其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吧。
2.关于“不摹仿古人”
胡适滔滔雄辩:“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一味摹仿古人而不知创新者,其所作“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件‘逼真赝鼎’而已。”他指陈三立 (伯严)工于仿古,“半岁秃千毫”,不过是古人的钞胥奴婢。他盛赞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认为今日中国只有以白话文、白话诗“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且不论胡适所谓文学进化,是指“愈晚出愈精妙”①吴宓《论新文化运动》:“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见于《学衡》第四期,1922年4月。,还是指“代有所胜”②[清]焦循《易余龠录》:“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强调文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总是不错的,强调文学关切社会总是必要的。除此之外,文学是否一概不能摹仿古人,则是可以商榷的。譬如,文学有一些永恒的主题,所谓母题,如生命感伤、文化乡愁和对自由的向往,就是古今不变的。从“帝力于我何有哉”,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目无皇权蔑视权贵的自由颂歌,怎能逃出前人窠臼?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缠缠绵绵的情歌,又怎能不落入古乐旧题?文学还有基本的创作手法,如现实主义的写境和浪漫主义的造境,也几乎是亘古不变的。甚至胡适这篇“刍议”本身也不乏摹仿古人之处,如“务去烂调套语”之于韩愈所谓“惟陈言之务去”,如“不摹仿古人”之于韩愈所谓“辞必己出”。
3.关于“不作无病之呻吟”
胡适写道:“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此事的提出,体现了胡适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有其积极意义。民国初年,乱象纷纭,百废待兴,青年们当然应该积极进取,报效国家,而不可沉溺于一己愁思,伤春悲秋,暮气沉沉。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冯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乾坤初定,国运多艰,时代需要催人奋进的诗,胡适此论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感人的。如果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兼济与独善,志士与逸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诗则有两种处世方式可以选择。“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其诗固然可嘉;“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其诗也未尝不可。中国诗史上的绝唱,恰恰多是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以及蔡文姬、李煜的感伤之作,悲痛之歌。
而且,诗原本就有人生和社会两大基本主题。人生主题包括生命的感伤,青春的怅惘,人生的困惑,生与死的意义的追问,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的浅吟低唱。社会主题关注的,则是社会风气的清与浊,政治生态的善与恶,乃至家国安危,民族存亡,其主题往往是感时伤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乃至以身许国,救亡图存。胡适此论把人生主题大多归入无病呻吟,显然是过于偏颇了。仅举一例,中国早期的流行歌曲——学堂乐歌,至今广为传唱的唯一的一首,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就恰恰是在“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试看其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如此伤悼华年,凭吊逝者,把酒惜别,究竟算是有病呻吟还是无病呻吟?此种主题或许少儿不宜,却终究是诗歌所不可或缺的。
4.关于“须讲求文法”
陈独秀见胡适所约八事之要领,即已复信指出:“第五项所谓文法之结构者,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若谓为章法语势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①见陈独秀给胡适的信,《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1916年10月。
但不知何故,胡适完全不理睬陈独秀的批评,《文学改良刍议》关于这一事的阐述极为简略,仅寥寥数语,仿佛真理在握,不容置辩,自信得有点失礼:“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实际上,以西洋文法套我中文已觉勉强,套我汉诗更属生硬。文有文法,诗有诗法,两者未必完全相容。“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②语出胡适《〈尝试集〉序言》。一说显然不妥。即便中国的骈文律诗也并非不讲语法,而是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语法,中国诗人和读者心领神会,彼此高度默契,中国诗歌包括骈律在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理解上的障碍。而诗家语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受语法的规范,诗的遣词造句不肯遵守通行的语法规则。方东树谓之:“文法高妙,无定而有定,不可执著,不可告语,妙运从心,随手多变。”[1]不仅唐诗会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样的主宾倒置,会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强拼硬贴,白话诗也会有“云很天鹅,女孩子们很孔雀”、“很四月”③余光中《大度山》。、“星空,非常希腊”④余光中《重上大度山》。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演,他朗诵此诗至“星空,非常希腊”,被一位留美博士打断:“文法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余光中一愣之后,反击道,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余光中后来解释说,有一次仰望星空,发现很多星座是以希腊神话命名的,因而得句。参见《从缺席诺贝尔文学奖谈起》,载台湾《联合报》1999年1月1~5日。这样随机的词性改变,会有“禁城里全部的海棠/一夜凋成/秋风”⑤洛夫《长恨歌》。这样的语序颠倒。
当然,这种有违语法的诗句不可滥用。间或为之,会给人以新奇、惊艳、痛快之感;用得多了,通篇都是“病句”,不堪卒读,读者则不免弃之而逃。
5.关于“务去烂调套语”
胡适所论也理据充分,无可辩驳:“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然而,悉数去除古典语象,作诗必以“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究竟能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却是可疑的。容举一例:
毛泽东1927年有一首《西江月·秋收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全是亲历之事,全是自铸之词,于中国古诗几乎无一字有来处,且平仄不协,韵脚不工。可是,其艺术成色如何呢?可能连作者自己也觉得看不过去,后来的版本里,“修铜”改作“匡庐”,“平浏”(平江、浏阳)改作“潇湘”,大概是想借助“匡庐”和“潇湘”这两个“陈言烂调”既有的诗意积淀,使作品增色。
全盘继承前人的遗产,不再创业,坐吃山空,是没出息;一概拒绝前人的遗产,把阿房宫一把火烧了,自己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是不是又太过愚蠢?
6.关于“不用典”
因为受到“攻击”和“误会”,胡适用了两千余字、占全文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详加辩解论证,其中不乏精审之见。堆砌僻典以显摆博学,掩饰诗意和才情的贫乏,自是一种可恶的诗风。尽管前人早有讥讽,诗中用典之风仍然绵延不绝。胡适1916年8月21日致陈独秀的信里,就指责《新青年》刊登并极力推崇的一首长律[2],用典竟不少于一百处。当然,前人的妙语趣事,后人偶尔援用,仿佛中国园林的借景借境,让诗平添韵致,是不必一概排斥的。白话诗用典也不乏精彩之例。1982年,严力有一首小诗《失约》,写一对恋人约会,迟到的女生终于出现,“……她拎着一袋苹果∕堵住了黄昏的长廊尽头∕她解释说∕苹果晚熟了一个钟头”,这晚熟的苹果、迟到的恋人,就在用闻捷1955年所作《苹果树下》一诗的典故吧。在闻捷诗中,天山脚下的果园里,爱情就曾经与枝头的苹果一起,从春到秋,同步开花、结果,直到成熟、采摘。
中国成语多有典故,禁止用典无疑会使汉语的表达大为减色。唐德刚就曾指出:胡适“教人不用典的那篇《逼上梁山》的大文,文题本身就是大典故!正因为他用典,他那篇文章才有劲。不信?且看我把它换成个不用典的题目:‘我本不要做呀,他们硬逼着我做啊!’写了这样一个题目不用典的文章,那胡适还能成其为胡适吗?”[3]
7.关于“不讲对仗”
胡适并非一概反对对仗,他欣赏《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式的自然天成的对仗。作为一种修辞,对仗毕竟可能增进语言表达的效果。胡适反对的是骈文律诗的文胜于质、刻意为之的对仗,以为那是文学末流之末技。
胡适就此感慨:“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陈独秀对此极为赞同,其编者按“独秀识”云:“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①归、姚: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姚鼐。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不过,律诗的对仗固然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炫技,以至留下“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之类“实无此事,唯图对仗亲切耳”②[宋]范正敏《遁斋闲览》:“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官衋然哀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若是!’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唯图对仗亲切耳。’”之类的笑话,作为“纯粹的中国艺术底代表”,“首首律诗里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4],方块汉字独有的对仗的魅力,怕也不是轻易所能否定的。唐代的古文运动破骈为散,也并没有进而剑指律诗。而今,工整的律诗都被前人做去了,不刻意求工的对仗留了下来,白话诗何妨运而用之?北岛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因其大致的对仗而脍炙人口。
据说,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考试,陈寅恪出的国文试卷,有一题是对对子,上联出的是“孙行者”,要求对出下联,而下联的最佳答案就是“胡适之”。大概是陈寅恪有意要调侃一下这位“不讲对仗”又曾大闹天宫的“猢狲”吧。
8.关于“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又称:“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此论意在废止文言“死字”,而改用白话口语之“活字”。一如近代欧洲各国以各自的方言口语创作的“活文学”代替拉丁文的“死文学”。
胡适认为,到了元代,中国的白话文学已大为兴盛,《水浒》《西游》《三国》纷纷问世,戏曲尤不可胜计,这种言文合一的趋势不幸被明朝的八股取士阻断。但胡适这一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水浒》等话本小说的成书年代尚难定论,而前后七子的复古并非明诗的全部,时调小曲在民间兴起,以致“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不要说民歌小调不是诗,《诗经》三百篇即多是当年的民歌小调。冯梦龙辑评《挂枝儿》十卷流传至今,试看其开卷第一首《私窥》:“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舔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俺怎肯把你的恩情负,欲要搂抱你,只为人眼多。我看我的乖亲也,乖亲又看着我。”事实上,这种不避俗字俗语的白话诗、自由诗,至迟在明代已经有了,而且已经非常成熟了。试对比胡适《尝试集》中任何一首,无论语言的通俗自然,还是格式的自由无羁,后者都大为逊色。
当初作《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尚在美国求学,自是“横的移植”多于“纵的继承”。待到1922年,胡适作《北京的平民文学》一文指出:“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吧。”[5]这时,带着生硬、粗糙、无根种种缺陷的胡式白话诗木已成舟,胡适批评“他们”时,忘了自己正是始作俑者。
另外,在痞子文化盛行的今天,有必要提到的是,白话诗不必回避俗字俗语,但诗终归是诗,诗的艺术旨趣和归宿是雅。诗即便俗,也应俗得雅气。徐志摩笔下的东瀛女子,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可以代之以“像一只乳燕不胜骊歌的娇羞”,“像一行假名不胜吟诵的娇羞”,却不能改做“像一朵狗尾巴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或者“像一只绿头苍蝇盯上了我这块臭肉”。俗毕竟有通俗与庸俗、粗俗之分,某些粗话如“不须放屁”“砸烂狗头”,某些脏话、薛蟠体、下半身,还是不宜入诗的。
二 《谈新诗》浅谈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原载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适逢辛亥革命八周年,加一个副标题,意在强调新诗创立的重要意义。大概觉得先前《文学改良刍议》的表述过于克制,不够尽兴,这篇《谈新诗》便直率多了,痛快多了。其主要论点有:一、诗体必须大解放;二、诗的进化即诗体解放;三、新诗语言须有“音节”;四、新诗语言须“具体”。笔者试谈一点浅见。
1.诗体必须大解放
胡适认为,古今中外的文学革命,大概都是由“形式”入手,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的大解放。“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这就是胡适的诗体解放论。其中,后三句还是互文,显示着胡适此处出语的精审。
胡适此论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之说且不论,其“对方辩友”之一,南社领袖柳亚子就曾宣称:“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6]
今天回头看去,胡适主张从“形式”入手,即从语言文字 (白话文)、文体 (自由体)入手,立即推出白话诗,让诗的精神内容挣脱形式的束缚,其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有效的。否则,势必重蹈清末“诗界革命”的覆辙。
只是他对白话诗的设计和期许还可以商榷。除了思想感情,还要容纳“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这怕不是诗之所长——既不是传统诗词 (格律诗)之所长,也不是白话诗 (自由诗)之所长。自由诗较之格律诗,尽管舒展了许多,宽松了许多,要想做到“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的无障碍表达,仍然是有难度的。人们进而要问,这些内容究竟是诗所应该承载的,还是散文应该承载的?1997年,克隆羊在英国问世,克隆人呼之欲出,这侵犯造物主专利的冒失之举,让世界大惊失色,各国名流纷纷呼吁立法禁止。笔者有感而发,写下一组自由诗《克隆人四章》[7],意犹未尽,扩充为八章仍不尽兴,直到改为散文《坦然迎接克隆人》[8],方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
诗体的大解放,到哪儿才是一个边?诗体解放的最终目标竟是散文化吗?诗之为诗,该不该有它自己的文体分工和审美偏好,有所为有所不为?
可以质疑的还有,中国诗史上那么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佳作,那么多万口传诵的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名篇,格律限制了诗意的表达吗?“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歌德十四行诗《自然与艺术》不是还有此一说吗?另一方面,无意于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无意于兴观群怨,而专注于“非功利的审美活动”的所谓纯诗,也是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的。
胡适以自己的诗为例,问“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达得出的吗?”这里人们当然也可以反问,像“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①[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这十个字的隽美意境,白话诗能表达得出来吗?
2.诗的进化即诗体解放
胡适寻找到的诗国革命的理据是历史进化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胡适认为,从《三百篇》到南方的骚赋,这是一次解放。骚赋到汉以后的五七言诗,这是二次解放。诗变为词,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这是三次解放。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已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
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文学研究,胡适不是中国第一人。1903年,梁启超就曾写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9]胡适在其文学革命的鼓吹中,坚持进化论,对于破除古典诗文的迷信,建立白话诗文的正统地位,则有其独特的贡献。
这里可以质疑的是,诗的进化,果真就是诗体的不断解放,由格律诗变为自由诗吗?诗的发展,就只有自由解放这一个方向吗?在胡适的论述中,至少由骚赋到五七言诗这一节是不通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胡适说:“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②此句之中的“些”字,疑为“也”字之误。,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经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可是,单看《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分明有自由诗、散文诗的元素在其中,哪是删除“兮”字等就“解放”成五言诗了呢?
一部中国诗史,在胡适眼里,就是诗体的四次解放。如果换一个视角,我们却可能看到,一条中国诗史的长河,就是诗体之舟在格律化与自由化这左右两岸之间的摆动前行史。由《诗经》的四言到《楚辞》的杂言,是从格律到自由;由《楚辞》的杂言到汉唐的五七言,却是从自由到格律。由五七言到词曲,是从格律到自由;由句法不整齐的宋词元曲,到句法整齐的戏曲、曲艺唱词,又是从自由到格律。由传统诗词到现代白话诗,是从格律到自由;此后,闻一多等人探索新诗格律化,则又试图从自由到格律。
3.新诗语言须有“音节”
胡适说:“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胡适认为:诗的音律美,不在韵脚和平仄,而在于“语气的自然节奏”,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白话新诗应该追求“自然的音节”,其诗句应该是依着意义和文法,长短不定的。关于用韵,胡适说新诗有三种自由:用现代的韵,平仄互押,有韵固然好,无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
胡适此论,作为他的“作诗如作文”“诗体大解放”的注脚,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其新诗鼓吹的误解。不过,胡适关于新诗的音律美的设想和表述还很不到位。他把音律美的要素称为“音节”,把音节分为“节”和“音”,节即节奏,即诗句里面的“顿挫段落”,音即声韵,即“平仄”和“用韵”。沿用传统诗学的概念和术语,界说他心目中的新诗的音律之美,不乏牵强之处。事实上,今人的白话自由诗较之古人的文言格律诗,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其“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入诗的音律,是需要另一套语汇来言说的。
而胡适所谓白话诗的音律论,已经走得很远,已经走到了自由诗的边疆,近乎散文诗的国度了。其白话诗的音律设计,已经近乎新诗散文化的主张了。这就难怪后来的学者探讨新诗散文化,会到胡适门下寻找理论资源了[10]。
4.新诗语言须“具体”
最后,胡适强调诗的形象思维或意象表达。不过,他没有用“形象”或“意象”的字眼,他用的是“具体”。他说:“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他举例说,李商隐所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不成其为诗,因为他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明了浓丽的影像。而“绿垂红折,风绽雨肥梅”是诗,“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是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是诗,因为他们都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他赞叹“五月榴花照眼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何等具体的写法!他还举了几首白话诗,尤其是用他自己的《老鸦》做一个“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的例子。
强调诗的意象表达当然没错。“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①《易传·系辞上》。是中国先哲的一大发现和发明,将抽象的情思做具体的、意象化的表达,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不过,意象化并非诗歌的唯一表达方式。“立象尽意”之外,诗也不妨“直言其意”,或两种表达方式并用。李商隐这首《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首联直言其意,主题则更为鲜明。历代诗歌里,“立象尽意”兼以“直言其意”的例子很多,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②汉乐府《长歌行》尾联。,“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③[宋]方岳绝句《别子才司令》前两句。,“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无向易中轻。也知贵贱皆前定,未见疏慵遂有成”④[唐]李咸用律诗《送谭孝廉赴举》中间两联。。依胡适之见,它们用的都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都不成其为诗。更不待说,明代文嘉的《今日歌》:“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通篇无一意象,完全以抽象语言出之,何诗之有?此后,殷夫译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抽象到底,意象全无,中国人竟也乐于接受,视同己出。
胡适此论显然失之偏颇。诗应该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立象尽意,二、直言其意,以及二者并用。直言其意,又何尝不能成就好诗好句?此时,时空澄澈,大象无形,只有一个深沉高远的声音,诗的声音,先知的声音,或神的声音,在吟诵,在独白,在宣示着一些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真谛,如“道可道,非常道……”
而作为诗的一种,歌词诉诸听觉,要求明白晓畅,直抵心灵,得助于音乐旋律和节奏对文学语言的维系和整合,得助于音乐形象对于文学形象缺席的弥补,歌词更允许无意象的情思直陈。
20世纪初,中国诗歌的意象艺术曾经漂洋过海又回流故国。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 (1885-1972)通过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发现“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①Ezra Pound,‘Chinese Poetry’,Today,no. 3,1918,p. 54: ‘because certain Chinese poets have been content to set forth their matter without moralizing and without comment’.,但庞德所推崇的,只是中国诗的表现方法之一,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尽管中国诗中“立象尽意”的比重更大。
但不管胡适的论述是否准确精当,关于白话新诗的审美规范,胡适《谈新诗》已在强调其音律建设和意象表达了。而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其语言美不过两大因素,诉诸听觉的音律美和诉诸视觉 (通过想象)的意象美。在论述了诗体大解放的必然论和诗国革命的合理性之后,胡适此文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白话新诗的音律 (胡适称之为“音节”)和意象 (胡适称之为“具体”),无疑是抓住了要领。
三 《〈尝试集〉自序》等试评
胡适《尝试集》的自序前后有三篇,分为“自序”“再版自序”和“四版自序”。《尝试集》初版于1920年3月,《〈尝试集〉自序》篇末所署的写作时间为1919年8月1日,所论与《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两篇有重复之处,其诗观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作诗如作文,二、文学革命毋庸置疑,三、打破一切枷锁镣铐。《〈尝试集〉再版自序》强调新诗的音节须顺应诗意。《〈尝试集〉四版自序》的一个论点是: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
1.作诗如作文
被视为胡适白话诗的理论纲领的“作诗如作文”一语,据《〈尝试集〉自序》的记述,出自胡适1915年9月的一首以诗论诗的《依韵和叔永戏赠诗》:“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由于梅光迪、任鸿隽 (叔永)等友人的“误会”,胡适做过答辩,称其“作诗如作文”一说的提出,是由于“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胡适认为,“诗之文字”原不异于“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于文之文法。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之类的“诗之文字”一点意思也没有。而白居易《道州民》“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一类的“文之文字”才值得推崇,因为这些诗言之有物,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
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与韩愈及宋人苏黄一脉“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之说有相通之处。但韩愈们只是在五七言诗的框架之内,以较为自由的散文的句法、章法,对于近体诗的形式规范做一定的背离,胡适则试图对整个古典诗词曲赋的形式规范进行彻底的颠覆。
当年,梁启超本想以“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三长兼备,终于退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拒绝“新语句”。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也没有实质进展。从“诗界革命”止步的地方出发,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正是想要抛弃五七言诗的“旧风格”而引入散文式的“新语句”,换用白话口语吧。
胡适自释“作诗如作文”,是在强调诗应该像散文一样言之有物、风格质实,然而,由于在所难免的望文生义,“作诗如作文”一说还是常常被人误解,以为胡适是在强调诗要用散文的文法 (句法、章法),从而取消诗与散文的界限,取消诗这样一种文学体裁。
应该说,在胡适自己的理论思绪中,强调诗的内容应该质实有物,与强调诗的形式应该散文化,二者本来就兼而有之,遇到质疑,不得不做的阐释,终究未能让人释疑。在胡适的论述中,由于“作诗如作文”以及“文之文字”的文 (散文)与“以文胜质”的文 (文采)这两个含义迥然有别的“文”字交替出现,读起来还不免拗口。
2.文学革命毋庸置疑
胡适提出,文学革命乃历史必然,为白话诗问世寻找理据,其《〈尝试集〉自序》写道:“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是呀,三番五次的革命,诗史都接受了,有什么理由独独怀疑最近这一回呢?胡适此说,听上去相当雄辩。至于这一回的新文学革命之前,诗的体裁已经历了几次革命?是这里所说的五次,还是《谈新诗》所说的三番?这倒无关宏旨,胡适的理论兴奋点,不在过往的诗体革命史研究,只在此次革命的合法性昭告。
有趣的是,作为文学革命的鼓吹者,接下来引述的一首《誓诗》,自称是一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前半段攻击旧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后半段为文学革命立誓,用的却是前人《沁园春》的旧词牌,和文言文的旧风格:“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这份尴尬,有点像是20世纪初,中国人刚刚接触现代音乐,还不大会作曲,歌曲创作多用外国歌曲重新填词。其中,1912年问世的一首畅想着洗雪前耻、重振国威的《海军》:“纵横舰队密如云,此是中华新海军。国旗飘扬军威壮,将来独霸东海滨。”其曲调竟然借自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那首歌中唱的,是甲午海战中身负重伤的日本水兵三浦虎次郎临死还在询问,清军的定远舰击沉了吗?
3.打破一切枷锁镣铐
胡适认为:“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胡先骕反驳道:“然则何以有句法不整齐之元曲之后,乃一变而有句法整齐之剧本弹词,与乡民之曲本乎?”“是诗歌句法整齐,反较不整齐为自然也。”[11]28
胡适的格律枷锁论,胡先骕的“诗之有格律,实诗之本能”[11]27论,可能各有偏颇。依笔者浅见,在格律化与自由化两者之间,诗歌有着双向的冲动,既向往格律的严整,又向往自由的舒展。就像男女婚恋,人们既向往婚内的纪律和有序,又向往婚外的自由和无羁。在某一时代,格律化的冲动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格律诗成为主流;在另一时代,自由化的冲动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由诗便成为主流。一种诗体成为主流,也并不排斥其它诗体的并存。
《〈尝试集〉自序》里,更为人们熟知的一段话是:“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
这已是胡适的名言了,痛快淋漓,多次重申①这段话始见于1918年6月5日胡适给朱经农的回信:“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见胡适《答朱经农》,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尝试集〉自序》后,复见其《谈新诗》。,却是一种极端的、偏激的主张。诚然,诗可以用白话来做,用现代口语来做,可以打破五七言诗的格律,可以不理会长短句的词牌曲谱,可以抛弃典雅而艰涩的文言,可以打破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但白话诗毕竟还是诗,诗终须有诗的语言,包括诉诸听觉的乐感和通过想象诉诸视觉的意象。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语言,不加选择和提炼,是不大能入诗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果然如此,怕真是只有白话,没有诗了。故胡适此论一出,备受攻击。不仅宿敌胡先骕指其“主张之屏弃一切法度,视之为枷锁自由之枷锁镣铐,则为盲人说烛矣”[11]26。就连先前的追随者闻一多1922年5月作《〈冬夜〉评论》也大发感慨:“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12]1935年,梁宗岱更指胡适此论: “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②梁宗岱《新诗底十字路口》,见于1935年11月8日《大公报·文艺》第39期《诗特刊》。
然而,胡适此论更应该看做一种宣言,一种义无反顾地与旧诗决裂的姿态的宣示,而不是胡式白话诗的技法说明。胡适哪会如此愚妄,如此作践新诗,胡适《谈新诗》就分明在谈论着新诗的音律和意象的经营。而把白话诗的某些后继者由于才情不足粗制滥造而导致的种种劣质品的产生,统统归咎于胡适此论,更是不公平的。
至于这位白话诗的鼓吹者,一生未能写出一首白话诗的传世之作,其《尝试集》第四版补入的一首《希望》(我从山中来),半个世纪后被谱曲传唱,改题《兰花草》,却是一首“句法太整齐”、“不合语言的自然”的五言诗,这就真有点造化弄人了。
4.新诗的音节须顺应诗意
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已经批评五七言诗“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谈新诗》已经谈到新诗“句里的节奏也是依着意义的自然区分”,但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甚至还得意于“吾自己也常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和谐”。为此,朱执信批评了胡适所论之不足,明确提出新诗的音节应该“声随意转”,“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长短,跟着意思的转折,来变换”[13]。
《尝试集》再版于1920年9月。胡适在《再版自序》(1920.8.4)里说:“我极赞成朱执信先生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这话的意思是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朱君的话可换过来说: ‘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的音节’。”较之此前所论,胡适这里明确了一点:新诗的音节应顺应诗意。
大概在胡适看来,古典诗词的音律规范是预设的,一成不变的,词是填词,诗其实也是填诗,诗词的意蕴与所选择的格律是无关的;白话新诗则没有预设的音律规范,每一首诗的音节构成,都是以诗的情思表达为基础的,音义结合的。
不过,胡适的白话诗尝试结果,达到了他自己的理论诉求了吗?尽管胡适不无得意地宣称“最近这两三年,玩过了多少种的音节试验,方才渐渐有点近于自然的趋势”,待读到他所举之例:“一屋里都是太阳光,/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雪消了,/枯叶被春风吹跑了。”“热极了,/有没有一点风!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不知读者诸君意下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一种诗的音律的妙处,还需要诗人自己来做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赏析和导读,正说明个中妙处还难与君说。
5.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
《尝试集》的定本是1922年10月出版的“增订四版”,其《四版自序》(1922.3.10)称:“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这里,“缠脚”无疑是指旧诗,“天足”则指新诗。
可是,这比喻其实是很不得体的,是带有极大的偏见的。如果说五七言诗像缠过的脚,扭曲的、畸形的、残废的脚,惨不忍睹,白话诗 (自由诗)像天足,天然美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那么请问,散文诗像什么呢?像浮肿的脚,或溃烂的脚吗?散文诗在中国可是古已有之的,《庄周梦蝶》就是一篇经典的散文诗,它比通常的诗体的诗更见诗意盎然。
1916年,胡适与梅光迪等争论的是“白话是否可以作诗”[14],在最初的《〈尝试集〉序言》里,胡适还只是“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几年下来,胡适对白话诗已经充满信心,以至于非白话不成诗了。然而,白话诗 (自由诗)终归只是诗的存在形式之一,既不是唯一合理的存在形式,也不是唯一合法的存在形式,而女人的脚,却只有天足是天经地义的。可见,以脚为喻,只能是一个蹩脚的比喻。
格律诗、自由诗乃至散文诗,各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论诗如果一定要用比喻,依我拙见,水的三种存在形式,冰、水、汽 (云雾),黄豆的三种制品,豆腐干 (以及豆腐)、豆腐脑、豆浆,乃至书法之楷书、行书、草书……都不妨用来设喻,都比以脚为喻要科学得多,得体得多。舞蹈至少有程式舞、自由舞,绘画至少有工笔画、写意画,诗如何只允许有白话诗 (自由诗)一枝独秀呢?
结 语
就凭那远不完善的理论,远不完美的创作,胡适登高一呼,八方响应,白话诗几乎兵不血刃,便一举攻陷传统诗词的千年王朝。这一幕,让历史目瞪口呆。
1916年8月,胡适给陈独秀信中说“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随后成文,标题却改成《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后来解释说:“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15]待白话文、白话诗渐成气候,胡适关于白话文学的理论鼓吹便理直气壮,不再羞羞答答了。1918年4月,胡适写成《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直言革命,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1919年10月,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问世,其主张为《新青年》等诗人群所共信,“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16]。此后,白话诗成为诗坛正宗,取得了话语霸权,大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①独秀《答适之》,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之底气。于是,1921年胡先骕的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撰成后,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亦无一敢为刊登者”[17]。只得创办《学衡》杂志载之。
其实,作为对方辩友,胡先骕们的意见纵然偏颇,听听又何妨?胡先骕关于白话诗,关于胡适《尝试集》的结论倒是非常精彩的:“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此或《尝试集》真正价值之所在矣。”[11]59
不过,潮头总不免有泡沫和浮渣,泡沫和浮渣决不是潮头的光荣,但不识潮流的时与势,一味责骂泡沫和浮渣,尽管言之凿凿,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是历史的蛮横逻辑。
[1][清]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5.
[2]谢无量.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J].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
[3]唐德刚.《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N].联合报,1979-04-25.
[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0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59.
[5]胡 适.北京的平民文学 [J].读书杂志,1922(2).
[6]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N].民国日报,1917-04-27.
[7]毛 翰.克隆人四章[J].金秋科苑,1997(6).
[8]毛 翰.坦然迎接克隆人 [N].南方都市报,1998-05-25.
[9]梁启超.小说丛话 [J].新小说,1903年5月第7号.
[10]王泽龙.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 [J].中国社会科学,2007(5).
[11]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上卷[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1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77.
[13]朱执信.诗的音节 [M]//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34.
[14]胡 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
[1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9.
[1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M]//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7]吴 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29.
The Criticism on Hu Shi’s Advocacy of Vernacular Poems
MAO Han
( College of Humanities,Huaqiao univ. ,Quanzhou,362021,China)
Hu Shi’s theoretical advocacy of vernacular poems,mostly appear in Literature Improved Series,Opinion onNew Poetry and three admissions of Attempts Poetry. The Eight kinds of views in Literature Improved Series are completelyrelated to the poem,such as“must have contents in speech”. There are four arguments in Opinion on New Poetry as follows,Verse must great liberation,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ry is verse liberation,new poetry language must have " syllable"and " specific" . The main points in Admissions of Attempts Poetry are as follows,writing poets is like writing composition,literary revolution is definite with no doubt,breaking all chains,syllables must comply with new poetry,and old poetryis like bound feet while new poetry is free. The theories advocacy on Hu Shi’s period is all very much to the point,however,there are still many questions that can be discussed nowadays.
Hu Shi; vernacular poems; Literature Improved Series; Opinion on New Poetry; Attempts Poetry
【责任编辑 程彩霞】
I207.2
A
1006-1398(2015)03-0101-13
10.16067/j.cnki.35-1049/c.2015.03.012
2015-03-27
毛翰 (1955-),男,湖北广水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