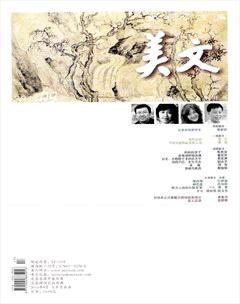采薇
熊莺
熊 莺
资深媒体人现供职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山色一时空寂广大起来,是因为,那时山下的一座寺院——大光明山普照禅寺,那日正举行盛大的法典。
梵唱声声,磬声如叩。
山,自从昆仑山脉延亘而来。大大小小的70座峰峦,山坳吐息,仿佛一时都醒着。它们相拥相偎,好一茎云莲。
那一年,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可圈可点。生得燕颔虎头的班超,那个墨夜,潜伏在西域楼兰古城大风嘶鸣的月色深处,几十号人,手持鼓、弩,屏息在匈奴人的帐后。他们正在孕育一个成语,“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他侧过脸,用气声与他的兵约定,“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
同年,公元73年,在南方古蜀的四川,仅晚于中国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而落成六年的大光明山中的这座寺院,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升座”典礼。
自印度来的两位高僧伽叶摩腾和竺法兰,闭目于禅堂,如如不动。
没有更多的史料显示那一盛事的细枝末节,但当地的地方志里留有这样的描述,此后,那里“方数十里,栋宇错落,皆缁舍(僧舍),绝无杂居……”
满山满壑,星月棋布着108座禅院,所谓山中“108盘”。杨慎曾流连于此,文人的叹息声被拓在一块石碑上:禅教之总持!
金色布地,玉砌天峦,异象无穷,同一片天空之下,当年这样的光景,留存了时光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一端。1900多年之后的这个七月的午后,当我踏入此山中时,昔年的寺庙、庵院、缁舍已荡然无存。唯见的人迹,是我上山的路上,伐木工新近留下的一条泥泞未干的山道。新伐的树木,就着一条窄窄的泥泞山路滑滚下山,是不是,那一日伐木人图省事,背来山泉将这路浸了个透。泥泞很深,黏黏的泥洼有一阵一下子吃住我的一只鞋,雇请的背夫在后面指路,我索性赤着一只脚,拎着那只鞋,一步一踬地往山上行。
还有的人迹,便是这山中,一座孤寺——明月寺里唯一的修行僧,释寂慈。
净灰的一袭中长僧衣,在屋前他平常吃茶的一张石桌前,我们坐了下来。
(一)黄昏
安好单(入住),晚课,是从下午五时开始的。
五开间的人字顶的屋宇,正中一间为禅堂。男女两众的寮房,分别在禅堂的左面。最右面的一间,为师父的寮房。寮房与禅堂之间,过道相通,仿佛,禅堂门,为殿门,同时也为这禅寺的“山门”。
背靠背,两对木门各自背在一起,背在大殿禅堂的门口。门,仿佛从未曾关闭过。山中的潮气,将门自下而上,雾出一层渐变的湿漉漉的青苔。
须弥座下,一张低矮的几案上,一张毛巾,师父掀开一角,取出两本经书,递过来。
临开课前,山下的一位田居士也赶上了山来。男众女众隔案对坐。棕垫的蒲团上,我结如意坐,坐在女子田居士的身旁。
一只引磬,师父从案上那陈年的锦囊中取出。他抬起把持并同时敲击这件法器的那只左手。
第一次坐在这样的蒲团上,那一坐,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寂慈师父,是不是,恰好“坐”在一个少年懵懵懂懂的心上。小小年纪,为何总被童伴唤作“小和尚”。亲生父亲,自己只能称“干爹”而不能父子相认。父子相克,克由宿业造,业又是什么……
佛门,总洞开在少年欲前行的每一径小路的拐角。
成年之后的他,那年从武昌佛学院修学出来,天初霁,好多条路延展眼前。空空净净的一张心,“话头”妙境都印在上面。好比雁过留声,云去有影。他跟自己说,于“唯识”宗,自己还远在门外。
从问生死、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只道是去佛门窥一窥,到如今,那年30岁的年轻僧人依稀得悟。经由坐禅,心空法喜,刹那之间的禅悦,他是受养到了的。
他转身择了一径,游学。
入籍江西真如寺后,一张枕套大小的薄薄的棕垫卷在身后,芒鞋竹杖,三两件僧衣,一如旧时的云水僧,山河,他拟一一踏访。
行脚至广东东华禅寺时,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闭长关。
他闭的是黑关。
东华禅寺外的狮子山,一山的岩洞,有一洞,是他的栖身处。
无声、无色、无光、无人、无已,亦无日月光华与四季冷暖。20多米深的山洞里,重门三锁。突兀的水泥台上,他寂然而坐。
一日一餐,那日,“护关”人将斋饭送至第二重门外,来人问,“山外,发大水了……要不要出来避一避……”那一瞬他方知,入关时,洞外春暖花开,而此时,外面已是秋风瑟瑟。
那时他也才觉知,莲台下那些溶洞里的暗流,受山洪影响,不知何时已涌作细流,涓涓有声……
庙堂之下的此山此寺,也是他当年行脚的到访地之一。
禅寺里的晚课,与别的寺院一样,也持诵经文《大悲咒》《蒙山施食咒》,还有《回向谒》。不同的是,药食(晚餐)之后,禅院,要打禅。即修禅定。
开素食店女子田居士,从山下带来食材,她提前退课,不多一会就做出了三两样素食放在屋前的石桌上。
课毕的刹那,师父从他的蒲团上起身。他手擒一杯,杯中“七粒米”。步态如履云。他往禅堂门口的寒林墩方向去。
一袭袈裟,浓烈的一袭明黄,给这个黄昏,着了一层绮艳。

(二)是夜
他将平日吃茶的一只搪瓷缸子放在石桌上,“有没有?”
缸子就在那里。
“还有没有呢?”他将缸子移走,移到石桌下。匿在掌中。
前面的有,为妙有,后面的空,为性空。性空,才是正觉,是实相。他对视着我。
那么,是夜,于漆黑的天宇下,田居士和我随师父修习禅定,黑夜之于我们,又或者我们之于黑夜,又怎的分解,哪是性空又哪为妙有?
师父的寮房,一张禅床,床前一立柜。柜子挡在床前,也同时是他平日诵经的书案。禅床,长,一米,深70厘米。好比一只单人的木椅子。
从狮子山出来,他自此习惯坐眠。腋不沾席,以禅坐的姿势而入眠。
初来此山中那一年,那夜,他坐于床上,如果从禅床的位置看出去,正好看到禅堂口一个侧面。
窸窣有声。他睁开眼,有人影晃动。谁会夜半造访呢?
他用手电筒照过去,影子匿去。
翌日,雨后的房前走廊,歪歪扭扭的硕大脚印。似人非人。后来知道,山下一户人家的玉米被掰倒了一地。山里来“老熊”了。
据说,先前,这深山里还有豺狼和豹子。
游化至此,决意留下,是在四年前。1900多年前的那座大光明山普照禅寺,早不复存在,后来空山之下的开化寺,应当算是老禅寺如今的法脉,山下的此寺有意在山上恢复重建山中的几座寺庙,以做开化寺的下院。砖头铁皮扛上山来,刚搭好了工人的工棚,不知缘何,工程又戛然搁浅。工棚于山中,一荒,多年。

五开间的砖屋,墙角蹿出荒草,何时何人,于此塑起了一尊等身佛像。圣像,正襟危坐,座于堂屋中央。蛛网尘封岁月。
用完最后一点随身带上山的干粮之后,他往山下走。当日他买回来一锅、一铲、一整盒的打火机,还有米和一些食盐。
三块鹅卵石垒在房前,悬锅做饭。拾来的薪柴,他绾成团往灶膛里送。
那日,有书生模样的读书人,拾起一节炭在他身后的白墙上书,“飘如风”。他见那人的字有骨秀,“您能替这寺写个名吗?”他递上一炭。
工棚下,十步开外处有昔年的“明月池”,六角形的水池,波光回文千度,当年曾引无数文人将相吟咏。他道,“就写,明月寺这三字吧。”
明月寺这三字,至今,仍如眉似黛,描在禅堂的门额上。
“明月寺”的屋后有昔年的晒经寺,紧临,是石佛寺。二寺之间,是七佛寺。杂草荒丛里,昔年那些庙宇阔廊曾经的龙头石柱,还有凿满横纹的庙基,偶尔你会看到。
是夜,这个夜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禅坐于曾经经声款款,华盖宝幡祥云瑞兽绘满穹顶的庙址上,这小小的禅堂顶,铁皮的屋顶之上,偶尔会有黄柏籽还有山核桃就着外面的青色果皮蓦地滚落下来的声音,啵!嘭嘭!——啵!嘭嘭!也有树叶在屋顶沙沙走过的叹息声。
一如,旧时的木鱼声、经声、“只手之声”,次第响起。“要止静了”,古僧尼合上“贝叶经”(当年印度传来此地)。如叶飞声,一纵人列队沙沙走向自己寮房的脚步声。今夜,好清晰。
黑夜合上幔子,十方虚空。
(三)清晨
指腹上的光阴,寂慈师父就这样维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那些个月与年的大时间大齿痕,他通常会掐着指头算。
隐居空山的差不多第二个年头,有山下的居士慕名而来。
田居士母病故,金兰姐妹又意外而亡,不知她们好不好,只是于梦中,她常给她们许愿。多凄怆无助的梦呀,梦醒时,自己却又总想不起来。人活在恍惚中。做着一个大品牌的当地独家代理,人也生得俏丽,她四处去烧香,去拜师。某日,一僧见她锁着眉头在庙廊里疾走,那僧侣叫住她,“别到处寻了,我给你介绍一位‘善知识,你去找他吧。”
做素食店符合她的因果,寂慈师父建议她开一间素食店。如今,她礼佛茹素,女强人的脸谱摘下来,心思已无滞碍。
清晨的早课,我们依旧并排而坐。有凉意,她用一床绒毯齐腰罩下来,罩住蒲团上的自己。譬如赤子,襁褓中的婴儿。我将带去的厚厚薄薄的衣物悉数加裹于身,护着双膝。
几部常规的经文诵完,师父从案上的毛巾下取出一部厚厚的经文,大部头的《大佛顶首楞严经》“每日一卷,今天我们诵‘卷七。”他开卷,然后,合十。
领诵。
《楞严经》是一部大经,这部共十卷,六万六千多字的经文被誉为“法门精髓”“性相总要”。第一次在寺院早课时相遇这样的经卷,我郑重地屏一回气。
“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皎如冰霜,自在能生一切枝叶……”
《楞严经》“卷七”重点开示,如若修持,如何设坛。
蜗牛从门口爬行过来,有体如蚕豆大小的蜘蛛在墙上迟疑,而昨夜在厨房的水槽边见到的一种发出击节韵律声音的“梆梆鱼”,是不是它?伏在那里状如青蛙。
一只蛤蟆蓦地一纵,吃掉前面一只无辜小虫。分不清哪一树哪一林的小鸟,啁啾啼转。一匹光,正正地照在一株柳杉的树梢。
每一个晨曦,这里是不是都如此这般醒来。
一炷香多一点的时间,“卷七”诵完。蜗牛留下一路艰难的来痕。见我垂念于它,田居士从外面拾来一片叶,渡它上去,然后送它到禅堂外的一棵黄柏树下。
“它无力自渡,生而为人,人才有这样的福分去渡它们。”她在树下与小生命呢语。
……
上午,师父出坡,打理寺院后面一片菜园。田居士早餐后独自去禅堂诵经。她在为母亲和自己的金兰姐妹诵一回《地藏经》。诵经是她每回上山的必定功课。
师父蹲在田垄间,在土豆、番茄、芋头和小白菜的那些菜苗间除草。地衣,间或地毯似铺陈在他的脚下。
从禅堂里出来,田居士邀我,“摘野菜去。”
水芹菜,长在野径旁,相对更加潮湿一点的荒草里。径旁树枝蔽日,她用手荡开,里面阳光明艳,果然另有天地。她在齐腰的水草中走,偶尔俯身,偶尔回头看我,手中一把菜,“佛法圆融,怎么说呢,不知哪种语言,那边(彼岸)的她们能够听懂……”
空山中的野菜,一年四季都有,打柴烧饭都是修行,不修之修。寂慈师父就是靠着这一山的野菜,隐居至今。耕地种菜,是后来有居士带种子上山来后才有的事。
从荒草地里踅回,她与我相商,“我带去你‘晒经寺吧?”
哪里有路呢?我折一棍,蜘蛛网网满小径,我一步一挥。
总疑着这林中会有蛇。
在一块悬在山岩上的巨石下我们止步。总以为,既为寺,曾经的寺的“影子”还是该有吧,而前方已再无路。
一块巨石从树冠丛中脱颖而出,仰向天空,所有的生灵,肃然侍立。六月六晒经书,想当年于这里的那些日子里,当是怎样的热闹与充满法喜。巨石与山岩下的洞穴里一僧正闭关,而巨石之上,一帙帙的经书被山风吹得哗哗作响。小和尚用手压住书,一边朝着师父的寮房急唤,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不知这山中,可还留存有,一梁半柱,可让世间人去匍匐,去找回人之初心、找回人之对天地鬼神对人类自己敬畏膜拜的那一庙。
……

纳满补丁的一件僧衣挂在厨房外的柴房雨淋不到的屋檐下,补丁覆盖补丁,仿佛“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那些话头禅机,都匿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布片下。
厨房里,半人高的薪柴,纹丝不乱,每一根薪柴如何堆放上去,自有方寸。锅台灶案,不落人间气……
“身心明净,犹如琉璃”,早课的“卷七”里,我反复咀嚼着这八字。已在这空山苦修四年的寂慈师父,还有田居士,他们又会心落哪些句子,反刍哪些妙章?
写下《空谷幽兰》的美国人比尔·波特竭尽心力近些年也在参修这部大经,他也日日禅坐。那年于四川青城山下的一书院,他从晨曦中晨练跑回来,那是他第几次来中国他自己都道不清,一次又一次,他缘何而来?佛法能纳须弥于芥子,无相的斑斓,他曾照见几许?那一次,他是否,也到访此山?
陆游钟爱这山中一鸟,此鸟声音清脆,一如捣药,他为之写下著名的《捣药鸟》。
此山所辖,四川境内的大邑。始称“大光明山”,后称,“雾中山”。
《四川通志》里关于此山这样记载:
东晋永和年间有佛图澄,唐代显庆年间有僧伽、僧护,后唐天成年间有僧简栖,宋代开宝年间有圆泽,明代永乐年间有普答舍耶,明正统年间有铁纳星吉在此住持,不断光大禅林。尤其是明代宣德七年,雾中山寺庙奉敕每岁征收二州八县钱粮作为培修寺庙之用。明代正德年间,皇帝敕赐开化寺僧人圆曦为都纲司官员,并赐给象牙图章……时僧众数千人……盛况空前。
这一季的野菜,除了水芹菜,还有洋篙、龙包菜(音)、红参叶、山药和笋子等等。因为我是客,那日中午,师父又去寺院后面讨来一把蕨菜,开水一汆,漂它在清水中。这菜,在《诗经》里,名“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