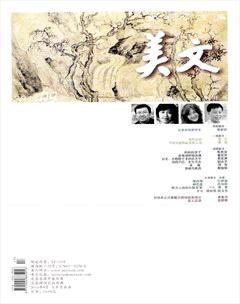那时记忆
西可
西 可
中国作协会员1980年代末曾赴深圳入N.P.L诗画工作室主持流浪诗人诗展和『现代风』画展1990年代起主编《大西北诗报》近年旁涉小说散文写作作品收入多种选集曾出席在以色列举办的第三十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出版诗集散文集等著作11部
看戏记事
我的很多记事都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唯独这看戏的事儿并不是小时候的事。
我老家在崇信乡下,信息也真够闭塞的,据说当年县城解放好几年了,乡下人还不知道,直到政府闹土改,工作组的人挨家挨户地给人家说,现在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不是民国了,那些人才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县剧团的消息当然也不知道。我那时正在县一中复习高考。大体上是一个星期回一趟老家背上一个星期的干粮,对县城的许多事儿并不知道。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里,庄里有人问我这个“城里人”可知道演戏的事,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笑着对我说,县城里请了陕西陇县剧团要演《野猪林》。经不起几个青年人的煽动,当天晚上几个人跑了20多公里路,去看戏。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秦腔吧,并不记得什么,在县城影剧院挤满了人,前排是一些椅子,后面腾出一些空地,可以站着看,算是站票吧。为了防止观众拥挤,在最后一排椅子后面挡了一根大木头。我那时年轻气盛,竟一直挤到那根大木头跟前,爬在木头上看。第一次看那舞台上的人穿着绣袍,戴着花里胡哨的戏帽。唱的什么,一句也没有听懂。
我最初认真地看戏并且逐渐喜欢看戏,大概是在乡下的土台子。草席子围成的或者是用大卡车上的棚布搭成的,一人多高的台子,开始用的是汽灯,天色还没有大黑就开始烧那灯罩子,打上汽,也透亮的,还吱吱地冒汽儿。那灯光似乎只照台面,里面极暗。但台上的演员却是如此地吸引我,花旦美如天仙,又穿着绸啊缎的,一张嘴更显婀娜。我那时候所在的乡是高庄公社,公社的戏台叫“人民广场”,还是公社中学的操场。在那个操场上我上过早操,打过篮球,或者来回走动去背书,或者坐在树下乘凉、聊天、吹牛,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看戏。我那时已经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教育,首先是在家里祖父的没有被抄被烧的书籍中找到了一些秦腔剧本,大概都是手抄本,如《荆轲刺秦》《二十四孝》。而我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秦腔爱好者,祖父那时刚刚平反,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工职,每个月不但能领到工资,还可以到公社的粮站上去打自己的面粉,尽管那份国库粮里面还有一半的杂粮,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来说,已经是天上地下,高兴得不得了。身心憔悴的祖父似乎恢复了自己记忆,能闭着眼睛倒着背诵《诗经》,是他给我讲述唐诗,也给我说了许多秦腔的事儿。西安的“易俗社”,平凉的“平乐社”,还有一些名角。我那时已经对秦腔充满了好感,恰在这个时候,县上剧团开始招收小演员,我的一个堂兄竟被选中,我那时的想法是要当一个演员,化了彩妆天天唱,将来说不定还是个角儿,结果令我懊丧了很长时间。
那时候公社演戏是不经常的,偶尔要演戏了,四面八方的人都会赶来看戏。台子底下并没有什么座位,刚开始就是土场子,观众自己有带小凳子的就座,没有的则席地而坐,坐下的都是上了年纪的,年轻人都站在后面,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有时候挤来拥去,尘土飞扬。场子周围会摆上小吃,诸如瓤皮、油糕、麻糖,还有卖的水果,颜色发黑的梨,蔫蔫的苹果。所以站在那里看戏,炸油糕的味儿会钻到鼻子里。还有看戏也成为青年男女看对象的好机会。我那时就有几个亲戚都是这样找的媳妇。当然,戏场上还会有许多绯闻,谁跟谁好了,谁跟谁亲嘴了,云云。我的那个堂兄一直在县剧团工作,和他一起进剧团的女孩子很多,他们刚开始都是一些吼娃娃,跑龙套,有几个女孩子确实很好看,我们常常议论,找那样的女孩子当媳妇应该是一件幸福事,但是他后来也还是找了一个做其他工作的女孩子,并不是自己的同事,我还替人家惋惜了好一阵子。那时县剧团当红的旦角大概叫段珍娥,是从陕西陇县调过来的;还有一个旦角在一个国营农场,县上一个副书记亲自去接,中途发生了车祸;唱的最好的须生叫张孝良,平凉草峰人。现在大概他们都还健在吧?那时平凉一带出名的演员好几个,崇信剧团王艺民,平凉县剧团的王朝民,泾川县的“麻女子”等等。王艺民平反后到剧团,我看过他演的《下河东》,只记得他整个一个大红脸,唱的戏很多,但一句词都听不清,似乎因为牙齿掉了原因,按音调儿哼哼。有一次,台下的小孩子扔了土块去打他,让他赶紧下去,他哼着调儿骂到:“我日你妈妈呀!你打疼老子了。”后来听说他的一个女儿也照顾在剧团工作,唱的太一般了,没有什么名气。王朝民更绝,九十岁了,在一些戏迷票友的纵容下,让人搀扶着还唱。路过的人都说他是一老“疯子”。王朝民还有一个儿子也在剧团工作,是敲扁鼓的,后来找对象就是父亲的学生,陕西人,两口子在平凉工作时间不长又调到西安去,听说还闹离婚。王朝民去世以后,两个人都回来奔丧,就在小区门口搭了一简陋戏台,和平凉剧团的朋友一块唱戏悼念自己的老师,很多熟知的人都说,儿媳妇唱得最好,动感情了,自己泪流满面,几度哽咽唱不下去。
有一年,平凉白水民间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在邻村搭台唱戏,演员都是农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唱《金沙滩》和《二进宫》,扮演杨继业和杨四郎的那个须生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就是他拉起这个剧团,自己导演自己也上场,杨继业数儿越数越少,他真哭,妆被冲了,有黑线流下来。也许,是真替那戏里的人哭,也许是为他自己。多少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听到过白水的那个民间剧团,我曾经问过白水当地的几个年轻人,竟然不知道。也许那个老人之后再没有人当导演了,也许是那戏箱烂了,不得而知。
在平凉工作期间,有幸看到马友仙的演出,算是真正看“戏”了。《玉堂春》最是精彩,苏三一身红色镶蓝边儿的囚服,戴了鱼形儿的刑甲,却艳得惊人,颜色对比十分鲜明,再跪在那里泪眼婆娑。在我看来她应该是最好的“戏子”了。有和我一样喜好的朋友给我分析说,单是那丹凤眼,鹅蛋脸,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的身段儿,别人就没有法子比,不要说人家的唱腔,那个脆!如同金做的铜做的一般,天生就是个艺术家坯子。从那时起,我便是马老师的忠实“粉丝”了。后来听磁带,吱吱拉拉的声音。我那时坐的车是辆老红旗,不能听CD只能听老带子,有陕西和甘肃出的带子,陕西录的声音要好一些。可我听来仍然如同真的一般。司机小何也似乎知道我喜欢听谁的带子,车上就买了不少这样的带子。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除了喜好秦腔的瘾儿,还接触了其他剧种,最迷当是京剧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京戏的,想来想去,大概是在某一次去静宁县下乡,在会计小斌的床上放着随身听,听的竟然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让我很吃惊,爱好如此广泛。后来知道他是在杭州上的大学,四年耳熏目染竟有如此收获,真是没有白上。我也买了一随身听,索尼的,声音不错。然后试着听起京戏来,一来二去,就这么喜欢上了。
我在长安大剧院看的第一场戏是《图兰多》,北大的齐国先生约了中央戏曲学院的曲老师一起去,票都没有买,直接留了最前排的座位,后面全是戏曲学院的师生,他们的声声喝彩声,让人羡慕不已。曲老师对我们说,她的学生中有不少日本和韩国的留学生,念完本科念研究生,有的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角儿”了。我那时真想去学戏,如果年轻一点,也许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曲老师说,没关系啊,我随时可以收学生,你只要到北京就找我好了。戏文没有学多少,票友也没有机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戏迷而已。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看张火丁的《春闺梦》,也是和齐国先生一起看的,火丁一出场,他先嚷嚷开了,好——啊,全然忘了是在剧院,如一个人一般。齐国先生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平时是个极其沉稳的人,但那一刻,却非常忘形,可见他早就是火丁的“粉丝”了。其实我也同样被吸引住了。火丁如一只蝴蝶一般,在台上翩翩飞舞。齐国先生对我说,张火丁冷艳逼人,似乎不容易与她热络,那种性格正是他所喜欢的。他竟然提议,要不要去后台看看她?去到后台,掀起帷幕,只见她正在镜子前,看看仍然盛装的她,俨然不是人间的女子,好像在云端,分外地遥远与薄凉。我们和她谁也没有说话,还有来回走动的其他演职人员,大概知道我们的喜好吧,并不说什么,旁若无人,京胡霎时响起来,该上场的上场,该卸装的卸装,台上人一张嘴,这台下还是一派唏嘘与叫好。我们就站在侧幕的边上,如同此刻的火丁,这台上台下的人生,有几个能识得了其中真正的滋味呢?
后来我看到中央十一频道白燕升主持专访张火丁的节目,谈了很多问题,还接通了火丁戏校的一位同学谈火丁,黄梅戏大家马兰谈火丁,谈了那么多,火丁也就淡淡笑了几次,真是冷艳逼人。再后来也说到在很多晚会上演出,火丁似乎不大情愿唱,赶紧逃开去了。火丁自己则说,主要是无法进入角色中去,唱得自己都不满意,所以,她大概不愿意那样又不得不那样。
关于张火丁,齐国先生还告诉我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张火丁自己出来成立张火丁工作室已经有好几年了,作为程派传人,生活很单纯,为了少去一些世俗的干扰,或保持一定的距离,业余爱好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冷美。2007年1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有人曾经问她,平常有过孤独吗?她自己则说,有时有,最开心的是一出顺畅的演出之后,与自己的哥哥一起去吃宵夜,当然,京胡一响她本人首先就被迷倒了。读到最近出版的《青衣张火丁》,深感真正的艺术家是孤独的,与世俗常常保持相当的距离。张火丁平常不多言一字,每年的演出数量都要严格控制,生活中更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但是在舞台上她却总能焕发出超乎想象的激情。也许这就是当下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作为真艺术的修行!京剧程派风格清脆如笛,和婉如萧,悠曳婉转,藕断丝连。这种风格也只有火丁这样的艺术家才能展示,在舞台上,似乎她游弋于戏的艺术海洋里,并不像诸多明星频频露面。我看她的《白蛇传》,到了断桥的时候,她哭了,观众也哭了。也许,这才是真正戏的开始。
去年秋天,我和育武几个人去安康看望诗人李小洛,第一次听到安康地方戏曲汉黄二调,觉得也很优美。小洛叫了她的朋友罗玉梅,她是安康市戏剧研究所的,原来是汉剧团搞音乐的,汉剧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之后,就专门去做研究,当然她也在带自己的学生,时间最长的大概研究九年了,但是她对我们说还不能独当一面。她就陪着我们几个站在一座公园的凉亭里唱《三娘教子》,然后给我们讲汉剧的历史。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汉剧就是京剧的前身,汉剧比起京剧来委婉凄美多了,似乎少了一些京剧的高亢明亮。而汉剧也一直活跃在地方戏曲舞台上,在汉江流域流传甚广。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们几个每每回味汉剧的那种优美动人的曲调,总是想着什么时候把小洛和罗玉梅老师请来演唱,几成梦想。
碾 窑
北方的山村多石碾。铁青色的碾盘,碾盘之下支垫的是一些大石头,沾满黎黑色的尘垢和一层厚厚的糠灰。碾盘之上一轮光滑的石磙,套着一副木架外连一支横杆,亦磨得光滑如涂油。用力推动那横杆,那石磙铁的凹窝与木架上木的凸锤相磨,发出一种咯叽咯叽的呻吟声。
“碾子口渴了。”或用早已预备好的清油抹布往那凹臼里滋润几下,碾子便会轻柔地转动起来。
我那时所见过、推过、碾过的碾子,安置在山庄最远的一座败落的院落,庄里人称着“碾窑”。最常碾的是小米,也碾其他物什。有的人推,有的牵着驴拉,碾盘四周的地上,一圈儿细细的尘土,布满牲口的蹄印和人迹,散发出扑鼻的糠味和牲口粪的青草味儿。一般是碾三茬,一茬碾罢,这家的妇人就用簸箕蹲在窑后簸去糠皮,由于天长日久,簸糠的地方变得格外光滑,谷油会染上半个洞壁。新谷上场,往往这家碾毕那家接着,来得早遇上谁家没有碾完,偏偏又是妇人领了几个孩子在推,便会帮着推上几圈,人来人往,荒凉的碾窑真热闹。农活忙的还有晚上来碾的,碾窑里早有搁油灯的台子,点上油灯,一圈一圈去碾。从早到晚,那里总响着“咯叽咯叽”的石碾声。如有谁家带了顽皮的孩子来碾米,则又有几个去碾窑凑热闹的野孩子,或折枝柳条儿帮助赶牲口,或几个孩子又推又拉把石碾曳得飞滚;这家大人赶忙阻止也来不及,“慢点、慢点,米颗颗全碾碎了”,赶紧扔下手里的簸箕,用扫帚飞也似的往外圈扫米儿,戛然,这碾又停了下来,孩子们头上冒热气,流着汗又跑到外面去了。惹得大人又大声呵叱自家的孩子,那孩子必是撅着小嘴,嘟嘟囔囔,一副极不情愿的姿态,边往外看又重新走了回来,推自己的碾子。而那些野孩子,先是去了涝池畔耐着性子钓泥鳅,接着捉了只蚂蚱或小青蛙,或是爬了老柳树捣鸟窝,拣得一个两个鸟蛋,用手捧了,重新回到碾窑来,喊着这孩子的名字,说是送鸟蛋来了,这孩子又碍着自家大人的阴沉脸,边推碾子边说着话,一直到这米碾好为止,大伙一块作鸟散。
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上学去了,等到略知人事,偏偏又听得奶奶讲了个关于碾米的故事。说是很早以前,有姑嫂两人一块去拣野菜,嫂子对姑姑说,明天早上我要碾些米,你听到碾子响就起来帮我推碾子吧。不想这话偏让一个狐精听见了。原来这家人的院里就有碾窑。第二天早上,小姑听到碾子响,就跑出来推碾子,那狐精见小姑上当了,就背起小姑跑回家去了。那狐精的家,实际是窝,偏又在一处碾窑。小姑一看屋里还关着一个大姑娘,那姑娘也是这么偷来的,而且已生下两个小狐精,还有一位老婆婆就是狐精的妈,狐精一个人蹲在门外磨一把刀子,小姑一看心里很害怕,就对狐精说:“狐哥哥,狐哥哥,你磨刀干啥?”狐精瞪着一双红红的眼睛说“杀猪!”“不见猪跑。”“杀羊,”“不见羊吃草,”“杀鸡!”“不见鸡叫。”“杀你!”小姑吓得一声也不敢吭。又过了一会儿,狐妈妈见小姑怪可怜的,就对她说:“好姑娘,我儿子是个狐精,你怎么敢来呢?”小姑哭着说了一遍经过,狐妈妈叹了一口气,就对小姑说:“门外有柴禾,你赶紧用柴去烧碾盘去,啥时候烧红,我啥时救你。”小姑听后赶紧去烧碾盘,狐精对他妈说:“刀已磨快了,赶紧杀了煮着吃吧!”狐妈妈说:“我老了,吃烤下的,我已叫那姑娘去烧碾盘了,等烧好了烤着吃。”狐精听了就放下刀子等着烧碾盘。狐妈妈对狐精说:“我儿的眼睛怎么烂得很?”狐精说“那是因为好几天没有吃肉了。”狐妈妈就说:“我给我儿治眼睛,你快去打一盆浆子来。”狐妈妈用浆子糊上狐精的眼睛,又给他一罐肉臊子,对他说:“你赶快到有太阳的地方去晒,只要臊子吃完,眼睛就好了。”狐精照着做了。这时过了一天一夜,小姑把碾盘已经烧红了,狐妈妈把关着的大姑娘也放出来了,大姑娘还舍不得两个小狐精,一边一个领着,和小姑沿回家的路跑了。过了好长时间,狐精问她妈:“怎么这么热呢?”狐妈妈说:“耐心等着太阳上来。”又过了一会儿,狐精再问没人答应,他赶紧撕了糊眼睛的浆子,一看,狐妈妈已经上吊死了,小姑和妻子跑了。就一路哭着追了上来,一直追到一条河边才追上。他在河边嗷嗷直叫,想跳过河来,不想河太宽,掉进河里淹死了。两个小狐精见自己的爸爸淹死了,就双双碰死在石碾上。因此,碾子一推就咯叽咯叽响起来,那实际是两个小狐精的阴魂不散,一直不停地哭呢。
不知从何时起山庄通了电,买回了磨面机、碾米机,石碾已经闲置了。渐渐地,人们似乎忘记了它。当然更没有孩子去碾窑打闹了,连那首古老的歌谣也一起消逝了。
@ 小狐精
@ 真可怜
@ 哭了妈妈哭爸爸
@ 有时哭有时笑
@ 有时跳到碾盘上
@ 又碾米
@ 又买盐
@ 又娶媳妇又过年
@ ……
我曾信步走进那座荒芜已久的院落,总想看看碾窑现在的样子。安置石碾的窑顶上坍塌半露,碾盘周围的野草丛生,且碾盘斜倚,石磙滚在一边,因风雨剥蚀,已不显光滑,蓠蒿草中传出蟋蟀和纺织娘幽幽的吟唱。而我总是隐隐地听出“咯叽咯叽”的石碾声,且有头小毛驴慢悠悠地拉石碾,得得得得的蹄音;那碾盘上可是新碾成的小米映着晚霞,闪着金子般的光芒;也有顽童日日做的那种游戏,捣鸟窝,捉青蛙;也有人正唱起那有声有韵的小调来;也有小媳妇红着脸挎一草筐与她的小姑缓缓走来;碾盘已经烧红,小狐精正在幽幽地哭泣……
火车的记忆
上世纪末是中国人以铁路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人们踏上离家和回家的路,艰辛疲惫却能泰然处之的旅途,全都在火车与铁轨的隆隆声中呼啸而去。
时间似乎一直在考验我们的记忆,让我们忘记什么不忘记什么,都在恍然之中。仿佛一切也都在冥冥之中,说不出,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一个时代的结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诞生。火车的记忆让我们不能不感叹时代的飞速发展和我们自己生命的更迭。
大凡坐过蒸汽火车的人都对那样的经历有着浓浓的感情。蒸汽机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真正的蒸汽火车只有在博物馆里参观,而且只能听讲解员的讲解,你一定看不到那白色的蒸气,听不到苍凉的汽笛。偶尔在老电影里,在电视剧里你突然看到了,也听到了,你一定会回忆起当年太多的遭遇,太多的人和事来。我那时竟然冲动到半夜里打开电脑,在互联网上搜索关于蒸汽火车的信息、资料和文章。接连几天,我在我的日记里寻找当年乘坐蒸汽火车去出差的行踪。我还和我的妻子讨论这个话题,在博客里邀请朋友来说说。结果是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规律,是人类进化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令我满意,难道是我自己神经过敏?
我还是找到了一位老铁路工人的回忆录:“每当听到蒸汽机车长鸣的汽笛,铿锵有力的节奏,有如声势威猛的巨龙吞云吐雾,好不威风。我的心率仿佛被打乱,能够听到自己血管里血液奔涌的声音。你再看看那些大红色的车轮子,就像我们北方人,豪爽浓烈。”原来这位老大哥是东北人。是啊,上世纪在中国这块美丽的大地上,黑与红,血与火,生与死,曾经无数次地冲刺着我们的眼睛和记忆,黑红相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拥抱着自己的血色北国;蒸汽升腾的火车头就像一位怒发冲冠的将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战场。“库——库——库”的隆隆之声,着实让人震撼!
内燃机车比不了,现在的电动机车和高速列车也比不了,它们都不冒烟,乖乖地像被人们降服了巨龙少了气势,多了温顺。
但是,蒸汽机车毕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后来的内燃机车、电动机车肯定也要退出,只是还没有走完自己的旅程,就连现在世界上流行的高速列车也会退出,只是我们这些人看不到了,我们无法想象后来者的智慧,如同那些网友无情地戏谑一样,我们和我们的未来都在进化。
我还是想说说毕竟古老的蒸汽机车。据可靠资料记载,2005年12月9日,内蒙古集通线大阪机务段,全世界仅存的最后一条蒸汽机车线路正式停运。据说,蒸汽机车从它诞生点火的那一刻起,从来不会停炉,从来不会熄火,因为停炉和熄火就意味着这列机车将要退役,然后拆散、破碎、挤压成一堆废铁!这该是怎样惨烈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反复观看的那些所谓大片,人类自己一直不停地试图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机器人,然后再想方设法打碎这样的想象,杀死那些为人类的智慧而献身的机器人。有生就有死,所有的生命都不能例外。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过程,进站、鸣笛、吐气、落火、灭灯,然后把没有烧完的机车煤卸下来,把水放出去,一列一列在线上停好,最后的蒸汽机车,最后的时间,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夙愿,我决定去看看记忆中真正的蒸汽机车。从平凉古城经银川到内蒙古一路高速,车少不限速,第一天就到呼和浩特,第二天擦黑就到了集通。幸好内蒙古人还保留了4台机车作为旅游专列,到时候谁要包车,拍电影,旅游兜风,就可以重新点火。据说,刚开始就有外国人花几十万来包。这样的美事我等是万万办不到了,好在其中还有一台专门作展览,我们就在车门口留影,满足一时的遗憾。
出火车站不远,有一“老工人酒菜馆”,蛮有怀旧的感觉,我们就在这里吃饭。没有想到这小店的主人就是一位退休的老火车司机,我们就蒸汽机车这个话题重新聊了老半天。他说他会把“火车”叫“老伙计”,就像他的另一个老伴似的,他那时擦车、修车、给车上水,就像照顾自己的老伴一样的心情。你想象看,机车的锅炉距人不足1米,司机室也就3个多平方,夏天熊熊炉火炙烤难当;因为司机瞭望口不便安装玻璃,冬天里外一样刮风,一样飘雪,因此,我们火车司机几乎都是关节炎。还有一台蒸汽机车一次要加22吨机车煤,都是副司机和司炉工一锨一锨送到炉膛中区的。在蒸汽机车上工作,夏天守着锅炉就不要说了,冬天面对锅炉经常前面是汗,后背上却是冻冰,总是半身被风吹,半身被火烤。而且还不能定点儿吃饭,饱一顿饥一顿,从年轻时生物钟就被打乱了,老了反倒习惯了。冬天一身霜,夏天一身汗,浑身都是机油味,回家洗完澡,躺在被窝里都是油味儿,老婆孩子都跟着闻习惯了。尽管这么艰苦,但是老人的眼睛里充满兴奋,看得出他对机车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他反复说:“做梦都在机车上。”
几杯酒下肚,老人似乎敞开了自己的胸怀,也许同事、家人、朋友,他们并不知道,老人开这样一个酒菜馆的真正理由,他想抬头就能看到自己工作了近30年的火车站,他也希望能够看到那白色蒸汽,听听那醉人的汽笛声。他还说他先后带了几个徒弟,他们现在还在开火车,开的是内燃机车,干净、有暖气、有电扇,还能烧开水,他们很高兴。
最让他伤心的大概是曾经陪伴了他大半生的机车很快就被切割成废铁。他说:“那几天,当我看到那些被切割的机车,又被压缩成铁块,装上卡车,拉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的,仿佛失去最亲的亲人一样。说实话,我父亲去世了,我都没有掉眼泪,都是那几天我哭了,我就是受不了,我就是这么个人。”
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位老工人当时的心情,但是,我突然想起这些年以来,我在崆峒区任职以及后来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任职期间,处理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改制中,诸多老工人当场痛哭的情景,我那时总是简单地认为,他们的失态也是为了自己的工龄补偿或者医疗药费的多少,现在想来我是多么无知和粗心。人只有在经历了某种生活工作的历练之后才有自己的发言权。过去的已经无法弥补,将来也已不属于我等筹划,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点点善良竟然没有表现的机会。
据说,在蒸汽机车的娘家英国,每年还要举行蒸汽机车节来纪念这位对人类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功臣。从1871年第一台蒸汽机车进入中国,延续到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蒸汽机车退役的国家,蒸汽机车也带来时代的革命。除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人类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不光是人们的出行得到了自由,物流得到了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梦想也随之飘扬。
回头一笑,自家又是那里的“老”呢?蒸汽机车这个词就让它在钟爱它的人们心里永远冒着热气闪着火花,永远地保留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