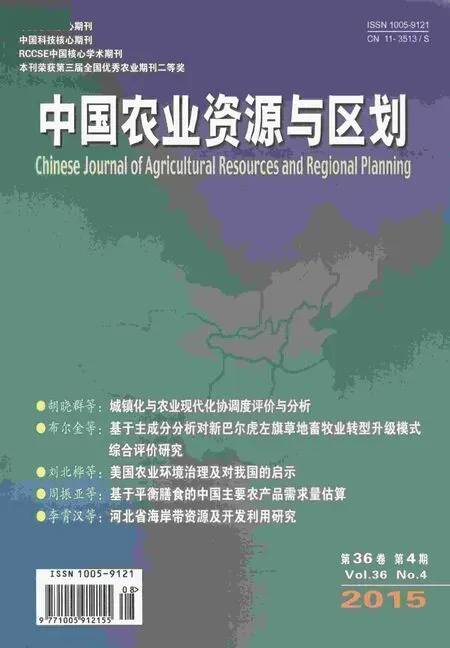广西县域农民农业收入差异时空变化研究*
张恒松,黄 跃
(广西大学商学院,南宁 530004)
农业收入高低是农产品实现价值与否的重要判定条件,是一个地区农业发展好坏的直接外在表现。农业收入是衡量区域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关系到农民,尤其是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的扩大再生产意愿及能力,是农村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因此,正确地认识农业收入的区域差异及时空变化对于发现农业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现代化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是我国西南重要的农业省份,近年来农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与此同时,有关农业收入的文献逐渐增多[1-9],已有成果为正确认识广西农业收入现状,发现问题所在,制定合理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收入提供了有益理论借鉴。但通过研读,发现已有文献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如,现有研究多将农业收入以夹杂在农民收入结构中的角度进行[1-4],并未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导致分析口径较为宽泛;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多局限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5-9],缺乏直观的可视化效果,无法反映广西农业收入在空间层面的动态变化。鉴于此,作者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改进:首先,将农业收入从农民收入中剥离开来,进行专门研究,数据的变动只涉及农业收入这一方面,借以改善对纯农业收入研究的轻视。其次,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纳入农业收入在各个县域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时、空角度分析广西农业收入存在的区域差异及其格局变化,更好地反映农业收入变化特点,以期弥补目前广西农业收入研究缺乏空间分析的现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过程中相关数据的权威性、一致性,数据资料均源自《广西统计年鉴》 (2005、2009、2013)。研究过程中,基于区域空间单元在行政区划层级的可比较性,选取广西74个县 (县级市),以及14个市辖区 (14地级市所辖市辖区分别进行合并,且各市辖区人均农业收入数据取算数平均值)共88个基本空间单元作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作为空间分析的常用方法,文章引入Global Moran’s I,Getis Ord General G两个重要的分析指标来测度全局的空间关联特征;引入Getis Ord G*来测度局域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识别观测区域的热点区与冷点区,及其空间分布变化,进而反映目标区域的时空变动。
2 农业收入差异时空变化
为保证研究的系统性与分析角度的全面性,该文对县域农业收入差异时空变化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全局层面上广西县域农业收入差异。其次,分析局域层面收入分布状况,针对冷热区域的时空变化进行研究。最后,在综合全局与局域分析的基础上,以广西目前的经济区划板块为空间载体,对具有相似区划背景的县域进行收入差异的进一步分析。
2.1 农业收入总体格局演变
2.1.1 农业收入分级
图1为2004、2008、2012年广西88个空间单元的人均农业收入分布,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Jenks)将各年份数据分为5个收入等级,依次为:低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

图1 2004年、2008年、2012年广西县域人均农业收入等级分布
通过分析得到主要结论有:(1)较高、高收入集聚区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字形,主要集中在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和以柳州为中心的广西中北部。(2)2004、2008、2012年均显示为高收入的县域仅有柳城县、宜州市、武鸣县、崇左市辖区,其余高收入县域在不同年份多有变动,可见,多数高收入县域并未形成等级优势的自我强化。(3)较低、低收入地区广泛分布于东部、西部,尤以西北部地区显著,西部涵盖河池、百色两地级市绝大部分县域,东部则涉及梧州、玉林、贺州多数县域。(4)收入格局显现凹陷点,2004年柳州市辖区位于较高收入等级,但在2008、2012年一直位于中等收入等级,且处于高收入分布区的包围圈,局部凹陷现象出现。(5)与广西西南部崇左、南宁相比,桂林、柳州的农业县域收入高等级数量上不稳定程度更为明显,“双核心”向“单核心”转变趋势初露端倪。
2.1.2 总体分布格局
文章计算了3个时间截面的人均农业收入的Global Moran’s和Getis-Ord General相关指标,并对结果进行了相应的分析,通过分析可知:
(1)检验结果Z(I)显著,2004、2008、2012年Global Moran’s估计值全部为正,且数值从7.961 0下降到2008年的6.781 9再到2012年的6.059 7,不断降低。这表明,2004年以来,广西县域人均农业收入处于同一分级或者相近分级的县域空间集聚趋势不断减弱,散点现象增加。例如西部地区的百色市辖区、田东、田阳3个空间单元独立构成较高收入等级集聚区,远离南宁辐射圈。同时,2008年相比2004年的Moran’s I减少值为0.076 7,2012年相比2008年的减少值为0.048 9,同等时间段内,减少幅度小于前者,说明收入等级相同或相近县域散点态势有所缓解。
(2)Z(d)值显著,且3个年份的Getis-Ord General统计指标的观测值和期望值均大于0,表明广西县域农业收入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现象。但2004年以来,G(d)数值逐渐下降,从0.064 7到2012年的0.062 3,说明空间集聚现象有所减弱,同时,G(d)数值变化幅度较小,表明广西县域农业收入的中间高、两侧低的整体格局仍然存在,并无明显空间变迁。
2.2 农业收入冷热区域格局变动
前面分析了广西2004年以来县域人均农业收入的分级以及初步变动,但并不足以反映收入格局的深层次变化。为全面反映农业收入的地域变化,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空间单元的冷热变动。2.2.1 冷热区域的演化
针对2004、2008、2012年数据,分别计算其局域空间关联指数Getis-Ord G*,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将相关数据分成4类,依次为“冷点区域”,“次冷区域”,“次热区域”,“热点区域”,并可视化 (图2)。
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农业收入冷热区域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热点区域”、“次热区域”集聚中部地区,“冷点区域”、“次冷区域”集聚东、西两侧,且各自呈现显著“俱乐部趋同”现象。(2)2008年、2012年部分“冷点区域”转化为“次冷区域”,冷点县域数量显著减少,梧州市、百色市所辖冷点县域集聚区在2008年消失,2012年仅河池市仍存冷点县域集聚区。尽管如此,上述区域仍处于收入边缘化圈层。(3)局部地区出现“次热区域”向“次冷区域”的逆转化。以桂林市所辖县域为例,2004年、2008年桂林市部分县域为“次热区域”,却均在2012年滑落“次冷区域”,据统计,2012年桂林13个空间单元的农业人均收入占人均总收入比重平均高达79.35%,在农民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他收入所占比重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如何巩固既有成果,避免收入等级下行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4)“次热区域”、“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广西西南部以及中北部,且环状分布特征较为明显。(5)2004年以来,以南宁、柳州为“双核心”的热点聚集区域状态始终未变,但柳州的热点核心区所辖县域数量有所减少,相比之下,南宁的热点核心基础更为牢固。
2.2.2 冷点集聚区缺乏“热点飞地”
进一步分析发现,3幅图中,在西部冷点县域集聚区,均不存在最高等级“热点区域”与最低等级“冷点区域”的地理邻近,冷点县域集聚区缺乏强有力的热点县域借以带动发展。由于冷点地区自身缺乏活力,规模性冷点集聚将加剧发展环境恶化,易于形成恶性循环累积,最终不利于当地发展。当前,广西热点飞地的缺失将约束“局部突破,点状带动,多点开花”发展模式的形成,西部河池、百色所辖众多冷点县域将长期存在。

图2 2004年、2008年、2012年广西人均农业收入冷、热区域分布
2.3 各经济区板块内部县域农业收入差异
为促进广西区域经济发展,2009年国务院根据广西各地级市的职能属性和区位分布,以及资源、产业状况,在沿袭各自地区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将广西分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桂西资源富集区、西江经济带3个经济区板块 (图2)。该划分明确了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分布,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内部归属,推动了集团化发展,增强了区划内部的互联互通及对外竞争力。为满足研究需要,作者借用3个经济区板块的划分方式,将广西农业收入区域进行范围界定,进一步研究经济区划板块内部县域的具体差异。
2.3.1 北部湾经济区内部农业收入差异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板块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4个地级市组成,是广西的优先发展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造就了该区域农业收入分布呈现如下空间特征:(1)县域之间收入等级结构较为均匀,无明显空间差异,2004年以来,仅有个别县域出现收入等级的上行或下滑,南宁市隆安县实现突破,进入热点区域,钦州市灵山县则退出热点区域。(2)该区域整体收入水平较高,长期缺失农业低收入区。南宁以现代化农业种植为主,拥有海岸线的钦州、防城港、北海市则以水产品养殖为主,辅之以畜牧业。虽农产品类型差别明显,由于交通便利,区域内互联互通发展相对成熟,市场共享较为充分,农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及时实现价值转换,农业收入等级并无明显差别。
2.3.2 桂西资源富集区内部农业收入差异
桂西资源富集区包括崇左、百色、河池市,近年来由于资源开发而获得发展。由于所辖县域单元数量较多,区域内农业收入空间分布特点较为显著:(1)南高北低阶梯状明显,崇左所辖县域收入在较高、高等级分布上占有绝对优势,百色、河池与之相比差距明显。在边境区位价值的竞争方面,百色、河池难以匹敌崇左,2008年崇左市凭祥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诱发的巨大政策优势迅速挤压了前两者的发展空间;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竞相落户崇左,固定投资迅速增加,农业发展获得强力助推器;同时,由于邻近南宁,崇左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资金投入、市场销售等环节占据优势,并成为南宁农业生产辐射圈的组成部分。(2)河池所辖县域冷点居多,但仍有局部突破。所辖宜州市、罗城县成为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另一个“次热区域”,也是河池仅有的较高收入集聚地。罗成县“公司—基地—农户”的订单式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收入,而作为“全国最大桑蚕养殖基地”的宜州市,农业收入同样不断提高,随着农民对特色农业生产重视程度的提升,益州、罗城的农业优势逐渐形成“循环累积”。
总体上看,2004年以来,除去南部崇左多数县域,中部百色部分县域,北部河池罗城县、宜州市,桂西资源富集区其他县域仍为冷点集聚区,且空间分布呈现稳态。
2.3.3 西江经济带内部农业收入差异
西江经济带包含柳州、桂林、来宾、玉林、贺州、梧州、贵港市,与另外两区相比,西江经济带所辖县域数量最多,农业收入差异空间分布也更为复杂。表现如下:(1)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西高东低态势,冷点区域集中在东部梧州、玉林、贵港、贺州,热点区域则以柳州、桂林、来宾为主,且2004年以来整体格局未有明显变动。(2)从活跃程度上看,南部地区县域强于北部县域。中部贵港市所辖平南县,梧州市所辖岑溪、藤县摆脱收入冷点区域,实现收入格局的转变,南部玉林所辖博白县成为次热区域,而北部贺州所辖富川县,桂林部分县域出现下滑。(3)传统农业大市,农业收入偏低。以玉林为例,2012年玉林市农业人口为485.72万,仅次于南宁,排名第2,农业生产总值排名第3,仅次于南宁与桂林市;但以市级单位衡量的人均农业收入,玉林排名13,仅高于河池市。可见,传统的养殖与耕作效率不断降低,优势逐渐丧失,农业收入增长空间有限。
3 收入差异时空变化影响因素
广西农业收入的区域差异现象源于多方面因素,可以归纳为:地理位置因素,各区域农业细类结构及农业新技术采用速度,区域发展战略。
3.1 地理位置因素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地理位置常通过距离消费市场远近、交通可达性等渠道发挥作用。地理邻近性等因素对农业生产及农户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大[10],与相对发达地区的“地理邻近”成为一种地缘优势,并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比如,北部湾城市群所辖县域人均农业纯收入近年来持续走高,与南宁在地理上的邻近成为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靠近南宁,基础设施建设隶属南宁辐射圈的战略规划,多条高速公路为农产品市场价值的顺利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外界环境。以现代化农业发展迅速的崇左市为例,近年来,凭借“首府后花园,农业战略储备基地”的角色地位,崇左日益强化与南宁的农业生产合作,努力实现农业资金、技术互联互通,诸如扶绥县、宁明县逐渐被纳入南宁农业生产辐射圈,“南宁—崇左”互联互通格局下的人均农业收入热点集聚区初步形成。
偏远的西部、东部部分县域则因远离地区性中心城市,地理区位价值较低,农产品销售受到抑制。同时,偏远的地理位置还限制了企业落户,约束了农产品的就地采购与加工,强化了中低收入县域的集聚与收入劣势。
3.2 各区域农业细类结构及农业新经营方式采用
农业有细类之分,且各自地理根植性不同,种植业、林业、渔业因其对土壤、地形和水资源的强依赖而造成生产灵活性较低,一旦地域分布形成,难以改变;畜牧业则因主要依赖饲料和市场而地域选择性较强。由于农业的根植性,广西不同区域不同农业生产格局将长期维持,并导致农业收入比重的显著差异(图3)。

图3 2004年、2012年广西各区域地级市农业细类收入比重变化雷达示意
图3显示了广西14地级市农业细类收入比重在地域分布上的显著特征。进一步来说,农业细类引发的收入比重差异,将逐渐诱使不同地区对农业生产进行微调,重视程度也将不断变化。由此,对先进农业经营方式的采用快慢将强化农业收入差异。以甘蔗种植业为例,甘蔗滴灌技术对甘蔗增产效果显著[11],崇左市作为甘蔗种植集中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2004年,崇左市江州区的农民人均甘蔗种植收入多于广西其他地区542元。而在新的经营方式逐渐普及之后,2012年,该区农民人均甘蔗种植纯收入达9 645元,比非项目区农民高出2 478元。[12]与此同时,江州区甘蔗产量继续稳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而崇左市甘蔗产量更是占到整个广西的1/3,继而诱使崇左市种植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3.3 区域发展战略因素
近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不断深化,广西地缘优势蕴含的经济价值得到彰显,南部地区尤甚。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10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镇群规划纲要》陆续实施,重大项目优先部署、政策支持适当倾斜的措施推动了南宁、钦州、崇左等市的经济发展。连续不断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了区位价值的循环累积,由此产生的空间辐射效应与空间邻近效应产生叠加,这种“局部高地现象”促进了上述区域的经济发展。良好的政策优惠加速了一批农业生产企业的落地,借助原有的群众基础,“农户—公司—市场”的生产模式在这些地区逐渐得到拓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联动一体既活跃了县域经济,加剧优势积累,又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增加了农业收入。
4 结论与讨论
该文以2004年、2008年、2012年3个时间截面的人均农业收入为切入点,以时间、空间变化为分析角度,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全局、局域、经济区板块多个层面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2004年以来,广西县域人均农业收入普遍增长,但收入绝对差距逐渐加大,较高、高收入分布格局呈现“/”字形,且此形态将长期存在;中低收入县域广泛分布于东、西两侧,虽部分县域向中高层次转化,但仍呈零星分布。
(2)县域收入空间格局整体保持稳定性,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2004年以来,虽有一定转变倾向,但以南宁、柳州为双核心的热点聚集模式得以维持,百色、河池为收入边缘化集聚区;在农业收入仍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防止农业收入等级下行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冷点区域集聚区缺乏“热点飞地”,具有“局部突破,点状带动”功能的县域单元尚未出现。
(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农业收入最具竞争力,且县域收入等级在结构上较为均匀,无明显空间差异;桂西资源富集区农业收入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将长期存在,但局部热点区域出现;西江经济带因涵盖县域较多,农业收入问题较为严重。
(4)地理位置、农业细类结构及新经营方式采用、区域发展战略是造成农业收入地区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地理位置主要通过消费市场远近,以及交通通达性来影响农业生产,农业细类凭借地理根植性强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新经营方式的采用来影响农业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则通过政策获取、生产组织方式改进来促进农业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整体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广西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农业收入与产业结构的错位现象:即农业比例越高的地方,农业收入往往较低,而第二、三产业发达的地区农业收入往往较高,可见,传统农业生产经验以及群众基础并未有效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如何将农业传统生产区域的生产经验、群众基础与现代科技有效结合,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摆脱“家家户户务农,家家户户低农业收入”的现状,成为收入冷点地区诸如百色、河池、梧州、贺州等地区需要重视的问题。
[1] 窦登全.广西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及其收入来源分解.特区经济,2014,(1):177~179
[2] 程波,王敏琦.新时期广西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及地区差异状况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5):9451~9453
[3] 徐世平.中国最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研究——以甘肃省“两州两市”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33(2):78~82
[4] 于平福,麻小燕.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特点及原因分析.广西农业科学,2001,40(3):157~159
[5] 陈光春,马小龙,周柯.广西农产品外贸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江苏农业科学,2012,(8):382~384
[6] 卢小丽.基于灰色模型的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以四川省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34(6):219~223
[7] 欧家瑜.基于协整与Granger检验的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产值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国证券期货,2013,(5):193~194
[8] 郭绪全,秦娟,覃伟.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演变特点及对策研究.广西农学报,2009,24(4):69~73
[9] 黎雪林,吕永成.广西农业投入与农业增长灰色关联分析.广西科学院学报,2004,(2):88~91
[10] 樊新生,李小建.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8,(3):16~23
[11] 黄运好,等.滴灌技术对甘蔗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现代农业科技,2010,(19):107~108
[12]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蔗田蓄积“节水能量”.广西新华网http://www.gx.xinhuanet.com/2014-08/25/c-1112585.htm
——居住在“冷点社区”与健康欠佳、享有卫生服务质量欠佳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