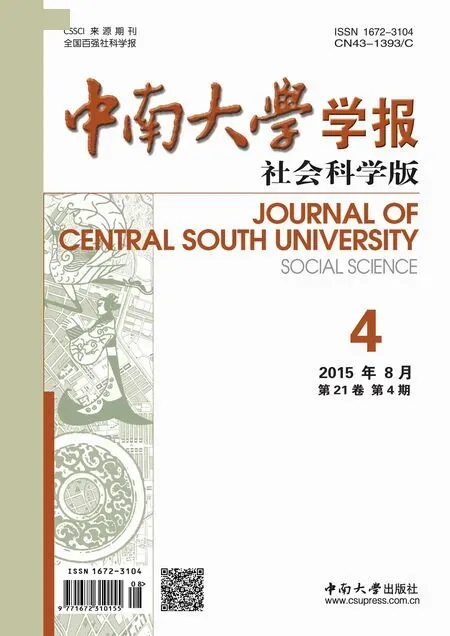唐代武氏世系史料源流关系辨析
李轶伦
(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江苏南京,210023)
唐代武氏世系史料源流关系辨析
李轶伦
(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江苏南京,210023)
唐代武氏家族世系主要见于《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其记载有同有异。岑仲勉先生以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主要史源为《元和姓纂》,但研读武华以前世系,有充分理据可证其间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当各有史料来源,其记载可互为补充。《古今姓氏书辩证》则抄撮《元和姓纂》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而成,且以前者为其主要的史料来源。
武氏世系;《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史源
武氏为唐初显姓,其家族成员大多身居要职、封爵王公,且五人官至宰辅①,在初、盛唐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人研究唐初历史,尤其武周一朝,多会涉及武氏诸人,包括其族员世次及所任之官职。唐代武氏家族世系主要见载于《元和姓纂·卷六》《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三》。此外亦见于《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六·武氏诸人本传》《唐中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润州司马赠吏部尙书沛国公武公(就)神道碑铭并序》[1](265−268)《大唐故右勋卫宣城公武君(希玄)墓志》[2]《贺州刺史武府君(充)墓志铭》[3](5004−5005)《兵部侍郎赠工部尚书武公(儒衡)墓志》[4]《大唐故怀州刺史赠特进耿国公武府君(懿宗)墓志之铭》[5]等。诸书记载之同异情况如何,其间是否有直接的史源关系,厘清这些事实,将有助于我们判断各家史料之信值。
一、武华以前世系
关于武氏早期传衍之记录,今本《元和姓纂》(下文简称《姓纂》)只存两段,云:
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汉初,武臣为赵王,又有武涉。功臣表,梁邹侯武彪,传封六代,后居沛国。汉又有祭酒武忠,望出太原。
【沛国】武彪裔孙周,魏南昌侯;生陔,晋左仆射、薛侯。五代孙洽,魏晋阳公,始封居太原永水,或号太原武氏。洽曾孙居常,北齐镇远将军;生俭,永昌王咨议。俭生华,隋东都丞。华生士稜、士让、士逸、士彟。[6](822−883)
其中“汉又有祭酒武忠望出太原”十一字乃洪莹据《氏族志》增补,未必是《姓纂》原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文简称《新表》)则载作:
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汉有武臣,为赵王。梁邹孝侯臣,生徳。生东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婴。婴生中涓、济阴侯山附,后以酎金国除。山附生陈留太守、内黄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宣,字文达。宣二子:尚、浮。浮字符海,司徒、左长史。生临漳令静,字伯济。静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禄勳笃,字猗伯。笃生太常、中垒校尉悌,字周笃。悌生九江太守、临颍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7](3136)
自武臣以下即与《姓纂》不同:首先是梁邹(孝)侯之名,《姓纂》作“彪”而《新表》作“臣”,岑仲勉《四校记》以为“言‘臣’者避唐讳也”[6](882)。《新表》编于北宋,无由避唐帝之讳,当是承袭了武氏谱牒之讳字,由此可知邹侯之名当作“虎”,《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即载作“虎”[8]可以为证,《姓纂》作“彪”当为误。②其次武虎至武周世次,《新表》记载详尽,而《姓纂》则削去其间各代,仅著“武彪裔孙周”五字。
武周至武华,《新表》亦与《姓纂》有较大差别,《新表》云:
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周三子:陔、韶、茂。陔字符夏,晋左仆射、薛定侯。陔生太山太守、嗣薛侯越。越生威远将军、嗣薛侯铺。铺生太子洗马嘏。嘏生洛州长史、归义侯念。念生平北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洽,别封大陵县,赐田五十顷,因居之。生祭酒神龟。龟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袭寿阳公克己。己生北齐镇远将军、袭寿阳公居常。常生后周永昌王咨议参军俭。生华。[7](3136)
主要差异有以下三点:其一,《新表》所载世次较《姓纂》为详,陔至洽、洽至居常间诸代,后者均削而不着。其二,武洽封地称名不同,《姓纂》载封于“永水”③而《新表》则作“大陵县”。“永水”为唐时称名,汉代则称“大陵”,《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魏恵王卒十六年肃侯游大陵”。《正义》引《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县北十三里,汉大陵县城。”(《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正义》引《括地志》同[9])《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河南道三》载:“文水县……本汉大陵县地。”可以为证。[10]是“永水”“大陵”并不矛盾,《新表》盖以汉时名称之。其三,诸人官职封爵互有详略,如洽、居常等,不备举。
至于这些差异的性质,则当是二书原本记载之歧,《古今姓氏书辩证》(下文简称《辩证》)可以为证,云:
汉有武臣,为赵王。梁邹孝侯臣生德。德生东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婴。婴生中涓济阴侯山附,后以酎金国除。山附生陈留太守、内黄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宣,字文达。宣二子:尚、浮。浮字符海,司徒左长史。生临漳令静,字伯济。静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禄勋笃,字猗伯,生太常、中垒校尉悌。悌生九江太守、临颍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周三子:陔、韶、茂。陔字符夏,晋左仆射,薛定侯。陔生太山太守、嗣薛侯越。越生威远将军、嗣薛侯铺。铺生太子洗马嘏。嘏生洛州长史、归义侯念。念生平北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洽,别封大陵县,赐田五十顷,因居之。生祭酒神龟。神龟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袭寿阳公克己。
沛国武彪裔孙周,魏南昌侯,生陔,晋左仆射薛侯。五代孙洽,魏晋阳公,因始封居太原永水,或号太原武氏。洽曾孙居常,北齐镇远将军,生俭,永昌王咨议。生华,隋东都丞。生士稜、士让、士逸、士彟。[11](350)
对比前引《姓纂》及《新表》,可见《辩证》前段与《新表》几乎完全相同,后段则与《姓纂》无大差异④,《辩证》当径抄自二书。同时,《辩证》前段所载周、陔、洽等人在后段再次出现,明显重复,当是邓名世径抄而未细审之故。
读武华以前世系可知,《姓纂》与《新表》间存在较大差异,其间没有直接的史源关系,而《古今姓氏书辩证》则恰好保存了这些差异。
二、武华以下世系
武华以下世系,《姓纂》与《新表》亦多有差异,却与《辩证》大体相同。除个别叙述之差别,及某一方可能存在文字脱误外,《姓纂》与《辩证》间有明显不同者五处。
第一,《姓纂》载信官“秘书监”[6](885−886),《辩证》作“秘书监同攸止”[11](351)。“秘书监同攸止”无义,疑为“秘书监同正”之误,《新表》即作“秘书监同正”[7](3138)可为其证。今本《辩证》“止”当是“正”之坏字,传刻者不明其意,于“止”上臆补“攸”字。至于《姓纂》作“秘书监”,极有可能为“秘书监同正”之误脱。如此则《姓纂》《新表》《辩证》所载并同。
第二,《姓纂》载士逸官“韶州刺史”[6](886),《辩证》作“始州刺史”(《新表》同)[11](351),当均不误。罗振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云:“《新书·士彟传》:士逸,字逖。官终韶州刺史,封六安县公。《旧书》亦作韶州刺史。均不作始州。”(由此可见《新唐书·武士彟传》当本自《旧唐书·武士彟传》)[12](704)据两《传》,韶刺是终官,士逸曾为益州行台左丞,始州恰属剑南道,益州为治所,是其或曾刺始州,《新表》当有所据,《辩证》则据《新表》而改。
第三,《姓纂》载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6](887),《辩证》作“神丘道大管公”[11](351)。《辩证》误。首先,《辩证》“丘”当系“兵”字之误,《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懿宗传》即载作“神兵道大总管”[7](5842),此亦见于《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四》《新唐书·契丹传·卷二一九》《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册府元龟·卷四五三·将帅部·怯懦》《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第五·卷九八六》,均可证。其次,《辩证》“大管公”不词,其文作:“懿宗,河内王、殿中监、汴魏州刺史、神丘道大管公,生瑾、瓌。”[11](351)据《新表》,懿宗子为震、益,嗣宗子为璍、瓌,嗣宗爵又为管公,则《辩证》冒嗣宗子为懿宗子,因疑其“大”字下脱去“总管生震殿中监益试太子中允嗣宗浦州刺史”一段;而今本《姓纂》此段全同《辩证》,唯“大管公”作“大总管”,颇疑其宋本即作“大管公”,今作“大总管”系馆臣见其不词而臆改。如此则《辩证》同《姓纂》。
第四,《姓纂》载延安爵“邢公”[6](890),《辩证》作“邗公”[11](351)。唐代罕见邗国之封,两《唐书》未见载,“邗”当为“邢”字之坏。
第五,《姓纂》载延晖“驸马、陈公、羽林卫将军,孙恽、斌”[6](890),《辩证》作“驸马、陈公、生羽林卫将军,生恽、斌”[11](351),当系邓氏见《新表》亦未载延晖子,而延晖为羽林卫将军又无⑤[13],故认为《姓纂》“羽林卫将军”当属延晖之子,遂补“生”字于前,又改“孙”作“生”。⑥
以上第一、三、四条,《辩证》或《姓纂》均存在互讹的痕迹,因此《辩证》原本当与《姓纂》相同。第二、五条,虽无明显致误之迹,但亦可解释为邓氏有意之改动。故《辩证》武氏华以下世系当抄自宋本《姓纂》。至此,联系上节所引《辩证》两段,明显可见其史料之来源:自首至“神龟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袭寿阳公克己”盖源自《新表》,而“沛国武彪裔孙周”以下至末则全抄自《姓纂》。
三、武华以下人物世次
武华以下世系《姓纂》虽多同《辩证》,却与《新表》有较大差异,首先即在于人物世次。除去今本《姓纂》或《新表》可能有文字脱误外(详见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不备列),其主要差异有以下六处。
第一,《新表》载怀运孙胜及其子、孙辈,不见于《姓纂》。若《新表》源于《姓纂》,则或今本《姓纂》脱去“怀运孙胜……”一段,或吕夏卿据其他史料有所增补。考符载《武充志》:“左右仆射、司徒、太尉、尚书令、楚僖王士让之玄孙,九江王弘度之曾孙,纳言、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定王攸暨之孙,尚书膳部员外郎、徐州刺史胜之子……嗣子曰异曰典……从子沇。”[3](5004−5005)《新表》未载胜、充之官,且充子亦与《志》不合,可知吕氏非据此而补。
第二,攸止子之名,《新表》作“昕忠”“信忠”而《姓纂》作“昕”“忠”“信”。《四校记》曰:
劳格《英华辨正补》云:“《世系表》,武昕忠,鸿胪卿,《元和姓纂》同,昕当是忠兄,《表》误合一人,《姓纂》单作忠。”按《姓纂》云“昕忠信”亦可分作三人读,今鸿胪卿之上单作忠,如劳说,昕别为一人,则《姓纂》固与《新表》异,不得谓之同,同者只鸿胪卿耳。至《英华》三九七孙逖《授武三思鸿胪卿制》,劳氏谓“思”当作“忠”,“三”字衍,引《旧·后妃传》为证,⑦其说可信。[6](886)
岑考有据,张说《郑国夫人神道碑》载:“郑夫人者,弘农杨氏之女也……夫人言归武氏,曰恒安郡王,生恵妃及家令忠、仆信。”[14]亦可为证,然此说尚有三点可疑。首先,今本《姓纂》版刻不善,脱误极多,颇疑《姓纂》“鸿胪卿”上脱一“昕”字,作:“攸止子昕忠、信忠。昕,鸿胪卿。信,秘书监(同正)。”后称“昕”“信”乃承上文而省,如此则《姓纂》《新表》所载相同。其次,三子之说唯见《岑校》,武昕诸书均未见,《姓纂》亦未载昕官爵,《旧传》《新传》《新表》均记二子,且张说《神道碑》亦作二子,名忠、信同《旧传》,唐人有复名单称之例,是二子之名当时或即省称作忠、信,唯官职不同。再次,《全唐文·卷九六二》载《制》同《英华》,编纂者云:“谨案此制《文苑英华》误为孙逖作,考逖知制诰在开元二十四年,时武三思久被诛,且《新唐书》《旧唐书》亦不载三思官鸿胪卿,题与撰人必有一误。今存疑编入阙名。”[15]所考甚是。至于《英华》制题之误,当非衍一字误一字,而是“忠”先误“思”,传抄者见武昕思并无此人,因臆改作“武三思”。是《新表》当不误,今本《姓纂》脱一字耳。
第三,《新表》载温眘,为怀运孙、攸望子,不见于《姓纂》,《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四年四月)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眘,坐交通权贵,杖死。”[16](6817)可知确系攸望之子。若《新表》源自《姓纂》,则或今本《姓纂》脱去“攸望子温眘”云云,或吕夏卿据《通鉴》增补。
第四,《新表》载有元衡子翊黄、儒衡子筹、忱三人,不见于《姓纂》,虽亦容为今本脱文,然三人同辈,均为元和后人。⑧[17]《姓纂》原本未必见载,若《新表》源自《姓纂》,必据他书而补。
第五,《姓纂》承嗣子无延义、延安二人,容系今本有脱文。
第六,君雅二子之名,《姓纂》作“敬真”“崇真”[6](883),《新表》作“敬真”“敬宗”[7](3136),赵超考云:
《武希玄墓志》云:“字敬道……祖稜,唐司农卿、宣城县开国公赠潭州都督。父雅,右卫铠曹参军、轻车都尉,袭宣城公。”志中所言稜,即士稜;雅,即君雅。希玄为《新表》失载。据希玄字敬道,可知君雅诸子以敬字排行,故《新表》作敬真、敬宗较《姓纂》作敬真、崇真可靠。[12](698−699)
由是,《新表》不误,《姓纂》当系字误。
至于造成以上六处差异的原因,或是今本《姓纂》文字有脱误,或吕夏卿据他书有所增补。故从世次上看,《姓纂》与《新表》间不存在绝对的矛盾。
四、武华以下人物官职爵位
《姓纂》与《新表》所载武华以下诸人世次基本相同,然官职与封爵则有较大差异,见下表1。⑨
我们将二书记载之差异分作三类。
一是C类,共六例,为《姓纂》或《新表》某方可能存在文字讹误。
(1)怀道官,“左”“右”二字形近易互讹。
(2)信忠官,《姓纂》或脱“同正”二字,然若其原本即作“秘书监”,则《新表》作“秘书监同正”必是其史源如此,绝不可能在抄撮《姓纂》的基础之上反据他书将“秘书监”正式官衔改作编制外之同正员。
(3)懿宗爵,罗振玉《补正》云:“两《书·承嗣传》⑪及《姓纂》并作懿宗,河内王。《大云寺圣祚碑》同。均不作‘河间’。”[12](704)赵超亦云:“懿宗,《旧唐书》卷一八三本传云:‘封耿国公,累转怀州刺史。’《新表》不应称河间王,西安出土景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唐故怀州刺史赠特进耿国公武(懿宗)府君墓志》可证,《志》中亦云懿宗曾封河内郡王,后降为公。”[12](707)懿宗为河内王又见于《陈伯玉集·卷四·为河内王等论军功表》《通典·卷二〇〇》《太平广记》《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又据《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承嗣传》,武后秉政初封武氏诸王,懿宗与仁范同时所封,仁范即爵河间王,可证懿宗爵非河间王。《新表》当误“内”为“间”。

表1 《姓纂》与《新表》所载武华以下诸人官职与封爵差异对比表
(4)尚宾官,《姓纂》“益府”二字间或脱“王”字。然《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三》同《姓纂》作“益府”[1](351),则其原本或即作“益府”。某州都督府常简称作“某府”,而某王府则甚少简称作“某府”,则《姓纂》“益府”当是“益州府”简称,益州府长史与《新表》益王府长史显然是不同的官职。同时,《新表》作“益王府长史”当误:检两《唐书》,益王最早见于记载者乃代宗第九子,大历四年(769年)封,尚宾则武后、中宗时人,若曾官益王府长史,其人至大历间当年逾百岁,堪任此官乎?是知《新表》非源自《姓纂》。
(5)元爽官,《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承嗣传·卷七六》《则天皇后传》均载武后掌权封诸武,其时元爽官少府少监,同《姓纂》,则《新表》当脱“少”字。
(6)承业官,《世系表》或脱“左”字,或泛称作此。
其中(1)(3)(5)三条当可确定乃今本《姓纂》或《世系表》文字有误,其原本之记载当无差别;(2)(4)(6)三条虽存在二书原本不同之可能,但并无明确之书证,故暂付阙疑。
二是B类,共七例,《姓纂》与《新表》完全不同。
(1)士让爵,“路公”与“楚僖王”间无互讹之迹,《四校记》引符载《武充志》:“左右仆射、司徒、太尉、尚书令、楚僖王士让之玄孙。”[6](884)同《新表》,“路公”当为初封,后改封或追封为“楚僖王”。
(2)惟良官,“卫尉少卿”与“始州刺史”间无互讹之迹。据《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承嗣传》《通鉴·卷二○一·唐纪十七》,武曌为后,惟良由始州长史超迁卫尉少卿,后贬始州刺史,寻被杀,是始刺为其终官。
(3)怀运官,“淄”“魏”间无互讹之迹,怀运为淄州刺史见《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〇六·武承嗣传》《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通鉴》又载:“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16](6349)是其又曾官瀛州长史。淄州属河南道,而瀛州、魏州均属河北道,《新表》载魏州刺史当有所据,唯今不可考。魏州(雄)级别高于淄州(上),按唐代士人官职迁转之一般顺序,其刺魏当在淄之后。
(4)士逸官,“始”“韶”间无互讹之迹,《姓纂》《新表》则各有所据。⑫
(5)士逸爵,“六安县公”与“酂国节公”间无互讹之迹,当各有依据,权德舆《武就碑》载:“太原生酂国节公讳士逸。”[1](265)《文苑英华·卷八七五·攀龙台碑》载:“是日封帝……次兄行台左丞相士逸为六安郡公。”[3](4617)可证。封于六安,《英华》作“郡公”(《全唐文·卷二四九·攀龙台碑》作“安陆郡公”,虽改“六安”为“安陆”,然作“郡公”同)误,《姓纂》作“县公”是,据《旧唐书·卷五八》《新唐书·卷二〇六·武士逸传》,六安(安陆)县公系武德初以战功而封。⑬
(6)儒衡官。“殿中御史”与“中书舍人”间无互讹之迹,当均不误。《旧唐书·卷一五八》《新唐书·卷一五二·武儒衡传》均载其为中书舍人,《四校记》则云:“《全文》六三九李翱《武儒衡志》,郑余庆守东都,得监察御史,转殿中御史,此其见官也……”[6](889)可证。殿中(侍)御史武德初正八品上、垂拱改为从七品上,中书舍人则正五品上,后者为唐代中央位于枢纽地位的重要文官,故中舍之任当在殿中御史之后。⑭[18]
(7)延秀爵,虽“恒”“桓”二字形近有互讹痕迹,然均不误。《四校记》曰:“按《旧书》一八三,先作栢国公,后作恒国公,《新书》二○六作栢国公。”[6](891)今按,《旧传》载先封桓后改封恒,《新传》载先封栢后改封恒,两《传》所载初封及改封时间相同,又《姓纂》与《辩证》均作“桓”,可知《新传》“栢”当是“桓”字误,《姓纂》载初封而《新表》载后封。
以上七例,由于《姓纂》与《新表》文字间无互讹之迹,且均有直接或间接史料可以为之证明,故二书记载当并不误。只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新表》承袭了《姓纂》以外史源文献的记载,还是其在以《姓纂》为骨干的基础上参考他书有所修改,尚难以断定。就两书所载官、爵之授予时间与品级高低来看:

名 官爵 先后高低士让 《新表》 楚僖王 后 高《姓纂》 路公 先 低惟良 《新表》 始州刺史 后 高《姓纂》 卫尉少卿 先 低怀运 《新表》 魏州刺史 后 高《姓纂》 淄州刺史 先 低士逸 《新表》 始州刺史 先 高《姓纂》 韶州刺史 后 低士逸 《新表》 酂国节公 后 高《姓纂》 六安县公 先 低儒衡 《新表》 中书舍人 后 高《姓纂》 殿中御史 先 低延秀 《新表》 恒公 后 −《姓纂》 桓公 先 −
《新表》所载并非全为终官(如士逸),但品级均高于《姓纂》,故若以《姓纂》为《新表》之直接史源,则造成此七处差异的原因当取后一说。然而,这一推论其实并不成立,我们在分析A类诸例后将对此作出解释。
A类为《姓纂》与《新表》所载详略有别者,又分为两类:A1为《新表》详者,A2为《新表》略者。A1共九例:
(1)惟良爵,《姓纂》未载。
(2)怀运爵,《姓纂》未载,《武充志》云:“九江王弘度之曾孙。”[3](5004)是《新表》所载有据。
(3)志元官,《新表》较《姓纂》多库中。仓中见郎官石柱题名[19],又《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懿宗传》载:“父元忠,高宗时仕至仓部郎中。”[20](4737)仓部司属户部(中行)、库部司属兵部(前行),元忠既曾官仓中,其当有进(或赠)库中之可能,惜今不可考。
(4)仁范爵,《姓纂》未载,《武就碑》《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均作“河间郡王”。[1](265)[7](5838)
(5)载德谥,《姓纂》未载,《武就碑》《新承嗣传》均见载。
(6)平一官,修文馆直学士《姓纂》未载,见于《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武就碑》《佛祖统纪·卷四○》《佛祖统纪·五三》则作“修文馆(殿)学士”[1](265)[21],或为泛称,或曾由直学士进为学士。
(7)求已官,《四校记》曰:“《新表》误‘太子仆少卿’,太子仆不名卿也。”[6](889)是,然《新表》亦未必误,吕夏卿谙习唐史,非不知“太子仆少卿”不词者。若以《新表》原本同《姓纂》作“太仆少卿”,其流传过程中又不至无端衍出一“子”字。窃以《新表》原本作“太子仆太仆少卿”(太子仆从四品上,太仆少卿亦从四品上),流传中涉两“仆”字而脱“仆太”(或“太仆”)二字,如此则《新表》所载较《姓纂》多太子仆一官,惜无确证。
(8)崇训爵,《姓纂》未载,见于《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后降爵为酆国公。
(9)崇烈爵,《姓纂》未载,见于《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
以上九例,《新表》所载较《姓纂》为详,若以后者即前者史源,则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今本《姓纂》有脱文,其二则是吕夏卿据他书增补。若取前一说,则《姓纂》脱误岂非太甚,且并无其他史料可以为之证明。取后一说,则《新表》较《姓纂》多出者:惟良爵今无考;平一《新表》既已载品级较高之考功员外,又缘何而增修文馆直学士?故就此九例而言,尤其第(1)(6)两例,以《姓纂》为《新表》史源之结论尚有疑问。
A2类15例:
(1)攸宜官,雍州刺史《新表》未载,工部(冬官)尚书又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为其终官。
(2)崇敏官,《四校记》以为《新表》“字正卿”为“宗正卿”之误[6](885),如此则同《姓纂》。然并无明确史料可证崇敏之字非正卿,未可遽言《新表》有误。
(3)崇敏爵,《新表》未载。
(4)崇行官,《新表》未载。又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
(5)攸归官,《新表》未载。
(6)攸望爵,会稽王《新表》未载,仅载蔡公,《四校记》曰:“余按《旧书》一八三作‘邺国’,《新书》二〇六作‘叶国’。”⑮[6](886)《文苑英华·卷八九八·故吏部侍郎元公碑》又作“鄎国公”[3](4726),彭叔夏《辨证》云:“《唐书》攸望封叶国公,攸宜封息国公。”[3](5270)“邺(叶)”“察(蔡)”二字间不易致误,是攸望当曾改封。至于“察”“蔡”二字则未知孰是。
(7)懿宗官,《新表》未载。汴州刺史、魏州刺史今不可考,殿中监见《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诬誷》,神兵道大总管见《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卷二○六《武懿宗传》、卷二一九《契丹传》、《通鉴》卷二○六《唐纪二十二》、《唐会要》卷四一《酷吏》、《册府元龟》卷四五三《将帅部·怯懦》、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
(8)重规官,司礼卿、神龙朔方大总管《新表》未载。司礼卿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册府元龟·卷三○一·外戚部·封拜》,《文苑英华·卷五七七·为司礼武卿让官表》,武卿即重规;《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载:“则天令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20](5169)(《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十四》《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六·四夷二十五·北狄八》《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通鉴·卷二○六·唐纪二十二》《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并同之)当即《姓纂》所谓朔方大总管。
(9)载德官,殿中监《新表》未载。
(10)士彟官,利州、荆州都督《新表》未载。士彟为利州都督见《谭宾録·卷八》《大唐新语·卷一三·记异》《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唐会要·卷七·封禅》《册府元龟·卷三五·帝王部·封禅》《册府元龟·卷八六○·总录部·相术》,为其贞观初所官;荆州都督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新唐书·卷一九一·李彭传》《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唐会要·卷四五·功臣》《唐会要·卷七九·谥法上》《册府元龟·卷三○三·外戚部·褒宠》《册府元龟·卷六八一·牧守部·感瑞》,为其卒后赠官。至于工部尚书则为其武德中所官。⑯[22]
(11)崇训官,太常卿、太子宾客《新表》未载,见《旧唐书·卷八六》《新唐书·卷八一·节愍太子重俊传》《新唐书·卷八三·中宗女安乐公主传》《新唐书·卷二○六·武三思传》《册府元龟·卷四六九·台省部·封驳》《册府元龟·卷七○八·宫臣部·总序》《册府元龟·卷七一五·宫臣部·昵狎》,其神龙中由太常卿擢驸马都尉、太子宾客。
(12)延基官,驸马都尉《新表》未载。
(13)延秀官,《新表》未载。《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载:“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改封恒国公,实封五百户。”[20](4734)则天令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据《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事在景龙二年十一月。驸马都尉《姓纂》《新表》均未载。
(14)承业爵,《新表》未载,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其卒后赠陈王。
(15)延晖官,《新表》未载。
除第(2)条存疑外,余十四例,崇敏、崇行、攸归、懿宗、延秀、承业、延晖七人之官或爵《新表》均为空白,若其乃抄自《姓纂》,则无论《姓纂》所载是否终官,或品级高者,《新表》必著而存之,不会削而不著;崇训、延基同为驸马,崇训由太常卿授驸马都尉、太子宾客,《新表》仅载驸马,前官太常卿及与驸马同时之宾客均不载,延基为驸马右羽林将军,《新表》却载将军而不载驸马,果其源自《姓纂》,无由崇训仅载驸马、延基又不载驸马;攸宜、攸望、重规、载德、士彟五人,如以《新表》源自《姓纂》,则其于《姓纂》所载诸官职爵位,必当有统一之选择标准:从攸宜官雍州刺史(从二品)、冬官尚书(正三品)《新表》载后者可见非取品级高者,从士彟载工部尚书不载荆州都督可见又非最终授者。故由A2十四例可证《新表》之史源绝非《姓纂》,由此亦可证明A1类及B类《新表》源于《姓纂》之推测不能成立:A1类《新表》源自《姓纂》之条件为吕夏卿据他书增补各人官、爵,B类则为吕氏据他书改为品级更高者,其分别与A2类崇敏等七人官或爵《新表》空白,攸宜等五人官、爵《新表》于《姓纂》所载无统一选择标准之实际情况矛盾。对比武华以下世系可知,《辩证》之记载当源自《姓纂》,而《新表》与《姓纂》间则不存在直接之史料源流关系。即使《姓纂》《新表》原本所载各人世次可能完全相同,但在人物之官职及爵位方面却有诸多不同,并且这些差异绝非流传中致误,或吕夏卿有意改动所致。
五、结论
岑仲勉先生在《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一文中首次系统论述了《新唐书》两《世系表》的史源问题⑰[6](62−94),依据北宋时期唐代谱牒的存世情况以及两《世系表》与《元和姓纂》记载唐人世系高度一致两个证据,得出《世系表》大部本自《姓纂》——即以后者为前者主要史源这一结论。这里所谓主要史源,并不是说《姓纂》是《世系表》的史源之一,岑先生认为《世系表》是在以《姓纂》的记载为基本骨干的基础上、少量参考史传碑志为之修订而成,即《世系表》几乎完全移录了《元和姓纂》的记载。然而具体到武氏一支,虽然《姓纂》与《新表》对武华以下各人世次的记载大体相同,然而在武氏早期传衍,及武华以下各人职官、封爵等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可以证明,就武氏世系而言,《姓纂》为《新表》主要史源的观点不能成立。
其实,王力平教授已对岑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依据《新表》与《姓纂》在杜氏襄阳望的归属及郑氏荥阳房下房支记载的差异,认为至少就这两支世系而言,《新表》的史源应该不是《姓纂》。[23]其实,不仅杜氏襄阳望、郑氏荥阳房及武氏全支,我们比读《姓纂》《新表》所载其他姓氏之世系可以发现,虽然二书在某些方面的记载可能完全相同,但这并不能作为证明其间存在史源关系的有力证据,因为从某支世系的整体来看,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并且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明显不是某一方文字有误,或吕夏卿据他书有所增减改动。因此,以为《新表》之大部源自《姓纂》的结论不能成立。
《姓纂》与《新表》所载唐代武氏之世次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今本《姓纂》可能存在较多脱文,因此《新表》的记载相对更加完整;在人物官职及封爵方面,《姓纂》与《新表》间虽多见不同,但各有其史料来源,故均不误,其记载可互为补充。
注释:
① 据《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为武攸暨、武攸宁、武元衡、武三思、武承嗣。
② 《姓纂》作“彪”当系原本如此,否则必讳“虎”而改作他字。
③ 《四校记》考证云:“《攀龙台碑》:‘大周无上孝明皇帝……太原文水人也。……六代祖洽仕魏,封于晋阳,食采文水,子孙因家焉。’《旧书》五八《士彟传》:‘并州文水人也。’‘永水’当作‘文水’。”是。
④ 《辩证》与《新表》不同者:《表》“生太常”上有“笃”字,“中垒校尉悌”下有“字周笃”三字,无“神龟生本州大中正”之“神”字;与《姓纂》不同者:《姓纂》无“因始封居”之“因”字,“生华”上有“俭”字,“生士稜”上有“华”字。
⑤ 《加嗣陈王实封制》载“云麾将军行太子左鹤禁率嗣陈王延晖”,无“羽林卫将军”,他书亦不见载。
⑥ 钱熙祚按云“生”字疑衍,王力平云“生”字未必为衍文,是,惜未深考。
⑦ 《旧唐书》卷五一《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云:“同母弟忠,累迁国子祭酒;信,秘书监。”《新传》(卷七六)同。忠为国子祭酒,《姓纂》作鸿胪卿,均见于逖《制》,益信劳氏“武三思”系“武忠”误之说。
⑧ 《金石录》卷九《唐张諴碑》注云:“白居易撰,武翊黄正书,侄孙磻篆。长庆二年六月。”
⑨ 《新表》宰相例载作“某相某宗”,无具体官职、封爵,故不列入表中。
⑩ 当为“卫尉少卿”之脱误,《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卷一八三《武承嗣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卷二〇六《武承嗣传》、《通鉴》卷二○一《唐纪十七》均作“卫(司)尉少卿”,诸书无作“卫尉卿”者,可证。
⑪懿宗为河内王亦见两《唐书》他卷,不备引。
⑫考证见论文第二节。
⑬《旧传》作“安陆县公”,《新传》则作“六安县公”,或宋祁改“安陆”为“六安”;或《旧传》原本作“六安”,而今本作“安陆”则系传抄者因唐无六安郡、又不明唐人实多以古地名为封而改,《文苑英华辩证》卷三即云:“当从二《唐书》作‘安陆县公’。《唐志》安州安陆郡安陆县,无六安郡。”(见《文苑英华》页5269~5270)唯彭氏云两《唐书》均作“安陆县 公”,未知所据何本。
⑭据孙国栋统计,初唐有三例由殿中御史迁中书舍人,分别是陆元方、陆余庆和萧嵩,反之则无。
⑮据《旧传》,邺国公之封在会稽郡王之后。
⑯《册府元龟》卷四六四《台省部·谦退第二》载:“唐武士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赐实封八百户。”
⑰《再序》首论两《世系表》的史源,再论郑樵《通志·氏族略》多本自《元和姓纂》,后又附《跋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及《杂论姓氏书数条》两短文。
[1] 权德舆. 权德舆诗文集[M]. 郭广伟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 周绍良, 趙超. 唐代墓志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31.
[3] 李昉等.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 李翱. 李文公集·卷一五[M]. 四部丛刊初编本.
[5] 周绍良, 趙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416−417.
[6] 林宝撰. 元和姓纂[M]. 岑仲勉校记.郁贤皓, 陶敏整理. 孙望审订.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7] 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550.
[9] 司马迁. 史记[M].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2160、3333.
[10]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贺次君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71.
[11] 邓名世. 古今姓氏书辩证[M]. 王力平点校.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12] 赵超.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3]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74.
[14] 张说. 张说之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15] 董诰等.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4429.
[1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胡三省音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7] 赵明诚. 金石录校证[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67.
[18] 孙国栋. 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45−358.
[19] 劳格, 赵钺.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M]. 徐敏霞, 王桂珍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779.
[20]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1] 释志磐. 佛祖统纪[M].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22] 王钦若等. 冊府元龟(校订本)[M]. 周勋初等校订.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5244.
[23] 王力平. 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344−347.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Wu’s lineage in Tang Dynasty
LI Yilun
(Ancient Book Section,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Wu’s lineage in Tang Dynasty was recorded in three books:Compilation of Surnames in Yuan-he Age,Table ofPrime Ministers’ Lineage of New Book of Tang Dynasty, andDiscrim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Surnames. The records of these three book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ough with similarities. Mr. Cen Zhongmian believes that the record ofTable ofPrime Ministers’Lineage of New Book of Tang Dynastyis mainly fromCompilation of Surnames in Yuan-he Age. However, we insist that there is no direct orig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ord of Wu’s lineage of these two books. They both have respective sources of historical fact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s forDiscrim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Surnames, its record is copied fromCompilation of Surnames in Yuan-he AgeandTable of Prime Ministers’ Lineage of New Book of Tang Dynasty, especially from the former.
Wu’s lineage;Compilation of Surnames in Yuan-he Age;Table ofPrime Ministers’Lineage of New Book of Tang Dynasty;Discrim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Surnames; sources of historical facts
K242
A
1672-3104(2015)04−0216−09
[编辑:颜关明]
2014−07−08;
2015−06−18
李轶伦(1985−),男,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校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