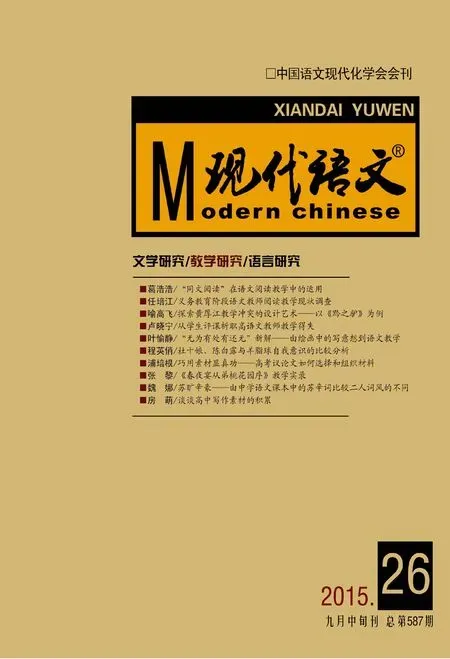略谈余光中的散文观
◎吴永福
略谈余光中的散文观
◎吴永福
关于散文,余光中颇有知见。他在《日不落家》后记中说:“五四以来,不少人认定散文就是小品文。其实散文的文体可以变化多端,不必限于轻工业的小品杂文。我一向认为小品也好,长篇也好,各有胜境,有志于散文艺术的作家,轻工业与重工业不妨全面经营。”此种区分着眼于篇幅的短与长,对应于内容的轻与重。而在《不老的缪斯》中说:“散文分狭义与广义二类。狭义的散文指个人抒情志感的小品文,篇幅较短,取材较狭,份量较轻。广义的散文天地宏阔,凡韵文不到之处,都是它的领土,论其题材则又千汇万状,不胜枚举。”这里的广狭之分,包括体裁及取材。除此之外,还有质素方面的区分。余光中在《美文与杂文》中说:“习见的散文选集所收的,几乎尽是抒情写景之类的美文小品,一来读者众多,可保销路;二来体例单纯,便于编辑。其中当然也有不少足以传世的佳作,可是搜罗的范围既限于‘纯散文’,就不免错过了广义散文的隽品。长此以往,只怕我们的散文会走上美文的窄路,而一般读者对散文的看法也有失通达。”美文的说法,多指抒情写景之类的小品。不过,作者又进一步作了界定。“所谓美文,是指不带实用目的专供直觉观赏的作品。反之,带有实用目的之写作,例如新闻公文论述之类,或可笼统称为杂文。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由作家来写。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不过两者并非截然可分,因为杂文写好了,可以当美文来欣赏,而美文也往往为实用目的而作。”在这里,杂文是作为与美文相对的概念提出来的,但区分的标准并不绝对。其实美文杂文都可以是散文,“把散文限制在美文里,是散文的窄化而非纯化。”
众多文体的并举中,诗与文的比较甚多。余光中在《缪斯的左右手》中说:“诗和散文,同为表情达意的两大文体,但诗凭想象、较具感情的价值,散文依据常识、较具实用的功能。”散文不离人生日常,正是基于生活的提炼。“散文是一切文体之根:小说、戏剧、批评甚至哲学、历史等等,都脱离不了散文。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和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韵;它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文体之根,换个说法就是有其母体之义。不仅可催生出许多子文体,其本身也是一体,一种很弹性的文体。余光中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自序中说:“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诗与文可互相借鉴,但又各有规范。把散文当成诗来写,或把诗写成散文,都是在借鉴中忘了本身的规范,其实就是过头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自序中还说:“大致说来,散文着重清明的知性,诗着重活泼的感性。”对于散文创作中的知性,作者甚为强调。他在《左手的缪斯》新版序中说:“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只是一堆现象,很容易落入滥感。”光写感性经验,是比较浅的,任其泛滥开去,就很疲软了。换言之,就是需要知性来作脊梁。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这样说:“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为‘理趣’。”知性并非纯理性的,尽是概念的抽象演绎,而是一种智慧的观照,这样才能与感性交融。“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能兼顾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有心肠,才有观感的印象或事实;而有头脑,才有见解或看法。
余光中在《四窟小记》中说:“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性,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与窄化。”就余光中自己的写作来说,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他在《四窟小记》中说:“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于此可见,作者的写作方向是多元的。又说:“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此种交错,表明不同文字中有一种相通的内蕴或节奏。且就散文写作来看,文体也是多样的,有小品、随笔、杂文、书评等。比如小品,余光中在《凭一张地图》后记中说:“《凭一张地图》是我唯一的小品文集。论篇幅,除少数例外,各篇都在两千字以内。论笔法,则有的像是杂文,有的像是抒情文,但谓之杂文,议论不够纵横,而谓之抒情文,感触又不够恣肆,大抵点到为止,不外乎小品的格局。”这里所说的小品写作,包括了字数及写法等。但余光中的散文写作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一种自传性的抒情散文,即略带自传而写实,更多的是恣于自剖而写意,其代表性的篇章有《听听那冷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在这些散文中,作者既写了自己的经历及观感,又有历史文化方面的依托,这正是感性与知性的结合。再就是虽不乏现实的感慨,又颇多诗情诗意的飞扬。笔锋所向,真可谓汪洋恣肆。
此种兼容渗透落实到语言层面,语言也就得有变化。余光中在《消遥游》后记中说:“在《消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的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这是写作中甚为自觉的尝试,而在理论上又概括为“现代散文应该在文字的弹性、密度,和质料上多下功夫;在节奏的进行上,应该更着意速度的控制,使轻重疾徐的变化更形突出”。(《六千个日子》)对于散文语言的论说,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还作了专题阐述。他在文中先举出散文写作中的三种弊端,即伪学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妇的散文。显然,这三种类型都可以在现当代散文中找到对应。作为补救之道,余光中提出了第四类的散文,那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散文,一种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这里所说的,包括了语体和文体。“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这讲的是内容的含量,反对汤汤水水或稀稀松松的内容。“所谓‘质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这如同前人所说的诗眼,即使在一篇散文中也很重要,由此可以见出作者对于语词的敏感。弹性、密度和质料虽各有侧重,又互相关联,且主要就是语言表达问题。举其大者,不妨说余光中着重强调的就是语言表达的弹性。而语言表达的弹性,自是为了适应于内容及表现方面的弹性。
余光中在《不老的缪斯》中说:“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散文家只凭自己的本色,这话说得真好。而在《焚鹤人》后记中又说:“任何文体,皆因新作品的不断出现和新手法的不断试验,而不断修正其定义,初无一成不变的条文可循。与其要我写得像散文或是像小说,还不如让我写得像——自己。”散文不管写什么及怎么写,最关键的是要能写出自己,这是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说到:“在所有文体之中,散文受外来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原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力所在,并且有哲人与史家推波助澜;……和诗小说戏剧等文体相比,散文的技巧似乎单纯多了,所以更要靠文字本身,也更易看出‘风格即人格’。”散文写作靠文字,靠为文之人的本色。古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余光中也作了新的阐释。他在《为人作序》中说:“我不认为‘文如其人’的‘人’仅指作者的体态谈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仅指此,则不少作者其实‘文非其人’。所谓‘人’,更应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此一‘另已’甚或‘真已’往往和外在的‘貌已’大异其趣,甚或相反。其实以作家而言,其人真的已是他内心渴望扮演的角色: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每受压抑,但是在想象中,亦即作品中却得以体现,成为一位作家的‘艺术人格’。”这种艺术人格的提出,使其人不会与其人等同起来。散文中的我,应当是内心深处的自“我”。自我介于大我与小我之间。若是大我出场,仍是载道的口吻,充当的是某种代言人的角色。但若尽是小我言说,则过于琐碎,一点细事唠叨不已。散文中的“我”,要在把握上注意分寸,才能表现出自我。
(吴永福 福建省长汀一中 36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