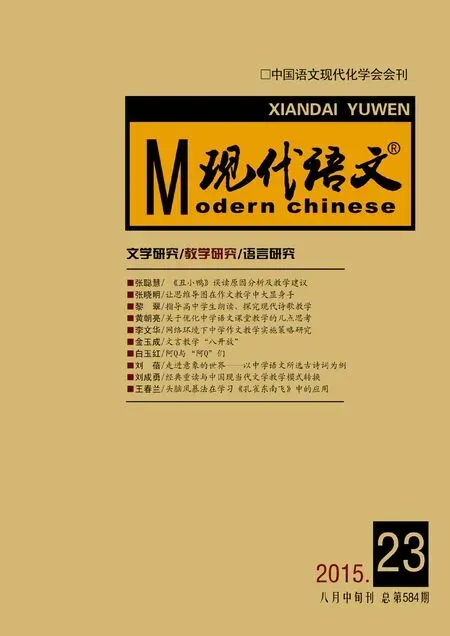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简述悼亡诗词的一般特点
◎程治国
自《诗经·唐风·葛生》和《诗经·邶风·绿衣》始,悼亡这一题材便已见记载,“悼者,哀也”(《广雅释诂》),悼亡,顾名思义,主要抒发对亡者的悼念之情。后西晋的潘岳首先以“悼亡诗”为题,来抒发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后人遂专以“悼亡”指悼念亡妻之作。虽然有许多专家学者对以“悼亡”专指悼念亡妻之作颇存异议,但本文还是以“悼亡”专指悼念亡妻来立论。随着时间的流逝,悼亡诗词层出不穷,名作迭出,蔚为大观,成为古典诗词之林中独特的一株。具有死亡和爱情双重主题的悼亡诗词在内容和艺术特色上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下面试作简要分析:
一、“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诗经·唐风·葛生》)——浓烈的物是人非之孤
虽然逝者已矣,但生者却不能学太上而忘情,尤其逝者是和诗人朝夕与共、琴瑟和鸣相处了若干年的妻子,妻子生前的每一件遗物都会成为一个触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屏筵空有设,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无不勾起诗人对已逝妻子的无限思念,“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诗人想予以回避,可是却又回避不了,于是诗人只能痛苦的陷入思念的泥淖里,而且愈挣扎陷得愈深,终至无法自拔。
遗踪仍在,可燕去楼空;山盟虽在,却锦书难托。往日的温馨、恩爱虽历历在目,可此时“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一切都随着爱人的香消玉殒而不复存在,强烈的物是人非之痛给诗人带来了无边的寂寞之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译文:“角枕灿烂啊,锦缎被子鲜明啊。我的爱人葬身此地,谁来陪伴孤独的白日?”)“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爱人的弃世使诗人陷入了无边的孤独之中。
二、“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贺铸《鹧鸪天》)——浓郁的阴阳两隔之悲
除了睹物思人之外,诗人所能做的也只有到爱人的坟前去寄托哀思了,许多悼亡诗词都写到了“坟”、“垅”、“穴”的意象。“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纡轸。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蹰。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诗人在爱人的坟前久久徘徊,不忍离去,而如果诗人身处他乡,连爱人的坟也不得见,也只能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了。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随着爱人的离去,从此人鬼殊途,阴阳两隔,诗人自然的想起了灵魂的有无,“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然而无情的现实告诉诗人“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诗人与爱人在现实世界里再也无由得见,“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即使“百岁之后,归於其室”,那也只能是一种遥远而美好的期许罢了。
三、“世间无最苦,精爽此销磨”(梅尧臣《悼亡三首》之二)——极度的永失鸳偶之痛
“梧桐半死清霜后,白头鸳鸯失伴飞”,永失鸳偶之痛对诗人的精神打击颇大,“心之忧矣,曷维其亡”、“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诗人的忧思无时能止,并且日积月累,渐成心灵的重负。“垂涕视去景,催心向徂物”,情感的闸门一经触发打开,诗人便情不能自己,内心郁结了许久的愁情便喷薄而出,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别忘了下一句“只是未到伤心时”,伤心人忆及伤心事,自不免“泪飞顿作倾盆雨”了。悼亡诗词中,诗人直抒胸臆,多情的泪水洒的到处都是,“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多少滴残红蜡泪,几时干”、“泣尽风檐夜雨铃”、“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可谓水汽淋漓。痛到深处,自不免肝肠寸断,“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料得重圆密誓,难尽寸裂柔肠。”
四、“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陆游《沈园二首》之二)——幽邈的横亘时空之思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诗人自不能效庄周鼓盆而歌,对爱人的思念就如醇酒,随着时间的沉淀,显得越发浓厚。虽然诗人想喝到忘情之水,惜乎此水无厂家生产,“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因而诗人只能困在思念和回忆的茧中,无法挣脱。
“当时只道是寻常”,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这些当年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成了诗人的无价之珍。“沉思往事立残阳”,诗人沉浸在对往事的无限回忆之中,“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爱人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眼前浮现:“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往日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思至深处,诗人的思念跨越了时空;“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从而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五、“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苏轼《江城子》》)——强烈的情至深处之幻
情至深处,幻境便油然而生,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陆游的“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情至深处之幻更多的表现在梦境上,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悼亡诗词中写“梦”之作比比皆是。通过梦这一个纽带,诗人能穿越时空,可以一偿和爱人见面的心愿,“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诗人可以完成在现实世界里想要完成却不能完成的事,“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诗人可以去重温当年的美好,“续残香,留好梦,鸳瓦不销霜重”;梦境是梦好的,却不能长久,终究要梦醒,“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醒来以后诗人内心的难堪与痛苦可想而知。
在有些诗人的悼亡诗词中,梦境已经成了一种惯常的抒情达意的方式了,像梅尧臣的悼亡之作中,《不知梦》、《椹涧昼梦》、《灵树铺夕梦》、《戊子正月二十六日夜梦》、《来梦》、《梦感》等,另外像元稹、纳兰性德也写了许多记梦的悼亡之作,格外的催人泪下。
六、“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纳兰性德《沁园春》)——哀伤的动人凄怨之美
古人云:“伤逝惜别之词,一披咏之,愀然欲泪者,其情真也。”夫妻恩爱,本该举案齐眉,琴瑟和谐,白头偕老,现在却陷入“白头鸳鸯失伴飞”的境遇,这教诗人情何以堪?爱人的重重“好”不时萦绕心头,往事历历在目,而这一直都将永远的无从追寻,诗人极度的思、悔、悲、伤、痛交相杂糅,五味杂陈,剪不断,理还乱。诗人囿于礼教的束缚和世俗的眼光,自不能大张旗鼓的宣扬夫妇之爱,只能默默地把这种情感诉诸笔端,悼亡诗词作为诗人感情的喷发口,集中体现了诗人对爱人长期积淀的深挚情感,带着这样的情感“抒其情,写其事”,悼亡诗词自然“缠绵哀感”、“动人凄怨”。
另外,生离死别本就惹人伤悲,而诗作者催人泪下的真情流露和情感倾诉更增添了悼亡诗词的凄怨之美,无怪乎《四溟诗话》曰:“一读则改容,再读则泪下,三读则断肠矣。”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悼亡诗词以其至情至性打动着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王国维如是说,悼亡诗词正可谓“字字看来都是血”,以自己的凄美风格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
——评孙犁散文《亡人逸事》的结尾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