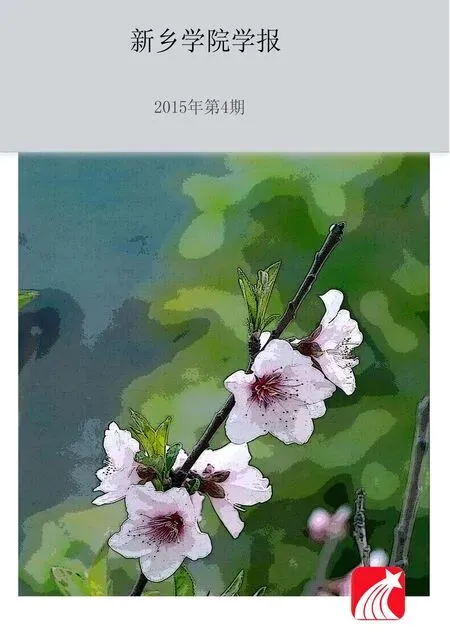《墨子》的非攻主张及其对禹征三苗的叙事
刘 洋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墨子》的非攻主张及其对禹征三苗的叙事
刘 洋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禹征三苗”是发生在上古时期的一次著名事件。墨子充分利用古代文献,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适当的文学演绎,将一场不同部族文化之间的武装冲突,表述成为文明征服野蛮的“正义之战”,最终塑造出了一位符合墨家价值观的一代圣王大禹。墨子对大禹形象的塑造和“禹征三苗”事件的叙事,文学风格整体上是质朴的,其中又不乏浪漫化、神秘化的色彩。
非攻; 禹征三苗; 文学演绎
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强调“兼爱”“非攻”,反对以扩张、聚敛为目的的战争行为。但同时他又对那些以“保民”“诛暴”为目的的“正义”战争持肯定的态度。首先,墨子在理论上划清了“攻”与“诛”的区别。《非攻下》云:
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孙诒让写道:“《说文·言部》云:‘诛,讨也。’谓讨有罪,与攻战无罪之国异。”[1]145“攻”的原初义本来和战争并无关系。甲文中的“攻”字,像一个人手持锤头敲击某物的样子[2]187。《说文》:“攻,击也。”段注:“《考工记》攻木、攻皮、攻金。注曰:‘攻犹治也。’此引伸之义。”[3]125“攻”字本义是描述工匠劳作的过程。工匠制作物品时用工具、器械来对一些原材料进行加工,免不了一些敲打、击打的过程。“攻”字中“进攻”“攻击”的义项即是由此引申而出。周代文化传统重视名实之辨,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载:“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而对“攻”则没有专门的定义。从先秦文献来看,“攻”字用于战争较为中性化。如《论语·为政》:“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门弟子冉求作了季氏的家臣,帮助季氏聚敛钱财,引起了孔子极大的反感。“攻之可也”,说明了孔子愤怒的心情,而“攻”在此是具有褒义色彩的。在《左传》中,“攻”字更多的是泛指战事,如“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桓公二年)、“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桓公九年)等等,感情色彩均较淡。
而在《墨子》的文本中,“攻”作为一个概念是与“守”相对的。墨家善守御,《墨子》中也专门列有讲解如何守城的篇目。《备城门》篇云:“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所以在《墨子》的文本中,“攻”与“侵”同义,是指不义之战。《左传》认为“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建钟设鼓,俗云“大张旗鼓”,即为“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地去讨伐“罪人”。而无钟鼓则“师出无名”,属不义之战,也即指春秋时期经常发生的以兼并、掠夺为目的战争。《襄公二十五年》载:“(子产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侵”在这里已经与后世所谓的“侵略”“侵犯”等同,也与《墨子》所谓的“攻”等同。而“诛”字,原义是指以言语问责,后来又延伸出“诛杀”之义。《说文》云:“诛,讨也。”段注:“杀戮、纠责皆是。”[3]101而墨子正是取“诛”字“纠责”之义。凡是涉及圣王的杀戮、战争等行为,墨子往往采用“诛”字进行表述,如“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非儒下》)、“郑人 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鲁问》)等等。其实“诛”字本有“诛杀”的义项,只不过墨子运用文学化的手法尽量地将其弱化了。
为了说明“攻”与“诛”的区别,墨子特地举了一个“禹征三苗”的例子: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这个故事记载了上古时期华夏部族与三苗集团的一次战争。关于古三苗国的地理方位,《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后汉书·西羌列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李炳海先生认为:“《山海经·中次八经》列有衡山条目,属于荆山系列。其中提到睢水,东南流注于江。漳水,东南流注于睢水。睢水、漳水均在今湖北宜昌东北,发源于荆山。衡山位于荆山东北千里左右,当在今河南南部。《中次十一经》又提到衡山,坐落在宣山以东大约20公里处。宣山在今河南泌阳境内,位于方城山附近。照此说来,南岳衡山最初指今河南方城山和伏牛山一带。”[4]27根据文献记载,三苗与中原华夏部族的对立冲突由来已久。孔颖达曾对中原部族与三苗的冲突过程作过一番梳理:
《吕刑》称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谓尧初诛三苗。《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谓舜居摄之时,投窜之也。《舜典》又云“庶绩咸熙,分北三苗”,谓舜即位之后,往徙三苗也。今复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数干王诛(法)之事,禹率众征之……《吕刑》称尧诛三苗云“无世在下”,而得有苗国历代常存者,“无世在下”谓诛叛者,绝后世耳,盖不灭其国,又立其近亲绍其先祖。鲧既殛死于羽山,禹乃代为崇伯,三苗亦窜其身而存其国。故舜时有被宥者,复不从化,更分北流之。下传云“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其国在南方。盖分北之时,使为南国君,今复不率帝道。[5]138
孔颖达以《尚书》中的《吕刑》和《舜典》为依据,述说了尧、舜、禹时代华夏部族与三苗部族的斗争经过。长期以来,华夏部族对待三苗的方式都是以武力征服为主。舜还曾经将其流放至西北三危山一带,试图彻底断绝三苗的生存根基,虽然“天下咸服”,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三苗既没有被灭族也没有被征服,而是继续活跃在南方荆楚之地。《尚书·大禹谟》载: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祇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5]119
《大禹谟》中的这段话当是最早关于“禹征有苗”的记载,也是墨子所依据的文献出处。在《大禹谟》中,禹奉舜帝的旨意,“奉辞伐罪”,召集四方部落首领,誓师伐苗。然而禹初期的武力征伐似乎没有见效。“苗民逆命”,亦即三苗没有降服。因此伯益劝说禹放弃武力征伐,而改用“文德”感化苗民。舜采纳了伯益的建议,于是这场战争最终以“七旬有苗格”而告一段落。这段记载虽然简短,但其传奇色彩丝毫不逊色于后世文学。“禹征有苗”的过程一波三折,先武后文,反映了华夏部族对周边部族的外交态度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了上古时期“华、夷”部族之间斗争与融合的痕迹。
《大禹谟》以舜帝“敷文德,舞干羽”作为“有苗格”的前提条件。结合前面记载的伯益告诫大禹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等内容,再参看所引舜帝孝敬父母的故事,就可以推知舜帝“敷文德,舞干羽”的行为是在向“三苗”传达某种信息。这种信息肯定不是威慑或威胁,而是一种“示好”的表现。《大禹谟》并没有透露“禹征有苗”的前提背景,只是称“有苗弗率”,孔安国传称:“三苗之民数干王诛。率,循。”[5]137“数干王诛”云云,是汉儒在华夏正统论的支配下所作的解读。在氏族父系社会向着君主制社会进行转变的过程中,有着独立文化传承和不弱的武装力量的三苗部族与不断扩张的中原华夏集团发生冲突。尧帝时“遏绝苗民”,舜帝时“迁三苗于三危”,但是到了“禹征有苗”时,却“三旬,苗民逆命”,武力征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就说明,在长期与中原部族的冲突中,三苗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已经到了可以与中原部落联盟相对抗的程度了。在这时,伯益提出了“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的建议,可以说是从战略大局出发的明智之举。对于中原部族传达的和平意向,三苗部族也作出了同样明智的选择,主动回应了舜帝的示好信息。这大概就是“有苗格”的真正含义。
“禹征有苗”事件是上古部族之间政治外交斗争的一个缩影。《尚书》被奉为儒家经典之后,“禹征有苗”也被视为“修文德以来之”的经典案例而得到传颂。但在以“非儒”而著称的《墨子》文本中,这一事件最终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在墨子的刻意描绘下,“禹征有苗”成了一种“替天行道”式的正义之举,“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其文学色彩大大地增强了。
关于“禹征三苗”的记载,《尚书·大禹谟》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纪实,而《墨子·非攻下》则是对历史事件的文学演绎,二者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大禹谟》列举三苗的种种弊政,而对那里所出现的灾异则是轻轻地一笔带过,只是称“天降之咎”而已,没有进行具体陈述。《非攻下》则从天人感应的观念出发,对于三苗的灾异具体加以列举:“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所列举的灾异均属于反常现象。对于“日妖宵出”,孙诒让称:
“日妖”不可通,“日”疑当为“有”之讹。下云“妇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鉴外纪》引《随巢子》、《汲冢纪年》云:“三苗将亡,日夜出,昼日不出。”则疑“妖”是衍文。[1]145
对于“日妖宵出”之语,孙氏或疑“日”为“有”之讹,或疑“妖”字是衍文,感到这句话扞格难通。其实,“日妖宵出”并无讹误和衍文,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妖”字的含义。妖,在这里指的是反常,违背常规。《荀子·天论》的“妖怪不能使之凶”,妖怪俱指反常的事象,预示灾祸的出现。《礼记·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妖孽,也是指预示灾患出现的反常事象。“日妖宵出”,指太阳反常地在夜间出现。妖,谓反常。至于后面提到的“妇妖宵出”,妖,亦取反常之义。古代女子通常夜间不出行,因此,把妇女夜间出行视为反常,不守常规。
《非攻下》列举三苗所出现的灾异事象是成系列的:太阳本来出现在白昼,可是却在夜间升空;通常情况下,天空降落的是雨雪,可是却是血水连降三个早晨;龙本来生于水,然而却在庙中生发;犬本来用于守门田猎,它却在市场哭泣;本来是冬天结冰,三苗却是夏季出现寒冰,以至于地面崩裂,泉水涌出。在这种反常的生态下,五谷也发生变异,使百姓受到震慑,处于恐惧状态。这里所列举的一系列灾异,带有恐怖的性质,展示的是处于反常状态的画面。
灾异现象在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经常出现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古人认为灾异现象的发生多与人事变迁有关,是早期“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如《左传·庄公十四年》载: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申繻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星相学家。他的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对“天人感应”思想的认知程度。蛇的争斗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而在申繻等人的眼里却变成了政治斗争的隐喻。人世间的“反常”行为引发了自然界的灾异现象。这种“灾异”、“反常”被称作为“妖”,往往预示着不祥的降临。墨子将种种灾异现象放置在“三苗大乱”之后,即暗示着这一系列的反常现象是由三苗的倒行逆施所引起的。这就为“禹征三苗”制造了舆论基础,将“禹征三苗”的战争行为推到了道德的高地上。这与前面墨子强调“诛”与“攻”的区别直接相呼应。
墨子明确承认鬼神的真实存在,强调“天鬼”洞察一切的超凡伟力和“赏善罚暴”的无私公正。在《明鬼》篇中,墨子即指出“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在“禹征三苗”的过程中,即出现了神灵参战助战的情节。
首先,禹伐三苗,是奉上天之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上天因为三苗大乱而要把它灭掉,使那里出现一系列的灾异,为禹的出征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禹征三苗是顺天承命,替天行道,上天保佑他一定能够成功。
然而,上天的意志并不是直接下达给大禹,而是由颛顼加以明示的:“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对此,孙诒让引王引之如下辨析:
此当作“高阳乃命禹于玄宫”。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下文“天乃命汤于镳宫”,与此文同一例,今本脱“禹于”二字,则文义不明。[1]145
王氏所作的辨析是有道理的。大禹是在玄宫接受颛顼所传达的上天的指令,然后率兵出征三苗的。颛顼被安置在玄宫,是五行说的产物。按照五行说的划分,颛顼是北方之帝,与北方相配的色彩是玄色,具体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孟冬纪》及《礼记·月令》。因此颛顼所在之处称为玄宫。
在五行说体系中,东南西北中各有主管其方位的帝和神。那么,为什么上天的指令由颛顼在玄宫向大禹传达,而不是由其他方位的神灵担当此事?这就涉及了古代的军礼和习俗。
《尚书·甘誓》叙述夏启征讨有扈的战争,夏启在战前的誓师时说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传:
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攻,则赏祖主前,士不专。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5]259
中国古代早期,出征作战要把所供奉的祖先和土地神的牌位放置在战车上,与出征将士一道前往疆场。战争中的赏与罚,分别在祖先和土地神的牌位前进行。出兵作战要把祖先的木主载于车中,由此推断,出征之前必有告庙之礼,在向祖先神禀告之后,再把木主进行迁移。《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楚国伍举在讲述公子围前往郑国娶亲礼仪时说道:“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对此,杨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解释:
庄王,围之祖;共王,围之父。句谓曾祭告于祖与父之庙而来娶妇。《礼记·文王世子》:“娶妻必告。”郑玄注:“告于君也。亦既告君,必须告庙。”[6]1200
娶妻必向祖庙禀告,这是礼仪的规定。出兵作战是国家大事,并且要装载祖先的牌位出行,告庙之礼必不可少。那么,颛顼在玄宫向大禹传达上天的指令,是否以告庙之礼为背景呢?这就涉及了禹和颛顼的血缘关系。在古史传说的谱系中,禹与颛顼确实存在血缘关系。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颛顼高阳氏,……元年,帝即位。……三十年,帝产伯鲧,居天穆之阳。”王国维先生疏证:“《大荒西经》注引《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谓若阳,居天穆之阳。’”[7]205照此说法,鲧是帝高阳氏颛顼之子,禹是颛顼之孙。《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8]124这是明确指出禹是帝颛顼高阳氏之孙,并且假托孔子之口说出。《大戴礼记·帝系》亦称:“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8]126由此可见,把禹说成是帝颛顼高阳氏之孙,是早期古史传说谱系的普遍做法。司马迁继承了这种说法,《史记·夏本纪》写道:“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9]49这是在正史系统明确认定禹是颛顼之孙。这样看来,《墨子·非攻下》所说的“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并非空穴来风,全都出自虚拟,而是有它的生成根据的。一是以出征告庙礼为背景,二是传说谱系中禹与颛顼存在血缘关系。这条记载向人们传达的是如下信息:帝颛顼在玄宫向大禹传达上天的旨意,大禹遵从上天的指令,率兵征伐三苗。实际是他在拜谒祖庙时得到祖先神的指点,这使他的征伐更具有合法性。所谓的玄宫,实指供奉大禹祖先神的庙宇。
那么,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祖先神是否具有传达上天旨意的职责和能力呢?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左传·宣公三年》有如下记载: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兰。
在这则传说中,伯儵是燕姞的祖先神,又是天帝的使者,一身而二任。伯儵把兰草送给燕姞,向她传达天帝的旨意:她将因兰草而得到君主的宠幸,后来果然如此。《非攻下》所载“高阳命禹于玄宫”的情节,帝颛顼高阳氏同样扮演两个角色,他既是禹的祖先神,又是上天旨意的传达者。这两个故事可谓异曲同工。
大禹征伐三苗,是秉承上天的旨意,并且是由祖先神高阳氏向他传达,这就使得此次征伐显得天经地义,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上天和祖先神向大禹下达指令,是这次战争的幕后策划者。在征伐三苗的过程中,大禹又得到神灵的佑助。《非攻下》写道: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这段文字颇为精彩,但是,文字障碍也较多,需要进行深入辨析。“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对此,毕沅称:“‘把’,《文选》引作‘抱’。《说文》云:‘瑞,以玉为信也。’”[1]146毕沅引《说文》以释文中的“瑞令”,颇为可取。《说文解字·玉部》:“瑞,以玉为信也。”段玉裁注写道: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云:“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又云:“瑞,节信也。”《说文·卪》下云:“瑞,信也。”是瑞卪二字为转注。[3]13
段玉裁所引《典瑞》的经文及郑玄注,见于《周礼·春官·典瑞》条目。他把瑞释为节信,是可取的。瑞用玉制成,往往充当信物。大禹征伐三苗,“亲把天之瑞令”,这里所说的瑞令,相当于古代的兵符,是将领所持发兵的凭证。
大禹手持上天赐予的玉制兵符出征,是替天行道,上天也对此作出回应,“四电诱祇”。对于这句话,孙诒让称:“未详。疑当为‘雷电誖振’。‘雷’坏为‘田’,又误为‘四’。誖、诱,振、祇,并相近。”[1]146孙氏改字作解,显得牵强,不可取。这里所说的四电,指四方的雷电。四,谓四方。以四领起的词语,往往以四表示四方,如四邻、四极、四表、四隅等。这里的四电,也是以四表示四方。“诱祇”,诱,谓引导,前导。《楚辞·招魂》:“步及骤处兮,诱骋也。”王逸注:“诱,导也。”[10]214《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也。”郑玄注:“诱犹道也,引也。”[11]1529诱谓引导,前导。祇,谓敬。《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孔安国传:“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5]122孔安国是以敬释祇,得其本义。“四电诱祇”,是说大禹手持上天兵符出行之际,四方雷电为他充当先导开路,对大禹很恭敬。禹征三苗得到上天的佑助,雷电充当先导,气势浩大。气候物象作为出行的先导,这种叙事在《楚辞·远游》中也可以见到:“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王逸注:“飞廉奔驰而在前也。”[10]170文中前面有“前飞廉以启路”之语,王逸注据此而来。飞廉,传说中的风神。《远游》的主人公是以风神为前导,《非攻下》叙述大禹征三苗,则是雷电为他开道,二者出行的样态相似,前导都是由气候物象充当,并且是主动承担。
大禹手持上天赐予的玉制兵符征伐三苗,雷电在四方为他开道,并且遇到一位神人:“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孙诒让称:“若瑾以侍,义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误。……或云:‘瑾’当作‘璜’,于形亦近,但于四方之玉不合。”[1]146孙氏采用的还是改字作解的方式,仍不可取。“若瑾以侍”,其中的“若”字,当是“掿”字的简写,或是流传过程中偏旁残缺。掿,或作搦,这里指握持。“若瑾以侍”,谓手握美玉在旁边陪从。人面鸟身神人手握美玉在旁边陪从率兵出征的大禹,而大禹手中握持的是上天所赐的玉制的兵符,两人手中的玉交相辉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景呢?这与古代的兵符制密切相关。古代的兵符分为两半,一半由出征将领携带,另一半藏于官府,由专人掌管。如果更换领兵的将帅,要以合符的方式进行,《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有这种情节。从《非攻下》的记载考察,上天所赐兵符有一半由颛顼交给大禹,另一半则由人面鸟身神人掌握。这位神人手持玉制兵符陪伴大禹,表示他也有指挥军队参战的权力,是神与人联手讨伐三苗。
这位人面鸟身神确实身手不凡:“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孙诒让称:“‘祥’,当作‘将’……与祥形近而讹。《玉篇·手部》云:‘……今作将,同。搤矢,未详。”[1]146孙氏仍然是改字作解,难以圆通。搤矢,谓用手掐住箭。《史记·周本纪》:‘养由基释弓搤剑。”《汉书·娄敬传》:“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搤,指的均是紧紧掐住。这里的搤矢,指人面鸟身神人用手紧紧掐住箭,实际是发功施展巫术。他的这一举措,使得“有苗之祥”。有苗,谓三苗阵营。之,谓其,乃。祥,作动词,谓出现凶兆。在这种情况下,“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三苗队伍大乱,最终衰微失败。在这场战争中,人面鸟身神的法术,对于战胜三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禹谟》中大禹最初以武力征伐三苗而以失败告终,这一史实本身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在极力推崇“圣王”统治的墨子眼中,无疑成了有损大禹“圣王”形象的“污点”。墨子认为圣王是“天鬼”的代言人,代天牧民,替天行道,自当无往而不胜。可以说,“人面鸟身神”的介入,改变了《大禹谟》中“苗民逆命”的历史真实,也解决了大禹纠合四方诸侯却无法战胜三苗的结局的“尴尬”,完成了墨子对“禹征三苗”历史事件的文学演绎。
那么,协助禹战胜三苗的人面鸟身神属于哪个系列的神灵呢?对此,孙诒让称:“人面鸟身之神,即《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见之句芒也。”[1]146“人面鸟身”之神在墨子中出现过两次,《明鬼》篇里就曾出现过一位“人面鸟身”的神灵:
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
文中的“郑穆公”当为“秦穆公”。秦穆公在日中之时于太庙见木神句芒降临,获赐阳寿十九年。《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为句芒。”可见句芒为东方之木神,于四时主司春季。春季草木复苏,万物向荣,是大自然生命力逐渐旺盛的时候。句芒为东方木神,也是主司春天的生命之神。所以,由句芒代表天帝出现,赐予秦穆公阳寿十九年,是合乎内在逻辑的。但是在《非攻下》篇里,“人面鸟身”之神明显是一位“战神”,这与“生命之神”的句芒形象不符。而实际上,在古代神话里,“人面鸟身”的神灵不止句芒一位。在《山海经》中,就曾经出现过多位“人面鸟身”的神灵。如东海之神禺,西海之弇兹,北海之神禺强,无一例外是人面鸟身,分别见于《山海经》的《大荒东经》、《大荒西经》和《大荒北经》。但是,禹伐三苗是在内陆作战,与海洋无涉,因此,海神不会越界前来助战。有鉴于此,对于协助禹战胜三苗的人面鸟身之神,还要从陆地神系列加以认定。
《山海经》记载的陆地四方之神,有两位是人面鸟身。除《明鬼》篇提到的东方之神句芒外,另一位是北方之神禺强。《山海经·海外北经》称:“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12]248禺强是北方之神,与同在《海外经》系列出现的东方之神句芒、南方之神祝融、西方之神蓐收并列,是掌管四方之神。《庄子·大宗师》论述自然之道的功能时称:“禺强得之,立乎北极。”王夫之注:“禺强,北方神名。”[13]63王夫之的解释是正确的。禺强是传说中主管北方的陆地之神,与北海之神禺强不属于同一系列。
北方陆地之神禺强人面鸟身,与《墨子·非攻下》出现的协助禹战胜三苗的神灵在形体样态上是一致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非攻下》篇出现的人面鸟身之神,指的是主管北方的陆地之神。
在历史上尧都平阳,其地在今山西临汾一带。舜继位之后没有迁都,政治中心仍然在晋南。禹征三苗是在虞舜任部落联盟首领期间,应当是从中原一带出兵征伐。关于三苗所处的具体地域,李炳海先生有如下论述:
它东有洞庭湖,西有巴地的彭蠡湖,南面是位于川中的大雪山,北部有豫南的衡山,四周都有自然天险作为屏障。三苗活动在豫陕川鄂湘交界的广大区域内,巫山居于中心,自然也就成了三苗集团的根据地。[4]39
三苗集团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属于南方部族。大禹征三苗,是北军南征,是从中原地区向南方的江汉流域进军。既然如此,作为主管北方的人面鸟身之神前来助战,在古人观念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北方之神禺强是作为大禹的保护神身份出现,履行他北方之神的职责。
《非攻下》对于大禹征伐三苗的叙事,明显是以北方为本位的。先是“高阳乃命禹于玄宫”,北方之帝颛顼高阳氏在玄宫向禹传达上天的旨意,并把上天所赐的玉制符节授予他。玄宫,谓北方之宫,又指禹的祖庙。在出征过程中,北方之帝颛顼、北方之神禺强,对这场征伐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北方之帝、玄宫与北方之神、北方作为同一个系列加以叙述,这在《庄子·大宗师》中也可以见到:“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李颐注:“颛顼,帝高阳氏。玄宫,北方宫也。”[14]250这里也是把北方之帝颛顼所居之处称为玄宫,与《非攻下》的表述相同。《墨子·非攻下》《庄子·大宗师》都是把帝颛顼高阳氏、禺强纳入同一个系列,分别作为北方的帝和神看待。区别在于,《大宗师》明确标示出颛顼和禺强的称谓,而《非攻下》虽然提到“高阳”,而对于人面鸟身的北方之神禺强并没有出示他的称号,从而造成解读的障碍。尽管如此,经过深入的辨析之后,这两篇文章的上述记载仍然可以相互印证。
明鬼、天志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攻下》对于禹伐三苗所作的叙事,充分体现了墨子的上述理念。这段叙事涉及天神、祖先神颛顼、自然神禺强,他们所扮演的都是惩恶扬善的角色。其中祖先神颛顼高阳氏、北方之神禺强,还与大禹有过直接交往,出现的是人神杂糅的场面。《礼记·表记》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对此,孙希旦写道:
尊命,谓尊上之政教也。远之,谓不可以鬼神之道示人也。盖夏承重黎绝地天通之后,惩神人杂糅之蔽,故事鬼神而远之,而专以人道为教。[15]1309-1310
夏文化的特点是敬鬼神而远之,不以鬼神之道示人。而墨子对夏禹征三苗所作的叙事,却是人神杂糅,以鬼神之道示人。他虽然以夏族祖先为叙事对象,但是其中所渗透的理念却与夏文化相悖,叙事对象本身本来具有的属性,与叙事者所持的理念,形成二律背反的格局。
《非攻下》所渗透的明鬼、天志理念,使得对于战争的叙事带有传奇的色彩,并且有几分神秘气氛。人面鸟身之神用手紧掐箭矢,三苗军队就出现灾异事象,结果导致“苗师大乱”,仿佛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墨子·非攻中》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作了详细的陈述,揭示出攻战的巨大负面效应。而禹征三苗的战争,见不到刀光剑影、见不到死亡和血腥味。神灵的参与,使得对这场战争的叙事得到净化,与墨子的非攻理念相契合。
《非攻下》对于禹征三苗所作的叙事,是浓缩型的战争叙事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山海经》中的北方之神禺强,不但人面鸟身,而且珥蛇践蛇。《非攻下》出现的人面鸟身之神指的是北方之神禺强,但是见不到珥蛇践蛇的细节,从中可以见出墨子所作的剪裁,他没有对神话传说原封不动地袭用。《非攻下》出现的人面鸟身之神禺强,《明鬼下》出现的“鸟身”、“面状正方”的句芒,他们分别是掌管北方和东方的自然神。《墨子》一书对于人面鸟身之神的选取,遵循着同类相从的原则,体现出严密的逻辑。
《非攻下》对于战争的叙事带有传奇色彩,虽然以浓缩形态出现,但也不乏精雕细刻之处。大禹出征,“四电诱祇”,四方雷电充当先导。雷电交加具有威慑力,也还很容易造成人的伤害。可是,后面缀以“祇”字,凸现出雷电对大禹的恭敬、顺从,使得恐怖性得以弱化。如前所述,自然物象作为出行的先导,《非攻下》与《楚辞·远游》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人面鸟身之神对大禹“若瑾以侍”的情节,在《远游》中也有与之相类似者:“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10]171雨师在作品主人公左侧陪同,用的也是“侍”字,可以与“若瑾以侍”相参照。总之,《非攻下》对于禹征三苗的叙事,所采用的手法富有文学价值。只是由于用语过于简略,它的文学价值往往被人忽视。
[1]孙诒让.墨子间诂 [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3]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5]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附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王逸,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影印《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5]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 郭庆林】
Mo-tse’sAnti War Advocates and Narration of the Conquering Sanmiao people by Dayu Emperor
LIU 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Dayu conquered Sanmiao people was a famous event occurring in ancient times. Mozi took full advantage of ancient literature to conduct an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les. He transformed this armed conflict between two different tribes culture into a just war of civilization conquesting the savage in the literary form, so he shaped St. Dayu to line with the values of Mohist. The literature stytle ofMo-tse’sDayu character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Dayu conquering Sanmiao people is plainness in general, which is romantic and mystify.
anti-war; conquering Sanmiao people by Dayu;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2015-02-12
刘洋(1984—),男,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I210.6
A
2095-7726(2015)04-00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