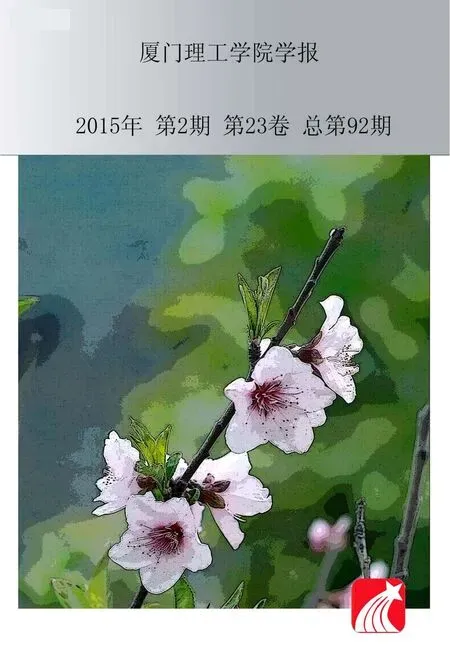论“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
——以鲁迅、凌叔华、庐隐为例
龚润枝,汪 杨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论“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
——以鲁迅、凌叔华、庐隐为例
龚润枝,汪 杨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女性解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凌叔华、庐隐作为最早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作者,他们的笔下都勾勒出沉睡之中和惊醒之后这两种女性形象,他们的“女性书写”显示出“五四”时期男女作家对于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差异。对于沉睡之中女性的书写,鲁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阐述她们所遭受的压迫,凌叔华则揭露女性灵魂的孱弱程度,庐隐主要描写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无助感;对于惊醒后女性的书写,鲁迅是站在“人的解放”的立场上期待她们自立,凌叔华描写女性的生存智慧,庐隐则着力剖析女性的情智冲突。他们的“女性书写”代表了“五四”时期对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时代的高度,并窥破了隐藏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女性将要面临的新的困境。
女性书写;“五四”时期;鲁迅;凌叔华;庐隐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女性一直生活在“地表”之下、文本之外,她们一直被“代言”、被“言说”,女性的世界于世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隐秘、暗哑的存在,直到“五四”新文学发现了“人”,也发现了作为“人”的女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为女性发声的不是女性自身,而是鲁迅,他也是最早对女性生存进行言说的“他者”,当代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必不能够绕开“娜拉”和“子君”的身影,可见鲁迅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启蒙之深。凌叔华和庐隐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女作家,凌叔华的小说基于女性内经验的书写,记录了中国新旧文化过渡时期女性生存的全貌,鲁迅曾说凌叔华的小说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1]。至于女性自身,最早对自我命运进行探索的则是庐隐,在近几年的庐隐研究中,庐隐被称为“中国现代女权主义的第一人”,而庐隐本人也正是出走的“娜拉”,她不仅言说也践行着自己的女性观。本文通过对鲁迅、凌叔华、庐隐女性观的剖析,探索“五四”时期男女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差异,以及沉睡之中的旧女性和被惊醒之后的新女性的不同生存境遇。
一、沉睡之中的女性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沉默寡言的女性比“一家之长”的男性遭受了更多非人性的压制,这压制来自于历史文化、家庭伦理和社会舆论,女性的人格受到社会的打压和自我内心的抑制,在这内外煎熬中的女性卑微地在男性秩序的社会里小心翼翼地讨生活。“五四”新文学发现了“人”,这其中也包括女性,在当时讲究“人格” “人权”的缝隙里,鲁迅是最早一位作为“他者”为女性发声的作家,他也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1918年鲁迅发表了他最早关注女性的一篇文章——《我之节烈观》,将男性和女性都放到“人”的位置,认为鼓励女性“守节”一事是非人道的,他直白地指出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苛刻,他在文章的末尾发愿女性应该受到正常的人的待遇: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2]
在鲁迅的这一小段发愿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鲁迅对当时女性生存状况的悲悯,可是鲁迅的这一悲悯也只是将女性放到“人”的位置,并没有给予她们开口言说的机会,他将女性归类为弱者和被迫害者,从“人性”和“人道”的角度出发,点出女性——弱者、被迫害者生存的畸形环境,以女性个体命运的悲剧性来折射封建时代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非人性特质,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阐述女性所遭受的非人性压迫。他的这一类文章还有《寡妇主义》《论秦理斋夫人事》等。鲁迅在《祝福》和《离婚》中描绘了两个具体的旧时代女性的形象——祥林嫂和爱姑。祥林嫂的命运一再受制于他人,她自己在这悲苦中渐渐地绝望,最后“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3]爱姑勤勤恳恳地侍候公婆、料理家务,最后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她起初愤愤不平地不愿离婚,最后面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只能喏喏地放弃。我们从鲁迅笔下涉及女性的故事梗概中,看到了女性被压迫的侧影,看到了女性已经麻木的面容,然而我们无法了解她们隐在文本之外的信息,这是作为旁观者的掣肘,女性隐在文本之外的信息也唯有作为亲历者的女性作家才能提供。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记录旧时代女性生存境遇的女作家,她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的底根,将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一一向我们描述。她的作品尤以《绣枕》和《中秋晚》最广受赞誉。《绣枕》中的大小姐一心期待绣出一对美轮美奂的靠枕以获得白家少爷的青睐,可是她费时半年才绣出的靠枕刚进白家就被践踏了。凌叔华在《绣枕》中塑造的“大小姐”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盲婚哑嫁的女子们,当她们被拾缀得像精致的绣枕等待送出的时候,她们自己也有着对爱情、对夫婿的美好幻想,这等待送出的“绣枕”也有着美好的情思,有着期待被珍视的心愿。在凌叔华的《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在中秋这天做了许多筹备,以期与丈夫共进一顿寓意团圆幸福的晚餐,她因丈夫临时有事未来得及尝一口象征团圆的团鸭而深感惶恐。凌叔华委婉地道出:女子生活的幸福,并不仅仅是靠一个有情义的男子就可以得到的,它也需要女性自身的维持和努力。凌叔华笔下的女性是以主角的身份在言说,她以自己作为亲历者的角度来对女性的内经验进行阐述和揭示,她以大小姐对绣枕、敬仁太太对团鸭寄予厚望的描写,来揭露依附在男性身后生存的女性灵魂的孱弱程度。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和鲁迅笔下的爱姑、祥林嫂的相同之处在于:愚昧不识和逆来顺受都深深地埋藏在她们的血液里,不同的是凌叔华是将旧时代女性的正面展示给我们看,而非侧影或背面,她们对未来的忐忑、对爱情的憧憬、对外界的惶恐等等都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个有情感有血肉的活生生的女性形象,而非一个模糊的被迫害者的形象。另外,凌叔华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让人悲悯的迷茫少女,抑或是惹人厌恶的愚昧太太,她都从女性的心理描摹出她们的另一面——对时代变动的茫然、被厌弃时的无措,这惶恐脆弱的性灵唯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到。如果说鲁迅向世人描述了覆盖在女性天空上的黑云,那么凌叔华则拨开了这一层黑云,让世人看清女性的世界到底困顿到怎样的程度。
庐隐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是在“五四”的风潮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茅盾曾说“庐隐是在‘五四’的怒潮中觉醒了的一个女性”,“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4]故当庐隐能够为女性发声的时候,她本身已在“五四”的风潮中接受新文学的洗礼,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批“出走的娜拉”活跃在文坛上。庐隐和凌叔华虽同为女性命运的亲历者,可是她们对沉睡之中的女性的态度还是有差异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她们虽都将沉睡之中的女性归为弱者,然而她们将女性划为弱者的依据不同。凌叔华笔下女性的弱主要体现在落伍于时代、对自身不幸命运的无知无觉;庐隐笔下女性的弱主要体现在对自身命运的无能为力,像《父亲》中“我”的庶母在得知“我”的父亲在乡下已有妻室后,她愤然离开大家庭,另租赁房屋居住,却仍因无力摆脱受钳制的现状而病猝。
二是凌叔华和庐隐对待沉睡之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态度不同。凌叔华虽悲悯于被时代所遗弃的女性,可也暗自嘲讽旧时代女性的愚昧、冷漠,像《中秋晚》中,敬仁太太幸福生活的转折点是她在中秋晚为了让丈夫尝一口象征团圆幸福的团鸭而拖延了丈夫去见病危的干姐姐,以致丈夫因未能见到干姐姐的最后一面而迁怒于她;庐隐则深切地同情飘零在凄风苦雨中的旧时代女性,并将这一根由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她在《憔悴梨花》中写道:“雪屏十分伤心,她恨社会的惨剧,又悲倩芳的命运,命一个柔弱女子,和这没有同情,不尊重女性的社会周旋,怎能不憔悴飘零?”[5]同是将沉睡之中的女性放在男性社会的对立面,但因创作者自身经历的不同,凌叔华的笔下有对女性自身的反省,庐隐则深深地沉浸在女性的悲哀之中,这是她们对这群茫然于时代与自我命运的女性群体的不同认知。
二、惊醒之后的女性
鲁迅曾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6]鲁迅对女性的描述一直是站在“国民批判性”的角度上,他对旧时代女子的不幸遭遇在“哀其不幸”的时候,还会“怒其不争”,他以女性在历史中的遭遇来警示当下和未来的人,他激励当下的女性拥有“自我” “自主”的意识,他站在“人的解放”的立场来要求和期待女性。《伤逝》中的涓生以启蒙者身份来引导子君迈出“我是我自己的”这一步,使子君只身离开了“圈养”她的家族,可是涓生对子君的启蒙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唤醒了子君,却没有给她新的可做的梦,于是子君郁郁而终了。凌叔华则是站在女性生存的角度上,期待女性能够安稳幸福地生活下去,她描写的新时代女性都具有生活的智慧,诸如《酒后》中的采苕,即使丈夫应允她去亲吻酒后酣睡的子仪,她还是选择了却步。凌叔华所描述的是女性不为人知的无奈和隐秘,她们在接受了新式教育后虽然脱离了愚昧,能够看清“形势”,可是这两千年来男女不平等的旧疴依旧让她们难以自立,凌叔华清醒地明白女性所处的位置,她才会安排笔下的新时代女性隐藏起“自我”来稳固自己的婚姻。
在“五四”时期,新女性被新时代、新文学、新伦理等从睡梦中唤醒,女性跟随“人的解放”的热潮而解放出来,当她们还在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新的生活方式时,鲁迅给予新女性“我是我自己”的期待,虽然惊醒了当时的女性,可是女性本身在这新与旧的撕扯中,不可避免地会“流血”,所以喊出“我是我自己的”子君“病逝”了,凌叔华笔下的新时代女性也在失去“自我”的时候“逝去”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7]28那么新时代选择“出走的娜拉”在“五四”时期的生存境遇又是怎样的呢?
1923年庐隐发表了她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篇小说以庐隐为原型,讲述在新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新女性在情感与理智、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痛苦挣扎,女主角露莎为追求“精神恋爱”与梓生远走他乡,她的女友们或妥协于世俗或郁郁而终。阿英曾评价庐隐的小说是自己的自叙传,苏雪林曾说“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不知,庐隐却很坦然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7]297鲁迅这一批最早的启蒙者教会了她“发声”,可是这刚学初啼的夜莺,却字字悲切、声声啼血。庐隐将她感受到的女性的心理和处境诉诸于文章,她多舛的命运让她对女性的处境有着切肤的体会,她的言说有着急于发声的嘶哑,混着血和泪,让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为之动容。
鲁迅以男性作家的身份发现了新式女性进退两难的境遇,他虽有志于启蒙正在成长的女性,可是他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在俯视、在冷眼旁观女性蹒跚的步履,当他教导女性走出家庭,争取婚恋自由的时候,庐隐却以敏锐的眼光对爱情产生了质疑,她发现在男权社会中,爱情只是一场虚幻,隐在爱情背后的是性别压迫。庐隐在《或人的悲哀》中描写了两个男子为亚侠争风吃醋,然而亚侠却一针见血地说:“人类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们要是欢喜什么东西,便要据那件东西为己有!唉!我和他们两个,只是浅薄的友谊,哪里想到他们的贪心,如此厉害!竟要做成套子,把我束住呢?”[8]在《象牙戒指》中庐隐更具体地描写了爱情在男权社会里让女子所受的压迫:沁珠在少女时期被伍念秋所蒙骗,当沁珠克服种种心理障碍准备和曹子卿订婚的时候,伍念秋竟然在报上刊登了沁珠曾给他写的情书,病中的曹子卿愤怒之下吐血而亡。《象牙戒指》是庐隐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故事为基础而创作出来的小说,真实地记录了“五四”时期女性在争取自由恋爱中的艰难。
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虽然艰难,走出父亲家庭的“娜拉”们还是有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的决心和魄力,譬如庐隐、萧红、丁玲等,无奈在爱情的光环笼罩下的新式家庭,并不是这群攻破了世俗壁垒的女英雄们所期待的那般美好,等在这里的是一个关于“夫权”的陷阱,她们历经千辛走出了父亲的家庭,接纳她们的却不是她们的家,而是丈夫的家,在这进退维谷之间,只有一个狭窄的甬道让她们暂时落脚。庐隐在《胜利以后》里说“胜利以后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回顾前尘,厌烦现在,恐惧将来。”在《何处是归程》中庐隐茫然地问到“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9]凌叔华和庐隐都发现了惊醒之后的女性在丈夫的家中所面临的新困境,她们又一次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凌叔华给我们列出了简洁的方案——淹没自我或逃离家庭:《花之寺》中的燕倩以陌生人的身份给丈夫写了一封仰慕的信,以图刺激夫妻间的感情,这是以女性的生存智慧来修护以爱情之名而结合的家庭;《绮霞》中的女主人公在自我存在和家庭责任无法调和的矛盾中,选择离开家庭去外国进修,这是依据自我意识在自我存在与家庭生活中理性地选择了自我。庐隐则描绘了女性被双重爱所负累的困顿——夫妻之爱、母子之爱时常让有志向的女性暂时忽略自我,在《何处是归程》中沙侣一面对幼儿倾注了满腔柔情,一面沉浸在丧失自我的失落中,当沙侣深陷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时,庐隐又借友人的口来劝慰她。庐隐作为新时代女性悲剧命运的亲历者,她曾试图超越,却反受世俗的安慰而哄劝自己退让、忍耐,与此同时,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她又对惊醒之后的女性的现状产生质疑与不甘,她不可避免地陷在情与智的矛盾中。
“五四”出走的“娜拉”们在实现“我是我自己”的路途上不断迷惘,却又一次次地重新振作,这一群被惊醒的女性虽然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坦途,可是在中国早期女性解放的征程上,她们一直在摸索着前进,带动了更多女性的觉醒和独立。
三、结语
鲁迅、凌叔华和庐隐的“女性书写”代表了“五四”时期男女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时代的高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时代女性的生存现状,并在不同的视野下探讨了女性群体的出路,他们窥破了隐藏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女性将要面临的新的困境,无论是女性命运的旁观者抑或亲历者,他们对女性命运的探讨都推动着女性群体对自我生存境遇的重新审视。虽然他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时代,他们的观念或许会不再适合后世的世界,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为女性的解放做出了无以估量的价值,永远值得我们去铭记。
[1]鲁迅.《小说导言》二集[M]//刘运峰.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8.
[2]鲁迅.我之节烈观[M]//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
[3]鲁迅.祝福[M]//鲁迅.鲁迅小说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47.
[4]茅盾.庐隐论[M]//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304.
[5]庐隐.憔悴梨花[M]//庐隐.柔肠一寸愁千缕.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287.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鲁迅杂文全集:上下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27.
[7]苏雪林.《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M]//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8]庐隐.或人的悲哀[M]//傅光明.庐隐:一个情妇的日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25.
[9]庐隐.何处是归程[M]//庐隐.柔肠一寸愁千缕.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14.
(责任编辑 马 诚)
Writing of Women in the May Fourth Era from Lu XunLing Shuhua,and Lu Yin
GONG Run-zhi,WANG Y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The starting point of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e 1920s.As the first-generation writers of women's life,Lu Xun,Ling Shuhua,Lu Yin all portrayed the sleeping women and the awaken,and ye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women in existential plight varied.In presenting the sleeping women, Lu Xun elaborated their suffering as an objective observer,Ling Shuhua tried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fragility of the tender soul,and Lu Yin focused on women’s helplessness for themselves.In portraying the awaken women,Lu Xun expected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a position of personal liberation,Ling Shuhua described the women’s wisdom of survival,and Lu Yin labored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them.Their writing represented the height of women’s literature during that era,and glimpsed something of a new dilemma for women hidden under the banner of gender equality.
writing of women;May Fourth Era;Lu Xun;Ling Shuhua;Lu Yin
2015-01-25
2015-04-20
龚润枝(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汪杨(1980-),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runzhi0111@163.com
I206.6
A
1673-4432(2015)02-0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