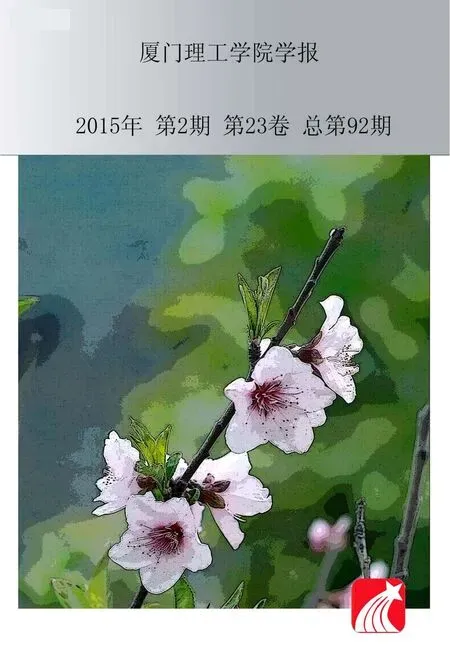鲁迅和林语堂女性叙事的解构
吴毓鸣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鲁迅和林语堂女性叙事的解构
吴毓鸣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鲁迅在文化视阈下呈现女性悲剧,林语堂在自然视阈下呈现女性喜剧,其女性叙事大相径庭,为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话语版本。然而,鲁迅和林语堂以关怀女性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往往因为“二元对立”法则变异为某种文化权利符号的政治解读功能。其实,“文化形成”和“自然造物”是中国现代女性乃至当代女性必须面对的文化叩问。 应改变论高下比优劣的批评模式,以“文化”观照“自然”,跨越“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话语围栏,从不同话语表述入手,探寻鲁迅和林语堂“二元”走向的思想意脉,在女性研究的框架内解构女性思想启蒙和身体解放不期而遇的文学意向,探寻“二元”和解的文学图景。
鲁迅;林语堂;女性叙事;“二元”和解
“五四”运动以后,关注女性命运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自觉。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争取社会权益重要,还是扮演性别角色更重要”“女性命运是文化形成,还是自然造物”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令人深思。“二元”解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话语模式。鲁迅在文化视域下审视女性命运,揭示性别不平等乃文化形成;林语堂在自然视域下解构女性命运,阐述性别不平等乃天然造物。处于同样的历史时期同样的社会背景,由于审视立场不同,评判眼光不同,文学表述大相径庭。20世纪80年代,褒鲁贬林者众。20世纪90年代以后,扬林抑鲁者兴,随波逐流成为时髦的批评模式。刘复生说:“批评,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而当代文学批评,所从事的正是价值创造的工作。因而,什么是文学的标准,何谓‘美’,对它来说,不是既定的神圣主题,而是悬而未决、有待发现的新尺度;它不是在不自觉地、盲目地肯定着既有的审美价值,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新的审美决断,在创造着新的审美价值。”[1]走进两位作家的女性叙事天地,发现用“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法则解构文本,很难产生新的审美价值。本文改变审美方式,以“文化”观照“自然”, 尝试从既定的女性研究框架内突围,阐述“二元和解”的文学图景。
一、鲁迅:演绎女性悲剧
1918年,鲁迅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对男尊女卑之文化形成提出抗斥,“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2]17,“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2]18,“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鲁迅的思想启蒙意识渗入他的女性叙事,祥林嫂、子君演绎了“文化形成”的命运悲剧。
鲁迅笔下最耳熟能详的当属祥林嫂和子君,祥林嫂是乡村无知女子,遵循礼教;子君是都市知识女性,反抗礼教,却一样逃脱不了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农村妇女,无名无姓,因嫁给比她小十岁的丈夫祥林当童养媳而得此称呼。她的第一段婚姻,以丈夫小小年纪去世而告终。虽说夫妻之间未必有刻骨铭心的男欢女爱,但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一心一意守寡。无奈她婆婆为赚取八十千(钱)聘礼替二儿子娶亲,逼她再婚。祥林嫂逃婚到鲁四爷家做女工,她婆婆打探到消息,捆绑着上了花轿。祥林嫂“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地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3]11祥林嫂一女不事二夫的勇毅,可以说是礼教规范下的感性行为。虽然烈女没做成,但如此奋不顾身,可见“一女不事二夫”的礼教已内化为女性自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被祥林嫂抗拒的婚姻出乎意料地美满,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儿子,“母亲也胖,儿子也胖”[3]12。仅此八个字,可见贺老六之知冷知热,祥林嫂之无忧无虑,可见先前抗婚之愚昧!此非闲来之笔,不显山不露水的反讽手法,揭示了祥林嫂抗婚的愚昧。可惜好景不长,贺老六得伤寒死了,儿子被狼吃了,大伯来收屋,赶她出门,祥林嫂不得不又到鲁四爷家做女工。鲁四爷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3]14。祥林嫂“败坏风俗”如果仅止是鲁四爷一人的想法也罢了,镇上的人们“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周遭人的冷落、蔑视、谴责,形成对祥林嫂的精神围剿。柳妈置问她“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总是你自己愿意了”,祥林嫂推说贺老六力气大,言下之意她当不成烈女非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强加。柳妈还要说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3]17柳妈恐吓祥林嫂,将来她到了阴司,会被阎罗大王锯开分给两个男人。并告诉她捐门槛,找替身赎罪。可怜的祥林嫂丧夫失子,还要经受如此的精神折磨!祥林嫂临死前念念不忘两件事:一个人死了之后有没有魂灵;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吗?
祥林嫂三十几岁,经历二次丧夫的命运,守寡受歧视,再嫁受歧视,这种歧视不单来自压迫阶级的男性眼光,还来自受压迫阶级的女性眼光。男子多妻,全然不惧身后事,一女二嫁却患死后分尸,祥林嫂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传统文化愚弄女性的荒谬逻辑。无知的祥林嫂说出了发人深醒的话语:“我真傻,真的”,“我当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3]13在鲁迅笔下“狼”无时不在,是吃人的动物,也是吃人的礼教,由愚昧的祥林嫂说出,有撼人的力量。
子君是富家小姐、知识女性,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有叛逆精神,与涓生私奔,爱情自主,似乎应该比祥林嫂有更好的归宿。不幸的是,子君一样没有逃脱悲剧命运。私奔之前,涓生和子君有共同的追求,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志同道合;同居之后,子君在筑就的爱巢里讨生活,涓生告诉她“爱情需要时时更新”[3]120,子君不解其意不知所措。子君以觉醒者的姿态追随涓生,沉醉于自以为是的女性解放想象。但“筑巢”之后思想追赶不上情感的节奏,和涓生貌合神离爱难以为继,无声无息地倒在追求爱情自由的场地上,鲁迅说她“毫无怨恨的神色”[3]130,为什么呢?因为追求爱情自由没有错,个性解放没有错。问题在于思想启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她走进爱巢之后以为大功告成,回到了旧的生活轨道。所以,把子君的悲剧归之于涓生的喜新厌旧,不免低估了鲁迅塑造子君的意义。 “私奔”是反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女性的经济地位和文化身份。子君追随涓生进入另一个私人空间,而不是进入公共领域谋取社会权益为立身之本,令人扼腕。
《祝福》写于1924年,《伤逝》写于1925年,祥林嫂和子君先后上场,一个被迫再嫁,一个主动私奔,一样遭遇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命运。鲁迅的女性叙事显而易见思想启蒙的女性学元素:女人的悲剧命运并非先天而来,而是后天形成的。
二、林语堂:演绎女性喜剧
林语堂对“多妻”有不同的看法,“纳妾制度可以被认为多少有些道理”,“中国人认为婚姻是家庭的事,婚姻失败时就纳妾。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而完整地存在”, “不管是由离婚、纳妾、同居、试婚引起的,还是由自由恋爱引起的,造物主在性的安排上,已经造成了一些永久的不平等和不公平。”[4]在“自然造物”不平等的前提下,林语堂提出了“妻妾和谐”的构想。
林语堂笔下最为人称道的当属木兰和牡丹,她们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荡妇,完美演绎了林语堂关于女性的“自然”构想。
木兰出身名门,诗书礼仪谙熟于心,嫁入曾家,生育一男一女,完成了妻子到母亲的角色转换,符合林语堂对女人的定义:“我以为一个女人,不论她在法律上的身份如何,只要有了子女,便可视之为妻;而如若没有子女,则即使是妻,也只能视做姘妇。有子使姘妇抬高身份,而无子女则使妻降级。”[5]素云、莺莺没有生育,屡遭作者贬斥。木兰儿女成双,家庭地位稳定,本来相夫教子无忧无虑,不需要节外生枝“纳妾”。可是,林语堂为了演绎“纳妾”有理的观点,让这位知书达礼的女性做形象代言人。木兰觉得曾太太有个桂姐,养尊处优事不躬亲。萌生了“替自己纳妾”的想法。“丈夫有一个妾,她心里越想越美。一个做妻子的若没有一个妾,斯文而优美,事事帮助自己,就犹如一个皇太子缺少一个觊觎王位的人在旁,一样乏味,她觉得这其间颇有道理。一个合法的妻子的地位当然是极其分明,若是有一个‘副妻子’,就如同总统职位之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总统的职位就听来更好听,也越发值得去做了。”[6]“纳妾”从男性欲望转为女性期盼。木兰认定妾辅佐妻子在先,侍寝丈夫在后,而且“妾”由自己任命,利于操控,万无一失。于是想把丫环暗香嫁给荪亚做妾。将“妾”描述为“副妻子”,再把“副妻子”和“副总统”相提并论,可以说是林语堂的男性虚构。副总统的地位低于总统,权力小于总统,可是妻子身居尊位,但妾行妻权屡见不鲜,悲剧比喜剧多。纳妾,有违性心理,亦有违性道德,可是在男性虚构的文化场景中,成为女性自欺欺人的喜剧变奏。
在《红牡丹》中也有潜在的“妻妾”画面,牡丹和妹妹素馨随梁翰林入京,一个侍寝一个奉茶,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情节透露了牡丹的“自然”身份。
虽然与木兰相比,牡丹显得不守妇道,婚前出轨,婚后不忠,守寡放荡,与钱庄老板金竹、翰林学者孟嘉、江湖艺人傅南德、文人安德年有过性爱关系,颠覆了“一男多女”的情爱模式。林语堂因此受到女性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赞其有“独特的女性观念”,对“女性解放”有独特贡献等等。其实,牡丹的情欲诉求与“女性解放”貌合而神离,它听从的是身体内部的声音,而不是思想层面的觉醒。扶柩返乡的路上,牡丹和孟嘉太湖不期而遇结伴同行。两人同船起居,牡丹故意放肆,衣裳还没扣上扣子就出来招摇。孟嘉浸渍四书五经,恨牡丹这样厚颜大胆,却情不自禁地迷上了“这么个无与伦比的妙人儿”[7]61。夫孝在身,她对孟嘉直言“我要离开亡夫家,再嫁个男人”[7]51。林语堂在牡丹身上融入的“道不远人”的哲学构想,与其“自然造物”的女人观一脉相承。译者曾言:“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主题似乎即在于是。”[8]“人性之本能”是否《红牡丹》之主题,此处不讨论,但“人性之本能”通过牡丹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性格得到张扬,赏心悦目。作者塑造牡丹,说“她的芳名儿叫红杏出墙”[7]279。“红杏出墙”指称女子不忠,并无褒意。但在林语堂笔下,透出喜气。可见林语堂毅然拆除女性贞洁的文化围墙的用心,在“自然造物”的现代叙事中放飞被禁锢的生命。但与当代女性作家以自叙传建构主场经验,批判男性不同,牡丹不是以玩弄为目的的性别颠覆,每次出轨留下一段爱的记忆。作者不着意于性别批判,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二元断裂”,离女性主义的极度现代有点遥远。牡丹放荡了一段日子后改邪归正,嫁给身强力壮的傅南涛,归隐园田,履行“生儿育女”的职责,复位“自然”角色。
木兰和牡丹殊途同归并不意外,毕竟,在“自然造物”的视阈中,身体溢出理性的秩序之外行之不远。
三、鲁迅与林语堂:文化形成与自然造物
鲁迅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男多妻,女守节;林语堂从自然的角度审视“一夫多妻”,两人执“二元”之一端。鲁迅和林语堂以关怀女性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往往因为“二元对立”法则变异为某种文化权利符号的政治解读功能。其实,“文化形成”和“自然造物”是中国现代女性乃至当代女性必须面对的文化叩问。探寻鲁迅和林语堂“二元”走向的思想意脉,从不同话语表述入手,思考个性表述中存在的思想启蒙与身体解放的共谋关系,旨在寻找“二元和解”的支撑点和切入点。
鲁迅笔下的子君,叛逆缘于新思想的唤醒。涓生张口谈家庭专制,闭口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口若悬河,子君佩服得五体投地,必追随之而后快。精神崇拜引领下的身体皈依,长辈不以为然诫之阻之。子君义无反顾,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116,毅然与家庭决裂与涓生同居。子君追求“个性解放”,更多地关注身体外部的人生要义,更多的是践行精神诉求。林语堂笔下的牡丹“是个宗教的叛徒”,她之叛逆,更多的是情欲诉求。牡丹蔑视道德、颠覆规范,金竹、傅南涛、安德年都是有妇之夫,牡丹和他们幽会,保持婚外情而不以为耻,听从的是身体内部的呼唤,想爱就爱,践行的是身体解放。她们的诉求不同,源于“文化”和“自然”的声音。
鲁迅认为,女子被压迫受欺凌,是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文化造成的,无关床第。所以,在鲁迅唯一的恋爱小说《伤逝》中,看不到床戏,看不到卿卿我我男欢女爱。子君的思想觉醒、个性解放、行为勇毅,倒是放笔描述。私奔,在当时是“伤风败俗”的行为,遭遇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涓生有点畏缩,子君却是视若无睹,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无畏无惧,因为有理想信念为她撑腰。身为富家小姐,操持家务不是她的特长,然而她不怕苦不怕累,倾注全务,终日汗流满面,两只手渐渐粗糙起来,为了爱的理想她愿意改变自己。可是围着锅台转罔顾思想进取,不知不觉地迷失了自我。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之后,即表现了他的厌倦,反嫌子君操持一日三餐烦扰,动不动“给看一点怒色”。一心一意筑爱巢的子君,面对爱的冷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奈走出冰冷的家,以“伤逝”谢幕。而在林语堂笔下,性爱场面有声有色,和初恋情人金竹幽会,牡丹从浴室里出来,赤祼裸一丝不挂,投身躺在金竹身边。金竹不由自主地被她奇妙的身躯,丰满的胸膛,柔软的身段所迷惑。和孟嘉共涉爱河,牡丹把孟嘉领到一个完全隐僻的所在,牡丹四仰八叉仰卧在草地上。目视孟嘉。她的两个乳房上下起伏,清楚可见。孟嘉挪动了身子,把头枕在牡丹的乳房上……欢娱场面活灵活现。牡丹以投怀送抱的主体意愿挑逗男人满足男人,情欲放纵。金竹、傅南涛、孟嘉、安德年为她神魂颠倒。当然,林语堂不可能让牡丹放纵太久,因为在他眼里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职,所以,追求身体欲念的牡丹最终返朴归真,离开繁华的北平,与傅南涛归隐京西田园,过夫唱妇随的生活。
子君诞生于1920年代的中国,时逢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女性关注社会权益,所以“娜拉”出走;牡丹诞生于1960年代的美国,时逢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改善,追逐社会权益的眼光转向了个体生命的欲望实现。涓生和子君,涓生是思想言说者,子君追随涓生,着迷的是女性社会权益的理论阐释,精神崇拜;牡丹和傅南涛,牡丹是身体言说者,牡丹选择傅南涛,因为他发达的肌肉,矫健的动作,着迷的是个体生命的欲望,身体崇拜。鲁迅以悲剧模式批判子君式解放想象,林语堂以喜剧模式赞扬牡丹式解放构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文化”和“自然”和解的现代性问题。
子君之落败与牡丹之完胜,源发点不是女性主义立场,却触及了女性学身体欲望和精神向度、个体价值和文化评判的问题。子君承载了鲁迅反封建反礼教的社会启蒙意识,鲁迅曾断言“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一条回家,一条堕落。《伤逝》收入小说集《彷徨》,表达了中国女性思想觉醒之后不知何去何从的困惑。牡丹承载了林语堂反禁锢的身体启蒙意识,女人属于“自然”,情欲也属于“自然”,应该拆除“贞洁”牌坊,符合女性身体自由飞翔的愿望。
从严格意义上说,《伤逝》和《红牡丹》不属于“女性文学”范围,这并非就自然性别而言,而是就新旧知识体系的转换和颠覆的策略而言。 鲁迅和林语堂的女性叙事,以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浮出历史地表,从不同向度揭示了“二元对立”背景下女性自我解放的尴尬。
“文化”和“自然”二元对立耳熟能详的解释是理性和感性二分,男性属于理性动物,缔造“文化”,女性属于感性动物,遵循“自然”。男性制定规则,男尊女卑;女性服从规则,三从四德。当人的文化启蒙阳光折射到女性身上,子君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牡丹肆无忌惮放纵情欲,践行“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她们追求自我解放的路径不同,却一样破坏了男性制定的文化规则。可是由于没有改变依附者的地位,没有改变“自然”身份,所以子君“伤逝”, 牡丹只能“回家”。虽然牡丹以喜剧的形式演绎她的精彩,可是当岁月退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道德不修的傅南涛会不会再一次见异思迁呢? 女性命运端赖姣好的容颜、曼妙的身材,永远改变不了被审视被评判的屈从地位。自然身份和文化符号如影随形,性别角色和社会舞台相得益彰,这才是女性的期盼。
四、结语
就性别而言,私下以为男女同权是“二元和解”的基础。当代文化场域,女性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权权在握,鲁迅期盼的社会改良已然实现。而且现代语境激活了中国女性的觉知和省思,追求美丽的外貌、诱人的胴体、澎湃的情欲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耳闻“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之类女性告白,我们不免怀疑:这是我们要的女性解放吗?当“男人用他的权力放出钓饵,诱取女人的色相,女人用她的色相做诱饵,诱取男人的权力”[9],当色相成为资本,女人陷入身体妄自尊大、精神妄自菲薄的迷宫,身体在思想迷失的状态下横冲直撞闯红灯,危及女人的生存境遇,我们仍然怀疑:这是我们要的女性解放吗?女人如何做“女人”?貌似荒唐,却是不少当代女人茫然若失的焦虑。如果沿袭鲁迅和林语堂孰是孰非的批评模式,只会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因为在女性叙事内部,意识和物质(身体)是统一的。不存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光明与黑暗,善与恶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尊重性别平等和承认性别不同并不矛盾,身体接纳平等、独立的思想检阅,思想尊重身体真诚热情的呐喊,可以避免“人格畸形已悄然融入了女性自传”还沾沾自喜的生活悲剧。[10]就女性而言,在性别平等的文化语境中,如何认知“自我”,既涉及自然造物,也涉及文化形成。文化语境提供了选择生活方式的多元空间,人造美女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所以,在女性身上,理性之于感性,不必居高临下;身体之于思想,不必耀武扬威。 时尚“辣妈”职场风生水起,爱情水涨船高,可以说是“文化”与“自然”二元和解的生动演绎。解读文学作品,观照现实生活,这是走出“二元对立”的女性批评思路体悟的审美感受,在此见教大方之家。
[1]刘复生.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J].新华文摘,2011(7):88-92.
[2]鲁迅.我之节烈观[G]//袁勇麟.20世纪中国散文:现代读本.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3]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68-169.
[5]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172-173.
[6]林语堂.京华烟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420.
[7]林语堂.红牡丹[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8]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214.
[9]林白.致命的飞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78.
[10]芭芭拉·约翰逊.“我的怪物/我的自我”[G]//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94.
(责任编辑 马 诚)
Lu Xun and Lin Yutang:Deconstructing the Female Narrative
WU Yu-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 350108,China)
Lu Xun presented the female traged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while Lin Yutang presented the female comedy from a natural perspective.The two female narratives provide different versions of discourses for modern female literature students. Meanwhile,their generation of meaning and style of speech developed fundamentally for the female care tend to be wrongly interpreted into certain symbols for cultural privileges our of politic purposes because of the principle of binary opposition.In fact,whether women are “the cultural formation” or “the natural creation” is the inquiry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must make.It is suggested that critics should stop arguing which is better.They should cross the barrier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to find out the tracks of thoughts of the two by discourse study,do the literary d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and female physical emancipation in clash and explore the literary picture of the binary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Lu Xun;Lin Yutang;female narrative;dual reconciliation
2014-12-15
2015-04-21
吴毓鸣 (1955-),女,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女性文学。E-mail:wuwu889@sohu.com
I206.7
A
1673-4432(2015)02-0073-06
——《祝福》的文本细读与推理
——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