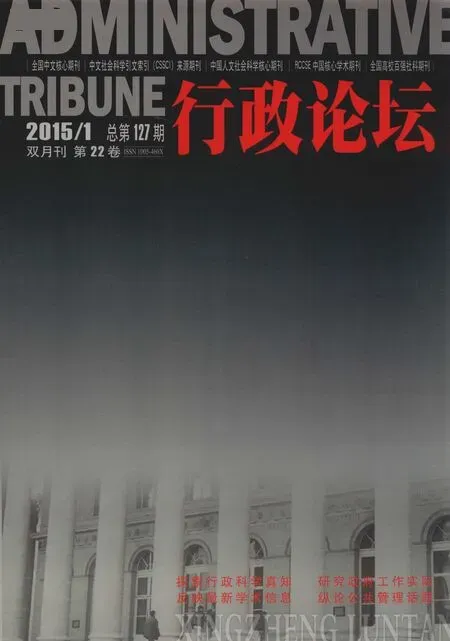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过程探析
◎韩致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871)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过程探析
◎韩致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871)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呈现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形态,是意识形态体系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相碰撞、相结合的过程,即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主体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主体与外部环境发生激烈碰撞时为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而作出调整的过程。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过程的探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体系结构特征,有助于我们掌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丰富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理论体系。
西方意识形态;媒体舆论;文化发展;公共话语
在新的冲击与挑战面前,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论从体系构成到表现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迫切需要我们对其变化的内容、结构与传播方式等方面尤其是对其变化的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解读,以追踪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变化的新趋向、新特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复合体,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是多种意识形态的集合体,在这一集合体的内部呈现了复杂的结构组合与结构文化,其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作为一个整体而发挥作用。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过程的探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体系结构特征、厘清不同构成元素之间彼此关系,有助于我们掌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脉络,研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丰富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理论体系,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激烈碰撞中取得优势,赢得未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胜利。
一、主体:自主性变化过程分析
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为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需要不断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自我调整与变革,解决发展中的困境,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之一就是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寻找新的思想支撑点,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问题与矛盾,延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大致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趋势的映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深化的集中体现。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需要主动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变革,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主性调适,目标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继续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种种变化,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基本制度的改良也将映射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意识形态体系也会主动调整去适应这种变化,为资本主义制度改良提供可行性方案,或者为其政策的出台与推行提供合法性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针对外部环境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遇到的困难与矛盾,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自主性变革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改良路径与发展方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改良方案:一是采取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进行制度改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路线进行微调整,走出一条非左非右的“第三条道路”,对内部进行调整,走出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求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二是将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制度上升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理论,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危机转嫁给外部世界,并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为这种扩张与危机转嫁提供合法性依据。
(一)“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内部自我调适的新选择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克服的矛盾。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环境与内部运行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外部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西方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也处于一个大调整时期,面临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厌倦了左与右的政治纷争,在政治生活中也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差距越来越大,产生了新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传统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受到破坏,经济增长乏力。
“第三条道路”就是冷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挑战,对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运行机制进行自我调整的尝试,是针对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线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困境,统治阶层为解决发展困境,进行社会改良的新探索。冷战结束,外部环境的演变既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也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淡化,务实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为寻求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所谓的中间道路提供了选择。90年代初,欧洲社会党认识到其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需要重新定位与调整,既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不足,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非左非右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第三条道路”是西欧左政党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反映了欧洲国家在观念形态上的“左倾化”现象。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以超越左与右为价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本价值观,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实质是左翼政党改良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其本质为改良主义,其目的是完善和发展资本主义[1]。
(二)从国家垄断迈向国际垄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扩展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自身矛盾与冲突转嫁给外部世界的企图,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鲜明特征。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滞胀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兴盛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在经济滞胀的危机困境面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无能为力。随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义理论正式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探讨拉美国家社会经济改革的研讨会上,会议抛出了经过讨论达成的十项政策,即“华盛顿共识”。这次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完成了从经济理论到国家政策,再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
“华盛顿共识”的抛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向全球的蔓延,实质上企图在全世界统一实施美国标准的自由竞争市并冠以全球化名义来确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逻辑[2]。“华盛顿共识”推出后,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正式向政治领域转移,更多地以经济发展为名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事务,以经济改革之名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改造与经济侵略,假借市场与经济发展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张与渗透,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改革,逐步弱化国家调控作用,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遭遇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东欧、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的现实与发展情况,机械照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改革模式,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成为新自由主义“三化理论”的忠实信徒,全面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与国家干预,导致社会秩序失衡,经济萧条、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初,俄罗斯实行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即“休克疗法”,这一方案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华盛顿共识”。结果俄罗斯并没走上体制转换、经济振兴之路,反而在10年经济转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危机。新自由主义在上述国家的实践结果更加证明,新自由义理论的本质是为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服务,西方将新自由主义理论由单纯的经济发展理论演化为全球规范与意识形态,主要目标是通过这种价值认同来更好地推行西方式的秩序与规则,将非西方社会统一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之中,方便其进行剥削与掠夺。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主性变化的过程中,“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展代表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不同路径——解决自身发展的方法与措施有所差别,其本质上并无分歧,最终目标都是不断改进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
二、刺激:外应性变化过程分析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在面对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的挑战,不断调整、适应,进行自主性变革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外部的重大变化与突发性事件,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严重挫折、国际政治的单极格局走向等因素,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促使其意识形态理论发生变化,以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与侵略,为其全球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托的要求,这一系列的变化可称之为外应性变化过程。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针对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解体,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剧变,从理论的本体到外延都发生了变革。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干涉主义的出台,再到9·11事件之后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演进,一直到最近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西方人的价值观与心理调整和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反思,都是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所导致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变化,这种调整带有强烈的外应性特征,并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理念与对外政策等多个方面。
(一)苏东剧变——从意识形态到历史的终结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这种外部因素的强烈刺激之下,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两大意识形态经历了数十年激烈的论战后,以一方戏剧性的解体终结了两极格局时代,无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当政者还是思想家,既有喜悦又有震撼。冷战结束后,苏东那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经济上采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强势推动的全球化也在此阶段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这些巨大的变化使资本主义自大、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已经打败与其抗衡的所有意识形态,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点,历史将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历史终结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1989年,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学者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国家利益》期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在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他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标志着“历史终结论”的正式出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主体思想是: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世界形势已经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社会制度。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3]。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主要目标是确立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垄断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历史终结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色彩[4]。首先,历史终结理论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苏东剧变并非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其次,人类社会不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选择。未来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是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二)“新干涉主义”——“一超独大”格局刺激下的新选择
“新干涉主义”是冷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新变化,西方借助冷战后对其有利的国际政治格局,依据西方价值理念与思维建构国际关系新体系。与传统的干涉主义以占领领土、掠夺资源为主不同,“新干涉主义”是基于人道或人权的理由,对其他国家实施干涉,目标是迫使被干涉国家改变国内政治的治理方式,建立西方的政治模式,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其称呼由此而得。
全球政治的“一超独大”格局是“新干涉主义”产生的强大外因。在军事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严重的失衡。苏联由一个超级大国分裂为15个独立的国家,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在大国格局中占有极大优势地位,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统治者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去统治、支配全世界,以西方资本主义行为模式改变世界的野心不断膨胀。“政治与技术方面的进展,增加了美国可能更有效地使用武力的机会。政治集团与联盟的削弱,使得(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个别国家使用武力变得容易一些了。”[5]两极格局的解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在不断下降,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其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在后冷战时代西方世界的内部需要寻求新的共同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统领其意识形态体系。而“捍卫西方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推行的普遍人权观,人权高于主权就成了维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纽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干涉主义”,使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合法化和机制化,实质上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统一世界,建立符合西方战略利益与价值观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新干涉主义”的出现带有浓重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取向意图。“新干涉主义”目标是向全世界推广其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所谓“人类共同价值观”,对违反这些原则的国家强行干涉。“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把人权与国家主权简单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否定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捍卫人道主义和西方“民主”、“人权”、“人类普通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和主权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目的,妄图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秩序[6],维护西方利益的国际意识形态。
(三)9·11事件——新帝国主义走向前台
新帝国主义论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首先提出的。2002年初,库珀发表了一篇《论“后现代国家”》的文章,分析了9·11事件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倡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即“后现代的帝国主义”。其基本观点是,当今作为后现代国家典型的西方大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要使用双重标准的理念,可以不必遵循国际法,不必经过联合国授权就动用武力[7]。新帝国主义很快被美国等西方国家上升为对外政策,走上历史前台。新帝国主义的核心是某种价值帝国主义也就是基于西方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它通过强制手段对外推行其自由与民主价值观。这一理论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是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对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掠夺与政治压迫的产物。
在意识形态的外应性变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变化呈现并暴露出其主观的乐观、自大与狂妄的心态,还有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冷战结束后,从历史终结论到新干涉主义,再到9·11后的新帝国主义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核心,以及推行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目标并未发生丝毫改变,改变的只是表达和推行价值观念的手段与方法,将传统政治理念通过新的话语形式实现转型,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霸权取得合法性的依托。
三、全球化:总体性变化过程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起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事实、一种发展过程或发展趋势,同时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全球化的视角,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变化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意在掌握意识形态变化的总体性趋势,从宏观上把握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全球化进程同步扩展,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意识形态呈现合流的迹象,经济全球化代表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全球化之初就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他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
全球化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后,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全球化发展的航标。全球化既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也为新自由主义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扩展为全球意识形态提供了机遇。新自由主义由此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强国欺骗和控制弱国的意识形态工具,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和载体。西方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全球化不断消解国家对主权的认识,以西方人权、主权观念主导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以强势的话语为全球化护航。资本的全球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权威逐渐减弱。
(二)文化全球化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
全球化在全球文化交锋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霸权。萨伊德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成了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彼此交锋。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成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8]冷战结束后,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野蛮暴力的对外扩张方式,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现代化传播手段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文化扩张。在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传播,隐蔽性更强,在传媒业的推动下传播速度更快,与经济手段的高度结合渗透力更强[9]。全球化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单向度流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理论随着商品的流动扩散到全世界,对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精神与文化层面的冲击。西方国家制造出的特定词语和理论为他们的全球扩张作辩护,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削弱和剥蚀。文化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平台,以文化产品为媒介在全球扩展。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国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通俗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使文化成为意识形态传播、扩张、侵略的重要工具。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的,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密切的联系。在全球化背后,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与民主、人权观念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发展并不同步,呈现出一个梯次渐进、彼此支撑、相互融合的过程。作为无所不包的动态过程,全球化可以跨跃民族、种族和国家的界限,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的共同体,它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包容性与意识形态的侵蚀性是显而易见的。
[1]刘启东.“第三条道路”实质解析[J].理论月刊,2003,(12):66-68.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化研究中心.全球化:时代的标识——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全球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62.
[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4.
[4]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51.
[5]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M].殷雄,徐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5.
[6]李玉峰.“新帝国主义论”研究综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5):79-83.
[7]周穗明.“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4,(3):32-37.
[8]爱德华·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J].谢少波,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4):50-55.
[9]李彦文.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J].东岳论丛,2007,(3):162-164.
(责任编辑:温美荣)
D089
A
1005-460X(2015)01-0097-04
2014-09-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与对策”(07BKS033)
韩致宁(199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生,从事国际传播及政治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