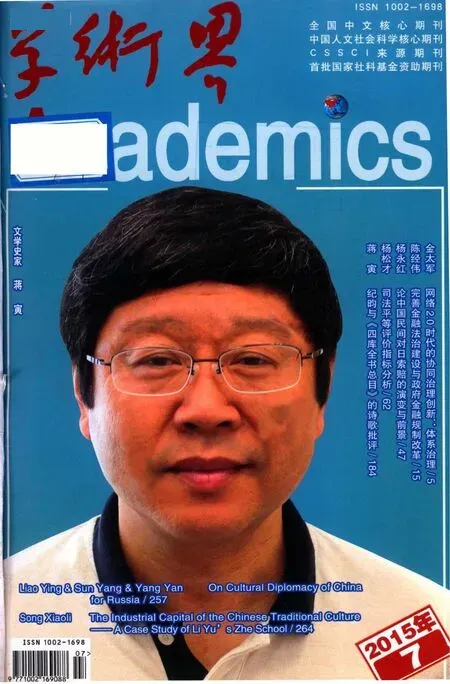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 胡作友,杨 莉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一、译介西方幽默文学作品,开启中国幽默文学的大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论语”派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因其翻译工作而为人熟知。1932年9月创刊的《论语》成为“论语”派形成的标志。《论语》初由林语堂任主编,第27期后因产权纠纷由陶亢德接任,不过林语堂仍为实际主持者。1937年8月出至第117期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6年12月复刊,1949年5月停刊,共出版177期,历时近18年。对于《论语》刊名的由来,章克标这样解释道:“……这时忽然从林语二字谐音想到了‘论语’二字。刊物的文章,总不过是论论议议,而且《论语》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是孔夫子的‘语录’,在中国真是尽人皆知的名字,用这个现成的书名做刊物的名字,号召力宣传力必定十分强大,而且又是怎样的奇特……”〔1〕《论语》与1934年4月创刊的《人间世》、1935年9月创刊的《宇宙风》一起,形成了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的热潮。与这些刊物相呼应的还有《逸经》《西风》《谈风》《宇宙风乙刊》等其他杂志。“论语”派的代表人物有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陶亢德、徐訏、老向、姚颖等。论语派是一个以提倡幽默为己任的文学流派,林语堂在《论语》杂志第1期中就明确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此后林语堂分别在《人间世》《宇宙风》的创刊词上进一步提出杂志内容“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创作宗旨。自此,“幽默”“闲适”“性灵”成为论语派的理论基础,并以小品文为主要载体。在此期间“论语”派进行了大量西学译介工作,尤其是西方幽默文学作品的翻译。“论语”派引进西方幽默文学,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创中国现代幽默文学之先河。“论语”派积极倡导幽默小品文写作,促进了现代小品文文体的生长,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园地。“论语”派译文着眼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发掘隐藏在生活琐事之下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推动了中国现代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发展。
“论语”派十分注意吸收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西学译介工作。以《论语》杂志为例,此杂志共发表翻译作品180余篇,其中翻译文章143篇、介绍类文章约40篇。题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内容涉及西方思想、文化、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其中西方幽默文学作品占了很大比重。《论语》杂志专门设立“西洋幽默”一栏译介国外幽默文学作品,发表了一大批从幽默理论到小说、散文、随笔、小幽默、漫画等的翻译作品。《论语》第12期正值萧伯纳逗留上海,《论语》半月刊借此推出“萧伯纳游华专号”,集中介绍萧伯纳及其作品。第56期更是推出了“西洋幽默专号”,第一次集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幽默文学理论及相关作品。《人间世》也从第14期开始特设“西洋杂志文”专栏。这一时期,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外幽默文学的集中介绍,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对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特殊时期,“论语”派以自由主义作家群体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面对剧烈的现实斗争,“论语”派采取中间派的立场,主张远离政治、坚持个性独立和文学自由。同样,这种中立的态度也表现在对西学的译介上。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强调对西方幽默文学理论及其作品的翻译与介绍。“论语”派提倡幽默,实际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中国虽然有新文化运动,但国人的心灵仍然苦闷,思想仍然枯燥,就是因为缺少西方的幽默精神。〔2〕林语堂在《论语》杂志的第1期中就明确了“《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墟,但吾辈非长此道,资格相差尚远。除介绍中外幽默文字以外,只求能以‘譃而不虐’四字自相规劝罢了。〔3〕”《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论语”派主要杂志上都刊登了大批外国幽默文学作品。其中,《论语》第56期“西洋幽默专号”,总共刊登了11篇外国散文和8篇外国小说的翻译作品,荟萃了莎士比亚的《人生七记》、尼采的《市场的苍蝇》、薄迎丘的《天堂捷径》、马克·吐温的《睡在床上的危险》、乔叟的《巴斯妇人的故事》以及欧·亨利的《警察有意和你开玩笑吧》等众多名家精品。林语堂在《读萧伯纳传偶识》一文中,从十几个方面对萧伯纳及其幽默思想、幽默行为进行介绍,认为“萧氏滑稽之中有至理”,“萧之幽默,在于洞达世情,看穿世故,就其矛盾,发为诙谐,人以其别具只眼,视为新奇,一读捧腹”,对萧伯纳的幽默给予充分肯定。〔4〕“论语”派对萧伯纳、莫泊桑、契诃夫、果戈里、欧·亨利、马克·吐温、毛姆、白朗宁、赛珍珠等名家优秀作品的译介,涉及英、美、法、德、西班牙、日本等数个国家。这些翻译活动对开阔国人视野,对释放当时的政治高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量西方幽默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直接影响了论语派文人的创作。他们吸收西方幽默文学的精髓,创造性地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重要基础。其中必须要提到“论语”派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幽默”一词最早出自《楚辞·九章·怀沙》中“孔静幽默”,但这里的“幽默”意谓沉寂无声,并无现代“幽默”诙谐、戏谑等意思。林语堂首先将“humor”音译成“幽默”,并且第一次真正把“幽默”当作美学概念引进中国。林语堂的《论幽默》一文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幽默观。他还以西方近代文学和表现派理论为参照,从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精神溯源出发,融袁氏三兄弟、李渔、袁枚、金圣叹等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与克罗齐、斯平加恩、笛福、司威夫特、梅瑞迪斯等西方作家的艺术理论于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幽默”“闲适”“性灵”为重要范畴的小品文理论体系。其中,“幽默”林语堂认为是一种人生观:“……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5〕“闲适”强调的是一种幽雅趣味的文人精神,即创作时态度安静平和,语气亲切自然,整体展现出作者心境上的心闲意适。“性灵”则集中体现了论语派自由主义的特征,注重的是不受内外界所缚,内部包括格套章法等,外部包括社会环境等。在一切都向政治靠近的特殊年代,小品文被左翼作家批评为只能是“小摆设”。但是林语堂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洪流中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争议的重要问题”,〔6〕都可以用小品文的笔调表现出来,而不受题材的限制。小品文的笔调也是可以用来“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论语”派对小品文的提倡推动了小品文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散文文体的成熟。庄谐并出的立意、新颖理智的妙语和自然冲淡的韵味构成“论语”派小品文幽默风格的特色。自此,“哄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论语”派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幽默风潮,从而开启了中国幽默文学发展的大门。
二、远离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论语”派翻译活动的轨迹与特点
王向远认为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翻译家翻译选题有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一是自觉服从于时代与社会需要,一是反映翻译家个性特征、审美趣味甚至一时的境遇和心情。〔7〕“论语”派坚持个性独立与自由,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远离政治,与“时代”脱离。显然,“论语”派属于后者。“论语”派十分注重日常生活的描述,他们常常能够从身边的日常事物中发掘出一些道理,能把这些日常琐事寓以文化内涵。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即表明:“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8〕“论语”派重视市民生活琐事,也是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继承。因此,在翻译选材上“论语”派多选择取自日常生活的幽默文学作品,体现出鲜明的市民文化立场和民间文学倾向。以《论语》杂志为例,故事性和话题性强的散文和小说一共有133篇,占到了译介作品总数143篇的93%。其中既有《论早起之无理》《口角》《买鸟》《中彩票》等这类对社会世相的针砭和对闲情逸致的抒写的题材,也有诸如《论中国之内战》《新爱国主义》《战云弥漫之欧洲》《今译美国独立宣言》这类针砭不抵抗政策专制统治、对国民性的探讨抑或是对官场政治病的揭露的文章。对此邵洵美有过明确的说明:“……假使间或有几篇政治意味的文章,那并不是我们对政治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对我们老百姓有切身的关系……”〔9〕在当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背景中,“论语”派沉湎于日常的生活琐事,难免显得不合时宜。但这其实也是自由知识分子在当时环境下的无奈选择,走向民间,书写市民的琐碎生活也是他们明哲保身的一种文化策略。而且从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来看,“论语”派文人对日常生活的注重也隐含着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进行批判的意味。后现代主义史学反对“宏大叙事”,认为“宏大叙事”只有在后现代主义对它的解构中才能获得自身真正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史学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为各种差异谋求与其他任何叙事平等而非更高的叙事权力。从这一角度来看,“论语”派的翻译活动具有促进历史叙述多元化的积极意义。
由于“论语”派翻译作品以幽默为主体,而且翻译选材偏重日常生活,所以其译作在语言上表现出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倾向。“论语”派文人提倡闲适笔调,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和西方是以文章内容为重而非笔调,“惟另一分法,即以笔调为主,如西人在散文中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e)是也〔10〕。”林语堂将“familiar essay”译为“闲适笔调”“闲谈体”“娓语体”。林语堂在谈到《人间世》的特点时说:“理想中之《人间世》,似乎是一种刊物,专提倡此种娓语式笔调,听人使用此种笔调,去论人间世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感,描绘人情,无所不可,且必能解放小品文笔调之范围,使谈情说理,皆足以当之,方有意义〔11〕。”“论语”派小品文这种娓语闲谈式的闲适笔调,体现在小品文自然亲切的闲谈语气、平和舒徐的叙述节奏和清新自然的口语化句法上。小到日常生活琐事,大至人生哲理,在论语派文人笔下都是娓娓道来,真诚亲切而又自然有趣。这种语言大多为平实之语,不铺张夸饰,不娇柔作态,常常在口语化的句法中见出真情真性。“论语”派这种闲适笔调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在市民阶层大受欢迎。例如郭明(邵洵美的笔名)的《碧眼儿日记》译自Gentlermn Prefer Blondes(今译为《绅士爱美人》)的第四章,该文以苏州白话译出,人物也换成了中国人陶老三,原文“用美国姨太太口调,叙述游英法奥诸国的感想,妙趣横生”。苏州方言语调平和而不失抑扬,语速适中而不失顿挫,发音方式常常给人一种低吟浅唱的感觉,与原文中的“姨太太口调”十分契合。正是“论语”派这种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文风,使之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与“论语”派在文学界广受批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市民意识与知识分子使命感的结合,一方面也是他们中西文化精神融合的文化取向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的结果〔12〕。
“论语”派翻译活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译者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识,并自觉遵从理论的指导从事翻译实践。很多“论语”派文人都对翻译理论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其中,林语堂就曾发表《论翻译》一文来阐述自己的翻译观。他提出译者应该满足三个条件以及译者的三项责任。对于翻译标准,林语堂认为是忠实、通顺和美,而诗歌翻译,林语堂认为意境第一,用字要传神。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还提出了“翻译即创作”的论断。他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的意义正是“Croce(克罗齐)所谓翻译即创作not reproduction,but production之义〔13〕”。谢天振在《译介学》一书中也这样说道:“长期以来,有些人对文学翻译存有一种误解乃至偏见,以为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语言符号的转换,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懂得一点外语,有一本双语辞典,任何人就都能从事文学翻译。他们看不到……文学翻译作品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14〕。”在当时,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十分具有先进性,对于正确认识文学翻译性质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论语”派文人还对造成文学翻译艰难的原因进行了思索,认为主要在于语言文化色彩的差异、体裁的不对等性、参考材料的欠缺和译者自身修养问题四个方面。〔15〕除此之外,“论语”派文人邵洵美的《谈翻译》、郁达夫的《说翻译和创作之类》《语及翻译》《谈翻译及其他》等都对翻译理论进行了相关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语”派文人在大量的翻译活动中总结出一定的翻译理论,又以这些翻译理论指导翻译活动。“论语”派对翻译理论的探讨推动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而且“论语”派提出的很多翻译理论思想与现代翻译观念不谋而合。
三、位处边缘,自成一体:“论语”派翻译活动的地位
“论语”派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贡献,可是这些成就却因为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而被主流翻译文学排挤到边缘位置,不为大家所重视和关注。我们研究“论语”派翻译活动的目地在于描述翻译活动的多样性,再现20世纪30年代丰富多彩的翻译历史画面,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引发新的理论思考。“论语”派的边缘地位可从多元系统理论找到答案,这又不能不涉及中国翻译史。
中国文化史上迄今为止共有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学翻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翻译高潮〔16〕。第三次翻译高潮,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20世纪的20-30年代。“论语”派翻译活动恰好处于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战乱纷争。而“论语”派提倡幽默文学和小品文,不顾当时的国情,自然招来了不少批驳之声。其中,鲁迅就曾预言幽默不会长久,“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17〕。之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论语”派被批评为“帮闲文学”,甚至论语派作家都被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走狗文人”的恶谥。在这样的情况下,“论语”派自然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其译介西学的努力也连带着被忽略了。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借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加以解释。
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建立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18〕各个系统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相互重叠,彼此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构成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之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多元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系统之间一直处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动态竞争之中。对于文学,佐哈尔认为文学多元系统由各文学多元系统组成,既包括像成人文学、原创文学这样的“高档的”或“典范的”文学形式,也包括像儿童文学或翻译文学这样“低档的”或“非典范的”文学形式。〔19〕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既占据过“主要地位”也占据过“次要地位”。〔20〕绝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文学处在次要地位,但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文学多元系统依然幼嫩;(2)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3)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中国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之中,翻译文学多数时候处于边缘位置。而五四时期,列强入侵,社会出现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弱势。之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系统崩溃,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也随之从强势变为弱势。于是翻译文学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了中心,翻译活动达到最高潮,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变革的一股原动力。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都占据着中心位置。而30年代,中国深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中。受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占据着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30年代普遍的文学期待是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人们的政治心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正是以普遍的文学期待和阅读需求的形式对文字的生成和发展起着制约和导向的作用。”〔22〕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与此同时,它又可能与其它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23〕因此,任何一个系统的转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个多元系统甚至更大的多元系统中的有关因素相联系。此时的翻译文学系统,受到与之相联系的文学多元系统这一大多元系统的影响,也是以反映社会残酷,讴歌自由和反抗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主。而“论语”派倡导的是幽默小品文,译介的也多是西方幽默文学作品,在翻译文学系统中自然处于边缘位置。之后的中国文学多元系统长期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与制约,“论语”派提倡的幽默文学被批判为“帮闲文学”,具有反动性质,导致“论语”派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1979年陈金淦发表《评“论语派”》一文,认为不应将“论语”派看成“反动的文艺派别”。这篇文章作为重新评价论语派的先声,在论语派研究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此之后,人们对于“论语”派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随着林语堂研究热潮的兴起,人们对“论语”派翻译活动的兴趣会越来越大,其自成一体的煌煌功绩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充分的认识。
四、脚踏中西文化,妙笔译介华章:“论语”派翻译活动的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提倡“幽默”“闲适”“性灵”的小品文,与时代“格格不入”,被排挤到文学的边缘地位。因此,如果我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凸显“论语”派翻译活动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时代发展的历史作用上,很可能会错失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和启示。为此,我们从当下所处的时代出发,力求解读“论语”派翻译活动的价值。我们认为,“论语”派翻译活动的研究对当前时代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强调“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的理论意义。“论语”派翻译十分重视译者的作用,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是决定翻译成败的最关键因素。林语堂提出译者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译者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技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林语堂还进一步提出了译者的三项责任,分别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译文读者的责任以及对艺术的责任。〔24〕由此可见,“译者中心”体现在微观操作层面上是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体现在宏观理性层面上是翻译伦理的“译者责任”。对于这种“译者中心”的观点不能单以译者“主体性”来作简单判定,一方面如今对翻译主体性的界定尚有分歧,另一方面即使译者具有主体性,也不表明译者一定处于中心地位并具有主导作用。这种“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实际上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对于具体的语言文字运用,更注重的是译者的整体能力。因此,提高译文质量,培养翻译人才,将越来越依靠发展译者自身的知识、智力、技能、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也越来越转向提升译者自身的技能,发掘和开发译者的翻译潜能。〔25〕这才是对译者真正的解放,也是提高译文质量和推动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论语”派“译者中心”和“译者责任”的翻译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译者培养和翻译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其二,重视读者,追求“视域融合”的实践意义。“论语”派的翻译实际上是通俗翻译的具体实践。通俗翻译是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它以其“震惊”的效果和亲和的魅力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和广阔的市场。“论语”派的通俗译本一方面内容上十分注重日常生活,往往对日常生活琐事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为每一件琐事注入某种文化内涵。然后将这种对细节的感受上升到审美的意味,从而化俗为雅,隐含着一种幽默的智慧。另一方面,“论语”派采用“娓语”体,语言上通俗易懂。正是在这亲切自然的娓娓絮语之中,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达到译者与读者的“视界融合”。“论语”派这样一种关注日常生活,并将生活艺术化的超脱态度,使处于20世纪30年代政治高压下的人们能够暂时从当下的人生境遇中超越出来,与现实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论语”派的通俗翻译文化在于它对刻板的日常生活的颠覆潜能和人类心灵的审美“救赎”。〔26〕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派的通俗翻译活动推动了我们今天的通俗翻译发展,也让我们在认识翻译艺术的功能方面有新的思考。
其三,跳出二元对立,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参考意义。“论语”派秉持稳健的文化观,理性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传统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看成一个整合的有机体,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的各个部分都是陈腐的,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的思潮。论语派作家大都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但同时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论语”派文人进行了更深入理性的思考。“论语”派跳出二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新关照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论语”派文人持有稳健的文化观,否认文化之间有优劣之分,并且采取中西文化拼合互补的方法来解决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林语堂正是以西方近代文学和表现派理论为参照,吸收克罗齐、斯平加恩、笛福、司威夫特、梅瑞迪斯等西方作家艺术理论的精华,将之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以及小品文文体相结合,建立起以“幽默”“闲适”“性灵”为中心的小品文理论体系。“论语”派这种稳健的文化观和中西拼合互补的翻译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以及处理翻译过程中的差异和冲突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其四,坚持独立思考,敢于反思主流思想的批判意义。“论语”派对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有着自己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不管是左翼文学还是自由主义文学,仍然深受文学现代性思维方式的深刻控制。对于文学的现代性,普遍认为时代的名义高于一切,对于文学的评判也往往以“时代”为标准。“论语”派文人游离于集团主义的宏大主题、徘徊于反动专制与新兴革命之间,对于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都不惜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有所乖逆,甚至抵抗和颠覆。〔27〕由此可以看出“论语”派文人对于文学的现代性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以“幽默”“闲适”“性灵”为中心,以“譃而不虐”的幽默风格和娓语闲谈的闲适笔调对功利躁进的文学现代性进行反思,对生活中的物质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反抗,重申自我和表现的自由。“论语派”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调整和横移了20世纪30年代散文的基调和主题,从意兴湍飞的激扬文字走向了对日常琐事的吟味与咀嚼。“论语”派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但这恰恰也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它本身仍然是在现代性叙事框架之内的。“论语”派文人对于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其五,引进异域之水,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意义。“论语”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将幽默的观念引进中国。“论语”汲取西方幽默文学理论之精华,与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闲适”和“性灵”相结合,建立起以“幽默”“闲适”“性灵”为主的幽默理论,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幽默文学,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体系。“论语”派大力倡导小品文写作,小品文形式自由,内容随意,是现代文学里非常自由的一种文体,更是处于散文中自由的尖端。通过“论语”派文人的实践,小品文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彻底脱离依附于杂感的形态,促使现代散文文体的成熟。“论语”派将写作的焦点移向市民的生活日常,反映了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态度。现代市民知识分子表现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从封建社会市民到现代市民,从知识分子到市民的转移。这种转移使得知识分子与市民之间的对话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式、灌输式,而是平等对话的娓语式、闲谈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倾向。“论语”派的翻译活动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五、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间徘徊:“论语”派翻译活动的反思
“论语”派活跃在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倡导以“幽默”“闲适”“性灵”为中心的小品文,同时将大量西方幽默文学作品引入中国。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下,“论语”派的幽默文学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论语”派译介西学的努力和成就也就无形中被遮蔽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倡导幽默文学的做法确实与时代相脱离,存在“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但是,其对翻译的执着,对幽默文学的呐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
反思“论语”派翻译活动的得失,恰恰关乎翻译家翻译选题的价值取向。个人价值为重,还是社会价值为重,抑或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间徘徊,这的确是翻译者,也是每个学者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论语”派的翻译活动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本文无意于评判“论语”派的功过得失,只是从当下出发,勾勒“论语”派翻译活动的基本轨迹及其特点,阐释“论语”派翻译活动的意义,从而再现20世纪30年代翻译活动的多样性,丰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希望能得出对现代翻译有益的启示,并引发新的思考。
注释:
〔1〕章克标:《林语堂》,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3月号,转引自施建伟编:《幽默大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65页。
〔2〕杨剑龙:《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00页。
〔3〕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语》1932年第1期。
〔4〕林语堂:《读萧伯纳传偶识》,《论语》1932年第1期,转引自杨剑龙:《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68页。
〔5〕林语堂:《幽默杂话》,《晨报副刊》1924年6月9日。
〔6〕林语堂:《论谈话》,《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7〕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108页。
〔8〕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年第1期。
〔9〕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第143期,转引自杨剑龙:《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79页。
〔10〕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11〕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12〕郭晓鸿:《〈论语〉杂志的文化身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17-123页。
〔13〕〔24〕林语堂:《论翻译》,《林语堂文集·孔子的幽默》,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198、184 页。
〔14〕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
〔15〕朱佳宁:《论语派翻译文学研究——以〈论语〉半月刊为中心》,西南大学2013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第43页。
〔16〕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第2-8页。
〔17〕何家干:《从讽刺到幽默》,《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7日。
〔18〕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2001年第4期,第61-70页。
〔19〕〔2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19-25页。
〔20〕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117页。
〔22〕朱晓进:《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50页。
〔23〕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5〕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29-35页。
〔26〕杨柳:《通俗翻译的“震惊”效果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精神——林语堂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第42-47页。
〔27〕吕若涵:《“论语派”研究论纲》,《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9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