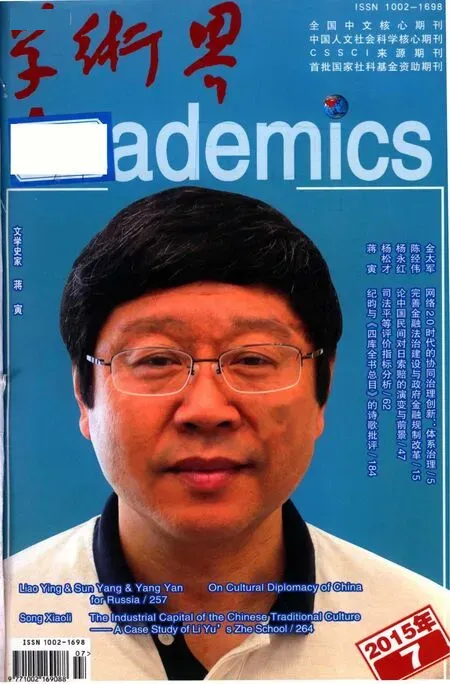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一、人文城市:从哲学意义上探寻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和永恒困境。时间问题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或“有没有时间去完成某件事”?空间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或“具备不具备做某件事的历史条件或社会土壤”?我们曾提出,中国式城市化在深层结构上是一种巨国型城市化。〔2〕“巨国”不同于“大国”。所谓大国,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国土面积”或“人口规模”或“经济体量”等某一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而“巨国”则特指像中国这样“人口多”“面积大”“经济体量大”等多重“巨量因素”叠加在一起的城市化国家。对于前者而言,或是由于发展空间大而人口数量有限,或是由于人口多但经济发展水平高,所以它们的很多问题处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对于中国则不同,由于它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因同时加入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参数而被无限放大,结果往往是每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会变得无比复杂,这就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有的“巨国效应”。巨大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异常复杂和分外曲折的根源。与以“地广人稀”为主要特征的其他大国相比,空间资源的不足和配置的不均衡,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直接的客观条件和现实背景。这也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3〕。就此而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前景,主要基于在机遇期内能否获得所需的空间资源与环境条件。但时间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如同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城市化从一开始也是在西方挟裹和胁迫下的产物,很多内在条件和客观积累都不成熟、不充分,而过快的发展速度又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也超过了城市自然环境和城市人的精神心理承受能力〔4〕,再加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过于复杂的发展环境,所以有没有充足的时间、会不会被各种突发事件(如自然环境破坏与资源缺乏、战争阴影、社会矛盾与冲突)打断或打乱,同样是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二、空间层面:资源不足已成为当下的突出矛盾
在当下,空间与土地资源已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矛盾,同时这也是一个在特殊时空条件制约下的两难问题。首先,空间与土地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无论是容纳新增人口、发展城市经济,还是解决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都需要获得更多的土地与空间。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近年来的“城市大跃进”已严重威胁到国土开发的“底线”,国家对土地与空间资源的管控正变得越来越严厉。如针对我国城市开发建设中的无序和失控日趋严重的现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则明确划定了2020年“城市空间控制在10.65万平方公里以内”的上限。另一方面,“发展缺空间”“用地缺指标”已成为各城市普遍面临的发展难题。以浙江嘉兴为例,在“十二五”时期,每年建设用地需求在3万亩以上,但省内下达计划指标仅为1万多亩〔5〕,如果这近2/3的缺口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其次,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与风险不断升级、积小成大。一方面,为了弥补用地缺口,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打擦边球”,其中最典型的是利用国土资源部2008年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所谓的“占补平衡”)做文章,如前两年以山东部分城市为代表的“农民上楼”,还有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周口“平坟”事件,结果都是弄巧成拙,影响很坏。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铤而走险。据今年3月发布的《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称,在2012年国家对460个开发区、工业园区规划及用地情况的督察中,查出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361.95万亩,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未纳入《中国开发区四至范围公告目录(2006年版)》的园区为255个,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305.55万亩〔6〕,表明各地违规非法的“圈占”问题仍十分突出。
这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两难选择:不强化土地与空间管控,18亿亩土地红线很快会被突破,城镇土地资源的粗放开发与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管控力度,被“掐紧脖子”的地方政府则会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式,继续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循环常态化。由于其手段不外乎“侵占农业用地”和“利用旧城改造”,直接损害农民或市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城市化风险越来越高。而目前最严峻的是,对此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和应对措施。
三、时间要素:一种更深层的作用机制
正如时空不可能分割一样,时间要素也是一个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深层机制。关于这一点,可以当下最大的城市空间——城市群的中西差异来了解。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7〕从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导模式得以尘埃落定。但中国城市群并不能走西方城市群的道路。根据我们的研究,中西城市群的基本差异可以“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对立来概括。西方城市群缘于戈特曼的地理学及其对自然空间如何演化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又如何演化为城市群空间的调查与跟踪。受其影响,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包括戈特曼特别重视的交通和信息,包括城市群理论的内部分歧,如大都市区强调的是空间中有农村和低城市化地区,如超级都市群概念强调的是几个城市群由于边界消失而结成一个等。由此可以得出,西方城市群理论起源于对“空间”变化的观察和研究,其在实践中遭遇的很多问题也可归结为“空间”问题,并倾向于从空间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路径。
与西方城市群不同,中国城市群在理论和现实中主要受制于“时间”要素。首先,与戈特曼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不同,我国城市群研究主要是西方理论传播和影响的产物;其次,与西方城市群主要是城市地理与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国城市群规划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是人工的规划、设计和推动。因而,在我国的城市群理论和实践中,必然更多地加入了时代特征、当下诉求等“时间性因素”,或者说,很多紧迫性、当下性的需要和愿望很容易混入并主宰我国的城市群发展。这些时间性的因素,有些符合城市群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但毋庸讳言,更多的是在违背城市群“自然历史进程”的前提下,揠苗助长、人工催化甚至是过度刺激的结果。就此而言,在我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中,如何充分照顾城市群自然成长和演化的内在规律,顺应全球都市化进程的主流趋势和基本原理,既是我国城市群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由于城市群代表了当今城市化的主流与趋势,这个问题与矛盾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层次的城市化进程中。
四、中国城市化:华丽的“窑变”与大量的“次品”
在空间资源不足和时间因素不确定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城市发展既有华丽的“窑变”,但更多的是大量的“次品”“半成品”甚至是“怪胎”,城市化的成本问题空前突出,未来的更新与重建任务艰巨。
(1)地震。该区所在的沙湾县区域上地处北天山地震带边缘,属多震区。多年来,一直被国家地震局列为重点地震监测区。据记录,该地区发生了12次以上的Ms4.0级地震,造成了塌方、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灾害。
首先,中国城市化的成绩不小。具体说来,一是传统农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2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8〕。二是传统小城镇在空间规模上的“都市化”。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9〕三是城市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层变革,即由传统政治型城市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特别是2005年以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探索城市科学规划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数以“国际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城市改弦更张,如北京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也包括更多的城市纷纷提出“生态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创新城市”等发展目标,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城市发展主流和先进城市化模式的殊途同归。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与持续发展,极大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
其次,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病的根源是城市发展过快,中国更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两会代表有关城镇化的建议和提案超过了500件,内容涉及到环境、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但从深层结构看,都可以归结为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相互冲突、相互扭曲的结果。以城市规划为例,“规划缺乏”“乱规划”和“无规划”曾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规划围着领导意志转”“规划跟着项目走”和“根据投资需要修编”,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新世纪以来,尽管城市规划意识逐渐强化,加大规划编制力度、提升规划质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基本策略和手段,但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做得太快、操之过急”,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的频繁出台为代表,中国城市规划正由“规划不足”迅速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极端。不仅未能解决过去由于“无规划”或“粗放规划”的后遗症,相反还进一步加重了城市发展在理念上的混乱、在产业结构与空间形态上的“同质化”,并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埋下更深的危机。以“鬼城”鄂尔多斯为例,因为发现了煤矿,有了钱,就把新城区做得非常豪华,且美其名曰“超前规划”,其设计者曾希望以此避免交通、住房等“城市病”。但实际上,鄂尔多斯市组建于2001年,当时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8.79%。按照一般规律,该市的城市化已开始进入慢车道,并应适当调整城市建设的规模等。但鄂尔多斯恰好相反。从2007年到2009年,该市的城市化率从70%左右提升到99.05%,总人口一直处于平缓增长状态,但其建成区面积却由30平方公里左右飙升至100平方公里,增长了2.33倍。从人口密度的角度看,鄂尔多斯最高峰值仅为102.85人/平方公里,与北京的1195人/平方公里〔10〕、上海的 3631 人/平方公里〔11〕相比,可以说根本没有建设新城新区的必要,所以鄂尔多斯成为中国鬼城毫不奇怪,也是任何辩护都掩盖不了的。〔12〕中国城市大跃进中的很多次品和废品,大都是在时间因素作用下产生的“扭曲的空间”。
针对华丽“窑变”与大量“次品”“半成品”“怪胎”并存的现实,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在战略上应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是,如何通过政策机制创新和规划布局创意,协调华丽的“少数城市”与灰头土面的“大多数”的不均衡问题,把中国大多数城市培育成具有“中产阶级”特征与功能的生产生活空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口的都市化、中小城市人才流失及村镇空心化问题。目前最严峻的是,如何改造、升级数量过多的城市“次品”或各种“城市瑕疵”,这个问题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好的。
注释:
〔1〕刘士林:《关于人文城市的几个基本问题》,《学术界》2014年第5期。
〔2〕刘士林:《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问题与启蒙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刘士林主编:《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4〕刘士林等:《城市科学理论建构与中国都市化进程》,《南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5〕《城镇化地囧调研:嘉兴两退两进一年腾退万亩工业用地》,《东方早报》,2013年3月4日A24-A25版。
〔6〕陈仁泽:《违规圈地面积近三成》,《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第7版。
〔7〕盛蓉、刘士林:《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主要形态与评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百姓蓝皮书》,《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9〕杜宇、刘媛媛:《建设部公布我国城市发展“成绩单”城市总数达661个》,新华网,2005年11月11日。
〔10〕《北京人口分布极不均衡核心区密度是涵养区109倍》,中国新闻网,2011年5月5日。
〔11〕杨群:《上海人口密度:3631人/平方公里》,《解放日报》,2011年9月24日。
〔12〕刘新静:《警惕中西部新城新区建设中的“鄂尔多斯”现象》,载于《交大城市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1期(总第7期)。
-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Analysis on Affordable Housing Financial Mechanism in USA〔*〕
- Studies on the Models of Childre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Investigating Learners’Satisfaction Towards MOOC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Western Ethics History Course〔* 〕
- A Correlational Study between Teachers’Emotional Factors and Class Interactive Teaching Efficacy〔*〕
- 早期天主教汉文小说《儒交信》论略
- 我国各时期印花税票题材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