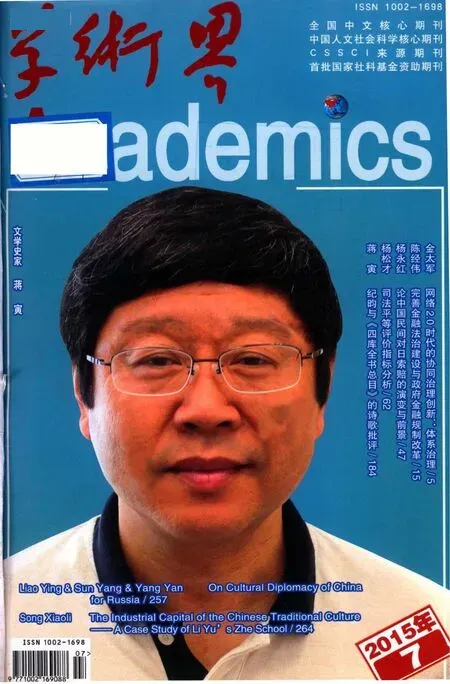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杨永红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杨永红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国家管辖豁免;强行法;属地侵权例外;国际习惯;赔偿
20年前开启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旨在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毒气战、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等暴行的受害者寻求正义,也意在向日本社会传达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促使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在日本右翼翻案之声一直喧嚣不绝、日本军国主义从未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之下,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显得尤为迫切。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兴起与演变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持续了8年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受害者在经历了20年的对日索赔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却仍然难尝胜果。虽然战争赔偿应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候解决,但是由于二战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对日和平条约的签署亦是迂回曲折,导致日本对中国受害者的赔偿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中国受害者的战争创伤至今仍难以弥补。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冷战局势渐渐明朗,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心从原来的扶植中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惩罚日本转向扶植与振兴日本。〔1〕在美国的主导下,1951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战胜国与日本签署了《与日本的和平条约》〔2〕(又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的第14条b项明确这些战胜国不仅放弃了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也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但中国未被邀参加旧金山和谈,也未签署《旧金山和约》,当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方,因此,放弃索赔条款对中国并无任何约束力。1972年9月,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称日方痛感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3〕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否也包括了中国国民个人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声明并未如《旧金山和约》一样予以明示。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化进程,中国人民的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得到提高,中国的一些战争受害者与中国学者认识到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开始探索民间对日索赔。1989年12月,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公开提出鹿岛株式会社进行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等三项要求,首开中国民间追究日本企业战争责任之先河。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花冈事件受害者11人在由日本律师组织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援助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哈尔滨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随后也在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越来越多的侵华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律师团和中国法律工作者的无偿帮助下陆续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其战争罪行给受害者带来的身体上、精神上及财产上的损失。迄今为止,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均系中国在二战中的受害平民作为索赔主体要求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本企业对在战争中因日本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的赔偿,所涉及的日本的行为均属国际罪行,其中有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屠杀平民、强征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具体包括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哈尔滨731活体实验,重庆大轰炸,永安大轰炸,花冈、京都大江山、北海道、福冈、西松、新潟等地的强征劳工,山西省慰安妇等性暴力案,共计30余件。〔4〕
2007年4月27日,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在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安妇案的判决中称,虽然原告在战争中遭受过日军和日本企业惨无人道的迫害,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5〕至此,在日本的诉讼之路已无胜诉希望。尽管如此,部分的中国受害者仍然继续在日本法院进行抗争。〔6〕同时有些受害者转向国内法院寻求正义。2012年9月10日15位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日本政府发起的索赔起诉,〔7〕2013年9月18日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在浙江省高级法院要求日方就侵华战争对其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与赔偿,〔8〕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案件均未被受理。在2014年3月18日,北京中级法院宣布对于26名强掳劳工向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提起的索赔诉讼予以立案,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9〕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日本仍坚持对受害者个人赔偿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得到了解决,更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视为是对其外交关系的威胁,〔10〕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依然任重而道远。虽然北京中级法院首次受理了中国强制劳工对日本企业的索赔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境似会有所改变,但这对于大量的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如大屠杀、大轰炸、人体实验、慰安妇等案而言仍然是前景渺茫。迄今为止,在日本的索赔无一胜诉,而那些惨案的受害者有的已含恨九泉,〔11〕尚在人世者已处于耄耋之年,对他们而言,正义的到来却似遥遥无期。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困境之根源
无疑,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入困境的原因纷繁复杂,有政治原因也有法律原因,有日本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国家的影响。但由于篇幅有限,以下仅就核心因素进行分析。
(一)日本未对二战罪行进行全面反省是根本原因
由于美国试图在亚洲扶植日本成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堡垒,迫使多数战胜国放弃索赔权,导致日本战后对其罪行清算不彻底,对战争赔偿也持消极态度。在二战结束之后,一批战犯相继进入政府,这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更不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直接导致日本对二战罪行的清算问题遗留至今,并屡遭亚洲各受害国诟病,更未能取得亚洲邻国的谅解。〔12〕虽然日本政府也有些认错行动,不能否认日本也存在能够反思战争、正视历史的和平势力,例如曾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反省战争罪行的“村山谈话”〔13〕以及反省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14〕但是在1978年10月17日,将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为代表的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在狱中或者假释后死去的14名日本甲级战犯以“昭和时代的殉难者”的名义被合祀于靖国神社,日本首相还多次对这些战争罪犯予以凭吊。〔15〕右翼政治势力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坛与民间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日本自民党的保守派政治家一直边对日本国内说日本在二战中发动的战争是场“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却同时对海外表示出接受东京审判的姿态,〔16〕这种两面派的做法直接影响到日本社会对二战罪行的反省,例如日本维新会发起的要求否定“河野谈话”的国民签名运动竟在两个月内征集到14万人的签名,〔17〕而要求继承与发展“河野谈话”的活动只得到了1600余名研究人士的赞同签名。〔18〕现日本政府右倾严重,安倍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强行参拜靖国神社,〔19〕力主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新安保法,〔20〕修改和平宪法,旨在“摆脱战后体制”。〔21〕正是由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一直影响着日本政坛,时至今日日本社会仍未能厘清战争责任,〔22〕而赔偿则意味着承认他们竭力否认的战争罪行,故日本对其行为给中国受害者带来的巨大损失根本不愿意赔偿,推卸责任成了日本政府对待战争责任的主调,这导致了通过和解来解决战争赔偿的德国模式无法推行,也造成了日本法院与其政府沆瀣一气否认中国受害者的索赔权,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屡屡碰壁的根本因素。
(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索赔权是日本否认中国民间索赔权的主要借口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不同于国家间的战争赔偿,民间战争赔偿是由加害国政府向受害国平民进行的赔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便是以中国在二战中的受害平民作为索赔主体要求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本企业对在战争中因日本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根据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即《海牙公约》)第3条关于赔偿的内容规定:“违反前述规则的条款的交战方,在损害发生时,应对损害负赔偿责任。交战方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其责任。”该条款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1条中更明确地得到了重申。这里的赔偿责任不仅包括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也包括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赔偿,二战后缔结的条约与相关实践都表明战争赔偿的内容既包括了受害国的国家损失,同时也包括了受害平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即民间损失。〔23〕因此日本无法否认其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遭受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侵害的受害平民进行赔偿,但却借口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中放弃政府对日本的索赔权包括中国受害者个人对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本企业的战争索赔权拒绝赔偿。〔24〕尽管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中放弃政府对日本的索赔权本为了维护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然而,该条款却成为日本拒绝赔偿的主要依据,日本最高法院甚至在判决中加以了认定。〔25〕与之相反,1995年3月,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尽管中国放弃了国家索赔权,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索赔权,〔26〕2007年4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2010年3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均再次明确中方的立场并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对该款的单方面解释系无效解释。〔27〕
显然,中日双方在对此条款的解释上分歧严重,难以取得共识,因此就应根据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对这一关键条款进行解释。按条约文本的通常意义来解释条约是国际法上关于条约解释的首要方法,而善意原则是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28〕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的文本含义,中国政府放弃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当然只能是政府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因为如若放弃国民的个人索赔权,应进行明示。其实日本法院也意识到这一点,承认“仅从语句来看,并没有明示(请求)的放弃对象,是否包括除国家间战争赔偿以外的请求权”〔29〕。而放弃权利应明示,特别是如此重大的利益,没有明示当然就难以确定放弃,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其次,二战后的其他条约均以明示方式表示放弃民间索赔权更是佐证。由于二战后战争赔偿已经演变为民间赔偿与政府赔偿两部分,前西德除了对相关战胜国进行赔偿外,还设立国内法对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战后日本与前苏联、韩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签署的双边条约及《旧金山和约》均区别对待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与对受害个人的赔偿。〔30〕1947年同盟国集团和意大利签署的“和平协议”也规定,意大利放弃了对德国的官方求偿和官方代表本国国民求偿的权利。〔31〕第三,现代国际法规定,国家无权放弃民间的战争索赔权。《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第148条规定:对于前条规定的有关违法行为,成员国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亦不能令其他成员免除其应承担之责任,另外的《日内瓦公约》相关条款均作了相同规定。〔32〕而国际红十字会为此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解释,即“原则上缔结和平条约时,对于战争受害者、发动战争之责任等问题,缔约国有权作出安排,但相关缔约国无权排除对战争犯罪的追究,也无权否定因违反诸项公约及追加议定书所规定的禁止行为而遭遇侵害的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权”〔33〕。而该解释也获得了国际实践的支持。如意大利政府不仅放弃了国家赔偿而且也放弃了民间赔偿,但意大利受害者仍然通过德国的赔偿立法与“纪念、责任与未来”赔偿基金会获得了赔偿,该放弃也未阻碍意大利继续代表受害者与德国的谈判,更未阻止意大利法院对索赔案进行管辖并做出胜诉判决。甚至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诉日本诉讼中,日本政府自己也主张其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的国民索赔权只是政府对国民的外交保护权,未放弃原子弹受害者个人向美国政府提出赔偿的权利。〔34〕显然该意见与其在中国政府的放弃声明上的意见完全相左,日本采取的双重标准彰显无遗。
综上所述,日本最高法院对《中日联合声明》的解释完全不符合条约的解释规则,违反了最基本的国际法则即“条约只适用于缔约国”,将《旧金山合约》扩大适用于作为非缔约国的中国,〔35〕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缔约国的战争责任不能被自己与其他国家免除的相关规定。无疑,它在2007年对“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和“山西省慰安妇案”的判决实质上以日本政府的单方解释为命题而为之,丧失了司法的独立性与公平性。这表明了日本根本不愿承担其二战罪责。
(三)国家豁免规则是中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主要法律障碍
当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抗争告败后,他们转而寻求本国法院的救济,然而国家豁免权规则阻碍着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进行管辖。虽然中国法院在受理状告日本企业的强制劳工案上没有法律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大部分案件系向日本政府索赔,国家豁免规则仍然是妨碍管辖的主要法律障碍。该规则是国际法上一个比较古老的原则,其本质上是排除管辖的一种特权,源自于国家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国际法上关于国家主权豁免范围的理论有两种,分别为传统学派的“绝对豁免主义”与后来的“限制豁免主义”。目前,国际社会已经逐渐接受限制豁免主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管辖豁免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36〕限制豁免主义将国家行为划分为事务权行为(acta jure gestionis)与统治权行为(acta jure imperii),国家对其事务权行为不享有豁免权,只对其统治权行为享有不受外国法院管辖的特权。《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豁免公约》)第一次以普遍国际公约的方式明确了限制豁免原则,但各国在国家豁免的例外上分歧明显,在限制豁免规则的具体内容上未能形成普遍接受的较完善的规范,致该公约未能实现国家限制豁免规则的统一化,它只是国家限制豁免规则进一步规范化的开始。〔37〕目前国家豁免规则仍处于一个新旧规则接替的转变期。〔38〕同时由于《联合国豁免公约》尚未生效,〔39〕故在国家豁免规则上仍是由习惯法主导。而国际习惯的形成来自于各国普遍实践的累积,〔40〕习惯法这种造法方式导致各国的司法实践在习惯法中扮演了最重要的地位。必须承认传统的国际法并不支持个人拥有在法庭上向国家索赔的诉权,尽管国家豁免规则发展了不少例外,但是战争行为被视为“统治权行为”仍继续享有国家豁免特权,导致在受害国或第三国法院提起的诉讼因国家豁免规则也难以胜诉。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意大利与希腊法院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障碍,判决数个二战受害者胜诉。希腊法院在Distomo一案中和意大利法院在Ferrini案中适用了“强行法例外”〔41〕、“属地侵权管辖例外”〔42〕等例外原则否认德国的豁免权,然而国际法院在2012年却令人失望地判决“强行法例外”、“属地侵权管辖例外”等尚未演变为排除战争索赔豁免权的国际习惯。〔43〕国际法院本应在相关法律缺失或不明确时对国际法规则进行引导与明晰,但是国际法院却未抓住机遇指引国家豁免限制规则的发展,〔44〕对国家管辖豁免的相关习惯法做出了保守解释。然而2014年10月意大利宪法法院在国家豁免权案中判定意大利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相关法案与判决违宪,进而拒绝在意大利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坚持适用“强行法例外”与“属地侵权管辖例外”对意大利的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45〕中国法院完全可借鉴意大利和希腊法院的司法实践,利用习惯法的特殊造法规则,成为引领国家豁免规则新发展的造法者,适用“强行法例外”与属地侵权管辖例外,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或可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走出困境。
三、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出路
诚然,中国受害者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历经艰辛,现仍陷于困境之中,但距离光明并不遥远,因为出路就在眼前。
(一)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进行管辖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在目前缺乏推行德国模式的前提条件和在日诉讼无望的情况下,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46〕便成为局势反转的关键,推动日本政府与民间对中国受害者的赔偿。在美国以日本企业为被告的接连不断的诉讼中,虽然美国法院驳回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同盟国军队原战俘的诉讼请求,但是这些诉讼却引来了美德两国的政府与民众对受害者的支持运动,于2000年7月德国设立了100亿马克的“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向被强制押送、强迫劳动的受害者个人进行补偿。〔47〕显然,美国法院对战争受害者的管辖对于之后开启德国主动向强制劳动者进行赔偿的进程居功至伟。
1.中国法院的管辖不仅不违反国际法而且引领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首先,虽然国际法院在国家豁免案中宣布意大利法院对对德索赔案的管辖违反了国家豁免习惯法,不少学者担心中国法院的管辖亦因此违反了国际习惯。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法院的判决并不具有判例法的效力,对国内法院亦无直接的法律拘束力,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edelline案中指出的国内法院虽需尊重国际法院的判决但却不受国际法院裁决的法律约束。〔48〕故国际法院在国家豁免案中关于国家豁免规则的解释并不对中国法院拥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不违反国际法。其次,由于通过违反旧的国际习惯法来创立新习惯法的特别造法方式使国家实践特别是法院的司法实践在国际习惯的形成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纵观国际法的发展史,习惯法这样的特殊造法规则多被西方国家利用发展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习惯,中国较少主动参加到习惯法的造法过程,多为被动地接受习惯法规则。面对中国受害者的困境,中国法院完全可以转换思路,利用国家豁免规则新旧交替的特殊局面,以参与新习惯法的造法为据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不同于意大利、希腊,中国并未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择性强制管辖权,这意味着中国法院一旦对这些案件进行裁决后,不经中国同意,国际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换言之,国际法院无权裁定中国法院裁判是否违反国际法。这无疑使中国法院处于一个发展新规则的有利地位。其三,国际法委员会曾指出关于属地侵权例外是否适用于因军事行动导致的侵权属于一个灰色地带,在属地侵权例外对军事行动的适用上各国对此的实践与立法差异明显。〔49〕国际法上的所谓灰色地带,指只要不偏离一般国际法,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立场。〔50〕换言之,在属地侵权例外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情形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在不违反一般国际法的前提下有不同的立法与实践,因此,中国法院完全可以将属地侵权例外适用于武装冲突状况。另外,“日本的关于对外国之民事管辖法案”第10条明确规定了外国不能在日本对个人的侵权损害享有国家管辖豁免,亦未规定属地侵权例外不能适用于统治权行为。〔51〕既然日本可以对外国在日本领土上的侵权行为享有管辖权,那么从对等原则出发,日本对其在别国的领土上的侵权行为也应不享有管辖豁免权。故中国法院可以依属地侵权管辖例外原则获得管辖权。其四,中国法院可依据强行法排除日本国家管辖豁免。国际法院在判决中以强行法为实体法不能排除国家豁免规则此类程序性规则的理由实属荒谬,无疑强行法优于其他所有的一般国际法,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国家管辖豁免特权会导致受害者无法通过适用强行法获得赔偿,显然二者发生了冲突,二者发生冲突后适用国家豁免规则既违反了强行法也有悖于公平正义。〔52〕因此,中国法院可明确表示,违反强行法挑战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不能享有管辖豁免权,这无疑顺应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可为中国赢得国际赞誉。其五,由于中国受害人在已经尝试了所有的救济途径其损失仍得不到弥补的情形下,中国的司法救济无疑已成为他们寻求正义的最后途径。中国法院的管辖符合国际人权诉讼的“最后救济”的条件,这表明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案的管辖建立在尊重日本主权的基础上。
随着中国综合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正在进入国际规则制定者的行列,中国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使中国能利用目前国家豁免规则所处新旧规则接替的转型期和习惯法的“不破不立”的特点进行角色转换,成为国家豁免新规则的强势造法者,提高自身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摆脱过去那种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形象。中国法院之管辖不仅不违反现行的国际法,反而引导国际法的发展方向,是维护人类良知实现公平正义之举。
2.中国法院的管辖是曝光真相的利器
众所周知,德国对纳粹历史进行的全民性的反省是真正地有效防止纳粹复活的关键。日本政府在此方面的所为可谓乏善可陈,近年来日本的右翼思潮明显占据上风,特别是安倍政府公然不顾历史地粉饰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否认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53〕他们的宣传蒙蔽了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一代。击破谎言、还真相于世人已经迫在眉睫。正如东京审判令战犯之一的重光葵震惊于南京大屠杀,在日记里写下“其惨状甚极,呜呼圣战”,“吾人只有掩面,愧死为日本人”,〔54〕中国法院对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惨案的曝光亦会震动日本人民,令其正视历史。整个过程应被全程记录,特别是强征慰安妇、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毒气战、强掳亚洲劳工等战争犯罪均未在东京审判中予以揭露和追究,〔55〕更需重视收集、保存证据,以达到重现、保存历史的目的。庭审结束后还可顺应社会舆情在惨案遗址建立纪念碑和展览馆,供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前往凭吊、铭记历史。这对于帮助日本进行全民性反省,破坏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十分必要。
3.中国法院的管辖有利于推动日本进行反思
由于法律方式的对抗性和国家地位的特殊性,在涉及国家的争端中通常只在不得已的状态下才选择它。中国一旦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势必使中日之间产生对立情绪,影响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为保护中日关系顾全大局,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避免使用对抗性的方式。但是中国政府的克制并没有换来日本正确看待二战历史,公道对待中国的受害者。日本政府反而拒不承担战争责任,一步步走向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右倾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目前,安倍政府的对外战略明确对抗中国,安倍政府展开了“地球仪外交”,拉拢非洲国家和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一些亚洲国家,妄图“围堵”中国,甚至血口喷人地暗指中国是一战前的德国,声言中国才是试图以武力挑战现有秩序的国家。〔56〕安倍通过颠倒黑白地丑化中国,为其修改宪法造势,旨在改变日本防卫力量性质,妄图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所谓“正常国家”,〔57〕其右倾化趋势十分危险,已对亚洲和平构成威胁。因此,中国不能再克制了,必须调整对日策略。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虽然会遭到日本的反对,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政府敲响警钟,更可以使中国立于道德的制高点,有利于中国团结二战中的战胜国与受害国,为共同遏制日本右倾化提供舆情与基础。同时,中国法院的管辖还可为其它受害国提供一个解决民间对日索赔的途径,或可引导其它受害国法院对类似案件进行管辖,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让日本军国主义在那些国家实施的暴行同时曝光,更大程度地促使日本进行反省,承担其战争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法院对对日索赔案进行管辖不只是一个正义之举,而且还是多赢之举,更是必须之举。不仅可以扭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困局,更重要的是能使中国高举和平大旗成为反军国主义的领导力量,而且能够推动日本正视历史承担战争责任。
(二)推行德国模式全面解决对日索赔
虽然中国法院的管辖能扭转民间对日索赔的困难局面,但是在局面扭转以后全面推行德国模式才能彻底解决民间对日索赔。实际上,由于法律手段的对抗性多会引发强制执行问题,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只有最终通过主动赔付的德国模式才能完成。德国和日本虽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但二者对待战争赔偿的态度与做法却有着天壤之别。尽管不少中日学者、律师与中国的受害者都期望日本对中国民间的赔偿能够借鉴德国对受害者个人的赔偿模式,然而由于日本对二战罪行清算不彻底,德国模式似缺乏基础的空中楼阁难以构建。但是如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迫使日本重新全面反省,推行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或可最终变成现实。
1.德国模式——以和解的方式赔付战争受害者个人的样板
德国通过与受害者所属国谈判达成协议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赔偿由德国政府主导德国民间共同参与,这样通过非讼方式对受害者个人进行积极赔付的方式被称为德国模式,也是国际法院极其推崇的解决途径。〔58〕必须强调的是,德国模式是建立在德国全面反省二战罪行的基础上全社会参与对受害者的赔偿,源于对集体责任的反省。联邦德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自我反省,谋求与邻国、被害国及被害民族和解,大多数德国人承认侵略事实,认为纳粹统治是导致战争和民族灾难的根源,承认种族迫害、大屠杀并不仅仅是纳粹政府造成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应对此负责。从政府到民间,正确对待二战历史问题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59〕在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的过程中,主动积极支付战争赔偿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德国主要通过与受害者的所属国的交流与合作,达成赔偿协议以和解的方式对受害者进行一揽子赔偿。在达成赔偿协议后,德国通过在国内立法,建立赔偿基金,规范地向受害者发放赔偿金。德国的民间赔偿不仅数额巨大,支付期限长,而且赔偿主体多,赔偿覆盖面广泛,赔偿形式灵活。自1945年以来,德国赔偿已持续近70年,至今亦未终止。德国的民间赔偿覆盖面非常广泛,覆盖了全世界几百万战争受害者。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动员德国企业参与,分期分批地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比如在2000年成立的“纪念、责任与未来”赔偿基金会中,约有6500家德国企业共同承担了15亿马克赔偿。〔60〕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放弃了对德的民间索赔权,但是德国亦未因此逃避赔偿责任。〔61〕正是德国向欧洲各国战争受害者大范围支付的赔偿,缓解了战争受害者的经济压力,抚慰了他们心灵的创伤,也使德国得到了欧洲人民的原谅,德国终于被欧洲各国接纳,并且成为引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领导者,〔62〕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勇于承担战争责任的楷模。
2.政府参与全社会动员推行德国模式
事实上,中国受害者也曾试图通过德国模式解决索赔,但未能如愿。日本福冈高级法院对强掳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的赔偿建议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通过和解的方式向受害者提供救济。〔63〕在2008年后中国的受害者开始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继续索赔,但只有少部分被强迫掳至日本的劳工通过和解获得部分赔偿。〔64〕如前所述,意大利民间对德索赔实践表明中国政府是否放弃民间赔偿权并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主要障碍,取决于日本能否如德国那样对侵略战争有深刻的反省和忏悔,只有正视历史,诚恳改错,才会主动承担赔偿责任,而赔偿的进程又会推动深入地反省。由此可见,之前德国模式在民间对日索赔上的失败毫不奇怪。
于是,推行德国模式的首要问题是要推动日本清算二战历史。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可成为推动日本全面反省的良机。在法院审理的同时,多管齐下,大力宣传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审理,传播真相。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曝光是击破谎言的有力工具,同时大造舆论攻势推动日本自我反省。今年2月27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65〕在这些纪念日开展各种活动为日本民众还原历史。当然还须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历史、曝光真相以推动日本集体反思,为德国模式的推行打下基础。其次,中国政府的介入可推动日本承担战争责任。德国模式无疑是德国与受害者所属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它通过政府间的磋商推动赔偿协议的达成。中国政府在介入民间对日索赔时须避免这样的一个误区,即“政府不宜介入中国民间索赔的民间运动”。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应高调帮助自己的国民争取赔偿,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看到希望,这不仅是顺应民心,更是行使国际法赋予国家对本国公民进行保护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的介入,让日本政府了解到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是不能逃避的义务,也能迫使日本政府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还能为全社会参与创造条件。其三,社会各界共同帮助受害者积极与日本进行磋商。尽管目前有了一些中国与日本民间组织的帮助,但远远难以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提供足够的支持,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仍然是步履维艰,资金缺乏、社会关注度不够、日本政府的抵触等阻碍着民间对日索赔的发展。事实证明对日索赔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长期的财力物力与人力的投入和正义必胜的信念,这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十分必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团体通过在美国政界的积极运作,使犹太人向德国的索赔要求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有力支持,为德国对犹太受害者的赔付提供强大的舆论攻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也应重视动员海外华人团体在海外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营造国际舆论的支持与政治支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特别应推动美国施加影响,改变日本政府将战争赔偿问题视为是对其外交关系的威胁的立场,〔66〕德国模式则推行有望。第四,在索赔的对象上不仅要针对日本政府,也要将那些在战争中受益的企业列为赔偿的承担者。无疑战争赔偿涉及的对象越多越有利于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反省罪行,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对受害者的损害予以修复与赔偿,才可能全面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而赔偿的进程又会推动日本国民更深入地反省。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推动日本全民反省,真正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三)借鉴韩国模式部分解决民间对日索赔
虽然德国模式可以全面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但是该模式取决于日本对二战罪行的全面反省。当德国模式的全面推行不具备此基础的情形下,借鉴韩国模式解决部分受害者的诉求或更具实际意义。
与中国相似,韩国民间对日索赔也经历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但从韩国受害者转向国内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后,韩国民间对日索赔困难局面有了改变。韩国也非《旧金山和约》的缔约国,韩日之间的战争赔偿由1965年6月22日的韩国与日本缔结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4个协定加以明确,其中的《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关于请求权及经济合作协定》第2条第1项规定:“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3亿美元、政府贷款2亿美元、民间贷款3亿美元以上。双方确认日韩两国和国民的财产、权利以及利益并请求权问题也已完全并获得了最终的解决。”〔67〕因此在民间索赔已经获得解决的基础上韩国受害者的对日索赔似乎应更加艰难。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韩国民众的索赔运动一直持续至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在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后,韩国民间对日索赔已出现转折。虽然韩国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均以败诉告终,但是他们的讼争在本国法院进行管辖后发生了转折。2011年8月30日,韩国宪法法院就慰安妇个人请求权问题作出判决。判决书中认定:“解决索赔权是国家的义务,政府应通过外交渠道予以解决。韩国政府在财产和索赔权争端上的不作为,侵犯了受害者的基本权利,违反了宪法。”〔68〕2012年5月24日,韩国大法院就2009年韩国广岛三菱劳工原子弹受害者在本国诉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被釜山高等法院驳回一案作出撤销原判,判令釜山高等法院重审此案,首次确认个人请求权并未因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的签署而失效。〔69〕2013年7月10日、30日,韩国首尔、釜山两地高等法院分别作出裁决,勒令三菱重工对其曾征用的韩国劳工作出赔偿。〔70〕同年11月1日,光州地方法院判决三菱重工业需向4名原告各支付1.5亿韩元的赔偿金,并向另一名已过世的原告的家属支付8千万韩元的赔偿金。〔71〕必须指出的是,韩国的这些胜诉案件均以日本企业为索赔对象绕开了国家管辖豁免规则,只能针对少部分民间对日索赔争端,这似乎对于大部分以日本政府为索赔对象的案件没有帮助,但是由于其扭转韩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被动局面,对于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已开始效仿韩国,由在二战中的强掳劳工向日本企业进行索赔,中国法院已对此类案件首次明确了管辖权。中国法院进行管辖后完全可借机从法律层面对《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进行解释,厘清政府放弃赔偿与民间索赔的关系,驳斥日本法院的荒谬逻辑,为其他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提供法律基础。因此,借用韩国模式或可扭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被动局面,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综上所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对于维护战后秩序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赔偿的过程是真相曝光与记录历史的过程,赔偿也是向曾经的战争受害者赎罪的一种方式,表示愿意反思过去的战争罪行并为此付出代价。〔72〕当德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赔偿全世界的战争受害者、企业抽出利润来安抚奴役过的劳工的时候,德国人民加深了对纳粹罪行的认识,加速去纳粹化的进程,德国的“赎罪外交”也为其赢得了赞誉,赔偿与反思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此清晰地得到了论证。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政府赔偿,日本在战后近70年来都未能完成全面反省的历史任务,因此日本承担其对中国受害平民的赔偿责任不只对于中国受害者同时也对于日本进而对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虽陷入困境,但是如果中国法院能够转换视角,适用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进行管辖,必将扭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局面。同时中国政府应积极介入,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全社会共同努力,迫使日本选择德国模式,促成受害者与日本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才可能全面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前二者皆不能进行,退而求其次的“韩国模式”最具现实意义,通过对涉事日本企业的诉讼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注释:
〔1〕乔冠华:《国际述评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15页。
〔2〕See“United Nations-Treaty Series”,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52,pp.45-150.
〔3〕《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111页。
〔4〕但不包括遗留生化毒气弹受害者的诉讼案、夏淑琴名誉权案、“中威”与“大陆”船舶赔偿纠纷案。尽管有人称“中威”案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起胜诉案例,但是由于“中威”船舶赔偿纠纷案实质上是一起发生在二战期间日本公司租用中国公司的船只的涉外商事案件。而遗留生化毒气弹的损害后果发生在战后,应依据《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予以解决,夏淑琴名誉权案亦是战后日本右翼作家的著述侵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名誉权纠纷。虽然都涉及侵华战争,特别是夏淑琴名誉权案涉及南京大屠杀且历经日本三级法院而最终获胜,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确有积极意义,但均不是在二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直接导致的侵害后果,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均不属于本文讨论的民间战争索赔的范畴。见共同社北京4月21日电:《中国表示日船被扣押只是商业纠纷案》,《参考消息》2014年4月22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终审胜诉名誉受损案》,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05/content_10770746.htm.
〔5〕2nd Petty Bench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Japan,27 April 2007,Minshu,vol.61,no.3(2007),1188;1st Petty Bench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Japan,27 April 2007,Hanrei Jihô,no.1969(2007),38.
〔6〕“Chongqing bombing victims sue”,The Japan Times,2006 年3 月31 日。
〔7〕《15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重庆起诉日本政府》,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20/c_123738052.htm.
〔8〕《杭州8旬老人状告日本政府当年烧毁其家园 索赔1.09亿》,浙江在线,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3/09/18/019602784.shtml.
〔9〕《二战劳工状告日本企业原告或达千人规模》,朝日新闻中文网,2014年3月24日,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news/AJ201403240045.
〔10〕〔日〕林望、贝濑秋彦:《中国以“历史问题”为武器 外交包围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2014年2月24 日,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china_taiwan/AJ201402240015.
〔11〕《“民间向日索赔第一人”耿谆辞世》,《新京报》2012年9月5日;《中国“慰安妇”受害作证第一人万爱花去世》,《中国青年报》2013年9月5日。
〔12〕徐志民:《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3〕《村山富市首相关于战后50年的谈话》,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33-935页。
〔14〕《慰安婦関係調査結果発表に関する河野内閣官房長官談話》,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ono.html.
〔15〕《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朝日新闻中文网,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politics_economy/AJ201312300018.
〔16〕〔日〕油井大三郎:《双重标准的战争观或令日本陷入国际孤立》,宫本茂赖采访整理,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opinion/AJ201401290004.
〔17〕《14万人签名要求否定“河野谈话”》,日本新闻网,http://www.ribenxinwen.com/html/c/201404/18-19862.html.
〔18〕《日本1600名研究者签名请愿 要求政府继承“河野谈话”》,《朝日新闻》2014年3月31日,转引自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01/c157278-24795314.html.
〔19〕〔日〕村山富市:《日本,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人民日报》2013年9月3日。
〔20〕《日本各党首将就安保法展开激辩 违宪问题成焦点》,人民网,2015年6月17日,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617/c35469-27168960.html.
〔21〕王珊:《试评析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举措》,《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9期。
〔22〕徐志民:《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3〕〔67〕管建强:《公平、正义、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律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225-226 页。
〔24〕高木喜孝:《中国战后补偿诉讼中的国际法论争点——个人请求的原则、海牙公约精神的复苏(下)》,舒雯译,《中国律师》2001年第9期。
〔25〕Masahiko Asada,Trevor Ryan,“Post-war Repar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nd Individual Claims:The Supreme Court Judgments in the Nishimatsu Construction Case and the Second Chinese‘Comfort Women'”,Case,ZJAPANR/J.JAPAN.L.,Nr./No.27(2009),p.258.
〔26〕《外电报道中国要求日本给予个人赔偿》,《参考消息》1995年7月1日;《中国政府容忍民间索赔》,《每日新闻》1995年6月24日。
〔27〕《日高院终审驳回中国慰安妇上诉 中方:日法院单方解释无效》,《解放日报》2010年3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建设”索赔诉讼案做出终审判决事答记者问》,中国外交部网站,2007 年4 月27 日,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314634.htm。
〔28〕《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国际条约集(1969-1971)》,商务印书馆,1980年;Antonio Cassese,“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8-180.
〔29〕〔35〕2nd Petty Bench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Japan,27 April 2007,Minshu,vol.61,no.3(2007),1188.
〔30〕Karen Parker and Jennifer F.Chew,“Compensation for Japan's War-Rape Victims”,Hastings Int'l& Comp.L.Rev.Vol.17:497,1994,pp.528-532;管建强:《公平、正义、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律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31〕Article 77.4 of The Peace Treaty with Italy of 1947,See Grant,John P.;J.Craig Barker,ed.(2006);“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Deskbook”,Routledge:Cavendish Publishing.p.130.
〔32〕《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31条,《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52条,《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51条。
〔33〕皮罗德等:《对1977年6月8日追加议定书之解释》第3651款,引自ICRC报告,1987年。
〔34〕高木喜孝:《战后赔偿诉讼的法律问题》,俞浪琼译,吉泽孔出版社,2005年,第13、26页。
〔36〕“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991,Document A/6/10,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1994),p.23.
〔37〕赵千喜:《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述评》,《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0日。
〔38〕Jurisdica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Germany v.Italy:Greece intervening),ICJ,No.143,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Giorgio Gaja,pp.9-12.
〔39〕The Status of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联合国网站,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mtdsg_no=III-13&chapter=3&lang=en.
〔40〕《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b,See“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July 2,2010,p.92.
〔41〕“属地侵权例外原则指外国对于其在法院地国对个人造成的人身与财产的侵权赔偿不享有豁免特权”,见《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第12条。
〔42〕强行法例外意味着由于强行法的“不可损抑”性使其具有国际法中的最高位阶地位,因此当国家违反强行法时,国家对此不享有豁免权。
〔43〕Judgment of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 Case,pp.150-5.
〔44〕Jurisdica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 Case,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Abdulqawi A.Yusuf,p.58.
〔45〕Judgment of No.238 of 2014(Italian Constitutional Court),p.14.
〔46〕由于能以日本企业为被告的对日索赔案只占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中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特指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本政府的索赔案的管辖权。
〔47〕高木喜孝:《中国战后补偿诉讼中的国际法论争点——个人请求的原则、海牙公约精神的复苏(上)》,舒雯译,《中国律师》2001年第8期。
〔48〕Medellin v.Texas,128 S.Ct.1346(2008).
〔49〕“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991,Vol.II,Part Two,United Nations(1994),p.23.
〔50〕Jurisdica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 Case,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Giorgio Gaja,p.9.
〔51〕Article 10 of the Act on the Civil Jurisdiction of Japan with respect to a Foreign State,Act No.24 of A-pril 24,2009,日本法务省网站,http://www.japaneselawtranslation.go.jp/law/detail_download/?ff=09&id=1948.
〔52〕Jurisdica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 Case,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Abdulqawi A.Yusuf,Cançado Trindade and Giorgio Gaja;辛润:《国家管辖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初探——从德国诉意大利案分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4期,第12页。
〔53〕《NHK会长为日强征慰安妇开罪》,《文汇报》2014年1月28日;《“南京”言论再起波澜》,朝日新闻中文网,2012 年5 月16 日,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news/AJ201205160073.
〔54〕〔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戦後史のなかの変容》,岩波书店,1995年,第66页。
〔55〕王希亮:《论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长期搁置的历史原因》,《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第38页。
〔56〕前川浩之、星野真三雄:《安倍提及一战前英德关系发言引争议》,朝日新闻中文网,2014年1月24 日,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politics_economy/AJ201401240061.
〔57〕《安倍急于推进“解释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朝日新闻中文网,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politics_economy/AJ201402210026.
〔58〕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 Case,p.104.
〔59〕李乐曾:《2009年对德国的意义》,《德国研究》2009年第2期。
〔60〕Manfred Grieger:“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Forms of Remembrance of National Socialist Forced Labour at the Volkswagen Plant”,Corporate Ethic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7(ed.by Walther Ch Zimmerli),pp.211-228.
〔61〕See Grant,John P.;J.Craig Barker,ed.(2006).“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Deskbook”,Routledge:Cavendish Publishing,p.130.
〔62〕孙文沛:《二战后德国赔偿问题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96页。
〔63〕王阳:《专访日本律师高桥融、犀川治:历史包袱现在不解何时解》,《京华时报》2010年5月10日。
〔64〕2009年10月,西松建设与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广岛县发电厂建设工地从事过重劳动的原中国劳工和解;2010年4月,西松建设就二战中被强掳至日本新潟县建设工地的中国劳工索赔案承认加害方的责任并作出道歉,同时以向败诉的劳工方支付1.28亿日元的条件达成和解。See Kang Jian,Arimitsu Ken and William Underwood:“Assessing the Nishimatsu Corporate Approach to Redressing Chinese Forced Labor in Wartime”,Japan,Asia 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23 Nov 2009.
〔65〕《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66〕〔美〕丹尼尔·施耐德:《东北亚的和解 战后处理美国需负起责任》,朝日新闻中文网,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opinion/AJ201311040016.
〔68〕《韩国宪法法院裁定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不作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30/c_121934262.htm.
〔69〕The Asahi Shimbun(朝日新闻英文网):“S.Korean Supreme Court rules in favor of forced laborers”,http://ajw.asahi.com/article/asia/korean_peninsula/AJ201205250048.
〔70〕《韩国法院判决日企赔偿二战劳工》,朝日新闻中文网,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news/AJ201307110033.
〔71〕《韩国法院命令三菱重工对二战女工做出赔偿》,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1-01/5455520.shtml.
〔72〕〔德〕康纳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44页。
China Civil Claims Against Japan:Evolution and Prospects
Yang Yongh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Law
After the Chinese war victim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have lost all lawsuits in Japanese Courts,the German model is highly recommended as a successful solution for them.However,as Japanese government dominant by Japanese right wing now tries to tamper with the history of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consequently,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o get the German model done.Chinese war victims have to search Justice before Chinese Courts and this is their final resort.Currently,the traditional immunity rules are facing transform.So it is a good chance for Chinese courts to make international laws an influential lawmaker.Chinese courts shall establish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hese cases in terms of state immunity exception rules as Italian and Greek courts did.The trials may not only repair the loss of Chinese war victim,but also make China as an influential lawmaker.More important,they can be a strong propaganda to tell Chinese,Japanese and other people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n Second World War.They can be explored effectively against attempt of distortion of the history from Japanese extremelism since the facts always beat big words.It is time to take action for Chinese courts.
state jurisdiction immunity;Jus Cogens;territorial tort doctrine;international custom;compensation
杨永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法、欧盟法。
嘉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