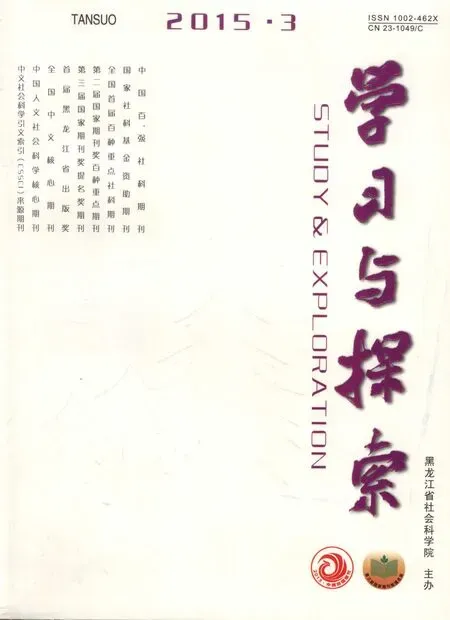论大众文化的“自治”
李 进 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论大众文化的“自治”
李 进 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自治,原是大众文化奢求之事,因为大众文化对文学有着较多依赖,接受着文学家与批评家的监督;文学则享有自治,并依靠自治而批判社会。今天强大的大众文化摆脱了对文学的依赖,建立起自治的王国——景观世界,但这种自治是虚假的,因为大众文化堕落为经济与政治的奴仆,丧失了揭露真理性内容的自由。自治的大众文化变得更可怕,它拥有更多的拥趸与辩护者,引发重写艺术的浪潮,具备更强的愚人功能。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文学;自治(autonomy)
自治(autonomy)原本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无缘,大众文化的前身——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对文学依赖较多,分担着文学的责任,承受着文学家和批评家的道德监督。但是随着电视、网络等的崛起,大众文化建立起自治王国——景观世界,它只要随意复制与拼凑一些内部资源,就能够制作出讨人喜爱的产品,轻松赚得盆满钵溢。摆脱了对文学的依赖与外在监督之后,大众文化看似无比自由,其实却陷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束缚中,即它的自治是虚假的自治。此时,大众文化无须在意他人的批判,它竭尽所能讨好大众,肆意愚弄大众,在不断更新愚弄手段与伎俩的过程中,它获得更大的自治空间,俘获了更多受众,赢得了更多辩护者。
一
历时地看,自治曾是文学的特权,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社会的体现,而大众文化只能奢望自治。阿多诺曾将艺术分为自治艺术(autonomous art)与依赖艺术(dependent art)。“自治艺术”立足于社会基础但保持一定独立性,它兼备自治性与社会性,自治性是这种艺术拥有自我法则的体现与保证;社会性则是自治艺术对其社会功能的实施,不过这种功能并非维护社会,而是对它的批判与反思,即这种社会性是“反”社会的。“通过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艺术变成社会性的,并且它只有作为自治艺术,也才拥有这种位置”[1]。为此,阿多诺强调“艺术是社会的反题”,并且这种否定是有的放矢的,“艺术的反社会性是对某个确定社会的否定”。“依赖艺术”则依靠技术而生,受制于经济与政治,是一种经济手段或政治工具。阿多诺认为电影就是一种依赖艺术,它无法享有像文学一样的批判性自治,电影以及大众文化只是商品的奴仆和政治的玩偶。
那么,文学因何能够自治呢?首先,文学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较少,具有较大自主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比较疏远,文学的自主性大于其他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漂浮于上层建筑的顶端,距经济基础有所疏隔,被一系列中间环节所阻滞而变得模糊,它只能通过诸多中介因素,间接地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2]184。因此,文学与经济并不完全同步,于是出现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如希腊神话并不逊色于当代艺术,第三世界的文学能够与第一世界的文学相媲美等等。其次,审美形式给予文学以自治的支持。有别于政治手册和历史书籍,文学有意识地加工着现实,如马尔库塞所言,文学将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内容转化为一些自足体——诗歌、戏剧和小说。这就是审美形式的功绩,通过重组语言,文学以自我方式凸显着现实本质,或批判现实、或嘲笑权威,无须复制现实,更不会违心歌颂社会。享有自治的文学并没有作茧自缚、孤芳自赏,而是更有力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只有作为自治作品的时候,艺术作品才能获得政治意义”。后来詹姆逊将自治修改为“半自治”,更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相比之下,大众文化则是逐利的贪婪之物,始于算计、终于计算;它也是高效的政治工具,统治者利用大众对肤浅娱乐的痴迷,悄然地将意识形态灌输到他们头脑中。换句话说,大众文化似乎拥有自治的工具,如广播传播技术、电影图像这些类似文学的审美形式,而传播与图像恰恰成为经济与政治实施控制的途径。所以,大众文化无法享有文学式的自治,它囚禁于经济和政治的牢笼中却自得其乐。不过,文学的自治绝不等同于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相反,自治暗含着责任和使命,它规定了文学的身份与职责。那么,文学的身份为何?单就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文学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让人们看清自己的处境。如莎士比亚所言,文学“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2]221。这种镜子角色是文学勇于承担的,文学家秉承良心无畏地呈现民众不敢说的真相,揭露民众看不到的真理,使他们明白身处何境,避免浑浑噩噩地生活。为此,列宁赞扬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异常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这场革命的力量和弱点”[2]325。当然,文学绝非像自然主义那样事无巨细地记录现实,而是积极地以审美形式书写着现实,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哈姆雷特》就是一个典范。至于责任,文学担负着给予人以幸福的重任。司汤达说:“艺术是幸福的许诺。”何谓幸福(happiness)?马尔库塞认为幸福即自由,自由幸福的人身心愉悦,这是卢卡奇肯定古希腊人是完美的缘由。反之,思想压抑的人绝非幸福的人,如被神学禁锢的中世纪的人。所以,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体现为复活人的感知与陶冶人的情操,使人体会到久违的幸福。幸福不分地域与肤色,文学要救赎“全世界受苦的人”。虽然自治的文学不受外力约束,但是它自己承揽了拯救所有受苦人的重任,萨特因有如此胸襟而赢得“世纪良心”的美誉。幸福也是一种持久的、内在的快乐。文学应给人难以忘却的快乐、沁人心脾的愉悦,从而渐渐渗透至人的心灵,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可见,自治的文学既没有放浪形骸,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自我规定了诸多责任,如揭露现实、救赎苦难的人,这些责任沉淀为文学的禁忌,所有作品都必须担负这些责任,所区分的只是责任多少、大小而已。而大众文化,无论是原初的低俗戏剧还是后起的电影,都是逐利之物,受制且沉迷于金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又异化为政治的工具,如苏联与德国的电影,所以大众文化难以拥有文学式自治。况且令大众文化难堪的是,它需要依赖文学,谨守文学的禁忌,接受文学家与批评家监督。具体而言,首先,文学曾是大众文化取之不竭的宝藏,后者分担着文学的责任。自电影显现感官的震惊效果之后,它便迅速俘虏诸多大众,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它的货源奇缺,此时丰厚的文学作品成为它的救命稻草,文学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内容与思想值得信赖。所以改编文学成为初期电影的生存之道,甚至今天的电影也没有完全丢弃这种生存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保证电影品格,也能预先确定一些受众,这些人原是被改编的作品的读者。当然,改编对文学不无裨益,一些作品因此重生,继续播撒思想的种子。本雅明赞成冈斯的形象描述:所有传奇、神话和历史都在影院门口排队,等待在银幕上复活。虽然这种复活不是文学意义上的重生,但是作品的精髓并未丢弃,其镜子作用依旧存在——揭露社会、启迪民众。其次,文学曾是大众文化的监督者,是后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大众文化诞生初期,它与文学的地位有天壤之别,文学自文艺复兴起便主导着人们的精神,文学家掌握着较多话语权,尤其在1750年的英国,作家更是一种体面职业。其后,大众文化(包括报刊、广播和电影)都需要接受文学家与批评家的道德监督,他们绝非无事生非,主要是把握大众文化的品格,审查它对大众的想象和思想有何不良影响。比如一些学者借助《爱丁堡评论》批评报刊文学削弱大众的想象力,暗含“愚人”(蒲柏语)功能。也就是说,因依赖文学,大众文化无形中接受着文学的责任;因处于文学的时代,大众文化需要接纳外在的监督,文学如“达摩克利斯之剑”,督促逐利的大众文化不要忘记一些责任。
可以说,文学给予大众文化以较高品格,并束缚着它的物欲。这对大众是幸福的,他们能从大众文化中兼得娱乐和审美教育;但对贪欲与日俱增的大众文化却是痛苦的,它需要摆脱文学约束,拥有自治。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出现,大众文化的势力骤增,它确立了景观王国,实现了自治,从此它无须顾忌文学的批评,可以随心所欲地逐利。不过,这种畅快的自治并非真正自治,因为大众文化完全蜕变为经济和政治的囚徒,丧失了揭示真理性内容的权利,这是一种虚假的自治。
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大众文化的自治,主要指它摆脱对文学依赖、免受文学家与批评家监督,建立自我王国——景观世界。当然,今日大众文化改编文学作品是它主动获取生存契机的表现,而非以前被动的、依赖的行为。
第一,通过明确立身之本,大众文化走出对文学的依赖。大众文化的前身——通俗文化发迹于娱乐,通过制造肤浅的娱乐,一些剧院赚得盆满钵溢。为此,歌德批判那些为获得报酬而写作的作家“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绝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尔后,报刊也借助娱乐原则,在18世纪中叶达到鼎盛阶段;最初的电影在改编文学作品时,也适时地加入了娱乐成分。也就是说,此时的大众文化已知晓娱乐是其安身的基础,但是因无法撼动文学的权威性,它便不能肆意妄为。而且电影尚未掌握如何娱乐的秘诀,所以大众文化踟蹰而行、左顾右盼。随着世俗社会的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对娱乐需求巨大,大众文化于是发现了成功的捷径——提供娱乐、悉心服务,无须道德和思想。于是它不再劳神求助于文学,而是本着娱乐原则,简单地制作、重复式制造,而观众只需接受娱乐即可,不必费心想象与思考。“庸俗艺术宣称除了金钱之外,对消费者无所要求,甚至不费时间”[3]。在赢得无数受众的喜爱之后,大众文化更是明确了立身之本——制造娱乐、尽心服务,大众文化随意抓取一些碎片就制造出娱乐作品、轻松骗取受众的好感,所以它不再依赖文学资源,也淡化了文学的责任,更漠视外在的批评。
第二,借助内部力量,大众文化缔造了自治王国。在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文学的地位相应下降,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大众文化不断增添新成员,迅速地扩张势力范围,尤其是电视这个“羞涩巨人”使大众文化渗透到寻常百姓家,其将悉心服务运用得淋漓尽致。对大众而言,大众文化带来双重舒心的服务。首先,可以轻松地观看图像,无须苦读文学作品。于是他们沉迷于图像之美,比如电影,“它具有典型的现代性;为人所喜闻乐见;诗情与神秘感、色情与道德存于一体”[4]。其次,能够足不出户就可享受服务,免除了购书的舟车劳顿。结果一些人患上电视依赖症,为光怪陆离的影像折服,他们模仿影像,从中获取所谓的生命体验。当影像不再可有可无而被奉为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它们转而成为大众的主宰者,控制着他们的行为与精神。此时,大众文化只需控制大众即可,无须在意文学家的愤怒和批评,最终它缔造出自治王国。在此王国中,景观之间相互聚合,形成内爆,使大众文化拥有更大自足性。如德波所忧:无处不在的景观已僭越现实的地位,成为大众的知识和思想的来源,而大众情愿受其支配与愚弄。
那么,自治的大众文化具有哪些表现方式呢?第一,自我衍生,苟且偷生。相较而言,文学追求原创而羞于重复,大众文化则乐此不疲地重复,毫不在意他人的批判和指责。它的一种固定配方就是由“成功作品”无限地衍生出相关作品,如狗尾续貂的续集,令人厌烦的是今日高踞票房前列的电影中总是不乏这类衍生品。对于文学家,几乎每部作品都是呕心沥血之作,讲述一个精巧完整的故事,所以他们羞于“貂不足,狗尾续”的做法,鄙视这种肤浅的、自我否定的行为。因此,以往的经典拒绝衍生品,即使有好事者与投机者炮制了这类作品,但它们与原作相形见绌,难登大雅之堂,如《西游记》的续集《后西游记》。而某些文化产品因利润蒙蔽了眼睛,因自治而漠视外在的批判,在衍生中苟且偷生,直至被人彻底厌弃。第二,相互攀缘,结成同盟。文学与大众文化存在着互惠关系,文学给予影视以优质资源,影视改编则赋予文学作品以二次生命,在互惠中,作品的精髓与责任基本上没有丢失。随着大众文化的成长,它的成员学会相互攀援,如由电影扩充为电视剧、或把电视剧缩小成电影。这都是偷巧的伎俩,改编者只需为某个影视作品换上新服饰,就制造出一个新作品。其实新作与旧作貌离神合,它们仅仅依靠不同服装欺骗大众眼睛,新作带来的仍是原本那些微弱意义,但由于大众无法或无意辨识这种伎俩,结果大众文化掌握了一种新的自治方法,进一步疏离与文学的关系。第三,碎片重组,自创生机。景观王国中充斥着影像碎片,投机者以一条不严密的线索拼凑一些碎片,组成一个貌似崇高的故事,这种作品是“瞎眼的雕像”——有躯体但没有魂灵。拼凑的作品曾因新异性、娱乐性,赢得一些观众的喜爱,但是其嬉闹的态度、松散的结构使其自毁长城,其毫不掩饰的愚人目的令人备感侮辱。不过,观众很快又坠入拼凑作品的陷阱中,因为自治的大众文化创造性地使用了拼凑方法,如《复仇者联盟》 通过择取几个娱乐英雄,然后以好莱坞最有效的配方——救世情结烹制,最后制造出一个眩人耳目、酣畅淋漓的娱乐大片。这类拼凑作品之所以能掩人耳目,是因为它的态度严谨、结构完整,但它与嬉闹的拼凑作品并无质的差异,它们都寄生于一些文化产品中,拼贴出毫无历史感和现实性的虚幻之作。可怕的是,凭此伎俩,大众文化获得更大的自治信心,它只需严谨地使用自我王国的资源就能俘虏更多大众、扩大王国的疆域。
自治的大众文化咄咄逼人,它也如自治的文学一样自由行事,似乎是一个胜利者,其拥趸越来越多、版图越来越大,很多辩护者为其摇旗呐喊、积极正名。不过,究其本质,大众文化的自治只是一种“虚假”的自治。文学的自治是为了更有效地批判和反思社会,而其反对社会则是为了获得更高级的自治;但大众文化在享有自治的那一刻,恰恰是失去自由的开始,它沦落为经济和政治的工具,丧失了言说真相、揭示真理的自由,这种自由曾由文学赋予。比如今天走俏的戏仿(parody)与拼凑之作无不是无本之木、毫无现实意义,只为娱乐和欺骗大众,赚取他们钱财而已。而把盈利作为宗旨之后,大众文化就完全被人视作商品运作,盈利成为它最大目的与最有效的检验标准,艺术性与道德水准遭到放逐。难言艺术性的大众文化,其道德水准也令人不敢苟同,其商品的本性驱使它异常在乎观众这个消费者的态度。为此,它卑躬屈膝,极尽讨好大众之能事,使娱乐越来越肤浅化、低俗化。比较地看,与文学联姻时的大众文化虽然不能自治,但它尚可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自主选择,“早期的流行文化在其社会意识形态与消费者所生存的现实社会状况之间保持着平衡。这有可能使18世纪的流行和严肃艺术的界限比今天还要流畅。”[5]但自治后的大众文化完全蜕变为摇钱树,成为经济模式的产品,难以拥有艺术这种清白之身,即使有人(如詹姆逊)竭力为其争取,所得到的仅是低等艺术的尴尬身份。获得虚假自治的大众文化推卸了文学曾传递的责任——批判社会、反思人性,但是它绝非一个脱离政治的闲云野鹤,实质上它暗含政治功能——通过简化大众的想象力和思想,将他们异化为逆来顺受的奴仆。这就是阿多诺与洛文塔尔所言的社会水泥(cement)与腻子(putty)的角色。大众文化在娱乐大众的同时降低着大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无力又无意反抗压制和统治,即大众文化就是辅助统治者的一个帮凶。另外,持续扩张的大众文化还隐含着更可怕的政治功能——文化同化,就是一种强势的大众文化侵蚀与吞噬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在域外建立起自己的飞地,使全球许多人转化为它的受众,这便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
三
对于大众文化的自治,文学信徒心情沉重。一方面,大众文化与文学存在着利害关系,前者的兴起某种程度上建立在蚕食文学领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越强大,被愚弄的人就越多,受愚弄程度也越深。这两方面都导致文学信徒仇恨大众文化,不同的是,一者是私仇,一者是无私的人文关怀。而多数文学信徒就是因大众文化的愚人特性而投出批判之矛,可贵的是,像波兹曼这样的媒介理论家也加入批判之列。这些批判者绝非杞人忧天,自治的大众文化如一头贪婪怪兽,吞噬着一切,迷惑着大众,混淆着价值判断。
具体而言,第一,大众文化独自培育着拥趸,赢得了更多辩护者。以前的影视爱好者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幼时耳濡目染文学,他们心目中不同程度矗立着一个文学标准,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影视作品,即使他们感喟这些影像之神奇,也不会陷入迷狂中。因此雷蒙德·威廉斯与霍加特虽然给予大众文化以极大肯定——普及知识、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是矢志不渝的。霍加特说:“简言之,我珍重文学,因为在文学里,人以他们所能掌握的全部弱点、诚实和洞察来看生活……并且通过跟语言的一种独特关系,把他们的洞察加以戏剧化。”[6]霍加特甚至强调:只有懂得文学的人,才能评价大众文化。就是说,以往大众文化的拥趸是由文学与大众文化共同培养的,他们能够发现大众文化的丑陋之处,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但是随着大众文化崛起与文学衰微,加之电视与网络服务到家,许多人是吮吸影像的奶水成长的,他们对大众文化带有先天温情,只看到它的长处,并拒绝他人对它恶语中伤。这些受众习惯于大众文化的给予方式,他们无须想象和思考就可“笼天地于域内”,而对召唤他们思考的文学存有畏难情绪。为此,他们选择逃避文学,这是文学受众锐减的一个主要缘由。基于此,希利斯·米勒忧虑地指出:信息技术从根本上威胁着文学,年轻人喜爱简单轻松的影像产品,畏惧深刻复杂的文学作品,而且这已成为社会习俗,体现出合理性,这对遭遇多种困难的文学无疑是雪上加霜。相反,囿于景观王国的人陶醉于炫目的景观、广博的知识、贴心的服务,坚信大众文化就是良师益友,强烈反对他人批判这个可信赖之物。可以说,随着大众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凸显自治性,它培育的支持者越多、为其辩护的声势就越浩大。有意思的是,大众文化一直生活于争议中,其批判者络绎不绝,但为其辩护者从未绝迹,比如蒙田肯定消遣的必要性,本雅明认可其解放功能,伯明翰学派赞美它给予民众多种帮助。今日为其辩护声亦不绝于耳,“理解”(understanding)它的人层出不穷,如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文化延伸了人的感知范围,增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约翰·菲斯克相信通俗文化是大众施展民主意识的场所,是宏观革命的试验地。无疑,这些辩护为大众文化招揽了新受众,拓展着它的势力范围。
第二,大众文化动摇了一些人的艺术观,引发重写艺术与美学的浪潮。对于现代性,艺术曾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其突破宗教禁忌、探知未知领域、鼓励人们运用才智。为此,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的,它与自由和理性休戚相关。“我们出于正当的理由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7]。康德认为快适的艺术以单纯享受为目的,从无思考的意向,也无长远打算,而美的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把反思判断力、而不是把感官感觉作为准绳的艺术”。可见,娱乐作品虽属于艺术,但身份并不高贵,无法与美的艺术相比肩。进入20世纪后,电影壮大了大众文化的力量,但是受极权主义(如希特勒)的控制,电影变异为愚弄人的政治工具,结果招致理论家的口诛笔伐,大众文化背负了巨大恶名。但是拥有自治后,大众文化将其悉心照顾普及到每个受众身上,让他们都感觉到它的和蔼可亲;它本着娱乐原则包容着一切,让人们从中看到思想、民主意识等积极因素。这些举措引发一些人的同情,他们置疑旧的艺术观,希望消除大众文化的恶名,树立积极形象,为此他们掀起一股重写艺术或美学的浪潮。这里的重写体现为两种形态:消除既有的成见,恢复大众文化的艺术身份;扩大艺术边界,赋予大众文化以艺术身份。第一种主要通过证明大众文化富有积极性来消除人们对它的偏见,而自然地恢复它的艺术身份。例如詹姆逊并不回避大众文化的物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功能,但也肯定它的乌托邦特性——向往集体生活,强调团结,这种乌托邦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种批判与想象功能是艺术必备的,所以兼备这两种功能的大众文化自然也位于艺术之列,只不过它是低等艺术而已。洛文塔尔也持类似观点,“文学中包含有两种强有力的文化合成物,其一是艺术,其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8]。他将商品文化(如通俗文化)视作一种文学,因为它也是个体对社会的一种体验,而且其娱乐性也非毒药。第二种主要借助为艺术界定一种宽泛的定义而将大众文化吸纳其中。例如在《超越美学》中,卡罗尔指出艺术是一种叙事方式,而低俗小说是一种程式化的叙事方式,程式化可以训练读者的解释能力,使其从解释中获得愉悦。韦尔施则敞开艺术大门,将电子作品与影像产品收容其中,“你应当能够享受旅行在不同电子世界之中的快感,但不仅仅是在电子世界,同样也在其他的世界里”[9]。有意思的是,他们著作的名字分别为:beyondAesthetics与GrenzgangederAsthetik[10],都以一种开放姿态对待新事物,合时宜地赋予大众文化一种较尊贵的身份。
第三,大众文化愚弄人的手段更高超,影响更深远。自治后,大众文化犹如脱缰的野马,不计道德与责任,醉心于如何更有效地愚弄人。一方面,它不断借助新媒介拓展势力范围。媒介是大众文化的福星,从报纸到影视再到网络以及手机,大众文化经历纸质——电子——信息等媒介的变迁,每种媒介都为大众文化开拓了新空间。而具有革命性的是电子媒介,如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占据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大众文化拥有与文学分庭抗礼的实力,甚至其势力超过文学。可怕的是,信息技术在加剧控制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还非常规地为大众文化拓展新空间,比如手机在为人们提供无微不至的娱乐服务的同时,悄然地将大众文化推至无处不在的境地,甚至最隐蔽的场所。另一方面,通过新的叙事方式,稳定旧的受众、俘虏新的支持者。作为一种商品,大众文化始终将取悦大众作为宗旨,为此它不断创新着叙事方式,希望借助新服饰迷惑大众视线,骗取他们信任。例如它通过自我衍生,制作出子虚乌有的前传与续集,满足大众对前因后果的好奇;依靠相互攀缘,以相异形式重复相同内容,如卡罗尔所言给予大众辨识细节差异的成就感;凭借戏仿和拼凑的手法,戏谑一些崇高人物和经典作品,迎合大众解构权威的心愿;选取内部的优质资源生产出娱乐作品,同时为所选取的作品带来二次生命,例如要想看懂《复仇者联盟》就需要按图索骥,观看《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相关作品。依仗这些叙事方式的合力,大众文化扩充了受众阵营,既扩大了受众的年龄范围、种族数量,也突破了地域界限、文化差异,更多人尊奉它为知识与精神的源泉,它也由此拥有更多愚弄对象。此时,它的愚人效果更令人担忧!首先,它取消了自然差异,修改人类的特征。在大众文化的王国中,不同年龄的人都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儿童与成人共享同一作品,其实这种貌似公正中隐藏着抹除自然差异的阴谋。如波兹曼担忧:取消年龄界限会导致童年这个人类必经阶段消失,致使儿童成人化,童真、可爱等词语将仅存于人类记忆中,世界充斥着少年老成的儿童,真不知这对人类是福是祸?其次,抹除文化差异,塑造同一面孔的人。经过几千年文明的洗礼,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是创造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文学虽提倡世界性,但前提是独特的民族文化,大众文化则试图将全世界过滤,而过滤最严重的后果是某种强势文化垄断天下,其他文化唯其马首是瞻。目前,美国文化借助发达的传播技术与物美价廉的优势,俨然是世界霸主,布道着其意识形态,培育着效仿者,“通过直接的经济控制以及间接的贸易和外国的仿效,传播已经成为美国世界权力扩张的决定性因素。”[11]
当前,随着文化转向在全球蔓延,大众文化已进化为一个“星丛”——包含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各国竞相发展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而当它们备受重视的同时,人们更需要警惕其愚弄人之功能,因为它们想要愚弄的是整个人类,并且手段更隐蔽、更多样。
[1] ADORNO.Aesthetic Theor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225.
[2] 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C]//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5.
[4] 桑塔格.沉默的美学[M].黄梅,等,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74.
[5] 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M].London:Routledge,1991:162.
[6] 霍加特.我为什么珍重文学[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1).
[7]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6.
[8] 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M].甘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9] 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杨,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17.
[10] 姚文放.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J].江海学刊,2012,(1).
[11] 席勒 赫.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6.
[责任编辑:修 磊]
2014-12-13
李进书(1972—),男,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从事文化理论研究。
I0
A
1002-462X(2015)03-01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