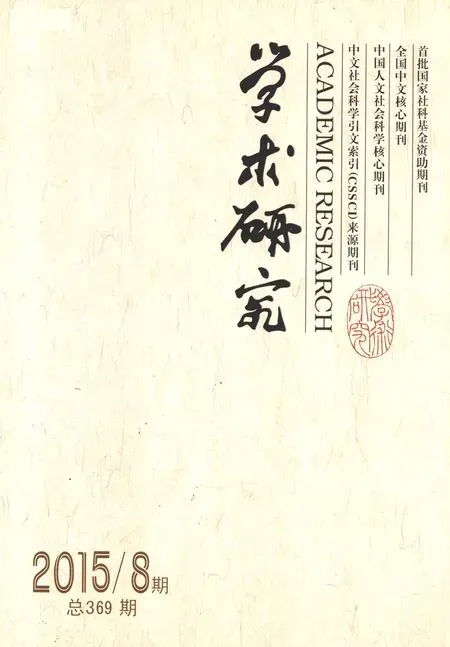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限制的现状考察与司法适用
李娟
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限制的现状考察与司法适用
李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其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刑最高刑配置了死刑。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比例高居不下,这与当前国际社会限制及废止死刑适用的潮流以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相悖。本文考察了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反思了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适用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我国立法尚未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现阶段,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准确适用毒品犯罪死刑相关法律规定、扩大死缓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控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以及充分利用财产刑替代死刑等司法手段,以减少和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毒品犯罪 死刑限制 现状考察 司法适用
一、引言
毒品犯罪不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罪行已被国际公约确认。1976年生效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罪行的惩罚”。而 “最严重的罪行”按照 《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84年第50号决议)所阐述的,是指有致死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此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监督机构更是多次强调 “毒品犯罪并不符合最严重罪行的门槛……因而,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等于违反人的生命权”。[1]然而,该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自我国1982年对毒品犯罪引入死刑以来,毒品犯罪便被视为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0928件,同比增长16.47%;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56125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7462人,重刑率为31.11%,高出当年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4.81%。可见,我国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比例高居各类犯罪之首。毒品犯罪属于非暴力犯罪,与暴力犯罪相比,对之配置死刑显失公允。尽管在国际社会大力呼吁各国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的趋势下,我国在2011年通过 《刑法修正案 (八)》废除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毒品犯罪作为典型的非暴力犯罪却仍然保留了死刑的配置。另外,毒品犯罪属于无被害人犯罪,对之配置死刑也缺乏判处犯罪人死刑的对称性补偿根据。因此,对于毒品犯罪配置死刑,不仅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也有违社会公正理念与朴素的报应理念。然而,由于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以及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废止
毒品犯罪死刑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先通过司法手段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将死刑适用压缩到最低限度,以此缩短立法废除的进程,以积极有效的方式促进我国死刑制度改革和刑事法治进步。
二、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现状考察
(一)立法现状及评析
在我国现行的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刑法》)中有关毒品犯罪的条款共11条、12个罪名。关于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集中体现在 《刑法》总则第48条、第49条及分则第347条第2款。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该条规定了死刑适用的总标准。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该条是对死刑适用的排除标准规定,这两条总则规定也适用于毒品犯罪。 《刑法》第347条第2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刑法》第34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 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是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具体规定。
从1979年 《刑法》到1997年 《刑法》,毒品犯罪的死刑范围不断扩大。1979年 《刑法》仅有第171条规定了毒品犯罪,即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没有对其配置死刑,最高法定刑规定为有期徒刑15年。但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严峻,法定刑不断升级,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做了补充规定,即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该条将毒品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死刑,这是我国引入毒品犯罪死刑的开端。1988年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又将走私毒品罪的最高法定刑从10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死刑。1990年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项规定中,将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法定刑全面提高到死刑。到1997年 《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就可以判处死刑。该条完整地保留了立法演进过程中毒品犯罪死刑的最大范围,表明了毒品犯罪的死刑范围逐步扩大。
适用死刑的数量标准不断降低。1979年 《刑法》按照 “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原则,没有具体规定毒品数量标准。同时,该罪的结果加重情节只限于 “一贯或者大量制造、贩卖、运输毒品”。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贩卖毒品死刑案件的量刑标准》中规定,对个人制造、贩卖、运输鸦片判处死刑的标准是500两以上;个人制造、贩卖、运输海洛因、吗啡处死刑的标准是500克以上。②另1987年司法解释还进一步规定:对个人制造、贩卖、运输鸦片在300两以上不满500两和个人制造、贩卖、运输海洛因、吗啡在300克以上不满500两的,也可以判处死刑,但必须同时具备加重情节,即 “情节特别严重”的相关情形:(1)贩毒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一贯贩毒的;(2)武装贩毒的;(3)以暴力抗拒检查或者抗拒逮捕的既贩毒又开设 “烟馆”容留他人吸毒的;(4)内外勾结进行国际性贩毒活动的;(5)贩毒犯在劳改期间脱逃后又进行贩毒等等。可见,当时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数量标准的控制仍较为严格。而1997年 《刑法》不仅在刑法条文中直接规定了可适用死刑的毒品数量,且数量大大低于1987年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数量,即针对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海洛因和鸦片的死刑数量分别低于1987年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数量的1/10和1/25,这与保留死刑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要严酷得多。可见,从立法的角度,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在不断降低,体现了毒品犯罪趋重于死刑的数量标准。
适用死刑的条件标准不断宽泛。在毒品数量的计算方式上,1997年 《刑法》第347条规定:“对多
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这种计算方式导致实施多次毒品犯罪的人很容易达到死刑的适用标准数量。此外,1997年 《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该条款完全排除了司法机关将毒品纯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考虑的可能性。由于定罪量刑不考虑毒品纯度,使得掺假也会导致毒品数量的增加,从而更易达到适用死刑的数量标准。虽然2000年的司法解释规定:“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仍然保留了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在适用死刑的情节安排上,1997年 《刑法》第347条,将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选择性情节与上述数量标准并列作为可适用死刑的规定,其他适用死刑情形的规定没有进行具体的限定,从而在立法上降低了死刑的条件标准。[2]在刑种的规定上,将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列为选择性刑种,其刑罚幅度之大在适用上难免造成死刑的扩大化。
死刑适用的程序限制不断弱化。1979年 《刑法》第43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对死刑的适用还是规定了严格程序。而1981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1983年修改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同年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行使。[3]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1993年、1996年、1997年又先后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贵州等六个省、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死刑核准权,直到2006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然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不仅使死刑适用的程序性约束大大被削弱,而且也使得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率居高不下。尽管2010年颁布了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严打”刑事政策的影响,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程序限制明显弱化。
(二)司法现状及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起着普遍的指导作用。然而,现行的司法解释无不体现出重刑倾向。目前,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主要包括:2000年印发的 《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2007年的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2月印发的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 《大连会议纪要》);2015年5月印发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 《武汉会议纪要》)。 《大连会议纪要》专门对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详细列举了五种可以判处死刑的情形和九种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归纳起来,对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标准就是 《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五种情形,如果具有某些从重处罚的法定或酌定情节,可以判处死刑。对毒品数量达到死刑数量标准,但有某些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会议纪要》特别说明关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在 《大连会议纪要》基础上做出补充性规定的 (并非修改),两者配套使用,《武汉会议纪要》强调了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政策把握问题,提出充分发挥死刑的威慑作用,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同时,《武汉会议纪要》特别对运输毒品犯罪、毒品共同犯罪和上下家犯罪以及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做了补充性规定。不少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指导辖区法院审理毒品案件的规范性文件。而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在刑法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设定量刑标准的情况下,就自行制定量刑标准。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司法解释中的重刑主义倾向。
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 “唯数额论”,即把毒品数量作为是否适用死刑的决定性根据,这也是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比例高居不下的原因。在案件审理中,只要涉毒数量达到了司法机关内定的判处死刑的
数量标准,如果被告人又不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一般不会考虑被告人的酌定量刑情节。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我国毒品犯罪被判处死刑的实际人数,在所有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甚至在一些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时有5—10个左右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2007—2009年,毒品案件的重刑率分别为34.02%、31.9%和31.11%,分别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7.8%、16.13%和14.81%。[4]
三、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反思
(一)对毒品犯罪个罪的法定刑偏高
在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适用死刑的情况大量存在。我国 《刑法》第347条第1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刑法给毒品运输者配置了与制造、走私、贩卖毒品者相同的法定刑。然而,无论从主观恶性,还是在毒品犯罪中的作用来看,对之配置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同样的死刑处罚,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从运输毒品罪的性质来看,运输毒品行为只是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在整个毒品犯罪中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的特点,其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有所不同。[5]从运输毒品犯罪的主体来看,大多数运输毒品者是受雇佣的农民、妇女、未成年人或者无业人员,这类人员占到了全部毒品运输案件中被告人总数的70%左右。[6]这些人主观目的往往是谋取经济利益而非贩卖毒品,主观恶性较小,而且往往在这些人被抓获的同时毒品就被缴获,基本没有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较小。从死刑威慑的角度来看,对运输毒品罪适用死刑无助于减少和控制毒品犯罪的发生,即使对他们判处死刑也无法遏制毒品犯罪的源头。从刑法总则要求对从犯从宽处罚的精神来说,对毒品犯罪的运输者大量适用死刑将造成量刑的失衡,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
(二)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不合理
首先,以毒品数量作为定罪量刑唯一标准是导致死刑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在毒品数量的计算方式上,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实行累加计算的方法,这就很容易导致多次实施毒品犯罪的人的毒品数量达到甚至远远超出死刑的适用标准的数量,导致死刑适用率过高。其次,对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也是造成死刑扩大化的重要原因。1997年 《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此规定的优点是便于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可以有效地提高办案效率,但毒品纯度实际上对量刑的结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当被告人达到或者接近死刑的量刑标准时,纯度往往可以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对毒品不进行纯度鉴定,将直接导致数量等同但纯度有很大差异的毒品犯罪被处同种刑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以纪要形式强调要对毒品进行定量检验以准确量刑,这仅仅是对刑法规定毒品不以纯度折算所做的修改和补充,但具体如何操作却没有具体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对涉案毒品不进行纯度检验的情况仍然存在,忽视毒品纯度而产生的死刑扩张问题仍亟待解决。
(三)忽视酌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受 “严打”政策的影响,在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时追求 “从重从快”,导致司法部门处理毒品犯罪案件,更多注重的是犯罪分子的从重法定情节,而忽视了一些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从轻、减轻酌定情节,如犯罪人的主观态度、生活状况、犯罪手段、犯罪的损害结果等酌定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应该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客观来讲,酌定量刑的操作层面相对于法定量刑要复杂繁琐,一方面,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审判适用中可能会因量刑 “畸轻”、“畸重”而被改判;另一方面,酌定减轻适用必须层层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获批准才能适用,这在程序上限制了酌定量刑情节的有效适用。
(四)死刑对遏制毒品犯罪的效果不明显
从立法和司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效果来看,毒品犯罪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遏制。[7]从1982年走私
毒品罪的最高法定刑升至死刑开始,我国刑法一直持续不断降低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期望通过大量适用重刑来威慑毒品犯罪,但事实证明,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越多,毒品犯罪的发生率反而越高。据统计,1991年至1998年破获的毒品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增长20.7倍,平均年增长率达55.2%。[8]而在2005—2011年间,中国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增长1.2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7.7%。从抓获的毒品犯罪人数看,1991年至1998年间增长11.5倍,平均年增长率近43.4%,而2005年至2011年间,被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数量增长0.94倍,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3.4%。①数据来源:国家禁毒委员会2001年至2012年发布的 《中国禁毒报告》。尽管自2006年以来,开始逐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限制与减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尤其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后,死刑司法适用与执行之数量均有大幅下降,如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的重刑率为22.6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3.23%。[9]相比2010年以前,占比有所下降,但这并没有导致毒品犯罪的急剧泛滥,司法机关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和抓获的毒品嫌犯人数的平均年增长率反而均趋于下降。这些数据和情况表明,是否配置和适用死刑,对毒品犯罪的遏制作用非常有限,严格限制与减少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并不会对毒品犯罪的发生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毒品犯罪死刑限制的路径选择
从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效果以及国际社会关于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来看,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适用死刑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上应当废除死刑,但是,我国现阶段毒品犯罪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现实的选择是通过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直至最终废除毒品犯罪中的死刑。
第一,准确适用法律规定是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关键。首先,对1997年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总标准应该从司法的角度进行理性阐释和把握。 “罪行极其严重”应当是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犯罪人的主观罪过和社会危险性三者兼具,才能对其适用死刑。其次,《刑法》第347条规定的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五种情节,进行严格把握和严肃对待。除了这五种情形之外,其他任何情节,均不能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再次,重视毒品数量与毒品纯度的适用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确立 “以数量为主,考虑纯度”的标准,对毒品数量达到死刑标准,但纯度很低的,不宜适用死刑。同时还应全面地综合考虑与量刑有关的一切因素,特别是在没有法定从轻情节的情况下,不能忽视酌定从轻情节的考量。
第二,重视死缓刑种的有效运用。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中,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种。虽然同属于死刑,且都是以被告人应被判处死刑为前提,但执行刑罚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具体到毒品犯罪案件中,只要不必立即执行死刑的,一般也都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运用死缓最大程度的代替死刑立即执行,这种做法也符合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限制死刑适用的精神。
第三,严格限制运输毒品死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应把制造、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首要分子与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相区别,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的几类行为进行区别对待。其中,构成运输毒品罪包括两种情形:明知他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而受雇为他人运输毒品;因不明真相而为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者运输毒品的人。很显然,第二种情况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第一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为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而运输的行为,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定罪;对于帮助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运输毒品的行为,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从犯论处,从宽处罚,不宜判处死刑。这样不仅有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数量,而且还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精神,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第四,加大对毒品犯罪财产刑的适用力度。1997年 《刑法》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被适用:一是第347条第2款规定,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二是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 3000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然
而,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的 “空判”现象已成为刑罚执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究其原因,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对生存无望,逐抱定 “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决心,拒不配合执行财产刑。笔者认为,尽可能适用财产刑,也是降低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只要被告人或其近亲属主动积极交纳罚金或财产的,可以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依据,财产刑的执行也可以作为减刑、假释的条件。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能主动交纳罚金,积极自动地履行财产刑的,可以认定为罪犯在服刑期间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又有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的,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给予犯罪人减刑、假释。这些手段一方面可以辅助财产刑的顺利执行,最大程度地弥补毒品犯罪分子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这也是间接限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甚至替代死刑的有效措施。
[1]Patrick Gallahue and Rick Lines,The death penaltyfor drug offences:Global overview 2010,London:The International Harm Reduction Association,2010.
[2]彭旭辉、李坤:《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张文:《十问死刑——以中国死刑文化为背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4]袁林、李林:《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适用标准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赵秉志、[加]威廉·夏巴斯主编: 《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6]马骊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应用》,《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2008年第4期。
[7]张远煌:《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废止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年,第102页。
[8]何荣功:《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9]李婧:《最高法:对符合死刑条件的毒品犯罪案件坚决核准死刑》,人民网,http://legal.people.com.cn/n/2015/ 0624/c42510-27199898.html。
责任编辑:王雨磊
D624.13
A
1000-7326(2015)08-0050-06
李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5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