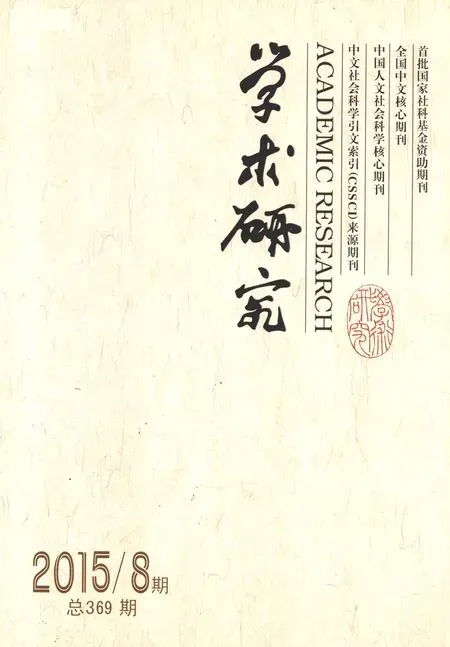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
——重估上古神话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
罗苹
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
——重估上古神话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
罗苹
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写作者和研究者在 “疑古”思潮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把上古神话排除在学科研究之外。如果能够借鉴和吸取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的新成果,中国哲学史史料应该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通过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这一研究路径,一方面,确定上古神话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寻绎出建构它的天文历法基础,才能褪去它神秘、虚幻的外衣。
神话 天文历法 形而上学 中国哲学史
一、神话①本文所谈的神话指的是上古神话,包括古代文献记载和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还包括考古发现的上古图像和实物叙事,不包括后世文人有意识创作的神话传说。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上古神话的有 《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列子》等。思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缺位
在中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研究中,神话资源已经是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但是却很少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古希腊神话对西方哲学影响颇为深远,但中国上古神话在哲学领域一直被漠视与悬置。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多少研究者重视神话思维的存在,以及它对整个民族思维的影响。造成中国哲学研究者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大程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论语·述而》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2000多年来,儒家正统思想认为神话是荒诞不经的而加以排斥,导致神话思维在中国思想世界的缺失。“许多人 (评论态度则有褒有贬)都观察到,在中国,神话一直是残碎的和边缘的,而且最终未能在高层文化的文学经典之中得到体现”。[1]学界对这方面的论述不少,这里就不再赘述。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写作者和研究者在 “疑古”思潮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把上古神话排除在学科研究之外。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哲学史进入了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19年2月正式出
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写作 《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对神话是不屑一顾的。他在对哲学史料的审定上断言:“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2]胡适批判谢无量高谈 “邃古哲学” “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 “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 ‘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3]胡适不明白,神话作为 “哲学史前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我们了解先民思维方式以至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最好史料。正如有学者分析:“由于夏、商两代以及更早时期文献的佚失,我们根据现有的、已经明显被后世儒学所历史化和伦理化了的古籍材料,要想还原中国神话的本来面目,显然是难以从心。因此中国神话的原始面貌和脉络谱系对于我们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从大量修改过的神话典籍中发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留下的印迹,通过分析中国神话传说演化的轨迹,总结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诸多特征,以及统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识。”[4]胡适这种审定史料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顾颉刚秉持 “古史即神话”的理念,推翻了传统所谓的 “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而在哲学界,胡适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冯友兰。
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期间,冯友兰对陈黼宸的授课方式颇有意见:“在我们班上,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就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当时的学生真是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5]冯友兰当时迫切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则评价陈汉章的授课方式说:“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 ‘洪范’。我虽是早受了 《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6]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问世,冯友兰认为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他用汉学家的方法审查史料,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他所认为是伪的都不用了。”[7]冯友兰后来在写作 《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也延续了胡适这种审查史料的方法,最早从孔子讲起,没有给上古神话、三皇五帝的历史留有任何余地。
蔡元培在为胡适所著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评价道:“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8]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让人们觉得老子、孔子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老子、孔子之前的哲学史被剪切了,上古神话的历史更不会被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但仔细分析蔡元培的这段话,我们发现,蔡元培并不是一味地褒奖胡适的写作手段,他还是有保留意见的。第一,蔡元培确定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已经生成。第二,蔡元培区分了 “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和 “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胡适选择了前者作为书写哲学史的内容。哲学史多按照人物思想出现的时间顺序去书写,胡适采用这种方法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哲学史中,这种书写方式也会带来弊端,一些包含哲理的典籍,因为作者无法考证,或者作者不是学界认定的哲学家,其理论就无法被书写进哲学史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蔡元培并非主张不要去研究神话,而是说要研究这块领域需要穷年累月的时间。而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包括全中国的哲学界,都迫切需要引入新式的写作与研究方法,暂时放弃这块领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是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体悟蔡元培的苦心。蔡元培其实隐含了这样的意思:等以后学界有条件、有能力,应该转而研究老子、孔子之前的哲学史;研究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从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将其系统化。而在当今中国哲学界,应该是有条件、有能力来完成这些任务了。
二、诠释神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任务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与 “神学”两词是混用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
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至公元1世纪,柏里尼 (Pliny)仍然别称 “哲学”为 “神话学”。[9]但是,这些都只是概念上的粘连,神话和哲学毕竟是本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我们不能赋予神话结构以理性的特征,而哲学又必须不断去追逐理性。正如西方近代神话学的先驱人物维柯所说:“神学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则是人类智慧的理智。”[10]
面对上古神话,中国哲学史要做的首先是诠释神话,找寻中华民族的始源思维。卡西尔把他的哲学称为 “符号形式的哲学”,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 “符号形式”——语言、神话、艺术、科学等进行研究。人是生活在一个由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交织成的符号宇宙中,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中取得的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 “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成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出的和听得懂的。”[11]依照卡西尔的分析,神话思维并没有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隐退。如果把文化流变中神话思维这条支流探测清楚,对整个文化的追根溯源可谓意义重大。从当今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神话世界是一个原始、落后、虚假的世界。但在神话世界里,在看似虚幻的背后隐藏着真实,在看似原始的表述中包含着科学的萌芽。而这些问题,正是需要哲学去诠释、去探究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石是形而上学。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都是人文之元,都是中华文明的本根,也是组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元素。[12]中国古代哲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体系这个支点上的,以这个支点构成的扇面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共同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形而上学运用语言文字、卦象和数来描述世界图式,在描述过程中,也延续了上古神话包含着的宇宙观念。对于记载上古神话的典籍,以及考古发现的包含有神话思维的上古图像和实物,哲学研究需要去体察这些文字、文献和数字、符号背后更庞大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蕴,这可以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奠定基础。 “哲学深信,神话创作功能的产物一定具有一个哲学的,亦即一个可理解的 ‘意义’。如果神话在所有各种图像和符号之下隐匿起了这种意义,那么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就成了哲学的任务。”[13]
哲学不能完全远离神话。哲学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它总要溯本求源,找寻自己的本根和渊源。在哲学思维系统形成之前,人类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神话思维时代。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之前这种普遍存在的思维而无中生有、另起炉灶地产生。正如叶斯帕森所言:“转化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无中生有,则是人类理智绝不能理解的。”[14]
面对 “中国有无哲学”的质疑,找寻中国古代哲学、形而上学的来源,成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那么,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神话是否存在渊源关系呢?我国神话学专家叶舒宪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神话与哲学之间本来并不存在这样一条界线分明的断裂带,而是具有渊源与承递关系的。考察从神话到哲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考察神话思维如何向哲学思维转化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哲学中抽象的概念范畴的由来和形成,而且可以找到这些抽象概念的具象原型,从而可望使对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哲学范畴的理解达到溯本求源的澄明状态。”[15]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叶舒宪直接将中国上古神话与古代哲学比对,找出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递进关系。例如,他从神话思维的角度重读 《老子》一书,从而找出书中运用的与神话逻辑十分相似的类比推理方式和比喻论证方式。叶舒宪认为,中国哲学是神话思维方式的延续,而 《周易》和 《老子》正是最能体现这种神话思维特质的典型文献。 “从神话思维的运演逻辑出发考察这些原始性文献将使我们从实质上把握中国哲学起源方面及其与西方哲学迥异之处,进而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与价值所在。”[16]但是,这种研究路径往往不能说明哲学起源于神话,而让人觉得哲学是在借用神话。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哲学家运用神话,那大半由于他先有了思想,然后才寻求形象以表达思想……如果思维一经加强了,要求用自己的要素以表达自己的存在时,就会觉得神话乃是一种多余的装饰品,并不能藉以推进哲学。”[17]
为了避免这种研究路径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做两方面的调整。第一,不是把上古神话和先秦哲学对接,而是将先秦哲学置换成在上古时期就形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也就是分析由太极、八卦、阴
阳、五行、河图、洛书这些元素构成的古代形而上学与上古神话的联系。第二,借助天文历法。上古神话包含天文历法的萌芽,天文历法才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来源。如果没有天文历法的介入,古代形而上学就好像直接脱胎于神话,会让人们在二者之间画等号。例如,胡适就断言:“从前一切河图、洛书、谶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说。”[18]他还说:“至于 《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 《十翼》,止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19]胡适认为,古代的书只有一部 《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让胡适有这一认识的是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这首诗,诗中有一句:“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这次日食被天文学家证实是发生在公元前776年8月29日。因为有这个科学铁证,胡适因此认为这本诗集作为那个时候的见证的可靠性是毋容置疑的。[20]如果能通过文献史料、考古史料证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来源于天文历法,那么就可以除去它被误解的神秘、虚幻的一面。
三、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探寻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
民俗学和人类学专家邓启耀认为,“神话中的宇宙模式,是将时间 (春、夏、秋、冬四季,晨、午、暑、夜四时)与空间 (东、南、西、北四方,扶桑、昆吾、昧谷、幽都四极),自然 (太阳运行周期、星宿方位等)与人文 (人神轮回的神界、阳界、阴界三界),神话 (四方四季神的神性与功能)与科学(原始的天文历法知识),形象 (各方时空的形、色、音、容等)与数理 (各方时空的取数性质等)……统统集合在一个互相制约、生生不息、变易万端的整体结构之中。由此而系统化、图式化的易象图说和阴阳五行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天文学,而且也深刻决定了中国医学等科学技术的思维模式与操作方法。”[21]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宇宙模式中,找寻中华文化的本根,找寻中华民族的始源思维,找寻古代形而上学体系的来源。中国哲学史应该把视野延伸,在宏大叙事中去与神话对接,探索出新的研究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就是把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三者链接起来研究。
何新认为:“中国上古时代几乎一切宗教、哲学、科学以至政治、伦理观念,多数都与天文历法和占星学有关。”[22]顾颉刚晚年给陈维辉编著的 《中国数术学纲要》作序时,肯定了神话、巫术所起的作用,肯定了谶纬中包含有天文历法。他说:“予尝谓科学发端于迷信,其始巫觋,握知识界之威权,任意放言天地鬼神,以博取蚩蚩者之信仰。其后接触实际日多,遂得据之以为人民服务。故医学者,所以疗疾也,而始作于巫彭。地理学者,所以认识地形与生产者也,而集合巫者长期之经历,以成 《山海经》,凡山川、矿物、禽兽咸有记载。开科学性记载 《禹贡》,《水经注》之端。谶纬者,假托孔子语言以为最高统治者服务者也,其浅薄极彰著。而其于天文、历法则多出于实测,纬观象授时者所不能废。昔人对此诸端,疑信参半,迄未能定其真价值。”[23]在中国上古时期,神话蕴含了天文历法;而形而上学与天文历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天文历法是建构形而上学的基础。
从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图腾崇拜神话、文化英雄神话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先民们对宇宙秩序的探寻。先民们需要建立统一的时空观念,从而来确立宇宙的统一性和合法性。后羿射日的神话在不少中国古籍里出现。 《楚辞·招魂》有言:“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楚辞·天问》有言:“羿焉日?乌焉解羽?”《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何新认为,后羿射日这个神话的深层结构中,实际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文化隐义——历法的变革。后羿射日的神话象征着太阳神中心地位的衰落,“其后即进入了古华夏历法上一个多元化发展 (试验)的改革时期。”[24]《淮南子·览冥训》有言:“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这就是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将后羿与嫦娥联系在了一起。后羿射日,十个太阳射落九个剩下一个;嫦娥奔月,一个月亮变成了十二个月。一个太阳、十二个月,两个神话前后有连续关系,即十月太阳历改革为十二月历。 《山海经·大荒南经》说:“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西经》亦说:“大荒之中,有
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生十日和常羲生十二月,应该是代表两种历法。十日指的是十月太阳历;十二月指的是十二月太阳历或十二月阴阳合历。天文史学家陈久金等人就证明了这些说法。[25]而十月太阳历和十二月历对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影响极大。
《周易·系辞上传》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 “洛书”。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 《周易》来源。黑格尔说:“易经的起源据说是出自伏羲。关于伏羲的传说完全是神话的、虚构的、无意义的。”[26]陈久金、张明昌认为:“所谓黄河显现龙马,洛水显现神龟,这都是人们用以神话的借托。实际是说远古圣王依据天象物候作为法则,制订历法,以利于万民纪时使用。”[27]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的 “八角星纹图”,广泛分布中华大地,湖南汤家岗、安徽凌家滩、四川大溪、山东大汶口、江苏青莲港、甘肃马家窑、内蒙古小河沿都发现了不同形式的 “八角星纹图”。考古学家认为,“八角星纹图”可以解释为八卦的雏形。[28]八卦既可以解释为历法中的八节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又可以解释为空间中的八方 (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土鲁窦吉》(宇宙生化)是一部论述天文历法的彝族古籍,使用的是神话史诗的叙事方法。书中附有两幅图,一幅名 “鲁素”,一幅名 “付拖”。“鲁素”意为 “龙书”,又称 “十生五成”图,相当于先天八卦,是十个月为一年的历法推理依据。 “付拖”意为 “联姻”,又称 “五生十成”图,相当于后天八卦,是十二个月为一年的历法推理依据。[29]“鲁素”即为洛书,“付拖”即为河图。受彝族 “鲁素” “付拖”两幅图的启发,刘明武认为:“洛书,表达的是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十二月阴阳合历。这一解释,符合天文学是人类第一学,历法是人类第一法的历史。”他还进一步论证了阴阳五行学说是由十月太阳历奠定的。[30]
《土鲁窦吉》一书利用神话叙事,将天文历法、形而上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阐释。这里从中撷取几段诗歌。 “诗歌讲天文,诗歌叙地理,不说不知道,要说从头起,从头来讲起:高天十二层,大地十二道,哎哺 (意为影形,宇宙万物的根本,彝族八卦名,相当于乾坤两卦——引者注)十二源,日月十二轮。” “先是高天影,次是大地影,末是才子影。哎哺源九十,生于宇宙顶。哎哺两阴阳,两者一母生。” “远古的时候,腮色吐足佐,弘色舍吞蒂 (两位人名,彝族哎哺时代,研究天文历法的圣人——引者注),他俩结论合,建立了九宫,制定了八卦,划分了疆域,确定了地界。若不立九宫,若不定八卦,就像宇宙门,没有开的样。” “在关键时刻,苍天在发展,哎哺佳根本,清浊气一变,金木水火土,五行样样生,布满中央后,各有其土根,各有其根本”。[31]从这几段诗歌里,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中的八卦、九宫、阴阳、五行都有出现,并与古人的宇宙生成演化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家陆思贤在所著的 《神话考古》一书中,将神话传说与地下文物结合在一起解释天文历法。书中多处谈到了远古先民用图腾柱立竿测影的天文实践活动。 《山海经·海内经》和 《淮南子·地形训》提到的 “建木”就是图腾柱,即今之 “华表”。 《山海经·南山经》中的 “招摇之山”,是以图腾柱作为立竿测影的起点,在此白天观测太阳晷影,夜晚观察星辰与月亮。[32]有学者考证,太极图实质是古人立竿测日影所得的太阳视运动立体投影图。[33]屈家岭、河姆渡出土的 “漩涡纹”,是太极图的雏形。 “漩涡纹”可以解释一物的循环,也可以解释寒暑昼夜的循环,还可以解释天体的循环。玄与旋同义,《山海经》中出现的 “玄龟、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大玄之山、玄丘之民”都是受这种旋转理念的影响。 “漩涡纹”可以表达历法,但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历法:“说明先民们既认识了旋转的运动,也就不断地探索旋转的原理,追求旋转的技巧,由此产生一连串哲理观念,小至一个角状物的运动,大至天象的旋转,最后构成宇宙本体的旋转,而又抽象化为 ‘太极’”。[34]
借助天文历法,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中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抽象符号的玄妙难解之谜就可迎刃而解了。抽象符号表达的是上古天文历法,之后的文字解说,例如 《周易》,则是对抽象符号以天文论人文的诠释。我们通过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这一研究路径,一方面,确定上古神话在中国哲学
史研究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寻绎出建构它的天文历法基础,才能褪去它神秘、虚幻的外衣。
朱谦之指出,“甲骨文字中的哲学史料包括多神崇拜、五行说之起源和殷礼三个方面。因而,殷代思想也应从诸神的神话中去探求,在 《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中取得二重证据之后,还要再求助于民俗学、神话学。这就是其所谓 ‘三重证据的史料研究法’。”[35]朱谦之的 “三重证据的史料研究法”是对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的合理推进。如果说胡适当时因为考古学的证据不足而产生疑古思想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已经成果丰硕,在高喊 “走出疑古时代”“走出神话”的口号之时,哲学界却还对神话研究无动于衷就说不过去了。假如等考古学、历史学都将神话证实或证伪,哲学才来面对神话,那么,哲学的作为就滞后了。如果能够借鉴和吸取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的新成果,中国哲学史史料应该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1][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2][3][8][18][19][2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16、ix、62、17、17页。
[4]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5][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自序第36页。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页。
[10][意]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35页。
[11][13][1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9、102、162页。
[12]罗苹:《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命运》,《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15][16]叶舒宪:《老子与神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7][2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6、120页。
[21]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221-222页。
[22][24]何新:《诸神的起源》第1卷,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40、312页。
[23]陈维辉编著:《中国数术学纲要》,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序一第1页。
[25][27]陈久金、张明昌:《中国天文大发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44-45、16页。
[28][32][34]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59-268、10-11、239页。
[29][31]王子国整理翻译:《土鲁窦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67、228,10-11、16、100-101、31页。
[30]刘明武:《换个方法读 〈内经〉灵枢导读》,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33]田合禄:《论太极图是原始天文图》,《晋阳学刊》1992年第5期。
[35]曹树明:《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王 冰
B932;B2
A
1000-7326(2015)08-0010-06
罗苹,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 (广东 广州,51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