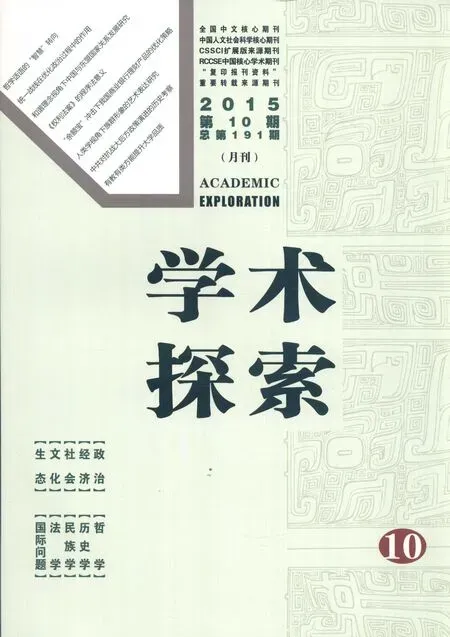人类学视角下族群形象的艺术表达研究
罗 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人类学视角下族群形象的艺术表达研究
罗 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艺术在人类学视域下,更多地面向艺术生产环境,即艺术所在的族群生活和文化情境,艺术的符码象征系统具有阐释族群文化和表述族群形象的服务功能。而族群形象的表达和建构涉及各个方面,艺术族群表达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更新扩展,但对文化本性的言说从未中断。为探讨艺术塑造族群形象的机制功能问题,本文从艺术族群表达的理论沿革、文化叙事、地方性表征和构建族群形象的尺度四个方面做了讨论。其意义在于丰富了艺术与族群形象在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地方性因素和文化尺度方面的有益探讨。
艺术;族群形象;文化;地方性;尺度
艺术作为人类文化景观之一,不仅是人类知识体系中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人类用以交流和炫耀的载体。针对人类所具有的视觉、听觉和可调动的感知,人类在艺术生产和创作上的不懈探索可谓用心良苦,但一切艺术活动所展现的无非都是个人和他所在群体的因素。族群形象,主要是族群主体展示出来给予他者以识别认知或感受的形式,包括直观的和象征的。地球上一直有如此多的族群,他们需要在社会交往中表述自我、区分他者,而“社会表述的形式是通过某种观念、某个图示,或某种姿势、某个事物的符号反映出来的”。[1](P77)艺术的视知觉符码构造性质,比之语言文字的想象构建,能更为直观地表达族群的形象。
现代艺术虽然明显地体现艺术的产生属于“私人冲动”,但艺术在人类历史中的实际情况是更多地作为集体活动发展起来的,最终体现为群体话语或群体象征体系。根据西方艺术产生情境论,艺术首先产生于制作者的族群情境约定[2](P51)当中;其次艺术的历史证明了艺术是从简单到复杂地展示个人和群体的生命体验;再次艺术体现其社会背景中特定的信念和价值体系,艺术形式所在的群体基础,如社会存在一样深邃,艺术品的知觉表达,即是社会关系体系的象征形象。[3](P48)因此,艺术的族群服务功能,首要地表现在族群形象的塑造和表达上。形象的存在才能使不同群体得以直观区分,同时获得传播交流。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说:一个画面首先应该是对眼睛的一个节日。借用过来,可以说一个形象应该也是对知觉的一个节日。通过对形象的感知,获得形象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和族群背景。
一、艺术的族群表达功能理论沿革
黑格尔美学体系中,他在论述艺术风格时引用了一句法国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4](P372)众所周知,黑格尔探讨了民族精神须借助艺术的具体形式以得到恰当的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5](P130)中,提到一位艺术家叫斯库里尔,其所绘的宗教人物玛丽,是印度比拟于女性美之“梦寐”精神的形象表达,尤其符合印度作为狂想和感觉境地的民族特点。受前辈影响,丹纳提出艺术的族群(种族)决定论和艺术的族群服务论,在其实证主义方法论名著《艺术哲学》[6]中,丹纳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是以保存团体和种族为目标的社会行为。在此书中,丹纳很细致地讨论了环境、时代、种族对艺术风格特征的决定性影响,洞见了艺术能轻易地表达出族群的精神、情感、性格和气质,甚至从中可以判断出一个民族是否快乐勇敢。艺术的族群表达功能后来经过歌德、沃林格尔和李格尔等人的诠释,更多地将族群心理状态与艺术风格形成联系在一起。沃林格尔1911年出版《哥特形式论》[7],是一部探询德国现代美术与民族精神根基的著作,以艺术风格心理学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进行阐释,把哥特式建筑和日耳曼民族的一般心理和精神状态联系在一起,确证哥特式代表的是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精神形象,试图寻求一条不同于南方古典主义、不受巴黎和地中海传统影响的北方日耳曼民族艺术发展道路。民族精神实际上是民族形象的抽象化,艺术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叙事方式。
随着人类学、民族学在20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除美学、历史学、心理学外,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符号学等也加入到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研究当中,艺术的族群表达理论在方法论上对前人的继承有所扬弃和创新。以博厄斯为首的人类学家们开始对小规模族群社会艺术材料素材进行实地调查搜集[8],考查艺术制作材料、技术、规则、风格特征等与族群社会体系、族群文化结构之间的规律。人类学家们对亚非拉各洲及太平洋等族群艺术考察成果日渐丰盛,便间接推动了艺术起源研究的兴起,而对小型社会艺术的研究,则促成了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这一时期,简·艾伦·哈里森受弗雷泽影响,提出“神话—仪式”学说,用民俗仪式、族群生活阐释艺术、神话。[9]简·布洛克则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宇宙语言”,是人类跨文化交流最简易的方式之一,而对小型社会艺术的把握,应基于对本土族群观念和族群集体本身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跨文化的交流和接受。[10]阿尔弗雷德·C·哈登认为,小型社会艺术越是制作精良,就越显出其所在群体生活水平的优越性,形式、线条、色彩和图案这些视觉符号与财富地位、宗教和群体表征形象密不可分。[11]布洛克和哈登都强调了艺术品和其生产群体的社会互动关系,这将艺术的族群表达在心理的和社会的层次都更进一步了,并且也开始了对族群表征系统与艺术制作的新探索。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离开制作他的人群和社会氛围,一切原本的艺术“真理”便会失去。[12](P120)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人类学家所看到的族群艺术,不是纯粹美学观照之下的艺术,而是族群世界观体系下的艺术,借助艺术,人类学家得以把握艺术所根植的族群文化结构,艺术不过是一种统领文化世界的形式。格尔兹和罗伯特·莱顿,则将艺术与族群集体的地方性知识阐释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两者都将艺术形式之研究转化为视知觉符号结构,不仅从阐释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艺术和群体生活的经验模式,还突破艺术制作的技术与思想层面,去观照艺术制作者的族群生活和精神面貌状态。艺术的视知觉符号体系,因此被赋予更多阐释的空间和层次,为艺术经验阐释又敲开了一扇新的理论之门。简言之,艺术品是表达自我、我族或我群的符号,符号的视觉感观,即是族群形象,也是文化形象。作为符号系统的艺术,是用来阐释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强化社会价值观的精心之作。[13](P128)艺术因此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族群服务使命,形象表达仅只是其中最为直观的表征方式。
二、艺术表达族群形象的文化叙事
谁构造了一个族群的集体意象,谁就表达了千言万语,族群形象恰是集体意象的文化载体。族群形象从政治上来说即是民族形象,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既是自我认同下的精心塑造,也是他者肯定下的稳定模型。族群形象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给人以宽广的文化想象空间,在众多的文化事项和差异化的族群生活中,族群形象的树立必然要捍卫族群文化的典型特征,因而表达形象的艺术作品更多地成为文化性存在。一项艺术活动或人工制品同时也是物质性的,参与制作或使用它的人群在社会宗教生活中得以被构建,而它也因此成为传播其文化的一个积极组成。[14]也就是说,面对一件艺术品,无论你是否介意,它总是在向你展示它生存的文化背景,叙述它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世界观。
较早关注族群形象研究和介绍族群形象史学理论的是香港学者鲍绍霖,他所引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东西方历史背景对比下和史学理论研究范式下的族群形象,鲍先生所用的是以国家为各族群集合的大族群概念。他于1994年发表《民族形象与文化交流史研究》[15]一文,文中历数了西方研究中国族群形象的一系列著作,如:1938年美国学者玛利·美孙(Mary C. Mason)所著《西方对中国及华人的观感:1840年—1876年》,1946年路易斯·马华力克(Lewis Maverick)出版的两册《中国:欧洲的典范》,1961年胡哈·安那尔(Hugh Honour)出版了《中国热:中国的形象》,1989年澳洲学者可林·马克拉斯(Colin Mac Kerras)发表了他的《西方对中国的形象》专题研究等等。这些书中,探讨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认识,其中讨论了中国形象的来源——事件、生活、文学文本、器物和其他文化艺术等,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有赞誉也有贬抑,有客观认识也有为着政治目的的主观认识。由此可知,西方学界一直比较注重族群形象研究,他们认为族群形象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参与政治、经济利益等的活动当中,形象是考量对方价值的方式之一。
成功的族群形象多以视觉性特征来传递信息,因为视觉对于身份确立的识别远比文字要直观有力,古今中外的成功族群形象或地方性形象,都是以简要直观的视觉表征而被铭记延续的。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当下,影视艺术作品对族群形象的塑造传播,要比其他艺术作品更有优越性,因其具有迅速面对千家万户的共时性和便利性。当然,人创造了意识形态,也必然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艺术所塑造的族群形象与社会集团、族群习俗、时代需求和精神惯例,是不可分割的。
当下的少数民族形象的构建,一直在进行,从影视作品到其他艺术活动,但仍然缺乏足够多的族群典范形象,这与对文化叙事力量的把握程度不无重大关系。或许,经典形象需要时间沉淀,也需要艺术工作者们更多的努力。中国少数民族当中,如果没有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姐等这类广为人知的民族形象,这些民族的文化传播突出性会减弱,也不会给一代人留下如此深刻的集体记忆。当下比较成功的族群形象构建者杨丽萍,她的“孔雀舞”和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她用富有族群文化特征的舞蹈,塑造了云南以傣族为主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系列文化艺术形象,舞蹈只是艺术形态之一,但在杨丽萍的创作中,舞蹈的风格特征都已成为表述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力。歌曲《小河淌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月光下的凤尾竹》等,则通过隐喻和转喻的强大力量,将云南少数民族的美好族群形象置入广阔的想象空间当中表达出来,优美的旋律低回流转,而叙事却不失张扬。当然,广大族群文化中,除舞蹈、音乐以外,还有太多的艺术门类可以担当族群文化的言说者,服饰、雕刻、仪式、建筑和绘画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20世纪80年代罗中立所绘的《父亲》声誉巨大,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族群形象,塑造了一个时代深沉沧桑的父亲群像。2008年奥运会,从奖牌到礼仪服饰的众多中国元素标识,有包括京剧在内的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诸如祥云火炬等等,这些符号,是中国传统族群形象的强调和彰显,也是官方意识形态建筑设计的一部分,以期强化社会凝聚,起到了格尔兹所言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向他者传递社会控制和文化叙事的力量。
当然,所有艺术形象的产生,无论在观念、方式和信念上,都要为其所在社会群体中先在之文化意义所接纳,并在接纳者的接受过程中不断被诠释,最终演变成具有扩张性的文化叙事。
三、族群形象的地方性表征
人类学所建立的文化批判基础就是差异,或者说是对异域文化的阐释而得以印证和反省自我的文化,按马库斯的观点,人类学传达异域文化的经验包括人、自我和情感,[16]在格尔兹看来,将这些因素扩展开来,一系列的人和事都属于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13](P273)人类学视野中的艺术,很难脱离地方性表征系统而存在,艺术本身是建构地方知识和文化的一种显著方式,艺术的表述也总是难以摆脱地方、国家或民族这样的划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文化中,艺术逐渐成为叙述差异性、赋予行为和思想以意义的主要文化生产场地。[17](P46)艺术自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起,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地参与了人类学的他性建构,正是地方感的呈现,使艺术的族群形象表达尤其鲜活,在漫长的艺术史当中,艺术家和艺术批评者都一直在费尽心思地寻找和辨认地方来源,并解析地方性表征因素,以便更容易将其纳入一般化的艺术准则当中。
族群形象的表达,不可避免被划分到时间和空间中去,时间的背景与社会变迁、历史更迭相关,而空间的维度必然与地区、地方或国家建构有关。艺术史上许多代表地方特点的艺术活动和经验,不仅塑造了地方族群形象,同时也建构起地方文化尊严,表明地方文化生产的能力。有太多的艺术是通过地方名字命名的,从非洲部落艺术、印第安土著装饰、台湾原住民雕刻等,到中国艺术当中诸如越剧、苏绣、湘西傩戏、江浙民居等等,还有无数更为准确细致的地方命名。这些艺术经验,既向外树立了当地人的文化话语权力,又在地方知识系统内部建立起地方文化记忆,成为当地族群形象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族群形象的文化记忆一旦形成,无论是祖先传承的意识行为,还是接受外来影响后的想象重构,就会成为本地或本族群的社会结构成分,按照地方性“法则”和地方性“话语”进行重组,但仍然能维持原有的地方性文化价值和意义。艺术的族群形象表达因此也会从物质性的存在(服饰、民居、绘画、雕刻等),延伸到观念性存在,参与构建地方文化和地方意识形态。
从艺术审美角度而言,族群形象的地方性表征应追溯到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来源,上文提到的艺术与族群的关系,变相标志着艺术与地方的关系。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态环境,族群的生活习俗和方式有很大差异,所生产的艺术品必然千差万别,最终各自形成不同的风格特征,艺术史上几乎大部分批评家和艺术家都以此为研究范畴。非洲的雕刻和象牙装饰影响过毕加索的艺术作品风格,中国文人画和波斯细密画也影响过野兽派创始人马蒂斯的创作,地方性艺术元素,可以被他者借鉴,通过与他者因素的结合而重构为另一种形式和风格的艺术品,地方性表征还存在,但族群形象传达已然丧失。因此有一定地方性表征的艺术经验,并不一定是族群形象代表,而象征族群形象的艺术品,则一定是地方性表征系统的产物,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都是难以更改和颠覆的,尤其是小型社会具有原始风格形式的艺术品。列维·布留尔曾描述过英属圭亚那印第安人制作艺术品的情况,他说,尽管当地人在制作某些物品时展现了惊人的灵巧,但他们仍然准确按照其历代祖先那样来制作这些物品,不做形状或形式的改变,因为他们相信与之联系的物体的神秘属性,一旦改变这些物品哪怕最微小的细节,这种神秘属性就不为人所控制了。[18](P32)在小型社会区域中,象征族群形象的艺术品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维护和保存地方共有象征规则系统的群体行为密切相关。
另一个与地方性表征相关的族群艺术话语是族群身份呈现。族群形象首先是一个文化形象,当中内含位置的观念,这类关于空间位置的意识能够唤起家庭、家族或者地缘身份的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正是某块地方或区域,构成了家庭的源泉,[19](P103)通过家庭的血缘关系结成“地方性纽带”,从而形成地方性身份,这种身份是由家庭、家族扩展开来的地缘性身份,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排他性,以及和其他地方相区分的对比参照性。族群形象唤起的地方意象,对身处其中的群体产生的影响长久而固定,地方意象好似一种固着在族群名称上的魔力,将群体生活反复定向在与之相关的事件和纽带上,并规范着当地群体的社会关系,保持其族群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保证了地方文化的延续更迭。地方身份认同在艺术的族群形象传达中,一直对艺术生产者群体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只要支持认同的社会仍然存在,地方性表征会在族群文化中不断获得滋养,并推陈出新,以强化其独特存在。在全球化速度加快的当下,族群形象构建也在遭遇认同危机,但地方性表征能成为其对抗全球化西方化的一种策略,因为普遍文化或国际文化仍然需要强调差异,地方性作为最根本的文化信息,不能丧失其多样性的生动传统。
四、艺术建构族群形象的尺度问题
一个艺术作品就是一个小宇宙,也是一个文化的系统,在艺术人类学视角下,作为族群形象表达的艺术品,则不能仅仅停留于“是否美”或“美的解读”层面,去做贵族式的哲学思辨,艺术在人类学视域中更多要面对族群社会生活和文化情境。表达族群形象的艺术品除了与生俱来的审美尺度外,应该包括文化尺度和价值尺度,这里的价值尺度应是一种世界观性的导向,而非经济价值或消费价值尺度,族群形象建构在经济消费上的成功当然会有益其认同的产生,但在人类学话语中,更关注的是文化价值。消费价值可以是艺术族群形象制造的目的之一,而不能作为前提,否则文化向度会被歪曲。探究艺术建构族群形象的文化尺度,才能较好地研究族群的社会经验、结构和由之而显的文化因果系统。
在美学和文化学领域中,审美和文化两者素来皆因难以阐释而著称,而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审美规则和文化特点。中国美学界对这一句话比较熟悉:“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0](P58)马克思在这里所言之“美的规律”曾在国内学界引起大讨论,而这个规律定然与“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内在尺度”密切相关,从学理上来阐述这些关系颇为繁杂,但如果纳入到文化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框架中来,艺术的功用之一,在于展示它的文化之明白性,则可以简单归结为:一个艺术作品该如何加强其族群、文化身份和文化形象,才能被身份内外的人认可。这样,尺度问题就不仅仅是审美规律问题了,文化和价值的尺度因此便显得尤其重要,或者说,艺术品“美的规律”也转化为“制作规律、接受和阐释”的尺度问题。
作为文化有效定位的族群形象艺术作品,是对生产者理解把握族群文化生活是否准确的一种严峻挑战。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精神惯例,在艺术品制作当中,则必须通过准确理解其文化各方面才能有族群形象的合理性。格尔兹认为,对所有族群来说,崇拜的形式、载体与对象都充满深深的道德庄严。[21](P148)艺术具有象征的力量,这种力量依赖于它使象征对象得到理解的能力,也就是说,是否合适地表达了现实的基本性质,且给予一定的价值指向,是判断一个族群艺术品是否合宜的重要前提。他还指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文化的道德和审美方面的评价性元素)是生活的格调、特征和品质,它的道德、审美风格和情绪;它是一种潜在态度,朝向自身和生活反映的世界。”[21](P148)艺术品所呈现的世界观,不能背离艺术制作者的族群文化规则,更不能破坏族群现实性的价值观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相互参照。因为,正如豪塞尔所言,所有的艺术,无论通过怎样迂回曲折的方式,或迟或早会把我们最终引向现实。[22](P3)当下的全球化背景,越来越多的族群想在同化席卷中选择有效的文化定位,确立自我族群身份形象以示自我独特性,与他者相区分而引人注目,但遗憾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容易将此诉诸旅游、商业和经济利益的运作,导致在构建族群形象的过程当中,许多股力量加入进来,无限扩大消费价值,纯粹的艺术建构已很艰难。一些文化元素则不免生搬硬套,难免不会在价值观引导方面有所偏差。例如摩梭人的“走婚”习俗,本是族群习俗中文化庄重的一部分,如今被一些宣传者在吸引旅游消费的渲染中导向低俗;还有丽江,在几方力量的构建下,也成了“艳遇之都”,而这样的地方形象很多时候指向了价值观变异的族群形象。而为旅游而生的“某地印象”或“印象某地”艺术展演活动在全国多地曾一度十分热闹,但真正建立起地方文化形象来的并不多,或许这些艺术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使族群民众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族群民众的认同和安全感是否提升了还有待商讨。还有一些涉及民族形象的影视作品,对民族的文化习俗把握不够准确,也遭到多方诟病,尤其会受所涉族群成员非议。
一个成功的艺术族群形象,其人类学意义在于它摆脱了个体限制,超越了个人利害,扩展到族群个体和集体的文化生活中去,完成了自身的审美理想和文化理想,从而达到了象征表述的目的。荣格认为,一种象征对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来说,始终是一个重复不断的挑战,正因如此,象征之作才那样富有激发力,并能强有力地摄人心魄,同时带来美的享受。[23](P76)他用分析心理学方法,来解读好的艺术之所以让人很享受的问题,虽然只是分析艺术的普遍性问题,却也揭示了艺术创作要契合人思想和感情,要与人心理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过于冲突。豪塞尔比荣格讨论得更直接,他说,针对没有受过太多艺术教育的族群民众来说,使他们做出反应的不是艺术上的优秀或低劣,而是那些对他们生活进程产生安定或造成不安作用的特征,他们乐于接受在艺术上有价值的、能够表现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幻想、他们的想象并为他们提供充满生命活力价值的东西,接受能安慰他们的焦虑不安和增强他们安全感的东西。然而,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单单就这些艺术的不熟悉、不习惯、难以理解而论,对于一个未受教育的爱好者来说,是会产生令人不安的后果的。[24](P8)言下之意很清楚,族群民众或艺术族群形象的受众,不会接受令他们感到陌生至极且让他们身心反感的艺术,他们的艺术体验需要心安理得和精神抚慰。因而不单是族群形象的构建,所有族群艺术品的制作,都应该有适宜的文化尺度和价值尺度,否则给受众带来的是不安的折磨。
艺术是表达、表现和强化一个群体的社会意识和信仰关切的永恒形式,艺术构建族群形象的尺度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在族群形象的呈现中,表明拥护和尊重其社会群体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理想,而不是仅凭视觉的享受或审美的快感,让族群形象的构建跌出文化想象的边缘。
[1]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郑元者.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黑格尔(G.W.F.Hegel).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6]H.A.丹纳(H.A.Taine).傅雷译丹纳名作集艺术哲学[M].傅雷,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7]威廉·沃林格尔(Wilhelm Worringer).哥特形式论[M].张坚,周刚,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
[8]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原始艺术插图珍藏本[M].金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9]哈里森著.古代艺术与仪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0]布洛克(H.Gene Blocker).原始艺术哲学[M].沈波,张安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1]Alfred.Cort.Haddon:“Evolution In Art:As Illustrated By The Life-History Of Designs,New York: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Ltd,1907.
[12]汤因比(Toynbee,A.J.)等.艺术的未来[M].王治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3]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4]丹尼尔·米勒.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15]鲍绍霖.民族形象与文化交流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1994,(4).
[16]George E.Marcus: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17]乔治·E.马尔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M].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0.
[20]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1]豪塞尔(Hauser Arnold).艺术史的哲学[M].陈超南,刘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2]荣格(Jung,C.G.).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M].孔长安,丁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Ethnic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LUO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art ismore oriented towards its production environment,namely,the ethnic life and cultural situation where art is rooted.And the artistic codes and symbolic systems have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interpreting ethnic culture and expressing ethnic images.What'smore,although the expre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ethnic images relate to various aspects of art theory andmethod,the study ofwhich continues to update and expand,its talk of the essence of culture has never stoppe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ethnic imag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evolution,cultural narration,lo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building scale.Itwill shade some light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ethnic images in historical origin,cultural connotation,local factors and cultural scale.
art;ethnic images;culture;locality;scale
I042
:A
:1006-723X(2015)10-0087-06
〔责任编辑:黎 玫〕
罗 瑛,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