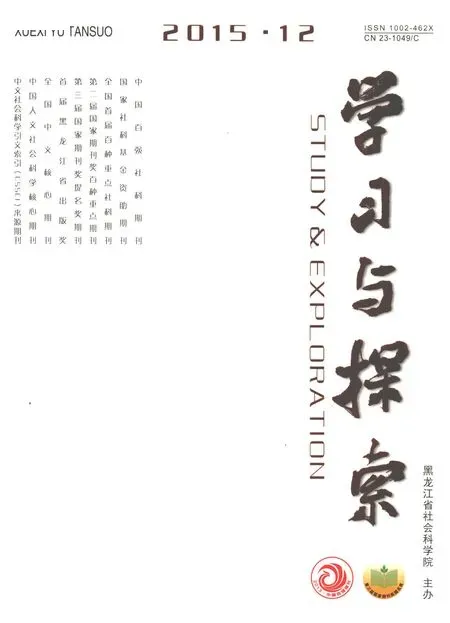宋代城市商业性文化消费中的词与词人
张玉璞
(曲阜师范大学 《齐鲁学刊》编辑部,山东 曲阜 273165)
宋代城市商业性文化消费中的词与词人
张玉璞
(曲阜师范大学 《齐鲁学刊》编辑部,山东 曲阜 273165)
宋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具有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空前兴盛。从花间樽前的聊佐清欢,到秦楼楚馆的声妓传唱,词与娱乐、与都市皆有天然联系。其从“诗余”蔚然而为两宋“一代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宋代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发达的都市文化。无论是歌馆、酒肆、茶坊的商业运营,还是郡斋、宅第的公私雅集,大都会伴有词人填词、歌妓唱词、饮者听词等侑樽佐欢的娱乐活动,都会因此而形成一个或大或小的词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市场。“生产—传播—消费”过程的不断重复、扩展与延续,是造就宋代词坛辉煌繁荣局面的重要因素。
宋词;歌妓;词人;城市经济;文化消费
一、“夜市”的兴隆与宋代城市的商业性文化消费
中唐以前,城市的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制度非常严格,商业活动只限于市中,且“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 (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商品交易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唐代中后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营性的商业活动逐渐突破了坊、市的界限,且“夜禁”稍开,出现了夜市。*据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载,唐末长安的崇仁坊,“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不仅长安,都城以外的扬州、成都、苏州、杭州、汴州、楚州、梓州、象州、湖州等城市也出现了夜市。参见张邻《唐代的夜市》,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1期。但这种情况并非常制,还时时受到朝廷的打压。*如《唐会要》卷八十六载:“开成五年(840)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断。”到了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商业的日趋繁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的生活,城市原有的坊、市界限已被打破,市民可以沿街设铺开店且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
在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甚至在“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还有潘楼东街巷拂晓前的“鬼子市”,“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著名的“州桥夜市”主要经营小吃,而马行街的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这里是“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每到夜间“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连不喜油烟的蚊子也无法在此生存。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活动比之汴京更为繁盛。《梦粱录》卷十三《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都城纪胜·市井》也载,临安的“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至于岁时佳节,都城之夜更是车马骈阗,歌吹沸天,彻夜狂欢,盛况空前。汴京的元宵节,各种“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粼粼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烛,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南宋临安的元宵节更为热闹,从正月十四晚上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六夜收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赏,不忍舍去”。中秋之夜,则“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吴自牧《梦粱录》卷四)。夜市的兴隆和市民夜生活的丰富多样,使茶坊酒肆的生意也异常火爆,营业时间大大延长,“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宋代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汴京、临安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成了一座座不夜城。
唐代以前,大多数城市,尤其是都城,其社会结构和根本性质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经济、文化职能的发展依赖于政治、军事的带动。中唐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经济因素开始在城市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到了宋代,由“镇的人口规模、经济职能、政权机构进一步发展而形成一批经济型城市,逐渐改变着中国城市以政治型城市居住的总体格局,这是宋代城市化高潮最突出的表现”[1]。这种城市社会结构和根本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的消费市场高度繁荣,这其中有因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口膨胀、城市生活活跃而形成的正常消费行为,但也有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非正常或畸形消费行为,即奢侈性的消费行为[2]。《宋史·舆服五》载:“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闾阎之卑,娼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3]《燕翼诒谋录》卷二云:“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朝廷不得不屡次下诏禁断。但奢靡之风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禁绝。直到南宋末期,此风愈扇愈昌,不仅高官豪富一掷千金,普通的中产之家也是出手阔绰,“士夫一饮之费,至糜十金之产,不惟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 (王迈《臞轩集》卷一)。这种因城市商品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奢侈性生活消费观念和行为也带来了娱乐文化活动的商业性品质。
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通常是作为特权享受,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开展的,一般不发生交易行为。中唐以后,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开始在市场上出现[4]。但这种娱乐性消费服务尚处在雏形阶段,且不具有普遍性。到了宋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具有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空前兴盛。宋代经济型城市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居民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二是“城市不再是由皇宫或其他一些行政权力中心加上城墙周围的乡村组成,相反,现在娱乐区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5]。两者合力,决定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平民化和世俗化趋向,而这种社会生活倾向又决定了其文化的娱乐性质。在宋代城市特别是在城市的娱乐区中,士庶混杂,商铺民居间处,茶坊酒楼餐饮业与娼妓业的合流以及官妓的商业化,都使得城市的消费文化呈现出浓郁的色情味道和俗化特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的燕乐(又称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汉族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从花间樽前的聊佐清欢到秦楼楚馆的声妓传唱,词与娱乐、与都市皆有天然联系。其从“诗余”蔚然而为两宋“一代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宋代高度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异常发达的都市文化。因此之故,学界才认定词是“一种都市娱乐文学”[6],“其生成和发展确与都市的娱乐生活息息相关;或者说,燕乐的盛行、歌伎歌词佐酒与文人应歌填词的往复互动,主要体现在都市的娱乐生活中”[7]。
二、茶坊酒肆中的词客风流
在唐代都城长安,妓女们主要集中居住在平康坊,其他则零散居住在平康坊周围各坊。而在北宋汴京,随着坊市制度的破坏,娼妓业也与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一样,散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城内妓馆主要集中分布于南北斜街、牛行街两边、马行街两边、里城正门朱雀门内西大街、朱雀门外东西大街、相国寺东南的录事巷及蔡河两岸。此外,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也是妓女们经常出入的营业场所。南宋临安的“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与唐代相比,宋代城市妓女的服务对象虽有所扩大(诸如各阶层市民、经商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员等),但文化层次较高者所招揽的主要顾客仍然是官贵士人和应试举子。
樊楼,又叫白樊楼,北宋末年改称丰乐楼,位于皇城东华门外的繁华街区,“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载,在汴京城里,像樊楼这样规模宏大、官府允许其自家酿酒的“正店”有“七十二户”,而规模较小、酒由“正店”供应的“脚店”更是“不能遍数”。供应酒食只是这些酒楼最基本的业务,令文士们趋之若鹜的还有其中色情味极浓的文化娱乐。宋代的酒店很多也是秦楼楚馆,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如汴京马行街上与樊楼齐名的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若神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一般的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烛,各垂帘幙,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在一些下等的“脚店”,也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席前歌唱。临安的熙春楼、赏心楼、花月楼等酒店,“俱有妓女,以待风流才子,买笑追欢耳”(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这些酒店“每楼各分小阁十余”,“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这是酒店中的情况,茶坊与此相似。在临安,“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在清乐茶坊、珠子茶坊、八仙茶坊、潘家茶坊等茶肆,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似这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的声色氛围,最适宜的文化消费当然应带有一些软媚、香艳甚至色情的味道,而素有“夜文学”之称的曲子词理所当然成了这种文化消费的首选者。因为诞生于民间的曲子词到了文人手中,其樽前月下“浅斟低唱”的娱乐性功能越来越强,五代后蜀词人欧阳炯(蜀亡后仕宋)的《花间集序》对词的这一功能作了如下界定:“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意谓词是供“绣幌佳人”在酒筵舞席上用以“佐酒”演唱的,而文人作词也无非是以其“清绝之词”来增强歌妓演唱时的“娇娆之态”。绮筵、词客、声妓三者的完美结合,方能将词之“浅斟低唱”的娱乐性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何况歌妓们不仅能唱词侑酒,其所居住的环境宽敞清静,且谈吐优雅,能文词、善品评,与文士的趣味和好尚颇为一致。罗烨《醉翁谈录》丁集卷一云:
平康里者,乃东京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吐谈,亦评品人物,应对有度。
歌妓麇集的茶坊酒肆、秦楼楚馆,大抵也是风流词客们惯常出入的风月场所。在这些场所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词文学消费市场。在当时,“小唱”是最普遍的唱词形式,这也是宋词重要的传播方式。“小唱”主要演唱小令或慢曲。《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云:“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与四十大曲、舞旋为一体。”《梦粱录》卷二十也谓“小唱”“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就是说,“小唱”主要是指声妓执拍板清唱小词,也可伴以一二简单乐器,或者在简单乐器伴奏下既唱小词又随之舞蹈。所谓“慢曲”是指节拍缓慢的曲调,“曲破”是指唱大曲中间称为“破”或“入破”的一段。音调的处理一般是起音重而结尾轻柔,营造出一种“浅斟低唱”的氛围。“宋人要求小唱艺人色艺俱佳,而且风流多情,以便在浅斟低唱时得到精神与感官的愉悦。瓦市、歌楼及流浪的小唱艺人使用的唱本,有的是文人如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人的应歌之作”[8]。“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欧阳修《玉楼春》)。在花街柳巷、秦楼楚馆、茶坊酒肆中,“画堂迥,玉簪琼佩,高会尽词客”,歌妓们“逞朱唇,缓歌妖丽,似听流莺乱花隔。慢舞萦回,娇鬟低亸,腰肢纤细困无力”(聂冠卿《多丽》)。词客与声妓的互动,共同拉动了词文学消费市场的繁荣。
宋朝统治者鉴于晚唐五代武人跋扈、政权迭更的教训,立国之初即实行右文偃武、“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一面裁抑武臣,一面优遇文士,高其官职,厚其俸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且鼓励官员“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脱脱《宋史》卷二五〇)。至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伎自娱”[9]。在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优裕的生活条件下,宴饮雅集、交游唱酬便成了士大夫文人休闲生活中很普遍的一种形式。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10]在汴京、临安等大城市中,设有官库酒楼,“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其中多用官妓唱曲侑酒。官妓是供封建帝王与士大夫们娱乐的工具。唐代教坊中官妓的人数众多,北宋教坊的规模有所缩小,官妓人数也相应地有所减少。至南宋,教坊虽被废除,但各州县的地方官府仍然直接控制着不少官妓。官妓对于官差的应承,主要是伺候官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各种集会、游乐与宴享。《梦粱录》卷二十载:“官府公宴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祗应。”宋代不少官妓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是相当高的,她们不仅能歌善舞,而且知音晓律,能赋诗填词。宋代杨湜《古今词话》载:
成都官妓赵才卿,性黠慧,有词速敏。帅府作会以送都钤帅,命才卿作词,应命立就《燕归梁》……都钤览之,大赏其才,以饮器数百厚遗,帅府亦赏叹焉[11]44。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载: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
这些官妓、营妓(军中歌妓)大都有着良好的文化艺术素养,自然能得到士大夫们的青睐,而那些为数更多的私妓和茶坊酒肆、秦楼楚馆中的商妓也有文化艺术素养不下官妓者。由此,文士们热衷于出入茶坊酒肆、秦楼楚馆,并非仅仅为了“喝花酒”“吃冷茶”,满足生理上的需求,更重要的还是能得到文化层次上的精神愉悦;而歌妓们也大多乐于与文化素养较高且风流多情的文士们交游,这一则能提高自己的身价,二则能得到文化上的熏陶与情感上的交流,甚至还可能获得真挚的爱情。文士与歌妓的这种双向需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种影响在词文学的创作中显得尤其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词人在特定情境中进行创作最直接的心理动因之一。
三、词人与歌妓的互动交往——宋词的生产、传播与消费
在词人的词作结集出版之前,单篇传播的媒介很多,如镂板传播、刻石传播、题壁传播等等,但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席间樽前的歌妓口头传唱。明代的毛晋说秦观“性不耐聚稿,间有淫章醉句,辄散落青帘红袖间。虽流播舌眼,从无的本”[12]。淮海词赖以流播的主要途径就是“青帘红袖”间的口舌传唱。这一传播方式,不仅保留了词作,也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
宋代的城市消费与前代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个人消费的行为有很多是在经由市场这一重要环节之后才最终完成的。物质生活消费如此,属于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是如此[13]。既然宋代的都市文化消费带有浓郁的商业化色彩,那么一切就得按商业的操作规范进行。词的创作与传播也不例外。宋代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自太宗起就开始了官卖酒制度,后来至神宗时又开“设法卖酒”之风:
官榷酒酤,其来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管,宜募民掌之。减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
朝廷实行“设法卖酒”本来是为了国计民生,但娼妓“坐肆作乐”以招揽生意的做法却遭到了士大夫的不满。两宋之交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就认为:“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官吏遂张乐,集妓女,以来小民,此最为害教。”(杨时《龟山集》卷十)但直到南宋末年的理宗朝景定年间,这种状况也没有改观。《梦粱录》卷二十云:“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利润的最大化,因此需要竞争机制,即便是“榷酒”这样的政府行为也是如此。以“设法卖酒”来说,一个酒楼卖酒多少,一看歌妓的姿色,二看歌妓的弹唱技艺,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为了在同行竞争中占得先机,歌妓们必须加快词曲更新的速度,否则,老调重弹没有新鲜感,也就没有了吸引力,也就丧失了竞争力,老顾客也就不会再上门了。为利所驱,歌妓们必须与词客保持密切的关系,随时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的歌词。这样一来,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围绕歌词作品的产—供—销一条龙的供需市场。文士填词是产品的生产过程,经由歌妓弹唱传播给广大受众,词作也由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在这一过程中,词作者、歌妓、受众都从中获得了各自的利益。
宋代的润笔,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特定的公文写作可获润笔,一是受人请托所作的诗文可获润笔[14]。宋代词人以词作获取“润笔”的方式属于第二种情形,从宋代流传下来的大量的干谒词、寿词、赠妓词来看,词人很有可能就从受赠者那里获得“润笔”。而宋代不少笔记杂著中也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献。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耆卿一日经由丰乐楼前,是楼在城中繁华之地,设坛卖酒,群妓分番。忽闻楼上有呼“柳七官人”之声,仰视之,乃角妓张师师。师师耍峭而聪敏,酷喜填词和曲,与柳密。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时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妾之房卧,因君罄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填一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令量酒,具花笺,供笔毕。柳方拭花笺,忽闻有人登楼声。柳藏纸于怀,乃见刘香香至前,言曰:“柳官人,也有相见。为丈夫岂得有此负心!当时费用,今忍复言?怀中所藏,吾知花笺矣。若为词,妾之贱名,幸收置其中。”柳笑出笺,方凝思间,又有人登楼之声。柳视之,乃故人钱安安。安安叙别,顾问柳曰:“得非填词?”柳曰:“正被你两姐姐所苦,令我作词。”安安笑曰:“幸不我弃。”柳乃举笔,一挥乃止。
张、刘二名妓都提到曾支付费用给柳永,现下旧话重提,也无非是为了获取新词。从作者填词到歌妓赠以“金物”,这是一个商业性交易过程,词的作者和歌者互利双赢。
在作者一方,为歌妓填词,既可获得当下的物质利益,又可借助声妓弹唱其歌词而赢得更高的词名,可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得。柳永之所以能获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样广泛的社会认可度,歌妓传唱其词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时文人吟诗作文一般还得不到“稿酬”的情况下,为歌妓作词却可以名利双收,焉能不刺激词人们的创作热情,这对宋代词文学创作的繁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而歌者一方从中获得的利益则更多。名词人如柳永等的评价可以使歌妓迅速蹿红,“声价十倍”;而多一首新词,就等于多了一个与同行竞争的砝码,也就等于掌握了赚取财富的金钥匙,借以赢得更多的商机和利益:“绮罗丛里,独逞讴吟。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倾听处,王孙帝子、鹤盖成阴”(柳永《瑞鹧鸪》);“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柳永《木兰花》);“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晏殊《山亭柳》)。下面几则资料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
耆卿初登仕路日,因谒福之宪司,买舟经南剑,遂游于妓者朱玉之馆。朱玉云:“素闻耆卿之名。”倾意已待之。饮数日,偶值太守生辰,朱玉就耆卿觅庆寿之词,耆卿乃作词与之。及贺,太守闻朱玉所讴之词,大悦,厚赏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
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妓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周煇《清波杂志》卷五)。
东坡掌翰苑,一日,王定国置酒与东坡会饮,出宠人点酥侑尊。……坡叹其善应对,赋《定风波》一阕以赠之。……点酥因是词誉藉甚[11]21。
这些歌妓或以新词得“厚赏”,或因名人奖誉而“声价增重”,都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一旦有与词人交往的机会,她们总是想方设法从词人那里求取新词,于是歌妓“乞词”与词人“赠词”成了宋代词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宋代笔记、杂著中,有很多关于歌妓于歌筵酒席上当场“乞词”的记载,同样的内容在宋代词人的词作、词序中也俯拾即是。如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曰:“建安章质夫家善弹琵琶者,乞为歌词。”毛滂《虞美人》(柳枝却学腰肢袅)词序曰:“官妓有名小者,坐中乞词。”朱敦儒《鹧鸪天》词云:“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刘过《西江月》(楼上佳人楚楚)词序曰:“武昌妓徐楚楚号问月索题。”高观国《生查子》(蓬莱一念云)词序曰:“史辅之席上,歌者赠云头香乞词。”管鉴《桃源忆故人》(寿牙初长香莫嫩)词序曰:“醉中诸姬索词,为赋一阕。”吴文英《声声慢》(春星当户)词序曰:“饮时贵家,即席三姬求词。”凡此等等,足可说明歌妓“乞词”风气之盛。
关于词人“赠词”,兹仅举清人叶申芗《本事词》卷上两段文字以说明之。一段是关于张先“灯筵舞席”作词赠妓的:
张子野风流潇洒,尤擅歌词,灯筵舞席赠妓之作绝多。其有名可考者,《谢池春慢》为谢媚卿作也。……又,《南乡子》听二玉鼓胡琴也。……又,《望江南》赠龙靓也。……他如赠年十二琵琶娘者,有《醉垂鞭》云……又听九人鼓胡琴者,有《定西番》云……又舟中闻双琵琶者,有《剪牡丹》云……而咏吹笛、咏舞、赠善歌诸作,又不胜枚举矣[15]2305-2306。
另一段是关于苏东坡“歌席酬赠”的:
坡公喜于吟咏,词中亦多歌席酬赠之作。其赠楚守田待制小鬟,则有《浣溪沙》两阕。……又赠黄守徐君猷三侍姬,则有《减兰》(《减字木兰花》)三阕。……又赠君猷家姬懿懿《减兰》云……又赠楚守周豫舞鬟,则有《南歌子》两阕。……又赠陈公密侍姬秦娘歌紫玉箫者,则有《鹧鸪天》云……又赠田叔通舞鬟,则有《南乡子》云……又赠王都尉晋卿侍姬,则有《殢人娇》云……而咏美人足之《菩萨蛮》,尤觉清丽。……似此体物绘情,曲尽其妙,又岂皆铜琶铁板之雄豪欤![15]2314-2315
从歌妓“乞词”,到词人“赠词”,再到歌妓唱词,都是在歌筵酒席间完成的,词的创作与传播基本上是同步进行,“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黄庭坚《木兰花令》),词人填词甫就,歌妓便应声而唱以侑酒,“蓄意新词轻缓唱,殷勤满捧瑶觞”(赵长卿《临江仙》)。
无论是词人“赠词”,还是歌妓于“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柳永《玉蝴蝶》),其结果都会使歌妓身价倍增。她们手中握有新词的首唱权,既是其睥睨同行的资本,也是其获取“金物”的筹码;而词人的作品也通过歌妓们的传唱而广为流播。词人与歌妓的双向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成了一个词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词作也如同其他产品在市场流通中转化为商品一样,不可避免地成了商业性的文化消费品。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扩展与延续,是造就宋代词坛辉煌繁荣局面的重要因素。诚如论者所言:“宋代的都市风情是带有强烈的商业文化气息的。如此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无疑地,会为词的繁荣提供肥沃的土壤。一方面,是空前发达的市妓声色的诱惑,一方面,是以涉艳为性情自然的文化心理,两者如风水相激,顿掀高潮。必须承认,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必然要体现其精神于文学创作之中,而与其他形态的文化所不同的是,商业文化可以直接以物质的力量来刺激文学创作使其朝着顺应自己意志的方向发展。”[16]
[1] 吴晓亮,林文勋.宋代经济史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145.
[2] 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J].中国文化研究,2002,(2).
[3] 脱脱.宋史: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3577.
[4] 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J].历史研究,2002,(5).
[5]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24-125.
[6]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8.
[7] 沈松勤,楼培.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宋初百年词坛考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8]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60.
[9] 苏辙.龙川别志: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74.
[10] 沈括.梦溪笔谈: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65.
[11]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45.
[13] 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J].思想战线,1999,(5).
[14] 王兆鹏.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J].学术月刊,2006,(9).
[15]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50.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9-15
张玉璞(196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宋代诗词研究。
I206.2
A
1002-462X(2015)12-014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