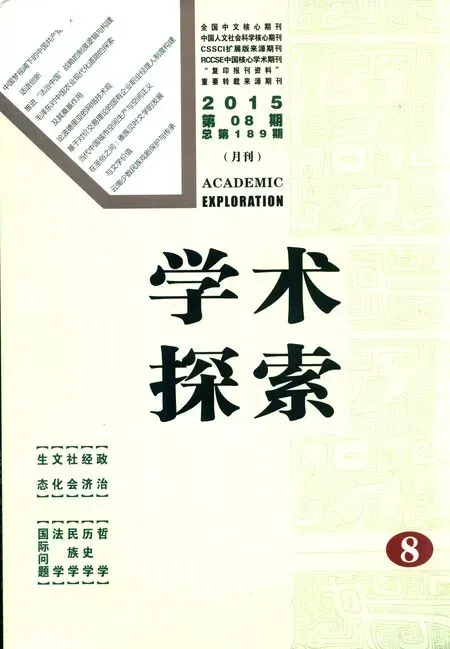无心而顺性与习以成性
——郭象玄学意义的功夫论刍议
刘 晨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无心而顺性与习以成性
——郭象玄学意义的功夫论刍议
刘 晨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郭象的玄学体系中,一方面强调独化自性,强调万物的差异性和性之不可变,另一方面也不否定后天的练习对成就性的作用,这就是郭象以独化论为基础的功夫论。独化即是要顺性而化,人要做到顺性而化则要无心,这既是从万物存在的本体论的角度对人的存在方式提出的要求,也是人的应然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依据。而如何成就人的独化,就是功夫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习以成性并非能够改变人的性,而是通过不断地反复练习,使人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使性之能能够全然的凸显出来,从而实现人生的逍遥。
独化;无心;顺性;习以成性;功夫论
以“独化”来描述万物存在的状态,从而消解单纯地以抽象的“无”或具体的“有”作为万事万物的本体所带来的矛盾,实现“有”和“无”、本体和现象的统一,是郭象本体论哲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对于郭象来说,这样一种哲学本体论上的建构显然不是单纯地以哲学的玄思为目的的,其目的依旧是用以构建其理想的政治人生状态:一方面以万物之“独化”的存在状态来解释人所追求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理想人生状态与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以万物因“独化”而得以生生不息,且因“独化之至”而使物与物之间得以相因,从而构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和谐宇宙,来作为他所追求的“民皆独化而天下大治”的理想政治局面的依据。而人如何顺应万物存在之道,以成就人自身的“独化”,无论是对其理想人格的构建还是理想政治局面的实现,无疑都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这也就是功夫修养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成性而独化。郭象正是以“无心而顺性”为基础,以“习以成性”为方法,形成了他的独化论意义上的功夫论。
一、无心而顺性——独化论在休养功夫上的要求
在郭象看来,“人之独化”和“物之独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依性而自生、自化,从而相因的。从万物之生成来看,物皆是依性而自生的;从万物之存在来看,物皆是依性而独化着存在的;从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来看,物皆是依性而独化之至从而相因的。物是如此,作为“万化之一遇”的人也应如此。所不同的是物无心,因而无知无虑,其独化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人有心,继而有知、有识、有思虑,而这种由心而发的“知”“识”“虑”的作用往往使人的行为违背自性的要求,所以要实现“人之独化”就要弃知忘虑、依性而自为,使心处于依性而自发的状态,从而实现对自身之独化和万物之独化的体悟,这种对自身独化及万物独化的体悟其实质是对万物独化的自觉,就是依性而用心,非有心而感:
“不虑而知,开天也;知而后感,开人也。然则开天者,性之动也;开人者,知之用也。性动者,遇物当足则忘余,斯德生也。知用者,从感而求,勌而不已,斯贼生也。任其天性而动,则人理亦自全矣。民之所患,伪之所生,常在于知用,不在于性动也。”(《庄子·达生注》)[1]
人可以认知万物,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弃知的目的并非要摒弃人的认知本身,只是要摒弃人基于自身闻见而形成认知的方法,基于自身闻见而形成的知并非真知,并不能认知事物的存在本身,只能使人处在无休止的对外物外在联系的认知之中,“知用者,从感而求,勌而不已”,其结果是“斯贼生也”;只有不依思虑而依性之自动,这样获得的知才是真知,“性动者,遇物当足则忘余,斯德生也”,也只有依性而自动,人才能自然地体悟人之性,实现自身的独化,“任其天性而动,则人理亦自全矣”。物也好,人也好,之所以能独能化在于“性之动”,而人往往基于心之“闻”“见”而为,从而违背了“自性”,其言、其行并非“性之动”的结果,而是心违性而动的结果,这样当然就不能体悟独化之道,亦不能实现人自身的独化了。
独化的实现在于“顺性”,“顺性”而为就是“无心”而为,显然,理解郭象的“性”就成了理解“无心”的关键了。那么如何来理解郭象的“性”呢?或者说如何来理解郭象的人之性呢?我们不妨来看看郭象关于人之性的论述:
“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庄子·骈拇注》)
“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庄子·骈拇注》)
“夫仁义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横共嚣嚣,弃情逐迹,如将不及,不亦多忧乎!”(《庄子·骈拇注》)
“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过去则冥,若滞而系于一方则见。见则伪生,伪生而责多矣。”(《庄子·天运注》)
这里郭象以“仁”为人之性,似乎和儒家的仁没有太大的分别,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多引几句郭象的言论:
“夫至仁者,无爱而直前也。”(《庄子·天运注》)
“谓仁义为善,则损身以殉之,此于性命还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庄子·骈拇注》)
“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情,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庄子·大宗师注》)
将这几段文字合在一处我们可以看到,郭象虽然讲“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但他的“仁义”的内涵及实现的途径已和儒家的“仁义”大相径庭,其“仁义”是玄学化了的“仁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看似和儒家的仁义相同,但实质却已大不相同。在郭象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和动物区别就在于人有能“仁”之性,“仁义”是人性所具备的,“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这样一种人能“仁”之性与郭象讲的牛马之性一样,都是性之自然的结果,非由外而强加,亦非人有意而为的结果,“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故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乎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庄子·缮性注》)。牛马能供人骑乘看似是人为的结果,实是牛马自身有供人骑乘之性,若牛马无此性,虽人力再强也无法骑乘之,正如人可骑乘牛马不能骑乘猪羊一样。人之“仁义”亦是如此,人之所以能行“仁义”是因人有能“仁”之性,从这一点上说,郭象和孟子有相通之处,把仁义归为人自身之性。但就“仁义”自身而言,郭象的“仁义”和儒家的“仁义”显然是不相同的:对儒家来说能“仁”之性就是“仁义”,“仁义”即是人的本性,“仁义”=人性,而要实现“仁义”的本性,就要行仁义之事,就要“克己复礼”;郭象讲“仁义”,“仁义”是“性之动”的结果,并非“人之性”本身,性动→“仁义”,要实现“仁义”就要依性而动,而非依“仁义”而求“仁义”。在郭象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是“然”、是“迹”,并非“所以然”“所以迹”,“信行容体而顺乎自然之节文者,其迹则礼也”(《庄子·缮性注》),这样的仁义是固定的,不变的,以这样的“仁义”来求“仁义”就是以“然”求“然”、以“迹”求“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离真正的“仁义”越来越远。而真正的“仁义”是“人性”的体现,这个“人性”是具体的、个体性的“人性”,是因时,因个体的人的不同而变化着的,“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所以儒家讲“仁者爱人”,郭象则讲“至仁无爱”;儒家讲“杀身成仁”,郭象则以此为“不仁”,讲“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儒家以忠、义、孝、悌为礼,强调外在的行为的约束,以此来达到内在的“仁”的要求,而郭象则以此为虚妄,强调“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的内在的依性而自为。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郭象的人之性和物之性是一致的,都不是以“性”是什么的下定义的认知方式来认识“性”的,而是从人与物地存在自身来认识“性”的。从存在自身来看,万物包括人都是如此这般的存在着的,而万物存在的根据都源于自性,且各不相同,这样的“性”显然是无法从认知的角度以抽象的方法来给它下一个定义的,因为存在着的事物各不相同,而不同之根据在事物之“性”,因而一个个具体之物的“性”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对于决定事物存在的“性”只能以描述、摹状的形式对万物依性而自生、自存、自然的状态来加以描述,或者从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内在结构上来理解,即事物的“有——无”统一性。[2]从这个角度看,人性也好,物性也罢,都是“性分”和“足性”两个层面的统一,正是基于“性分”,万物之间才有差别,才各不相同,所以鲲鹏能够翱翔于九天之上却不能穿梭于厅堂之间,燕雀能穿梭于厅堂之间却不能翱翔于九天之上,人能行仁义之事才有别于动物,才称之为人,但翱翔于九天、穿梭于厅堂、行仁义之事却非“性”本身,而是基于“性分”所形成的差异的体现,其根源在于“性”;正是基于足性,万物才能有不同于他物之能,这种能的具备正是自足其性的结果,鲲鹏之所以能够翱翔于九天之上,燕雀之所以能穿梭于厅堂之间,人之所以能行仁义之事,都是各自自足其性的结果,正因为各自自足其性,才有了各不相同的“能”。“性分”是就物之间的差异而言,“足性”是就物自身的存在而言,正是由于万物各自自足其性,所以万物才有差异;而万物自足其性的存在正是通过一个个有差异的具体的物体现出来的。显然,在郭象那里“仁”是人性的必然,是人依性而为的必然结果,这样一个结果也使得人和动物有了区别。而造成人和动物的这一区别的根源却不在“仁”而在“性”,因人之性使得人能“仁”,从而有别于动物,并非因“仁”而使人别于动物。这样,如何实现“仁”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如何来“依性而为”的问题。那么怎样做才能顺性而成仁呢?郭象说:
“世所谓无私者,释己而爱人;夫爱人者,欲人之爱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庄子·天运注》)
“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顺公乃全也。”(《庄子·应帝王注》)
这里,郭象以“无私”来解释“爱人”,反对“推己及人”的主张,认为这样一种推己及人实质上是以爱己为先,爱人为后,爱人之目的在于爱己,是“私”而非“公”。至于何为“公”、何为“私”,郭象进一步以任性为“公”,心欲为“私”,任性自为就是“公”,存心而为就是“私”,而只要任性而为就自然会存仁义,“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庄子·大宗师注》),存心而为则会离仁义越来越远。显然,这里的“人性”和“仁”的关系和郭象所述的“双遣”“无心”是一致的:就“双遣”而言,所要遣掉的并非是非本身,而是之所以形成是非之别的主客二分的认识构架,要遣掉这一构架的关键就在于要做到“无心”,即是使心处于镜子照物般的“无私”“无情”,全然由性而自发的状态之中,只有这样,人性之应然的“仁”才能得以实现,也唯有这样实现的“仁”才是真正的“仁”。反过来,为求仁义而行仁义之事,就是在行为之前先有了是非之别,而这个是非之别是建立在“知”“闻”之上的,非本于“性”,是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因而是“私”而非“公”,是用心的结果,这样做看似是行仁义之事,实是对“性”的背离,所得的也并非真正的仁。这样“顺性”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无心”的问题了,“顺性”即是要“无心”,亦唯有“无心”才能“顺性”,“顺性”是万物存在之道——“独化”的要求,而“无心”则是实现“顺性”继而实现“独化”的途径,“无心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顺性而为”的过程,而“顺性而为”则自然“得仁”,使人有别于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郭象将“性”“心”“仁”统一了起来:人要实现其自身的应然的存在状态就要“无心”而“顺性”,而“仁”是人性之应然,只要人能“无心”而“顺性”,自然就能行仁义之事,这样的无心而顺性、顺性而得仁就是人应然的存在状态,亦就是人的独化。
顺性就是无心而为,无心而为就是依性而为,要做到依性而为一方面要“无心而顺性”,即是要使心处于镜子照物般的“无私”“无情”,全然由性而自发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要无心而安于性分,就是要在性分之内而为,即是要安于性命。在郭象看来,物皆有性,且一旦化定成形则“性”不可变,人的能力的大小,人生命运的顺与不顺、遇与不遇,都是由“天性”所定,是无法凭借人自身的意愿改变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庄子·养生主注》)。有心之为就是超出了“性分”的范围而强力为之,而人往往容易用心去追求性分之外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改变人生之命运,只能是离性越来越远,平添人生的痛苦而已,“若乃开希辛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亡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措也”(《庄子·齐物论注》)。若是安于性分之内,依性而为,虽然不能改变性分之大小,命运之变化,却也能做到安居乐业,“凡得真性,任其自为者,虽复皂隶,尤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故知与不知,皆自若也”(《庄子·养生主注》)。
独化→顺性→无心,这是从万物存在的本体论的角度对人的存在方式提出的要求,也是人的应然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依据,问题是如何实现无心,进而实现独化?这就是郭象的功夫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习以成性——独化论意义上的修养功夫
郭象在肯定“性”之不可变的同时,并不否认后天的努力对“性”的作用,这就是郭象的“习以成性”说,即郭象的玄学意义上的功夫论。通过后天的练习,一方面可以成就性中隐而不显的能,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一步步进入到无心的状态之中。
在郭象看来,“性”是不可变的,“性”的不可变也决定了人的能力的大小和类型的确定性,能够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多大的能力,这是禀受于自然,是后天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但性分之内的能力的显现却不是当然的能够彰显出来的,这需要后天的“习”,以使“性”中本有的、尚未彰显出来的“能”转变为现实的“能”。换句话说,“性”中所定的能力的大小和类型是潜在的、可能的,而要把这样的能力转化为当下的、现实的,就必须通过“习”,以成就“性”。郭象说:
“言物虽有性,亦须数习而后能耳。”(《庄子·达生注》)
“习以成性,遂若自然。”(《庄子·达生注》)
“此言物各有性,教学之无益也。”(《天道注》)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大宗师注》)
“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虽希翼凤,拟规日月,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注》)
“夫积习之功为报,报其性,不报其为也。然则学习之功,成性而已,岂为之哉!”(《列御寇注》)
不难看出,郭象既坚持“性分”的确定性和不变性,同时又肯定了后天的“习”的必要性,并将“习”和“学”做了严格的区分,强调“习以成性”,反对“假学以成性”。在郭象看来,“能”是“性”的外在表现,是由“性”所确定的,对于这一点人是无法改变的,但内定于“性”的能力的彰显却需要后天的“习”才能凸现出来,“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耳”,这里的“自然之理”就是受之于自然的“性”,“性”之能的彰显需要经过冶炼锻造才能成之为有用之器,其能才能显现出来,正如钢铁要打造成器物才能彰显其性,牛马虽有供人骑乘之性,但也得经过训练才能供人骑乘。在肯定“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郭象坚决地反对“学”。在常人看来“学”与“习”是统一的,郭象则不以为然,他将“学”和“习”做了严格的区分:认为“习”是依性而为,看似有为实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因性而为,“教因彼性,故非学也”(《外物注》),而“学”则是依主体意愿有目的有意识的有所作为;“习”的目的是成就其自然本性,“然则学习之功,成性而已,岂为之哉”(《列御寇注》),而“学”的目的则是增益其所不能,求之于性分之外,是“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及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庄子·胠箧注》);“习”的结果是“习以成性,遂若自然”(《庄子·达生注》),以成就其自然本性,而“学”的结果则是“学弥得而性弥失”(《庄子·齐物论注》),背离其自然本性。显然,“习”和“学”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依性而为,顺性、依性而为、不越性分即是“习”,反之则是“学”了,而“习”可成性,“学”则失性。这里,郭象通过对“学”和“习”的区分充分肯定了后天的“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实质上依旧在强调“性”的先决性和不变性。“习”的依据和基础在于“性”自身,如何“习”,“习”什么也都是由“性”所确定的,“由外入者,假学以成性者也。虽性可学成,然要当内有其质,若无主于中,则无以藏圣道也”(《庄子·天运注》)。在《庄子·列御寇注》中郭象以“穿井”与“通泉”来解释“吟咏”与“通性”,进一步来说明“习”与“性”的关系,郭象说:“夫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无泉则无所穿,无性则无所咏,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识穿咏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在郭象看来,一方面本性之中潜在的、尚未彰显出来的能和地下的泉水一样,都是自然的存在,只是尚未显露出来,性有多大的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地下有多少泉水、有何种质地的泉水一样,都是人的意愿所不能决定的,是本之于自然的;另一方面,性中潜在的能要凸现出来,地下深藏的泉水要涌出地面又离不开人的努力作为。但就二者之间的本末主次关系而言,地下有泉水的存在显然是“穿井”的先决条件,只有首先具备这一条件,其后的努力、穿凿的功夫才有意义,才能有通泉的结果。如果地底下原本就没有泉水,那之后的一切努力,人为的功夫都不会有结果。这正如性中之“能”的存在是后天之“习”的先决条件一样,在“吟咏通性”的过程中,后天的种种“吟咏”、研习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作用只在将性尚未彰显出来的能凸显出来而已,若是“性”中本无作诗之能,再多的“吟咏”工夫也不会使其添一分作诗之能力,这样的认识倒是和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有着异曲同工之意,“天才,百分之一是灵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而世人往往看不到性的先决作用,只看到了人的后天的努力,将性之能的彰显归功于后天的强力作为,而背性为学,努力追求性分之外的东西,这样的做法实是本末倒置,其结果只能是学的愈多而离性越远,“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虽希翼凤,拟规日月,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庄子·齐物论注》)。明确了“习”和“性”的关系,我们就不难理解郭象的“习以成性”了,显然所谓“习以成性”并非指后天的“习”可以成就“性”、塑造“性”,而是指“性”之内在的“能”需要后天的“习”方可彰显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性”和“习”是统一的,“性”是“习”的前提和基础,“习”是彰显“性”的途径和方法。换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性”有“能”,后天之“习”才有意义;正是因为“性”之能隐而未显,后天之“习”才有必要。
那么,人如何来“习”呢?“习”又如何来成“性”呢?又或者说怎样的作为才叫“习”呢?事实上,郭象《庄子注》中提到“习”的地方并不多,除了上文所引导的,我们不妨再引一句“凡所能者,虽行非为,虽习非学,虽言非辩”(《庄子·庚桑楚注》),这里的“习”“行”“言”是在一个层面上的,是和“学”“为”“辩”相对的。显然,就人的存在而言,“习”“行”“言”就是人的存在本身,只要人存在着,就得有行为、有言谈、有举措,若无言谈行为举止则人如死物一般,也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了。郭象并不排除人的言行举止,只是强调真正的“习”“行”“言”应是依性而自发的,这样的“习”“行”“言”既是性之作用的结果,也是成就性的途径。而“学”“为”“辩”虽然也是人的行为,但却不是依性而发,是心之作用的结果,是对性的违背。在郭象看来,禀受于自然的性是先天所具备的,但性之能并非都能直接运用的①郭象并不否认有先知先能者,在《外物注》中就提到了有“泛然无习而自能者”,虽是对《庄子》原文的随文发意,但郭象并未否定这样的人存在。,多数的能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能力存在于事物自身,而要将其显露出来就必须经过不断的反复练习,使潜在的能彰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积习”的过程,也是成性的过程,“夫积习之功为报,报其性,不报其为也。然则学习之功,成性而已,岂为之哉”(《庄子·列御寇注》)。在这个过程中,“习”看似有意,实际却是由性而自发、顺性而为的自然而然的行为。这个过程就像有着舞蹈天赋的三两岁的幼儿,在听到音乐时会随着节奏而舞蹈,且乐此不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既定目标的设定,没有名利虚荣的追求,亦没有外在压力的胁迫,全然是自我内心喜好的自然流露,发之于性,见之于行,一步一步地与音乐融为一体。显然,这个“习”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将“性”中原本就具有的、潜在的能一步一步地彰显出来的过程,也是排除物我两分、以意代性的过程,其实质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使人达到“无心”的状态,成就人的独化的过程。
三、民皆独化而天下大治——郭象功夫论的人生目标
就“无心”而言,是实现人的独化的途径,所谓“无心”也并非是指不要人的思虑,只是指排除主客二分的认识架构,全然由性出发、依性而自为的状态,而如何来实现这样一种状态却是难之又难的,执着于排除主客二分,又何尝不是执着于是非之别,强调依性自为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以我之意愿指导我之行为?郭象反对“学”而强调“习”也正是基于此,“习”和“学”的区别不在于为或不为而在于是否依性而为,是否无心而为。正是在这样的区别之上,郭象看到了通过不断地反复练习,人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使“性”之能能够全然地凸显出来。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人可以一步步地实现“无心”的状态,从而实现人的独化。可以说,“无心”是实现人之独化的途径,同时也是人实现独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或境界,但更多的时候这样一种实现独化的途径却很难被人所把握,人只能从无心所体现出来的状态上去体悟,而“习”正是实现这一状态的现实的方法,这就是郭象所谓的“习以成性”,就是通过不断地练习来使人实现其本应呈现的存在的状态——独化,这就是他的玄学意义上的功夫论。
那么这样一种玄学意义上的功夫论的现实意义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郭象的功夫论是为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回归物一样的存在状态?那人岂不是如死物一般?显然不是,通过“习以成性”来实现人本应呈现的存在状态只是郭象功夫论的本体论基础,其功夫论的最终目的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讲,是为了实现人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安顿,即逍遥的境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讲,个体生命的双重安顿则是整个社会得以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在个体生命所能实现的人生境界上,郭象认为是有圣人的无待逍遥和常人的有待逍遥的区别的,“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庄子·逍遥游注》)在郭象看来,常人的逍遥是“有待”的,受到“自性”的局限,是只能在“性分”的范围内实现的逍遥,因而是相对的;圣人的逍遥是“无待”的,是圣人基于“自性”,无心而顺应万物的逍遥,这样的逍遥是内外玄冥的,是不仅能够实现自我的逍遥,而且可以达到与物同化,成就“万物与我齐一”的境界的,因而是绝对的。虽然常人的有待逍遥与圣人的无待逍遥,有着境界层次的差别,但从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无论是圣人的逍遥还是常人的逍遥都实现了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生存的双重安顿,都是适性而为的结果,二者的逍遥又是一样的。这样,通过“习”,可以彰显“性”之能,可以使人的行为回归“性分”的范围之内,做到适性而为,从而实现逍遥的境界,这就是郭象的“习以成性”的功夫论在个体生命上的体现。
从理想社会形态而言,郭象的功夫论的目的正是试图通过个体的适性逍遥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从独化论的角度讲,万物都是独化着存在的,而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独化之至的结果,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正是因为各自独化着存在才相互关联,和谐共存。从人与社会的角度而言,如果每个人都能实现自身的适性逍遥,那社会自然也就会安定和谐了,“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于所受;帝尧、许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各得其实,又何所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尧、许之行虽异,其于逍遥一也”(《庄子·逍遥游注》)。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之中,人人都能适性而为,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的程度,并且能安于自己的性分所确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没有越性而为的纷争,人人都能有生活的安定和精神的逍遥,这样的理想社会就是郭象的“习以成性”的功夫论的终极目标。
[1](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康中乾.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许抗生.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研讨[J].中国哲学史,2000,(1).
[4]王晓毅.郭象“性”本体论初探[J].哲学研究,2001,(9).
[5]刘笑敢.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Being Inadvertently Com pliant and Learning by Practice——Discussion of the Self-cultivation in Guo Xiang's Metaphysics
LIU Che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062,Shaanxi,China)
In Guo Xiang's Metaphysics,while self-transformation(or Du-hua)of one's nature is emphasized,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things and the immutablity of the nature,the role of practice is also important in improving it,which is Guo Xiang's self-cultivation on the basis of self-transformation.Du-hua is to be inadvertently compliant(or“Wu-xin”).From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this is the requiremen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the should-way of living of humans.Then how to achieve Du-hua is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self-cultivation.Learning by practice cannot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individual;however,by constantly repeated practice,the realm of being above worldly concerns can be reached,the perfect spiritual state of human beings come out and thus a free and unfettered life be achieved.
self-transformation;inadvertent;compliant;learning by practice;self-cultivation
B235.6
:A
:1006-723X(2015)08-0001-06
〔责任编辑:李 官〕
刘 晨,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