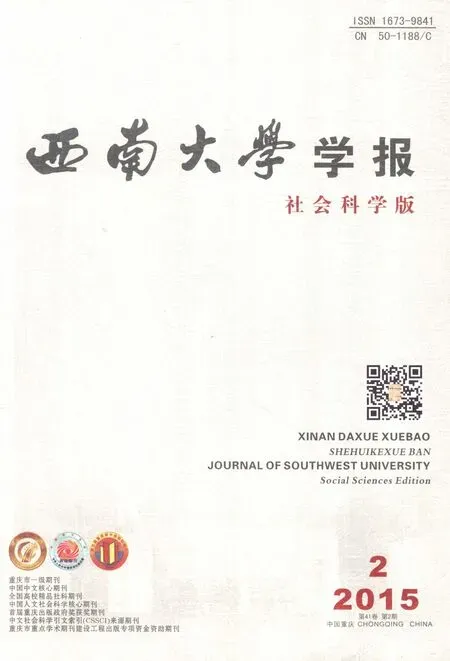北魏宗室的家族制建构与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北魏宗室的家族制建构与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拓跋宗室的家族制建构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它在形成长幼尊卑秩序的同时,也改变了宗室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早先植根氏族习俗的平均主义被废弃,服纪关系开始作为衡量的基准。与皇帝亲缘愈近,获取的资源越多,反之则少。当世五属,即在位皇帝的有服宗亲是优先照顾的对象,出服疏宗则渐趋边缘化。现实中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推行宗室族制改革的初衷,它强化崭新的家族身份,客观上起到肢解氏族体制的作用。
北魏;宗室;家族;五服制;利益分配
胡人的家族制改造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宗旨是要摆脱血亲氏族的羁绊,以适应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统治形势。拓跋宗室①“宗室”一词在这里特指皇帝所在之族。据《魏书》、《北史》“宗室列传”的记载,北魏官方以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作为宗室的范围。作为胡人贵族的总代表,在改革过程中自然首当其冲。对此,学界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如台湾学者康乐先生的《孝道与北魏政治》[1]指明了推动宗室族制改革的礼制因素。大陆学者柏贵喜先生的《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2]分析了宗室族内关系的变更。罗新先生的《北魏直勤考》[3]探讨了宗室直勤传统与家族制过渡阶段产生的激荡。本文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侧重考察宗室家族制建构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联,进而从现实层面管窥其运作机制。
一、北魏宗室家族制关系的建构
北魏宗室的族群结构长期受到草原时代“直勤”遗俗的制约和影响。罗新先生研究发现,在南朝正史及出土文献中,拓跋宗室名讳之前通常标注“直勤”字样,“直勤”语义实际上与“宗室”接近,其深刻内涵在于“反映了具体氏族内部、或具体家族内部血亲成员的平等关系,收继婚或相关婚姻形态及制度所造成的血亲男性成员间亲缘关系的混乱与复杂,或许是这一平等关系的社会基础”[4]。简而言之,错乱的婚姻关系使拓跋男性成员间难以区分亲疏行辈,因而彼此处于对等的地位。直勤制度是氏族社会的产物,但它并未随着北魏步入文明国家阶段而退出历史舞台,在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始终是宗室内部凝聚的基本纽带。
由于直勤遗俗的束缚,宗室族群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政权建设,还不时引发激烈的夺权斗争,干扰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有鉴于此,孝文帝决心利用汉人的五服制对宗室进行系统的家族制改造,借助身份级差导引伦理道德的贯彻。五服制属于华夏丧礼的范畴,它用丧服的形制和丧期的长短来衡量人们的亲疏关系。五服由近及远分别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5]2。宗室以帝系为轴线,根据各自与皇帝的亲缘关系被置于相应的服纪位置上。孝文帝参考的方案极有可能是萧齐王俭所撰,代表东晋、南朝礼制发展最新成果的《丧服记》。此书于太和十七年(493)随王肃北归而传入[6]16,加速了改革的进程。当年,平城皇宫中举行了隆重的宗室家宴,以乡饮酒礼的方式确认彼此的行辈年齿。《魏书》卷七《孝文帝纪下》:“(五月)壬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旋即又“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7]卷一九《任城王云传附澄传》,p464。宗室全新的服纪身份通过所坐席位和行酒轮次得以生动展现。此后,宗室在表述族内关系时基本使用五服术语。如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诏曰:“朕宗室多故,从弟谐丧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朕欲遵古典,哀感从情,虽以尊降伏,私痛宁爽。欲令诸王有期亲者为之三临,大功之亲者为之再临,小功、缌麻为之一临。广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临。”[7]卷二○《广川王略传附谐传》,p526意即根据宗室服纪的远近确定皇帝临丧吊祭的次数。这条史料不禁引发笔者的联想,除死后享受荣誉外,五服制在其他权益分配过程中是否也会起到类似的尺度作用呢?
二、五服制与宗室阶层的利益分配
在直勤体制下,人们对于血缘亲疏不甚看重,利益分配还秉承着氏族时代平均主义的思想,厚此薄彼的现象被严格杜绝。但在家族背景下,“亲亲”的理念深入人心,资源的配置相应地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这种巨大的反差集中反映在家族制改造前后宗室成员的身上。下面将从宗室名分、授爵、仕宦、法律和经济五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一)家族制改造前后的宗室结构
围绕拓跋族制的演进,宗室资格的判定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事关宗室族籍的存废、名号的有无,乃切身利益之所在。太和改制之前,凡是以拓跋为姓氏,拥有直勤称号者皆可视为宗室。这个群体涵盖极广,上限可至分部之始的献帝邻①罗新先生考证直勤是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这与《魏书》、《北史》“宗室列传”体例正合,参见其著《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也有学者认为,直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宗室,况且力微始祖尊号乃北魏建国后的追赠,而直勤起源甚早,以后世之事比附前代是错误的,直勤的上限应是七分国人的献帝邻,最直接的证据便是祖出圣武帝诘汾的源贺(贺豆跋)亦有直勤名号,参见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向下则漫无边际。孝文帝充分发挥五服辨族之功效,认同“当世五属”的原则,把宗室限定在以本人为中心,上自高祖、下到玄孙、旁及五世的狭义的家族结构内。易言之,只有在位皇帝的有服宗亲才是宗室。若配合宗庙序列,这个范围可概括为“四庙子孙”,前文提及的两次宗宴,召集的对象就是他们。于是,每当新君登基,就会有大批宗室因出服而被革籍,丢掉了天潢贵胄的荣耀。比如孝文帝的四庙断至世祖太武帝,则太武以前诸帝后裔就要剔除出宗室,后世皆以此类推。孝文帝死后,大规模辨族尽管停止,但个体甄别仍不时发生。孝明帝时,出服宗室景穆皇孙元遥除籍、道武曾孙元继停祭事件算是后续未平的余波[7]卷一九《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卷一○八《礼志二》,p446、p2763。实际上,北魏后期充分借鉴中古北方汉人的宗族体制,并未强制清除出服者,相反还对其宗室身份予以保留和默认[8]。但在等级待遇方面,出服疏宗与服内近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近宗荣宠备至、礼遇优厚,疏族却时常遭受排挤和歧视。如元树攻讦元叉,“险慝狼戾,人伦不齿,属籍疏远,素无问望,特以太后姻娅,早蒙宠擢”[7]卷一六《京兆王黎传附叉传》,p406。孝庄帝抨击元天穆,“宗室末属,名望素微,遭逢际会,颇参义举。”[7]卷一○《孝庄帝纪》,p266前者内心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
(二)家族制改造前后的宗室授爵
爵位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同时又连带着丰厚的权益,国家授爵可以起到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之功效。北魏照搬西晋的五等贵族爵,宗室在封君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指出的是,在族制变革前后,宗室各支系在爵位数量和级别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遍检史料,北魏太和中期以前,宗室授爵记录共106次,其中远属4次,神元系6次,章帝系2次,昭帝系2次,桓帝系4次,平文系6次,烈帝系10次,昭成系29次,道武系8次,明元系7次,太武系5次,景穆系12次,文成系5次,献文系6次[9]32-46。由此可见,除昭成系因人丁兴旺、功绩显赫而稍占优势外,宗室其余诸房在爵位的配置比率上大致对等。再具体分析爵级,同期宗室获王、公、侯一类高爵者共97人,其中远属3人,神元系6人,章帝系2人,昭帝系2人,桓帝系4人,平文系3人,烈帝系7人,昭成系27人,道武系8人,明元系7人,太武系5人,景穆系12人,文成系5人,献文系6人。高爵在宗室各房的分布亦相对均衡。尽管天赐爵制规定了皇子自动封王的特例[7]卷一一三《官氏志》,p2973,充分保证传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其余宗室晋身高爵的路径同样宽敞,他们完全可以凭借事功与之分庭抗礼。总之,北魏早期,宗室授爵的几率区别不大,没有显现出悬殊的落差,血缘亲疏或许存在一定影响,但远非主导性因素。太和改制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期,孝文帝授予宗室爵位28例,其中有服宗亲18例,且14例是侯以上的高爵;宣武朝苛禁宗室,授爵仅3例,暂且不论;孝明朝宗室授爵28例,近宗18例,又15例品登王公;孝庄朝宗室授爵27例,近宗18例,全部位列侯爵之上①该数据采自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9年,第49-69页。依据“当世五属”或“四庙子孙”的标准,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有服宗亲的上限分别是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孝庄帝本彭城王勰之子,即位后尊亡父为帝,因其祖出献文帝,故复以景穆帝为宗亲界限。。综合统计,北魏后期,在宗室全部86个授爵记录中,人数寡少的服内近宗竟有56例,占到总数的64%;就封授高爵而言,近宗多达44例,疏族只有12例。这些数据无不表明,经过家族制建构,宗室在授爵方面的均势平衡被彻底打破,皇帝的服内近宗处于绝对的强势状态,五服体系居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若以个案验之,我们发现,同等条件下授爵,服纪的远近决定爵级的高低。如并肩反抗元颢傀儡政权、拥戴孝庄朝廷立功,近宗景穆后裔元暹可以封王,稍有距离的道武后裔 元 均 封 伯 爵,而 最 为 疏 远 的 平 文 后 裔 元 子 思 仅 授 子爵[7]卷一九《京兆王子推传附暹传》、卷一六《阳平王熙传附均传》、卷一四《高凉王孤传附子思传》,p444、p392、p354。
(三)家族制改造前后的宗室仕宦
北魏深受中古门阀制度的影响,士人的仕途前程基本取决于家世门第。宗室虽贵为皇亲,但也不能例外,他们凭恃父祖的恩荫获得中正乡品[7]卷一一三《官氏志》,p2974,而后再由吏部依据乡品授予相应的官职。北魏早期,宗室子弟晋身,只计世资高下,未见亲缘之分。在王的层次,诸王无论远近,惯以诸大将军起家,以三都大官或州镇长官迁转[7]。亲尊莫二的皇子亲王最为典型。如明元皇子乐安王范,泰常七年(422)授中军大将军,后“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7]卷一七《乐安王范传》,p414。太武皇子晋王伏罗,“真君三年(442)封,加车骑大将军。后督高平、凉州诸军”[7]卷一八《晋王伏罗传》,p417。景穆皇子南安王桢,“皇兴二年(468)封,加征南大将军、中都大官,寻迁内都大官。高祖即位,除凉州镇都大将”[7]卷一九《南安王桢传》,p493。其他宗室王同样如此,平文后裔高凉王那,“袭爵,拜中都大官”[7]卷一四《高凉王孤传附那传》,p350。道武皇孙武昌王提,“拜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平原镇都大将。……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统万镇都大将”[7]卷一六《河南王曜传附提传》,p396。太武皇孙东平王道符,“袭爵,中军大将军。显祖践阼,拜长安镇都大将”[7]卷一八《东平王翰传附道符传》,p418。足证诸王仕宦权利之平等。普通宗室亦不辨亲疏,只要父祖有相当级别的官爵,便可保举进入权力中枢内侍内行系统供职[11]189。如桓帝之后拓跋郁,“初以羽林中郎内侍”;拓跋目辰,“初以羽林郎从太祖南伐至江”[7]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p347、p348。烈帝后裔拓跋大头少年英武,“擢为内三郎”;拓跋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7]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p362、p357。昭成子孙拓跋干,“少有父风,太宗即位,拜内将军、都将,入备禁中”;拓跋素,“少引内侍,频历显官”[7]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p372、p375。上述诸人与皇室的距离参差不齐,但却大体遵循相同的仕进程序,血缘关系似无足轻重。北魏早期,宗室可以无差别地介入政治活动,疏族像近宗一样有跻身最高权力领域的机会。如神元之后拓跋婴文,“太宗器之,典出纳诏命,常执机要”[7]卷一四《建德公婴文传》,p345。章帝之后长乐王寿乐,“高宗即位,寿乐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总揽朝政,位极人臣[7]卷一四《长乐王寿乐传》,p346。烈帝之后拓跋处真,“位殿中尚书,……委以大政,甚见尊礼”[7]卷一四《扶风公处真传》,p364。更为疏远者如拓跋屈,位列明元朝的八公会议,行右丞相职,“命掌军国,甚有声誉”[7]卷一四《文安公泥传附屈传》,p365。拓跋吕在太武帝时,“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见尊重”[7]卷一四《江夏公吕传》,p349。可以说,这个时期,宗室成员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共同起到政权基石的作用。
孝文帝汉化改革彻底颠覆了宗室内部既有的权利配置格局,近属开始凌驾于疏宗之上,成为掌控权力的重心。实际上,二者的差距早在仕宦的起点便已彰显。北魏后期,同等条件下的宗室入仕,亲缘近的往往更受优待。以父祖皆有王公重爵者为例,作为骨肉至亲的孝文、献文后裔一般以五品官释褐,如元邵、元顼、元诞、元睿、元谌的起家官是从五品上阶的通直散骑侍郎,元诲、元子直、元端的起家官是正五品上阶的散骑侍郎;略微疏远的文成后裔则以六品官解巾,如元子永、元礼之、元子邃的起家官是从六品上阶的给事中;位于服纪边缘的景穆、太武后裔六、七品起家者兼有,过渡性质明显,如元崇业、元灵曜、元晔、元熙、元融的起家官是正七品下阶的秘书郎,元愿平、元显魏、元义兴、元略、元诱、元肃、元赞远的起家官是正七品上阶的员外散骑侍郎,元固的起家官是从六品下阶的太子舍人;太武以前诸帝后裔改革之际业已出服,七品起家乃为常制,且职务类型多为幕府僚佐,如元晖、元愔、元弼、元贤、元忻之、元禹、元法僧、元馗、元罗、元均之的起家官都是七品以内的各类参军[9]119-128。至于那些宗室末枝,只能补入宗子羽林,赐八品宗士出身[7]卷一一三《官氏志》,p3004。据此可知,改革之后,服属远近成为制约宗室入仕的又一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国家重要职位和公权日益向宗室近属集中。据张金龙先生统计,孝文帝时,宗室担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地方州镇长官分别是114人次和57人次,其中有服宗亲太武以来诸帝后裔有96人次和44人次,各占总数的84%和77%,具有压倒性优势[12]106。这种优势突出体现在孝文帝晚年钦定顾命大臣“六辅”的人事安排上,位居其列的宗室咸阳王禧、北海王详、任城王澄和广阳王嘉均是有服宗亲[7]卷七《孝文帝纪下》,p185。若从洛阳时代统治结构整体来看,近宗占据中央及地方要职的比率也都远超半数[9]134、158。所以说,家族制改造使宗室势力出现分野,近宗是最大的赢家,而疏族则渐趋边缘化。
(四)家族制改造前后的议亲范围
北魏移用魏晋律法,条文中有“议亲”的规定,即皇亲国戚有罪,可享受司法复议、减免刑罚的特权。宗室非违,援引议亲便能逍遥法外[13]。孝文帝改革宗室族制前后,议亲的适用范围大相径庭。《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荫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宣武帝)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宗室疏族元显富仰仗“皇族有谴,皆不持讯”的旧制逃脱罪责,推知北魏前期的议亲是泽及宗室全体的。不过,后来情况发生改变,尚书李平故而提出限断的主张。宣武帝诏书“先朝既无不讯之格”云云,说明孝文帝对议亲规则做过调整,只因未及实施,才使元显富之流有机可乘。今本《魏书》保存的《议亲律》很可能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其文曰:“非唯当世之属籍,历谓先帝之五世。”[7]卷一○八《礼志二》,p2765时人对此的诠释是“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7]卷七八《张普惠传》,p1743。也就是说,议亲仅限历代皇帝的服内亲属,这个范围相当于广义的家族结构,它虽比辨族的尺度宽泛,但远逊于传统意义的宗室。需要注意的是,北魏后期的议亲资格也是以服纪关系进行界定的。
(五)家族制改造前后的宗室禄恤
为保障宗室的日常生活,朝廷以禄恤的名义向其发放经济补助。伴随家族制关系的形成,宗室享受禄恤的对象大为缩减。北魏早期,禄恤表现为人口、牲畜等战利品的赏赐。如道武帝天兴元年(398),攻克后燕邺城,“收其仓库,诏赏将士各有差”[7]卷二《道武帝纪》,p31。太武帝始光三年(426),“车驾至自北伐,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太平真君八年(447),“行幸中山,颁赐从官文武各有差”[7]卷四《太武帝纪》,p71、p101。文成帝兴安二年(453),“诛河间鄚民为贼盗者,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7]卷五《文成帝纪》,p113。宗室作为征伐、镇戍的主力,都有获赏的资格,数量的多少取决于战功的大小和官爵的高低,与血缘亲疏毫无关联。宗室族制改革后,这种禄恤只提供给皇帝的有服宗亲,孝文帝“制皇子封王者、皇孙及曾孙绍封者、皇女封者岁禄各有差”[7]卷七《孝文帝纪上》,p155,又“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7]卷七八《张普惠传》,p1743。太和末年,财政吃紧,孝文帝下令:“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恒贡,亦令减半。”[7]卷七《孝文帝纪下》,p184献文皇子彭城王勰带头响应号召,“表以一岁国秩、职俸、亲恤以裨军国”[7]卷二一《彭城王勰传》,p574。可见,禄恤是宗室近属独享的特殊优礼。疏宗既已出服,便再也无由获得了。《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所载“七庙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则爵禄无穷,枝庶则属内贬绝”,描述的就是这个事实。
三、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拓跋氏族的解体
北魏宗室的五服制建构是拓跋族群进化的里程碑,它变平等无别的直勤传统为亲疏有序的家族关系,加速了氏族组织的瓦解。诚然,礼制因素是孝文帝厉行改革的重要初衷,旨在借助其载体灌输华夏的纲常名教[14],以使宗室明确自身角色,巩固皇权专制。但是,与利益相关的现实考虑也是推动改革的原动力。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他们的利益诉求与日俱增,起先那种面向全体宗室无差别的资源分配难以为继,压缩受益范围势在必行,而家族制蕴含的“亲亲”原则恰可作为断限的基准。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众所周知,数额巨大的宗室禄恤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到了多事之秋的太和末叶,这笔开支令本已窘迫的国库捉襟见肘。于是,削减宗室禄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孝文帝的心腹近臣元遥日后回忆道:“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7]卷一九《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p446也就是说,孝文帝辨族意在裁撤宗室员额,以节省开支、补贴军用。同理,准五服甄别议亲资格可大幅减少法律特权的拥有者,防止非违宗室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而按照服纪远近配置官爵的数量和等级,则是要堵塞宗室仕宦猥滥的趋势,确保国家公权的严肃性,同时也是协调统治结构、平衡力量对比的有效之举。对皇帝而言,将宗室限定在狭小、闭塞的准入群体内部,着力打造精英家族,又有助于提升皇权的威严。总之,北魏宗室的家族制建构不是改革家的异想天开,亦非汉人理念的跟风盲从,它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是统治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要求。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经过家族制改造,宗室的权益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平均主义的信条被全盘摒弃,好处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与皇帝或帝系服纪的远近。当世五属,即在位皇帝的有服宗亲成为优先照顾的重点,出服疏宗则被排除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皇族内部的冲突,起初还是低烈度的维权纠纷。如为争取禄恤,“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7]卷七八《张普惠传》,p1743。元遥不满宗籍被革,忿然上书:“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7]卷一九《京兆王子推传附遥传》,p446江阳王继抱怨太庙祭祖资格的丧失,言道:“臣曾祖是帝,世数未迁,便疏同庶族,而孙不预祭,斯之为屈,今古罕有。”[7]卷一○八《礼志二》,p2763元遥乃景穆皇孙、元继是道武曾孙,虽为先帝五世,但与当朝的孝明帝早已无服可言,故有此辩。矛盾日积月累,又缺乏合理的疏导,后来竟激化为针锋相对的政争。《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鸷传》:“曾于侍中高岳之席,咸阳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众皆下之,不敢应答。坦谓鸷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鸷即答曰:‘斩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众皆失色,鸷怡然如故。”元坦的父亲便是元鸷口中的“反人元禧”,他们属献文后裔,乃服内近亲;元鸷祖出平文,与皇室血缘极端疏远。双方台前幕后的较量无疑是当时宗室关系的真实写照。由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宗室疏族纷纷走向朝廷的对立面[15]。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上文提到的元鸷,他在河阴之变中坐视同胞血花飞溅,还与元凶尔朱荣联结。应该说,疏族扮演了北魏政权掘墓人的角色,这是构想改革的孝文帝始料未及的。总括以上,实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及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导致宗室共同目标的确认和身份归属感严重弱化,这才是切割拓跋氏族肢体的真正利刃。
综上所述,拓跋宗室的家族制改造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其宗旨不仅是要确立长幼尊卑的身份秩序,同时也是搭建资源配置的等级框架。新的利益结构以皇帝为圆心,宗室根据服纪关系分置于不同层位的外圆上,距圆心越近,地位越高,发展空间越宽广,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反之则少。时人甚重当世五属的界限,服内近属和出服疏宗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如此规划的现实目的是限制宗室特权,减轻因人口激增而不断膨胀的利益占有,并以此强化“亲亲”的家族理念,巩固族制改革的成果。这其实是向汉族王朝宗室政策和宗法原则的回归,《孟子·离娄下》中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汉室宗亲“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16]卷一一一《论财》,p2721。但是,利益分配不均引发宗室对固有身份的质疑,它在碾碎氏族体制之余也为北魏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1]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G].“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册,1993.
[2]柏贵喜.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罗新.北魏直勤考[J].历史研究,2004(5):24-38.
[4]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G]//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1):43-47.
[8]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9]严耕望.北魏军镇制度考[J].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3(34):199-261.
[10]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M]//魏晋南北朝史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1]张金龙.北魏孝文帝时期统治阶级结构试探[M]//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
[12]刘军.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J].云南社会科学,2011(3):143-146.
[13]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J].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64):51-87.
[14]刘军.北魏宗室亲恤制度试探[J].甘肃社会科学,2011(4):173-177.
[1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张颖超
K239
A
1673-9841(2015)02-0169-06
10.13718/j.cnki.xdsk.2015.02.021
2014-05-10
刘军,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北魏宗室阶层士族化进程研究”(2012QY046),项目负责人:刘军;吉林大学“985工程”建设基金项目资助,项目负责方: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