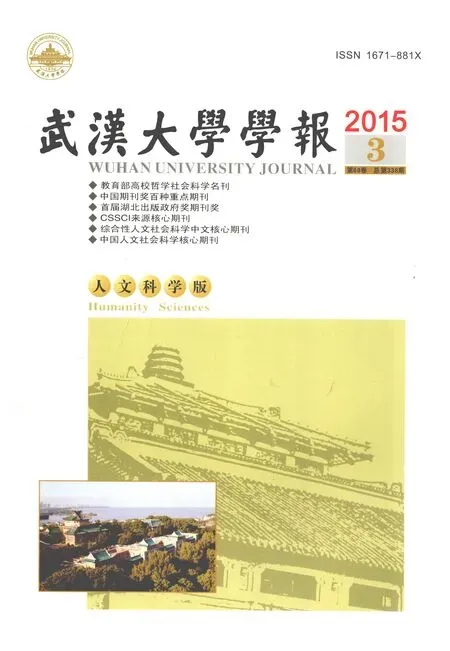始于阳明心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周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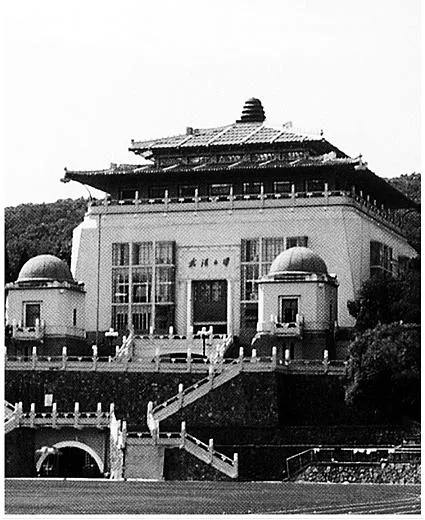
始于阳明心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历史演变
——兼论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周可真
摘要:古代哲学,无论中、西,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都还处在原始综合状态,至16、17世纪,中、西哲学才各自形成其偏向明显、取向明确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逐渐形成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两个明显不同的研究传统,中国则从16世纪初开始向文化哲学转型。中国文化哲学起步于阳明心学,其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作为把握人性(“良知”)的方法,这种直觉型文化哲学后来过渡到由黄宗羲开创的通过史学来把握人性(“本心”)的史学型文化哲学和顾炎武开创的通过经学来把握人性(“性与天道”)的经学型文化哲学,而清代朴学和晚清今文经学则分别提供了解读经史的不同诠释方法——前者属于信息还原法,后者属于信息重构法。现代“中”“西”“马”均属于诠释性哲学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哲学来把握人性的哲学型文化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自休谟、康德至文德尔班、狄尔泰一脉的哲学固然属于文化哲学,就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标准科学哲学”亦具有文化哲学属性。中西哲学有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自然哲学; 文化哲学; 阳明心学; 中国传统文化
一、 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传统哲学的两种研究传统
在一个被当今世界公认并同称为“哲学”的学术领域里,其实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被一切自称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所共同接受的哲学概念。对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1892)中曾有所论:
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根据这种目的提出来的概念,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自称为哲学的思维活动的结构。*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页。
也因为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中只能这样来描述哲学: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12页。
面对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定义纷纭、莫衷一是的哲学概念,若非随心所欲而自行其是,像文德尔班、罗素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权威哲学家的意见,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些普通学者从事哲学研究的必要参照和主要依据了。
罗素对于哲学的总体看法,与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按照中世纪到近代对于哲学的分类习惯对哲学所作的分类是大致相应合的,后者将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大门类,其中“理论哲学”被认为是探讨“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和“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实践哲学”被认为是探讨“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包括伦理学、社会学、法律哲学以及美学、宗教哲学*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31~33页。。显然,罗素所指哲学中属于广义科学范畴的那部分内容大致即是文德尔班所说的理论哲学,属于宗教与伦理范畴的那部分内容大致即是文德尔班所说的实践哲学。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亦称“巴登学派”或“西南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哲学分类中所使用的所谓“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概念是来源于康德所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而康德是以二元论思维来进行“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文德尔班语),通过这种理性批判,康德把在他看来是彼此不可调和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别判归于科学和哲学,将理论理性判归于科学、实践理性判归于哲学,主张科学与哲学“井水不犯河水”地各行其道,所以,综合罗素和文德尔班对哲学的总体看法,哲学区别于神学与科学的学术特征便可描述为:哲学坚定地信靠被神学弃之不用的人类理性,又不是像科学那样单靠理论理性,而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兼取并用来开展自己的研究。
这一描述至少是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兼取并用。这一思维特征在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学派乃至于不同的民族哲学通过其具体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所显示出来的两种基本研究向度:偏倚于理论理性的研究向度和偏倚于实践理性的研究向度。按照德语世界的科学(wisseschaft*德语wisseschaft(科学)一词的含义与英语science(科学)一词的含义不同,对此,英国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辨析道:“拉丁语词Scientia(Scire,学或知)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的简称,虽然最接近的德语对应词Wisseschaft仍然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我们所谓的science(科学),而且包括历史、语言学及哲学。”(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9页。))概念,可以把这两种向度的哲学研究当作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领域的哲学研究和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领域的哲学研究来理解,从而也就可以把它们当作分别属于自然哲学范畴和文化哲学范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研究来理解。这就是说,当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兼取并用看作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时,这就意味着是肯定和承认传统哲学发展中实际并存有两种不同向度和不同性质的研究传统——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在理论上,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按照著名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的观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是以经由对经验实在的抽象所获得的概念来把握事物的普遍法则,而文化科学是以对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的描述来展示事物的特殊个性;另一方面,因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故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个文化现象都必有价值意义,所以文化科学非谈论价值不可,这意味着这两大学科是各有其特殊的思维模式:自然科学是非评价的思维模式,文化科学是评价的思维模式*参见韩林合:《石里克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3期。。自然哲学固然不等于自然科学,文化哲学也不等于文化科学,但是自然哲学有同于自然科学者——都无需谈论价值,都属于非评价思维;文化哲学也有同于文化科学者——都必须谈论价值,都属于评价思维。
其次,按照我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哲学权威学者江天骥先生的说法——“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主张科学的职能在于探索真理,哲学则揭示意义,特别是科学概念、假说或理论的意义,这是两者的区别及关系。”*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按:江先生这里所讲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哲学”是指他所谓的“意识哲学”及“文化哲学”;同时,江先生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一个在内涵上被他严加限制了的极狭义的文化哲学概念,这不同于本文用以标志在实践向度上所开展的哲学研究的广义文化哲学概念,但二者在均有别于自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意义上是同义的。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区别也可描述为前者“探索真理”,后者“揭示意义”,或按“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观点*2011年12月17日,清华大学学生会时代论坛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办了“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对话(中国新闻网2011年12月18日报道:《杨振宁出席清华“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对话》, http://www.chinanews.com/tp/2011/12-18/3540307.shtml)。,将其区别描述为自然哲学“求真”,文化哲学“求善”。
再次,按照文德尔班的观点,理论哲学所要把握的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规律,实践哲学所要把握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文德尔班本人所提倡的“文化哲学”则是属于他自己所讲的“实践哲学”范畴,它是研究被作为整体看待的文化的发展目的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的的学问(参见周可真:《构建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文化哲学的首倡者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概念的解读》,载《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据此,又可将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前者研究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后者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
要之,作为传统哲学的两种基本研究传统,自然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靠和运用求真的理论理性,以非评价思维来探索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文化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靠和运用求善的实践理性,以评价思维来探讨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
二、中西方古代哲学的共性特征: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然未分的原始综合
作为统一于传统哲学的两种研究传统,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不仅同时存在于古代哲学中,而且无论是在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它们都表现出了总体上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特征。
西方哲学固然是起始于“对于自然真理的探索”,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论及古希腊早期的哲学,把那些从事“对于自然真理的探索”,“从可感觉事物追求原理”,并认为“万物唯一的原理就在物质本性”、“万物的唯一原因就只是物质”的“初期哲学家”称为“自然哲学家”(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32页)。,但是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残篇表明,他不但研究自然,同时也开始关注人事和探求人的活动的目的了。他是以精神宁静与肉体愉快的结合所达到的“怡悦”为幸福生活的最高境界*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95~297页。,但同时强调“对人来说,精神与肉体二者应该更注意精神。精神的完善可以弥补躯壳之不足,但如果没有智慧的精神,躯壳再强壮也没有用”*转引自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297页。。苏格拉底就更是摒弃了他早年曾研习过的自然哲学,转而专注于人事研究了,他说:“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5页。苏格拉底所求诸心灵世界的真理,是兼具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双重意义的,即它既是知识范畴的真理,又是价值范畴的正义。在苏格拉底哲学中,求真与求善、知识与道德是一致的,这与“合真善”(张岱年语)的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明显一致性,只不过相对说来,苏格拉底是明确地强调了“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297页。,而中国先秦儒家与道家均未尝如此鲜明地强调过知识对于道德的先在性、根源性。
但是,道家老子讲“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这其实隐含“无得道之知则无守道之德”的观点;而庄子虽然表面上显得似乎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其实和老子一样,他也是以“道”为“知”与“德”的标准,在他看来,合“道”之“知”则为“至知”*《庄子·齐物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加矣!”,合“道”之“德”则为“至德”*《庄子·马蹄》:“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只是较诸分辨“母”“子”、“道”“德”*《老子》分《道篇》与《德篇》,即有分辨“道”“德”之意。通观《老子》全文,其“道”与“德”是截然分明的。的老子,他不是像后者那样将“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的“得道(母)”与“常德不离”( 《老子·二十八章》)的 “守道(母)”分作两截,而是将“至知”和“至德”融合于“齐物”——“齐物”具有“以为未始有物”的“齐物之知”(“至知”)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之德”(“至德”)双重意义(《庄子·齐物论》)——在“齐物”境界里不再有“知”与“德”的分别。
与道家老子相似,儒家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又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更是明显蕴含“不知礼则无仁德”的观点,只是到了儒家“亚圣”孟子那里,他将“仁”“义”“礼”“智”四者并举而将“智”放在末位,这大异于孔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之说对“智”“仁”“勇”三者的前后排序,从而显示出孟子有将“仁”高置于“智”之上的倾向——后来发生于宋明理学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其实就是关于知识(“智”)与道德(“仁”)之相互关系的争论,其论争诸方都肯定抑或至少不否定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不过相对说来,主张“知先行后”的朱熹是偏执于强调“道问学”的优先性而近似孔子以“智”为优先的思想;主张“立先乎其大者”的陆九渊是偏执于强调“尊德性”的优先性而近似孟子以“仁”为优先的思想;而主张“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王守仁则有模糊乃至于消除知识与道德的界限而使其融成一片的明显倾向。
据实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将知识与道德融成一片的显著特征,因为他把探究被他认为既是“万物的原因”又是“世间第一原理”的“神”的哲学凌驾于其他一切学问之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如此写道:“于神最合适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圣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正如此:(1)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2)这样的一门学术或则是神所独有;或则是神能超乎人类而所知独多。所有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6页),成为如康德所说的“一切学问之女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一版序文第1页。,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是将其哲学所立的“通式”——被他看作是对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的理性都起作用的“世界第一原理”*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28~29页。——当作自然真理和人间正义的“极因”(吴寿彭语)来看待了,而他对于这个“真善合一”之“神”(“极因”、“第一原理”)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实际上正是在他所谓的“理论”的意义上对古希腊哲学最初的自然研究和继之而起的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等哲学家的人事研究的一个综合,其《形而上学》便是这种综合性理论研究的成果,其《物理学》、《政治学》、《尼可马各伦理学》等则是以其形而上学的“通式”作为逻辑大前提来进行演绎性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自然哲学的内容,也有文化哲学的内容。到了古希腊哲学晚期,“斯多葛派认为哲学有三部分:物理学、伦理学与逻辑学。当我们考察宇宙同它所包含的东西时,便是物理学;从事考虑人的生活时,便是伦理学;当考虑到理性时,便是逻辑学,或者叫做辩证法”*《哲学原理发展概述》编写组:《哲学原理发展概述》(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页。。其后,“在中世纪,更多的在近代,头两门学科(引者案:指逻辑学、物理学)通常合称理论哲学,以别于实践哲学”*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30页。。
可见,自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这一西方古典哲学发展之盛期,它一直是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上展开其研究,而且这两个向度上的研究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
当然,中、西互相比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在理论向度上所开展的自然研究确实从未有过如古希腊早期哲学那样独立而鲜明的表现,故相形之下,古希腊哲学便显得它有一个自然哲学传统,虽然该传统其实主要是表现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而中国古代哲学就显得缺乏这样一个传统,虽然其宇宙观中以“五行”、“水”、“精气”、“元气”等作为其标志性概念的思想或学说,以及以《周易》为代表的对“数”与“象(形)”的数学研究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理研究,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其实也不乏自然哲学的内容。
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作为两个互有区别的研究传统在中西古代哲学中表现出总体上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特征,这恰好说明了古代哲学具有这样两个显著特征:(1)它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它是介于或游移于评价思维与非评价思维之间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是否作价值判断,取决于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的具体情况;(2)它既是崇尚真理的“爱智之学”,又是坚持正义的“贵德之学”。借用朱熹的话语来说,中、西古代哲学这两个方面的旨趣及其研究活动可一言以蔽之曰:“穷理”。朱熹道:“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 “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或人七》)中、西古代哲学的“爱智”特征即体现在为达到“心不惑”而探求“事物之所以然之故”;其“贵德”特征则体现于为达成“行不谬”而探求“事物之所当然之则”。
三、 17世纪以后西方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分化
在哲学发展的古代阶段,固然无论中、西,其文化哲学和自然哲学都是处在混然未分的原始综合状态,但是到16、17世纪,中、西哲学在研究向度上都各自从这种原始综合状态中逐渐分化而形成各有其明确偏向和取向的特定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
就西方哲学而言,一方面,以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著《新工具》(1620)、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著《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1637)为标志,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明显侧重于自然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培根的《新工具》提出了“哲学和科学的正当分划”,事实上是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作了明确区分,因为他这里所讲的“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他所主张建立的“查究那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式”的所谓“形而上学”,按其对象和内容来说,就是关于“自然的永恒的和基本的法则”的自然哲学*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6页。,而且由于培根意识到“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培根:《新工具》,第13~14页。,因而主张运用由他所首创的包括观察、实验和归纳三个主要环节在内的“发明知识”的“新工具”,故他所倡导并致力于研究的自然哲学是根据“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的原理”*培根:《新工具》,第14页。的归纳原则来认识自然界,按照“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通的原理”*培根:《新工具》,第12页。的归纳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原理,这种经验型自然哲学不再像传统思辨型自然哲学那样是按照“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培根:《新工具》,第12页。的演绎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原理,这是17世纪初西方自然哲学所发生的一次划时代的学术转型,由此所引发的“智力革命”(康德语)改变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久已形成而根深蒂固的知识观念和相应的认知路线与认知方法,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自从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以来,现代科学就已奠基于对自然的详细研究之上,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这就是:只有已被实验证实的或至少能被实验证实的陈述才是容许作出的”*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6页。。如果说培根的《新工具》是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笛卡儿的《方法论》则实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因为此书不仅探讨了“什么是知识”的知识本体论问题,更探讨了“我怎么能知道”的知识方法论问题,其“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正是表明了笛卡儿所提倡的“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乃是一种始于怀疑而非始于信仰的反神学方法。这种方法较诸培根自然哲学所提供的经验自然科学方法,是属于理论自然科学范畴的方法——如果说培根哲学是一种经验型自然哲学的话,那么,笛卡儿哲学则是一种理智型自然哲学。这两种自然哲学作为不同类型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后来演化成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现代形态的自然哲学——努力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参见石里克:《自然哲学》,陈维杭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页。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以石里克等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标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另一方面,以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著《人性论》为标志,西方哲学又开始逐渐形成另一种明显偏向于文化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因为休谟主张哲学应当以人性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同期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有与休谟类似的观点,他曾宣称“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8页。。休谟、爱尔维修等之所以主张哲学应该去研究人,其背景是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挤压了自然哲学的发展空间,使哲学在自然领域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了。到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时,曾经自认为能给人以“最高智慧”的形而上学已然衰落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让康德发出了“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学”的感叹,甚至戏称曾经长期被尊奉为“一切学问之女王”的玄学(形而上学)已然沦落成如同遭人鄙弃而颠沛流离的“老妇”了*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页。。正是在形而上学的学术地位如此一落千丈的情况下,康德开展了“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详参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11页。。通过“三大批判”*康德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康德不但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而形上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还认识到了“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详参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11页。。这意味着康德是抛弃了“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解”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将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从原先大而无当的全宇宙或自然界转移到了人类理性世界,使形而上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变为限于研究人类理性的人本论。另一方面,康德为完成“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更致力于构建以“人”为主题的新哲学,这种被他自我称名为“实践哲学”*语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参见叔本华:《论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1~142页。的新哲学,在他看来应当是立基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三大假设之上,但显然,这些假设是既不能从经验中产生,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的,只能归因于康德自己指摘“玄学”时所说的那种“高翔于经验教导之外”,“唯依据概念”来进行的“完全孤立之思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文第13页。。可见,康德哲学仅仅是在“科学认知”方面摒弃了玄学,在“生活实践”方面则仍然承纳玄学。由此可以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这里,不仅其知识论早在培根时已然发生历史性转变,其本体论也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变——从探求宇宙终极原因和第一原理的宇宙本体论转向探求生活实践原理的人本论。康德的实践哲学作为一种人本论形态的本体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参见范进:《康德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但按江天骥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哲学导源于尼采,因为尼采对意识、自我和主体进行彻底的摧毁,并且主张重估一切传统观念的价值”*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似乎江先生的观点更有道理,因为从西方哲学史上最先提出“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一词的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倡导“文化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挽救19世纪哲学从康德发展到尼采时所发生的在他看来是由于尼采的价值观所引起的深刻哲学危机。按照文德尔班的看法,尼采要求“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这是表明他主张“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这种“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可能导致“哲学的解体和死亡”,面对这种危险,“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详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912~927页。。文德尔班所谓的“文化哲学”,正是指的将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而“继续存在”的“哲学”,故他所说的“价值”也是就“文化”而言,是指文化的价值。在《哲学史教程》(1892)的结语里,文德尔班从研究对象方面对“文化哲学”做出了明确界说:“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哲学的对象。”*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928页。紧接着这个文化哲学定义,他又指出:“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然而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928页。这是表达了他对文化哲学的任务的看法,即文化哲学是要用清晰和纯洁的概念来全面反映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充分展示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的人性。由此可见,文德尔班所谓“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就是指通过文化哲学所把握到的通过由“理性的人”所创造的文化产物及其成就表现出来的“人性”。所以,他所提倡的文化哲学,其实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是从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中去探求人性的学问。
四、 16世纪初中国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
较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约提前了一百年就开始走出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状态:16世纪初,以王守仁“龙场顿悟”而创“致良知”之说为标志,开始形成明显侧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至西汉武帝时,已形成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传统,其中“究天人之际”一语概括性地表达了先秦以来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此语出自司马迁之口,乃是表明中国哲学发展至司马迁时已达到了对“究天人之际”这一自我本性的高度自觉。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在总体上一直都是在“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之下自为地发展的。不管人们怎样去理解“究天人之际”的具体内涵,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它的基本意义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有些哲学家(如董仲舒)将自然之天神化为超自然或非自然的神灵,这个神灵也是不离于自然万物抑或寓于自然万物之中的万物之共性,对这种共性的界说,也还是一种自然观——一种神学性的自然观。。以这种关系作为根本问题的哲学,恰好是说明了它具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双重性质,抑或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为一体的原始综合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观演变角度来看,先秦时代前荀子时期普遍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天人不分”意识,直至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主张,乃有自觉的“天人有分”观念。在“天人不分”阶段,“究天人之际”尚未免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盲目性,此时的哲学研究还谈不上有什么自觉而明确的研究取向。到了“天人有分”阶段,荀子在研究向度上有了自觉而明确的取向,提出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的观点,这似乎意味着他有不求“知天”但求“知人”的研究取向,但至少他未曾从理论上说明为何在“知天”与“知人”之间应当做出不求“知天”只求“知人”的选择之理由,故即便其哲学已显其文化哲学的研究志趣,也不能说他已然有自觉的“知人”取向了。
汉唐时期,从董仲舒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观念,到刘禹锡 “天人交相胜”和柳宗元 “天人不相预”的观念,都还反映不出此一时期哲学的研究向度到底是偏向“知天”还是偏向“知人”。到了宋明时期,张载首先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之说(《正蒙·乾称》),从其上文“因诚致明”和下文“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的话来判断,其“天人合一”是指“得天而未始遗人”,这是通过“因明致诚,因诚致明”的“致学”所达到的“圣”境。故在张载哲学中,“天人合一”是针对“致学”这一道德修养问题所提出的一个知行观命题*所谓“得天而未始遗人”者,“得天”是指点知天道,“未始遗人”是指“行人道”。所谓“天人合一”,也就是指达到或实现“知天道”与“行人道”的统一。,还不是直接针对“天人之际”这一哲学根本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天人观命题。这一时期,倒是首先由程颢提出了“天人无间”(《二程集》)的天人观命题,从其“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集》)的话,可见“天人无间”的意思,是“天人无二”或“天人不二”,而非“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和“天人合一”是思想上并不等值的两个命题,在程氏哲学这里,“天人无间”是绝不可以用“天人合一”来代替的。程颢“天人无间”的命题在逻辑上蕴含“天人相即”之义,也就是说,在该命题所陈述的天人关系中,天人之间是“天即人,人即天”或“天不离人,人不离天”这样一种互不相离的双向互依关系。这种天人观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知天”与“知人”相即不离的认识论观念,由此更未免进一步导致认知取向和研究向度上把“知天”和“知人”视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南宋“朱陆之争”的情况来看,朱熹及其学术上的反对派陆九渊,就都是坚持了“知天”“知人”的统一观,只不过朱熹是偏重于“知天”而以“知天”为先、为主,陆九渊是偏重于“知人”而以“知人”为先、为主罢了——朱熹从程氏“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集》)之说引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子语类》卷九)之说,但又声称“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卷十),于是将《大学》“格物在致知”之语解读为“即物而穷其理”,从而要“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如此将“知天”路向的“格物穷理”作为达到“得自家这道理”的“知人”之手段和路径;(然据王守仁所“手录”的《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到了晚年则自我意识到“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且表示“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机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王阳明全集》,第132页。)陆九渊则继承和发展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求放心”之说,认为“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与胡季随》)。“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 (《与赵孟》)“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 (《与姪孙濬》),“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 (《与邵叔宜》),“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 (《与曾宅之》),因此坚决反对首先向外去“格物穷理”,以为如此将导致“道之不明”而“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与姪孙濬》)。 但他并未否定“知天”路向的“格物穷理”之必要性,仅仅是强调“格物穷理”须“先立乎其大者”而已。
及至“龙场顿悟”之后的王守仁,他对“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天人无间”关系方有明显不同于程朱的新见解: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
充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
这些见解表明,王守仁将“天人无间”的意义由“天人相即”转换为“天即人”或“天不离人”了——在这种天人关系观念中,天人之间不再是一种互相不离的双向互依关系,而是天对人的单向依赖关系,由此在理论上确立了“人”在“天人之际”的中心位置和主体地位,也因此,他对《大学》“格物在致知”的诠释就大不同于朱熹所解释的那样是所谓“即物而穷其理”,而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顾东桥书》)了。这意味着中国哲学发展至阳明哲学阶段,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在研究向度上游移不定的“究天人之际”,而是将“知天”与“知人”的关系确定为“知天不离知人”或“知天依赖于知人”的关系,使“究天人之际”的方向明确偏向于“知人”并使“知人”落实于“知行合一”的“致良知”——阳明哲学断然摒弃了以往“究天人之际”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到人和人心之外去追求知天明理的那种研究传统,将目光从“天人之际”的方向上彻底收回,全部投向“人”,全力关注“人”,并且直指“人心”,直接向“人心”讨回“良知”,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显然,这种被称为“心学”的哲学,其实质乃是一种人事之学,一种生活之学!它是在肯定人人都有“良知”的前提下,欲使“良知”成为彼此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互相评判道德是非及其个人自我评判道德是非的价值标准,以消解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而且经常遇到的因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互相评价和自我评价的标准不一致、不统一所造成的价值冲突,抚平由于这种价值冲突给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心灵上与环境上的创伤,质言之,就是要让“良知”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普遍有效且绝对合理的价值标准,从而使人类能按自己的“良知”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创造自己的生活。十分明显,这种合乎“良知”的社会与生活,就是阳明心学所期望达到的人类生活的总体目的。故阳明心学的创立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终于走出了其原始综合状态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阶段。
由王守仁所开创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起初表现为心学形态。这种心学文化哲学不再以“究天人之际”的思辨形式来讨论“性与天道”,而是把“性与天道”理解为人所固有的“良知之天理”,从而使“究天人之际”转化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道德实践。这种主张直接依赖于“本心”来开展“致知良”的道德实践的文化哲学,至明清之际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信奉阳明心学的黄宗羲和批判阳明心学的顾炎武这两位政治见解十分接近而学术道路明显相异的学术大师身上。
黄宗羲是曾师从于刘宗周而受到刘氏心学熏陶甚深的一位心学家,其心学特色,刘述先先生曾以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中的三句话及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铭》中所引的一句话来概括之:(1)“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2)“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3)“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4)“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参见刘述先:《论黄宗羲心学的定位》,载吴光:《黄宗羲论——国际黄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7~148页。黄宗羲的这种心学世界观使他走上了思想史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冯契先生曾指出:“在黄宗羲以前,王阳明把理看作一个过程,以为工夫与本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黄宗羲进而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的著名论点。他否定心是虚寂的本体,把本体看作是随工夫(精神活动)而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此心‘一本而万殊’,于是表现为‘殊途百虑之学’。那些学术卓然成家的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去把握真理,虽深浅有异,醇疵互见,但对本体各有所见。学派纷争的历史,正体现了本体随工夫而展开的运动,而史家只有运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系统的批判考察,才能把握其‘一本而万殊’的脉络。”*冯契:《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论》,载吴光:《黄宗羲论——国际黄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55~156页。正是这样,黄宗羲将“致良知”的心学引向了史学之路,使王守仁那种主张直接依赖于“本心”来开展“致良知”的道德实践的直觉型文化哲学转变为主张通过“殊途百虑之学”来把握“一本而万殊”之“本心”的史学型文化哲学。
顾炎武在学术上无明确的师承关系,早年主要是受其嗣祖父“士当求实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的家教影响,17岁参加复社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复社通经致用学风的影响*周可真:《顾炎武年谱》17·1条,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继而更从“朱子之说”中领悟到了“圣人下学之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明道救世”为根本宗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基本原则、“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为实学理念的“修己治人之实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这种实学指摘“其说盖出于程门(案:指程颐、程颢)”的“宋之三家”(案:指上蔡谢良佐、横浦张九成、象山陆九渊)以及“源于宋之三家”的“今之言学者”(案:指明代以来的理学家)是“淫于禅学”(《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是“语德性而遗问学”(《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尤其指摘后者为“谈孔孟”之“清谈”,是“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然而,尽管其学术批判的矛头主要针对的是王守仁及其后学,但顾炎武本人所提倡并从事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其实是一种比较接近于阳明心学的以“尊德性”为本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基本特点是:根据“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将“文行忠信”本质地理解为“性与天道”寓于其中的道德实践形式,并将这种道德实践看作“尊德性”的现实表现和实现人道与天道(“性与天道”)互相统一的现实途径与方式*参见周可真:《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7~25页。。由于其道德实践哲学是形成和发展于清初特别是康熙以后,其时顾炎武原有的“保国”意识随着明朝灭亡和南明诸政权的逐渐消亡亦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保天下”意识了,这种意识是出于对“吾道”(儒家仁义之道)有被毁之危险的警觉*顾炎武《日知录》有云:“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素夷狄行乎夷狄》,《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日知录校记》),由此推动他去从事“明道救世”的学问,这种学问所追求的是“救世之道”,这与其早年所追求的“经生之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经生之术”是其个人赖以从事济世经邦之实践的知识基础;“救世之道”则是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正是出于“明道救世”的需要,其学术活动才由追求“学识广博”转变到追求“学务本原”,从而最终归本于“经学”。这个“经”即“五经”及“圣人之语录”,其实就是顾炎武心目中华夏民族文化的“本原”。就此而言,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学”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华夏文化学*参见周可真:《顾炎武实学的特点》、《顾炎武对异族文化的态度》,载周可真:《顾炎武与中国文化》,黄山书社2009年。。故如果说黄宗羲哲学是一种史学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顾炎武哲学则是一种经学型文化哲学。
黄、顾的文化哲学和王守仁的文化哲学一样,都是属于道德实践哲学范畴,都是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来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并且都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所固有的天命之性,更把这种人皆有之的天命之性归结为“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又都属于儒家“仁学”范畴,都是继宋明理学而起的明清“新仁学”。但是,黄、顾的文化哲学都不再是像王守仁的文化哲学那样主张直接诉诸人的“本心”来开展“致良知”的直觉性道德实践,而是主张通过史学或经学的学术方式来达成其道德实践目的。故如果说王守仁的文化哲学是一种以崇尚“明心见性”为特征的直觉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黄、顾的文化哲学则分别是以推崇史学和经学为特征的知识型文化哲学——到章学诚提出并较系统地论证了“六经皆史”的史学观点以后,分别由黄宗羲和顾炎武所开创的史学型文化哲学和经学型文化哲学就逐渐合流为一了。
黄宗羲、顾炎武之后,通常奉顾炎武为始祖的清代朴学(考据学)兴起并盛行于乾嘉时代。因其考据范围既涉及史更涉及经,故清代朴学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黄、顾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就其史学考据而言,则可视其为黄宗羲史学型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就其经学考据而言,又可视其为顾炎武经学型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换言之,清代朴学其实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只是由于其发展至17世纪晚期,“自我认同趋明确、具体,人们不再把道德修养视为求知问学的首要途径,而是看作理性质疑的对象。崇尚道德修养之风式微了”*狄伯瑞:《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页。,故朴学形态的文化哲学便不再具有道德实践哲学的性质,从而原本属于儒家“仁学”范畴的道德实践哲学就演变成属于儒家“智学”范畴的智能技术哲学了。这种智能技术哲学具有鲜明的诠释学特征,它主张“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载《潜研堂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提倡“实事求是”的“征实之学”,并通过理证、书证、物证等考据方法的实际运用,提供了一种“以信息还原为本质特征的诠释方法”*参见周可真:《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载《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五、 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相当晚出的,是到了20世纪初才由文德尔班首次提出来*参见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页。案:该名词首次出现于文德尔班所著《文化哲学与先验观念论(Kulturphilosophie und 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1910)中。。当这个名词成为中外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一个哲学术语以及相应地文化哲学成为中外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或重要领域时,人们对文化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就变得多样化了。这里不拟也不便于具体地考察和评论这些互见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解和解释,只是根据笔者对于文化哲学的上述理解以及对相关情况的有限了解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一些浅见。
笔者是从文德尔班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学术背景和他同康德的学术渊源关系以及他对哲学的总体看法中,从德语世界的特殊科学概念和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德国哲学家对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讨论中,领悟到了“文化哲学”的一般意义应是指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向度,即实践向度的哲学研究,进而把这一向度的哲学研究理解为就是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它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自然哲学)相对应。当把文化哲学纳入文化科学范畴,把它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来理解时,要准确地把握文化哲学的学术特质,就应该也必须将其置于同文化科学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和理解。据说,在德语世界里,是“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参见肖建华:《文化哲学简论》,载《中南论坛》2006年第1期。按:也有学者说,“1838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第一次提出‘文化科学’一词,主张全面系统地研究文化,建立专门的学科”(林坚:《“文化学”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5月24日第5版)。。而德语中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这两个学术名词在指称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相对的学科的意义上是异名同谓。“文化科学”概念后来被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从德语世界引入英语世界,使用于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参见肖建华:《文化哲学简论》。。但是,一进入英语世界,“文化科学”概念在内涵上便发生了变化,其涵义不再是它在德语世界的时候那样系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那些学问,而是指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了。这明显地表现在泰勒起初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了“关于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 )的概念,而在其后所著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中,又把原本被他称作“关于文化的科学”的学问(即该书所谓的“文化研究”)归入“人类学”了。
以笔者浅见,文化科学在德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实是按下述不同学术路向发展的:
在德语世界里,文化科学是在哲学家们探讨它同自然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它与后者的区别的学术理论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研究最终导致了由文德尔班首先以“文化哲学”一词来命名的新哲学的诞生;在英语世界里,文化科学则是在人类学的先驱者们对原始部落社会的实地观察记录和采访报道的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经验科学研究导致了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诞生*西方学术界鉴于爱德华·泰勒对人类学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把他尊为“人类学之父”。而实际上,泰勒的人类学研究是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故准确地说,他是“文化人类学之父”。文化人类学在广义上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则仅以民族学为限。而广义的人类学则除了文化人类学,还包括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一词实际上是由德国学者亨德(Magnus Hundt,1449-1519)发明的,他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的著作《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1501)的书名。此后直至19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人类学”一词一直是用来指称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由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所发明的“culturology”(文化学)这一专有名词来加以标志的文化学概念,此概念的确立实是怀特受德国著名物理化学家、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瓦尔德《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1909)一书的思想的影响所成,奥斯特瓦尔德在该书中提出,人类的独特之处不是社会而是文化或文明,故理应在社会学之外另外建立文化学,他并且把文化学置于科学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在1915年所作的题为“科学的体系”的一次讲演中,他又提到“很久以前,我就提议把这一正在讨论的领域称之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参见陈建宪:《文化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按:据陈序经研究,德文“Kulturology”(文化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德国经济学家拉弗日尼·培古轩,他在《动力与生产的法则(Bewegungund Productions-Gesetzen)》(1838)一书中,不但使用了这个名词,还有意倡导建立一门文化学。1854年德国学者C.E.克莱姆(格雷姆)于1843—1852年分批出版了十卷本《人类普通文化史》,又于1854—1855年出版了两卷本《普通文化学》,其中均使用了“Kulturology”一词(参见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怀特赞同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所以提出用“culturology”这个英文单词来做关于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 )的正式学科名称,并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此书为论文集,中译本有两种:其一,由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书名是《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其二,由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书名为《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1959)一书中对文化学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由上述可见,德语世界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概念和英语世界的文化学(culturology)概念在外延上有如此差异:前者是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后者则仅指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故完全可以也应该把文化学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一门具体学科来看待。在文化学这门具体的文化科学领域中,诚然也可以开展某种形式的哲学研究,但这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被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待。这也就是说,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之外,不存在抑或根本无须建立另一种意义的文化哲学。换言之,文化哲学概念应该被统一到指称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这一意义上来,以免造成与该主题相关的思维混乱和文化哲学领域的学术乱象。
就文化哲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来说,文化科学所研究的是与自然现象有根本区别的作为人的本质(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人文现象及其规律,因而它是属于经验科学范畴,文化哲学所研究的则是人性本身,它视文化科学为认识人性的具体途径,试图为具体文化科学提供认识人性的一般方法,换言之,文化哲学本质上是认识人性的一种方法论。从理论上说,正是基于对文化哲学概念内涵的上述理解,才足有理由将中国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阶段的心学本质地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因为这种心学提供了一种把握人性(“良知”)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致良知”;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就是关于把握人性的一种方法论,但它所提供的“致良知”方法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直觉方法。其后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哲学之所以也可以被当作文化哲学来理解,是因为黄氏哲学和顾氏哲学都各自提供了不同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独特方法——黄氏哲学以史学作为把握人性(“本心”)的方法,顾氏哲学则以经学作为把握人性(“性与天道”)的方法。至于清代朴学,其“征实之学”并不是直接用于把握人性的方法,而是它为经学和史学所提供的用于解读经史的诠释方法。在其诠释方法归根到底是服务于把握人性的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清代朴学所自我标榜的“实事求是”的“征实之学”也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继朴学而起的晚清今文经学,其实和朴学一样也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只不过晚清今文经学所提供的诠释方法不再是“征实之法”,而是“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一种以文本重构(text reconstruction)为特征的诠释方法。从信息论角度看,文本重构就是信息重构(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它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变换(information conversion)*信息论中所谓信息变换,主要是指信息形态变化、信息内涵的转换变化、信息扩展拓宽、衍化派生新信息的过程。,由此当然会产生信息失真(information distortion)的情况。所以,如果是以“求真”的科学(science)标准来加以评价,清代朴学的诠释方法是比较接近于科学而具有一定科学性,晚清今文经学则是远离科学而缺乏科学性;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以“求善”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标准来加以评价,清代朴学的诠释方法倒未必适用于文化创造活动,而晚清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倒是更贴近文化创造活动的本性。
自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8)、创立中国哲学史学科以来,中国哲学界的哲学研究,无论“中”“西”“马”,实际上都不过是运用某种诠释方法或综合运用某些诠释方法来解释各自领域中用文字写成的文本——中哲研究是解释国学中的某些经典文本,西哲研究是解释西学中的某些经典文本,马哲研究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按照笔者在2013年参加中国哲学史年会所发表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哲学知性是人类知性的一种形式,无论这种知性在人类知性系统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怎样的作用,它都是人类本性(人性)内容之一,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它也无疑是我们自己作为人类成员的类本质的内容之一,在此意义上,哲学史研究不过是从一个方面对自己的类本质进行历史维度的自我反省,以达到对这种自我本性之来龙去脉的自知之明。就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来说,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不过是对自己的民族本性进行历史维度的自我反省,以达到对这种自我本性之来龙去脉的自知之明”*周可真:《体古今人性之常,通古今人性之变——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目的》,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现代“中”“西”“马”的诠释性哲学研究与黄宗羲的史学研究、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如果说黄、顾的研究分别是属于史学型文化哲学和经学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现代“中”“西”“马”的诠释性哲学研究则是属于哲学型文化哲学——以哲学作为把握人性的方法。
就现代西方哲学界而言,文德尔班、狄尔泰等一批德国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固然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就是以石里克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所从事的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科学哲学,实质上也具有了文化哲学特性,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不是将包括其命题在内的自然科学看作仅仅是由一系列通过一定语言(语词、句子)表述出来的概念、命题所构成的既定知识系统,而是把自然科学本质地理解为人类的一种历史活动形式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命题”就无疑可以且应当被纳入“人类历史活动”范畴,从而所谓“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也就同“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有内在联系了,而不只是同“自然律”(石里克语)有本质关系,于是,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自然哲学活动,就不仅可以甚至也应当被当作研究人类历史活动总体目的的文化哲学活动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来看待了;而且更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初的自然哲学的转向,还意味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从原本关注自然事物和揭示自然世界的规律,转移到了关注人文事物(自然科学)和揭示人文世界(科学知识领域)的意义,这样,自然哲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化哲学的属性,从而使自然哲学具有了同文化哲学开展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学术对话当然有可能导致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学术争端或冲突,但同时也有可能在它们互相排斥的学术冲突中逐渐走向互相求同存异的学术合流或融合。这也就是说,在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江天骥先生曾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变角度论及文化哲学所当具有的四个特征:(1)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点;(2)主张我们所感知的直接对象并非在心里,而是在外界;(3)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4)属于广泛的实用主义传统的新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基于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的彻底语用学观点)。江先生认为,其中第三、第四个特征是一切严格意义的文化哲学所必须具备的,他强调了文化哲学以生活世界为基地,也就是以文化世界为基地(胡塞尔虽然以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其先验现象学却又放弃了生活世界),并认为同一文化世界的居民具有某种相同的意义场,以便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理解、交谈或争辩,或者说,同一种生活方式的行动者,必定具有彼此共同预设的确定信念系统,以便相互了解,进行意见交流;同时强调了语言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活动,语言的意义是由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所决定,即由讲话、交谈的活动所创生,因而语言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以讲话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环境(context)为转移的,他坚决反对把语言看作表达私人心里观念、思想或者表象某些事物的工具,因为这是错误地预设了语言的意义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东西*详见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江先生的这些文化哲学论见,实际上是讲明了从意识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到生活哲学(即文化哲学)转变的基本条件。
笔者在18年前所撰《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一文中,曾如此论证过现代哲学向生活论形态的哲学过渡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哲学典型意义上,通观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它实际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依次逐步上升的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首先,存在论所致力于探讨的一般与个别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存在,原本是自在地统一于存在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开展,它们才被自觉地区分开来,并且只是由于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片面地强调和夸大了感觉或理智的作用,它们才被对立起来。然则,存在之成为问题,实是因认识而起。故当存在问题被研究且不断向纵深推进时,作为引起该问题的原因的认识本身,就必然要被当作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决定了存在论的发展最终必然逻辑地归结到认识论上。
其次,认识论之所以必然进展到实践论,则是由于认识是起因于实践。人们出于实践的要求而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交往;而语言和意识就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可见,认识原是实践着的人们用以实现其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不过是实践的产物,是服务于实践的第二性的东西。因此,要使认识问题得到澄清,就不能局限于认识论,而必须扬弃认识论而使之上升到实践论;只有站到实践论的高度,才能认清并正确地揭示出认识过程的本质。
要之,西方哲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展,皆是由于探寻前一个阶段的问题的原因而引起的,即由于探寻存在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认识论,进而由于探寻认识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实践论的。据此规律则可以预断: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以探究实践的原因为理论驱动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生活论。
继实践论而起的哲学形态之所以必定是生活论,是因为生活是引起实践的原因,人只是为了生活才需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论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79页。这说明了人的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实践是以生活为归宿的,实践只是生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故实践论向生活论发展乃是势所必然。
在此基础上,拙文将生活论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人论、文化论和历史论三部分*以上内容来源于周可真:《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按照笔者现在的见解,这三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可简要描述为:“人论”是对人性的研究,而人性是通过文化即人类生活的总和表现出来的,故对人性的研究必须通过研究文化的“文化论”来实现,而“文化论”所要研究的文化是以历史形式存在的,故“文化论”的文化研究只能借助于“历史论”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是说,曾经被笔者称为“生活论”的文化哲学,实质上是通过对人类创造自己文化的生命活动过程的历史研究来把握人性的人学。“创造”、“人性”、“文化”、“历史”构成为这门人学的四个关键词,其中“创造”可作为另外三个关键词的核心意义的通诠之词:“人性”是一种创造性,即人创造自己生活的能动性;“文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即人创造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历史”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的发展过程,即人创造自己生活的生命活动发展过程。因此,文化哲学作为认识人性的一种方法论,它必须去认识人类的创造本质和创造规律,从而提供关于人创造自己生活的基本方法——文化创新方法。按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关于创造力是指最能代表创造性人物特征的各种能力,是经由发散思维而表现于外的行为的观点,文化创新作为一种创造力,其本质是经由发散思维而表现于外的行为,则文化哲学理应对发散思维以及与发散思维相关的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并把非逻辑思维置于它同逻辑思维的互相关系中来开展这种研究。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Philosophy
Since Wang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And the Converging Tr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towards Cultural Philosophy
ZhouKezhen(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In ancient times,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were in their primal states.Not until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did they form their own focuses and orientations and establishunique research styles and traditions.Since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Western philosophy gradually evolved to natural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search traditions.In the meantime,Chinese philosophy started the transition towards cultural philosophy in the 16th century.Chinese cultural philosophy was originated from Wang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who used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and “extending the intuitive knowledge” as moral practice to discipline the human nature (“intuitive knowledge”).This intuitive school of cultural philosophy was later innovated by Huang Zongxi through historical study (“conscience”)and Gu Yanwu through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uman nature and heavenly principle”).In Qing Dynasty,Down-to-earth Learning and Jinwen Confucian Canon further develop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sion classics and history by providing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methods.The former used information reduction method,while the latter used 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method.Moder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shall all be characterized as interpretive research philosophy.In essence,they attempt to discipline human nature through philosophy itself.In the Western world,Hume,Kant,Windelband and Dilthey all gave weight to cultural philosophy.Even the Standard Philosophy of Science,represented by the Vienna School,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philosophy.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re converging towards cultural philosophy.
Key words:natural philosophy; cultural philosophy; creation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