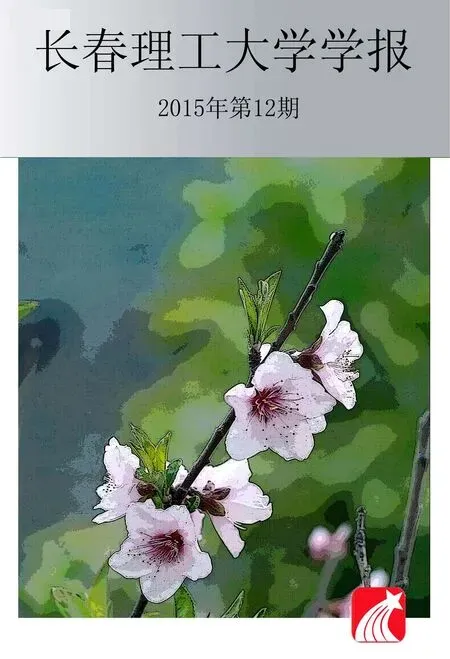葛兰西社会契约论思想抉微
王临霞,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130024)
葛兰西社会契约论思想抉微
王临霞,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130024)
葛兰西在对霍布斯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社会契约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之所以说特殊,原因就在于葛氏的社会契约论实则是无产阶级在温和的表面下借助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以阵地战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捍卫自身利益,使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种设想。虽然葛兰西的社会契约论为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宝贵的路径,也使得社会契约思想继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熠熠生辉,但这条路径毕竟设计得太过理想化而缺乏对现实可操作性的慎重考虑,难免会落入“乌托邦”,向现实低头。
霍布斯;卢梭;葛兰西;社会契约论
16-18世纪,是属于“社会契约论”的世纪。“社会契约论”把它的灿烂光辉投射在生活在这两个世纪的人们身上,它的余辉更是照亮了后人前进的道路。麦克里兰曾经这样盛赞过,“自激进宗教改革的时代以至18世纪下半叶,社会契约的理念主导政治思想。这并不是说所有重要的政治理论都是社会契约,而是说,凡是政治理论,如果本身不是社会契约论,则必须将社会契约说纳入考虑,否则就会遭到抨击”。[1]不得不说,“社会契约论”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仅给当时人们的思想打下了深刻烙印,更深深地影响着其后人们的思维方式。
一
作为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第一人,霍布斯在掀开预设的“自然状态”之幕时,就已经开始为他的“绝对”“服从”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埋下伏笔了。在预设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去运用自身的力量以保全生命的自由和安全。然而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恶”的本性便会导致与他人发生激烈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仅是频繁的,更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2]94战乱频繁使正常的生活无法继续,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产业被挤压的没有生存空间,航海、种植及时间计算无法正常进行,文学、艺术不断凋敝,“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与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2]94,95因此,战乱的生活状态不会给人们提供任何关于是与非、公正与不公正的衡量标准。为了求得生命的自保,为了和平,人们开始考虑相互转让一定的权力,订立契约,“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2]58——国家。既然这个人为的人——国家是人与人相互转让权利、订立契约而来的产物,并非出于其他——上帝或神,那么国家也会像充满生命力的人一样充满力量。但是在霍布斯看来,国家的力量却应该远在人的力量之上,因为它是人们为了避免战乱的生活状态,维护和平稳定的生活而设立的,国家就理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理应是专制的。除此之外,人民订立契约形成国家,并选举出建立在人民自愿同意基础上的国家领导者——君主,这个君主也应当是专制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君主并没有参与人民订立契约的过程,也就没有遵守契约的义务;除此之外,如果君主不是专制的,谁才能成为这个契约的绝对的执行者与审判者?这样的契约,效力又谈何保证?显然,在霍布斯眼里,不仅国家是专制的,君主也必须是专制的。只有建立了专制的国家,选举出专制的君主,确保人民对专制国家与君主的绝对服从,这样的契约才能发挥效力,不至于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人民的权益才会得到保障,不至于朝不保夕,仍然为了保护自身的权利枕戈以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霍布斯本身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它的理论从内在上就决定了自身要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所以这种人民对国家与君主、新兴资产阶级统治的“绝对”“服从”正是他从一开始就埋下的伏笔,正是霍布斯“绝对”“服从”型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内在根源。
可以说,霍布斯的契约论对葛兰西契约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葛兰西看来,霍布斯的契约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绝对”,一个是“服从”。出于维护社会安定与人民利益的考虑,在这二者之间,葛兰西坚定的选择了“服从”,摒弃了“绝对”,因为他不想让这本该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契约变成君主用来束缚人民的枷锁。
二
“道德王国的牛顿”不仅看到了自然状态下人的善的本性,他同时也意识到了仅凭借着善的本性是无法克服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困境的,于是向社会状态过渡,改变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方式便是紧急且必要的。当人们从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以后,卢梭却发现,人们又陷入了新的枷锁带来的桎梏之中。如何使人们摆脱枷锁的羁绊,重获自由平等,卢梭指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人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而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3]23不难发现,卢梭的这段话指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的实质——以人为本,每个人与其他人或社会联合体订立契约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自己的自由、平等,生命和财富而服务。不同于霍布斯“对君主与国家绝对服从”的社会契约,在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中,每个人都参与订立契约,不仅与其他每个人订立契约,与集体订立契约,更与社会联合体订立契约;在这一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将自身的全部权利,甚至自己,交给联合体或者集体,每个人让渡的权力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例外。既然每个人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是等价的——完全让渡自身权力(包括自身)交予集体,那么便不存在自私自利,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共同体中“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它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当时所付出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3]24不难发现,这一契约的最终目的不仅充分表达了建立在每个人相同意愿基础之上的“公意”,更合理保护了每个人的权益,使每个人只服从并服务于自身,使每个人在充分享有自身权益的同时走向新的自由与平等。这也正是卢梭“以人为本”的社会契约论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所在。
不得不说,就连社会契约论自身的发展都不能避开卢梭,葛兰西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多多少少带有卢梭的痕迹。在分析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的时候,葛兰西也看到了两点:“激进”和“以人为本”。为了能够合理地捍卫人民的合法权益而不至于矫枉过正,葛兰西决绝地选择了“以人为本”,摈弃了“激进”。因为他不想让人民的合法权益在激进的洪流中被吞噬、被湮没。
三
当葛兰西在呕心沥血建造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大厦的时候,他把最好的“钢筋”——社会契约论都用到了他的核心“楼层”——市民社会与阵地战。在葛兰西市民社会与阵地战理论中,我们总能感受到“社会契约论”的强大力量所在。只不过,葛兰西的社会契约论既不是霍布斯式的单纯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卢梭式的“激进”的“人民主权”,而是对二者加以改造、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形成的他独特的“温和”、“博弈”的社会契约论。
(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之所以说葛兰西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种“温和”的“博弈”,是因为在葛兰西眼中,无论是霍布斯的“绝对”的“服从”,还是卢梭的“激进”的“以人为本”,都既有其合理之处,又有其弊端,而葛兰西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就是要摒弃这些弊端,汲取他们的精华与营养。
通过对“绝对”的摒弃与对“服从”的吸收,葛兰西完成了对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改造。在葛兰西看来,对统治阶级的服从是必要的,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但同时他也指出,盲目的“绝对”服从则容易导致统治者滑向专制主义,甚至暴政,这种隐藏在“绝对”服从中的专制主义倾向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人民在出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意愿的前提下服从统治者的统治,但“绝对”服从是不能采取的。对于统治者的那些残暴蛮横的无理要求,人民必须拥有反抗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这样的权利是不能交给统治者的,只有保留适度反抗权利的服从才能真正起到既能有效捍卫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又能有效制约暴政,促进并形成合法统治的作用。因此,霍布斯式的“绝对”“服从”的社会契约论在葛兰西这里是必须加以改造的。
通过对“激进”的摒弃与对“以人为本”的吸收,葛兰西完成了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改造。在葛兰西看来,“以人为本”,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契约论的根本目标,因此对“以人为本”的社会契约论的保留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但对于卢梭的“激进”的观点,葛兰西却做出了合理的扬弃。因为在他看来,过度的激进容易使人民群众滑向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而这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陷入中世纪的那种恐怖的黑暗之中;人民权益遭受社会极端分子的肆意践踏,甚至毫无权利可言。为了避免吞噬这样的恶果,葛兰西决绝的摒弃了“激进”,适度地保留了“以人为本”。
(二)温和博弈,契约探赜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被统治阶级让渡一定的权利以服从统治,保留适当权利以捍卫自身并最终夺取政权,这就是葛兰西在市民社会与阵地战思想中表达出的“温和的博弈”的契约思想。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关于博弈双方的问题。在葛兰西的契约论观念中,被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因而博弈的双方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就葛兰西自身所处的时代而言,资本主义发展如火如荼,资产阶级蒸蒸日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让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无产阶级虽然还比较落后,发展比较缓慢,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坚持不懈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虽然如日中天,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压迫与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其不会是民心所向,决定了其必然走向灭亡。无产阶级虽然筚路蓝缕,但其为的是谋求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发展是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因而无产阶级能够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温和”、“博弈”型社会契约论的双方,葛兰西是明显倾向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
其次需要阐明的是博弈所遵循的原则的问题。为了正确分析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活跃的力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并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葛兰西认真设计并提出了二者博弈所遵循的两条原则:“1.如果完成任务的某些充分必要条件不存在,或者根本没有开始形成和发展,社会不会为自己提出这些任务;2.如果社会的内部关系中隐含的所有生命形式没有首先得到完善,社会不会崩溃,也不会被取代。反思这两条原则,人们可以进一步发展一整套关于历史方法论的原则。”[5]140通过对葛兰西这段话的分析,我们不难从中看到马克思的影子,也就是说,葛兰西在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博弈原则的时候是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而这思想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秩序,在生产力尚存发展余地之前都不会灭亡;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没有在旧社会的子宫中发育成熟,它们永远也不会出现。因此,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只有当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时,任务才会出现。”[6]显然葛兰西正是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博弈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才能发动对资产阶级的博弈,而这条件不仅是博弈的前提,更是博弈所应遵循的原则。
再次需要阐明的是如何博弈的问题。在葛兰西的观念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博弈需要在契约的框架内温和的进行,而这种温和的博弈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遵守事先订立好的契约,同时无产阶级辅之以必要的在市民社会中采取的阵地战,而不是采用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订立契约,由于自身的弱小,把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交予资产阶级以维护自身利益与社会稳定。一方面,无产阶级会服从资产阶级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如果资产阶级滥用权力,损害无产阶级利益,无产阶级则有权推翻资产阶级以捍卫自身。无产阶级会利用自身创造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步攻占资产阶级控制的市民社会机构以维护自身,直至全部掌握在自身手里。“任何在争取统治的集团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做斗争,该集团越是成功的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越快捷、越有效。”[5]5,6在关于市民社会的一篇文章中,葛兰西指出,被称作“私人组织总和”的市民社会承担着资产阶级的“霸权职能”,而这种职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学校、公会、社区及新闻媒体等市民社会机构才能完成。无产阶级把关于这些市民社会机构的管理权让渡给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必须在这些市民机构中为无产阶级留出表达自身合法利益诉求的渠道与空间,保证这些市民社会机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能够畅通无阻,真正发挥它应该具有的作用,而非成为资产阶级用以控制社会、灌输他们意识形态的“喉舌”。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的考虑,无产阶级让有机知识分子以阵地战的方式——无产阶级借助市民社会这个平台不断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发起进攻,并逐步攻克市民社会中对资产阶级来说至关重要的许多机构(例如学校、公会、家庭、出版社以及群众性的宣传工具等)的长期进攻策略——去逐步夺回对市民社会机构的控制权,直至最终掌控整个社会,从而真正让自己成为自身的管理者、利益捍卫者。
最后需要阐明的是“温和”、“博弈”型社会契约论的目的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在博弈的初期,这些充分必要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无产阶级“发展为一系列意识形态、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的论战形式”,[5]141并且坚定地认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推翻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不仅可能,也绝对必要(之所以绝对必要是因为辜负任何历史责任都会加重必然的混乱,预示着更大的灾难)”。[5]141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只有确立了崭新的现实,这种证明才会成功,才会变成‘真的’”。[5]141因此不难发现,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自身利益的捍卫者,才是葛兰西“温和”、“博弈”型社会契约论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瑕瑜互见
之所以说在葛兰西的“温和”、“博弈”型社会契约论中有“瑜”,是因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了霍布斯与卢梭呕心沥血创造的契约论的精华后——用他睿智的眼光远见卓识地看到了如何在捍卫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服从统治者的管理,如何巧妙地避免那种过犹不及的“人民主权”。不得不说,在那个被社会契约论的光辉投射的时代,人们不是因为担心遭受严厉的批评而不得不将契约论思想纳入自己的思考中,而是早已将社会契约思想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就好像身体里奔涌不息的热血,就像不断生长的充满活力的机体。像霍布斯、卢梭这样杰出的前辈,他们留给整个时代的精华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化在人们的思想中,而葛兰西也正是其中一员。只不过葛兰西能够脱颖而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汲取了霍布斯、卢梭这些杰出前辈社会契约思想的精髓,更将其加以改造,为社会契约论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使其获得新生,让它继续充满活力,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让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继续熠熠生辉。葛兰西的思想发展轨迹在这个意义上类同于现代性,“现代性自发地与前历史保持距离,谋求对前历史的超越和断裂,又自觉地继承传统的给养,在否定前现代的过程中又无法彻底隔绝前现代,所以现代性就在与前现代的纠结缠绕中生发滋长”[7]。
之所以说在葛兰西的“温和”、“博弈”型社会契约论中有“瑜”,同时也是因为它确实为完善文化领导权思想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巩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留出了广大的空间。不得不说,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如火如荼,资产阶级蒸蒸日上,而无产阶级发展缓慢——他能想到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葛兰西为无产阶级规划了一个美好的蓝图,那就是让有机知识分子一手执着矛——“阵地战”的“博弈”,一手执着盾——订立“温和”的契约,在这坚固的盾的保护与锋利的矛的进攻下在市民社会中去逐步攻占资产阶级的阵地,直至最终夺取博弈的胜利。不得不说,葛兰西以一种温和的博弈对资产阶级打了一场漂亮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此上升为统治阶级,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成为社会安定团结的维护者,成为自身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捍卫者。
之所以说它有“瑕”,是因为葛兰西对这种“温和”、“博弈”型社会契约规划得“太”过理想化以至于忽略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无产阶级能不能成功地与资产阶级建立这种契约,葛兰西没有慎重考虑,只是理想化地认为“是”。如果真的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的情况下成功地与资产阶级建立起这种契约关系,那么为防止资产阶级单方面违反契约,无产阶级能不能以“阵地战”的方式夺取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机构以发挥实质性的“博弈”与制约作用,这些问题葛兰西也没有真正地从现实层面考虑过,只是理想化地按照他的预设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残酷的现实却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温和”、“博弈”型契约是很难付诸实施的,现实并没有给它留下太多的可操作性空间。一旦资产阶级采取强硬措施,坚决不同意与无产阶级订立这种契约,动用暴力机关残酷镇压、无情打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只有为数不多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有机知识分子,悬殊的力量对比也会早早地宣告无产阶级失败的命运;或者即便资产阶级不采用暴力手段残酷镇压,订立契约却又不遵守,在遭遇到无产阶级的阵地战时继续顽强反击,那么这份看似完美的社会契约仍旧无法付诸实施,结果都只能“流产”,这份美丽的设想也只能“胎死腹中”。所以说,由于现实的残酷性——资产阶级过于强大,无产阶级却又势单力薄——葛兰西“温和”、“博弈”型的社会契约最终都很有可能落入“乌托邦”,向现实低头。
A8
A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12&ZD121)
王临霞(199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韩秋红(1956-),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