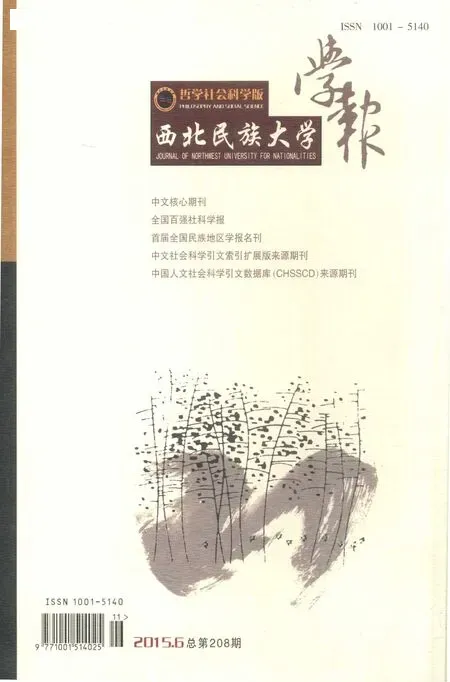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格萨尔》史诗在北美的跨界传播——以DouglasPenick英译本为例
宋 婷,王治国
(1.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翻译基地,天津300204;2.天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7)
继欧陆汉学对《格萨尔》译介之后,随着二战后北美汉学的迅速发展和藏传佛教在北美的传播,《格萨尔》穿越了欧亚大陆,在美国连续出版了几个英文译本。1996年波士顿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出版了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 J.Penick)《格萨尔王战歌》(The Warrior Song of King Gesar),这是一个较新的英译分章本(2009年由Mill city press再版)[1]。潘尼克英文译本在文体方面的处理策略既有变化也有保留。变化最多的是将史诗改译成了歌剧剧本以供舞台演出,但同时保留了史诗原始的本质特征,即以现代诗歌的形式尽量重现史诗的说唱部分。而这种变异是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一致的,即用现代诗歌的形式重现美国化的《格萨尔》,并最终朝向歌剧、戏剧表演发展,而这样的翻译策略恰恰和史诗研究的新视野即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相吻合。毕竟史诗的原发意义存在于口头表演中,所以称为原形态的活态史诗,而潘尼克为之而作的文体变异趋向于歌剧表演,不能不说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尝试,理应受到格萨尔学界的关注。
一、译者道格拉斯·潘尼克简介
道格拉斯·潘尼克出生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196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潘尼克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多部长篇小说、戏剧、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同时也是一个歌剧作家。他身兼数职,涉猎广泛,既是纽约市博物馆现代艺术馆的副研究员,也是纽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研究员,还是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影视作家及圣达菲歌剧团的歌剧作者,其著作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法国出版发行。潘尼克创作了大量有关藏传佛教和《格萨尔》的作品:(1)The Warrior Song of King Gesar(Wisdom Publications,Boston,Mass.1998/Mill City Press 2009),《格萨尔王战歌》是本论文要分析的译本之一。(2)Crossings On A Bridge of Light(Mill City Press-2009),副标题是 The Songs and Deeds of Gesar,King of Ling as He Travels to Shambhala Through the Realms of Life and Death.该本是格萨尔地狱救母的一段情节,借鉴《西藏生死书》的“中阴”观对《格萨尔》的一次解读。(3)歌剧King Gesar,1996年与作曲家彼得·莱伯森(Peter Lieberson,美国作曲家)合作,将《格萨尔》改编为交响乐在慕尼黑首映,参加演出的有钢琴家艾斯(Emmanuel Ax)、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和彼得·塞尔金(Peter Serkin),奥马尔·易卜拉欣(Omar Ebrahim)作为讲述者,影像资料由索尼经典(Sony Classical)发行,剧本的英文本由潘尼克撰写。(4)他为由加拿大导演Lesley Ann Patten(李斯莉安·巴顿)的电视剧《格萨尔王传奇》(King Gesar for Bravo!Network(Lesley Ann Patten,Prod))编写剧本,其英文剧本就是根据《格萨尔王战歌》译本创作而成的,该剧本将在美国布拉沃(Bravo)电视频道播出。目前正在从事两部小说《书法的秘密》(The Secrets of Calligraphy)和《北极星的影子》(Shadow of the North Star)的创作工作。显然,潘尼克既是《格萨尔》研究者,同时也是《格萨尔》在美国传播的翻译者和推动者,而他对《格萨尔》译介主要是借助戏剧、影视文学和音乐剧的形式,致力于史诗的普及和大众化推广。
二、译本的主要内容与结构
译本《格萨尔战歌》共分八个部分,包括作者致谢(acknowledgement)、序言(foreword)、导言(introduction)、正文七章与正文标题(calling on the power of goodness in our hearts)、文本致谢(text acknowledgement)、导言注释(notes to the introduction)、术语表(glossary)和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翻译文本。致谢中译者说明了本译本的成因,以及在成书过程中得到大师们的支持和众多人士的帮助。译者特别指出,《格萨尔战歌》的创作初衷是应作曲家彼得·莱伯森邀请,为其小型歌剧(chamber opera)《格萨尔王》所写的歌剧本。萨姜米庞仁波切(SakyongMiphamRinpoche)为其作序,并中肯地评价了潘尼克译本对《格萨尔》的合理阐释,以及该译本在《格萨尔》美国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接下来便是东杜法王仁波切(TulkuThondupRinpoche)较长的导言部分。
导言(introduction)主要介绍了《格萨尔》的内容和流传情况、艺人的种类、演唱形式、格萨尔的象征意义以及与当下时代的密切相关性。导言为不熟悉《格萨尔》史诗的读者提供了基本概况,构成了潘尼克译本完整的一部分,补充了因译本重在歌剧的歌唱而忽略了史诗的情节介绍所造成的理解困难,为读者提供了《格萨尔》故事梗概。值得重视的是导言部分有17条注释,统一作了尾注,主要是关于《格萨尔》版本和一些关键词的解释。然而,在导言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格萨尔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征战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以及到“2424年格萨尔还会回来”等[2],当然,这样叙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吸引美国读者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得格萨尔故事更加生动有趣。总之,导言尽管篇幅不长,但体现出一种研究性导语特点,是非常必要而有益的补充。
正文涵盖了《格萨尔》的主干部分,正文七章大体上和《天界诞生》《赛马称王》《北地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之战》和《返回天界》等分部本主要情节内容相对应。最重要的是正文开头有一标题统摄全文,这个标题是Calling on The Power of Goodness In Our Hearts,译成汉语是“唤起我们心灵中向善之能”,可见译本在内容上还是带有一定的佛教说理倾向。
文本致谢(text acknowledgement)部分非常重要,提供了这个译本的原本来源。潘尼克指出,“this text contains echoes,paraphrases,and borrowings from the following”(本文包括下列文本的引用、翻译和借用)[3]。显然据以翻译的原文来源不止一个,而是多个。直接的来源既包括大卫·尼尔1981年版《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英文本[4],还包括艾达·泽特林1927年《格斯尔汗》英文本[5]以及其他藏族高僧的藏学研究资料,可见在原文的来源上体现出强烈的互文性。
术语表(glossary)是该译本同样重要的一部分,共有17个。这些术语是史诗佛教世俗化、美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核心词汇,也是藏传佛教在美国流传过程中新出现的核心词汇。此外,还涉及如何用英文阐释一些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对等概念的佛教理念以及词汇的翻译处理方法,它为普通英文读者理解佛学概念提供了参考,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说明。“jnana”一词梵语是智慧之义,“jna”是词根,意思是认识,“jnana”是认识的名词化,认识的结果,引申为智慧。译者这里没有使用佛教常用词汇prajna(音译为“般若”,是佛教特殊的智慧,可以帮助处在痛苦中的众生解脱痛苦,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涅槃),旨在说明这种智慧是一般世俗的智慧,比如科学知识之类。事实上,通过用词措辞可见潘尼克是在尝试着将史诗朝向世俗化发展。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是该本的最后一部分,简略介绍了道格拉斯的学术背景和代表作品。
整个本子尽管篇幅不是很长,但内容翔实,目录齐全,布局合理,各部分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译文文本体系,非常适合读者在短时间内阅读和赏析。而这一切是与文本的文化语境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分不开的。潘尼克是从藏传佛教入手进入藏学领域的,但是他对《格萨尔》的翻译和改编却是面向大众的,以普通读者为期待读者,尽量使《格萨尔》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也就是说,译本在内容上呈现出一种由宗教转向世俗的倾向,由此实现对《格萨尔》自由精神的颂扬,借以阐释史诗《格萨尔》对当下美国现实生活的启示。
三、译本的翻译倾向
潘尼克《格萨尔王战歌》在内容上体现出宗教和世俗化并存的倾向,当然原史诗本身就是在佛教影响下产生的,带有宗教倾向和意味是不难理解的,完全世俗化而没有一点儿宗教痕迹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考虑到翻译发生的时空背景,久远的史诗在当代美国的传播,必然有所改变、有所变化或者说是经过美国化之后才能为当代美国人喜闻乐见。佛教在美国的传播本身就有一种世俗化的倾向(藏传佛教世俗化),再加上潘尼克的主要目的是译为一部通俗本子,以供剧本歌唱演出为主,所以就使译本在总体上更加倾向于世俗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格萨尔》史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二三百年之前传教士之间分享的状态,而是走向了当代的世俗世界、走向了当代的凡夫俗子。当然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因素,那就是史诗所蕴涵的精神是和美国人的精神追求一致的,那便是对自由精神家园的向往。
译本在开篇就用散体诗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Our earth is wounded/Her oceans and lakes are sick/Her rivers are like running sores/The air is filled with subtle poisons/And the oily smoke of countless hellish fires blackens the sun/Day has become night.[6]整个人间一片萧条,处于瘫痪之中,几乎是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写照。世上的人们流离失所、备受煎熬,于是在这混乱、迷茫的人间,有的追求权力、知识和技术以求解脱,有的受制于欺诈和虚幻的操纵,有的则放纵于激情的自我满足,人类成为了机器被技术化了……人类面临着诸多的绝望和无助。于是,人们发出了呼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善良和勇敢、智慧、和谐,那一定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而能够唤起人们向善的能量,那就是格萨尔的诞生。伤痕累累的地球上惟一的声音便是人们的呼唤,在人们的呼唤和期待中格萨尔降临了,来重建众生心中永恒的自由王国。这就是潘尼克译本开篇神子降生部分,没有天神开会决定派谁下界的情节和诸神讨论的情节,而是直接讲述人间的状况以及众生的境遇。
由于原史诗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体现在译文本中佛教的因素依然是很明显的。在译文本第二章开始部分,也就是格萨尔长大成人后,莲花生大师(直译为Padmasambhava,the lous-born embodiment of spontaneous Buddha activity)出现了,并对他说了如下的话:
Wake Gesar,lion king of ling.You are now not a man and your dream-like life of peace here is at an end.You and I are one.I have brought the Buddha’s teachings to the land of snows and taught the extraordinary path of meditation so that men can free themselves from mind-born slavery.It is for you to show the way that rests on the innate virtues of the human realm.It is for you to open the path of the four dignities.Join the ways of Heaven,Earth and Man,and bring into this world the kingdom of enlightenment,the deathless realm of true goodness and genuine dignity……[7]
这里,莲花生将格萨尔作为自已的化身“you and I are one”,去完成莲花生没有完成的事业,这些都会让史诗或多或少渗透着宗教气息。尽管莲花生将佛教传到了岭部落,并传授以坐禅修行的方式来摆脱思维被奴役的状态,但格萨尔的任务更重、更艰巨,他是给人类内心世界指明出路,打通通向四方的道路,加入“天、地、人”三道,把文明、善良和尊严的自由王国带到人间来。格萨尔的任务不仅仅是佛陀和神的事情,而且主要是解决人世间的问题。译本把史诗的渊源由佛界和神界拉回到了世俗人间。而且在莲花生大师告知要完成的宏基伟业时,也是以人物的对话直接进行的,突出了人的地位。可见,该译本的信仰模式由信神转向了信人。
格萨尔降临时既没有佛陀的参与,也没有奉旨下界,更没有众佛对他的承诺。也就是说,在史诗内容上一开始译本就呈现出一种世俗化倾向,不再是一味地强调超自然的、神圣的东西,而把关注来世天国逐步转移到今生和现世,转移到对人世的关注上,即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演进,不再单纯向往神秘而遥遥无期的天国和来世,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问题,解决的是人间的苦难,突出的是人心灵深处那份向往和平与宁静的祈盼。
四、译本的文体变异——史诗的歌剧化编译策略
潘尼克译本总的倾向是适合于歌剧表演的史诗翻译。事实上,包括贵德分章本在内的藏文《格萨尔王传》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叙述故事时,人物对话经常采用歌唱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来源于戏剧的影响,并称为“史诗说唱的戏剧化倾向”。“因史诗《格萨尔》的说唱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戏剧化倾向(艺人说唱表演的戏剧化倾向及其在民间传播方式所表现的戏剧化倾向),所以《格萨尔》不仅是一部文学生命力很强的作品,而且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8]”
潘尼克译本由于是为歌剧而作,译本中出现的大量诗歌唱词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翻译创作目的决定了译本在呈现的时候不能以纯叙事方式展开,一个必然的要求便是有适合咏唱的唱词和诗行在里面,所以将史诗朝向歌剧化编译就是情理之中的策略了。歌剧化编译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现代散体诗歌的运用,用现代散体诗歌诠释《格萨尔》自由思想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启示,用符合西方的现代语调来阐释《格萨尔》的精髓。译文尽量保持了原文的说唱形式,除了在征战事件进程、史诗情节上下勾连、分部情节的梗概介绍方面恰当地运用了记叙文进行描述之外,绝大部分是使用现代散体诗歌,用浅显的诗歌话语重塑了美国人心目中格萨尔形象,从而体现出一种再创的元素。
《格萨尔》是民间以口头形式说唱的叙事性史诗,大量的词语重复,不仅可以创造一种愉悦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说唱艺人恢复对史诗内容的记忆,促进现场表演时的即兴创作。然而,如果在现代印刷文本中作为诗来发表,这样大量没有演唱形式的字、行、段的重复会占据较多的文本空间,而且以文字形式重复出现会使读者产生阅读审美疲劳和沉闷之感。对这些重复冗长的诗行,译文采用各种编译法对原作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取舍,竭力寻求与原作品思想感情对等的字、行和段,捕捉到与原作品的“心智状态”对等的东西。英译本适当地删掉了一些唱词开篇中用于咏唱的部分,同时努力保留了原作的韵律、节奏、比喻、象征等艺术特点。但更多的是体现了艺术上基于现代英语对史诗的改造和再创作。
首先,在诗歌节奏方面,译文采取了句式调整的方法,形成大量的局部节奏,弥补英文散体诗歌造成的原史诗节奏感的丢失。主要表现为译文中诗节简短,行数居多。史诗及一些较长的诗体更注重内容和叙事,译本变为散体诗歌后,译者需要重新划分诗节,每个诗节的行数通常在6到10行,在文体上保持简洁、明快的特点。还有其平行结构多,铺陈排比并重。形式上则多用类似鲁体民歌的短体诗,大量同一结构的重复出现使译文产生节奏感,通俗易记。在译本中这种散体诗歌不仅仅是在翻译唱词时运用,而且在叙述描写部分也常常使用。
其次,在韵律方面,潘尼克译本中除了唱词中保留了一定的押韵以外,诗歌部分基本不押韵,舍弃韵脚,但在散体诗歌部分也有很多押头韵、句内韵和尾韵的地方。这些韵律并不一定与古典格律诗保持一致,无论押韵方式和韵律出现的位置都可能和严格的英语格律诗不同,但是在对仗、节奏方面取得补偿,而且在排列上也有一些变化,更多地适应了现代英文的规律。英译文就如同是诗句的连写,有散文的形式,却也不失诗歌的节奏感。在英诗的格律、建行、分节上,以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要求和期待为出发点,译文自然地确定句式的开合、诗句的跨行、译行较为整齐,节奏抑扬顿挫,起伏有致,保留了原作品的说唱风格,因而读译文仿佛是说唱艺人用英语演唱的藏族史诗。类似的例子在整个译文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下面的一段唱词:
LU TA LA LA,A LA LA LA.TA LA LA.
At the eastern tower of the flaming tongues of hatred,
O wisdom,kindle the fire,
Still the pain of birth.
At the northern tower of the black wind of envy,
O wisdom,kindle the fire,
Still the pain of old age.
At the western tower of billowing lust,
O wisdom,kinkle the fire,
Still the pains of illness.
At the southern tower of the immense cavern of pride,
O wisdom,kindle the fire,
Still the pain of death.[9]
这是第二章格萨尔在消灭北方魔王,与之进行决战时的一段唱词。唱词共四节,每一节均有三行。开头部分是《格萨尔》说唱艺人开始说唱的典型词语:“LU TA LA LA,A LA LALA.TA LA LA”,也是过渡词汇,非常具有代表性。汉语中一般是以“鲁阿塔拉啦”开始。显然,该译本在这一点和原来史诗保持高度一致。每一节都以“At the(…)tower of(…),/O wisdom,kindle the fire,/Still the pain of(…)相同的结构重复出现。格萨尔分别从eastern/northern/western/southern(东、北、西、南)四个方向,对代表hatred/envy/lust/pride(憎恨、嫉妒、欲望、傲慢)的魔王城塔进行火攻,而(hatred/envy/lust/pride)又分别对应birth/old age/illness/death(生、老、病、死),最终目的是消灭这四种苦难(still the pain of…)。显然,这里译者运用了隐喻,映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前的传说,每一个城门都是与生、老、病、死相关的受苦受难,而格萨尔的出现便是减轻或是消除这些苦难的。
尽管相对于原作而言,《格萨尔》英译本的文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史诗译成了歌剧化的散体诗歌,但译者并未放弃对原作一些艺术特点的创造性再现。译者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史诗整体意义,没有拘泥于藏文史诗形式,而是打破原文外壳,进行现代英语诗歌的重写,为英文读者创作了一部歌剧化的英雄史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义、意境上,译者都采用了较为自由的翻译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造、再现。歌剧化倾向的译本影响很大,成为了Peter Lieberson《格萨尔王》的底本,其中的部分章节陆续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以剧本、诗歌、散文等多种形式发表,成为英语界《格萨尔》传播的重要源泉。
总体而言,《格萨尔王战歌》英译本不论是对原史诗内容的把握方面,还是对史诗艺术形式再造性表达方面,与其他英译本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译文语言的优美性、流畅性和欣赏性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尤其是对史诗翻译新类型的发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译学观念的更新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必须做出学科的合理性回答,并总结出一定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探索史诗的翻译方法与原则。
[1][2][3][6][7]Douglas J.Penick.The Warrior Song of King Gesar[M](Paperback).Mill City Press,Inc.(October 1,2009).
[4]Alexandra David-Neel&Lama Yongden.The Superhu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M].Boulder:Prajna Press,1981.Kessinger Publishing,2004(new edition).
[5]Zeitlin,Ida.Gessar Khan A Legend of Tibet[M].Illustrated by Nadejen.Montana USA:George H Doran Company,1927.(First edition,1927;reprint,1997).
[8]扎西东珠.《格萨尔》的艺术改编及《格》对民间文艺和文学艺术家创作的影响[J].西藏艺术研究,200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