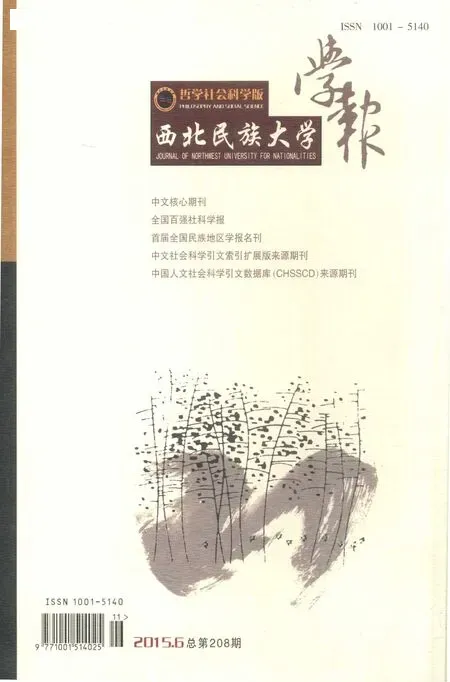叙事伦理的规范性与《瞻对》的文体驳杂性
郭国昌,许亚龙
(1.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天水师范学院 人事处,甘肃 天水741001)
2010年10月11日,《人民文学》举办“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研讨会,吁请作家们“走出书斋,走向现实,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1]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开始开设“非虚构”专栏,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再到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作家们用非虚构的写作方法,展示了当代中国的底层、人文和生命存在,也揭示了古老土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苦难与现实问题。
2013年,阿来的非虚构作品《瞻对》在《人民文学》连载,并于年末获得当年的“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显然,《瞻对》顺承了近几年的“非虚构”写作浪潮。很多作家“走出书斋,走向现实”,阿来则更明显的走向历史。现实从历史进程中演进而来,历史自然潜藏了现实的种种渊源。阿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历史文献中爬梳真相,再用半年多的时间通过民间走访、考察询问去印证文献的记录,最后用近半年时间完成写作,钩沉出川属藏地自雍正八年(1730年)始,近两百年的传奇故事。
《瞻对》讲述藏地“瞻对”近两百年与西藏嘎厦政府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纠葛以及汉藏文化冲突。最终,“瞻对”这块铁疙瘩融化于大势所趋的历史进程中。既要讲述历史,又要观照现实,在历史叙述中映射现实,阿来的选择是利用“非虚构”的写作方法。《瞻对》的全称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这个题目本身就有学术研究论文的形式意味,可见,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作品。如阿来所说:“这本小说不是历史小说,非虚构本身就是一种文体。”[2]细读《瞻对》,可以发现,“非虚构”文体特征的生成与其文学特性和文学伦理是相辅相成、必然联系的。
一、《瞻对》的文体生成
《瞻对》引述各类历史文献,颇有内容与形式上的考虑。就内容而言,历史文献本身就是历史事实的记录,既然是“非虚构”写作,那么对历史文献的忠实引述便是体现历史认知限度内真实的最好方式。就形式而言,历史文献作为历史的镜像化叙述,自然附着了特定历史时期历史见证者的主观体验。“非虚构”所追求的真实,自然也包括历史态度的真实,那么历史文献的忠实引述会让文本在形式上切近真实。如何处理历史文献是《瞻对》写作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又必须包含于非虚构写作原则之内,于是,《瞻对》形成了自身的文体特征。
首先,《瞻对》的文体与报告文学有所不同。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轻骑兵”,传统报告文学讲求纪实性、时代性、叙述性,形成特有的叙议结构。报告文学也追求非虚构性,在尽可能靠近真实的同时,提倡文化批判,立足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有学者认为,“现实的直击和反思从来都是报告文学最为擅长的领域。”[3]可以说,报告文学是最早的“非虚构”体裁。然而,报告文学,其首要是“文学”,所谓“报告”是为文学服务的,是统摄在“文学”这个概念之下的。
《瞻对》一书,在讲述历史,在反思现实,但其与报告文学最大的区别是不同于报告文学的趋利与纪实。白烨表示,“坦白说,如果以狭隘的报告文学概念来评判,阿来的《瞻对》的确不能算报告文学。但我想说的是,《瞻对》这种非虚构作品,阿来用很文学化的方式进行历史探究,里面出现的文学面貌,要比报告文学更丰富,超越了报告文学。”[4]所谓对报告文学的超越,笔者认为其扩展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质,传统的报告文学习惯于“一人一事”的叙述,如1978年引发广泛关注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的人生成长进程为依据,还原了一位历经磨难的真实数学家。《瞻对》不以“一人一事”为中心,而是展现了藏地“瞻对”的族群群像,清朝大臣和皇帝以及地方官员等的形象都跃然纸上。它借助于对历史的考察对现实进行反思,比报告文学更靠近文学。
其次,《瞻对》的文体与现代散文亦有所不同。现代散文,介于针砭时弊与个人抒情之间,在叙述上多条线索运用自如,即所谓宕开主线,着些“闲话”。郁达夫在评介现代散文的闲话风格时,说这种体裁“看来却似很容易,像是一种不正经的偷懒的写法,其实在这容易的表面下的作者的努力与苦心,批评家又哪里能够体会?”[5]《瞻对》中“说说夹坝”一节如此描述:“在我少年时代,家乡有喜欢显示英雄气概的男子会在腰带斜插长刀一把,牛皮做鞘,刀出鞘,宽三四寸,长二三尺,寒光闪闪,刃口锋利。在我家乡方言中,此刀就被称为夹坝。”这样的叙述颇有散文的味道,以致成为第二章的序言。下文又接着写道:“是的,这就是夹坝,这就是劫盗,这就是游侠。劫盗,是世界对他们行为的看法;游侠,是他们对于自己生存方式的定义。瞻对一地,山高水寒,林深路长,自然适合这样的‘夹坝’来往。”这样的语言就是散文的语言,闲适自由又不偏离主题。
在《瞻对》中,阿来仿佛特别迷恋这种散文化的叙述。诸如“瞻对,说从前”“闲话岳钟琪”“民间传说,迷乱的时空”“老故事再三重演”等等这样的标题,几乎每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标题之下,文本内容所对应的正是散文化的叙述方式。阿来说:“在今天的新龙县,在过去的瞻对寻访旧事时,我常常陷入民间传说如此这般的叙事迷宫中,不时有时空交错的魔幻之感。”[6]是历史的复杂繁琐让作者思绪纷飞,他需要一种言说方式,释放丰富的历史认知。“散文的创作既富有创造性又能给人带来满足感,说它富有创造性,是因为作者变成了故事讲述者和诗人;说它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是因为在对个人经历巧妙叙述的过程中,作者和读者分享了这种经历的意义。”[7]于是,在《瞻对》的阅读过程中,阿来仿佛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叙述的网络世界,乐此不疲的追本溯源,与历史对话,与读者对话。
再次,《瞻对》的文体与历史小说也不相同。通常的历史小说,在描写战争场面时,无不极尽铺展渲染之能事。在《瞻对》中,我们则看到这样的开篇:“由四川进西藏的大道上,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有三十六个人被藏语称为‘夹坝’的人抢劫了。在那样的年代,一行人路经僻远而被抢劫,以致被谋财害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先上报到川陕总督庆复那里。又由庆复上奏给乾隆皇帝。说明这件抢劫案太不一般。原来被抢的人是一众清军。”寥寥数笔,一个在历史小说中通常被渲染描述的情节就此戛然而止。而在第九章,作家不惜长篇抄录当时赵尔丰所领边军《评定德格赠科行军规则》中详细规定的边军战法,这在文学写作中并不多见。但是,“藏军剿灭瞻对英雄贡布郎加”一节又不乏情节渲染,则是因为材料来源于民间传说。
阿来说,《瞻对》是“不是小说的小说”,前一个“小说”当是普遍意义上的小说,后一个“小说”是为了强调《瞻对》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历史态度的不同,即作家主体的存在方式。在《瞻对》中,作家是显在于文本叙述中。纵观小说,有两条叙述线索:有关瞻对的叙述和有关写作过程的叙述。而写作过程的叙述不单单是为了增强作品的非虚构性,更是为了体现叙述者主动对历史的建构。有学者指出,当代历史小说一个重要特征是“采用了具有边缘性意识形态特征的第三人称叙述人,从而将‘自我’的历史改写为‘他者’的历史。”[8]正因为如此,阿来对历史是极为尊重的,以至于我们看到《瞻对》大量的文献引用和作者对写作过程的叙述,目的便是增强作品的非虚构性。
综上所述,《瞻对》形成了一种新的“杂”文体:在讲述清廷七次用兵瞻对时,借用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特征,文献史料分梳细捋,奏折训示往复誊写;在讲述瞻对历史源流及作家遍访民间时则具有现代散文的夹叙夹议、自由说理的特征;在讲述瞻对“夹坝”首领班滚和贡布郎加对抗清朝与嘎厦政府时则以塑造历史英雄的方式,营造神话与传奇色彩。
二、什么样的一种“非虚构”?
“非虚构”独立文体的形成源于其文学价值与追求的必然要求。正如阿来所说:“非虚构本身就是一种文体。”《瞻对》体现出这样的文体规律:历史文献——“杂”文本——超越文本。在历史文献的引述中,“拼贴式”叙述成为最主要的形式,历史文献呈现的是一种碎片化的历史真实,阿来所做的工作是厘清历史文献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叙述将碎片“贴合”在一起,讲述丰富的历史故事。作品用非虚构的创作讲述历史故事,吸收借鉴报告文学、现代散文和历史小说的技法,形成了新的“杂”文本。这样的“杂”文本,依据阿来的解释,“这样多角度交替观察,可能更接近客观事实。”[9]历史演进的规律就像是错综的河流,从源头分流出不同的现象,回溯源头。则要透过各种历史记忆,找寻不同的可能性。
“非虚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既非绝对意义的“非虚构”,同理,虚构也非绝对意义的非真实,只不过两种文学观念的倾向性不同。只要非虚构定义为带有小说性质的写作,那么它必然会有小说虚构的特征。只要作家进行了创作,便会产生作家的主体意识,那就必然会有个人化的情绪体验,就会产生虚构。从文本出发,超越文本,才能准确定位“非虚构”写作。
1.“镜像式”叙述重新定位了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历史文献属于创作过程中的“素材”,素材是为主题服务的。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搜集、整理、加工和改造感性的、分散的原始材料,写入作品,即成为“题材”。通常来讲,素材需要写作者进行提炼,经过创造性的改造,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进入文本。但是,《瞻对》一书,历史文献这样的“素材”是不加改造的直接作为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毋庸赘言,《瞻对》中最具叙述特色的便是大臣与皇帝的往复奏折。奏折本身就是一种文体,“汉初定仪则,把向皇帝进言的文书分为四种,其二为奏,主要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文心雕龙·奏启》)。奏的文体意义由此得到确立。”吴承学总结奏议类文体的特点,认为奏议类文体政论色彩强烈,“内容充实,逻辑严谨,文辞简明扼要,切中事理。”[10]到了《瞻对》叙述的大清朝时期,奏议类文书逐渐走向冗长,无法卒读,后有贴黄制度,复又简洁不失渊雅。此外,藏文文书、地方县志、史书,甚至中英条约的直接引述都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阿来说:“这次写《瞻对》,一方面因为突然发现材料太丰富了,另一方面,材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根本用不着我再虚构了。”[11]文献引用创造出一种历史的存在感,仿佛身临其境,触手可及。同时,文献自身所具有的简洁、渊雅、逻辑严密等特点也增强了文本的丰富性。
2.调查研究成为沟通作家主体与文本叙述的有效方式。调查研究在情感态度上有一个基本要求: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所谓“有距离的观照”。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中,“作家的任务是出现在作品中,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与读者交流,而非将自己作为作品的唯一主体。作家会去发现、质疑、品味、探索、观察、交流、好奇,最重要的是思考。就这样,事情发生了,他来到现场,将事情两两放在一起,拼凑出一幅与证据相关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果幸运的话,作家可以借助自己所经历的各种具体细节,向读者展示一个新的画面、新的世界。所以,非虚构文学作家就像一台传输机、一个媒介、一块透视镜片。”[12]历史文献的“镜像式”叙述功能,是一种证明,历史真实存在的证明。然而“镜像式”必定有其局限:作家是不在场的,于是采风与田野调查事实便成了作家在场的证据。历史文献是死的,是作家给予历史文献以生命力,让文献“发声”,讲述百年故事。同时,也为故事的讲述增添了丰富的历史意义。产生历史与现实的百年回响,过去与现在的交相辉映。
《瞻对》的文本叙述有两条线索:一条即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在自康熙以来因“夹坝”而演绎的一出出冲突与融合的传奇故事。另一条则是创作者阿来搜集历史资料,深入实地考察,从而在写作中梳理历史线索,反思现实问题的“心路历程”。历史故事与作家创作双线叙述,镜像式的历史文献引证,学者般的调查研究及论述方式,构成了《瞻对》的“非虚构”特质。
三、“非虚构”的文学伦理
“非虚构”被称作“第四类”写作,它为文学增添了新的可能性。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授予《瞻对》的授奖词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和细致艰辛的案头工作,以一个土司部落两百年的地方史作为典型样本,再现了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授奖的关键词是:调查、传奇、反思、文学,不妨将《瞻对》一脉的这种非虚构写作称为“非虚构历史写作”。这种写作不仅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范畴,也延伸了“非虚构”的文学伦理。
笔者认为,《瞻对》所体现出的“非虚构”的文学伦理,是指“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探索在文本自身如何处理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关系,如何产生话语碰撞,以及在文学建构过程中作家在交错的历史与现实中如何体现主体性,由此分梳历史脉络,映射现实人间的种种文化、价值、利益冲突。由此,文章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非虚构的历史性:历史与现实
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出发,文学和历史都是用语言符号对过去所做的艺术呈现。历史作为一种话语存在方式,它是过去的一种“认知”、“话语”,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正是历史的文本存在形式,历史是一种文本,是一种话语。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13]所以,对历史文本的解读成为理解“现实”与“过去”联系的有效方式。
在《瞻对》中,历史与现实具有互文性,历史的符号系统竟能如此与现实遥相呼应。沟通历史与现实的便是作品中的“文外之论”。在乾隆年间中央对瞻对的第二次用兵之时,由西藏地方政府派来领兵助战的台吉冷宗鼐擅离职守,称病返回驻防之地。对冷宗鼐的处理,也是煞费了乾隆皇帝的一片苦心。阿来分析皇帝“盖因愚鲁无知,以致获罪。其情尚属可矜。著施恩免其处斩,交颇罗鼐酌加惩处。余依议。”[14]的权宜之法。从而联系现实得出:“今天,常从各级行政机构人员口中听到一句话,西藏无小事,藏区无小事,恐怕这种感觉从乾隆时就开始了吧。”[15]诸如这样的论述,作品中处处可见。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史论今”,阿来说:“我主要是想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表达在这本书里。”[16]这样的表述根源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先验判断。朱光潜先生曾对此命题做了如下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现时思想活动中便不能复苏,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就这个意义说,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所以,“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某一种现时生活的兴趣引起历史学家对于过去史料的研讨和思索,历史就在这研讨和思索的心灵活动中产生”[17]。对阿来来说,正是他对“瞻对”历史的兴趣,促使了思索的产生,历史思索与现时生活的交汇,便产生了《瞻对》的非虚构文本。
在《瞻对》中,处处可见作者基于现实生活的历史认知,作者的论述甚为精到,似乎不必要再敷衍总结。如文所述:“写一本新书,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里子都很旧,旧的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18]阿来对“瞻对”历史的态度是带有遗憾和怅惘的。他对历史有着“同情之理解”:“法国一个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叫做‘历史归零’,意思是说,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所有事件的上演,就像一把中国算盘,打满了那有限的几档,便恢复了零,再来一遍。”[19]只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才能让思考客观且理性,不致走向“厚古薄今”的偏狭。
在非虚构潮流中,作家重在写作,创作被淡化了。毕竟,“非虚构历史写作”与历史学研究的写作是有巨大差异的。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的主体性体现在对史料的主观选择,作家在历史/史料中的主体性是明确的,其主体性受限于史料的占有程度。作家就像是一位拿着笔墨的画家,勾勒出历史故事的来龙去脉,挥洒出错综复杂的枝枝叶叶,画出一幅别致的画卷。打开画卷,观画者仿佛在欣赏一幅画,更像一次在历史场域中的精神探险。
(二)非虚构的文学性:写实与虚构
非虚构文学存在的前提是文学虚构与写实的基本二元判断。“非虚构”增强了这样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20]讲历史,又要立足现实,既要有对历史文献的调查研究,又不能丧失写作者的议论发言。在叙述技巧上,如何巧妙处理写实与虚构就成了关键之所在。
虚构,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品质,仿佛没有虚构,文学就没有其文学性,虚构似乎成了文学性的“乌托邦”。“非虚构”在叙事上的策略性,是为了解决“创造性”和“非虚构”之间的冲突。既然历史是一种文本,所谓“历史叙述”,是历史在讲故事,作者只是故事的转述者。那么,有没有虚构,那就要看历史文本自身了。在现代语境下,历史文本是带有想象和虚构特质的。对它的“话语”解释,无法脱离观念与语境的限制,所谓历史真实,只是特定观念构造中的真实。所以,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瞻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的非虚构作品,它的现实指向增强了其文学真实。
“虚构”的部分事实上可能更接近真实,“只要你给读者清楚地标出你的推测,那么推测就可能是通往生动、准确的一条途径。”[21]诸如《瞻对》中“说明”“其实”“于是”“也许”“依我的知识”等推测性词语既能让文本生动、真实,又表明写作者对历史态度的严谨、务实。“讲这些零星得来的故事,我倒觉得比依据史料叙说贡布郎加征服一个又一个土司的过程更有意思。”[22]离开了史料,故事便开始走向“虚构”,但是,叙述者对历史态度的严谨让故事依然真实,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也变得模糊了。
因为虚构的弱化,似乎主体性渐趋消退。但事实上,主体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主体潜入文本深层。为了防止陷入纯历史学文本的“叙事陷阱”,而采用叙事干预的手段,一方面与学者型的历史文本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增强文本的可读性、生动性。同时,也沟通了历史文献之“真实”与叙议闲话之“虚构”。“闲话岳钟琪”一节即有这样的桥段:“干脆再说岳钟琪,让此书暂告一段落。因为瞻对一地于史书中再兴波澜,要等到清代的嘉庆年间了。时间还要很久。瞻对战事结束后,乾隆还做了三十多年的大皇帝,然后才轮到嘉庆头上。”[23]再如文所述:“时间白白流逝,老套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不断循环。话到此时,当事各方孰对孰错,是是非非,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充满悲剧感的,是历史的停滞。”[24]创作者,成为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过渡,架设一座“非虚构”的文体之“桥”,从这个角度出发,“非虚构”是一种文学的新创造。
阿来的《瞻对》对非虚构写作空间的扩展有两点:一是写作技巧上,《瞻对》是一个故事套故事的好故事。讲述“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的同时,作家同时讲述了一个作家爬梳历史,调查研究,反思现实的“心路历程”。读者很难不从中得到启示: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二是文学伦理上,真实和虚构是辨证统一的。非虚构并没有挑战文学虚构性这一本质原则,只要叙述策略得当,内容的真实不会受到损害,反而能够杂糅各种体裁的优点,让形式和内容“创造性”的融合,创造出瑰丽新奇的文学文本。“非虚构”创作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有效探索,正是这种“四不像”的写作扩展了文学的边界,无论是《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非虚构现实写作”直面残酷的为现实“拍照”,还是《瞻对》这样的“非虚构历史写作”勾连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共振”,都让文学的边界向外延伸,也让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变得多样。
[1]编者.《留言》与《启事》[J].人民文学,2010,(11).
[2][16]阿来,童方.〈瞻对〉·“国际写作计划”及其他——阿来访谈[A].阿来研究(一)[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29,29.
[3]王晖.2006年报告文学印象记[N].文艺报,2007-3-1.
[4]“报告文学”已老“非虚构”请站起来[N].华西都市报,2014-08-15.
[5]鲁迅,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33.
[6][9][14][15][18][19][22][23][24]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77,24,86,24,33,266,126,62,217.
[7][12][21]雪莉·艾利斯.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M].刁克利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4,77,243.
[8]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意识倾向[J].文艺争鸣,1999,(1).
[10]吴承学,刘湘兰.奏议类文体[J].古典文学知识,2008,(4).
[11]阿来,刘长欣.“我不能总写田园牧歌”——关于〈瞻对〉的对话[A].阿来研究(一)[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3.
[13]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A].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3.
[17]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434.
[20]韦勒克.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