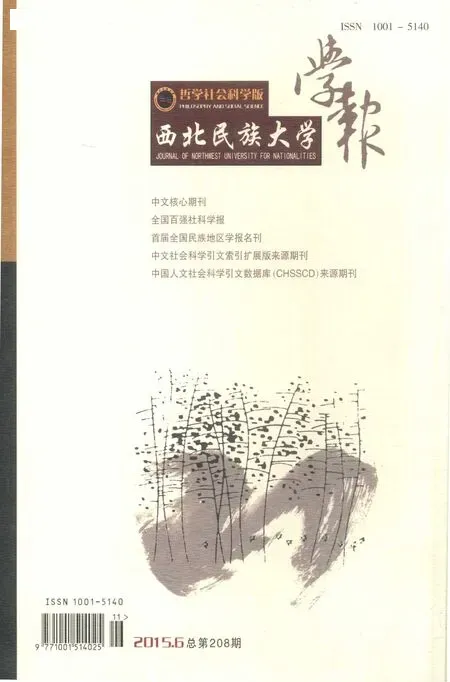从被符号化到符号化生产:丝绸之路的符号化审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
毕 剑
(河南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河南理工大学 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454000)
在现代社会,符号无处不在。罗曼·雅各布森曾说: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所构成[1]。瑞士符号学家索绪尔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把符号概括为具有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能指是符号形式,所指即为符号内容。能指与所指必须通过意指来完成符号的构建和表征。与索绪尔同时代的另一位现代符号学奠基人皮尔斯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符号学。按表征方式,皮尔斯把符号划分为图像符号、标识符号和象征称号三大类,并以实用主义作为符号解读的维度。艾柯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交流理论,进一步提出符号生产理论[2]。在艾柯看来,被“符号化是经验主体赖以交流的过程,同时交流过程又由于意指系统的组织而成为可能之事”[3]。艾柯的理论阐释使符号从一种被动的表征而发展为既与语境相关又具有生产功能的现代社会表征系统[4]。至此,符号不再仅仅是一种标识和交际,同时还是个体心理意识集体化或个体意识被社会意识整合的过程[5]。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被符号化的过程,即是这种事物或现象从原地被不断编码、解码和传播的过程。丝绸之路作为亚欧经济、文化交往的象征性符号,在亚欧各国间存在广泛共识。伴随亚欧交流的逐步深入,有关丝绸之路的话题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基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的广泛探讨。
一、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并以中国丝绸、茶叶、瓷器为主要交流物资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本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专指陆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丝绸之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从长安起程出使西域,历经多次限险最终为汉朝带回西域的丰富信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乌孙、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建立起联系。此后汉朝使者更远至安息、身毒、奄蔡、条支、犁轩等国。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壮举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汉王朝对于匈奴的被动局面,更使中原建立了与西域的广泛联系,从此中原物产,特别是丝绸、茶叶等通过西域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西亚,直至非洲、欧洲各国,开启了亚欧陆上经济贸易的宏大序幕。73年,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再次恢复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疏通了中断多年的西域贸易通道。张骞和班超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外交家,不仅有效扩大了中原王朝对西域及中亚、西亚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使中原王朝的政治边界向西大大延伸,为中原物产向西安全流通提供了重要保障。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及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将张骞打通的这条横贯东西、连接中国与欧洲的古代贸易通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丝绸》著作,至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承认[6]。丝绸之路作为当时亚欧经济交流的重要通商大道,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亚欧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进行公平贸易、平等交流、互利合作的对话之路,是人类文明成长的繁荣之路[7]。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丝绸之路已由一条人类经济、文化、商贸、交通的实质性道路升华为一种人类精神理念的象征──勇于探索、平等交流、友好合作、文化融合[8]。至此,丝绸之路的符号象征意义凸显。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并得到哈方的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中国、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原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则主要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以及中亚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本文则主要探讨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古丝绸之路为文化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合作平台[9],以丝绸之路沿线综合交通通道为基础,以沿线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国际区域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动力,以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跨国经济发展带[10]和特定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11],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12]。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连着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尽管该区域被称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带,但其指涉中亚各国由于政治制度、经济规模、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等存在诸多差异,且长期相对封闭的区位条件、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都严重制约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表现为明显的“经济凹陷”,从而在世界上形成较为突出的“网球拍”现象[13]。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相关各国能从大局出发,充分尊重对方的国情和文化,以古丝绸之路为情感纽带,贯彻“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14]理念,实现“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15],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16]以及传承、交流、传播、创新的重要平台,从而缔造一个共同富裕、生态平衡、全面繁荣[17]的新型国际合作区域。
二、丝绸之路的被符号化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18]。被符号化的过程在于使事物本身的信息能够简化并快速传递出去,同时能够使受众通过符号背后的意指获得产生新的联想[19],即把能指形式与所指蕴涵提炼明晰[20],也就是能指被所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的意义更加丰满,符号得到更多的认可,甚至可以说被符号化为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一)经济领域的被符号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更多是西汉王朝受匈奴王朝的政治压制、军事压制而采取的侧面缓解措施。西域东向汉朝、西通波斯、南联天竺、北达高加索各国,地理区位极其重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改变了西域诸国对西汉王朝的原有政策,从此西域与西汉王朝建立了通畅联系,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大宗物资为丝绸,丝绸贸易彻底改变了亚欧各国对中国的认知。丝绸在拉丁语中为“Seres”,即“赛里丝”,中国也因此被称为“赛里丝国”或“丝国”。随着丝绸之路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其后的贸易不再局限于丝绸,仍被认为是具有丝绸气息的经济之路。
丝绸之路第一次沟通了亚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以中国丝绸的名义开启了亚欧各国的贸易旅程。丝绸在这里不再只是一种商品名称,它同时承载着亚欧各国繁忙的经济联系,映照着沙漠中的驼铃声声,传递着欧洲各国对中国丝绸的无限憧憬。显然,丝绸之路已不只是一种贸易通道,它更被象征为自由贸易、平等贸易和贸易繁荣。丝绸之路在经济上的被符号化更彰显出古代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突出地位。
(二)文化领域的被符号化
伴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开展,亚欧各国间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上的交流不可避免。蔡愔的西域求法及竺法兰白马驮经至洛阳并建白马寺开启了佛教经西域内传的序幕,唐三藏西天取经,袄教、摩尼教和景教及伊斯兰教东传,印度语和吐火罗语及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的广泛使用,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体育等东传中原,敦煌莫高窟的多艺术展现等都是西域沟通亚欧各国文化并经丝绸之路传播的典型文化现象。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是显性的,文化是隐性的。显性的经济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文化上的了解、认知、接触、改变和重建。
从符号学意义上讲,所谓“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域、团体、阶层的富有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载体[21],丝绸之路不仅传递着中国的文化符号(丝绸、瓷器、茶叶),同时,丝绸之路本身也被符号化。这种被符号化是在经济贸易的显性化背景下缓慢发生的,亚欧各国文化的互通和互认,来自于经济贸易,而后在经济贸易的刺激下快速发展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民族领域的被符号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亚欧各国的文化,同时,也使亚欧各国,特别是西域各国的民族基因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彻底改变了某些民族的民族特征,民族融合加剧。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多次上演民族融合大戏,月氏人、粟特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羌人、回鹘人、契丹人的民族变迁使丝绸之路成为民族融合之路,有些民族永远消失了,有些民族获得了重生,甚至通过丝绸之路的民族融合,还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回族。尽管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战争的冲击,但文化上的影响因素同样不容小觑。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2]。显然,民族具有变迁性。民族基因、民族文化都可以在历史演变中发生改变,民族融合则是民族变迁的重要途径。丝绸之路沿线曾经列国并存,文化冲突不断,丝绸之路的开通,有效加深了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文化上的共通推动民族上的融合,民族上的融合则进一步演变为宗教上的共同信仰或多宗教信仰并存(同一区域不同宗教的共同存在)。被符号化的丝绸之路传递着民族合作、民族变迁、民族融合的博大情怀,丝绸之路也被象征为民族融合之路。
(四)科技领域的被符号化
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文化上的丝绸之路只能是其历史价值的一部分,丝绸之路同样为亚欧科技文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四大发明”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欧洲,并引发欧洲的经济、科技、文化和航海的颠覆性革命;在西域及其他沙漠地区流行的坎儿井及井渠技术同样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科技传递作用。另外,医学、天文、铸造、农业种植等技术在亚欧各国间也深深地映现着丝绸之路的印迹。
科技发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需要借助不同民族的聪明才智进行接力式改进,而丝绸之路就肩负起了亚欧各国科技文明传播的重任,可以说,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世界科技文明之路。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的符号化生产
从符号主义文化观出发,文化具有符号特性[23]。构成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意指”的关系示范中,形成完整的符号体系。符号与符号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以符号资本为基础的[24],符号资本是指在被尊重和认同层面上具有的资本,它是一种被承认的经济或政治资本,因而,符号资本也是信誉资本[25],同时也是情感资本,甚或为政治资本及权力资本。
丝绸之路作为一种被全世界认可的文化符号,在其被符号化的过程中,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因特殊的情感联结而逐步接收了其符号资本,并把这种资本以一种国家意志的形式进行生产。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同建设的经济合作区域,把政治合作、经济合作与文化符号进行结合,使文化符号在国家层面进行符号化生产。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曾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26],但从符号互动理论出发,文化并不仅仅是“历史延续”的符号传递[27],文化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在符号的作用下产生出新的内涵。丝绸之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符号象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式在更多领域进行符号化生产,并创造出更加具有时代感的符号化内涵。如果丝绸之路的被符号化是历史、社会、文化综合积淀的结果,是一个被动过程,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是一种主动的符号化生产过程。符号由被动产生到主动生产,反映出符号价值内涵的深刻变迁和重构。
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丝绸之路被符号化为经济之路、文化之路、民族之路和科技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又以符号资本作为前进的动力,以符号化生产的方式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借用,在政治、安全、经济、能源、文化、旅游等领域进行着创造性生产。
(一)政治、安全领域的符号化生产
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除中国)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曾受前苏联及俄罗斯影响较深,前苏联解体后又长期作为独联体成员国与俄罗斯保持着较为紧密联系。由于政治体制差异及国际环境制约,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各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关系较为松散,对其影响有限。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影响日益提升,对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各国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增强;同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各国从最初的安全合作逐渐扩展至政治、经济、能源、社会等多个领域。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长期盘踞于中亚各国,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三股势力”的受害国,也迫切需要与其他各国在安全领域开展更加充分合作,从而有效打击“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
政治互信、安全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保障。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作为具有共同情感纽带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治上更加贴近和信任,安全合作仍是第一要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借助了丝绸之路的文化情怀,以符号化生产的方式把政治和安全置身于一个经济合作框架内,使相关各国能政治上充分信任、安全上充分合作,共同为丝绸之路注入新的内涵。
(二)经济、能源领域的符号化生产
长期以来,由于受前苏联经济体制影响,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各国普遍存着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的经济结构,致使其经济发展迟缓,但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地处世界战略重心,又都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富集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美国等欧美大国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甚至直接插手其经济政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轻工业发展较快,小商品市场活跃,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但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强调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发展相对迟慢。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也逐步开始推动经济领域的合作,并把经济合作作为其重要职能,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经济与能源领域的符号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个跨越国际的区域经济合作区域,从根本上保证上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经济合作,特别是能源经济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之中重。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具有悠久的经济贸易合作传统,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符合各国互通有无的共同追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文化、旅游领域的符号化生产
文化是符号化生产的灵魂,旅游是符号化生产的重要媒介。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涉各国(地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具有共同的信仰空间,特别是中亚各国曾在前苏联政治框架内共同发展半个世纪以上,具有浓厚的兄弟情怀。中国西北各地伊斯兰文化表现明显,与中亚各国具有较强的情感感应。同时,中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旅游出境国和世界第三大旅游入境国,具有广阔的旅游发展前景。中亚各国作为相对封闭的内陆国家,长期以来对外开放严重不足,旅游经济发展迟缓,而中国又对中亚的灿烂文化具有深厚兴趣,双方在旅游领域的互动必将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区域,文化与旅游的推动必不可少。特别是丝绸之路文化本身的吸引力,曾经长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把这种文化符号引向更广阔的范畴,以符号化生产的方式,把文化、旅游进行深度结合,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下,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创造。
丝绸之路作为世界的共同记忆,曾经演绎过灿烂的丝绸之路文化,并把这种文化符号化为探索、自由、平等、合作的经济繁荣之路、文化融合之路、民族变迁之路和科技传播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符号资本为动力,充分调动相关各方的积极性,以符号化生产的方式在政治、安全领域和经济、能源领域及文化、旅游领域进行着符号化重构。但这种符号化生产过程需要充分尊重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他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自主性,应该是在自由、自愿、复合、共赢、开放[28]的精神框架下的符号化生产。
[1]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9.
[2][4]黄华新,陈宗明.符号学导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3]艾柯.符号学原理[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358.
[5]齐效斌.意象符号化与文化逻辑[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3):64-68.
[6]贾云峰.纵论江河[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212.
[7]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路径与实施对策[J].经济纵横,2013,(11):60-65.
[8]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9]白永秀,王颂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纵深背景与地缘战略[J].改革,2014,(3):64-73.
[10]唐立久,穆少波.中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9-24.
[11]卫玲,戴江伟.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地理空间的内涵识别及其当代解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1-39.
[12]卫玲,戴江伟.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机理与战略构想——基于空间经济学语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9-50.
[13]张建勇,杨恕.试论第二亚欧大陆桥空间形态与空间经济结构[A].鲍敦全,何伦志.经济全球化与21世纪中亚经济[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187-191.
[14]王海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能源外交运筹[J].国际石油经济,2013,(12).
[15][17]古龙高,古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解析[J].大陆桥视野,2013,(9).
[16]白永秀,王颂吉.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走廊[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2-38.
[18]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19]汤际澜.太极拳符号化传播探析[J].搏击(武术科学),2013,(12):29-30.
[20]陈又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存[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6):66-69.
[21]范秀娟,王晶晶.民族文化符号化与文化生态空间的建构——以壮锦为例[J].梧州学院学报,2011,(4):43-48.
[2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A].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
[23]阳宁东,刘韫.符号化生产在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运用——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31-34.
[24][25]章兴鸣.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政治传播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08,(9).
[26]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3.
[27]覃琮.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符号化生产及其互动——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74-77.
[28]程贵,丁志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互利合作[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9-125.
--Монголия--Россия содействует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