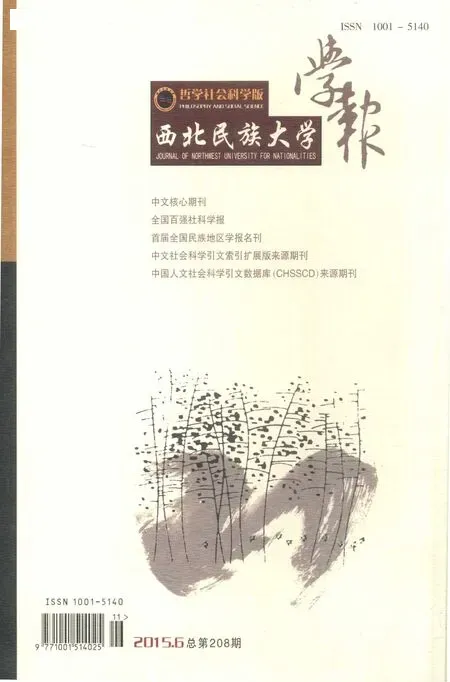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宽容”概念释义
王浩宇,何俊芳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一、引言
“宽容”的践行乃是一种政治实践,例如沃尔泽将“宽容”视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能使有着不同历史、文化和身份的群体和平相处。”[1]“宽容”最初产生的社会基础来自于人们对社会网络或社会等级二元分类的“想象”与感知——多数与少数、同质与异质、正统与异端的对立。但在洛克的《论宽容》之后,“宽容”不断地受到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审视”——其理念与实际行动之间往往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这是因为“宽容”这一概念最初的合理性来自于政治环境本身,但人们往往将“宽容”置于“普世的道德”中进行探讨与实践。正如Richard Vernon和Samuel V.LaSelva所指出的那样:“以一个过于宽泛的视域理解宽容,会对人们产生误导,最终造成对这一概念边界的忽视,或让人们完全失去对‘宽容’的认同。实际上,‘宽容’只是一个政治概念。”[2]
无论“宽容”是一个被“泛道德化”的概念,还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概念,人们必须承认在所有与“宽容”有关的语境中,似乎很难找到宽容的“边界”。一方面,“忍耐”、“容忍”和“忍受”等概念均在道德外衣的掩饰下变成一种对他人和他物的“宽容”。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平等”“多元”等价值信条已被普遍视为个人或群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宽容”本身的价值又何以体现?本文在对“宽容”这一概念探讨的基础上,认为受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所谓道德上的“宽容”往往会演变为一种“表面的宽容”或“消极的宽容”。特别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宽容”应以制度保障为基础,将其视为巩固多民族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一种理念或策略,从而促使“真正的宽容”得以实现。
二、“宽容”的起源、理念与实践
从“宽容”的起源来看,在17世纪末的西方社会,“宽容”逐渐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形成,它在当时并不是一种“道德的提议”,而是对待多元化的“现实评估”和“政治许诺”,意义在于禁止政治团体以牺牲公民自由的方式去维持国家秩序[3]。上述“多元化”和“自由”的实质是指宗教团体的多元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最早对“宽容”的认识来自于“宗教宽容”的实践,其中心问题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对不同宗教团体给予合法性的承认与保护,目的在于防止由于经常性的宗教冲突而产生的国家分裂。从国家层面来看,早期的“宗教宽容”实为一种对宗教“异端”的“特许自由”。
同时,人们对“宽容”最初的认知与实践实际上并不在于对美好道德的向往,而在于对国家所要求的“宽容”这一公民义务的履行。17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普芬道夫曾指出,公民有两项基本义务:对国家及统治者的义务——服从与尊重和对本国同胞的义务——友好与和平,避免产生冲突,对同胞的义务乃是一种“宽容”,确切地说是对具有不同信仰的同胞的“宽容”。戴维·伯切尔认为,“人们之所以履行这种‘宽容的义务’不在于这将对他们的灵魂与精神产生任何益处,就像尊重财产权利一样,‘宽容’是创造并且维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家的基础。”[4]而这也与许多学者的看法相似——人们所表现出的“宽容”并不是为了展现自我高贵的品质和德行,而是展示出自己服从国家的决心与忍耐力。实际上,“宽容”的核心意义是同现代公民权利与义务密切联系的,如哈贝马斯曾指出:“民众作为国家公民相互之间的不断包容,不仅是为国家提供了新的世俗合法化源泉,而且也提供了一个以法律为中介的新的社会抽象一体化层面。”[5]
完全将“宽容”从道德的光环下剥离的确“有失公允”,人们不能否认“宽容”的起源具有道德的基础,但最初的“宗教宽容”是一种政治实践,不是一种如同人们追求“真、善、美”那样的道德实践。从国家层面来看,“宽容”是一种“治国方略”,它通过赋予某些宗教团体“自由”来实现其脱离国家的“不自由”,鼓励公民之间相互容忍、尊敬以维护一个国家的完整。从个人层面来看,“宽容”所展现的是公民对国家、政府和权力的尊重与服从,人们所认同的是“宽容”背后的权力国家,而非“宽容”本身。
在讨论“宽容”的理念时,自由主义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许多政治学家看来,自由主义者相信“宽容”既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也是社会富足发展的手段……对立的观点和利益之间能够达到平衡或自然和谐,这往往会降低不同思想间爆发水火不容的冲突的可能性。”[6]由此,人们也认为“宽容”理念的合理性也恰恰在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一种价值,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接近真理的实践。
虽然“宽容”的理念与自由主义息息相关,但是在对“宽容”的实践中,“自由”与“宽容”之间“孰轻孰重”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实际上,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人们该如何认识“宽容的边界”。如前所述,“宽容”最初是一种“政治实践”,而非“道德实践”,“宽容的理念在于“解决问题”,维护国家与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而非“美化心灵”,如旨在践行“真、善、美”那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宽容”的理念的确是一种自由,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自由是建立在“宽容”之上的自由,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7]自由的观念是“宽容”的理念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宽容”就建立在绝对的自由之上,胡适在《自由主义》中指出:“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8]
从实践层面来看,“宽容”是一个具有严格边界的概念,它的发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人们最早对“宽容”的实践来自于一定的现实基础,即多样或多元化的社会。“宽容”的出现正是人们意识到差异的存在,这种“差异”表现在宗教、文化、民族、地域等方面,而“宽容”的目的正是要尊重“差异”,以维护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环境。所以,“宽容”的首要特征就是一种“接受差异”的态度。
第二,人们对事物具有三种认知判断的结果:肯定、怀疑与否定,只有接受“否定的差异”才可被认为是“宽容”。仅从字面上理解,接受一种“肯定的差异”很难称为“宽容”,这只是简单的“赞同”或“支持”。另外,从严格意义上讲,接受“怀疑的差异”也不是一种宽容。尽管“宽容”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在于人们不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是否正确,所以我们才需要去“宽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正如人们赞同一些事物在于赞同它们是正确的一样,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赞同”某些事物在于赞同它们是不正确的,那么,接受“否定的差异”其实就是一种对“不赞同”的接受,即“宽容”本身的意义仅是一种对“不赞同”的接受。所以很难认为“宽容”包括那些尚未决定正误的“怀疑的差异”的接受,也就是说接受“怀疑的差异”仅仅是一种不确定,而非“真正的宽容”。
第三,“宽容”的实现与权力的“禁止”密切相关。接受“否定的差异”仅仅反映了“宽容”实践的一个维度,权力的使用是决定“宽容”还是“忍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从认知上来看,“宽容”与“忍耐”很难区别,两者都可解释为对“否定的差异”的接受,但“宽容”表明主体处于主动地位,即主体有权力使“宽容”变为“不宽容”。在政治社会学给出的关于“宽容”的经典定义中,权力乃是判断“宽容”的最主要因素,如“在相互竞争的群体中,无论是支配群体还是被支配群体,都不能试图侵犯其政治对手作为国家公民和演讲自由的权力。”[9]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宽容”中的权力:一方面,对于“宽容者”来讲,“宽容”意味着其避免使用权力而压迫或同化“被宽容者”。另一方面,对于“被宽容者”来讲,“宽容”意味着其拥有足够的权力来维护自我利益和自由。
三、民族宽容:差异性社会整合的工具
“民族宽容”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动,它既要求赋予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以抵御外界的“同化”压力,又禁止其他民族使用权力压制或消除民族差异,它不仅不会造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与内部冲突,还会消除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而带来的民族不平等。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乃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内部文化差异的意义,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多样或文化多元被视为一种战略资源而非社会问题。同时,很多理论家认为,尽管一个民主政体可能会被激烈的冲突所分裂,但如果公民拥有且能够享受由民主政体和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那么国家仍然是稳定的,正是从这一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宽容”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有利于维护一个民主政体的稳定[10]。“民族宽容”作为差异性社会的整合工具,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个体公民权实现的重要依托。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对各种文化的保护不仅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每个民族公平发展的体现。承认这种文化权利就意味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们不仅不能干涉个体的文化选择,同时还要保证个体能够依据他们所选择的文化路径而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民族宽容”不仅是一种对异文化的简单允许与尊重,同时也是一种“外部的保护”,即保证少数民族成员具有广阔的文化自主实践空间。
“外部的保护”所代表的是“真正的”公平,而非“绝对的”公平。对于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来讲,行使自主选择文化实践的条件容易得到满足,甚至可以认为主体民族成员能够自动获得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来讲,情况并不乐观,他们总是面临来自外界的巨大的同化压力,即使没有公开的歧视,一般情况下,主体民族的成员对待少数民族文化成员都是一种“善意的忽视”。因此,实行公平,就要求这些文化的成员能够采取特殊的措施来使他们的成员获得所需文化资源,以实现其作为自主选择者(恰如多数民族文化能够做的那样)的潜能[11]。
在一个社会内部,少数民族正是由于其“少数”的地位,使得他们的思考与行动不断地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与限制。践行“宽容”以维护其文化、宗教发展的稳定并保护少数民族群体免受来自外部压力的冲击,这一“外部保护”的行动是与多民族国家的自由民主相一致的,它有助于使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处于更加公平的基础而自由选择其文化实践的路径。但这里必须指出,宽容的限度在于行为是否对自我和他人造成伤害。如果行为是对自我造成伤害,那必须得有合理正当的理由才被允许;如果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则超过了宽容的界限而不被允许[12]。
另一方面,“民族宽容”不仅是对群体文化权利的“外部保护”,还是保证少数民族公民个人权利实现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权利依附于个体行动者”的理念不仅没有很好地实现少数民族个体成员作为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还逐渐侵蚀着其作为多民族国家一员的“特殊权利”。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在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内部,只有群体身份和群体权利得到支持与维护,才能保证许多个体基本利益的实现。群体对个体之所以重要,在于少数民族个体通过群体的成员资格能够获取“真正的”而非“绝对的”公平,这种“身份政治”和“少数的权利”来自于国家政策对民族群体的支持。同时,人们似乎也很难想象单独行动的个体能够保证多元机制的活力,以维持某种社会文化的生存。
由于各种社会因素所限,少数民族成员个体往往需要借助少数民族的“群体身份”而实现基本的公民平等。“民族宽容”正是一种建立在少数民族群体之上的“宽容”,它针对的客体乃是一个群体和作为“某一群体中的个体”,而非单一的公民“个体”。“民族宽容”作为一种差异性社会的整合工具,其作用不仅在于保障群体权利的平等弥合以民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多民族国家的差异性裂痕,还在于通过群体身份来保障民族成员个体权利以整合公民作为最小单位的民主国家。
四、反思“民族宽容”的困境:“真正的宽容”还是“表面的宽容”
在伯纳德·威廉姆斯看来,“宽容”是一种“不可能的美德”,因为它要求人们接受、服从和适应那些人们所拒斥的观念,它还要求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产生认知冲突并以追求矛盾为目标的世界中[13]。这一论断直接指出“宽容”作为一个道德概念的困境——理想与现实、观念与行动的不一致。同时,在多民族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与平等不仅无法真正实现,还往往将“宽容”变为一种“表面的宽容”,使其“泛道德化”。
人们将“宽容”泛道德化的根本表现在于:接受自己所赞同或认可的差异,人们往往称之为“宽容”;排斥或不愿接受那些与自己相比具有较大差异的人或物,同时也往往避免使用“不宽容”。由此,“宽容”便体现出其作为一个道德概念的“霸权”:某种差异能够被我们接受,是因为我们“宽容”,某种差异不能够被我们接受,不是因为我们“不宽容”。实际上,这一现象反映出“民族宽容”作为一个道德概念的困境:第一,“宽容”本身是一个具有明确限制条件的概念,即接受“不赞同的差异”,而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美德”。第二,“宽容”中的自由主义理念在保证所谓的自由与平等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现代社会的“冷漠”或“善意的忽视”。正如胡适所言:“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14]
对于“民族宽容”来讲,接受“不赞同的差异”就明显呈现出这样一种张力:对本族的观念价值与宗教法令做出承诺和遵守,同时又要接受或容忍那些与本族教义相悖的宗教成员[15]。如果说由于受到宗教信仰、认知取向、价值判断等因素的影响,“宽容”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道德任务”,那么人们更应该警惕的是,与自由主义理念息息相关的“宽容”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宽容”,却造成一种“冷漠”而致使“表现的宽容”逐渐作为“美德”而实践。
“表面的宽容”并非是由于人性或道德的缺失而产生,其真正原因在于:受自由主义信条影响的“宽容”是建立在对个人自由、平等公民权的尊重与保护之上,并非建立在“宽容”本身是“好的”这一理想基础之上,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对多元与差异的日趋尊重和理解,“宽容”逐渐变为一个“自我实现”的概念——同时也丧失了其最初的意义与价值。
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在于如何调和“多数的规则”与“少数的权利”之间所不断产生的张力,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探索一条道路保持与促进文化及民族的多元,并逐渐消除那些可能分裂国家的差异性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包括避免采取强制压力的同时,摆脱一种“粗暴生硬的多元文化主义”,其所有的价值观念仅仅是“相对的”多元[16]。我们必须明白,自由意志不是一种宣传式的口头表达,它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体系作保障,使真正的民族自由与民族平等得到实际落实。同时,在协调国家与民族群体、民族群体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宽容的沟通机制使不同利益有了合法的表达途径,各种利益得到切实落实[17]。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正在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各类民族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面对这一现实情况,各民族之间要加强交流与互动,通过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理解彼此的文化习俗,接受彼此的行为方式,杜绝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构建践行“宽容”的社会制度,使“真正的宽容”从多种途径得以实现,为维护国家的稳定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迈克尔·沃尔泽.论宽容[M].袁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2]Richard Vernon,Samuel V.LaSelva.Justifying Tolerance[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7,No.1(Mar,1984),pp.3-23.
[3]Gerson Moreno-Riano.The Roots of Tolerance[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65,No.1(Winter,2003),pp.111-129.
[4]David Burchell.Multicultu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J].Majorities,minorities and toleration,Ethnicities,2001,1:233.
[5]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5.
[6]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三版)[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9.
[7]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
[8]陈根发.宽容是什么[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3).
[9]Mary R.Jackman Prejudice.Tolerance,and Attitudes toward Ethnic Groups[J].Academic Press,Inc.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1977),pp.145-169.
[10]Mitchell A.Seligson,Dan Caspi.Arabs in Israel:Political Tolerance and Ethnic Conflict[J].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1983,(19),p.55.
[11]尼古拉斯·巴宁,邱仁宗.政治哲学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02.
[12]冯润,何俊芳.试论西方国家的“宽容”与少数群体权利[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13]Adam B.Seligman.Tolerance,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Boundaries[J].Society·Jaunary/February,2004.
[14]胡适.容忍与自由[A].胡适文集(第11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23.
[15]Adam B.Seligman.Toleration and Religious Tradition[J].Society·July/August,1999.
[16]Gail Lewis.Welcome to the margins:Diversity[J].tolerance,and policies of exclusion,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8:3,pp.536-558.
[17]冯润.试论民族宽容[J].贵州民族研究,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