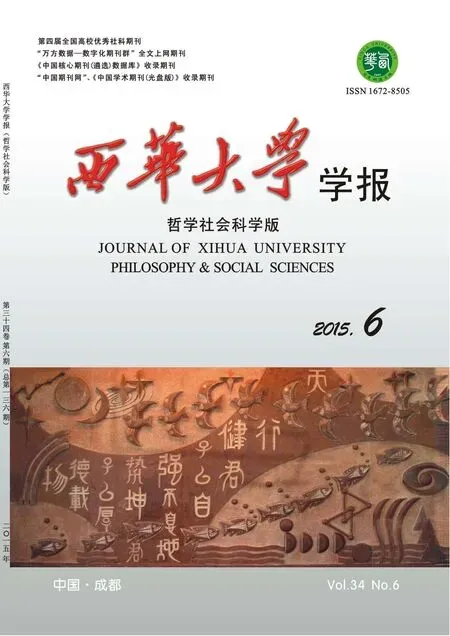口译中的显化与隐化——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视角
许丽学 符荣波
(1.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5;2.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口译是一种即时的跨语言交际行为,译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捕捉源语中的信息并迅速地完成目标语的计划、组织和发布。通常而言,受现场压力、话题难度以及个人的知识结构、思维视角、观点立场等因素的影响,译员并非原封不动地表述源语中的字面意义,而是对信息的内容做一定的取舍。Gile认为,若是这种增减无碍于源语中话语意图的传达,则仍不失为口译忠实的表现[1]。显然,这是从口译的标准和交际效果来论的。在Baker看来,源语和译语之间的这种信息偏移其实涉及翻译活动的共性(universals),且与语言组合无关,显化与隐化就是其中之一[2]。不过,从以往不少有关显化与隐化的研究来看,大多停留在笔译层面,涉及口译语篇的考察较少。本文首先对翻译中的显化与隐化研究作一梳理,随后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视角,对一场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口译语料进行分析,以期加深我们对翻译中共性特征的理论审视。
一、显化和隐化的研究概述
翻译研究中的“显化”(explicitation)和“隐化”(implicitation)概念可以追溯到 Vinay & Darbelnet[3]的定义,分别指“把源语中暗含但可凭上下文或情境推理而得的信息在目的语中明确表述的过程”和“使译语语境和上下文呈现源语中所明示的特定信息的过程”[4]。Nida[5]也注意到了翻译中的此类现象,不过他运用了增添(additions)、删减(subtractions)、更改(alterations)等翻译技巧,并根据使用目的区分了详细的子类。一般认为,Blum-Kulka[6]开启了对翻译中此类现象的系统研究,她在《翻译过程中衔接与连贯手段的转换》一文中将显化现象置于语篇层面进行了考察。她选取了英语和法语的组合,通过对比职业和非职业译者在两种方向下的衔接标记转换,指出译者对源语的阐释往往会使得译文相比原文出现更多羡余(redundancy),具体表现为衔接手段的使用增加,并推测这可能是所有翻译中的普遍现象,这也是后来译界广为所知的“显化假说”(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不过,Blum-Kulka所说的显化不包括因为两种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差异而使用的衔接标记,而是翻译过程中的内在属性。对此,Séguinot[7]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显化不仅包括Blum-Kulka所说的“原文未表,译文明示”的那部分信息,还应考虑译文中明确提及而在原文中以暗示或通过预设的方式蕴含的信息,以及那些译文相比原文更为凸显的成分。同时,她还考察了英法互译的翻译实例,指出主题链改变、连接词增加以及从属信息转换为并列句或主句结构同样导致了译文比原文更为显化。
在翻译过程中,信息的显、隐、增、减往往是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显化假说的提出为研究者研究翻译中的共性规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比如,为了检验该假说,Linn Øverås[8]截取了各 20 本挪威语小说的英译本和英语小说的挪威语译本片段并建立了双语平行语料库,随后抽取每个小说片段的前50句分析句中的衔接手段使用情况。她的研究发现,译入挪威语产生的转换达496处,其中显化347处、隐化149处;译入英语产生的转换为324处,其中显化248处、隐化76处。从显化与隐化占所产生的转换比例来看,该实证分析无疑是对 Blum-Kulka[6]假说的有力佐证。此外,Vehmas-Lehto[9]比较了译自俄语的芬兰语报道材料和同一体裁的芬兰语源语文本,发现在连词使用频率方面,翻译文本的显化程度更高。他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假说。
受西方研究者的影响,国内学者把对显化和隐化的考察拓展到了英汉语的翻译文本中。贺显斌[10]选取 O.Henry 的短篇小说 The Last Leaf,以Séguinot[7]的概念论述为参照,对中译文中的显化现象进行了统计,发现汉语采用增加词量、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等方法能使显化程度有显著提高。不过,相比前面几项实证研究,贺显斌的研究数据偏少(小说原文仅134句),缺乏代表性。王克非[11]也曾利用自行研制的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考察原文与译文的语句对应情况,发现在语篇层面,无论是译入英或汉,目标语文本都呈扩增迹象。这似与Lin Øverås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陈建生和蒋扬[12]以自建的中国译者英译本语料库和英语原创小说语料库为类比研究对象,发现中国译者英译本皆呈现显化的共性特征。此外,柯飞[13]从汉语的自身特点出发,认为显化与隐化的发生应与翻译方向和语言的形式化特征有关,形式化程度较高的语言译成形式化程度较低的语言,显化程度发生递减,隐化则相应地递增。
与上述笔译中的显化和隐化研究相比,口译语篇中的类似现象则较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Shlesinger[14]曾系统考察了英语-希伯来语同传文本中的衔接转换现象,认为显化假说在口译中可能同样适用。她同时指出,不论译入何语,译员都倾向于增加衔接手段将隐性的关系显化。Gumul[15]的研究从形式入手,关注了英语-波兰语同传语料中句子结构、词汇和语用等层面的显化特征,并结合回忆访谈(retrospective comments)就显化的成因作了初步的解释。胡开宝和陶庆[16]基于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对记者招待会语料和政府工作报告语料进行了句法操作规范的对比分析,发现显化规范对前者的影响要甚于隐化规范,且显化规范对前者的影响小于后者,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英汉语的形式化差异、口译时间的紧迫性和译员的介入等因素。这些研究虽然对口译中的显化和隐化作了初步解读,但是其缺陷还是明显的。比如,Shlesinger仅截取了时长11分钟的同传语料作为研究对象;胡开宝等的研究虽然有庞大的语料库作支撑,但对显化和隐化的考察仅涉及连接词,缺乏普适性;Gumul尽管对显化现象作了详细的分类,不过其基于语法形式的分类总有零碎之嫌。
鉴于此,下面我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观出发,对翻译过程中显化和隐化现象进行讨论。随后,通过对一场汉英政治口译的语料分析,探讨这一规则在口译语篇中的具体体现。
二、显与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解释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翻译中的显化或隐化现象虽然是译语在表述源语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形式化特征,但不可否认,其根本内涵仍是语义的,因为显和隐的实质是意义的醒豁和掩藏。在功能语言语法中,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符号系统,包括语义、词汇语法和音(字)系三个层次。在这一系统网络里,词汇和语法是合二为一的,词汇是语法的最精密化和直接体现形式,语法是词汇的抽象化描述和概括,两者在表达语义时是互补的[17]。Halliday[18]从功能的角度,把语言看作是表达意义的符号资源,任何言语行为都是语言使用者从语言的多层次网络中不断作出选择的结果。就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而论,功能语言学家普遍认同,形式是意义的实现手段,意义则由形式来体现。可见,形式与意义是体现和被体现的关系。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形式未必是一般的具体词汇,还包括结构性的语法手段。Halliday同时指出,意义是一种潜势,具体语言语用中的能指和所指或形式和内容并非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也即同一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述。Halliday的这一说法是对单一语言而论的。不过,在翻译这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中,我们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同样成立。一方面源语和译语都来自于作者和译者基于不同语言系统的选择,都是特定交际场合中同一命题的意义潜势被现实化(actualized)的结果;另一方面译者选择何种词汇语法手段再现这一命题意义受到译语自身特点、语境或社会文化关系的制约。源语中以词汇化手段表征的意义成分既可以在译语中选取同样的词汇形式得以表达,也可以通过语篇结构和上下文的形式蕴含在字里行间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显化和隐化都是意义的不同呈现方式,是译者根据话语情境和交际意图作出的语义选择。
在Halliday&Hasan看来,语篇是意义的交换形式,意义的交换是所有言语活动的核心。Halliday[18]从功能的角度对自然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即语言可以表达概念(ideational)、人际(interpersonal)和语篇(textual)三种意义。在小句层次,概念意义指的是语义系统中能够呈现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经历和经验的成分。在语篇层次,概念意义还包括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人际意义成分指的是语言具有的表达讲话者身份、地位、动机、态度、立场判断以及建立社会关系的功能。语篇意义则反映了语言连字成句,组句成篇的成篇功能(enabling function)。在系统功能语法的框架体系中,意义的这三个层面分别与上层的语境和下层的词汇语法发生联系。在语境的作用下,构成语域的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变量分别对应于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并由词汇语法层内的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系统、主述位结构(Theme-Rheme)和衔接等来体现,最终形成现实化的语篇。因此,考虑到意义在词汇语法层内的体现方式差异,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自然应具有多维度的特征,而不仅仅是Blum-Kulka等人所谓的衔接手段转换。
此外,Halliday[18]提出的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概念对我们审视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现象亦不无启示。他从意义的不同体现方式出发,把表达相同意义的不同语法形式区分成一致式(congruence)和隐喻式,前者是更接近外部世界事态的表达方式,后者则是词汇语法形式对其本义的背离,也即意义的再符号化[19]。因而,根据意义的不同,隐喻式的表达又可分为概念语法隐喻、人际语法隐喻和语篇语法隐喻。
例1:All roads lead to Rome可以译为:
a.条条大路通罗马;
b.殊途同归。
前者是意义表达的一致式,后者则是语法隐喻。同样地,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源语表达人际意义的语气和情态以及体现语篇意义的主述位和信息结构发生等方面改变时,都能使语义的呈现方式变得更“显”或更“隐”。
三、口译实例分析
口译活动是一种典型的交际行为,涉及意义的表述、理解和再现过程。Halliday[18]认为,尽管言语的角色多种多样,交际者一般扮演两种角色,即“给予”(giving)与“求取”(demanding),且涉及对象无外乎“物品或服务”(goods&services)和“信息”(information)。以此为根据,他区分了提供、命令、陈述和提问四种言语功能,由语气系统中的祈使、感叹、陈述和提问来体现。从这一点上讲,同样是翻译,口译员一般要比笔译者行使更多的言语角色。这是因为,口译属于即时交际,具有互动特征,并且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由讲话双方的关系决定的。以英汉总理记者招待会为例,该情境语境中的语场是内政外交和国计民生,语旨是作为执政者的总理和中外记者,语式则是口语。译员尽管是该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但其作用是促成双方语旨的实现,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因此,译员同时要履行陈述和提问的言语功能,扮演问者和答者的话语角色。记者招待会口译语篇的这一特点是笔译文本所不具备的,也为我们考察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此,本文选取了2012年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答问的口译语料,根据上述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所作的阐述,把口译中的显化和隐化按照表达意义的不同分为三类,即概念、人际和语篇显化/隐化,同时参照Séguinot给的显化定义,考察它们在口译语篇中的不同体现形式。
1.概念显化与隐化
例2: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
I don't feel surprised at all that there have been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Internet about t 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根据《新词语大词典1978—2002年》,“拍砖”一词指的是在BBS(电子公告板)上发表批评他人的文章。就其命题意义的表达方式而言,源语用的是隐喻式,而非一致式的“批评”。译员不仅在口译中将其处理成一致式的表达,同时还将“拍砖”的对象予以显化,而非僵硬地照搬源语的字面语义,此举无疑有利于目的语听众对信息的接收。
例3:温总理您好!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Lianhe Zaobao:in recent years,you have addressed the topic of political structural reform on many occasions,which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我们注意到,在记者招待会现场,提问者一般均会采用称呼语(vocative)以示客套,而这在译员的翻译中常常省略。在上例中,译员不仅将此类表达略去不译,对表达提问者心情和指示问题开始的话语标记也干脆跳过直奔主题。尽管不能排除这种处理是译员个人风格使然,但是考虑到记者会现场提问机会和人数比例的悬殊,这种表达多为客套和礼节性质,往往无关主旨。因此,译员对此类概念意义进行隐化不但不影响整个表达,还保证了互动交际的紧凑和高效。
例4:听到香港记者的提问,我想起在2003年我访问了香港,也就是在那一年那次访问,我见证了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定。
Your questionreminds me of my visit to Hong Kong in 2003.It was during that visit in that year that I attende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在例4中,小句“听到香港记者的提问”在及物性系统里是一个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虽然在汉语中省去了主语,但不妨碍话者经验意义的传达。但这一过程在译语中直接以名词结构your question体现,出现了表达形式上的级转移(rank shift)。按照林正军、王克非[20]等人的论述,这一意义体现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跨语言语法隐喻。由于缺少施事者和环境成分等的参与,名词化的语言结构往往在语义的充分程度上不如动词性结构,因而往往成为意义隐化的一种途径。不过,语境中的预设可以对信息的完整性起到较强的互补作用,使交际得以维系。此外,译员对下文中协议名称的缩写CEPA进行翻译则是显化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口译的有效交际原则。
2.人际显化与隐化
例5: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I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people and the history.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appreciate wha t I have done,but there will also be people who criticize me.Ultimately,history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在上例中,源语引用古语,是意义的隐喻式表达。汉语中的古诗词具有极其精炼的语言结构,一般在呈现概念意义的同时,往往也是作者情怀和思想的寄托,所谓“诗言志,歌咏言”。源语中话者借诗明志,显然,这涉及到话语表达的人际意义。在体现话语的人际意义方面,情态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英语中,情态动词是表达情态意义的重要手段。本例中译员通过三个“will”的连续使用将源语中蕴含的情态意义充分显化,再现了源语所表达的人际功能。
情态系统为人际意义的表达提供了重要的词汇语法资源。这是因为,系统功能语法对英语中的情态解释超越了传统语法中的情态动词,还囊括情态附加语(如probably,always,certainly,usually,definitely等)、谓语扩展式(如 be willing to,be determined to,be supposed to等)和投射性的小句结构(如 I believe/think/suggest等)[18]。译员往往借用这些手段明示、强化或弱化源语中的人际内涵,如:
例6:我2010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In 2010,I told the story of the Dwelling in theFuchun Mountains.I believe that with utmost sincerity no difficulty is insurmountable.
例7:我为能做人民的公仆而为人民办些实事而感到欣慰。
I feeltruly encouraged and happythat I have those opportunities to serve the people as a public servant.
例8:所以日本领导人应当恪守中日关系的三个政治文件,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We hopethat the Japanese leaderswill strictly abide by the three China-Japan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can truly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除情态意义外,语气也能体现人际意义。在语气的几种类型中,陈述语气一般用于提供信息,疑问语气则用作求取信息。如果语气结构在具体的语境中发生了变化,即交际者选择非一致式表达言语功能,则会产生语气隐喻。在口译中,如源语的一致式在译语中以隐喻式体现,相应的人际意义必然隐化,反之则呈显化。如:
例9:记者先生提到,如果我做一件事能够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那么我选择哪一件事情。
If there wa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do to ease the China-US trade imbalance,what will it be?
例10:Reuters:……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this matter.
路透社记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语篇显化与隐化
“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不是句子或段落的简单堆砌”[21]。除了表达概念和人际意义,语言在被交际者不断选择并构成现实化的语篇过程中还能表达语篇意义,从而确保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衔接性[22]。语篇意义可以由主述位结构和衔接系统来体现。一般而言,主位是话者表述信息的起点,是小句关心的部分,述位则负责对主位进行充分阐述,使语篇不断延伸。在口译中,如源语中的主述位结构在译语中发生了变化,也会对语篇意义的表达产生影响。
例11:AFP:……What can your government do?What’s the best way for your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is situation?
法新社记者:……您认为您领导的政府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应对这个局面?
在上例中,源语中记者提问采用的两个主位“what”一个充当宾语,一个充当表语,属于有标记主位(marked theme)。译员在口译中对两个小句的语义进行了整合,使用单个小句复合体,并以“您”作为复句的主语,属于无标记主位(unmarked theme)。源语中的主位成为译语中述位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其实是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关系,源语中的语篇意义有些在译语中被隐化了。不过,语篇的这种组织方式应与英汉语在表达形式上的差异有关,又如:
例12: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I have often thought about inviting some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whoregularly make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to Zhongnanhaiso that we can have a face-to-face discussion about the issue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普遍认为,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因此,同样是表述意义,源语中的句式结构较松散,小句间的语义联系仅使用了一处照应(reference)予以维持,而且还省略了主语;译语的句式表达形式则更为紧凑和严谨,运用定语从句和连词手段把话语信息连成一个整体。就语篇表达的衔接关系而言,译语无疑比源语更趋显化。与上例中的主述位差异一样,语篇的这种处理方式面向的是同一情境内不同的交际对象,其最终的交际效果是大同小异的。
结语
语篇是交际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呈现经验、表达观点和组织思想的媒介。由于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的不同,人们在用语篇表达意义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翻译中尤为明显,显化和隐化则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视角,指出显化和隐化的语义本质,并从概念、人际和语篇三个维度予以区分。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对一场总理记者招待会口译语料的考察,探讨了显化和隐化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体现。虽然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语篇的这三层意义总是相互交织、合为一体的,但这并不排除词汇语法的特定选择在表义上各有侧重的可能。因此,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语义观入手,我们可以对翻译中的显化和隐化现象作出比以往研究更为全面的透视。以此为出发点,未来的研究不妨继续深化实证方面的探索,检验“显化假说”和翻译规范在口译中的适用性。
[1] GileD..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Revise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1.
[2] Baker M..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C] //M.Baker et al..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233-225.
[3] Baker M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4] Klaudy K..Explicitation[C]//M.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80-84.
[5] Nida 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6] Blum-Kulka S..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C] //L.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298-313.
[7] Séguinot C..Pragmatics and the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J].TTR:Tradtion,Terminlogie,Redaction,1988(2):106-114.
[8] Øverås L..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An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J].Meta,1998(4):557-570.
[9] Vehmas-Lehto I..Quasi-Correctness:A Critical Study of Finnish Translations of Russian Journalistic Texts[M].Helsinki:Neuvostoliittoinstituutin,1989.
[10] 贺显斌.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63-66.
[11] 王克非.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410-416.
[12] 陈建生,蒋扬.中国译者英译本的翻译共性考察——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13] 柯飞.翻译中的隐和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303-307.
[14] Shlesinger M..Shifts in cohes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J].The Translator,1995(2):193-214.
[15] Gumul E..Explicit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strategy or a by-product of language mediation?[J].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2006(2):171-190.
[16] 胡开宝,陶庆.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句法操作规范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5):738-750.
[17] 杨信彰.英语词汇研究面面观[J].中国外语,2011(6):34-39.
[18] 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Arnold,1994/2004.
[19] Thompson G..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Arnold,2004.
[20] 林正军,王克非.跨语言语法隐喻探讨[J].外语学刊,2012(1):59-63.
[21] 李辉,陈玉秀.基于口语语料库的非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学生连接语使用状况的对比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22]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