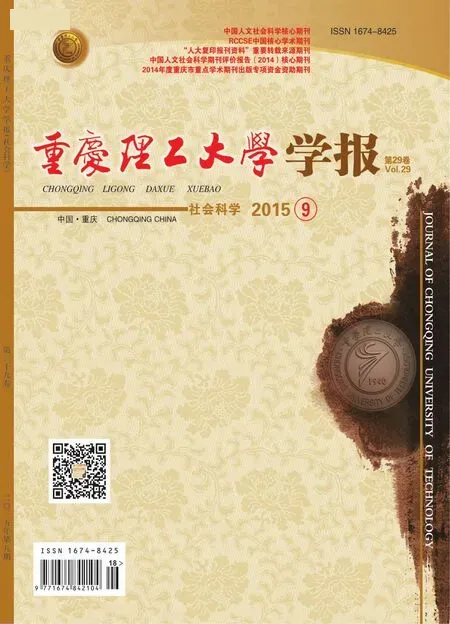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视阈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
——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文本研究的分析与探讨
李 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视阈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
——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文本研究的分析与探讨
李 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文献当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两个概念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出现并具有理论意义的。生产劳动是直接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则只是为人们提供了生活和精神上的服务,不能增加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得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劳动指向对象和劳动产品享用者的变化,很多非生产劳动在实质上也转为了生产劳动。在当代社会,由于现实需要,通常人们对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解不只是局限于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将二者的内涵做出了调整,使其具体化。马克思独特的经济学—哲学视域中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也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和哲学本体论思想,使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具备了永久性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价值。
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劳动;剩余价值;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论》的创作史始于19世纪40年代,青年马克思独特的哲学家气质赋予其早年的经济学笔记极具个性的哲学探究特质;50年代后,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文献中放弃了对较多哲学议题的繁缛、艰深的论述,转而针对经济学领域内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的攻坚和思索。但是,马克思仍然擅长在阅读、审查、批判前人文献的过程中扬弃其思想,并运用辩证思维,将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蕴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之中。这使得《资本论》的手稿始终处处透着浓郁的“经济学—哲学”双重话语气息。百余年来人们热衷于挖掘、探讨和钻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哲学思想正是根源于此。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写于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共23本,1 472页,大约200个印张,堪称鸿篇巨制,很多经济学、哲学问题在其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与理析。尤为可贵的是,马克思在研究各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从多个视角出发,从而对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加以全方位的阐释。在揭开蒙在剩余价值头上的面纱时,马克思十分专注于查清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真实样貌”,进而充实、丰富和扩展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特定涵义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源起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其在《手稿》及《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文献中得到了系统、完整的阐述。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索周期,在与多位杰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思想“交锋”和“切磋”的过程中,马克思一点点地积累、总结和完善了自己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同《资本论》相比,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文献更能反映出马克思在阐明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性和严谨性。而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创作一个阶段性“节点”的《资本论》,则囿于其中很多结论性的语句而未必能成为探析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最佳文献。
不过,不管是相对于普及的《资本论》,还是大多时候为专业研究人员所用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其中所论述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阐发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涵义和区分在这里有着严格学理上的使用范围:从字面上去理解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不困难,人们很容易将生产劳动归结为产出实在财富(主要是物质财富)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则是精神性劳作的代名词,甚至可以与“第三产业”划等号。
这种理解方式显然看重了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本身无可厚非。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文本出发,这里面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和澄清。马克思是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和詹姆斯·斯图亚特(重商主义)、魁奈、杜尔哥(重农学派)等人的经济学理论的语境中阐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问题的。1861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接近于成熟,但如何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具体形式研究透彻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大难题。他唯有深入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和书本当中去寻找答案。
在亚当·斯密之前,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一步步地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向完备与严整,特别是魁奈和杜尔哥等人“不再在流通过程中寻找剩余价值起源”,“而是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转到了直接的生产领域”[1]6,这在认识深度上远远强于只信奉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尔虞我诈”的重商主义。但是,重农学派过于看重农业生产,他们认定农业生产是唯一能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人类生产形式,只有农业劳动才称得上是生产劳动,因而剩余价值也必须以地租的面貌出现。
显而易见,重农学派的观点较极端。亚当·斯密毫不含糊地对此给予了否定,指出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就是“工资+利润”,它是产出剩余价值的劳动,它与资本直接相交换。马克思认为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十分到位,他并没有纠结于生产劳动的所谓“物质规定性”,而是从社会关系的深层角度来看待劳动的内在性质,因而是科学的见解。但是,斯密无法将这一立场坚持到底,他坚信“生产劳动也是物化在任何商品中的劳动,即体现在一种有用的产品上的劳动”[1]7。斯密终究未能完全将“生产劳动”和“物质内容”二者分隔开来,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有极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初期,第三产业不可能占据社会生产的主流地位,人们观察经济事物和现象的目光和视域还不够宽广。再加上斯密本人对剩余价值的看法也较为狭隘,他和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一样,殚精竭虑地找出某种或某几种利润形式来表征剩余价值。斯密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并不情愿对劳动价值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不会意识到剩余价值是内含在商品当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也不会承认不管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规定性。
马克思是否全面和正确地解释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呢?仅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目的上来看,马克思是成功的。他在斯密等人的基础上进了一步,更为明确地阐明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在赞美斯密的同时继承了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合理区分;另一方面又把二者之间的差异辩证化,从而更加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给人类劳动造成的异化后果——已成为社会力量的资本不会放过任一人类劳动,只要人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劳动终将被烙上“剩余价值”的印记。
马克思分析道,生产劳动是直接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既生产出剩余价值的劳动才算是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真正产物是剩余价值,所以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就是说,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2]520生产劳动自然包含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它不是纯粹的抽象劳动。非生产劳动起作用的中介是交换价值,但是对于特定的消费者来说,非生产劳动只提供了“服务”,即购买非生产劳动者劳动的人只是享受了非生产劳动所给其带来的使用价值。
同一个劳动,对于不同的主体可以既是生产劳动,也是非生产劳动。例如,歌剧院里的歌者的工作给听音乐剧的观众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感染,观众支付的听音乐剧的费用对于观众本人来说仅仅是得到了精神性服务,因而此时的歌者的劳动对观众来说就是非生产劳动;但是,如果歌者有雇佣者,就是剧院的老板,那么观众所付给剧院的门票钱里就包含了歌者的工资和剧院的利润。利润的存在说明了歌者的劳动对于剧院老板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歌者的劳动给资本家带来了剩余价值。因而,歌者的劳动在剧院老板这里,充当的是生产劳动的角色。
马克思在批判斯密的过程中不断明确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在《手稿》当中,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探讨该问题与其劳动价值论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呈现出的所有劳动都在资本的力量下变成了异化劳动这样的景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种种经济现象放到更深刻的理论层面上来解读:工人的每一项劳动,即便是在面对普通的消费者或是从事因由自己兴趣爱好而全身心投入的各种活动(如音乐、绘画、歌唱、体育、书法、管理、科技等等),都在无形中被资本的牢笼所困囚——人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当中,演变成了赤裸裸的“生产劳动”!
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到,就是当人作为个体来进行经营或是社会活动时,应该怎样判别个体工商户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例如,裁缝自己开了一家布艺店,他给客户裁剪衣物和缝制产品,他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这时他所挣到的金钱是源于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呢?这里有三种情形:
(1)如果裁缝的店铺是租赁而来,那么这个裁缝的劳动对于房东来说毫无疑问是生产劳动,因为房租本身就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2)如果裁缝是店铺的拥有者,那么他总会千方百计地赚取更多的报酬。他可以通过提高技艺和增加布料成本来为自己提价找到更多更好的理由。消费者不可能从他这里得到“纯粹”的服务,他们必须多支出一部分费用来为裁缝日后的“扩大生产”贡献原始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裁缝依然是在付出生产劳动,只不过这种生产劳动的行使主体是他自己——这或许是最纯洁和励志的“资本原始积累”。
(3)裁缝如果雇有伙计、帮手或学徒,那么这些雇佣劳动者肯定在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劳动。
这就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是无法规避的,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铁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联接,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生产劳动,又好像在享有着非生产劳动。这被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描绘成终极的、美好的社会图景,但这不过都是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表象罢了。不管是资本持有者以何种方式来组织进行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资本家的生产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获取剩余价值”[1]12。
在研究剩余价值的进程中阐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根本性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大特色。诚恳地说,马克思只有在涉及到经济学问题时,才会如此精细地定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依照马克思所想,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类劳动做出极致的异化和严苛的限制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分支,之前的私有制形式和理想中的、之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都不会这样极端地“展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知晓何谓剩余价值,而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占有,剩余价值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价值”,劳动才算是属于劳动者的愉悦实践体验:“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价值,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对于这样的劳动才可以说,这个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他创造新价值。”[1]137
如此看来,我国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一场关于如何规定社会主义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讨论是有原因的。毕竟马克思阐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原初语境较为学理化,而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包含的内容与其内涵必然会有所拓展,它们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当中都充当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只是把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研究限定在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内,就会为理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实践设置诸多不必要的障碍和难题。
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学理内涵的“变形”与“具体化”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在现实中最明晰的显现,自然是生产劳动增加了社会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量,而非生产劳动则没有如此的“增添效用”。由于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而剩余价值往往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品,即那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发展成果。“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实现在商品中,实现在物质财富中”[2]416,故而人们很容易就会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简化处理,即生产劳动是实体性的劳动,各种投身生产建设的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而不能为社会带来实际成品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是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统一,但生产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境遇当中,其地位似乎总是比其社会规定性高一筹。“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是一切社会形态生产劳动的共性,劳动的社会规定性是不同社会形态中生产劳动的特殊性。”[3]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发展形态,当人们去强调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时,生产劳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属性必定会被放大,因为人类的物质生产行为终究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根本。此时,非生产劳动不得以退居其次,“服务性劳动”的标签便牢牢地贴在其身上。特别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中,非生产劳动的特性更是看上去无关紧要:在阶级社会,它只是供剥削阶级最大化享乐和腐化的代称;在非阶级社会,由于劳动被私有制钳制的局限性被消除,非生产劳动在相当多的时候是被排斥在“主流生产活动”之外的。
有学者坚持认为非生产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是异常薄弱的。例如,商业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即便是利用自己的销售性的服务为雇主挣得了剩余价值,但因为这样的劳动没有形成任何的物质结果,也很难被认定为生产劳动[3]。这个时候,非生产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的色彩非常强烈,它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各个社会形态当中表现的整体性称谓,同时与具体的生产部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性劳动泾渭分明地互相区别。为了细化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二者之间的分别,有学者概括了以生产劳动为主的相关产业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内贸、外贸和物资供应部门,以及文学艺术、图书出版、影视、应用技术研究等部门[4]。这些生产部门都为社会提供了物质产品(商品),理所应当是生产劳动的集聚地。
与生产劳动相对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非生产劳动的阐明——社会当中的服务性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的“总称”——绝对是真知灼见。服务(非生产劳动)毕竟是一次性消费的劳动,它侧重于精神和生活领域,并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生产性劳动。并且,服务提供者给消费者送去的直观体验和感受就是满足了某种内在需求,其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合而为一的,劳动结束则消费完成,这也证明了服务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因为它没有为这个世界或是人类社会留下什么。“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2]529如果说生产劳动是劳动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那么非生产劳动就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当社会当中没有资本,非生产劳动就只剩下了“特殊使用价值”,也就是非实物性的“服务”。
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即刻应用,物质生产的效率大大超出了马克思那个时代人们的想象,即使是马克思本人也不会预料到时至今日非生产劳动对于现代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物质生产部门的高生产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入服务经济领域,仿佛生产劳动不再是人类社会基始性的人类劳动了。虚拟经济和网络化经济的成长与繁荣更加加深了人们心中对此的认知与印象,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界限已经愈发模糊,究其本质是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早就意识到,尽管马克思是在研究剩余价值的时候去阐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但终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话语扎根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都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具象,它们都有鲜明的社会规定性,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展现。为便于辨认与分工,人们在面对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时就会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进行“具体化”的处理,就好比上文对生产劳动部门的归纳那样。到此,马克思文本中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形”,这既是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又是理论运用于实际的必然要求。
同生产劳动的“具体化”一样,相关学者也列举了非生产劳动的相关内容,这些劳动在明面上,不能算作是实质性的生产性劳动。它们一般集中在下面一些单位和机构:
(1)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部门。如各级政府机关、军队、公检法,以及各种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譬如金融、计划、财税部门)等。
(2)教育部门。如国民教育系统、党政官员的训练系统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机构。
(3)卫生部门。主要包括医院、疗养院、各级卫生防疫机构。
(4)各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各种学术团体等[4]。
这样的划分肯定是有道理的,它遵从了马克思《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小心翼翼地将具有双重性质的劳动(如文学艺术、影视传媒、科学研究等)排除出了非生产劳动的范畴。其实,认同生产劳动不应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而应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改变、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容量”:“劳动在促进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着,突出表现为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以直接劳动为主转变为以间接劳动为主、以有形劳动为主转变为以无形劳动为主、以物质劳动为主转变为以精神劳动为主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带来了劳动内涵与外延的相应变化,使更大范围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劳动者。”[5]与此同时,非生产劳动的“领地”显得愈益狭小,到最后就只剩下了纯粹的社会、行政服务性劳动。不得不说,这既是对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继承,又是对其的发展:人们摒弃了对“非生产劳动不如生产劳动重要”的偏见,转而对生产劳动本身加以了灵活和包容的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社会中很多被指称为“服务性劳动”的劳动并不是非生产劳动而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当年为了讲清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将很多从传统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的劳动都看成是非生产劳动:“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6]513这些不断涌现的新的工种究其本质而言仍然是生产劳动,因为它们也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如各级建筑用材的供应商、制造食品半成品和其他食材的食品加工厂、为机械生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小型厂矿、高科技产品的组装企业、安装部门等,都为社会的生产和建设持续地添砖加瓦。这些在马克思看来是非生产劳动,然而在本质上应当归属于生产劳动的“服务性产业”,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经济”。有人把服务经济错误地看作是非生产劳动,并试图论证非生产劳动与生产劳动之间应该“消除区别”,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误解。当今人们所谈到的服务经济中的“服务”的含义不同于马克思《手稿》中的“服务”二字,前者更多地意指多样化、现代化、科技化、精细化、网络化的产业运作与生产,后者则专指使用和消耗一定的人类劳动量来满足“服务”(通常是技艺性劳动)购买者在生活和精神上的某种需要。混淆二者会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做出过度的“延伸性”解读,从而把繁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掺杂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概而言之,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内涵的“变形”和“具体化”不是要否定《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相关思想,而是赋予这些理论新的内容和指导实践活动之价值,并没有违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即便是将非生产劳动简化成上述的那些地地道道的服务性劳动,这些单位和机构还是要通过征收劳动者的税收来维系。税收归根结底来自于劳动者的生产实践活动,而它们的设立也是为了方便和优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终归是生产劳动在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劳动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有着根基性的重要意义。
三、“劳动本体论”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劳动”。劳动关涉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历史就是经由劳动创造的,整个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劳动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196,“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7]193。劳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近乎于“本体”的意义,历史车轮的转动,没有劳动是万万不能的。那么,是否能够把“劳动本体论”当作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呢?
我们知道,《手稿》是一部充满“经济学—哲学”双重话语的经济学文献,马克思在讲到剩余价值时经常将劳动和人类历史引入到行文当中,这使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时不时闪现着马克思历史观和本体论的洞见[8]。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劳动过程进行了鞭辟入里、细致入微的分析,指出“劳动过程是工人从事一定的合乎目的的活动的过程,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9]64。工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加工生产资料,从而改变劳动材料的形式,赋予其新的物质样态。一方面,劳动磨耗掉了旧有的物质(劳动资料),制造出了新的物质(劳动产品),进而满足人们(各类消费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人的劳动能力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转变了自身“活劳动”的性质,成为了“对象化劳动”(“死劳动”),也就是将自己物化在了客观世界之中。这就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维系和运转都是以劳动为轴心的,劳动创造世间的一切存在物,世界也是根源于人类劳动的现实化和对象化(物化)。
当然,劳动资料本来就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中介,马克思在经济学的语境当中论析劳动过程,必然会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放眼更为纵向和宏观的人类历史之变迁,劳动既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石。劳动相异于动物行为的典型标志便是劳动的创造性,它不是简单地利用自然界中存有的现成物质,而是经过人类智慧的指导和人类行为的参与,将本来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东西“创作”出来。不管是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还是为人类文明之火添薪加柴的精神性劳动,都不会凭空在大自然里显现。而动物的活动则明显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动物至多是利用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它们无法给自然界带来新颖和独创的东西。即便是较为接近人类的黑猩猩,他们所谓的“发明创造”(如黑猩猩懂得垫高箱子或是石头来取得高于他们身体高度的食物,等等)充其量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然界中本已存在的自然物,其“精神”或是“思想”行为只能是看成“适应世界”,而不是像人类一样的“改变世界”。而劳动的出现、改进与发展,显示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历程,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宏大和雄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遗产。活劳动永不停息地转为“对象化劳动”,每一阶段的劳动成果都为后一阶段劳动和人类的发展提供必不可缺的基础和条件:“单纯从物质来看,从现实劳动过程本身的观点来看,一定的过去的劳动过程表现为新的劳动过程的准备阶段和条件。”[9]66人类社会历史由里至外看都是叠加式的发展轨迹,出现在后的社会形态在生产力上总是要超越在前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状况脱离了劳动是解释不清楚的。因为原有的生产资料都源于劳动,而人们在这样的生产资料上所进行的新的劳动肯定会对其物质属性进行变更和加工,使其更加适合人类生存和社会的要求。故而,世界越来越以人类所期望的形象示人,劳动改变了最初的自然界,使其成为了人化自然。
在这个意义上,人所接触的自然,人所看到的世界,人所居住的社会,人所拥有的关系,都始于劳动。在人的视域范围内,全部物质都带有劳动的痕迹,没有劳动,世界根本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马克思甚至说:“任何一种自然物质通过以前的劳动而获得的属性,现在是它本身的物质的属性,它就是通过这种属性而起作用或提供服务的。”[9]67很明显,在这里马克思不再将劳动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将其意义普遍化和一般化,试图回答人类社会的本原问题。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马克思这样的阐述正是在提出他的哲学本体论观点。所有的劳动过程,都是“消耗旧材料,产出新产品”,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新的产品通常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而已。从劳动第一次发生在人世间起,它就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这段话针对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不是单指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货币、生产资本还是其他的劳动资料、劳动工具以及劳动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前提下才成为资本”[9]71。而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乃至人类世界本原的劳动过程,则始终活跃在历史舞台,它的年代同人类一样久远:“既然现实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生产的需要还是个人消费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那么,现实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同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定的社会形式无关,它是所有社会形式共有的。”[9]69到这里,完全可以认定马克思有着“劳动本体论”的倾向,至少,他在《手稿》里留下了令人察觉出此的文字证据。
确切地说,“劳动本体论”只能包含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当中,即“劳动本体论”至多说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体”是什么,它不可能是全宇宙的“本体”。人类未出现时的自然界里不包括劳动,物质世界的优先存在性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申明过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0]269“劳动本体论”成立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涵盖社会历史发展全部因素的根源。于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把劳动理解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集合,劳动本体论是否能够成立?
如上文所述,生产劳动是能够为人类社会“产出”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不具备此功能。照此来看,非生产劳动只是人类社会的修理工或是平衡器,充其量算是润滑剂或是加速器。总不能说,诸如政府的管理行为这样的劳动为这个社会直接生产出了什么成品吧?可是,非生产劳动能够增值社会效率,它和科学技术一样,起码间接性地给人类社会提供了“物质加成”。如果将其排除在了“社会本体”之外,显然是不适当的做法。也就是说,“劳动本体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劳动本体论”这样的表述是否会引起歧义。
从起源上看,劳动是否和人类一同出现还有待考证。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说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前后就学会了劳动,更无法证实劳动与人类出现这两件事情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是什么。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的讲解来看,劳动是“人”的另一个指示词语,但这一点终究未能得到考古界和历史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严谨地说,“劳动本体论”颇为值得怀疑,毕竟称作“本体”的事物,起码要在时间点上具有先在性。
但“劳动本体论”也可以在理论上成立,只是由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甄别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因而使得“劳动本体论”的说法较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假使我们将“劳动本体论”置换为“生产劳动本体论”则过于偏颇,写成“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本体论”又显得繁琐和冗余。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非常庞大和繁杂,这也使得他不能将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和劳动等相关的核心理论问题做出明确和精要的总结和概述,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极具探究性和研讨性的理论难题,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王成稼.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4(1):3-10.
[4] 谭华辙.有关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6(3) :15-27.
[5] 宁阳.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与现代服务经济发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4) :45-4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李锐.《资本论》创作史上的“历史路标”论析——关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若干理论问题解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11):96-10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张佑法)
Problems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Marx’s Economics-Philosophy Theories:Based on Analysis and Study of 1861—1863EconomicsManuscripts
LI Ru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In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such as 1861—1863EconomicsManuscripts,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have their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text. Productive labor is a direct residual value for the capitalist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s only for people who want living and spiritual service, so unproductive labor cannot increase the capitalists’ wealth. There is no insurmountable gap between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because human society is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In fact, with the changing of labor and consumers, many unproductive labors turn into productive labor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due to the practical need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s not limited to the Marx’s original text. The contents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are modified and enriched, and the range of them is more specific than before. All in all,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which in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philosophy enlarges and deepens Marxist theories of labor and Marxist Ontology, and it proves that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has permanent research value.
productive labor; unproductive labor; labor; surplus value; human society; capitalist society
2015-03-06 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文本研究”(12YJC710030)
李锐(1984—),男,河南焦作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李锐.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视阈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文本研究的分析与探讨[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9):68-74.
format:LI Rui.Problems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Marx’s Economics-Philosophy Theories: Based on Analysis and Study of 1861—1863EconomicsManuscript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9):68-74.
10.3969/j.issn.1674-8425(s).2015.09.013
A811
A
1674-8425(2015)09-006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