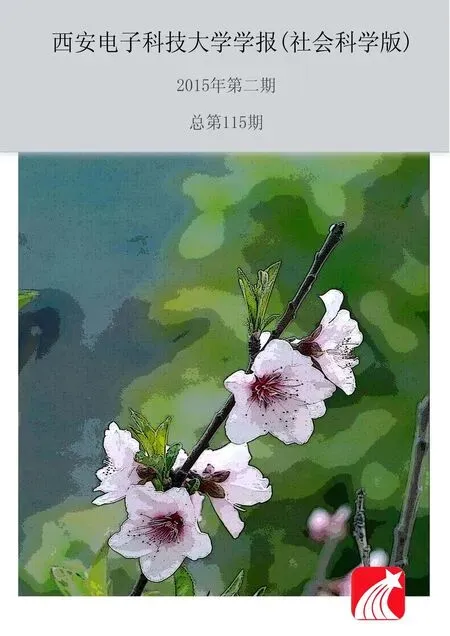李商隐与爱伦·坡诗歌中超自然描写之比较
唐臻娜
李商隐与爱伦·坡诗歌中超自然描写之比较
唐臻娜1,2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2.西安医学院英语系,陕西西安 710021)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中国唐诗的海外传播进程中,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广大读者与批评者的青睐。本文在中西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对李商隐与美国诗人爱伦·坡以他们诗歌中的超自然描写这一共通的文学现象为切入点,展开平行研究,以超自然描写的心理形成原因、特点、功用等诸方面为经,以中西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为纬,对二者的超自然描写进行深入探究,揭示出二者在超自然描写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对于寻求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美学本质,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均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与启示。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超自然;神话传说;浪漫主义
一、引言
晚唐诗人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不但备受中国读者与学者、批评家的关注,而且在中国唐诗的海外传播进程中,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了西方读者。将李商隐与西方作家进行平行研究,是国外李商隐研究的一大特色。美籍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先生将李商隐与波德莱尔进行比较,他认为“李商隐诗歌境界中出现的慵懒的美人,异域的香氛,奇异的药物,刺绣与宝石,音乐与舞蹈,都令人不由地想起波德莱尔”[1]。叶嘉莹在《旧诗新演》中对卡夫卡与李商隐的创作异同作了比较,认为两位作家都善于“把真实生活之体验揉入自己充满梦魇的心灵之幻想中”[2]。
然而,波德莱尔是法语作家,卡夫卡是德语作家,现代西方汉学的研究重镇却是英美国家。“随着世界政治文化版图的转移,英语世界的影响日趋扩大,西方的汉学研究逐步扩展到以英美为中心的地域展开”[3]。倘若将李商隐与英美国家的某位作家展开平行研究,对于促成李商隐诗歌艺术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广泛理解与接受、拓宽国内本土李商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均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李商隐与英语世界的某位作家展开平行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与某位作家放在一起比较,而是要建立在比较文学的学理基础之上。“单纯相同或单纯相异而无共同点的文学现象,是不具备这一比较基础的,只有那些同时具备相同与相异两重关系的文学现象,才具有比较的价值。它们应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在这种异同关系中体现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对比探求这种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间的异同,对寻找整个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美学本质,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4]。
那么,英语世界有没有一位同中国诗人李商隐同时具备相同与相异两重关系的作家呢?前文已述刘若愚先生认为李商隐与波德莱尔在创作上颇相似,关于波德莱尔与美国诗人、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比较研究论文已很多,我们可不可以绕过波德莱尔将李商隐与爱伦·坡作平行比较呢?再看国内本土对爱伦·坡的比较研究,吴宓曾将爱伦·坡与李贺作比较;李后兵的“简析李贺与埃德加·艾伦·坡的异同”分析了李贺和爱伦·坡在创作主题上的一致。既然认为爱伦·坡与李贺在创作上接近,而我们知道李贺又与李商隐诗歌有着诸多相似(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一书第五章“李贺的遗产”中对二者的文学承继关系有详细论述),笔者认为不妨可以将爱伦·坡与李商隐进行平行比较研究。设想一经产生,还需大量的研究来证实设想能否成立。笔者在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发现,这个设想是完全可行的。
尽管目前学界对李商隐与爱伦·坡的比较研究尚处空白,然而倘若我们重审李商隐短暂的一生与丰富的创作,会发现他在人生经历、创作精神上和爱伦·坡非常相似。综观李商隐与爱伦·坡,皆是年少失去至亲,生活凄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然而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均未曾让他们宏远的抱负实现,反而饱受磨难,命途多舛,他们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却又遥相呼应,在浩瀚的世界文学星空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青睐超自然描写,通过超自然描写使得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与浪漫主义的色彩。本文实质上是在前人的李商隐研究与爱伦·坡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与拓展,也是对二者分别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整合。
二、改造神话的东方诗人
李商隐诗作中超自然描写比比皆是,有超越时空的沧海桑田、飘渺玲珑的宫宇仙境,还有地下冥界的重逢、青女素娥的斗妍,“在《碧城》和《圣女寺》里,我们不仅看见爱的复杂的境界,而且看见幻想的境界。……有时虚假的超自然的境界用令人吃惊的力量撞击真实的境界”[5]。商隐的诗歌世界泗溢着夸张的想象、感伤的情调、华丽的用词、明艳的色彩,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而后来我们在爱伦·坡的诗歌中重逢类似的情形。
(一)游仙诗的巅峰
我们知道,超自然在信仰方面表现为相信存在上帝、鬼魂、灵魂,或其他超越人类感知的神灵,在文学上表现为他们的出场。如果我们将义山作品中的超自然描写按类型划分,便会发现天上神仙类的数量居多,而鬼魂、冥间类的较少,如“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异俗二首》)等。义山诗歌中的超自然描写多数是关乎神话传说的,有神仙人物故事诸如紫玉化烟、弄玉吹笙、穆王西游、嫦娥奔月、宓妃留枕等作为典故潜藏在诗句之后,嫦娥、麻姑、萼绿华、紫姑、西王母、巫山神女等这些神仙经李义山信手拈来,形象生动地出现在他的诗文中,成为义山诗文叙事中的一个角色,也有绮丽飘渺的仙境仙物的环境描写,例如碧城瑶池、阆苑女床、绛河云圃、蓬山青鸟、彩凤灵犀、碧牙床、白玉堂等。目前学界达成共识的是,义山诗歌中的这些神话传说与道教密不可分,道教幻想的神仙世界的意象体系(如:“沧海桑田传说”、“刘晨、阮肇传说”、“西王母传说”等)成为李商隐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李商隐早年有“学仙玉阳东”的经历,他的诗作《寄永道士》、《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等诗,都是他与道士来往赠还之作。“到了晚唐时代,唐王朝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现实政治没有出路,因而很多文人都在追求虚无缥缈的仙境,隐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游仙诗的发达与兴盛。这一时期道家思想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李贺与李商隐……”[6]。此外,道教的内丹学说、存思观念则为商隐的想象通向超自然境界搭建了天梯。商隐正是顺着道教内丹学说、存思观念的天梯,翩翩通向那无涯虚幻的超自然的境界,使他的作品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义山游仙诗的聪明高超之处有二,其一在于他不止步于运用神话传说,他还改造、演绎它们,使它们具有新的面貌与叙事抒情性,在诗歌的空间里获得延续自身的力量。这也正是义山超自然描写最突出的特点——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再创造再发挥,若无旷世的文学创新精神与想象力自是难以企及。正如叶嘉莹先生曾说:“李商隐不只是写神话的典故,而且他要把神话里的典故改造,这是李商隐自己的创造”[7]。
我们来看他的《霜月》: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南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淮南子》:“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是主司霜雪的女神,素娥就是嫦娥,月亮白色,故称素娥。在空明澄澈的世界里,皎洁的月宫里覆满了霜雪,青女与嫦娥两位美貌的仙女竟然相会,不畏寒冷,争奇斗妍,这是多么奇妙瑰丽的想象,多么得浪漫主义!传统神话中只说有靑女、嫦娥,却未曾教她们月中霜里相会,然而义山借用神话中的人物青女与嫦娥,自出机杼地创作出了崭新的情节与内容,延续了神话的魅力,使古老的神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得神话的叙事与诗歌的抒情令人惊奇地完美地融合,闪烁着中华民族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学智慧。倘若说古老的神话奔流在叙事的河谷,义山便是把它们引入了抒情的湖泊。
义山游仙诗的聪明高超之处其二在于揉入了爱情的主题,他笔下超自然描写的仙女并非清冷孤高、绝世独立,而是脉脉含情、温柔似水,其游仙诗作因而深情缱绻、摇曳生姿,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将游仙诗推上了至情至性的巅峰。李乃龙对此曾言,“在男权社会,拥有‘仙眷’成为男士一个心照不宣的愿望……对红颜永驻的仙女的共通倾慕,是全由男性组成的游仙诗作者群借仙述艳的一大内驱力……李商隐所爱之美、情爱之浓、结局之幻,都唯有一‘仙’字方可当之。其内容的深情绵邈和表达的婉转曲折,使李商隐的爱情游仙诗成为这类诗歌的极品”[8]。
“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9]。神话传说犹如一粒粒珍珠散落在李商隐诗作之中,是其超自然描写中最为耀眼最为成功之处,道教的存思观念与神话传说成为李商隐文学创作的根基,这位东方的浪漫主义诗人将游仙诗推上了文学高度至今无人可及的辉煌巅峰。
(二)多维度的感伤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表现出最显著的情感倾向是忧郁感伤,这是浪漫主义者与周围现实不协调的必然结果,反观中国古典诗歌长河,尽管流露伤感情绪的诗歌不计其数,然而李商隐诗歌的感伤情怀并非他某些篇什的情感流露,而是他全部诗歌所呈现出的显著艺术情感倾向与特征。对此,前人已有精辟的论述。如李商隐研究的著名学者刘学锴先生曾说,“对人生悲剧命运的深刻体认与深沉感伤,是义山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跟时代社会的悲剧,诗人自身的悲剧境遇、性格、心理密切相关”[10]。
笔者认为,深沉的感伤也是义山诗中超自然描写呈现出的情感色调。诗人一生仕途坎坷,羁旅愁苦,沦贱艰虞,晚唐政治的昏暗,民众的流离失所,家父的早逝、令狐绹的疑忌、爱妻的去世无不令其陷入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诗人自己就感叹道:“古来才命两相妨”,悲从中来,其笔下的超自然描写也弥漫着此种情感倾向。我们来看他的一首《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义山以离奇瑰丽的想象,塑造了一幅飘渺的仙境画卷:女仙欲饮云霞幻成的仙酒,却忽已成冰,女仙在此雪月交辉之夜,更居在那杳远难即的十二层瑶台之上!该诗言近旨远,抒发了理想之境高邈,纵然追求向往,然变幻莫测,终究永不可达,徒有空自长叹与怅惘的感伤之情。
义山可谓是中国诗人中去超自然境界探险飞得较高的一位,超自然描写总起来看抒发的是深沉的感伤悲哀的情调,感伤又是多维度的,伤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伤壮志难酬、皇帝昏庸;伤春悲秋、青春无返;伤爱情失落、相思磨人;伤友人含冤、天妒英才;伤百姓辛贱,贵族骄奢……多维度的感伤使李商隐诗作超自然描写在情感特征上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
(三)此岸与彼岸
李商隐十岁丧父,“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然而他的文学才华熠熠夺目,“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思想使他踏上求仕的征程,然而“名宦不进,坎坷终身”,“官不挂朝籍而死”,尽管李商隐早年有“学仙玉阳”的入道经历,然而他仍然是被儒家世界观所浸染、所武装的读书士子,摇摇欲坠的晚唐社会污浊昏暗的政治氛围使得心性高洁的他不满现实的肮脏和混乱,由此构成的强大张力驱使他去另一超自然的世界探索,释放自身的压抑与愤懑。“大多数诗人只是利用游仙主题,来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寻求精神的解脱和慰藉罢了……通过对虚幻世界的钦慕,表现对现实遭遇的不满,对人间社会的否定……中唐以后的诗人们更是借游仙诗的躯壳,浇铸现实的失意、无奈、愤懑”[11]。
义山的超自然描写星罗棋布于诗作之中,我们并不觉得超自然境界是陌生遥远的,超自然境界里的神仙有着和凡人一样的执着的追求——“姮娥捣药无时已”(《寄远》),也对民间的游戏乐此不疲——“玉女投壶未肯休”(《寄远》),也有着凡人的男女私情——“朝云暮雨长相接”(《楚宫》)……我们还可以在义山的超自然描写中觉察出其人间的原型,比如诗中常出现的“上帝”。《钧天》诗曰:“上帝钧天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冥”。再如《哭刘蕡》中的“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刘若愚先生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艺术精华》)中对此有深入肯綮的分析,笔者将原文译成中文,即“然而,有时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诗中的超自然描写实际上代表了现实世界的人。举例来说,李商隐在哀悼他遭到冤谪而死的朋友刘蕡时写下这样的诗句:‘上帝深宫闭九阍’。我们可以确定诗中的‘上帝’是指人间的天子——皇帝,原句表面上说天帝居住的地方有宫门九重,天帝深居其中,不知外界有冤情,实指唐朝皇帝难以接近,良臣蒙冤而不知晓”[12]。
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可居留,自然是不能直接抨击的,男女关系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是不能直抒胸臆的,义山诗中的超自然的彼岸正是现实的此岸的折射,藉此来抒写此岸世界不便明说的种种。“作梦或遇见本是日常的现实经验,却因神女的出现而转入超自然(非常)世界……一般文人则对凡男和神女之间的浪漫情愫特多好感,一再取作典故而拈为诗题,借以隐喻现实生活中不便明说的两性关系”[13]。
正是此岸世界的黑暗与不可居留驱动李商隐神游于光怪陆离超自然的彼岸世界,然而这彼岸与此岸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李商隐的超自然描写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社会,他是以超自然境界来写现实境界,依然回归到对此岸世界的关注,对世俗生活的叙述,他的人文关怀,依然是在此岸世界。
三、独钟幻境的西方诗人
李商隐之后又过了约十个世纪,也就是在19世纪的美国,一位伟大的文学人物出现了,他就是爱伦·坡。目前国内对坡的译介与研究主要集中他以死亡、凶杀、复仇为题材的小说上,对其诗歌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实坡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小说家,他在文坛上的初次亮相是他的一本名为《帖木耳及其他诗》(,1827)的诗集,这是坡正式问世的第一部作品。1845年,坡以《乌鸦》()一诗成为万人瞩目的文坛巨星。相形于国外学界对坡诗歌研究如火如荼的态势,国内坡诗歌的研究未免有些冷清。2008年在纽约出版的英文书《布鲁姆经典文学评论——埃德加·爱伦·坡卷》对坡的诗歌有较深入的研究,书中谈道:“尽管坡在今天以他的小说而更为人所知晓,然而他在他那个时代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乌鸦》在美国文学史上至今都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当它在1845年初次面世时就大获成功。坡的诗歌的新颖独创性与内在张力感染了大多数读者。其诗歌在韵律方面的独到之处使他跻身于19世纪伟大抒情诗人之列”[14]。
前文已述李商隐与爱伦·坡堪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中西双璧,下面就来详细论述坡作品中的超自然描写,与李商隐进行平行研究。
(一)奇异的世界
如同李商隐诗歌中超自然描写里有神话仙境、绰约仙女、地府亡灵一样,坡使希腊罗马神话驰骋在他的诗歌中,一个超自然的奇异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十四行诗——致科学》(1829)里,坡把科学描写成一只“兀鹰”,指责它把月亮女神“狄安娜拖下了马车,把山林仙子逐离了森林,让她去某颗幸运的星躲灾避祸,还从水中撵走水泽女神……”《以色拉费》(1831)描写了天使以色拉费美妙的歌声,天国里诸神听到歌声的反应,该诗中出场的普勒阿得斯(Pleiads)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诗末尾处梦想着将“我”与天使位置对调,“去以色拉费之处”,可以尽情地吟唱心灵的歌曲,这是多么奇异瑰丽的想象!而在李商隐诗歌中我们也常常见到人神相接、人入仙境的异乎寻常的情节,如“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海客》)。“《阿尔阿拉夫》(1829)的前29行描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的仙境,那里‘没有我们世界的浮沫沉渣——/有的全是美人,全都是鲜花’。在其后的诗节中,诗人表达了天国和人间共同存在的美好愿望,也就是两个世界的融合”[15]。《献给安妮》(1849)中tantalized一词的用典出自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坦塔勒斯(Tantalus)的命运,这一神话的引入使坡传神地表达了自己渴望爱情受到爱情的逗弄却无法得到的无奈与焦灼。
本文已述李商隐在他的游仙诗中溶入爱情主题,无独有偶,坡的超自然描写中也表现了爱情的炽热,不过坡对爱情的表达直抒胸臆、奔放大胆,而不似李商隐般曲折深婉、含蓄朦胧。比如《帖木儿》(1827)一诗以夸张的想象和天庭、人间、地狱的交错展示了爱情的甜美与权势和荣耀对人的诱惑——“哦,爱情!你给予人间以生气,给予我们希翼天堂赋予的东西!你浸入灵魂,润泽世人的心田,如春雨滋润被热风烤焦的平原……”[16]这真是典型的西方人对爱情直抒胸臆式地抒写,与西方社会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性的发展、个体的创造、个人的奋斗,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以及个人英雄和个人冒险”[17]。
李商隐与坡以中西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爱情相同的炽烈渴望与执着追求,游刃有余于超自然描写中,凡此种种使他们的作品都散发着浪漫主义的无穷魅力。
(二)单纯的感伤
忧郁感伤是浪漫主义作家的情感倾向。“在他(指爱伦·坡)看来,在所有最富有诗意的基调中,‘忧郁’或‘悲伤’是最适合的基调。因为任何形式,任何类型的美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都会使敏感的心灵兴奋得落泪......一位美丽妇人的死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论题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最合适的人选是亡者的恋人”[18]。美女的恋人哀悼她的死亡不正是笼罩着愁云惨雾的感伤吗?其实坡所热衷的美女死亡的主题恰恰正是中国悼亡诗的主题,“悼亡”在古汉语中就是指追悼正式配偶,在文学体裁上基本就是丈夫哀悼亡妻的诗作的代名词,爱伦·坡式的美女死亡主题不过是把中国悼亡诗里的“丈夫”扩大到“恋人”而已。中国的悼亡诗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名作不断,唐代的元稹、李商隐都有感人肺腑的悼亡诗作,由此又可见李商隐与爱伦·坡在文学上的灵犀与共。
美女死亡主题在坡的许多作品中可见,并且这一主题又常常通过天国、上帝、天使、恶神、地狱等超自然描写来使该主题表现得更具艺术感染力,同时,这些作品皆是弥漫着椎心泣血的感伤。譬如著名的《安娜贝尔·李》(,1849),该诗的场景凄清冷峻——远古的海滨,清辉的月夜,阴冷的墓穴,绵延的爱意,恶毒的天神,整首诗宛如一出凄婉的悲剧,音韵回环往复,任何时候读这首诗读者都仿佛能听见海涛拍打岸边的声音回荡在辽远孤寂的夜空里,像是忧伤的情人发出的对安娜贝尔·李的一声声悲戚的呼唤。《丽诺尔》(,1831)与《睡美人》(,1831)里也都流淌着对美人之死的悲伤。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基于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同是因死亡生发出的感伤,坡与李商隐还是有不同之处:虽然商隐早年学道,晚年入佛,但他骨子里却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厚,注重现世,死亡意味着永久的阻隔,故而李商隐的“伤”是决绝的、无望的、深刻悲观的,无法超脱的;而西方人受基督教的影响深远,基督教认为现世人生充满痛苦,只有在绝对永恒里灵魂才拥有幸福,而死亡能达到灵魂的永恒,故而坡在悲伤过后是以超脱平和的心态面对死亡,坡认为死亡是睡眠的一种形式,以这种形式升入天国,摆脱尘世的痛苦折磨,会受到上帝的照看,坡的这种死亡观在他的许多诗作中都有体现—— “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更是在悲伤中显示了一种超脱,一种幻想的乐观”[19]。
而且,坡超自然描写中的感伤情绪多是由美女之死引起的,爱情与死亡是生发坡的感伤的主源,相形于李商隐忧济苍生多维度的深广的感伤,自然就显得单纯些。
(三)、现实与幻境
“美女之死”主题与坡的现实经历密不可分。坡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美丽善良的女人都先后撒手人寰,令坡悲恸不已。
坡的生母伊丽莎白·阿诺德在坡三岁时因病逝世,是坡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美女之死”。“陪伴母亲在病榻前度过的时光或许是爱伦·坡终身挥之不去、难以忘却的阴影,那僵死的面容、深陷的脸颊、腐朽的气味和突兀的双眼不仅在爱伦·坡的作品中被一次次精雕细刻,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他身边的女性一遍遍重新上演”[20]。坡少年时玩伴鲍勃·斯塔那德的母亲简·斯蒂丝·斯塔那德夫人端庄美貌,坡不可抑止地爱上她,然而斯塔那德夫人于1824年即在坡15岁时病逝,在少年坡的心中留下了悲伤可想而知。1829年,曾给予了坡母性的温柔与爱的养母弗朗西丝溘然长逝。1842年,坡的娇妻弗吉尼亚确诊得了严重的肺病,每一次咳血都令坡痛不欲生,童年母亲口吐鲜血的惨状仿佛穿越时空袭来,促成坡的名作之一《红死魔的面具》(,1842)的诞生,超自然的红死魔游弋在金碧辉煌歌舞升平之中,“溅满了鲜血”,血淋淋的恐怖场景造成了强烈的视觉与情感的冲击。1847年,弗吉尼亚再次病发,撒手人寰。在同年的诗作《尤娜路姆——一首诗歌》(1847)以及稍后的《安娜贝尔·李》(,1849)中,可见坡对亡妻的缱绻深情。超自然描写镶嵌在这两首诗作中,令其熠熠生辉——希腊神话中灵魂的化身——仙女普赛克(Psyche)与“我”一同漫游在荒郊僻野,来到尤娜路姆的墓前;恶神嫉妒“我”与纯洁的美女安娜贝尔·李真挚的两情相悦,以她的死亡企图拆散“我们”,然而“我们”的灵魂却超越时空永远在一起......
前文已述李商隐诗中的超自然的彼岸正是现实的此岸的折射,坡作品中的超自然描写与此相类似。美女死亡主题源自坡亲身的经历,是坡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表现这一主题主要通过超自然描写来实现。坡许多诗歌中的“鲜花盛开,仙女起舞欢笑”、“天国里的绿洲”的美妙仙境正是饱受残酷现实折磨的坡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与憧憬,而那些“摧毁美好爱情的恶毒的天神”、“阴暗的死神”、“坠入海中的城堡”则暗喻了现实社会中嫉贤妒能、恶意陷害之人、以及社会的不公对天才的扼杀。
我们已经看到李商隐色彩斑斓的超自然描写受到道教“内丹”学说以及道教神仙意象体系的深刻影响,与此相平行的是,坡作品中超自然描写亦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西方基督教思想体系与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则是其“源头活水”。
基督教的教典《圣经》在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坡的诗歌《不安的山谷》(,1831)、《海中之城》(,1831)、《黄金国》(,1849)等都可以看到《圣经》的痕迹。美国2012年出版的英文版(《想象的中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坡在他作品中时常把死亡看作是进入天国乐园与神同在,这是基督教思想在他作品中的反映。在诗作《献给安妮》中,‘我’死后在所爱的女人南希·安妮·里奇蒙的怀中,好像到了天国乐园,坡描述乐园的词汇来自基督教的传统。安妮是‘天使的女王’,把她比喻成圣经中的圣母玛利亚”[21]。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出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然而在中国古代却有浪漫主义文学。上古神话传说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庄子的散文、屈原的辞赋张开想象的翅膀,描绘奇异瑰丽的事物,散发着浪漫主义的璀璨光华。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李商隐是继屈原之后又一卓越的浪漫主义诗人,李商隐怀有屈原“乘骐骥以驰骋”的浪漫主义思想,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具特色的一位诗人。
而在西方不仅出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而且浪漫主义的洪流绵延深阔,许多国家都有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家。正是浪漫主义这一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所共通的文学状态将中国的李商隐与美国的爱伦·坡联系起来,李商隐与爱伦·坡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的杠杆来撬动另一个世界(超自然世界)以此缓解现实社会的痛楚。他们二位的诗歌都飘洒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皆在超自然描写上浓墨重彩,倾向描写奇异的幻境、人神的相遇、缠绵的爱情、忧郁与悲伤,可谓时空相隔却遥相呼应。
笔者以浪漫主义为红线,将李商隐与爱伦·坡两位浪漫主义的中西诗歌双璧并联起来,进行平行研究,对于开辟李商隐研究新的空间与维度,加强李商隐与英语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消解民族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彼此陌生,研究探讨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美学本质,皆具有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1] JAMES J Y LIU.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Ninth Centry Baroque Chinese Poet[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251.
[2] 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6.
[3] 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136.
[4] 方汉文.比较文学原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68.
[5] 刘若愚.李商隐的诗境界——第9世纪巴洛克式的中国诗人[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9.
[6]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06.
[7] 叶嘉莹.叶嘉莹说中晚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2.
[8] 李乃龙.论唐代艳情游仙诗[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69-74.
[9] 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304-305.
[10]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56.
[11] 陈向春.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8-51.
[12] JAMES JY LIU.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M].Mass:Duxbury Press,1979:10.
[13] 李丰楙.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象[M].北京:中华书局,2010:58-81.
[14] HAROLD BLOOM.Bloom’s Classic Critical Views:Edgar Allan Poe[M].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8:113.
[15] 朱振武,王二磊.爱伦·坡诗歌的美学表征及诗学理念[J].外语教学,2011(5):66.
[16] (美)奎恩.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M].曹明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9.
[17]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
[18] 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上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26.
[19] 黄柏青.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1):69.
[20] 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4.
[21] JEFFREY J. FOLKS.Heartland of the Imagination : Conservative Valu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Poe to O’Connor to Haruf[M].North Carolina:McFarland&Company,Inc.Publishers,2012:65.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Supernatural Description in Poems of Li Shang-yin and Edgar Allan Poe
TANG ZHENNA1,2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oems in Tang dynasty, Li Shang-yin, a famous poet in Late-Tang dynasty, attracts heated attention from readers and cr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parallel research into Li Shang-yin and Edgar Allan Poe on the common ground of supernatural description. It elaborates on the mental caus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supernatural description in the two writers’ writings along with the analysi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explore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of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among both writers’ poems by the bridge of supernatural description, which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ursuing the common disciplines and aesthetic ess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adv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arallel Research; Supernatural; Myths and Legends; Romanticism
I0-03
A
1008-472X(2015)03-0110-07
2015-01-03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北美汉学界的中国唐代诗歌英语翻译与理论研究”(13JK0277)
唐臻娜(1978-),女,陕西汉中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西安医学院英语系讲师。
本文推荐专家:
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文艺学。
李西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论、文艺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