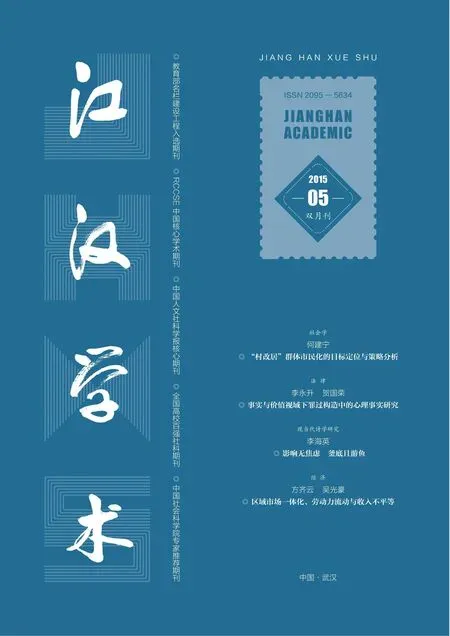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线逻辑——基于农村计划生育实践的分析
陈 恩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科研处,海口571100)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线逻辑——基于农村计划生育实践的分析
陈恩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科研处,海口571100)
摘要:在农村计划生育中,基层政府承担着出生控制和社会秩序双重矛盾的职责底线,而农民的生育底线牢不可破。基层政府的底线逻辑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所建立的单向责任模式。农民的生育底线植根于农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这些相互冲突的底线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农民通过抗拒结扎来坚守生育底线,并通过性别选择的妥协策略软化来自国家的规制压力;基层政府及其村庄代表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也遵循农民的生育底线,化解了出生控制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在三个底线之间的张力中,经过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农民互动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底线逻辑。各个主体遵循底线逻辑,使农村计划生育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国家的生育政策目标获得实现,社会秩序未受计划生育挑战,农民生育底线得到较好保持。通过农村计划生育案例,可以发现社会治理各主体必须坚守底线逻辑,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秩序。
关键词:农村计划生育;节育;人口控制;社会治理;底线
中图分类号:C923;C91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5-0011-0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往往坚持“不出事”的底线,但以往研究并不关注社会治理中其他主体的底线逻辑[1-2]。基层社会治理的底线逻辑在农村计划生育中体现得较为充分。以往农村计划生育被基层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国家生育政策面临着农民不服从的困境。国家对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进行限制以及为实现此目的而采取的绝育措施和惩罚手段,往往难于被农民接受。尤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农民抗拒比较常见[3-5]。以往研究用“生育意愿”、“生育文化”、“男孩偏好”等来解释农民抗拒的原因[6-9],但这些研究止于男孩偏好的表象,未能进一步揭示农民生育行为中某些不可突破的底线。比如,农民不生男孩不罢休;只生一个男孩的夫妇也坚决抗拒结扎绝育;基层政府一般不强迫未生男孩的农民夫妇绝育;村干部会极尽全力地保护未生男孩的村民逃避节育;上级政府强调要狠抓的纯女户结扎推行不下去等现象。有研究在讨论199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时曾试图指出农民生育的底线逻辑,如李建新将“两孩至少有一男”界定为农民的“极限生育空间”[10],陈震和陈俊杰将“生一个男孩”界定为“农民生育的文化边际性”、“农民在生育上难以逾越的文化边界”[11]。这两个富有启发的提法仍不能准确地表达农民生育男孩的底线特征。此外,以往研究也未指出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中所遵循的行动逻辑。基于此,本文将以“底线逻辑”来解释农民和基层政府在农村计划生育治理中的实践过程,并通过农村计划生育来讨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底线逻辑。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底线逻辑如何从冲突到妥协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本文以海南省H县北部沿海丘陵地区的一个行政村A村为例。该村人少地多,村民以从事菠萝等经济作物种植和对虾等海水养殖为主。A村下辖8个自然村,截至2009年底,家庭总户数为161户,合计733人。全村共有十几个姓氏,属于无主导姓
氏的杂姓村。本研究采取田野调查的访谈法和文献档案法收集资料。笔者对A村干部和普通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并获得该村自1979—2009年的全部计划生育对象的生育节育信息档案。
二、底线的张力:社会治理的难题
1.生育底线:计划生育中的农民逻辑
在农民看来,儿子既具有传宗接代的符号功能,也是养老送终的家庭福利保障。以往研究认为,中国人生育男孩的动机是传宗接代、养老保障、壮大家族势力、提供劳动力、感情需要、人生的终极目的、面子、期望孩子实现自己未竟的理想等[6]。传承香火是农民偏好男孩的观念基础。即使现实生活中女儿可能比儿子更加疼爱父母,农民还是担心年老时无子女在身边而出现生活照料缺失。农民不仅从老年照料的现实考虑去拼命生育男孩,整个村子的社会氛围也在逼迫农民必须生育男孩,在村里没有儿子的夫妇会遭到其他村民的歧视。“无后为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使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成为农民夫妇的生育底线。在1980年代及以前,农民家庭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多生儿子也是从干体力活的角度去考虑的。多生儿子可以壮大家庭势力,通常被村民作为家庭在村内的利益保护或者扩张途径。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前,村庄内部的资源归属等利益边界不清晰常引发村民之间的纠纷,儿子多的家庭在利益纠纷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势力单薄的家庭会遭到大家庭欺压——这些家族竞争因素在农村刺激了农民多生育男孩的愿望。男孩对农民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导致生育底线呈现刚性特征,因此农民在计划生育中遵循生育底线的实践逻辑,即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这是由农民的传统观念和现实利益所决定的。在婴幼儿死亡率较高的年代,农民倾向于通过多生育男孩来提高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的概率,以保证有儿子传承香火和养老送终。对此A村前村支书说:“从某方面说,只生一个男孩少了,想生两个,万一小孩得病或意外,还有一个,有这种想法。农村人都会这样想的。”特别是在1980年代及以前,孩子夭亡的现象还比较常见。当时A村很多农民的生育底线是防止“绝后”,因此采取生2个男孩的“双保险”策略。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男孩偏好传统即已存在,生育底线已存在于农村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安排中,农民一般通过多生育来实现生育底线。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国家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使农民的生育底线凸现,农民首先考虑的是“能否生儿子”,而非“能生几个孩子”。
A村多数农民生育男孩数量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分别为1—2个、1个、1个。从整体上看,农民的生育底线从2个男孩下降为1个男孩,并且止于1个男孩。在2000年之后,农民的生育数量随着生育意愿减弱而明显下降。A村农民的生育底线变为1个男孩,几乎没有人会为了生育2个男孩而抗拒强制绝育。在现代社会,孩子抚养费用攀升和追求生活质量的潮流转变了农民的生育观念。但是,1个男孩存活的生育底线仍然是农民的实践逻辑。丈夫出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的A村夫妇,平均生育男孩数分别为1. 38、1. 26、1. 12、1. 00个。生育1个男孩的夫妇比例从1980年代的63. 5%上升到2000年代的81%,生育2个男孩的夫妇比例则相应从31. 1%下降为9. 5%。在计划生育中,生育限制和强制绝育所施加的压力凸显了农民的生育底线。生育底线未遭突破说明了农民对生育男孩的有效坚持,也说明了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社会治理中较尊重农民的生育底线。
2.出生控制与社会秩序:基层政府的职责底线
承担多重职责的基层政府经常面临不同国家政策目标之间的张力。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社会秩序稳定和出生人口控制之间存在明显冲突。社会秩序可能遭到出生控制政策措施引起农民反抗的冲击;当出生控制任务成为基层政府的首要任务时,为此普遍采取的强制手段容易引起控制对象对社会秩序的可能冲击。然而,基层社会治理的底线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这又要求在出生控制过程中约束基层政府的强迫命令行为。因此,基层政府的职责底线是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出生控制指标,又要避免计划生育工作引发社会秩序不稳定,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国家的出生人口控制目标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层层分解给基层政府,并通过压力型体制传达任务目标的压力,特别是在1991年中央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之后,更强化了出生控制指标的刚性底线。出生人口控制及为其服务的四项手术等任务都以具体指标的形式下达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必须每年接受若干次严格的考核检查。在压力型体制下,保证指标完成并控制在上级允许的范围
之内成为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职责底线。
另一方面,社会秩序稳定也是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职责底线。承担出生控制刚性任务的基层政府在遇到坚守生育底线的农民抗拒时,易引发强迫命令行为。因此,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国家始终强调以“软”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主,但早期也没有明确提出要禁止“硬”的强迫命令。当上面对人口控制任务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时,强迫命令就少提或不提。在1983年的计划生育运动高潮中,基层政府也提出“坚持思想教育”,同时鼓励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①。1983年的全国性计划生育运动高潮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次年3月,中央要求基层政府必须“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强迫命令”[12]。随着生育高峰期的到来,完成任务的紧迫性再次得到强调。1986年起,对基层政府不再强调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一直延续到1995年“七不准”规定的出台。在1990年代后期,农村社会秩序不稳定使出生控制底线让位于社会秩序底线。1990年代末,国家多次要求基层政府在计生工作中避免粗暴行为,并在2000年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向群众公开宣传原来内部掌握的“七个不准”规定。“七个不准”禁令的公开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计生干部。2001年出台的《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地方计生条例明确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计划生育中的基层政府受到法律法规和禁令的约束,基层干部在计划生育执行中变得更加谨慎。这可以从基层政府对计生工作“老办法不能用”、“硬办法不敢用”等抱怨中得知。“和谐计生”作为“和谐社会”理念的延伸被提出来,“维稳”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显著增强了农村计划生育执行中对基层政府的约束。与“维稳”相配套的“和谐计生”实际上是将基层政府的社会秩序底线和出生控制底线相结合。2000年之后,在A村,基层政府在动员对象接受节育措施时几乎不用强迫命令,那些在1980年代、1990年代常见的“抓”、“关押”、暴力威胁等强制形式基本消失,转而依靠软的“思想工作”。
三、底线张力下的农民策略
1.坚守生育底线:抗拒绝育手术
生育限制政策和绝育手术对农民的生育底线构成严重挑战。1980年代相当多对象在结扎时已有2个男孩,结扎绝育不会突破农民的生育底线,也不会破坏农民抵抗男孩存活风险的能力,此时农民抗拒结扎多因“怕手术”。到了1990年代,那些抗拒结扎的对象是出于“只有一个男孩且孩子还小,担心结扎后男孩意外死亡”等原因抗拒结扎理由。结扎绝育冲击农民的生育底线、破坏农民抵御男孩存活风险的能力,农民抗拒结扎的理由由“怕手术”转为“抗风险”。A村一个生了2个女孩、1个男孩的妇女回忆自己在1993年做结扎时对生育底线的担忧:“只生一个男孩就叫去做结扎,晚上哭了一整晚。只生一个儿子太少了。”这种想法在2000年之前的A村很常见。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是农民的生育底线,结扎绝育使农民丧失了男孩存活风险发生后再生育的能力。当国家收紧生育政策,很多对象在生育了1个男孩后被要求结扎,使多数农民不能实现两个男孩“双保险”底线。纯女户结扎遭到普遍强烈的抵制表明,不突破生育底线是农民最低限度接受计划生育的临界点。农民抗拒结扎不是为了多生育,而是为了保持男孩存活风险发生后再生育的能力。结扎破坏了农民在唯一男孩夭亡后再生育的能力,从而威胁到农民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的生育底线。2000年之后,农村的婚姻关系不稳定变得较为常见,A村开始出现出于防止婚姻变故,有的妇女抗拒结扎的现象,这种抗拒依据也是建立在生育底线的基础上,即妇女改嫁后的再生育能力。
结扎之所以引起农民的抗拒,是因为它突破或者潜在突破农民的生育底线。保护生育底线和保持生育能力从而应对唯一男孩夭亡的低概率事件,是农民抗拒结扎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生育底线是农民抗拒结扎的逻辑依据。即使不愿意再生育,对象也不愿意接受结扎绝育,保持生育能力是有效维护生育底线的途径。所以,当另一种代替结扎的长效避孕方法可供选择后,农民纷纷选择可逆的避孕方法。在“合同押金免扎”推行之后,村干部一般不会通知对象逃避,也说明之前结扎手术因为会突破农民的生育底线而遭抗拒。
2.性别选择:农民的妥协策略
当国家的生育限制政策收紧,结扎作为绝育手段被推行后,农民很难抗拒基层政府的结扎要求。于是,农民会选择一种在基层政府的职责底线与生育底线之间平衡的做法,既接受计划生育政策(生育限制、结扎绝育),又保持至少1个男孩的生育底
线。胎儿性别选择是农民在计划生育限制之下实现生育底线的主要途径。农民的胎儿性别选择具有坚实的价值基础。中国农民没有把溺死亲生子女看作谋杀,在传统上并不把一周岁以下的婴儿当作完全的“人”。溺婴自秦代以来在法律上就是非法的,但是在道德上并未禁止;当时溺婴既是非法的,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流产在中国既合法,也受到鼓励[13]。B超技术应用之前,农民选择性别主要是通过溺弃或送养女婴等形式实现的。但是,在A村的农民看来,溺弃女婴是伤天害理的。在A村,没有听说溺弃女婴的故事。在B超技术推广之后,鉴定胎儿性别后堕胎成为农民进行性别选择的主要方法。1990年代初,B超的广泛应用使私下鉴定胎儿性别成为当地农民选择胎儿性别、达到生育底线的首选。在A村,前两胎都生了女儿的妇女在怀孕第3胎时都会去做B超鉴定胎儿性别,如果鉴定为女孩的,堕胎成为农民选择性别的普遍办法。1993年,A村一个生了2个女孩的妇女在丈夫妹妹的帮助下去海口做了胎儿性别鉴定:
如果生了,那是三个女孩了,人家(政府)哪还会让你生第四胎呢。……那时候决定了,如果是女孩就做掉,专门去看(检查),不敢留下来生。……那时候要是连续生两个女孩的,都会去检查的,去做B超,去看是什么(性别),哪敢留下来生。……他(医生)一说是男孩,我就高兴坏了,要是女孩,我就得做掉。
这个妇女在生了2个女孩之后通过做B超鉴定胎儿性别来缓解生育底线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冲突,实际也缓解了基层政府出生控制底线的任务压力。结扎威胁了农民至少有1个男孩的生育底线,一方面连续生育多个女孩,多次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会面临着来自基层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对象不愿意通过多生育来实现至少生育1个男孩的目的,所以选择胎儿性别。2000年以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妇女在怀第二胎时一般会去做胎儿性别鉴定。虽然结扎威胁了农民至少有1个男孩的生育底线,但是从结果上看,在A村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妇女多数接受了结扎绝育手术。但是这种结扎还在农民容忍的范围之内——农民通过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引产手术达到了至少有1个男孩的生育底线,强制结扎并未直接威胁其生育底线。从结果上判断,结扎并未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说明强制结扎没有突破农民的生育底线;而基层政府的出生控制底线和社会秩序底线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
四、坚守底线: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
基层政府要在社会秩序与出生控制之间寻找平衡,也必须尊重农民生育底线。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充分考虑农民的生育底线②,但是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断地强化对农民生育底线的保护。在制度安排上,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中所制定的具体实施细则充分体现了对生育底线的考虑。对纯女户结扎的暧昧态度,基层政府最多会采取利诱的办法试图说服纯女户接受结扎绝育,不会动用强制手段在这些纯女户身上,尤其不会强制纯女户结扎绝育。对于节育手术禁忌症对象,基层政府最初为限制其超生而发明了“合同押金免扎”的办法,但很快被广泛应用于不愿意结扎的对象。这避免农民对绝育之后绝后的担忧,并基本上形成一个有效规则——只生1个男孩的妇女可以合同免扎,但是有2个男孩的妇女必须结扎绝育。在制定超生惩罚措施时也体现出对生育底线的尊重。1987年,A村所在H县的超生处罚规定,“2女户抢生第三胎罚款200元,1男1女户抢生第三胎罚款400元,2男户抢生第三胎罚款600元”。这种对同样超生第三胎的对象进行不同标准的处罚体现了生育底线的逻辑,即达到生育底线的多孩超生重罚,未实现生育底线的多孩超生轻罚。即使后来的国家规定统一了超生处罚标准,但是基层政府在执行中仍遵循生育底线的逻辑。对于农民担心结扎绝育之后出现生育底线突破的意外,1990年代初基层政府开始提供生育能力再造的复通手术保障。从基层政府保护农民生育底线的制度安排上,可以看出生育底线在计划生育中具有不可突破性。
“人心从人心出”的乡土社会生育伦理几乎为所有农村社会阶层所接受。生育伦理为保护生育底线可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农村社会的国家代理人和作为计生对象的农民在保卫生育底线上形成了“共谋”关系。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村干部,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使村干部们感到“斧子打柴,柴打柴”,而作为村落共同体成员的村干部则强调“人心从人心出”。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村干部同时面临着这两种矛盾的心态。村干部作为村庄社区成员必须遵守村落的生育伦理和生育底线的行动逻辑,为未生育男孩的村民提供庇护。即使上级施
加的任务压力再大,村干部也绝对不会做让村民“断子绝孙”的“缺德事”。村干部在计划生育中会为那些未到达生育底线的对象通风报信、隐瞒、说情等。A村当时仅有的3个纯女户对象在原村支书的极力保护下躲避结扎,最后都生了1个男孩。在2000年之后,县聘的村计生信息员或镇计生专干往往会上门暗示那些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对象再次怀孕时去做胎儿性别鉴定,以免第二胎再生女孩而出现多孩超生。村里的国家代理人根据不突破当年考核指标的治理底线原则安排那些没有男孩的双女户再生育。A村信息员说,“纯女户要想生,也得由村里安排生,今年这个生,明年那个生”。这种有计划地安排超生是一方面避免本村的出生率突破镇计生办当年下达给A村的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遵循了农民的生育底线逻辑。乡镇干部甚至县下派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干部也会对为未实现生育底线的农民抱以同情,对那些未生男孩的纯女户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从未发生过强迫纯女户结扎绝育的事情。在村民看来,干部保护未生育男孩的夫妇规避计划生育管制是理所当然的。基层国家权力代表的有效庇护使农民的生育底线得以维持,也使得基层政府与农民在计划生育上的冲突缓和。
五、底线逻辑下的社会治理效果
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是基层政府的职责底线和农民的生育底线都未遭到破坏,而且国家的政策目标得到贯彻。自2000年之后,A村计划生育已经“上轨道”、“成规例”,这一方面说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已经规范化;另一方面表明,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农民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结婚—生育—结扎成为农村妇女生命周期不可逾越的环节,结扎被植入农村妇女生命周期,现在正变成农民自觉履行的生命仪式。A村未曾因计划生育而出现社会秩序不稳定事件,而基层政府的出生控制指标基本完成,农民的生育底线得以保全。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多孩超生的夫妇比例逐步降低,违反计生政策的比例越来越小。早期农民一般通过多孩超生(生育三孩及以上)来实现生育底线。根据表1,在A村,丈夫出生于1950年代的夫妇多孩超生的比例高达68. 7%,而丈夫出生于1960年代的夫妇多孩超生比例降为48. 7%,丈夫出生于1970年代、1980年代的夫妇多孩超生比例越来越低。丈夫出生于1970年代的夫妇只有7. 1%多孩超生,丈夫出生于1980年代的夫妇无人违反计生政策。虽然多孩超生逐渐消失,但农民的至少1个男孩存活的生育底线一直存在。丈夫出生于1960、1970、1980年代的夫妇未实现至少1个男孩生育底线的比例分别只有5. 4%、7. 1%、9. 5%③。

表1 丈夫出生于不同年代的A村夫妇接受计划生育政策比例(%)
为有效控制计划外生育,国家在农村实行“一环二扎”节育模式,农村妇女对避孕方法没有选择的余地,生育数量达到政策规定上限以后必须接受结扎绝育。绝育意味着对象丧失生育能力,结扎绝育威胁或潜在地威胁着农民的生育底线。在政策许可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下,如果不进行胎儿性别选择,至少生1个男孩的生育底线不一定能实现。即使生育了1个男孩,根据二孩结扎的规定进行绝育,绝育之后发生的男孩存活风险估计也促使农民对结扎手术产生抗拒。农民接受结扎绝育时已生育男孩数是农民的生育底线。在A村,只生1个男孩的对象接受结扎绝育(含男扎)的比例为70. 3%,生育2个男孩的对象接受绝育手术的比例为88. 9%,而没有生育男孩的纯女户结扎只有4例。与生育1个男孩相比,生育2个男孩的农民更可能接受绝育手术。在A村,1950—1980年代出生的妇女结扎时生育1个男孩和生育2个男孩的比例分别为80%和100%、81%和95. 8%、78%和83. 3%、22. 2%和50%。可见,生育2个男孩的妇女接受绝育的比例高于只生1个男孩的妇女。A村70. 6%的已婚育龄妇女接受了女扎绝育手术。在1950—198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接受女扎绝育手术的比例分别为90. 0%、86. 8%、78. 2%、18. 5%。2000年之后基层政府广泛采取“合同押金免扎”的变通做法,特别是2008年开始兑现“知情选择”的法定权利,妇女可以在“上吉妮环”和
“女扎”之间选择,结扎在1980、199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比例更低。
综上所述,基层政府的出生控制任务完成越来越好,多孩超生比例越来越少,2000年之后多孩超生基本消失,并且未曾出现因计生工作导致农民挑战社会秩序的现象。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农民夫妇都实现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的生育底线。各个社会治理主体的底线目标在计划生育中都得到体现,表明农村计划生育是成功的社会治理。现代社会治理是建立在法治、协商民主基础上的,法治基础上的权利保护、基层政府和对象之间协商使农村妇女在多种避孕节育技术中相对自主地选择,较圆满地解决了基层政府的出生控制职责和农民的生育底线之间冲突。
六、结语
底线是不可突破的最后防线,底线生成是为了保护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秩序,主体所嵌入的自然、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等共同作用形成一种维持社会平衡的底线机制。作为自我保护机制的底线被突破意味着主体关系秩序的溃败和社会治理的失败。基层政府的底线逻辑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所建立的单向责任模式。
在农村计划生育这个社会治理领域,基层政府与农民围绕着生育底线、出生控制和社会秩序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基层政府代表国家实施出生控制政策,并受到上级政府的监控;上级政府根据出生控制目标制定的各种任务指标成为基层政府治理绩效考核的内容。在中国压力型体制下,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成为基层政府的职责底线,出生控制在1990年之后以“一票否决制”来表达其底线地位,因此出生控制的职责底线可能会促使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而实施各种办法规制农民的生育行为。而农民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至少有1个男孩存活的生育底线受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引发保护生育底线的反应式抵抗行为,潜在地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基层政府还承担着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职责底线,因此迫使基层政府在执行出生控制政策过程中要尽量不触犯农民的生育底线。正是各方互相坚守底线逻辑的社会治理,农村计划生育才能最终形成和谐的关系秩序。
基层政府的变通做法常常被认为是对上级政府的执行不力,特别是基层政府为了顺利开展社会治理而采取隐瞒上级和农民的做法时。假设基层政府直接按照上级决策向农民传导压力,完全不考虑农民生育底线,则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正是基层政府的变通才使上级政府的决策得以在农村社会落实,出生控制底线和社会秩序底线都能得到保证,而农民的生育底线也得到了保护。
在由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法治、民主协商、权利保护、多元选择等原则都是基于对社会治理中各个主体底线逻辑的考虑。农村计划生育的底线逻辑折射出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的方向。现代社会治理具有多元参与主体,国家、市场、社会都有各自的底线。在其他领域的社会治理中,各种治理主体都存在不可突破的底线,这些底线可能存在相互冲突之处,但是只要遵循底线逻辑,社会治理可以实现共赢的局面。
注释:
①中共H县委书记许秀令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县人民动员起来切实搞好第二次计划生育行动高潮》(1983年9月19日);中共H县委书记《李永光同志在县计划生育行动高潮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83年6月6日)。
②部分地区农村实行“1.5孩”(即规定第一胎生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二胎;第一胎生育男孩的,不能生育第二胎)生育政策考虑农民的男孩偏好,但是仍未达到对生育底线保护的程度。
③丈夫出生于1980年代的夫妇还有继续生育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钟伟军.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分析框架[J].浙江社会科学,2011(9).
[2]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J].学术研究,2010(6).
[3]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M].北京:三联书店,2001:72-80.
[4]闵长鹏.“天下第一难”何难之有?[J].社会,1992(4).
[5]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M].北京:三联书店,2002:194-204.
[6]王文卿,潘绥铭.男孩偏好的再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5(6).
[7]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1-69.
[8]莫丽霞.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偏好研究[J].人口研究,2005(2).
[9]李树茁,马科斯·费尔德曼.中国农村男孩偏好文化的传播和演化:背景与主要研究结果[J].人口与经济,1999(S1).
[10]李建新.生育空间与生育政策挤压[J].人口学刊,1996 (4).
[11]陈震,陈俊杰.农民生育的文化边际性[J].人口研究,1997(6).
[12]全国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号召继续大力抓好计划生育工作[N].人民日报,1984-03-08.
[13]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M].北京:三联书店,2000:85.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hengxiaoyan1023 @ hotmail. com)
Bottom Line Logic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Planning in Rural Areas
CHEN En
(Scientific Research Office,CPC Hai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Haikou 571100,China)
Abstract:In rural family planning,grassroots governments bear the bottom line of dual responsibilities of birth control and social order,while farmers’growth bottom line is unbreakabl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bottom line logic is rooted in the unilateral liability model built by pressurized system. Farmers’growth bottom line is rooted in rur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re is a strong tension between the three bottom lines. Farmers evade ligation to stick to their bottom line and through the compromise strategy of gender selection to soften the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the stat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also follow the bottom line of farmers in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 to relieve the tension between birth control and social order.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ssroots governments,village cadres and farmers,the bottom line logic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formed. Since all subjects follow the bottom line logic,rural family planning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the fertility national policy goals are achieved,the social order were not challenged by family planning,farmers’bottom line growth is maintained. Through the case of rural family planning,we can find out that all the subjects of social governance must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logic,or the harmonious order can not be formed.
Keywords:rural family planning;birth control;population control;social governance;the bottom line
作者简介:陈恩,男,海南万宁人,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科研处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15 - 06 - 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