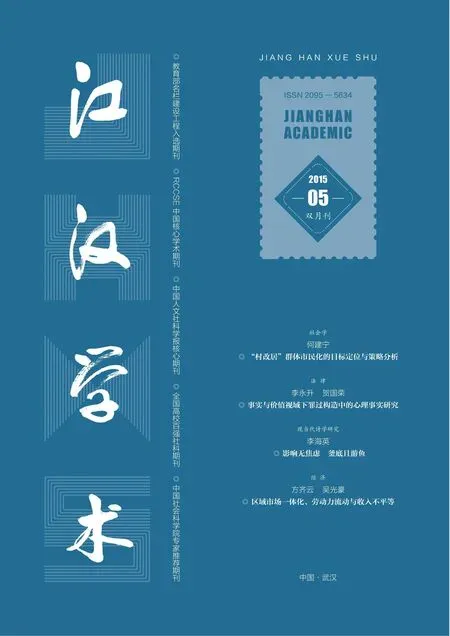黄昏里的行走与歌唱——从骆一禾的《大黄昏》看其诗学理想
林 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黄昏里的行走与歌唱——从骆一禾的《大黄昏》看其诗学理想
林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在骆一禾众多的诗歌作品中,《大黄昏》一诗不容忽视。于1984年4月创作的《大黄昏》一诗,不仅是第一首直接以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意象——“黄昏”来命名的诗歌,更是从文明视野俯瞰华夏文明的发展,饱含诗人深刻的文明思考和忧患意识,展现了骆一禾关于“文明黄昏”的思考,以及其对诗人形象与使命的期许和寄寓。骆一禾以独特的意象群构筑了其诗歌王国,自成一体,相互映照,使其诗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解性和对话性。《大黄昏》一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骆一禾早期作品的微缩和集合。此外,这首诗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为我们进入骆一禾的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更是因为这首诗凝聚了其重要的诗学观念。《大黄昏》在强烈的生命感受之中展现了对“燃烧”的强调和对“修远”的暗示,使其在文明意识之中也包含着骆一禾本人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和期待。
关键词:当代诗歌;诗学观念;骆一禾;《大黄昏》;黄昏
中图分类号:I207. 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5-0081-08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生于1961年的骆一禾,自1979年进入大学时开始诗歌创作,在其近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大体上保持了两三天便创作一首诗的高频状态,留下了短诗二百四十来首,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①,以及重要诗论多篇。诗人陈东东曾将海子与骆一禾并提,认为海子是一个不为任何一个时代歌唱、却竭力歌唱“永恒”和“生命”的歌唱者,而将骆一禾视为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1]。近些年,相较于海子研究的热潮,关于骆一禾的研究却处于相对冷清的状态。但正如姜涛所言:“长期以来,骆一禾也主要是作为海子作品的整理者、阐释者以及‘海子神话’的缔造者而被后人铭记的,他本人非凡的诗歌成就和诗学思考,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2]事实上,作为倾听者的骆一禾,也是一位歌唱“生命”和“朝霞”的歌唱者。骆一禾诗歌中所包含的高远的文明视野和强有力的生命跃动,及所构筑的具有一定完整性和自足性的诗歌意象群,值得重视和深思。这在他的代表性诗作《大黄昏》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有一种情绪黄昏般出现”
《大黄昏》一诗创作于1984年4月,后被整合入长诗《世界的血》中。也许是“那拾穗者/移动在黄昏里的背影/成了我的美感”(《平原》)所带给诗人的深深的触动和心灵的震撼,也许是“我有一种情绪/黄昏般出现/使我怆然泣下拒绝任何理由”(《四月》)的神启和执着,“黄昏”成为骆一禾诗作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不同于古典诗歌中的“日西愁立到黄昏”,骆一禾对黄昏的执着早已超越了往往与“黄昏”意象相联系的对时间易逝的感伤和惆怅。作为特殊的意象存在,“黄昏”不仅饱含了骆一禾个人的生命情感体验,更是他在文明视野俯瞰下的独特诗歌景观,与其诗学观念息息相关。
西渡称骆一禾是“鲁迅以来少数几个以文明为背景来考虑自身文学事业和文化使命的中国作家”[3]。在骆一禾的诗歌考虑中,诗歌问题始终和文明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他对文明问题的关注和思索,不仅仅停留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之下,
更是在其中,镕铸了属于骆一禾个人的独特的“朝霞气质”[3]。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致终结”[4],“20世纪的中国和西方都处于文化生命周期的最后文明阶段,一个心灵萎缩、创造力消失、拜物教的没落、解体、死亡的阶段”[5]。不同于斯宾格勒的文明终结论,汤因比亲子相继的文明再生理论则认为解体并不是结束和死亡,而是一种新文明的孕育和肇始。尽管汤因比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然而在其早期的文明思考中,对华夏文明的未来前景却持犹疑态度,看不到新文明的曙光。虽然骆一禾认同西方先哲对文明解体现状的认定,但是由其内在的“朝霞气质”,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在汤因比的观点上进行了生发,认为华夏文明尽管处于第三代文明的末端,但同时也包含了第四代文明的曙光:“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6]作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的生命个体,诗人骆一禾经历了从文明视野俯视华夏文明,并承认文明解体的现状的忧虑和痛苦。华夏文明解体所带来的强烈的飘零和悲凉之感,给予一个有着沉重责任意识和雄伟抱负的个体以生命之不能承受之重。而他的诗歌构想也建立在这样的文明认识之上,因此,“他要求从‘诗’的原初意义上恢复诗歌创造、创始、行动的力量,唤醒民族记忆,并以此对华夏文明进行结构性的改造,最终重塑我们的文明和民族性”[3]。
1984年,骆一禾在《滔滔北中国》第二部分的“孤独”之题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黄昏里/总有什么在死去。”西渡说:“骆一禾属于那些对国家和民族复兴寄予了最热烈希望的人们,也是最早从这新生之梦中醒觉的人。”[3]20世纪80年代初,诗人骆一禾感触到了斯宾格勒观念中文明解体的微妙状态:心灵萎缩、创造力消失、拜物教的没落。他不仅在对黄昏的感触中注入了对时间的观察和考量,而且在其中发现了某种契合。在骆一禾笔下,“黄昏”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成为了“第三代文明末端”的象征,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大背景和情感底蕴。
不同于此前诗作中出现的“黄昏”意象,1984年4月创作的这首《大黄昏》不仅是其第一首直接以“黄昏”命名的诗篇,更从此开创了以黄昏为主导意象、取代早期诗歌中以“清晨”为象征性和背景性意象的局面,“黄昏”给予人的心灵压力陡然上升,并成为生命运行的基调和背景。作为较早期的诗作,《大黄昏》包含了骆一禾对黄昏的原初感受,在这种黄昏感受中也饱含了诗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哲思。整首诗通读下来,是一副黄昏色调下的巨幅画卷的展现以及宛如流水的玄思。后来骆一禾将其整合溶入《世界的血》中,不仅体现了此诗对他的重大意义,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文明与使命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作为全诗抒情主人公“我”,实际上是一个隐含着的披戴着朝圣意味的行者形象,这个行者形象与《河的传说》中“背起布袋”的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对背起布袋的人/穿涉沼泽的时刻里/力是生命唯一的定义”(《河的传说》)。这个“背起布袋的行者”形象在其诗作中反复出现,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和寄托:
而我也穿过沼泽地
背负着原来的
空空的长布袋
(骆一禾:《青春激荡》)
但我们自海岸出发
涉过海床深处的沼泽
背负着空而且长长的布袋
为把海岸对波浪的情义
连成一体
(骆一禾:《告白》)
“背起布袋的行者”形象里寄寓着骆一禾对诗人形象的自我期许,而《大黄昏》中的“我”同样也担负着这样的自我期许。
全诗在广阔寂寥的探求道路上展开,包含了体现“行动”、“道路”、“生命”等深意的意象群,共同舞之,形成了一种“生命的律动”。此外,由于某些诗歌意象在其诗作中的高频使用,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诗歌意象群,这就使得骆一禾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互解性和对话性。他所建筑起的诗歌国度不仅自成一体,而且以农耕意象为根基,以道路主题为律动,众多生机勃勃的植物性意象和具有精神指向的动物性意象,在“水”系意象的滋养和渗透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和魅力。最初作为单独创作的《大黄昏》,后来进入长诗《世界的血》中,两次诗歌生命的唤醒和跳动,以及转换于短长诗之中和
整体与部分之中所带来的跨度和张力,为我们走进骆一禾的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理解其宏大的诗歌构想进行了预热。
二、“这黄昏把我的忧伤磨得有些灿烂了”
《大黄昏》共分为八节,总体上展现了诗人关于“文明黄昏”的思考,以及对行动的力的强调,同时显示了骆一禾对诗人形象的期许。前三节展现了一系列的农耕意象,农耕意象是骆一禾诗作中最为典型的意象群,它们构筑了其诗歌田园的基础面貌,并成为其诗作的基本元素之一,例如:平原、土地、麦地、玉米、葡萄、耕牛、马等等。诗人不仅在这些农耕意象中寄寓了生命的活力、生存的哲思、生命历程的把握,同时渗入了其对文明历程的思考,以及对道路的坚持和希望。
诗的开篇,即将读者的视野拉入广袤的平原:
走了很久很久
平原比想象更遥远
骆一禾在他的另一首诗《土地》中这样写道:“土地是没有声音的时间/人长不出/脱离它飞去的翅膀。”作为典型的农耕意象,“平原”不仅是土地的一部分,也承载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意义,人们在平原上耕种,付出劳动,也迎来收获;既要遵守自然的规律,也要克服和对抗不可预料的灾祸。世世代代的人类都在这与生存紧密相关的平原上繁衍和不断发展。因此,“平原”也成为了人们行走、奋斗的道路的象征。“比想象更遥远”喻示着人类文明历程的悠久和无尽。以抽象的动词“想象”来形容平原的无穷尽,将“道路”历程的广阔性拉伸到了极致。任何一个实体都无法超越“想象”的界限,个体生命在文明历程中始终处于行走的状态并无法出离其中。
接下来,“河”的意象开始出现:
河水沾湿了红马儿的嘴唇
青麦子地里
飘着露水
失传的歌子还没有唱起来
在骆一禾的诗作中,与“水”相关的意象较多,如“河流”、“血”、“雪”等,这些意象都与生命力紧密相关。如:“雪在春天/痛楚地酿成了/坚持不懈的生命/具有了/被白天和黑夜承认的/极地的弧光”(《河的旷观》);“作为世代的见证和希望/我们组成了大地的河/我们是蓝色星球的播种者”(《河的传说》)。此处不仅展现了黄昏下的自然图景,并且将动态的红马和河流与静态的青麦子地巧妙结合起来,其中暗含深意。“河水”往往象征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也作为哺育生命的源流,在骆一禾的诗作中不仅作为生命力的象征而存在,同时喻示着人类百折不回的生命历程。人类的发展如同河水的奔流,道路的曲直也亦如河道:“我们在那里流散/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哼唱着河道谱下的迈进的歌。”(《河的传说》)
而这几句诗中的“马”的意涵,则与骆一禾的道路主题相联系,他的《修远》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是道路/使血流充沛了万马”。“马”的意象在其诗作中通常与“道路”、“行动”、“牺牲”这些关键词相联系,并隐喻生命。“麦地”则可谓是骆一禾诗作中最为典型的农耕意象,他十分强调麦子的精神性,麦地记录了生命个体的所为和所获“我收过的几道麦茬/就是我一生的脚印”(《麦地(一)》)。对这首诗而言,麦地是生存景象的展现,它隐喻着千千万万的生命个体在文明历程中的生存状态,联系着家园意识。“青”色则寓意着生命历程正当发展之中,有着勃勃生机,等待耕耘和劳动,强调了过程,而对于收获与否还处于未知的状态。“失传的歌子还没有唱起来”则暗示了文明的断代现象依旧在持续。整体上,这几行诗在静谧、辽远的自然图景中释放了生命、文明的韵味,展现了博大的生存景观。个体生命走在曲折有限的生命历程之中,同时走在广阔无尽的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在一片饱含生机的的生存图景之中,精神上的文明断代还在持续。
在随后的诗句“只有我的果树林/还在簸扬着/春天的苦味”中,“果树林”是一个表现骆一禾爱情主题的词,较为集中地出现在较早期的诗作之中,如《给我的姑娘》(1983):“我亲爱的/果树林一样清新的/水一样给人纯洁和生命的/果树林/大地/是属于你的”;《爱的河》(1983):“果树林/你怀中的河要向哪里去/我的爱情/永远没有路/我只能沿河流淌/让空气成为我的母亲/你成为我的爱人”,等等。以“爱”为出发点的这一节,在复杂的情绪中透露了春天所蕴含的希望。由于对生命的热爱,对文明进程的关注,即使身处“第三代
文明末端”,面临“文明解体”的境况,也依然对未来抱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只有”一词,和“簸扬”的“苦味”,将“我”复杂的心理过程展现无余,生命个体在苦楚的思想精神境地中既饱受煎熬和重压,又不断地以乐观的精神自我抚慰,为自己树立精神支柱。
以上两节诗的情景,可以与骆一禾于1985年所写的诗论《春天》相对应:“对黄昏易逝的感受包含着人对时间的觉察,是生之春天的感受,活力的衰退概与时间的敏感的丧失共在,将茬口朝向春天,以苦色的香气触动黄昏——太阳西沉,面前散布着大片的土,大片的水,石头和树木,这些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就如此直观地呈现于眼前——能这样感受,处身心于鲜活的恐惧之中,教之玄思者苍雄的推理,更为深沉。”[7]这一段表述,几乎可以视为《大黄昏》一诗的基调解读。
到了第三节,这种感受得到进一步深化,突出对“行动”和“力”的强调:
弥漫江岸的水凇
还在结成白茫茫的树挂
在此,“水凇”象征着生命历程中的艰难和阻碍。象征着个体生命的树,在“水凇”的包裹下得到了定格:
在这些树木的年轮里
刻着一个春耕的人
没有光泽的寂静的低洼地
“春耕”是对行动的隐喻,是农耕意象群中有力的一部分,与树木生长的年轮类似的,成为生命发展的标志,并促使其不断壮大的正是行动的力量。即使被孤独团团笼罩,处于“没有光泽的寂静的”文明黄昏,处于曲折的道路之中,行动的力始终是现代文明生生不息的本质。
从第四节开始,诗的视角由人类生命历程、文明发展的高远视野转换到个体感受的视角。诗的后五节以隐含的行者形象为抒情主人公“我”,表达了在文明黄昏下,先觉者的切身体验和复杂情绪:
哦黄昏抵在胸口上
积雪在长风里
衰落着光
一个“抵”字,将其在文明黄昏和易逝之感中所深切感受的沉重心理压力表现了出来。集合了人类智慧、勇气的行者,在无际无尽的“平原”上孤独地行走,孤独是其所处的环境,也是其保持前进的动力。先于常人的醒觉,让其深感文明黄昏的重压和自身的使命:
我的心在深渊里沉重地上升着
好像一只
太大的鸟儿
骆一禾诗作中出现的动物性意象相对与植物性意象来说较少,并且比较集中,例如“鸟”、“野鹿”、“灰鹤”、“豹”等。不同于一般诗作中对“鸟”的轻盈和跃动的描绘,骆一禾笔下的“鸟”的意象常常处于困苦沉重的书写环境之中,“一如大鸟跌落/匍匐在地上泥土溅满双眼”(《沉思》)。整体上来看,这一节诗作是对文明黄昏下独行的醒觉者的切身体验的描绘,而这一部分,让我们不禁可联系其同作于1984年的诗作《大地》:“只有巨大的黄昏把我冲上山顶/巨大的黄昏/把我的心灵的火山震撼/我变得非常沉重……然后/你热爱黄昏吧/想象扑动一只翅膀/如受了重伤的鸟儿挣扎着/写下一句诗。”将心比喻成一只“太大的鸟儿”,以此来表现沉重的,饱含紧张扑动的“我的心”,被黄昏震撼,心的跳动如同鸟扑动的翅膀。
接下来的两节中,引入了抒情对象的第二人称“你”,呈现出一种对话关系,是醒觉者对人类的关切:
在哪里呵?
滚滚的黄昏
你在哪儿?
《大黄昏》暗藏着一种问题意识,这首诗被收录在《世界的血》的第三章中,第三章“缘生生命”中的六歌都呼应了“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乎存在的问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黑夜与白日过渡阶段的黄昏,包裹了各种复杂的情绪:充实的收获的喜悦或是空虚的无获的失落,归家的急切或是漂泊的茫然,黄昏这样一个时间段给予了人们
自省和思考空间。这是一个既夹带着疲惫又即将休整的时间,也是一个对末路者而言的茫然时刻。在一片茫茫的文明黄昏之中,同时处于文明的断代之中,作为生命个体的“你”和“我”既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将去向何方,发出了“在哪里呵”的疑问,这里人称的转换,使得这种困惑之境所围困的对象不仅仅只是醒觉者,而是面向了所有处于大黄昏之下的华夏人民。
随后的一节诗则将语调转变,从沉重、困窘的状态中抽离,对黄昏之景表示欣赏:
沉重的风雨和水纹
已经积满了平原
人类赖以生存的平原,行走并繁盛精神麦地的平原,生存的道路、人类生命的历程和精神文明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已打上了无数风雨的印记:
平原上就该有这样平坦的黄昏呵
一下一下撞你的心
每一步都踏在灵魂上
在经历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倍感文明黄昏的伤痛之后,转向积极与乐观。人类发展需要经历这样的文明黄昏,让黄昏震撼无数醒觉者的心灵火山,使行走更有意义。背负着使命的行走,“每一步都踏在灵魂上”,既不是轻轻地“走过”,也不是有力地“踩过”,而是稳稳地“踏”在了灵魂上。“踏”上的不是路,而是“灵魂”这样一个极其抽象的对象,其中所包含的使命感和神圣感陡然倍增。
紧接着的诗句,仍然着眼于黄昏与“我”的关系:
这黄昏把我的忧伤
磨得有些灿烂了
“磨”字将先行者“我”面对文明黄昏的复杂情绪和艰难的心理转变过程表现了出来;而“灿烂”则体现了一种积极的,饱含希望与期许的意味。西渡称:“骆一禾的诗歌行动既是一种醒目的晴夜之前的落日之舞,同时又沛然赋有分明的朝霞性质。”[3]应该充分体会骆一禾诗作中的这种朝霞气质,即其诗作中所体现出的希望,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在《大黄昏》中,便体现了这种朝霞气质:
这黄昏
为女儿们
铺下一条绿石子的河
“女儿们”是其诗作中具有较高频率的意象,它既代指了人类的繁衍生息,也蕴含了生命生生不息的顽强。“绿石子”从属于道路主题之下,石头作为组成道路的部分,既有顽强之意,也代指了道路。“河”则与之前出现的一样,喻示着百折不回的生命历程。“绿石子的河”这个意象十分精妙,将喻示道路的石子和喻示生命历程的河流相结合,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感官效果,获得一种力的动感和冲击,同时意味深远。文明黄昏不仅仅只是将人们笼罩于茫然、恐惧之中,更是借黄昏的悲怆和沉重来延续更为艰实有力的灵魂之路和文明发展史。
这节里接下来有一句十分醒目:“这黄昏让我们烧着了。”此句中的“我们”,是指与先行者一样在黄昏里醒觉过来的人,包含了骆一禾本人对诗人形象的一个自我期待。“燃烧”是骆一禾诗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他在《美神》中这样说道:“我想申说一下‘燃烧’,它意味着头脑的原则与生命的整体,思维与存在之间分裂的解脱,凝结为‘一团火焰,一团情愫,一团不能忘怀的痛惜’。”[8]燃烧使语言转化为诗,“燃烧”在其诗中更是打通生命全体,使其汇通,融化孤独坚冰的力量,诗是“生命的自明”,而“燃烧”便是实现“生命自明”的方式:
红月亮
流着太阳的血
红月亮把山顶举起来
这里的“红月亮”也可视为骆一禾对诗人形象的隐喻,它勾连着上文中的“我们”,“血”是骆一禾诗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哪一首血写的诗歌不是热血自焚”(《世界的血》)。骆一禾认为“诗歌写作时‘生命律动的损耗’,诗人靠血管中的血来写作的”,“每写一次,就在燃烧一次自己”。在其诗作中,血的外流则意味着爱与牺牲和价值的实现。“太阳”喻指光明与恢弘,“山顶”则代表了沉重、重压。在文明黄昏中,诗人对诗人形象和使命做出了构想,担负起重责和压力,燃尽生命的血,创造出能带
来希望、光明的诗作来解救“黄昏之境”,这也与其宏大的大诗歌构想相呼应:“骆一禾希望创造一种类似希伯来和古希腊的体系性的史诗,为文明复兴提供一个具有吸附力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构架,一个孕育新生命的蛹体。”[3]他在《水上的弦子》中这样描述:“我感受吾人正生活于大黄昏之中,所做的乃是红月亮流着太阳的血,是春之五月的血……一面是巨大的死,一面是弱者的生,美从拇指姑娘长成维纳斯,唯赖心的挣展,舍此别无他途,母性巨大的阵痛产出仅一六斤婴儿,生之规律大概都是这样的。”[9]可见,其对行动的力量的重视,这行动既指广义上的生命个体,也喻指诗人自身的自我期许和使命。
诗的最后一节,再次出现了“河流”:
而那些
洁白坚硬的河流上
飘洒着绿色的五月
这一节以清晰的画面透露了春之五月的希望与热情,和对生命历程的坚持和稳步前行。“绿色的五月”在色彩上与前面的金黄、红色这两个暖色调形成对照。整首诗正是在“红”与“绿”的色调的强力冲击下,织就了黄昏的弥漫之景,富有张力。
总体上看,全诗形成了有序的生命律动,饱含着骆一禾高远视角下的文明哲思,及其所持的诗是“生命的自明”的诗学观念。对“燃烧”的强调和“生命律动的损耗”的坚持,使得诗作中散发出的对诗歌创作的虔诚和敬意,极具感染力,令人震撼和感动。在看似隐晦、跳跃的意象之中,涌动着辽远的生命思索和希望之光。
三、“一个孕育新生命的蛹体”
《大黄昏》一诗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由于它为我们进入骆一禾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使我们能够触摸其诗作中的典型意象群的概貌,领略其诗歌王国的风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而独特,几乎可视为骆一禾诗学观念的一个微缩。《大黄昏》不仅饱含了他诗作中普遍具有的强烈生命感受,而且囊括了一些诗人对诗歌本身的思考,其中尤其体现了一种对诗歌的期待和寄寓。
正如西渡所言:“骆一禾始终是一个生命的热情讴歌者。”[10]在骆一禾看来,诗歌是生命的象征。他在诗论《春天》中这样写道:“以智力驾驭性灵,割舍时间而入于空间,直达空而坚硬的永恒,其结果是使诗成为哲学的象征而非生命的象征。”[7]将“生命”与“诗歌”对应起来,“生命”成为理解骆一禾诗歌和其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荣格将文学创作活动的内驱动力归结为源于集体无意识的自主情结:“创作冲动从艺术家得到滋养,就像一棵树从它赖以汲取养料的土壤中得到滋养一样。因此,我们最好把创作过程看成是一种扎根在人心中的有生命的东西。在分析心理学的语言中,这种有生命的东西就叫做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它是心理中分裂了的一部分,在意识的统治集团之外过着自己的生活。”[11]与荣格观点既有所相似又截然不同,骆一禾将艺术创作的内驱力归结为一种非艺术家本身的存在,但这种内驱力却不是集体无意识,而是生命。生命成为诗歌创作的内驱动力,因此,他用“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来概括他所讨论的诗歌创作论。骆一禾认为:“生命作为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8]他所论及的“生命”并非生命个体,“个体生命只是生命进程的一个次点”[8],而是指由无数个体生命实体构成的,包含了过去、未来和现在的生命历程。骆一禾的诗歌创作论则紧紧围绕“生命”展开,在他看来,诗歌创作是一种“燃烧”,“它意味着头脑的原则与生命整体,思维与存在之间分裂的解脱”[8]。诗歌创作的真髓在于“身心合一”,诗歌的欣赏则应是个体生命与艺术的直接汇通,实现艺术思维的发挥而非艺术原则的生搬硬套。
骆一禾对于生命原初感受的强调,使我们不难理解其诗作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生命感受。与此同时,不难发现,他的这种以“生命”为核心的诗学观念与其深重的文明意识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文明解体现象带给诗人骆一禾的是一种被他称为“人之无常”的“伟大的核心的恐惧”。他认为这种恐惧与“我们最基本的情感,我们整个基本状态,形成共同的原型”[8],而这种“原型”则是诗歌创作中所不应该回避的。与荣格所强调的原型不同,骆一禾所说的“原型”并不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和形式,而是一种更加具体的实在。他所指的“原型”指的是面临文明解体所产生的危机意识与人类基本情感和基本状态的融合。通过对“原型”的触动和感知而形成的创作,饱含了生命意识的律动。因此,骆一
禾所看重的并不是玩弄意象拼贴而获取某种技巧高度的诗歌,而是诗人直面“原型”,并在其驱动下所创作出的诗歌,这种诗歌所包含的意象序列具有整体的律动。
20世纪文明解体现象给予诗人骆一禾“生命易逝”的感受,使其更注重对“生命”的强调,同时,他也从“生命”本身探寻到了精神的出路。正如“生命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在这个不朽与长生的运动里,生命开辟创造,一去不返,迅暂不可即离,刹生刹灭,新新顿起,不断使生命燃亮精神,也就是使语流成为生命”[8]。文明解体所带来的也不会是文明的终结,“时代的建筑物是建筑在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的,除去个体之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真正死去过:红蜂在死前预先把卵子产生在螟蛉身上;一个文明在解体前,往往有一个外部的战群来占领它造成一个亚种。”[8]在骆一禾看来,诗歌创作不仅要融汇于生命,实现生命自明,形成意象序列的整体律动,同时也要使精神世界通明净化。骆一禾认为内心是一个世界而非一个角落,如果任由自我中心主义发展,内心空间的挤压会使得诗歌意象自身的势能受到压制,从而形成琐碎的拼贴。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对意象序列本身张力的保护。“万物自有光明”,语言不应成为压制意象的枷锁,而应使语词展现出自身的表现力,缺乏艺术造型的词符本身是没有魔力的,但出于生命内驱力而将其置于一定的文本语境中,则会使它的魔力得以显现出来。在诗歌创作中,骆一禾所看重的并非是艺术规则和艺术手法的运用,而是“生命自明”。
骆一禾曾说:“当我写诗的活动淹没了我的时候,我是个艺术家,一旦这个动作停止,我便完全地不是。”[8]骆一禾的这个观点与荣格对艺术家与艺术创作之间关系的辨析十分相似。荣格认为:“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11]但是不同于荣格过分注重集体无意识对艺术家的掌控,而将艺术家个人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作用抹杀。尽管骆一禾在其诗歌创作观念中十分强调“生命”作为诗歌创作核心内驱力的观点,但在其诗学观念中,诗人不仅发挥着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强调诗人所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与20世纪文明解体现象息息相关,无论是受80年代整体洋溢的理想主义激情氛围的影响,还是他自身文明观念的驱使,骆一禾在诗作中所展现的诗歌理想与抱负,“都显示了某种逾越20世纪80年代诗歌框架的努力”[12]。在文明黄昏的心理负荷下,骆一禾所希望创造出的是“一种具有一种类似希伯来和古希腊的体系性的史诗,为文明复兴提供一个具有吸附力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构架,一个孕育新生命的蛹体。”[3]与他的这种诗歌理想紧密联系的则是其诗学观念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修远”。
“修远”代表了一种具有崇高理想的诗歌精神,是骆一禾对自身诗歌理想和诗人使命的提炼。“修远”与其在文明意识下的诗歌构想紧密相关。正如论者张桃洲所言:“‘修远’一词的确体现了一种担当,试图回归屈原那样的诗人的高贵形象,但也可以说是对诗歌本身那种繁复的、复杂的技艺的追寻。”[12]骆一禾在诗作《修远》中这样写道:
修远。我以此迎接太阳
持着诗,那个人和睡眠,那阵暴雨
有一条道路在肝脏里震颤
那血做的诗人站在这里这路上
长眠不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骆一禾诗作中反复出现的“背着长长的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行者形象,几乎可视为他对诗人形象的一个比拟。尽管《大黄昏》一诗并未出现这样的行者,却俨然是这样的行者在黄昏背景下的低吟。在骆一禾看来,诗是生命的象征,诗歌创作则是生命的燃烧,诗作所凝聚的不仅是火光的温度,更有血的浓度。“带有灵性敏悟的诗歌创作,是一个比较易说得无以复加的宣言更加缓慢的运作,在天分的一闪铸成律动浑然的艺术整体的过程中,它与整个精神质地有一种命定般的血色,创作是在一种比设想更艰巨的缓慢的速度中进行的。”[8]诗歌创作是一种有浓度的创作,这种浓度并不单纯指物理时间上的长短,也包含了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内心的心理压强。相比于智性的哲思,骆一禾所强调的是根源自生命本体的血色搏动。面对文明解体现象,“修远”本身所担负的神圣感与使命感都陡然上升。从骆一禾的诗论不难发现,无论是其对“原型”的强调,还是批驳当时“自我与孤独”两大母题充斥在新诗中的现象,骆一禾所强调的是诗歌所应担负的文化
责任和整体性的文化功能。正如诗中所言:“红月亮/流着太阳的血/红月亮把山顶举起来”。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骆一禾的那种气象是对诗歌的一种期待,但是他没有把它外在化,他在诗歌里面试图包容而不是把它压碎,用它填充诗歌,而是以诗歌自身包容这些东西——文化的、历史的东西”[12]。《大黄昏》一诗饱含了诗人骆一禾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对宏大的“大诗歌”构想的向往所体现出的真诚和热情,让人真切地感受了“我在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深远意味。这个为华夏文明解体而忧虑痛苦,又对之抱以希望和深沉之爱的青年诗人,洋溢着青春激荡的热情和“黄昏时分/心灵的门向内旋转/我沉重地悸动”的思考,这个沉思“要背向你的前人/还要背向你的后人”,“以我的惊涛/站立在大地上/并以惊涛思想”(《沉思》)的青年诗人,尽管“我不知命运的突然/不知死亡怎样来临”(《头》),却也毫无畏惧,认定自己激荡的青春:“我不爱死不畏死也不言说死/我不歌颂死/只因为我是青春”(《生命》)。命运将骆一禾的生命定格于28岁的青春,然而他的诗歌精神和他诗作中所涌动的生命律动却将始终如春天:“这里坚硬/而/温暖”(《春天(一)》)。
注释:
①文中引用的骆一禾诗作均出自张玞主编的《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悼海子、骆一禾[J].上海文学,1989(9).
[2]姜涛.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重读骆一禾的诗论[M]//新诗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7.
[3]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04.
[5]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册[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张玞.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J].倾向,1990 (2).
[7]骆一禾.春天[M]//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8]骆一禾.美神[M]//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9]骆一禾.水上的弦子[M]//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0]西渡.灵魂的构造——骆一禾、海子诗歌时间主题与死亡主题比较研究[J].江汉学术,2013(5).
[11]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2]姜涛,等.困境、语境及其他——新诗精神的重建[M]//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 126. com)
作者简介:林琳,女,湖北应城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5 - 05 - 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