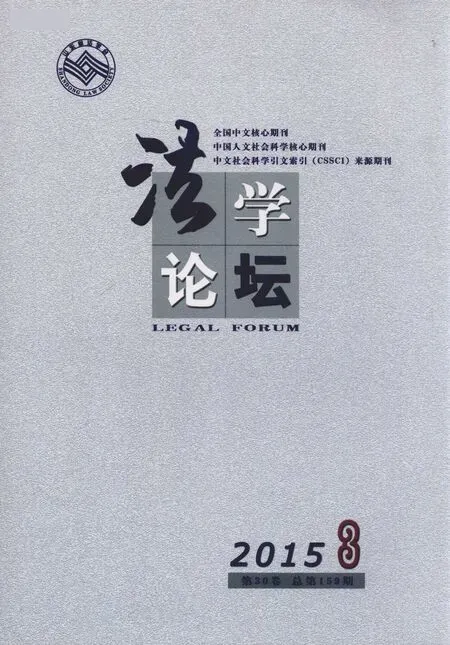法家的解放──以《劝学篇》引发的论争为中心
程燎原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在传统中国,自秦汉迄至清代,许多学者和士大夫都痛恨和诅骂法家之学,甚至视其为必欲摒弃的异端学说。这一传统,仍在晚清得以延续。宋恕在1895至1896年期间就写道:余虽“不屏法家之书”,但却“痛恨法家之学”。“余生平痛恶法家之学而深好名家之学,束发即然,年长尤甚。”①宋恕:《六字课斋津谈》,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89页。他并严厉指责汉儒(叔孙通、董仲舒)以及宋、明一些儒家(程伊川、朱熹等)的思想,不外乎阳儒阴法之学。他们“认法作儒”,即“阳尊儒术,而阴仇之,伪儒奴法,舞乱经义”,实为“认贼作子”,所以“著书十余万言以力攻阳儒阴法之学”。②参见宋恕:《外舅夫子瑞安孙止庵先生八十寿诗序》,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6页;宋恕:《致冈鹿门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6页。下文论及的张之洞,亦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不过,晚清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时局,包括社会政治的危机、西学的东渐以及整个诸子学的兴盛,却使得法家受到不少人士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晚清形成了一股重估法家价值以及对法家给予正面评价的强劲潮流,从而让法家学说迎来了渐次复兴的空前盛况。这无疑掀开了中国“法家学史”崭新的一页。而真正掀动这一页的一个重大契机,就是1898─1899年主要围绕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以下简称《宗经》)③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19-9721页。本文所引该篇文字,均见此书,不再一一注明。评论法家所引发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方面反映出法家仍然遭遇严重的抑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近代以来法家“解放”历程的开启。
一、“破道”的法家:张之洞等对法家的贬斥
众所周知,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批评守旧者的同时,重点旨在反击当时兴起的维新思潮与变政主张。按其《〈劝学篇〉序》的说法,甲午战败,全国上下震惊戒惧,“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尤其是“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故此,他出于护儒教、卫道统的目的,奋而对其所认定的杂学邪说予以尖锐的抨击。其中,《宗经》就是极力尊崇儒家经义的一篇重要文字。守住圣学之道,才是最重要的儒家事业。《宗经》篇的主旨,即在于此。为了大力扬儒教、颂圣学,该篇又着重贬抑诸子之学,包括法家之学。反诸子之学,其本身就是“宗经”。正如张之洞自己所揭示的那样:“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不听,必折衷于圣也。”①参见张之洞:《〈劝学篇〉序》,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9705页。其《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亦指出:读诸子,当“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29页。)所谓“破道”,即指诸子攻击、毁誉、损害圣门的经义道术与政教纲常。而诸子之学是否“破道”,必须根据儒家圣教或者六经之义来衡断。若诸子之学不“破道”,则可节取之;否则,就“不听(不听信、不采纳)”。
在张之洞看来,法家显然是“破道”之学。《宗经》一开篇就强调:“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他虽然指出先秦诸子亦有“中理之言”,可以“补经义”、“应世变”,其精华“皆圣学之所有也”。所以,“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鍼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②张之洞是主张学子、士人读点诸子的。他在1875年指出:“读书宜多读古书。……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包括《管子》、《商子》、《韩非子》等书。这是因为,“读子为通经。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不仅如此,“至其义理虽不免编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参见《语学第二》,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86─9792页。)他又指出:“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周秦诸子第一》中,所列法家著作善本有《管子尹知章注》二十四卷、洪颐煊《管子义证》八卷、严可均校辑《慎子》一卷(附《逸文》)、严可均辑《商子》五卷、吴鼒校刻本《韩非子》二十卷(附《识误》三卷)等。(参见《书目问答》卷三“子部”,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03─9904页。)但这往往是“虚语”,他要着重指明的“实言”是,先秦诸子“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不合于圣学大道,成为张之洞所言“九流之病”的核心,也是先秦诸子“破道”的主要表征。而这“九流之病”,都是“圣学之所黜”的。对于“九流之病”,张之洞进一步作了分析。他认为,除了“驳杂”之外,最重要的是九流“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法家当然也有此类祸患与病症,对此,他一一指出:(1)《管子》说:“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这有悖于儒家的民本思想。(2)“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3)“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任人、不务德。”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还认为:“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非孔门之政也。”③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24页。(4)“商鞅横暴,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这些指控虽然简略,但却一并将管、申、商、韩之学予以摒绝斥逐了。
从上述先秦诸子亦有“中理之言”的判断来看,张之洞并非全盘否定先秦诸子之学,也并非全然抛离法家。然而,在1895至1898年间,孔门圣教纲常的际遇,显然不是“腹背受敌”一语可以形容的,而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危险态势。面对这一态势,护教心切的张之洞,力图凭借《劝学篇》一书,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所以容不得他稍加宽贷,只能对包括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痛下狠手。第一,社会政治危机对儒家所维护的政治秩序构成严重威胁。“1895年以后,不仅外患内乱均有显著的升高,威胁着国家的存亡,同时,中国传统的基本政治社会结构也开始解体。这方面最显著的危机当然是传统政治秩序在转型时代由动摇而崩溃,这个在中国维持数千年的政治秩序一旦瓦解,使得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上失去重心和方向,自然产生思想上极大的混乱与虚脫。”④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而这正是张之洞为之焦虑和紧张的最根本的危机。第二,在思想学术上,逐渐传播的民主、民权、平等学说,对于“三纲”之学或孔门的纲常名教造成重大的挑战。第三,康、梁等人的维新改革,不再局限于先前的行政层面的变法,特别是其张民权、立宪法、开议院等主张,直接冲击传统皇权政治制度的核心之所在。第四,张之洞注意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由此开始重估法家之学。如梁启超多次倡导研习先秦诸子。他在《读书分月课程》(1892年)“最初应读之书”中,包括了“子学书”,列有《韩非子·显学篇》和《管子》。《上南皮张尚书书》(1896年)也主张借取诸子之学,以重视政治学术,即“以六经诸子为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之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年)更断言:“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①参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9、86页。另可参见《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万本草堂小学学记》(1897年):“正经正史,先秦诸子,西来群学”,都应读研,以求致用。(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章太炎1897年9月17日在《实学报》(第3册)上发表《儒法》一文,极力赞颂管仲、申、商以法术治国,驳斥儒者谓法家“言杂伯,恶足与语治”的论调,认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该文还表彰子产、诸葛亮并非不同于法家的治术,并“诵祝冀为其后世”。②章太炎:《儒法第四》,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湖南学政使徐仁铸1898年所撰的《輶轩今语》也认为:“诸子之学可与《六经》相辅而行”。只有诸子之学与孔子之教合而观之,“然后圣人之全体大用乃见”。而且,“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对于法家,他提出可先读《管子》,次读《韩非子》、《商君书》。③参见叶吏部(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载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6页。而张之洞认为,诸子之学渐兴,也威胁到孔门圣学。所以《宗经》篇最后指出:诸子之学,“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总之,张之洞深觉甲午战败激发的变法思潮、维新主张与诸子之学,将会毁坏圣门的道统、治统和学统,必须汲汲于鞭挞诸子之学包括法家之言,以拯救圣道纲常、护卫圣学根本。
《劝学篇》批法家、护圣道的心志与言说,并不孤立。在《劝学篇》刊行之前的1896年秋,康有为多次批判法家残暴、刻薄和反对礼教。他在《古今学术源流》中说:“刻薄一派,申、韩之徒也,其与儒教异处,在仁与暴,私与公。……刻薄一派,即刑也,流毒至今日,重君权、薄民命,以法绳人,故泰西言中国最残暴。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也;商君次之;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法家以刑为本,过于刻薄,出于道家。”④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7页。其《万木草堂口说》也指出:“商鞅非《诗》、《书》、《礼》、《乐》、孝弟、贞廉等语,谬甚”。⑤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谭嗣同在《仁学》(1896─1897)一书中同样痛斥申、韩的残刻。⑥谭嗣同说:“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页。)而在《劝学篇》甫一完成,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就在1898年6月呈奏说:“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当经奏请湖北督臣张之洞纂有《劝学篇》,持论切实平允,尚无流弊,……拟请饬谕将原书发交各省学政刊刻,交士子阅看,似于学术人心不无禆益。”而光绪帝“详加披览”后,对黄绍箕的评价和建议深表赞同,谕云:《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禆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⑦参见《光绪戊戌校经庐本〈劝学篇〉载奏折、上谕》,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58-10759页。由此,《劝学篇》一时称盛。此外,1898年9月刊行的《冀教丛编》一书,不仅收录了《劝学篇》中的五篇论文,而且称赞该书是“挽澜作柱”的宏篇巨制,亦附和、声援张之洞对法家的攻击。例如,叶德辉说:“诸子之学,间有可以治国者,大抵杂霸之主,偏隅割据之世耳。”⑧叶吏部:《〈輶轩今语〉评》,载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他针对梁启超所说先秦诸子“实皆本于六经”的观点,指斥道:“如韩非、如李斯,虽本于圣门弟子之传,其背经而驰也实甚,只得云离于六经,讵得云本于六经?”他还特别针对梁启超关于先秦诸子如同孔教一样各传其教的言论指出:“尸子之传为商鞅,惨刻无人理;……其人本无可取,其法尤不可用,谓其传教与孔子同”,实为一大谬误。⑨叶吏部:《〈读西学书法〉书后》,载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28页。叶德辉对法家的这些抨击,与张之洞前后呼应、一脉相承,似乎坐实了法家“破道”的形象与名声。
二、法家之善:章太炎等对法家的辨白
谭嗣同、康有为尤其是《劝学篇》对法家的指斥,立即引起了章太炎、何启、胡礼垣等人的反击和驳难。
章太炎与张之洞之间的纠葛,已自有其渊源。《宗经》批评法家,并告戒“好学诸君子”必须警惕法家的流弊,未尝没有针对章太炎《儒法》一文的意味。而章太炎对《劝学篇》内篇,亦有不满。据冯自由所记载:1898年春,章太炎应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的聘请赴鄂。“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也许《宗经》的一句商鞅“无足论矣”,就令章太炎觉得必须对商鞅宏扬一番,以抒发对商鞅的欣赏、赞许之情,并表达对张之洞的“不怿”。不久,章太炎即撰《商鞅》(1898年8月,收入1900年《訄书》初刻本时编为《商鞅第三十五》),批驳张之洞等人士的种种“淫说”(是非乖乱的邪说),奋力为商鞅辨白。②章太炎:《商鞅第三十五》,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2页。以下引用该篇文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对于《商鞅》与《宗经》的关系,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徐复认为:《商鞅》一文指出“谗诽”商鞅的言论,“今世为尤甚”,即是指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如张之洞《劝学篇》:“商鞅横暴,尽废孝悌仁义。”③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注[2]。至于《商鞅》一文也附带针对康有为、谭嗣同而发,章太炎亦有说明:该文末尾有一段“附识”,内中指出:“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所说“自谓近于维新”者,当指康有为、谭嗣同而非张之洞。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康有为、谭嗣同也的确对法家多有批评。因此,徐复先生认为《商鞅》一文同时反驳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显然是持之有据的判断。
1899年春,深受西学教育且身居香港的何启、胡礼垣,发表了《〈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的《劝学篇》内、外各篇分别予以辩驳。他们指出:《劝学篇》“二篇之作,张公自言,规时势,综本末,以告中国人士。其志足嘉,诚今日大吏中之矫矫者矣。独惜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故而“不得不辩,且不得不详辩者,诚欲为中国保其国”。④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序”),载《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页。何、胡二人的重点,在于力攻《劝学篇》内篇。其中,《宗经篇辩》为诸子九流特别是管子的言行进行了辩护。⑤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宗经篇辩》,载《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367页。以下引用该篇文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章太炎与何启、胡礼垣为法家所作的辨白,重在阐扬法家之善。他们并不否认法家有其弊端,如章太炎批评商鞅“诋《诗》、《书》,毁孝弟”;何、胡二人说韩非、李斯“持论太苛”。但对法家的弊害,他们只是略有提及、点到为止。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肯定法家的贡献以及其适于时用的意义。当然,他们的评述又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和标准:章太炎专重商鞅,且辩诬甚力;何、胡二人则重在阐明管子的法家言与赞叹管子的治功,并附及商、韩。但是,撇开这些差异不论,他们对法家之善的论证,以及对“谗诽”法家之言的驳斥,则大体相同。“法家之善”一说,出自章太炎,其《商鞅》一文指出:“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娸之,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九流之善”,是与张之洞所说的“九流之病”针锋相对的。“九流之善”自然包括法家之善。而对法家的攻击,则导致其善的丧亡与丢失。因此,《商鞅》一文的主旨,就在于确证和弘扬法家之善,从而让世人对其重新予以认知与认同。对这一“九流之善”的说法,何、胡二人亦引为同调。归纳而论,他们辨白法家的学说与法家的治行,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法家之善,首先在于其“以法治国”或者建立“法治”秩序的方案。《商鞅》说:“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⑥章太炎在《儒法第四》中指出:“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正葛第三十六》中也说:“大氐法家之旨,宪令为重,而都邑为轻,古今一也。”(《訄书》(初刻本),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82 页。)这是商鞅“法治”的根脉。鉴于世人常常将法家之“法”理解为“刑”,章太炎特别作出界定,所谓“法”、所谓“宪度”,并非专指刑律。“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 下,是之谓法。”既然“法”并非“刑”,那么“法家”亦非“刑家”。“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对于这些“法”和“宪度”,天下吏民是必须遵循的,否则就会施以刑律杀伐。因此,在商鞅看来,“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刑”不过是“法”得以施行的手段而已。以此观之,“则鞅知有大法”。而萧何所作的《九章律》,“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所以,继承萧何的张汤、赵禹之徒,佞媚人主以震百官、管束下民,从而废除天下法度,与商鞅并没有什么干系。
从退而求其次的现实选择来看,法家的“以法治国”亦不可废。章太炎认为,如果能有上圣明王之治,如夏、商、周的三代圣治,当然再好不过了。但是,假若“降而无王,则天下荡荡无文章纲纪,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餔。当是时,民不患其作乱,而患其骀荡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虽小器也,能综核名实,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犹愈于荡乎?”在没有圣治而法纪荡尽之时,法家之治亦不失为建立秩序的次好药方。至于有人宁愿国政不理,民生不长育,也“不欲使法家者整齐而撙绌之”,这就有如若不能用美酒佳肴救治饥民,与其吃粗菜淡饭,不如饿死了事。但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章太炎的思路,颇为似类于柏拉图:从最佳的“哲君”之治到次好的“法律之治”。既然最理想的治道、治法无法实现,就只能退后一步寻求次优的治道、治法。
何、胡二人在《宗经篇辩》中则引证管子之言:“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管子·法法》)认为这是合于世变时用的法治主张。他们同时指责张之洞的《宗经》,仅仅拈出《管子》“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一句以抨击《管子》,“不按其上文而专取其后二语以为断”,不仅有“割裂之弊”(“即句解亦不能通”),而且亦持过当之论。按《管子·法法》篇,其全句为:“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惠者多赦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仇也,法者民之父母也。”何、胡二人认为,“惠者生其祸,故为仇仇,法者生其福,故为父母,此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意,其理甚明”。从治国的长远谋划上看,“法治”显然优于“惠治”。可见,张之洞对《管子》的评论,的确不合《管子》的法治思想。此外,他们在《守约篇辩》中还指出《商君书》可以为治:“《商君书》为贤人君子所羞称,孔明独好之,而蜀称治。是以人读书非以书读人也。”其《循序篇辩》亦认为,因韩非、李斯的残暴而否定“以法治国”,实属迂腐可笑:“中国之弊惟用非所学,韩非李斯之过乃持论太苛,皆不在簿书文法以吏为师也。不然质剂之法,圜土之刑,姬旦何尝不以之致成康之治哉?今言惟俗吏始用簿书文法以吏为师,则是因噎废食,截趾适屦之类耳,迂腐可笑!”①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369页。这是针对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中批评韩非、李斯的言论(见上文)而为“以法治国”所作的辩说。
(二)法家之善,其次在于其匡救时弊、达成富强的治功。这主要是针对管子和商鞅而言的。对于管子,《宗经篇辩》征引孔子对管子“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高度评价,以表明称颂管子的心迹。《宗经篇辩》称道:“管子天下才也,而其道尤善在通商以富国,富国以强兵。”而齐国“崛然而起,岂学无本源而能至是”?人们只要读《管子》的《牧民》、《乘马》诸篇,就可以知道,西方大国之所以富强,实不外乎如此。所以,《管子》与西学、西政,多有暗合之处。同时,他们期待管子再世,从而拯救晚清艰危的时局国运:“中国近二十年间,居上位握权要者,倘有管仲其人,方将物阜民康积余藏羡待之于国,外邦不服,吾可以战,外邦宾服,吾可以布义行仁,岂有屡戒不悛,屡辱不悔,乞怜俯首,仰息于人者哉!”晚清之世,“以时势处此,非仲之事不为功也。”因此,应像诸葛亮一样,学习法家为治之法。在何、胡二人看来,正是管子无法重生,而晚清又未得一管子式的伟大人物,中国才积贫积弱、屡受外侮,而不能屹立自强。
商鞅变法致秦日富,受到章太炎的高度推许。《商鞅》引用太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相比之下,汉代“张汤行法而汉日贫”,“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与商鞅之治完全相反。商鞅行法以致储藏有余、赋税不乏、富民强国,比“厉民以鞭箠”而又聚敛以务充君主国库的行径,显然要高远得多。
在中国历史上,每每于社会遭遇重大变故乱局之际,总是有一些趋于现实与功利的人士,思时局、念法家。而富强正是贫弱的晚清所汲汲以求的,因而管子、商鞅的富强之术,岂有不弘扬而光大之理?章太炎与何启、胡礼垣亦作此想望,自然也是时势使然。据此以观,张之洞苛责《管子》和商鞅,实在是罔顾时局的立场。
(三)法家之善,其三在于其为官的心术。在《商鞅》一文中,章太炎认定商鞅为官的心术与张汤等人“殊绝矣”。虽然商鞅进身之途(借宠臣景蓝以进见秦孝公)与背信于魏公子卬,往往为人所诟病,但其为官行法处事,则高优可见,不容轻蔑和恶评。《商鞅》指出:“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窥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乌乎!其魁垒而骨鲠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借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在这里,章太炎一则推重商鞅变法,任法而治秦,凡事一断于法而不屈节于法,即使犯法的太子作为君嗣不可施刑,也要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二则颂扬商鞅刚直不阿与正直磊落的品节。而张汤等人则媚主曲法、毁坏法度,并以佞臣为能事。据《汉书·张汤传》: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①班固:《张汤传第二十九》,载《汉书》(卷五十九),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02页。另据《汉书·杜周传》:“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颜师古曰:杜周“善候司”,即善于“观望天子意”。(班固:《杜周传第三十》,载《汉书》(卷六十,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17页。)所以,张汤绝不可与商鞅相提并论。令章太炎十分愤慨的是,二千年来,商鞅总是被恶名缠身,受尽鞭挞:“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其结果是“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在中国历史上,商鞅之辈不再,张汤之徒横行,不能不让章太炎感慨万端。
(四)驳议种种“淫说”对法家的“谗诽”。《商鞅》文一开篇就为商鞅大鸣不平,意欲为商鞅洗尽二千年来的冤屈:“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乎!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统观《商鞅》全文,章太炎所欲攻破的“淫说”,主要是以下三点:
第一,将法家与刀笔吏等同视之,以为法家就是专为人主施行刑法的刀笔吏。但章太炎认为,法家与刀笔吏,不能等同量齐观,他们是有云泥之别、天壤之差的。法家之善,亦可从其与刀笔吏的比较中进一步加以确证。《商鞅》指出:“法家与刀笔吏,其优绌诚不可较哉。”又说:法家与刀笔吏,“则犹大岩之与壑也”。据章太炎的分析,其优绌悬殊,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鞅知有大法,而汤徒知有狴狱之制耳。”也就是说,商鞅是“以法治国”的政治家;而张汤仅为倚重刑狱、囹圄的刑官,“其鹊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薄书筐箧,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另一方面,商鞅变法强秦,不计一身荣辱,凡事秉法而断;而张汤则献媚于人主,并为人主专制作伥。“若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诅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所谓“见知”之法,是指吏知他人犯罪而不举报者,以故纵论处。②《史记·平准书》:“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索隐》按:“废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败诽谤之者,皆被穷治,故云废格沮诽之狱用矣。”(司马迁:《平准书第八》,载《史记》(卷三十,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07页。)“腹诽”之法,则是口不言而腹中讥笑者为犯罪。③《史记·平准书》:“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壁,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司马迁:《平准书第八》,载《史记》(卷三十,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14页。)而张汤坏法曲刑的行径,是商鞅所不为的。
第二,认为法家“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在章太炎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乌乎!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从汉代的史实看,恰恰是张汤等刀笔吏“恣君抑臣,流貤而及于民”。他认为,“夫使民有权者,必有辩慧之士,可与议令者也”。在民众愚笨无知的时代,民众“起而议政令,则不足以广益,而只以殽乱是非,非禁之将何道哉?”但即使到“后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凡此种种,都起始于公孙弘、张汤的屈膝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也就是说,“抑民恣君”的帽子,应该戴在公孙弘、张汤而非商鞅的头上。
第三,认为商鞅“横暴残刻”。这是中国历史上评说商鞅的一贯说词,也是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对商鞅乃至几乎所有法家的一个大批评。对此,章太炎也有一辩。《商鞅》一文说:“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这出自《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根据这一记载,商鞅当然是酷烈的,而且“其酷烈或过于汤”。但是章太炎为商鞅提供了两点辩解:其一,在商鞅那里,虽然酷烈,但“苛细则未有也”。酷烈与苛细各有不同。“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为什么呢?如张汤之徒,施行单单凭蓄意以定罪(或赦事诛意)的诛意之律,以及腹诽为罪的反唇之刑。“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与张汤不同,“若鞅则无事此矣”。又如唐代著名酷吏周兴、来俊臣的酷烈,无疑比商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残害惨毒乱施肆行,毫无法度,“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但是,商鞅“于此又不屑焉”。其二,必须考虑商鞅“以刑止刑”或“以刑去刑”的初衷,并考察其后的实际成效。一方面,商鞅通过“日刑七百人”,希望能够“以刑止刑”。譬如一群牛羊之中,有牛羊患上了皮肤病,牧养牛羊的牧人担心其传染给其它的牛羊,所以将其去之而毫不吝惜。只有这样,一群牛羊才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商鞅始之以酷烈之刑,终之以“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富民强国、秩序井然,也是一大治功。然而,世人“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所以,以为商鞅为人“终日持鼎镬以宰割其民者,岂不缪哉”!由此一辩,至少可以克减商鞅的酷烈之罪,而部分抵消康有为、张之洞的攻讦。
三、法家的初步解放
晚清关于法家之学的争议,早已存在于1840年至洋务运动的历史过程之中,有斥责者,亦有褒奖者。但上述1898年前后爆发的事关法家命运的论战,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意义。从参与其中的力量来看,这场论战的双方,无一不是那个时代思想学术界和士大夫中的重镇。在他们之间,亦有指名道姓、针锋相对的对评。这是过往的争议所无法具有的思想场景。就内容而言,其所涉论域之广、问题之深,也是从前的争议所远不可及的。可以说,它标志着法家在近代中国获得了初步的解放。那么,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一解放呢?本文认为,所谓“解放”,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法家之学从圣道一统、儒术独尊中解放出来。在传统中国,法家之学长期受到贬抑和压制。而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开始重建法家等诸子百家与孔门儒学的平等地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年)一文认为:“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又“当知诸子弟子,各传其教,与孔教同”。①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章太炎用“九流之善”来应对张之洞的“九流之病”,以树立“九流”的良好形象。何启、胡礼垣的《宗经篇辩》则反驳“宗经”一说:“宗经二字亦非孔孟之言也。孔孟未尝宗经也。”所以,何、胡二人明确指出:“儒者不过九流之一。夫各流皆有其所谓精,亦有其所谓病,未可以一流而概众流也。以一流而概众流,势必是非蜂起,是率天下以相争也。……今以孔孟之道概众流,搔痒不着,虽赞何益?”如此,又何以要“屏斥百家”?
章太炎与何启、胡礼垣的上述论断,显然回击了张之洞“以一流而概众流”的做法。按张之洞所言,九流亦有其精华,但它源自圣学,是圣学本有的,或者可收归圣学,即“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但在张之洞的心目中,“九流之精”最多只是圣学的偏房妾室,而非与圣学平等并列的道术。反之,“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所谓“九流之病”,都被关在了圣学大门之外。这种将九流之学剖分为二且归属不同的技巧,既在于维护圣学道统,也在于吸纳“九流之精”,同时又在于摒绝诸子邪说。在这个意义上,张之洞的“以一流而概众流”,显然包括了“以一流而摒(绝)众流”的涵义。而在章太炎尤其是何启、胡礼垣看来,九流各各平等并列,它们都有其精华,亦都有其病症。不论精华还是病症,都各属其流,而非前者归圣学,后者归各流。因此,法家之善,恰恰是法家自身之所有,而非圣学之所有。就此而论,诸子学的研究,并非佐治儒学经义的旁证,而是各诸子之学史自身的发展。准此来说,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也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二,将法家之学从“谗诽”中解放出来。上文已述,章太炎的《商鞅》一文,极尽辨白之能,为商鞅洗冤、昭雪。二千年来中于“谗诽”,使商鞅屡受恶名,因而见贬于后世。不除“恶名”,不克“谗诽”,商鞅何以恢复名誉、重树英名?因此,洗冤、昭雪是解放商鞅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而章太炎之所以如此着力为商鞅著文翻案、鸣冤,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一位具有光辉形象的商鞅、甚至是一位卓越政治家的商鞅。
第三,将法家之学从“不知世变而强效之”中解放出来。《商鞅》一文“借弟令效鞅,鞅固救时之相而已。①《汉书·刑法志》云:“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颜师古注:“言虽非长久之法,且救当时之弊。”(班固:《刑法志第三》,载《汉书》(卷二十三,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27-928页)。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指出:“是故论政治者,无论法家、术家,要是苟安一时之计,断无一成不变之法。”(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其法取足以济一时,其书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箸书,欲行其所说于后世者也。”这就是说,商鞅所行之法,并非一成不变之法,可以永远为后世所效仿。因此,运用商鞅之法,必须适于世变时用。法家的重要精神,恰恰就是救时济世。因此,脱离和悖逆时世而强守法家之学、法家之法,就不是真正的法家。凡弘扬法家之学,应用法家之法,这是应切实加以把握的紧要之处。但是,“后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强以其物色效之”,即从外表形式上强行效法,结果不是极其愚蠢,就是极其佞媚。章太炎认为,这是后世人们咎由自取,而怨不得商鞅。他联系到晚清的局势,主张晚清既要大行法家之道,又要考虑时局之变、时弊之易,以对症下药。故而《商鞅》一文的“附识”说:“叔季陵迟,非整齐严肃无以起废。今西人之异于商君者,惟轻刑一事,其整齐严肃则一也。”在晚清之世,以法律来建立整齐严肃的秩序,商鞅可资凭借。但是,商鞅的酷烈,则已不合时宜。这是后世对待商鞅以及所有法家的恰当态度。如果说摒弃主义是对法家的扼杀,那么教条主义则是对法家的奴役。只有将法家思想应时世而采纳,才可以说法家获得了真实的解放。
法家在晚清的这次解放,还只能说是初步的,它代表了晚清以来波澜壮阔的法家复兴史颇具引领作用的开启。正是得益于这一开启,在晚清的最后十余年,对法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阐发,进一步演变成为枝繁叶茂的晚清“法家学”。像刘师培的《政法学史序》与《法律学史序》,麦孟华的《商君评传》,汤学智的《管子传》,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沈家本的《新译法规大全序》,以及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和《管子传》等等,都不断点亮法家之思与法家之学的亮光,使法家的学说与精神呈现出不可阻挡的重光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