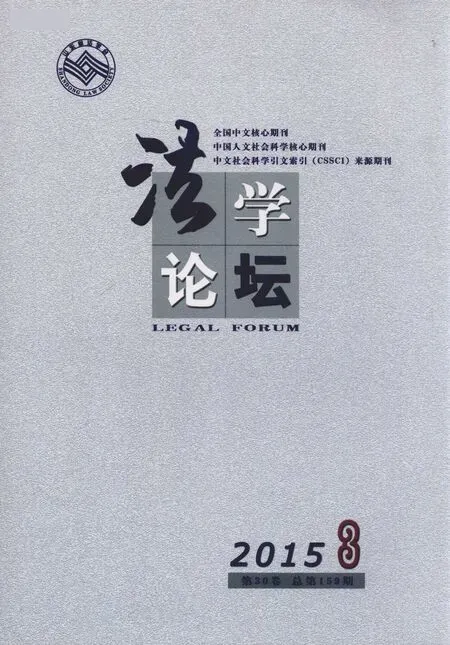减轻处罚的功能定位与立法模式探析
刘 军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我国《刑法》中的减轻处罚①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加重处罚量刑情节,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减轻处罚相关问题,但其实二者内在的法理是一致的,而且如果将来考虑加重处罚的立法模式,则可以有效改变我国法定刑偏重的印象。量刑情节存在功能不清、定位不准、角色尴尬等先天缺陷,是直接导致我国量刑过程思维混乱、层次缺乏、难以规范的幕后真凶。如果要进行卓有成效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必须正确界定减轻处罚量刑情节的功能,厘清与其他量刑情节尤其是从轻、从重量刑情节的关系,对减轻处罚量刑原则的规定进行修正,彻底变革当前量刑情节的立法模式,从源头处思所以、在顶层上做设计,如此才能有效化解司法实践的操作难题。
一、减轻处罚量刑情节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法》除了第63条(减轻处罚原则)之外共有20个条文规定了减轻处罚,其中,总则条文15个,分则条文5个。《刑法》总则条文中,除了第10条“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可以认为是刑罚的适用条件之外,其余的均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其中:(1)减轻与免除处罚连用的情形有4个条文,包括防卫过当(第20条)、避险过当(第21条)、胁从犯(第28条)、重大立功(第68条)②《刑法修正案》(八)第9条新近作了修正,“删去《刑法》第68条第二款”,即“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被删除。的相关规定,前三个条文为“应当型”的二功能量刑情节,最后一个为“可以型”的二功能量刑情节;(2)减轻与从轻处罚连用的情形有7个条文,包括未成年人(第17条)、已满75周岁老年人(第17条之一)、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第18条)、犯罪未遂(第23条)、教唆犯(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第29条)、自首(第67条)、立功(第68条)。除了未成年人和已满75周岁的人过失犯罪的情形为“应当型”的量刑情节之外,其余的均为“可以型”的量刑情节;(3)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连用的三功能量刑情节共有3个,包括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第19条)、犯罪预备(第22条)、从犯(第27条)。前两者为“可以型”的量刑情节,从犯为“应当型”的量刑情节;(4)单独规定减轻处罚的条文仅有2个,即第24条犯罪中止“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和第67条第3款关于坦白的规定,即“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相比较《刑法》总则关于减轻处罚规定的复杂情形,分则的规定模式相对较为简单,除了第276条之一“恶意拖欠劳动报酬罪”之外,其余四个条文均为贪污贿赂型犯罪,包括第164条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第383条关于贪污贿赂罪的处罚规定、第390条关于行贿罪的处罚规定、第392条的“介绍贿赂罪”,而且均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从以上的列举中可以看出,我国减轻处罚立法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与我国《刑法》中的从宽量刑情节类似,减轻处罚大多数为多功能量刑情节,①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加重量刑情节,从重量刑情节均为单功能量刑情节,从宽量刑情节大多数为多功能情节。单功能的从轻量刑情节只有《刑法》第67条第3款关于坦白的相关规定,即“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单功能的免除处罚情节有3个,包括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第24条第2款),自首“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67条第1款),“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第351条第3款);再加上减轻处罚量刑情节2个,单功能的从宽量刑情节共计5个。易言之,我国的从宽量刑情节大多数为多功能情节,属于功能选择性情节,仅仅认定与量刑情节有关的事实还远远不足,还不能就此确定对量刑轻重的作用大小,还需要法官依据《刑法》的规定在数个功能情节中进行选择才能最终确定究竟是减轻或是免除,或者仅仅是从轻处罚;(2)量刑情节又分为“应当型”(命令型)与“可以型”(授权型),因为从重量刑情节都是单功能情节,所以问题不大,但是,从宽量刑情节大多数为多功能量刑情节,再加上“应当”与“可以”的模糊指示,更让人难以确切地把握,而且法官是如何思维的并无法从外部进行观察,也谈不上监督;(3)竞合的处理方法不明,不但是同类的量刑情节竞合的处理方法不明(如多个从轻量刑情节或者多个减轻量刑情节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不同种类的量刑情节的竞合更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如减轻处罚与从轻、从重处罚的竞合,在适用了减轻处罚之后,是否还允许考虑其他的从轻、从重情节)。易言之,除了首先需要在多功能情节中进行甄别以决定是否适用减轻处罚之外,还需要厘清与其他从轻、从重量刑情节的关系,如果仍然需要考虑其他的从轻量刑情节,则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量刑不均衡的程度;对于从重量刑情节更是尴尬,“从重”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已经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了;如果不允许考虑其他的从轻、从重量刑情节,则会导致量刑情节闲置,量刑结果难以反映案件的全貌,更容易引起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对于量刑公正与否的疑忌;如此,惟一可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事实甄别并依法确定了所有的量刑情节(包括减轻、从轻、从重量刑情节)之后,再全面地进行权衡,最后决定是否适用减轻处罚。但是如此以来,减轻处罚因受制于其他的量刑情节也就失去了其功能与作用,并与立法原意严重不符。
与其他国家的刑法相比较,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颇具“特色”。除了个别国家刑法典规定了减轻与免除处罚选择适用的条款之外,例如《德国刑法典》关于对象不能、手段不能的未遂犯(第23条第3款),日本《刑法》关于防卫过当(第36条第2款)、避险过当(第37条第1款)、未遂犯(第43条)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情节之外,基本上都是只规定为“减轻”或者“加重”情节,而且是单功能情节,不会出现“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连用的三功能量刑情节,如俄罗斯《刑法》第61条“减轻刑罚的情节”、第63条“加重刑罚的情节”等都是单功能情节;②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刑法》中规定的减轻或加重处罚,其实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从轻和从重处罚。参见赵微:《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1页。另外,刑法典对减轻、加重的方法、顺序、比例或者幅度均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49条之“特别之法定减刑理由”,第50条“减刑理由的竞合”等规定。而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却出现了许多的特别之处,包括多功能情节的设置、应当与可以的区别、从轻与减轻的区分、法定减轻与酌定减轻的不同规定等等,弹性如此之大、选择性如此之多、关系错综复杂令人咋舌,已经远远超出了立法与司法的传统关系。立法的过度授权无疑会不当扩大法官的选择可能性,使得本来可以轻易确定的量刑情节,变得指向模糊、层次不清、难以操作,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量刑结果差异较大、量刑不均衡的现象。我国《刑法》之所以采取如此这般的立法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刑法》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不堪胜用”,担心出现立法事先考虑不周的事情难以应对,担心罪刑的匹配难以满足刑事政策的需要,从而延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窄”的立法思想,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主张,取消“可以型”的量刑情节,①参见陈航:《试论“可以”情节的取消——以未遂犯的处罚原则为例》,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4期。取消多功能量刑情节。②参见陈航:《取消多幅度情节立法的思考——兼论“从重”、“从轻”、“加重”及“免除处罚”规定的重构》,载《兰州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国《刑法》关于减轻处罚原则的规定以及理论上对减轻处罚的不同理解,加之量刑思维上没有明确区分处断刑与宣告刑的界限,没有法定刑的修正与狭义的量刑情节的观念,也是导致我国当前立法模式形成的个中缘由。因此,我国减轻处罚的立法模式究竟如何,还需要在探讨减轻处罚适用原则之后才能有所结论。
二、减轻处罚适用原则的司法困境
我国《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大多数为多功能量刑情节,而《刑法》第63条第1款又特别规定“减轻处罚原则”为“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通说认为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者相应的量刑幅度,即“量刑幅度说”。此种学说与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别无二致,即“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应是指低于法定刑幅度中的最低刑处罚”,从而否定了“刑种说”,因为“在同一法定刑幅度中适用较轻的刑种或者较低的刑期,是‘从轻处罚’,不是‘减轻处罚’。”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和掌握“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1990年4月27日)。“量刑幅度说”相比较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请示中所倾向采取的“刑种说”减轻的幅度更大,更加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为犯罪人架起一座复归的“金桥”,也更加符合从轻与减轻处罚的“逻辑关系”,但是却导致《刑法》第63条的适用过于僵硬,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量刑不均衡的现象。例如,共同犯罪中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共同犯罪人刑罚减轻幅度过大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④参见陈忠:《对减轻处罚的理解和法律适用》,载《江苏法制报》2005年4月19日。同时,坚持该学说还存在其他的许多司法适用难题。例如,当管制为法定最低刑时如何适用的问题,⑤参见张波:《减轻处罚之“法定刑”含义新探》,载《法治论丛》2003年第6期;亦可参见肖松平:《减轻处罚适用中的一个难题及其解决——兼谈〈刑法〉第37条的理解和运用》,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兼具两个以上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时如何适用的问题,⑥参见周连勇:《自首又立功能否两次减轻处罚》,载《江苏法制报》2006年7月12日。等等;另外,“量刑幅度说”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刑事责任的考证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仅仅因为一个量刑情节便大幅度地跨越刑期甚至数个刑种予以减轻,不仅淘汰掉了诸多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如影响违法性大小和有责性大小的细节性因素,即使仅仅从形式上来看,也有过于简化之嫌。如此,司法实践的难题便是:一方面,由于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常会导致量刑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为防止不均衡现象的出现,法官又惮于适用减轻处罚,想尽千方百计予以回避,这些都是量刑情节适用的不规范现象。
为了解决减轻处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各种难题,我国刑法理论作了多头探索,试图通过刑法解释而不是立法修正的方式对《刑法》第63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僵化表现进行化解。有学者提出“刑格说”,即应当减到下一量刑格,“减轻处罚的范围是相应法定刑与其下一格之间的幅度”;⑦王恩海:《“减轻处罚”含义新探——对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的质疑》,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有学者则建议将法定刑理解为法定最高刑,认为减轻处罚是一个法律上的方法问题,减轻处罚应当包括刑种的减轻和刑期的减轻;⑧参见张波:《减轻处罚的含义新探》,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有学者则提出“二次量刑说”,认为第一次量刑仅是概括性的刑罚裁量,即对刑种或法定刑期幅度的选择,裁量的结果即是《刑法》第63条第1款所指的“法定刑”;⑨参见李翔:《论我国刑法中的减轻处罚——兼评修正后〈刑法〉第63条第1款》,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9期。有学者则提出将《刑法》第63条第1款立法修改为一个授权性条款,“刑罚裁量中,司法人员被立法赋予一定的在法定刑以下处刑的权力,但必须受到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限制。如果是酌定减轻情节,则必须受到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程序性的限制。”①黄京平、蒋熙辉:《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归责探究》,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6月7日。以上学术观点②早期的学术观点还包括“罪名说”,即法定刑是某个罪名的整个量刑幅度,不论某罪有几个量刑幅度,减轻处罚都是指在整个法定刑的最低限度以下判处刑罚。参见常铁威:《“减轻处罚”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此种观点更容易引起量刑的不均衡,并无多少支持者。在立法修正之时均未得到采纳,2011年5月25日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仍然坚持了“量刑幅度说”,将《刑法》第63条第1款修正为,“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③从修改内容上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实质上是对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司法解释的立法确认。在此基础上,将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刑罚裁量不均衡难题的第68条第2款(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情节)删除了之,从而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的情节不再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转化为自首和重大立功两个量刑情节,均为“可以型”量刑情节。这一修正,从技术手段上来讲没有问题,虽然说所谓的“可以”其实也是“一般应当”的表达,但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还是认为所谓的“可以”其实是“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的字面含义,④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那么,“应当型”的三功能情节和“可以型”的三功能情节,前者如《刑法》第27条从犯,后者如第19条又聋又哑或者盲人犯罪,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能说是,如果是“应当型”的三功能情节,在量刑时至少要“从轻”,而且只要是“从轻”就算是符合了《刑法》的规定,当然也有可能免除处罚;而“可以型”的三功能情节,虽然按照《刑法》的规定此种情形甚至可以免除处罚,但是却也完全有可能根本不予考虑,即完全不予从轻也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因为无论考虑与否都是“可以”的。但是,删除第68条第2款规定的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情节,将不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揭发检举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帮助破获重大案件等;更为重要的是,真若如此解决减轻处罚所遇到的司法实践难题,则实在是“病在这上,只治这上便了”。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多种方案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减轻处罚适用原则的司法困境。以最新的规范性文件为例,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这两个规范性文件对于全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⑤参见刘军:《量刑如何实现均衡——以量刑规范性文件为分析样本》,载《法学》2011年第8期。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但是基本内容与《意见(试行)》变化不大,相关问题依然存在;对于量刑情节的部分,由于《意见》对量刑情节的功能没有严格区分(如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没有区分多功能量刑情节的优先或排序,没有明确区分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没有区分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而是予以同等对待,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后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结果必然会导致法官机械地进行数字换算,量刑行为程式化痕迹浓重。⑥参见刘军:《从法定刑到宣告刑之桥梁的构建——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蓝本对量刑基准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3期。当然,《意见》区分总则性的量刑情节与其他情节并分别进行调节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意见(试行)》颁布后,各地省高院均出台了《实施细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11月19日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于2010年12月1日施行;2014年9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在量刑情节中区分了罪中量刑情节和罪前、罪后量刑情节,在量刑方法中分别适用连乘公式和同向相加、逆向相减公式。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在附则中规定,“多个罪中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连乘公式’:A×(1±α1)×(1±α2)×(1±α3)…【注:A代表基准刑,α代表量刑情节调节比例,±根据量刑情节是从严情节还是从宽情节确定】”;“多个罪前、罪后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同向相加、逆向相减公式’:A×(1±α1±α2±α3)…【注:A代表基准刑或罪中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后的刑期,α代表量刑情节调节比例,±根据量刑情节是从严情节还是从宽情节确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后来颁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在“量刑的基本方法”第2条“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第(2)项中仍然保留了“连乘”和“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不同计算方法,但是在附则中却没有继续保留计算公式,原因不明。可以如此理解,即罪中量刑情节不仅反映刑事责任的大小(包括违法性大小和有责性大小),同时也能反映其改造可能性和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大小,而罪前、罪后量刑情节反映的主要是后者,因此应当区别对待。易言之,在量刑过程中应当明确区分关于该当或者危险的量刑情节,并明确二者对量刑的不同影响。①参见刘军:《该当与危险:新型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这两个公式相比较而言,在调节比例相同的情况下,适用连乘公式调节的幅度更大一些。此可谓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大创新。
量刑指导意见以及实施细则不但规定了量刑原则、量刑步骤和方法,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比例,而且给出了15个常见罪名的量刑起点、增加的刑罚量等非常细致的规定,仿佛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但其实这仍然是一笔不小的“糊涂账”。且不论基准刑的计算(即在量刑起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究竟从何而来,亦不论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比例为何如此这般,单单就《意见》未能区分量刑情节的功能而言,就已经是南辕而北辙了。以“从犯”量刑情节为例,在刑法典中,从犯属于应当型的三功能量刑情节,但是,《意见》在“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中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减少基准刑的20% -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可作如此解读,即无需事先确定从犯这一量刑情节在该案件中究竟是从轻还是减轻处罚,而是直接以估算的比例(减少基准刑的20%—100%)调节基准刑即可。如果调节的结果是在法定刑以下,那么便是“减轻”处罚,反之,则就是“从轻”处罚,如果达到了减少基准刑的100%就只能是“免除”处罚了。很明显,如此的“可操作性”其实是倒置了因果,而且直接违背了《刑法》的规定。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63条第1款规定,“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才“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所以,首先应当是判断该量刑情节是否是“减轻”处罚情节,而不是先“估算”调节基准刑的比例。
不过,《意见》所设计的量刑方法和步骤也有自身的优势,即如果存在多个量刑情节,尤其是兼有减轻和从轻、从重量刑情节的时候,可以全面地平衡多个量刑情节对于量刑结果的作用,而不会因为首先适用减轻量刑情节,或者个别从轻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过大,而导致其他的从轻、从重量刑情节被忽略。仅就此而言,《意见》的探索也非常值得称道。那么,域外国家或者地区是如何处理这一量刑难题的呢?
三、减轻处罚量刑过程的域外比较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刑法一般只规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轻处罚则授权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而且减轻处罚只是对法定刑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而不是直接适用另外一个业已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与我国规定的“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有较大差异。以《德国刑法典》为例,对于法定减轻情节,第49条第1款规定了具体的减轻方法和幅度,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终身自由刑由3年以上自由刑代替,这样同时限定了上限和下限,因为第38条第2款规定有期自由刑最高为15年;二是,有期自由刑上限采“比例制”,可判处的刑期可达最高刑的3/4刑期,下限采“直减制”,直接规定可以减轻的下限,最低自由刑为10年或5年的,减为2年;最低自由刑为3年或2年的,减为6个月;最低自由刑为1年的,减为3个月。其他情况依法定最低刑为准;三是,罚金刑上限亦采“比例制”,即日额金3/4为最高额,下限不低于刑法关于日额金的规定,即最低5单位日额金。②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如此细致的规定,使得“相关构成要件的刑罚范围以完全确定的方式被降低,而且——只要有上下限——既可以降低量刑范围上限,也可以降低量刑范围的下限。”③[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2-1073页。
下面以德国波恩州法院就一起故意杀人案所制作的判决书为例,④参见《德国波恩州法院关于一起故意杀人未遂案的判决书》,冯军译,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453页。简要说明德国司法实践中,实际案件的量刑过程和思维进路:首先,在该案判决书的E部分,认定被告人哈逖姆·马斯洛依(Hatim Maslouhi)的危害行为是刑法典第212条意义上的未遂的故意杀人,而不是第211条的谋杀;其次,在F部分,排除了被告人具备第213条故意杀人的减轻情节,从而按照第212条确定适用5年至15年自由刑的法定刑幅度;再次,考虑到止于故意杀人的未遂,适用第23条第2款、第49条第1款的减轻处罚,在量定具体的个别刑罚时,法庭应从2年至11年3个月的刑罚幅度出发(下限直接减为2年,上线为最高刑期的3/4);再其次,考虑到存在第21条的各种前提(限制刑事责任),法庭再一次根据第21条、第49条第1款的减轻处罚的规定降低这一刑罚幅度,因此确定处断刑的范围为6个月至8年5个月(下限直接减为6个月,上限则再次乘以3/4),具体的刑罚量定应当从这一刑罚幅度出发;最后,在考虑了全部有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况之后,法庭认为,为了抵消被告人的责任,判处4年的自由刑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基本上是处断刑的中间部位),并从特殊预防考虑依据第63条的规定将被告人收容于精神病院。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虽然广义的量刑是从定罪以后就开始了,但是却经历了选择刑罚幅度(包括减轻或者加重构成要件的适用与否)、形成处断刑(减轻或者加重情节的适用)、决定宣告刑(具体刑罚的量定,即狭义的量刑)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链接、先后继起,是从法定刑到处断刑再到宣告刑的过程,总则减轻、加重情节的适用是对分则具体个罪刑罚幅度的修正,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所有的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并决定是从轻还是从重,最后量定刑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允许法官自由裁量的仅仅局限在狭义的量刑阶段,而且仍然需要考虑责任的抵偿、特殊预防或者社会复归等刑罚目的,仍然需要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并进行论证,仍然需要注意量刑的均衡(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案件等之间的量刑均衡)问题。在广义的量刑过程中,形成处断刑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通常具有的阶段,其依据是刑法规定了基于法定事由可以对法定刑进行修正。例如,日本《刑法》第68条规定,除了死刑、无期徒刑的减轻之外,其他的减轻处罚均采取“比例制”,所适用的刑罚幅度的上限与下限同时减轻,如第(三)项规定,“有期惩役或者监禁减轻时,将其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减去二分之一”;①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再如,我国台湾地区2002年修订的《刑法》第66条规定,“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减轻者,减轻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同时有免除其刑之规定者,其减轻得减至三分之二。”第67条规定,“有期徒刑加减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减之。”由此,处断刑是经由对法定刑修正所得来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只有在刑法规定了法定刑可以修正的情形下,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处断刑,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像我国关于减轻处罚原则的规定,并未规定可以对法定刑进行修正,因此就不能说我国存在处断刑情形,从量刑的宏观过程来看,这或许是我国《刑法》关于量刑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最大区别。
处断刑是一个衔接立法与司法之间的阶段,是法定刑到宣告刑的过渡,当然,前提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并且出现了法定的情形,③一些国家刑法允许法官裁定对法定刑进行酌定减轻,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条-2规定,“除第62条规定的情节外,法官还可以考虑其他一些情节,只要他认为这样的情节可以成为减轻处罚的合理根据。”参见《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需要对法定刑进行一定的修正,易言之,形成处断刑并非所有案件的必经阶段,而只是依据刑法规定而为之,但却是将法定情节作为修正法定刑的情形,而并非直接影响宣告刑的情形。
四、减轻处罚量刑规则的修浚完善
我国《刑法》关于减轻处罚的量刑过程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相比较,显著的区别在于缺乏处断刑的阶段,④张明楷认为,在我国刑法中除了数罪并罚类似于处断刑的作用之外,“处断刑不是我国刑法中的概念”。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并不能通过修正法定刑形成新的处断范围,这样的结局便是当前关于减轻处罚原则的规定,只能在法定刑以下处刑;而且量刑情节往往同时具有多种功能,法官选择情节功能的内心历程难以量化,加之不同功能之间差异较大,容易造成量刑的不均衡。另外,对于量刑情节的竞合问题在当前减轻处罚立法体制下也难以恰当地处置。因此,借鉴域外关于处断刑的立法经验,探索量刑过程的进一步完善也就势在必行。
从性质上来看,处断刑属于对法定刑的修正,本质上仍然属于法定刑。当存在加重或减轻事由时,通过修正法定刑确定一个处断范围,在此范围内最后决定宣告刑,因此,这里的加重或减轻事由是加重或减轻法定刑的事由,而不是直接加重或减轻宣告刑的事由。①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页。之所以处断刑本质上属于法定刑而非宣告刑,在于其“通用”属性,即只要符合法定适用的要件,则均应当按照《刑法》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在这一问题上法官并无自由裁量之权限。惟有可以由法官依据个案情形“酌科”的刑罚,在性质上才属于宣告刑。易言之,该影响量刑的事由仅属于个案,且并无严格的量化指标限制,并不突破法定刑范围,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刑罚裁量,如此酌科之后的刑罚便是宣告刑。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刑法,在法定刑通往宣告刑的路途之上嵌入了一个处断刑,其功用究竟如何,主要在于维持罪刑之均衡:一是,因为法定刑可以加重或减轻,从而使得各基本法定刑之本刑在立法之初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契合罪刑之均衡,防止因为顾虑无法涵盖现实中的特殊情形而故意加大法定刑的涵盖面,从而导致法定刑跨度太大、伸缩无度的局面出现;二是,通过修正法定刑以确定宣告刑的处断范围,从而另一个方面,在出现特殊事由时可以适当地伸缩罪与刑的匹配,在新的范围内确定宣告刑,整个量刑思维其实就是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过程;三是,对刑罚加重或减轻事由予以规范化,明确适用的条件和场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加重或减轻事由可以区分为总则性加减事由和分则性加减事由,构成要件加减事由、违法性加减事由和有责性加减事由,以及区分为与犯罪轻重有关的加减事由和与刑事政策有关的加减事由等等,②我国台湾地区实务界认为,“刑总之加减,因非法定本刑之变更,应如何加减,法院在规定范围内,自有裁量之权限,并非一律应加重或减轻至所定比例。”此种见解即使在台湾地区也颇尚有争议。参见靳宗立:《台湾刑法有关刑罚加重与减轻之探讨》,载京师刑事法治网,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pkID=31236,最后浏览日期2014 年12 月31 日。这些加减事由的适用条件、作用场域和方向均有所不同,对于加减的缘由、幅度、顺序等均可一目了然,便于监督。综上,处断刑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法定刑,是在司法层面对法定刑的修正,但是却又不同于各基本法定刑之本刑,更有异于司法裁判所作的宣告刑。作为立法与司法、法定刑与宣告刑之间的中间环节,处断刑是一般中的特殊、抽象上的具体,在保持法定刑通常适用的情况下,补足了灵活性与适应性。因此,加入了处断刑环节的量刑,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过程,符合基本的思维规律与习惯,具有独特的优势。
既然如此,我国《刑法》有必要考虑借鉴域外立法模式,考虑增加处断刑的阶段,以完善量刑过程、缜密量刑思维。为此需要修改《刑法》第63条第1款的内容,立法规定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修正法定刑以形成处断刑,法定刑的修正建议采取德日刑法典的模式,即不同刑种直接减降、同刑种比例减降或倍比增加,③德日刑法略有不同:德国刑法是以“规定最低自由刑”的方式降低刑罚的下限,而日本刑法则是同比例减降;另外,德国刑法典关于累犯的规定已于1986年废除,因此已经没有加重刑罚的规定;日本刑法典则保留加重处罚,并实行倍比制,第57条规定的再犯刑罚要求处犯罪所规定的惩役的最高刑期的两倍以下。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除了并合罪以及分则个罪规定的加重构成要件之外,总则性加重处罚规定的立法模式势必趋于式微。而且刑罚的上限和下限最好同时增减以形成处断刑。因为如果不按照如此方式进行增减,所形成的处断刑范围仍在法定刑范围或幅度之内,则实质上仅仅是从轻或从重处罚而已。④如俄罗斯《刑法》第62条规定的减轻情节的刑罚裁量规定,“刑罚的期限和数额不能超过本法典分则相应条款规定的最高刑种、最高刑期或数额的四分之三。”第68条累犯规定,“所判的刑期不得低于相应犯罪的最重刑种、最高刑期的二分之一;对于危险的累犯,不得低于三分之二;而对于特别危险的累犯,不得低于相应犯罪的最高刑种、最高刑期的四分之三。”这些“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实质上仅仅是从轻或者从重处罚而已。参见赵微:《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3页。虽然对法官的裁量范围也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限制,但是并没有达到设立处断刑的目的。当然,处断刑与原法定刑在范围上存在相当大的重合部分,因此虽然经过减轻,但是最终的宣告刑仍然有可能落入原法定刑的范围,即宣告刑仍然是受具体案件刑事责任大小(违法性大小和有责性大小的乘积)的决定,依据可谴责性大小的排序以及在现有(或给定)的刑罚手段中所处的恰当序列来确定刑罚量。⑤参见:Paul H.Robinson.“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Modern Desert:Vengeful,Deontological,and Empirical.”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67(2008),p.151.如果其可谴责性大小的排序较高,仍然有可能在处断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罚,从而落入到减轻处罚以前的原法定刑范围之内。这样也就很好地解决了前文谈到的惮于适用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形,而且使得大多数多功能情节的存在成为不必要。至于是否允许法官在法定增减的比例内根据个案情形另行裁量增减的比例,笔者认为,既然处断刑也仅仅是一个处断的范围而已,在此范围内仍然需要综合考虑刑事责任的大小才能最终决定宣告刑,因此,无需也不宜由法官在此阶段另行裁量增减的比例,应当直接增减至法定比例或刑罚。
最后,处断刑的立法模式,能够妥当地处置量刑情节的竞合问题:一是,多个减轻处罚量刑情节的竞合问题,由于处断刑是法定刑的修正,本质上仍然是法定刑,因此,如果出现量刑情节竞合的情形时,则仍然可以再次进行修正,并再次形成新的处断刑,亦即可以递减或递加。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70条规定,“有两种以上刑之加重或减轻者,递加或递减之。”此种情形也适用于减轻处罚与加重处罚竞合的情形。基于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原则,一般应当先加重再减轻,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71条对之有明确的规定,“刑有加重及减轻者,先加后减。有两种以上之减轻者,先依较少之数减轻之。”再如,日本《刑法》第72条规定,“同时加重和减轻刑罚时,按照下列顺序:再犯加重、法律上的减轻、并合罪的加重、酌量减轻”。①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另外,加重处罚不得跨越刑种,即无期徒刑不得加重为死刑,有期徒刑不得加重为无期徒刑等。从加重处罚的情况来看一般仅限于累犯,而且当前的立法趋势是仅仅将之作为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二是,减轻处罚与从轻、从重处罚的竞合。由于减轻处罚仅仅是修正了法定刑,而从轻、从重处罚情节则是在处断刑的范围内进行考虑并最终形成宣告刑的“纯正”的量刑情节,二者互不冲突,是顺序递接的关系。这一司法难题在处断刑的立法模式下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三是,存在数个主刑时如何减轻处罚。定罪事实指向某一量刑幅度,但是在该幅度内存在多个主刑,如果需要适用减轻处罚,则应当对所有主刑按照减轻处罚的标准一并适用,然后最终确定经过修正所得来的处断范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69条规定,“有两种以上之主刑者,加减时并加减之。”假设立法规定死刑减轻处罚由无期徒刑代替,无期徒刑减轻处罚由25年有期徒刑代替,其余自由刑减轻至原法定刑期的3/4,则上述法定刑幅度经过减轻后形成的处断刑范围为无期徒刑、7年6个月至25年有期徒刑。当然,这个例子仅仅是一种假设的情形,实际立法应当更加细密而周全。
综上,通过改变减轻处罚的适用规则,借鉴处断刑的概念,诸多的立法难题与司法困境均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即便为了维持刑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保持当前各法定量刑情节的立法现状不变,司法实践的操作也变得简便顺畅而且符合思维逻辑,并有助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一步探索。